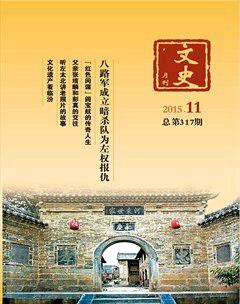一生滇緬情 一片赤子心
牛愛科

抗戰硝煙在中華大地蔓延之時,南洋各國華僑在陳嘉賡先生的領導下紛紛向祖國捐錢捐物。“南僑總會”利用募捐款在海外購買了一批汽車,但由于海路被日軍封鎖,只好先運到緬甸臘戍,再分批轉運回國內。這些汽車都是載重為3噸的道奇牌卡車。在緬甸裝配好后運回昆明。當時司機奇缺,于是我在1933年隨著一批愛國青年僑民回國參加抗戰,1937年進入“南僑機工”運輸處工作。
南僑機工和國內招募到的汽車駕駛員,都必須到昆明潘家灣司機訓練所進行集訓。受訓者大多是廣東人,集訓大隊的大隊長潘忠信來自江蘇,聽不懂廣東話。我因在廣州生活過一段時期,學過一些粵語,于是我成了潘忠信的傳令兵。那時我12歲,因此大家都叫我“小廣東”。司機集訓后,便去了緬甸。我隨潘忠信一同前往,協助他與司機們溝通,以便安排運輸。在緬甸工作將近一年時間里,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交接汽車。由于耐心、細致、準確的翻譯,我很快便得到了潘的信任,不久他便將汽車鑰匙交給我保管。我將鑰匙和汽車一個個對照編號,等汽車裝配好就安排運送回國。
汽車全部運回國后,我回到了昆明。1940年春,西南運輸處組織成立了“華僑運輸先鋒第一大隊”,我被調到先鋒隊當保養工。當時,每臺汽車由三個人保養,我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做了一年后,15歲的我被分配到了訓練所學習駕駛。由于我有修車和保養車的經驗,再加上學習刻苦,6個月后,便與其他成年人一樣拿到了駕駛證。有了駕駛證后,我就經常往返于滇緬公路,運送戰爭物資,支援前線的抗日斗爭。
日寇侵占越南后,由于封鎖了我國通往國外的水路和陸路,1938年國民政府組織20余萬人,在滇緬之間的崇山峻嶺間修建了一條長1300公里的運送軍用物資的緊急通道——“滇緬公路”。當時美國的援華物資就是從舊金山通過海路運到仰光,再從仰光用火車運到臘戍,然后再經滇緬公路運到中國。同樣,海外華僑籌集的抗戰物資也要從緬甸運回國內。就是這條通道,支撐了中國境外抗戰物資向境內的運送和供給,在這條“抗戰輸血管”上有3000多名南僑機工付出了血汗,其中有1000多人付出了生命。
滇緬公路是一條土路,不僅道路狹窄,而且彎急坡陡。不少路段還在懸崖上,雨天經常出現塌方,特殊路段還有懸索吊橋,車走上去搖搖晃晃,十分危險。走這種路需要有高超的技術。南僑機工中有不少人在國外就是駕駛員,但回國后必須重新培訓才能上路駕車。盡管如此仍有不少司機不適應路況,發生事故,也有些機工不適應天氣,再加上衛生條件惡劣,患上瘧疾后得不到及時醫治而失去了生命。那時我也患上瘧疾,身體時冷時熱,幸虧及時找到了“金雞納霜”,才從鬼門關上轉了回來。
在滇緬公路上行駛,沒有天氣因素影響,一個來回大約需要一周時間。但到了下雨天,時間就無法確定了。一下雨,道路泥濘無法行車,只能停下車來等待天氣好轉。因此在車里過夜就成了家常事。我們司機的生活非常艱苦,每人帶一個汽爐子和一些大米、榨菜、食鹽,蔬菜因不方便很少帶。感覺饑餓時,就停下車,在山溝里找些水,點起爐子,做點米飯充饑。我們運回的都是汽油和武器,向外運送的物資都是國產的桐油等。由于懸索吊橋有負荷噸位限制,因此車隊的單車載重就以3噸為標準。運汽油時6個桶為1噸,一般運20桶,汽油分為四個顏色:其中紅色的是軍用品,黃色的是機關單位用品,綠色的是飛機用品,白色的是商用品,還有兩個桶為汽車自備用油。為了強化運輸管理,滇緬公路上分段設有檢查站,車輛路過不同的關卡時,都要對運輸車輛進行核對檢查。
1942年4月,日寇攻占云南后,沿滇緬公路長驅直下。國民黨軍隊為了阻止日軍進攻,炸掉了滇緬公路上的惠通橋,滇緬公路從此中斷。滇緬公路中斷后,我們的運輸任務便轉向了國內,主要跑瀘州、重慶、柳州、貴陽、遵義等地,運輸的物資仍是以槍械、彈藥等軍用品居多。國內的公路也多是盤山路,從貴陽到重慶有400多公里,到昆明有600多公里。安順到昆明有24處彎道,遵義到重慶有72處彎道。山路樹多,經常有野獸出沒,單人出車最怕半路拋錨,一旦壞在路上,沒有配件,沒有工具,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在這樣特殊的條件下我們養成了一個好習慣,駕車十分謹慎,就像當醫生一樣,出發前全面檢查車輛,有問題爭取在出車前解決。由于我修理和使用過三種發動機的汽車,再經過幾年的磨練和摸索,對各種車輛了如指掌,只要聽一下汽車的聲音就大概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合適,哪些零部件需要更換,發動機有什么毛病,燃油的質量存在什么問題等。因此,路上經常有隊員等著我幫他們排除故障。
在國內公路上駕車不但要付出艱辛,還要時刻面臨生死考驗。日寇經常對“抗戰輸血管”進行狂轟濫炸。每次轟炸都會有隊友流血犧牲。有一次在廣西六寨縣,我們車隊正走在半路上,突然日機猖狂地飛來,對車隊進行超低空俯沖轟炸。我急忙將車停在路邊,順勢滑在路旁邊坡。一陣轟炸后,眼前一片昏暗,感覺身上壓了好多重物。炸彈煙消云散后,我爬出邊坡,發現有六七個司機被炸得血肉模糊,其他受重傷的司機由于無法救治,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犧牲了。他們的尸體沒地方掩埋,只得一個個抬進彈坑中掩埋。我們懷著悲憤的心情駕起各自的車繼續執行任務。轟炸中我的汽車轎頂被炸起的石塊壓扁,無法正常駕駛,幸好發動機還能正常啟動,我只能側著身鉆進去,窩著脖子將車開回昆明,完成了運輸任務。
在國內跑了三年多時間,一個突然而至的消息,改變了我的抗戰生涯。1945年8月的一天,我開車去送軍用物資,到了盤縣休息時,聽到陣陣鑼鼓聲和鞭炮聲,我們找人一問,才知道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勾起了大家的思鄉之情。第二天,不少人便離開車隊向各自的家鄉奔去。
這時我們碰巧遇上一支從印度歸來的遠征軍戰車部隊,他們開著美國造GMC牌十輪大卡車,汽車上拉載的是皮鞋、帳蓬、毛毯等物資。這支部隊的士兵聽到了日軍投降的消息,紛紛棄車回鄉,路上停滿了汽車。我打聽到這支部隊要回上海,便產生了跟隨他們的想法。
我向長官亮明了駕駛證,說明來意后,他十分熱情地同意我駕車隨行。于是我開著十輪大卡車奔向南寧方向,結果部隊卻開往了東北。之后我輾轉到了北京,為杜聿明開了一段時間車后,又回到了老家福建,后又去廣州尋親,最后落腳香港,在一家汽車公司當了機工。1955年,我離開香港到了廣州華僑農場機耕隊當了教練,1963年到山西煤礦工作,直到退休。如今我已經到了人生晚年,回顧過往充滿生死考驗的抗戰經歷,自覺無愧于心、無愧于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