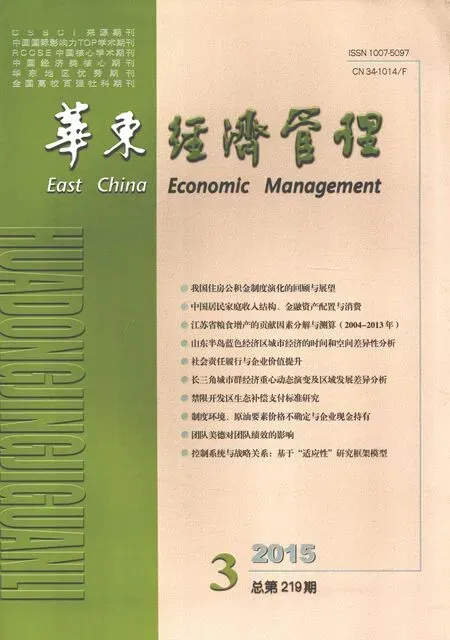禁限開發區生態補償支付標準研究
李 瀟,李國平
(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一、引 言
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和人民對生活環境質量越來越高的要求,2010年國務院頒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在國土空間劃分格局中,專門設定了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密切相關的區域——限制開發區內的重點生態功能區(以下提及的限制開發區均指重點生態功能區)和禁止開發區,它們涉及森林、水源、土壤、生物多樣性等眾多生態要素的保護與建設。其中,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功能定位是: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禁止開發區的功能定位是:自然文化資源、珍稀動植物基因的保護地。為了實現與保障兩個區域的功能定位,《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明確了區域內的管制措施,包括:禁止、限制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控制開發活動強度與規模,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治理沙化、保持水土等。對于區域發展的禁止、限制勢必導致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損失,對于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也勢必導致當地財力的投入,這“一減一增”兩方面的損失會對管制措施的順利實施提出嚴峻挑戰。因此,要保障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的功能定位,就必須對兩個區域進行生態補償,確保區域不因功能區建設遭受損失,同時具有保護、建設功能區與維護其成果的積極性。
實施生態補償,關鍵是確定生態補償的標準,針對禁限開發區內包含眾多生態環境要素的現狀,以禁限開發區整體作為補償對象,根據不同的禁限程度支付生態補償金額,將更具有合理性與操作性。本文試圖在梳理已有生態補償標準測算方法與文獻的基礎上,對生態補償的理論標準進行經濟學分析,提出適用于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為我國禁限開發區生態補償的實施提供政策建議。
二、生態補償標準的文獻綜述
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是衡量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與貢獻者補償額的依據,是生態補償能夠順利、有效實施的保障,是生態補償機制研究的關鍵問題。但是,學界對生態補償標準的成果目前尚未能達到統一,國家也沒有出臺生態補償標準的相關法律與準則。根據已有文獻對于生態補償標準的測算,其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如表1所示。

表1 生態補償標準的主要評估方法
總成本法主要應用在流域的生態補償上,如國內的新安江流域[1]、金華江流域[2]、南水北調工程[3]、漢江流域[4]等,國外的哥斯達黎加的環境服務支付項目[5]、尼加拉瓜草木生態系統的生態補償[6]、紐約流域管理項目等;恢復成本法主要針對生態環境的治理恢復成本,如胡熠等[7](2006)對閩江生態重建、虞錫君[8](2007)對太湖流域水生態修復、陸研等[9](2009)對礦區植被恢復、盧艷等[10](2011)對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研究,但是這些文獻中沒有給出具體的補償標準或沒有說明治理成本與補償標準之間的關系;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法多沿用或擴展Costanza[11](1997)提出的評價模型,如余新曉等[12](2005)對我國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李方等[13](2004)對三江平原的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劉雨林[14](2008)對西藏地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孫慧蘭等(2010)對伊犁河流域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仲俊濤等[15](2013)對寧夏區域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測算等,測算出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都非常巨大,很難作為生態補償的標準;支付意愿法在近些年也大量運用到環境價值和生態補償標準的研究中,如毛占峰等(2008)[17]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安康、鄭海霞等(2010)[18]對金華江流域、李青等(2011)[19]對天目湖流域、徐大偉等[20](2012)對遼河流域的支付意愿或受償意愿的測算等,然而支付意愿法容易產生策略性、假設性等偏誤,造成支付意愿或受償意愿的偏差。
除上述方法外,中國學者們還采用影子價格法、碳稅法、市場價格法、生態足跡法等評估生態補償標準。但在已有的估測生態補償標準的文獻中,僅是單純的補償數額測算,而沒有理論作為鋪墊,其測算結果不免產生爭議和質疑。因此,有必要對區域的生態補償理論標準和生態補償支付標準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研究。
三、禁限開發區的生態補償理論標準與支付標準
生態補償的理論標準是基于外部性理論、通過經濟學分析得出的理論上的補償標準;生態補償的支付標準是根據實際情況動態調整理論標準、最終應該補償給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者的金額標準;理論標準是支付標準的基礎,支付標準是理論標準的實踐,兩者緊密相關。
(一)禁限開發區的生態補償理論標準
在空間上,禁限開發區本質上是根據生態環境重要程度劃定的土地上的禁止、限制開發區域,相匹配的管制規定是對當地開發權的一種侵犯[21];在生態資源上,禁限開發區是在考慮全民環境權的情況下,對當地生態資源事實產權①的侵犯[22];換言之,禁限開發區的設定實際是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行為對當地發展權的損害,是對當地產權讓渡的一種強制規定,因此,必須做出補償,補償的理論標準就是外部效應內部化。
如圖1所示,MSB表示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進行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時的社會邊際收益(全社會獲得的收益),MPB為私人邊際收益,兩者之差正是外部效應;MC為邊際成本(社會邊際成本=私人邊際成本)。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者而言,管制措施的施加要求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量從僅考慮自身利益時的Q1提高到考慮社會效益的Q2(或比其更高的點),此時,均衡點由A向C移動,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自身增加的生態系統服務收益為AQ1Q2B,增加的成本為AQ1Q2C,成本大于收益。要將外部效應內部化,應補償大于面積ABC小于面積ABCD的款項。

圖1 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生態補償理論標準的經濟學分析
補償面積為ABC時,即是對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因供給量變化所遭受的凈成本(損失)的補償,在圖形上,它是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因增加供給而增加的生態環境保護總成本(AQ1Q2C)扣除其獲得的自身收益(AQ1Q2B);補償面積為ABCD時,即是對生態系統服務受益者獲得的凈生態效益的補償(外部效益);最終的補償額取決于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與需求雙方的談判。由于受益區的自然狀況、社會經濟狀況、消費目標等復雜因素的影響,生態系統服務受益區獲得的凈效益難以定量估算。因此,現階段我們將補償面積ABC作為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理論標準,公式表示為:

式中TS為生態補償理論標準,MC(q)、MPB(q)分別為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的邊際成本與私人邊際收益函數,TC、PB分別為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總成本和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的私人收益,其中對于總成本的核算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②,這也是下文中禁、限開發區不同支付標準設定的根源。
(二)禁限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
理論上,生態補償的標準應該是付出的總成本扣除自身因為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獲得效益;而在實踐中,基于我國目前生態補償工作實施的困難處境,應該對這一理論標準做出調整,使其有效地刺激與維持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行為。
誠然,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通過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自身得到了良好環境對健康的效用、美麗的景觀、對潛在高科技低污染企業的吸引等生態內部效益,但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無法意識到這種內部效應的價值,如果將其在支付標準中扣除,可能會造成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得到的補償額小于其心理預期,影響他們對繼續進行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態度。因此,為了鼓勵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的公益行為,現階段不宜在生態補償支付標準中扣除內部效應的價值。
此外,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不僅是短期的貢獻行為,而且是長期的維護行為,其結果需要得到長久的維持;即要使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將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建設作為一種“職業”從事,使得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建設成為一個長效且“有利可圖”的產業。而以總成本為標準的補償顯然僅是生態補償的最低標準,并不能很好的維持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活動,因此,需要在生態補償的支付標準中加入“激勵資金”。所謂“激勵資金”,即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進行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時,除過應當獲得的補償外得到的激勵性金額。綜上所述,現階段應實行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公式如下:

其中,PS為生態補償支付標準,TC為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總成本,F為激勵資金。這一生態補償支付標準在理論標準的基礎上取消了對“私人內部效益”的扣除,增加了對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行為的激勵,不僅能夠促進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積極性,而且解決實踐中補償標準過低導致的生態補償失靈和生態環境的新一輪惡化。
四、基于禁限程度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調整
生態補償支付標準是具有針對性的核算標準,通過具體分析區域現狀來調整、細化上述生態補償的支付標準,避免不分地域差異的“一刀切”標準,能夠有效地彌補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給利益相關者造成的損失。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不同的管制程度決定了其區內居民投入或犧牲的不同,即生態補償標準中總成本的不同。而無論是何種程度的管制均會造成機會成本的損失,直接成本的投入則不盡然,因此,支付標準的針對性主要體現在對直接成本的核算上。
(一)限制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
對于限制開發區域的管制程度主要體現在范圍的管制與發展的管制兩方面。在范圍上,《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只對限制開發區進行了大致確定,并沒有明確其邊界具體是什么、管制主體是誰。以三江源草原草甸濕地生態功能區為例,其范圍為青海省的16縣1鎮,但是這些縣鎮里的哪些草原草甸屬于生態功能區或是這些縣鎮(包括與生態功能無關的區域)都屬于生態功能區并沒有具體的解釋,這些縣鎮都是生態功能區的管制主體或是比它們更高級別的第三方是管制主體也沒有清晰的言明。在發展上,限制開發區的管制原則中提到“引導一部分人口向城市化地區轉移,一部分人口向區域內的縣城和中心鎮轉移,生態移民點應盡量集中布局到縣城和中心鎮,避免新建孤立的村落式移民社區”。
換句話說,范圍上的低程度管制,不能排除限制開發區當地政府、居民為區內生態環境的投入;發展上的低程度管制,也沒有完全脫離當地政府、居民與限制開發區域,其活動仍影響著區域內的生態環境,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仍需他們提供。因此,對限制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應包括區域為了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投入的直接成本、損失的機會成本以及持續從事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激勵資金”,公式如下:

式中PSl為限制開發區生態補償支付標準,DC為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直接成本,OC為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機會成本,F為激勵資金。
(二)禁止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
相較于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的范圍與發展的管制更為嚴格。在范圍上,《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明確規定禁止開發區包括自然保護區、文化自然遺產、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等,這些區域在實際中均有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風景名勝區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工作指南》等相匹配的管理規定,及詳細、明確的邊界與管制主體。在發展上,管制原則中規定“禁止開發區實施強制性保護,嚴格控制人為因素對自然生態和文化自然遺產原真性、完整性的干擾,引導人口逐步有序轉移”。
范圍與發展上明確而嚴格的絕對性規制設定,隱含在禁止開發區內禁止人為活動,隔斷人類活動與區域的聯系,也就是說,禁止開發區內的生態環境有特定的負責主體,可以隔絕當地政府、居民的投入。因此,針對其生態補償支付標準,不涉及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直接成本,只包括禁止進行工業化城鎮化開發所造成的機會成本損失和“激勵資金”,公式如下:

式中PSf為禁止開發區生態補償支付標準,OC為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機會成本,F為激勵資金。
(三)基于禁限開發程度的生態補償支付
綜上所述,有必要對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分別進行公式(3)、(4)的生態補償,但并不是所有的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都應該得到補償。首先,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是限制開發區域內涉及生態補償的區域,其總面積38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陸地國土面積的40.2%。一方面,全國幾乎一半的區域均要實行限制開發,進行生態補償,無疑存在巨大挑戰,劃定如此大范圍的生態補償區域是否科學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在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開發管制原則中,僅要求“限制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并沒有說明對已經實施“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的區域如何處理,而由于即成產業的存在,這些區域并不受到限制措施的影響,已有的工業和城鎮規模對生態環境繼續產生重要影響,不應該對其進行生態補償。其次,我國的禁止開發區域大多都已經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開發,尤其旅游開發,對過度開發的區域(禁止開發區域)實行完全的生態補償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必須對現在的禁限開發區中已經實行大規模工業化、城鎮化的地區進行關注,評價其(如某縣)現有發展模式對所處的特定類型的重要功能區(如水土保持型)的影響,對禁限開發區的范圍劃設進行調整和細化,進而根據禁限開發程度實行不同比例的生態補償支付。例如,按照目前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強度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實行分級,按照級別實行生態補償;對工業化、城鎮化級別低的區域實行完全生態補償,對工業化、城鎮化級別高的、且不能停止已有產業的區域部分補償甚至不補償。同樣,針對不同類型的禁止開發區域,也應在類型內進行開發強度劃分,根據開發強度進行生態補償。
五、以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保護區漢中市為例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測算
漢中市是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保護區的主要城市之一,其為水源區的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貢獻巨大,為了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可持續進行,有必要對漢中市實施生態補償。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對主體功能區的范圍界定,漢中市的1區、10縣③均屬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即限制開發區,我們采用公式(3)的限制開發區生態補償支付標準;本文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主要是針對南水北調工程引起的漢中市生態系統服務供給的變化,因此本文將測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起始年2003-2013的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
通過資料梳理,初步了解到漢中市為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保護所做的工作包括: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小流域治理、固體廢棄物處理、污水處理、廢氣處理等。按相關項目對成本投入進行分年核算,2003-2013年的直接成本如表2所示。
對于機會成本的測算,由于獲取資料的難度較大,我們采用間接算法進行核算。選取陜西省的整體作為參考區,分析南水北調后漢中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與陜西省平均情況的差異,以此作為限制開發所造成的機會成本,測算公式為:

其中,Co為機會成本,X、Q分別為參考區與研究區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為研究區城鎮人口數;S、M分別為參考區與研究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N為研究區農村人口數。2003-2013年漢中市的機會成本如表2所示。

表2 漢中市生態補償支付標準核算(2003-2013年)億元
各年的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相加,得到漢中市2003-2013年為了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區保護所付出的總成本為:660.09億元。考慮“激勵資金”,為了避免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進行違背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活動,包括重新從事為了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而退出的行業,或從事潛在的破壞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行業,且參照財政部公布的《關于2013年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監測考核及獎懲情況的通報》,我們設定“激勵資金”為保護、建設總成本的10%[23]。最終,2003-2013年漢中市作為限制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為:726.099億元,年均補償額為66.009億元④。
在已有的對于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區生態補償量測算的文獻中,研究多以整個陜南區域(漢中、商洛、安康)為對象,得出的測算結果有李懷恩等(2009)[24]的每年89.81億元補償額、史淑娟(2010)[25]的2006-2015每年104.09億元的補償額、李懷恩等(2010)[26]的2010年為80.046億元的補償額;張自英等(2011)[4]的2010年為89.46億元的補償額。按照“生態補償應直接針對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的補償思路,以2010年為例,上述文獻中測算出的生態補償額補償到漢中市的個人手中分別為1 070.28元/人、1 240.45元/人、953.92元/人、1 066.11元/人,而本文估測出2010年補償額應為1 316.15元/人。相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補償標準有以下特點:首先,對象僅為漢中市,對于直接成本、機會成本的核算更加準確;其次,對于“生態利潤”的添加,更能促使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最后,2010年的補償標準占漢中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07%、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1.46%,居民從生態保護與建設中獲得的高補償額有助于激勵其保護與建設的積極性;因此,本文構建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具有可行性。
六、研究結論
我國的禁限開發區面積巨大,包含豐富的生態環境要素,提供眾多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是關系到全局生態安全的重點區域,對禁限開發區的生態補償亟待實施。本文首先在梳理生態補償標準測算方法的基礎上,通過經濟學分析得到生態補償的理論標準;其次,結合目前生態補償實施現狀對這一理論標準進行調整,得出分別適用于禁、限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創新性地提出了不僅要在實際支付中取消對“私人內部效益”的扣除,而且要增加使得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成為“有利可圖”產業的“生態利潤”;再次,提出了以禁限開發程度,實施不同的生態補償支付標準的禁限開發區區域細化思路;最后,通過實證驗證了生態補償支付標準的合理性與可行性。
針對禁限開發區分別實施生態補償支付標準,一方面,作為未來國土空間發展的戰略規劃,《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具有穩定性與持久性,以其中的區域劃分來實行生態補償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從空間區域角度實行生態補償,不受不同生態環境要素差異的影響,易于核算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總成本。因此,未來的生態補償機制建設應以主體功能區的劃分為基礎,對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要根據區域特點分別實施生態補償,按照不同的理論標準與支付標準進行生態補償額測算。最終,在實現重要生態功能區域生態系統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推進主體功能區的穩定與快速發展。
注 釋:
①實際生活中存在的完整產權,法律雖規定生態資源歸國家所有,但生活于其中的居民可能自古就生活于其中,并依靠資源為生,實際上擁有資源的產權。事實產權雖比法律認可的產權安全性小,但是在產權完全界定成本巨大的情況下,存在著法律上產權與事實產權的交疊。
②總成本包括供給者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投入支出、維護操作以及由于增加生態系統服務所犧牲的機會成本等,按照已有文獻的定義,將其分為直接成本(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投入、支出)與機會成本。核算生態補償標準時要視其包括什么而定。
③漢臺區、鎮巴縣、留壩縣、勉縣、西鄉縣、南鄭縣、城固縣、寧強縣、洋縣、佛坪縣、略陽縣。
④由于生態系統保護與建設的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并不發生于一個時點,而是會延續數年,因此在進行生態補償時應對每一年的投入與犧牲進行及時補償,避免“折現”問題的存在。此處,為了與已有研究進行比較,故應用總補償額、年均補償額。
[1]劉玉龍,許冉鳳,張春玲,等.流域生態補償標準計算模型研究[J].中國水利,2006(22):35-38.
[2]鄭海霞,張陸彪.流域生態服務補償定量標準研究[J].環境保護,2006(1):42-45.
[3]蔡邦成,陸根法,安莉娟,等.生態建設補償的定量標準——以南水北調東線水源地保護區一期生態建設工程為例[J].生態學報,2008,28(5):2413-2416.
[4]張自英,胡安焱,向麗.陜南漢江流域生態補償的定量標準化初探[J].水利水電科技進展,2011,31(1):25-28.
[5]Stefano Pagiola.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Costa Rica[J].Ecological Economic,2008,65(4):712-724.
[6]Pagiola S,Ramirez E.Paying for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f silvopastoral practices in Nicaragua[J].Ecological Economic,2007,64(2):374-385.
[7]胡熠,李建建.閩江流域上下游生態補償標準與測算方法[J].發展研究,2006(11):95-97.
[8]虞錫君.構建太湖流域水生態補償機制探討[J].農業經濟問題,2007(9):56-59.
[9]陸研,張紹文.礦區生態恢復治理成本測算方法初探——以黑龍江省雞西煤礦區滴道林場矸石山治理為例[J].草業科學,2009,26(2):19-26.
[10]盧艷,王燕鵬,蒙志良,等.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研究——以河南省海河流域為例[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24(2):228-233.
[11]Costanza R,d’Arge R,de Groot R,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7,387:253-260.
[12]余新曉,魯紹偉,靳芳.中國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J].生態學報,2005,5(8):2096-2102.
[13]李方,張柏,張樹清.三江平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4,18(5):19-23.
[14]劉雨林.關于西藏主體功能區建設中的生態補償制度的博弈分析[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8,22(1):7-15.
[15]仲俊濤,米文寶.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寧夏區域生態補償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3,27(10):19-24.
[16]Davis R K.Recreation Planning as an Economic Problem[J].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1963,3(2):239-249.
[17]毛占峰,王亞平.跨流域調水水源地生態補償定量標準研究[J].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08,18(2):15-18.
[18]鄭海霞,張陸彪,涂勤.金華江流域生態服務補償支付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資源科學,2010,32(4):761-767.
[19]李青,張落成,武清華.太湖上游水源保護區生態補償支付意愿問卷調查——以天目湖流域為例[J].湖泊科學,2011,23(1):143-149.
[20]徐大偉,劉春燕,常亮.流域生態補償意愿的WTP和WTA差異性研究:基于遼河中游地區居民的CVM調查[J].自然資源學報,2013,28(3):402-409.
[21]劉明明.土地立法新探:以土地開發權為視角[J].行政與法,2012(1):120-125.
[22]Schlager E,Ostrom E.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nd natural resources[J].Land Economics,1993,68(3):249-262.
[23]財政部.關于2013年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監測考核及獎懲情況的通報[EB/OL].(2013-10-16)[2014-12-12].http://ys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310/t20131016_999692.html.
[24]李懷恩,謝元博,史淑娟,等.基于防護成本法的水源區生態補償量研究——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區為例[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39(5):875-878.
[25]史淑娟.大型跨流域調水水源區生態補償研究——以南水北調中線陜西水源區為例[D].西安:西安理工大學,2010.
[26]李懷恩,龐敏,肖燕,等.基于水資源價值的陜西水源區生態補償量研究[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40(1):149-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