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小說中的列錦修辭文本建構(gòu)與審美追求
謝元春 吳禮權(quán)
(1.浙江傳媒學(xué)院文學(xué)院,杭州310018;2.復(fù)旦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研究所,上海200433)
現(xiàn)代小說中的列錦修辭文本建構(gòu)與審美追求
謝元春吳禮權(quán)
(1.浙江傳媒學(xué)院文學(xué)院,杭州310018;2.復(fù)旦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研究所,上海200433)
詩歌中“列錦”修辭文本的建構(gòu),早在《詩經(jīng)》中便已肇始。后來歷代詩歌,包括詞、賦、曲等韻文都有“列錦”修辭文本的建構(gòu)。“列錦”修辭文本在韻文體中的廣泛建構(gòu),一方面固然與其審美追求有關(guān),另一方面也與其字句或格律上的要求有關(guān)。因為“列錦”的最大特點是以名詞或名詞短語連續(xù)鋪排的方式出現(xiàn),有“省文約字”與營造畫面意境的雙重效果。小說屬于散文體,沒有字句長短或格律框架的限制,因此無需“省文約字”。如果需要營造畫面意境,可以有別的表達(dá)手段。可是,在唐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卻出現(xiàn)了有意連續(xù)鋪排名詞或名詞短語的“列錦”修辭文本,這可能是受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影響。到了現(xiàn)代小說中,連續(xù)鋪排名詞或名詞短語的“列錦”修辭文本的建構(gòu),則就相當(dāng)普遍了。這與西方電影“蒙太奇”手法以及現(xiàn)代意識流小說的影響有關(guān),是小說家的一種審美追求。
小說 列錦 修辭文本 建構(gòu) 審美
中國的小說創(chuàng)作有著悠久的歷史,成就也令人矚目。在小說修辭方面,中國古代的小說家也多有創(chuàng)造。僅就“列錦”修辭文本的建構(gòu)來說,早在唐代的傳奇小說中就有非常值得重視的成就。其所創(chuàng)造的許多“列錦”修辭文本的結(jié)構(gòu)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是無復(fù)傍依的獨創(chuàng)。
“列錦”,或稱之為“名詞鋪排”,是說寫表達(dá)中特別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一種“有意摒棄動詞與助詞等,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詞或名詞性短語疊加聯(lián)合在一起,用以敘事、寫景、抒情的修辭手法”。以“列錦”修辭手法建構(gòu)的文本,稱之為“列錦”修辭文本。這種修辭文本,“由于突破了常規(guī)的漢語句法結(jié)構(gòu)模式,各名詞或名詞性詞組之間的語法或邏輯聯(lián)系都沒有明顯地標(biāo)示出來,因而從表達(dá)的角度看,就增加了語言表達(dá)的張力,使表達(dá)者所建構(gòu)的修辭文本更具豐富性、形象性和深邃性;從接受的角度看,由于修辭文本隱去了各名詞或名詞性詞組之間的語法或邏輯聯(lián)系標(biāo)識,這就給接受者的解讀文本增加了困阻,但同時也由于表達(dá)者在語言文字上沒有明確限死各語言組成成分之間的關(guān)系,這就給接受者在解讀文本時以更大、更多的自由想象或聯(lián)想的空間,從而獲得更大、更多的文本解讀的快慰與審美情趣。”
“列錦”雖然是現(xiàn)代學(xué)者的命名,但卻是古已有之的修辭現(xiàn)象。就現(xiàn)有的文學(xué)史料來看,“列錦”修辭手法“在先秦的《詩經(jīng)》中就已經(jīng)萌芽。”《詩經(jīng)·國風(fēng)·草蟲》一詩開頭兩句:“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就是現(xiàn)今所見最早的‘列錦’修辭文本”。從漢語修辭史的角度考察,“列錦”修辭手法最初是運用于詩歌之中的,既是詩歌限于字句而“省文約字”的結(jié)果,也是詩歌營造畫面意境的需要。由于具有獨特的表達(dá)與接受效果,后來便逐漸被文學(xué)家們應(yīng)用到賦、詞、曲乃至小說、散文之中。“列錦”運用到散體文中,最早是唐代小說家所為。不過,應(yīng)該指出的是,唐代的小說雖有“列錦”修辭文本的建構(gòu),但并不普遍,只是個別作家有意而為之,帶有鮮明的個性色彩。也正因為如此,加之受小說文體的影響以及宋代開始的小說以白話創(chuàng)作為主流的影響,小說中有意建構(gòu)“列錦”文本者在唐代之后難得一見。根據(jù)我們的考察,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列錦”文本,一般多出現(xiàn)于描寫景物的場合。小說中雖有很多描寫景物的地方,但因無字句的限制,一般很少會出現(xiàn)“省字約文”的現(xiàn)象。這樣,小說中就不易出現(xiàn)以名詞或名詞短語鋪排的“列錦”文本。另外,中國古典小說寫景還有一個慣例,就是以詩詞來表現(xiàn)。這樣,即使詩詞中有“列錦”文本,也不能算是小說本體中的“列錦”,而只能算是詩詞中的“列錦”。正因為如此,小說中的“列錦”文本就更是難以一見了。明代小說《水滸傳》第十回回目中的“林教頭風(fēng)雪山神廟”一句,算是一個典型的“列錦”文本,但這樣的例子實在是難得一見,而且并非是小說作者所為,而是毛宗崗等小說評點家加工改造的結(jié)果。因此,小說中的“列錦”,只是到了現(xiàn)代,在繼承中國古典創(chuàng)造與借鑒西方電影藝術(shù)手法的基礎(chǔ)上才真正出現(xiàn)了新氣象,有了很多創(chuàng)新的結(jié)構(gòu)模式。
一、繼承
小說“列錦”結(jié)構(gòu)模式的繼承,主要是與唐傳奇相比較。不過,應(yīng)該指出的是,唐代小說的“列錦”,鋪排的主要是表示器物的專有名詞。如唐人張鷟小說《游仙窟》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描寫:
(1)眾人皆大笑。一時俱坐。即喚兒取酒。俄爾中間,擎一大缽,可受三升已來。金鈿銅環(huán),金盞銀杯,江螺海蚌,竹根細(xì)眼,樹癭蝎唇,九曲酒池,十盛飲器。觴則兕觥犀角,尫尫然置于座中;……
例(1)中,“金鈿銅環(huán),金盞銀杯,江螺海蚌,竹根細(xì)眼,樹癭蝎唇,九曲酒池,十盛飲器”七句,從結(jié)構(gòu)形式上看,前五句是“NP+NP”結(jié)構(gòu)形式,第六、七句,則是“NP”結(jié)構(gòu)形式,都是名詞短語句。它們與其前后句都沒有語法結(jié)構(gòu)上的糾葛,是并列獨立的句子,屬于名詞鋪排的性質(zhì),即我們上面所說的“列錦”。從語義上看,它們都是器物描寫。現(xiàn)代小說中雖然也有繼承唐代小說這種“列錦”形式的,但從語義上看,所鋪排的主要是代表店鋪的專有名詞。就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看,現(xiàn)代小說繼承唐代小說“列錦”模式的,主要只有以下兩種情況。

類似于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最早出現(xiàn)于漢賦中,后來唐傳奇中也有運用。因此,這種“列錦”形式實際是漢賦與唐傳奇所創(chuàng)模式的繼承與沿用。不過,就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看,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文本在現(xiàn)代小說中并不多見,只是極個別作家偶一為之。如:
(2)許多天,他反復(fù)回憶那越來越遠(yuǎn)的一天。那個電話。魯巴托。比薩。三分之一月亮。乳房。(寧肯《詞與物》)
例(2)中“那個電話。魯巴托。比薩。三分之一月亮。乳房”,是由五個專有名詞或名詞性短語(“三分之一”是作為“月亮”的修飾語,不算帶結(jié)構(gòu)助詞)并列而構(gòu)成的一個“列錦”文本,猶如五個電影特寫鏡頭,將主人公的回憶內(nèi)容圖像化,因而讀來別具一種詩情畫意的韻味。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是連續(xù)鋪排七個名詞短語句,每個名詞短語表示一個專有名詞,類似于唐傳奇中的名物、器物的鋪排,明顯是對唐傳奇中“列錦”結(jié)構(gòu)模式的沿用。不過,唐傳奇中有四句或十句以上等各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名詞句鋪排,而現(xiàn)代小說則很少有這種情況。如:
(3)紅的街,綠的街,藍(lán)的街,紫的街……強(qiáng)烈的色調(diào)化妝著的都市啊!霓虹燈跳躍著——五色的光潮,變化著的光潮,沒有色的光潮——泛濫著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煙,有了高跟兒鞋,也有了鐘……
請喝白馬牌威士忌酒……吉士煙不傷吸者咽喉……
亞力山大鞋店,約翰生酒鋪,拉薩羅煙商,德茜音樂鋪,朱古力糖果鋪,國泰大戲院,漢密而登旅社……回旋著,永遠(yuǎn)回旋著的霓虹燈——忽然霓虹燈固定了:
“皇后夜總會”。(穆時英《夜總會里的五個人》)
例(3)描寫20世紀(jì)上半葉舊上海灘店鋪林立的商業(yè)繁榮景象,作者的敘事沒有用正常的語句進(jìn)行,而是用了“亞力山大鞋店,約翰生酒鋪,拉薩羅煙商,德茜音樂鋪,朱古力糖果鋪,國泰大戲院,漢密而登旅社”等一連七個表示店鋪名稱的名詞性短語進(jìn)行鋪排,猶如電影敘事中連下七個特寫鏡頭,用鏡頭推搖的手法將夜上海繁華的情景表現(xiàn)出來,給人以強(qiáng)烈的視覺沖擊,從而加深了人們對舊上海商業(yè)畸形繁榮景象的認(rèn)識。
二、發(fā)展
現(xiàn)代小說在“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上的發(fā)展非常多,就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至少有如下幾種情況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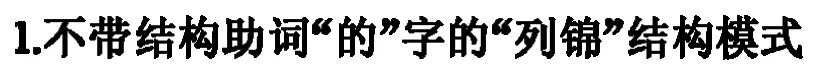
唐代小說以及古代詩詞曲中的“列錦”,都是不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現(xiàn)代漢語中的“列錦”,也有不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這可以看成是古代“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的繼承與延續(xù)。但是,現(xiàn)代小說中不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在類型上與唐傳奇是有區(qū)別的,很多都是現(xiàn)代小說發(fā)展出來的。就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看,這種不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的“列錦”有如下幾種情況。
1.1“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在唐傳奇中沒有,但在唐詞中卻已經(jīng)出現(xiàn)。因此,現(xiàn)代小說中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既可以說是對唐詞“列錦”結(jié)構(gòu)模式的繼承,也可以說是現(xiàn)代小說在“列錦”模式上的發(fā)展。就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看,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模式的運用并不多,只有個別作家有意為之的個別例證。如:
(4)追悼會和歡迎會。宴會和聯(lián)歡會。雞尾酒會和夜總會。默哀,握手,致詞,舉杯,奏樂,唱歌:Home,Sweet Home(甜蜜的家庭)。夏天最后一株玫瑰。玫瑰玫瑰我愛你。你不要走。快樂的寡婦。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怒吼吧,黃河。團(tuán)結(jié)就是力量。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來開?一條大河波浪寬……阿里盧亞!阿里盧亞!
有點像電影——有點不妙。云淡風(fēng)清近午天。人之出(初),狗咬豬。369畫報。你有外幣嗎?你還認(rèn)得我嗎?
你還認(rèn)得我嗎?(王蒙《相見時難》)例(4)有很多“列錦”文本,其中“夏天最后一株玫瑰”、“369畫報”兩句,就是獨立于其他句子之外的兩個名詞性短語句,屬于“NP”式“列錦”。它與古代的“列錦”文本一樣,是不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這兩個“列錦”文本插入上引一段文字中,就像兩個特寫鏡頭,使敘事文字增添了鮮明的畫面感,從而有力地提升了小說的審美價值。
1.2“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是古代詩歌中最為常見的模式,但是在古代小說中沒有出現(xiàn)。現(xiàn)代小說中出現(xiàn)這種“列錦”模式,從來源上看是對古代詩詞的繼承,但單就文體來看,在現(xiàn)代小說中運用則是創(chuàng)新。不過,就目前所能掌握到的材料來看,這樣的“列錦”結(jié)構(gòu)模式在現(xiàn)代小說中也并不多見,只是極個別的作家偶一為之。如:
(5)死亡。冬天。一場雪后,蘇為民推出房門,像一只活動小動物站在院子里的積雪
中。(寧肯《詞與物》)
例(5)中“死亡。冬天”兩個句子,都是由不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名詞短語獨立構(gòu)句,屬于典型的“NP,NP”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文本。與古代相同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相比,這里的兩個名詞短語表示的都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因此,它雖也是電影特寫鏡頭的表意,但呈現(xiàn)的圖畫則比較空靈,有一種抽象的朦朧美。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古今“列錦”文本建構(gòu)在審美觀念上有了很大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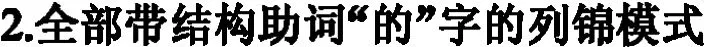
現(xiàn)代小說因為是以白話文寫作,所以名詞性短語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乃是現(xiàn)代漢語語法的常態(tài)。因此,現(xiàn)代小說中幾個并列的名詞性短語連續(xù)鋪排都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就顯得非常普遍了。根據(jù)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現(xiàn)代小說中這類“列錦”又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2.1“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古代詩詞曲中都有出現(xiàn),但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的,則是現(xiàn)代小說中才有的。從文體的角度看,也可以算是“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這樣的“列錦”文本,在現(xiàn)代小說中頗為常見。如:
(6)紅的街,綠的街,藍(lán)的街,紫的街……強(qiáng)烈的色調(diào)化妝著的都市啊!霓虹燈跳躍著——五色的光潮,變化著的光潮,沒有色的光潮——泛濫著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煙,有了高跟兒鞋,也有了鐘……
請喝白馬牌威士忌酒……吉士煙不傷吸者咽喉……
亞力山大鞋店,約翰生酒鋪,拉薩羅煙商,德茜音樂鋪,朱古力糖果鋪,國泰大戲院,漢密而登旅社……
回旋著,永遠(yuǎn)回旋著的霓虹燈——
忽然霓虹燈固定了:
“皇后夜總會”。(穆時英《夜總會里的五個人》)
(7)蔚藍(lán)的黃昏籠罩著全場,一只saxophone正伸長了脖子,張著大嘴,嗚嗚地沖著他們?nèi)隆.?dāng)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頭發(fā)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lǐng)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著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獨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著自家兒的神經(jīng)。(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斷片])
(8)一九四八的北平。
報紙上登載著“平漢沿線戰(zhàn)況吃緊”、“冀東戰(zhàn)況吃緊”、“銀根奇緊”的消息和“征美貌女友”、“征夫”以及“專治腎虛腎寒”的春藥廣告。大街上人人驚恐不安,……(王蒙《相見時難》)
例(6)“回旋著,永遠(yuǎn)回旋著的霓虹燈”,是一個獨立于其他句子之外的名詞性短語,單獨構(gòu)句,屬于典型的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的“NP”結(jié)構(gòu)模式的“列錦”文本,它以獨立的形式出現(xiàn),就像電影中特意推出的一個特寫鏡頭,意在強(qiáng)調(diào)突出舊上海灘上夜晚霓虹燈回旋閃爍的景象,讓人有如臨其境之感。例(7)“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以偏正式名詞短語句獨立構(gòu)句,意在以特寫鏡頭的方式突出夜總會中圓桌子擺放整齊的形象。例(8)“一九四八的北平”,也是一個“NP”結(jié)構(gòu)的名詞短語獨立成句,意在以獨立的鏡頭強(qiáng)調(diào)1948年的北平,讓“北平”成為敘事聚焦的背景。這些“列錦”文本的建構(gòu)都是受電影“蒙太奇”手法的影響,它們運用于小說中,使小說敘事別添詩情畫意的效果,對于提升小說的審美價值無疑是有益的。
2.2“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是以兩個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的名詞性短語并列對恃而構(gòu)成。從來源上看,它是古代詩歌“列錦”模式的繼承;但就文體而論,則是現(xiàn)代小說中的創(chuàng)造。不過,就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這種“列錦”在現(xiàn)代小說中的運用并不普遍,只在極個別有個性的小說家的作品中偶有一見。如:
(9)草的海。綠色和芳香的海。人們告訴過他,融化就是幸福,那就融化在草的海里,為草的海再添一點綠色的芬芳吧!(王蒙《雜色》)例(9)中“草的海。綠色和芳香的海”,從結(jié)構(gòu)上看,都是以名詞“海”為中心語的名詞短語,各自獨立構(gòu)句,是典型的“NP,NP”式“列錦”文本。兩個名詞短語句置于段落的開頭,就像電影開幕時首先推出的兩個特寫鏡頭,讓人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視覺沖擊。兩個名詞短語句雖都以“海”為畫面的主基調(diào),但由于各自的修飾限定語不同,畫面的色調(diào)就有所不同。這樣兩幅畫面就形成了對比,由此使所呈現(xiàn)的畫面更為生動而鮮明,文本的審美價值大大得以提升了。
2.3“NP,NP,NP”式
這種“列錦”模式,是以三個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的名詞性短語并列鋪排而成的。從來源上看,它是古代詞賦小說“列錦”模式的沿用;但就文體而論,則是現(xiàn)代小說中才有的。就我們目前所掌握到的材料看,這種“列錦”在現(xiàn)代小說中的運用相當(dāng)普遍。如:
(10)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草綠色的軍服,
閃閃的紅星。立正,一個軍禮。韭菜落到了地上,站起身來的時候碰翻了小板凳,咣當(dāng)。(王蒙《蝴蝶》)
(11)……麥麥歡喜得合不攏嘴,嚷著跑到小溪邊去照自己的模樣。段卯卯又把目光投向那遠(yuǎn)運走來的女人。
藍(lán)的天,綠的地,長長的小路,她走來了!近了,近了,只有百十步遠(yuǎn)了!他的心口窩突然那么厲害地跳了起來。啊啊,那年去領(lǐng)結(jié)婚證,他也是在這兒等著她,一起去小鎮(zhèn)的。那時的心,也是跳的這么厲害呀!他不禁失笑了,三十大幾的人了,莫非又在戀愛了?
他又把麥麥叫回身邊說:“麥麥,你看那邊誰來了?”……(張枚同、程琪《麥苗返青的時候》)
(12)永遠(yuǎn)不老的春天,永遠(yuǎn)新鮮的綠葉,永遠(yuǎn)不會凝固、不會僵硬、不會凍結(jié)的雨絲!
(王蒙《蝴蝶》)
例(10)中“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草綠色的軍服,閃閃的紅星”,三個句子都是名詞短語構(gòu)句,是典型的“NP,NP,NP”式“列錦”文本。三個句子并列置于段落的開頭,就像電影的三個特寫鏡頭。第一個鏡頭是全景式的遠(yuǎn)鏡頭,第二第三個鏡頭則是局部的放大式的近鏡頭。鏡頭的層次感與遠(yuǎn)近感,使文本呈現(xiàn)更具電影表達(dá)藝術(shù)的特點,讀后猶如觀賞電影的感覺。例(11)中“藍(lán)的天,綠的地,長長的小路”,與例(10)一樣,三句就像是三個電影特寫鏡頭,由高而低,由遠(yuǎn)而近,通過鏡頭的搖轉(zhuǎn),呈現(xiàn)出一幅藍(lán)天綠地小路的鄉(xiāng)村畫面。例(12)“永遠(yuǎn)不老的春天,永遠(yuǎn)新鮮的綠葉,永遠(yuǎn)不會凝固、不會僵硬、不會凍結(jié)的雨絲”,三句雖然長度不一,但結(jié)構(gòu)上都是以名詞為中心的偏正式名詞短語單獨構(gòu)句,以純電影鏡頭的方式寫景,讀之讓人猶如觀賞電影的視覺印象。
2.4“NP,NP,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在漢賦與古代詞曲中都已出現(xiàn)。但是,四個名詞性短語都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則是現(xiàn)代小說的創(chuàng)造。這種列錦模式,在現(xiàn)代小說中常被運用,并非個別作家的修辭行為。如:
(13)穿上了外套,抽著強(qiáng)烈的吉士牌,走到校門口,她已經(jīng)在那兒了。這時候兒倒是很適宜于散步的悠長的煤屑路,長著麥穗的田野,幾座荒涼的墳,埋在麥里的遠(yuǎn)處的鄉(xiāng)村,天空中橫飛著一陣烏鴉……(穆時英《被當(dāng)作消遣品的男子》)
(14)海云的淚珠,荷葉上的雨滴,化雪時候的房檐,第一次的,連焦渴的地面也滋潤不過來的春雨!(王蒙《蝴蝶》)
(15)古城的黃昏,像一陣煙雨,什么都浸在迷濛中。黑色的院墻,黑色的街心,黑色的行人臉,還有那看不見的黑色的人們的心。(碧野《燈籠哨》)
例(13)中“這時候兒倒是很適宜于散步的悠長的煤屑路,長著麥穗的田野,幾座荒涼的墳,埋在麥里的遠(yuǎn)處的鄉(xiāng)村”,例(14)中“海云的淚珠,荷葉上的雨滴,化雪時候的房檐,第一次的,連焦渴的地面也滋潤不過來的春雨”,例(15)“黑色的院墻,黑色的街心,黑色的行人臉,還有那看不見的黑色的人們的心”,都是由四個句子構(gòu)成,雖然長短不一,但在結(jié)構(gòu)上都屬于偏正式名詞短語,都是獨立成句的,是典型的“NP,NP,NP,NP”式“列錦”文本,它們在小說中作用就像電影敘事中插入的四個特寫鏡頭,畫面非常強(qiáng),對于營造小說“詩情畫意”的敘事效果,提升小說的審美價值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2.5“NP,NP,NP,NP,NP”式
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模式,在漢賦與元曲中都已存在。但是,每個名詞性短語都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則是現(xiàn)代小說的創(chuàng)造。不過,就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看,這種“列錦”模式,在現(xiàn)代小說中只是偶有運用,并不普遍。如:
(16)淡白色的果肉,褐色的核,青黃色的皮,兩個人的眼睛,各種題目的談話。于是我們就成了愛侶了。(巴金《春天里的秋天》)
例(16)中“淡白色的果肉,褐色的核,青黃色的皮,兩個人的眼睛,各種題目的談話”,五個名詞性短語并列對恃,構(gòu)成一個“列錦”文本,置于段落的開頭,猶如電影開幕時推出的五個特寫鏡頭,將小說敘事化為鏡頭呈現(xiàn),文字圖像化,給讀者留下的想象空間更大,對于提升小說的審美情趣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2.6“NP,NP,NP,NP,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的“列錦”,最早出現(xiàn)在漢賦中。但六個名詞性短語都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則是現(xiàn)代小說中才有的現(xiàn)象。不過,這種“列錦”模式,就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看,現(xiàn)代小說中也并不常見,只是偶一見之。如:
(17)滿座的觀眾,暗淡的電燈,悶熱的空氣,帶鼻音的本地話,女人的笑,小孩的哭。于是黑暗壓下來,一切都沒有了。(巴金《春天里的秋天》)
例(17)中“滿座的觀眾,暗淡的電燈,悶熱的空氣,帶鼻音的本地話,女人的笑,小孩的哭”六句,是寫劇院里人與事、情與景,以“列錦”文本來呈現(xiàn),六個名詞短語句就像電影的六個電影特寫鏡頭,空間畫面感特別鮮明,給人留下的想象空間也特別大,這對于提升作品的審美價值無疑是有重要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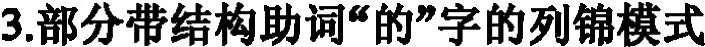
現(xiàn)代小說中部分帶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的“列錦”模式,根據(jù)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主要有如下幾種情況。
3.1“NP,NP,NP,NP”式
這種“列錦”模式,早在漢賦中就已出現(xiàn)。但四個名詞性短語句中一部分名詞中心語與修飾語之間帶有結(jié)構(gòu)助詞“的”字,則是現(xiàn)代小說中才出現(xiàn)的。就我們目前所掌握到的材料看,現(xiàn)代小說中運用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模式的并非個案。如:
(18)蔚藍(lán)的黃昏籠罩著全場,一只saxophone正伸長了脖子,張著大嘴,嗚嗚地沖著他們?nèi)隆.?dāng)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頭發(fā)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lǐng)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著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獨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著自家兒的神經(jīng)。(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斷片])
(19)北京——北平。從太平倉繞一個小胡同,黑漆門上的對聯(lián):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就在平則門里,就在溝沿,就在南磚塔胡同的拐彎處。兩塊大石頭墩子,一棵老槐樹,夏天的吊死鬼——槐蠶。雨后,蝸牛爬過以后,從墻根上向上延伸著白沫似的軌跡。孩子們唱著:……(王蒙《相見時難》)
例(18)中“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是四個簡短的名詞短語句構(gòu)成的“列錦”文本,猶如電影的四個特寫鏡頭,對舊上海灘舞廳內(nèi)人流混雜的情景予以呈現(xiàn),畫面感非常強(qiáng),讓人有如臨其境,如聞其味的感覺。例(19)中“兩塊大石頭墩子,一棵老槐樹,夏天的吊死鬼——槐蠶。雨后,蝸牛爬過以后,從墻根上向上延伸著白沫似的軌跡”四個句子,雖然長短不一,但都是以名詞為中心的名詞性短語,各自成句,構(gòu)成一個“列錦”文本,以電影特寫鏡頭的方式呈現(xiàn)了1948年的北平平則里的環(huán)境,讓人猶如觀賞一部追憶老北京的懷舊電影。
3.2“NP,NP,NP,NP,NP,N,NP,NP,NP,NP,NP,NP,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在漢賦中已有先例,但沒有這樣復(fù)雜,并列的名詞或名詞短語句的項目沒有這么多,這是現(xiàn)代小說在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不過,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的運用并不普遍,只是極個別作家有意而為之的產(chǎn)物。如:
(20)久別的重逢,另一個女人,新婚的妻子,重燃的熱情,匆匆的別,病,玫瑰花,醫(yī)院中的會晤,愛情的自白,三角的戀愛,偕逃的計劃,犧牲的決心,復(fù)車的死。
——許多的人在嘆氣,電燈亮了。藍(lán)色布幕拉起來。什么也沒有。我們?nèi)耘f在中國,不過做了一場歐洲的夢。(巴金《春天里的秋天》)例(20)整個一個段落就是一個“列錦”文本,它由十三個名詞性短語句構(gòu)成,就像電影中連續(xù)而下的十三個特寫鏡頭及其鏡頭組合,表意的圖像化傾向十分明顯,因此給讀者的視覺沖擊也就特別強(qiáng)烈,讀后讓人歷久難忘,回味無窮。
3.3“N,N,NP,NP,NP+NP,NP,NP,NP,NP,N,N,N,N,N,NP,NP”式
這種復(fù)雜結(jié)構(gòu)的列錦,是自古及今未曾有過的,是現(xiàn)代小說家的創(chuàng)造。不過,就目前我們所能掌握到的材料看,這樣的列錦是難得一見的,僅在極個別作家的作品中才能覓得一例。如:
(21)青春,熱情,明月夜,深切的愛,一對青年男女,另一個少年,三角的戀愛,不體諒的父親,金錢,榮譽(yù),事業(yè),犧牲,背約,埃及的商業(yè),熱帶的長歲月。
……
——許多的人在嘆氣,電燈亮了。藍(lán)色布幕拉起來。什么也沒有。我們?nèi)耘f在中國,不過做了一場歐洲的夢。(巴金《春天里的秋天》)
例(21)整個一個段落就是一個“列錦”文本,由十五個名詞性短語句(個別是由動詞或形容詞轉(zhuǎn)換成的)并列而構(gòu)成,就像以鏡頭及其鏡頭組合敘事的電影,給人的視覺沖擊特別大,留給讀者自行解讀的空間也特別大,因而也就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審美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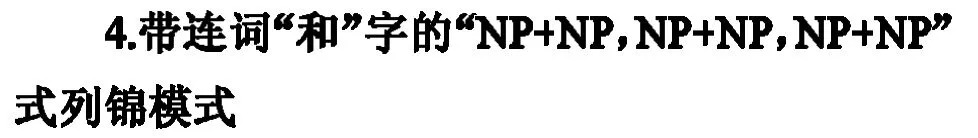
“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中帶連詞“和”字的,早在宋人岳飛的《滿江紅》詞中便已出現(xiàn),但是岳飛所創(chuàng)的“列錦”是“NP和NP”式(“八千里路云和月”),而非“NP和NP,NP和NP,NP和NP”式。可見,帶連詞“和”字的“NP+NP,NP+NP,NP+NP”式“列錦”是現(xiàn)代小說的創(chuàng)造。這種“列錦”文本在王蒙小說中比較常見,帶有王式風(fēng)格。如:
(22)追悼會和歡迎會。宴會和聯(lián)歡會。雞尾酒會和夜總會。默哀,握手,致詞,舉杯,奏樂,唱歌:Home,SweetHome(甜蜜的家庭)。夏天最后一株玫瑰。玫瑰玫瑰我愛你。你不要走。快樂的寡婦。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怒吼吧,黃河。團(tuán)結(jié)就是力量。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來開?一條大河波浪寬……阿里盧亞!阿里盧亞!
有點像電影——有點不妙。云淡風(fēng)清近午天。人之出(初),狗咬豬。369畫報。你有外幣嗎?你還認(rèn)得我嗎?
你還認(rèn)得我嗎?(王蒙《相見時難》)
(23)大汽車和小汽車。無軌電車和自行車。鳴笛聲和說笑聲。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點。(王蒙《夜的眼》)
例(22)中“追悼會和歡迎會。宴會和聯(lián)歡會。雞尾酒會和夜總會”,例(23)中“大汽車和小汽車。無軌電車和自行車。鳴笛聲和說笑聲”,都是帶連詞“和”字的“NP+NP,NP+NP,NP+NP”式“列錦”模式,而且都置于段落的開頭,儼然是電影開幕時首先推出的三組特寫鏡頭,不僅畫面感非常強(qiáng),而且意涵豐富,給讀者留下的想象空間也很大,對營造小說詩情畫意的格調(diào)明顯是有很大的作用。我們讀王蒙小說常常覺得有看電影的畫面感與讀詩的跳躍感,很大程度上與他喜歡運用“列錦”修辭手法有關(guān)。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模式,在古代詩詞、曲、賦,包括散文、小說中都不可能出現(xiàn)。只是隨著現(xiàn)代漢語語法的發(fā)展,才在現(xiàn)代詩歌、散文與小說中出現(xiàn)。所以,就小說這一文體而言,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運用,也算是一種創(chuàng)新。就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看,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又具體分為如下幾種情況。
5.1“NP+NP,NP,NP+NP”式
這種“列錦”模式,不僅古代詩、詞、曲、賦中沒有,就是現(xiàn)代詩歌中也沒有,是小說家在小說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列錦”新模式。不過,就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看,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的運用并不普遍,只是極個別作家偶一為之的產(chǎn)物。如:
(24)圓圓的天和圓圓的地,一條季節(jié)河,
一匹馬和一個人,這究竟是什么年代?這究竟是地球的哪個角落?(王蒙《雜色》)
例(24)“圓圓的天和圓圓的地,一條季節(jié)河,一匹馬和一個人”,是三個名詞性短語語并列構(gòu)成的“列錦”文本,它以三個特寫鏡頭的方式將天、地、河流、馬、人有機(jī)地組合在一起,以畫面與畫面組合的形式直觀地呈現(xiàn)給讀者,讓讀者不僅有如臨其境的感覺,更給其想象留下了豐富的空間,使作品別添一種詩情畫意的效果。
5.2“NP,NP,NP+NP,NP+NP,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是現(xiàn)代小說家的創(chuàng)造。不過,目前還難得一見有更多的用例,只在極個別作家中的小說偶有一見而已。如:
(25)男女廁所門前排著等小便的人的長隊。陸角的雙勾虛線。大包袱和小包袱。大籃筐和小籃筐。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這最后一段行程會是艱難的結(jié)論,他有了思想準(zhǔn)備。(王蒙《春之聲》)
例(25)開頭一段就是以五個名詞性短語句的并列而構(gòu)成的一個“列錦”文本,它是以特寫鏡頭的形式敘事,以畫面的形式將中國人出行的情狀予以直觀地呈現(xiàn),讀后讓人印象非常深刻,感慨萬千。
5.3“NP,NP,NP,NP,N,N,N,N,NP+NP,NP+ NP,NP”式
這種“列錦”模式,類似于漢賦,但在結(jié)構(gòu)上又比漢賦復(fù)雜得多,是現(xiàn)代小說家的創(chuàng)造。不過,就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看,這樣的“列錦”文本并不多,只是極個別的作家偶一為之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如:
(26)蔚藍(lán)的黃昏籠罩著全場,一只saxophone正伸長了脖子,張著大嘴,嗚嗚地沖著他們?nèi)隆.?dāng)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頭發(fā)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lǐng)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著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獨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著自家兒的神經(jīng)。(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斷片])
例(26)“當(dāng)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頭發(fā)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lǐng)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是由十個名詞性短語并列構(gòu)成的(其中“當(dāng)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是充當(dāng)這十個句子的公用定語)。十個名詞短語句,就像電影中的十個特寫鏡頭,讓舊上海灘舞廳中的眾生相以圖像的形式鮮活地呈現(xiàn)出來,讓人猶如坐進(jìn)影院觀看電影中的人物與故事一樣。
5.4“NP,NP,NP,N,N,NP+NP,NP,NP+NP,NP,NP+NP,NP”式
這種“列錦”模式,是以十一個名詞或名詞短語、名詞短語組合混合構(gòu)成,其復(fù)雜的程度遠(yuǎn)遠(yuǎn)超出以往任何種類的“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不過,就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看,這樣復(fù)雜的“列錦”結(jié)構(gòu)在現(xiàn)代小說中并不多見,只在極個別作家的筆下才偶有一見。如:
(27)華東飯店里——
二樓:白漆房間,古銅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長三罵淌白小娼婦》,古龍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綁標(biāo)匪,陰謀和詭計,白俄浪人……(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斷片])
例(27)簡直就是現(xiàn)代的電影劇本寫法,十一個名詞或名詞性短語一字鋪排而下,完全就是電影“蒙太奇”手法的運用,將舊上海灘舞廳那種魚龍混雜、醉生夢死的情狀以畫面的形式直觀地呈現(xiàn)出來,讓人如臨其境,親見其人其事。

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的“列錦”,也是現(xiàn)代小說所創(chuàng)造的。從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看,主要又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6.1“NP,NP,NP+NP,NP,NP,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的“列錦”,是由七個名詞或名詞短語構(gòu)成。從來源上看,是漢賦“列錦”形式的延續(xù)。但是,從結(jié)構(gòu)形式的復(fù)雜性與并列項目的數(shù)目看,卻不同于漢賦,明顯是現(xiàn)代小說的創(chuàng)造。這種類型的“列錦”,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運用的還比較少,只是偶有一見。如:
(28)各式各樣的風(fēng)景圖片。帆船上的繩索。沙灘與浪花的白線。鳥瞰下的小島。飛滿天空的海鷗。街道。牛魔王的洞穴一般的銀行房子。石頭有一種奇怪的紫褐色。燈光被古老笨重的的銅盞反射。(王蒙《卡普琴諾》)
例(28)寫異國的見聞,以十一個名詞或名詞短語句一字鋪排而下,就像電影中連續(xù)推出的特寫鏡頭及其組合,讀之讓人有一種視覺上的強(qiáng)烈沖擊,印象特別深刻。
6.2“NP,N,N,NP,NP,N,N,NP,NP,NP,NP+ NP,NP+NP,NP,NP,NP”式
這種“列錦”模式,由連續(xù)鋪排的十五個名詞或名詞短語、名詞短語組合構(gòu)成,是現(xiàn)代小說的獨創(chuàng)。就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小說材料,這種“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的運用并不普遍,而只是極個別作家有意而為之的偶然現(xiàn)象。如:
(29)需要一個提綱。
世界最大的航空港之一——芝加哥機(jī)場。名目繁多的航空公司,各霸一方而又聯(lián)營。熒光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飛機(jī)起飛時刻表和飛機(jī)抵達(dá)時刻表,綠光閃爍。候機(jī)樓里的茶,咖啡,可口可樂,橙子汁,蕃茄汁,三明治,熱狗,漢堡包,意大利煎餅,生菜色拉,熏魚,金發(fā)的白人與銀發(fā)的黑人,巴黎香水與南非豆蔻,登機(jī)前的長吻。女士們,先生們,飛行號數(shù)633……
還有一張半裸的女人像,背景是陽光燦爛的海水浴場,畫在半透明的塑料板上,燈光從后面照射過來,顯得就像是真正的太陽在照耀。下面幾個大字:你去過佛羅里達(dá)嗎?(王蒙《相見時難》)
例(29)是寫美國芝加哥機(jī)場所見場景,但是作者沒有用正常的語句敘事,而是用了十五個名詞或名詞短語、名詞短語組合一字鋪排而下,就像十五個電影特寫鏡頭從芝加哥候機(jī)大廳搖轉(zhuǎn)而過,將異國機(jī)場的眾生相以鮮活的畫面形式呈現(xiàn)出來,給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6.3“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P,N,NP,N,NP,NP”式
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的“列錦”,是以二十個名詞或名詞短語、名詞短語組合并列鋪排而成,是目前所見“列錦”文本中最為復(fù)雜的形式。不過,這樣的“列錦”文本,就我們目前所能找到的材料看,也僅此一例而已。如:
(30)……
沒有父母的少女,酗酒病狂的兄弟,純潔的初戀,信托的心,白首的約,不辭的別,月夜的驟雨,深刻的心的創(chuàng)痛,無愛的結(jié)婚,丈夫的欺騙與犯罪,自殺與名譽(yù),社會的誤解,兄弟的責(zé)難與仇視,孀婦的生活,永久的秘密,異邦的漂泊,沉溺,兄弟的病耗,返鄉(xiāng),兄弟的死,終身的遺恨。
……
——許多的人在嘆氣,電燈亮了。藍(lán)色布幕拉起來。什么也沒有。我們?nèi)耘f在中國,不過做了一場歐洲的夢。(巴金《春天里的秋天》)例(30)一整段共二十一句就是一個“列錦”文本,是由名詞或名詞短語(個別是由動詞轉(zhuǎn)換而成)、名詞短語組合共同組成,就像電影中二十一個連續(xù)推出的特寫鏡頭,以立體全方位掃描的方式將一些中國人的歐洲夢呈現(xiàn)出來,讓人印象非常深刻,也讓人思慮深深,感慨萬千。
三、結(jié)語
上文我們說過,“列錦”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在漢語修辭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最早是孕育于詩之中,既是詩寫作“省文約字”的需要,也是詩創(chuàng)造“詩中有畫”意境之需要。后來“列錦”修辭手法擴(kuò)及于賦、詞、曲乃至散文小說等文體,乃是因為“列錦”獨特的表達(dá)效果被文學(xué)家們所認(rèn)識。小說屬于散文體,與詩、賦、詞、曲等韻文體明顯不同,既無字句長短多少的限制,也無格律框架的約束,不存在“省字約文”的客觀要求。如果需要創(chuàng)造“詩情畫意”的意境,事實上有很多修辭手法可以運用。唐人小說中之所以會出現(xiàn)“列錦”,那是唐代小說作家(主要是個別作家)有意而為之,就像唐人“有意為小說”一樣。因為唐人小說中的“列錦”是有意而為之,所以所創(chuàng)的“列錦”結(jié)構(gòu)形式雖然相當(dāng)復(fù)雜,充滿了創(chuàng)造性,但在唐人小說中并不普遍。也就是說,唐人小說中運用“列錦”修辭手法,乃是個人行為,是個別作家修辭創(chuàng)造個性化的張揚,是對傳統(tǒng)詩歌“列錦”修辭手法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唐代之后直到現(xiàn)代小說興起,中國小說中一直難得一見“列錦”修辭手法的運用。這一事實說明,“列錦”與小說的淵源關(guān)系并不深。到了現(xiàn)代小說中,“列錦”修辭手法的運用突然多起來,結(jié)構(gòu)模式也豐富起來,這其間除了與中國古典詩、賦、詞、曲以及唐人小說運用“列錦”的傳統(tǒng)影響有關(guān)以外,更重要的是受西方現(xiàn)代電影“蒙太奇”手法以及意識流小說的影響。“列錦”手法與電影“蒙太奇”手法的相似性,在上文我們已經(jīng)說得很多了,無庸贅述。至于意識流小說與“列錦”修辭手法的關(guān)系,其實也是非常密切的。意識流小說在語言上的特點很多,其中動態(tài)性強(qiáng)、無邏輯性,與“列錦”只以名詞或名詞短語連續(xù)鋪排的特點非常近似。因此,中國現(xiàn)代小說家在小說中有意識地大規(guī)模建構(gòu)“列錦”文本,甚至是結(jié)構(gòu)非常復(fù)雜的“列錦”文本,不能不說是明顯受到西方意識流小說在語言描寫上強(qiáng)調(diào)動態(tài)性、無邏輯性的特點的啟發(fā)。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從巴金、王蒙等人深受西方小說觀念影響與他們小說中有意建構(gòu)“列錦”文本的事實中看得尤其清楚。
The Use of“LieJing”and Its Aesthetic In Contemporary Novels
Xie YuanchunWu Liquan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Hangzhou 310018,Zhejiang,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xiàn)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LieJing”in the use of poetry was found early from“ShiJing”(《詩經(jīng)》).After that,all kinds of poetry including Ci(詞),F(xiàn)u(賦),Qu(曲)are“LieJing”included.The use of“LieJing”is popular in poetry the reason is that“LieJing”fulfilled both aesthetic and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of poetry.As“LieJing”means the serial use of nouns and noun phrases,it gets the benefits on“being intensive”and creating atmosphere.Novel is a kind of prose,it doesn’t have requirements to limit the rhythm and the length of each sentence.So,being intensive is not necessary in novel.When it comes to atmosphere creating,“LieJing”is also not the only choice on that.However,indeed,“LieJing”has been found in the novels of Tang Dynasty.The reason of that maybe it was affected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Nowadays,“LieJing”,the skill of serial use of nouns and noun phares,has already become common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s.This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Montage”,a western technique for movie-making,and the idea of“Steamof consciousness”in contemporary novels.“Lie-Jing”has become a part of aesthetic in novel already.
Novel;LieJing;Use;Aesthetic
責(zé)任編輯:盧烈紅
謝元春(1978—),女,湖南冷水江人,文學(xué)博士,浙江傳媒學(xué)院文學(xué)院講師。
吳禮權(quán)(1964—),男,安徽安慶人,文學(xué)博士,復(fù)旦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xué)客座教授、臺灣東吳大學(xué)客座教授、湖北省政府特聘“楚天學(xué)者”講座教授,中國修辭學(xué)會會長。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辭格審美史”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zhǔn)號:10BYY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