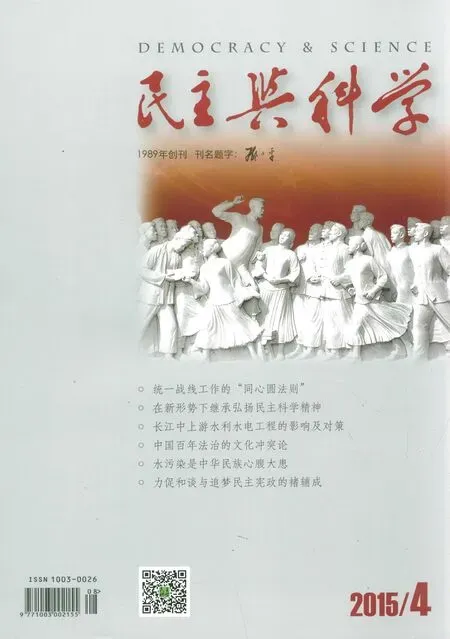科學傳播的責任
王大鵬
(作者為中國科普研究所媒體科技傳播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傳統上認為,科學的大眾化經歷了傳統科普(science popularization)、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三個階段,且科學傳播不同于傳統科普,它是傳統科普的躍升,包括傳播過程是雙向的,科學傳播是一種文化建設,科學傳播更注重科學與社會的關系等。
對于科學傳播是否可以取代科普的問題,在世紀之交還出現過一系列爭論和探討,其原因可能認為前者是舶來品不適合中國話語體系,當然最終結果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部分研究者和從業者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將科普與科學傳播對等使用。本文無意探討科學傳播與科普孰優孰劣,但是傾向于在當前社會情境下,科普和科學傳播并存,只是在二者使用方面應該注意相關語境。
為什么,怎么做,誰來做
科學大眾化(popular science)的歷史跟科學一樣悠久。盧克萊修、哥白尼、伽利略等都曾以各種形式向公眾傳播科學,但是隨著科學共同體的形成、科學的建制化和科學家職業化的出現,科學和公眾開始分離。向大眾傳播科學開始被排除在科學共同體之外,甚至一些開展傳播工作的科學家受到科學共同體排擠。在這個過程中,科學新聞記者承擔起傳播科學的工作,成為科學傳播的二傳手。
但是,對公眾進行科學傳播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科學共同體、決策者等眾多方面的重視。因為要獲得科研經費,科學家需要把其所開展的工作以通俗明白的語言解釋給手握投票權的公眾,同時公眾也需要利用各種科技知識作出理性的科學決策。科學傳播專 家 Jane Gregory 和 Steve Miller 總結了科學傳播的各種益處,包括有利于科學本身的發展,讓公民了解科學進展,科學研究才可以得到廣泛社會支持;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經濟發展需要一大批具備專業技能的勞動者,而消費者也需要知道購買的是什么科技產品;有助于提高國家影響力;有助于人的全面發展,從事一些工作的人需要科學武裝和豐富完善自己;有助于社會民主,使得廣大公眾緊跟科技步伐,促進民主發展進程;有助于美學、道德等文化的建設。
傳統上,媒體成為完成正規教育后公眾獲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國內外相關科學素養調查都證實了這一論述。但是媒體議程設置、框架理論和鋪墊理論等也對媒體科學傳播內容有所影響。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科學家通過講座、展覽、撰寫科普文章等形式參與科學傳播。但是無論如何進行科學傳播,科學傳播者(包括媒體記者和科學家群體)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精確性進行“中和”。正是基于這種做法才有了科學家與媒體之間的各種不適應,雙方互相抱怨,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話題。
隨著科技進步和公眾民主意識的提高,特別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發展,傳統媒體面臨著新媒體的沖擊和挑戰,這不僅限于科學傳播方面。當然媒體在公眾獲取科技信息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隨著Web2.0 時代的出現,科學傳播出現多元主體并存的狀況。一方面,傳統媒體繼續從事著科學傳播工作,當然部分媒體開始轉戰互聯網,比如NewsWeek 在2012年10月宣布將停止印刷版,并于2013年1月全面轉向電子媒體。另一方面,科學家和科研機構紛紛利用博客等新媒體開展科學傳播。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尼爾森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共追蹤1.81 億個博客,較2006年的3600 萬的博客數量有了大幅增長。而在國內,科學網博客上每日都不斷更新著各種科學資訊,果殼網日均瀏覽量400 多萬次,微信訂閱數高達40 萬(2014年7月數據)。而這些撰寫博客的作者絕大部分都是科研一線研究人員。
此外,隨著公民科學運動的興起,公眾通過各種渠道參與科學研究和科學傳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公眾也成為科學傳播的一個主體,他們不再是被動接受者,而是主動參與者和推動者。
誰的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以下稱《科普法》)指出,“國家機關、武裝力量、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農村基層組織及其他組織應當開展科普工作”,“科普是公益事業”。但是從根本上說,《科普法》是一部“應該”法,而非“必須”法,雖然它提出了科普是公益事業,各社會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都應該承擔科普責任,但是也存在“法不責眾”問題,人人都有責任,最終變成了人人都沒有責任。
當科學大眾化進入科學傳播階段后,上述問題依然存在。科學家和科研機構更加強調和追求其在公共領域的“可見性”,政府管理部門也愈加重視科學傳播的作用,但是在科學傳播中到底誰應該承擔責任依然不甚清晰。
隨著公眾參與科學的呼聲日漸高漲,為了獲得更多公眾支持和科研經費,科學家及其所在的科研機構越來越重視科學傳播,同時也應該承擔起科學傳播責任。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局的成立以及《中國科學院科學技術部關于加強中國科學院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見》的頒布,可以看作科研機構主動承擔科學傳播責任的進展。但由于科研機構和科學家從事科學傳播未被納入考核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學傳播的進展。
媒體是公眾完成正規教育后獲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同時也是非正規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因而媒體(包括新媒體)在科學傳播中也應該承擔責任。傳統上,媒體被稱為“第四權力”,即公眾把對信息進行“把關”的權力讓渡給媒體,由媒體為公眾提供及時、準確、科學的信息,但是往往媒體的議程設置和媒介間議程設置會左右公眾該想什么。然而在新媒體時代,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變得多元,信息過載和信息鴻溝同時存在,媒體更加需要在信息雜蕪時代承擔起科學傳播的責任。
科學傳播更加強調互動交流,公眾也開始根據自身需求主動檢索和獲取信息,公民意識的覺醒呼吁對科學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同時熱心科學傳播的公眾也開始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新媒體和自媒體渠道,傳播科學信息。通過科學參與和對話,使公眾融入科學研究進程,表達個人對于科學技術發展及相關問題的意見和期望,在這個過程中公眾(特別是意見領袖)也承擔一定責任。
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承擔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產品的重要責任,其中涉及技術推廣和普及,既有對企業員工的科學傳播,同時面向產品用戶進行科學傳播。社會組織也通過各種途徑發揮科學傳播作用,比如“自然大學”“自然之友”等眾多社會組織承擔著科學傳播責任。
責任的落實
科學傳播是一項社會事業,涉及多元主體的互動,而各參與主體應該相應承擔起科學傳播責任。科學傳播應從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角度系統性研究,而科學傳播責任的落實必然要求多元主體發揮各自作用,這樣才能促進科學傳播的良性互動和有序發展。這不僅給實踐帶來一定挑戰,同時在理論上也需要進行革新。
傳統上的科普將責任主要放在政府和科學共同體一方,公眾的責任就是接受,而科學傳播需要各方都發揮作用,都要承擔責任。
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為科學傳播營造良好社會環境,但不應該過多干涉科學傳播細節和具體實踐。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科學,從而贏得更多公眾支持,促進公眾樹立科學理性的世界觀,并且要在爭議性議題中及時準確地發出聲音。作為公眾獲取科技信息渠道的媒體也承擔著向公眾傳播及時、準確科學信息的責任。公民個人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成主動信息搜尋者,甚至開始生產內容(UGC),同時公眾通過參與科學(公民科學項目、公眾對話、科學咖啡館、共識會議等)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并對科學研究進程等方面施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