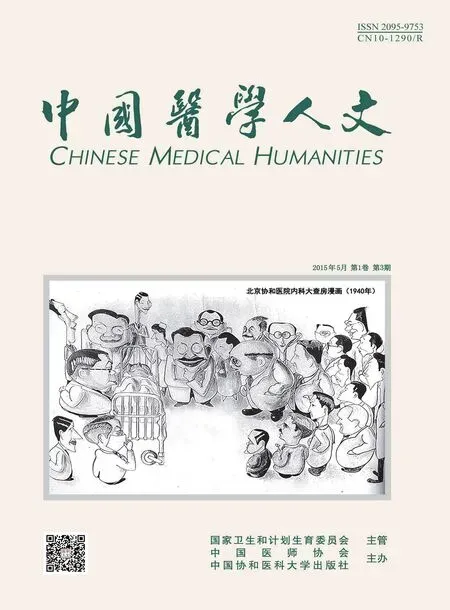一副拐杖
文/ 譚先杰
一副拐杖

前幾天一位同事尋找拐杖,說家里人要用。求助信息在微信群發酵不到半個小時,八年前我用過的拐杖居然找到了。
我使用拐杖的時間是2007年春天。
2006年9月,我受部委委派赴疆,支援新疆某醫院半年。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在那個民族地區根深蒂固,而當地醫院婦產科就我一個男的,所以在差不多半年的時間里,沒有異性同事請我吃飯或出游。而一同援疆的其他同行,隔三差五總會享受當地人民的熱情好客。
援疆即將結束前的一天,科里的民族領導對我說,很抱歉這么久都沒有請我出去玩,周末科里組織了滑雪,請我一定賞臉參加。
其實那幾天正是我每月一次才思泉涌的時候。我想在援疆結束前把荒廢的時間找回來,復印了一大堆文獻,準備趕出幾篇論文。于是婉拒,但后來提到了民族團結的高度,就盛情難卻了。
那天是周六,天氣比較陰沉。到了天山腳下的滑雪場后,科里指派一名女研究生負責我的人身安全。
我從小愛運動,拿大頂鯉魚打挺之類的是我的絕活,平衡能力也很好,之前有過滑雪經驗,所以很快就拋開她,到山坳那邊的高級滑道去了。來回滑了幾圈,有些意氣風發。
突然前方有人倒地,我本能躲閃,重重地飛了出去。我不知道翻滾了幾圈,只聽咔嚓一聲,右邊的膝蓋撕心裂肺般的痛,其余的記憶就沒有了。
整個過程大概就一兩秒鐘。后來我想,除了那句經典的“No Zuo No Die”(不做死,就不會死)之外,老天要廢掉一個人,瞬息之間可以搞定。
恢復知覺后,我的第一反應是右腿肯定沒了!一看腿居然還在,有些欣喜若狂,但試了幾次都沒能站起來。
山坳遠離了人們的視線,摔倒的人已經遠去。除了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
過了很久,我終于站了起來,拖著滑雪板,一瘸一拐向大部隊休息的地方挪動。那時候比較年輕,一是沒人可求救,二是不想求救,總覺得自己應該還行。
大概過了一個小時,大部隊的人才見到我。女研究生當場就嚇哭了(按時下的說法是嚇尿了)!我笑著安慰她,不用大驚小怪,休息一下就好了。
他們把我送回宿舍,下車時我才發現,休息了一個多小時后,疼痛不但沒有減輕,右腿完全吃不上勁了。
骨科大夫對我進行了檢查,初步診斷:右側膝關節內側副韌帶斷裂,或者手術,或者固定!我再也笑不出來了!一個月前,我剛剛貸款買了車,回北京后正好取車,而油門和剎車都得用傳統的右腿!
鑒于我身份的特殊性,當地醫院決定立即送我回京。又鑒于活動的特殊性,科室領導非常緊張,于是統一口徑,說我是在上班途中滑倒受傷。我說反正是集體活動,不如實話實說,遺憾的是,沒有被采納。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理解當地醫院的苦衷,只是隱隱有些擔心。
由于我是援疆干部,又是“上班途中受傷”,協和醫院方面當然重視。一行人經由國賓通道,捧著鮮花,從飛機上把我架了下來,還有人攝影,留圖留真相。
到醫院后緊急安排核磁共振檢查并組織會診,確診為內側副韌帶部分斷裂。穩妥起見,不使用現代的輕便支具,仍用傳統的石膏固定。有時候我在想啊,對于醫療這個特殊行業,貴賓享受的,是最貼心的服務和最燦爛的笑容。至于治療方案,雖然是最最保險的,卻未必都是最優選的。
醫院特別從中醫科調配出一張床。領導和同事們先后前來看望,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當地醫院院長專程前來探望。領導們親切問候,同事們強烈安慰。只有一位同事幽幽地說:你這條腿完了,我們在兔子身上做過實驗,只要關節被固定一周以上,肯定得骨性關節炎! 忠言,的確逆耳啊!
科里的教學秘書給我送來了一副木制的雙拐,恭喜我榮任它的第二任主人,說前任是一位髖關節受傷的同事。晚上我試著撐著雙拐上廁所,但極其不熟練,差點兒就摔進了坑里。
次日我被救護車送回家,同事們連扶帶抬把我弄上六樓。兩天后,拐杖的首任主人送來一張可以在沙發上寫字的折疊桌。她說桌子很好用,但她用過的已經臟了,就去家具店買了個新的。
一位前輩還給我送來了從新西蘭帶回來的小毛毯,她說春天咋暖還寒,可以蓋住膝關節保暖。這位以嚴格和嚴厲著稱的前輩,幾個月前曾因收治病人的問題劈頭蓋臉罵得我差點還嘴。
之后的半個多月,由于下樓很不方便,我幾乎足不出戶,成了名副其實的“宅男”。說實話,我不喜歡這副笨拙的拐杖,能不用它,就不用它。
人只有失去了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從那以后,我對街上乞討的殘疾人,或多或少都會給些零錢。有人說他們是故意示傷騙錢,但是我想,殘疾和不便總是真的。
同事們一撥撥到家里來看我,聊的都是科里的舊事和趣事,一聊就是一晚上。盡管如此,那段時間還是很漫長。我沒有像剛受傷時計劃的那樣借機惡補一輩子讓人肝腸寸斷的英語,也沒有心思繼續寫已經構思好的論文,而是自學視頻編輯。我給夫人錄了一段像,用蒙太奇的手法剪輯到一名清涼模特所做的廣告中。遠看和背影是人家模特,轉過身就是敝家夫人。
那時科里每年舉行春節聯歡晚會,每個病房要出演一個節目。婦產科的人都很有才,節目的內容和創意往往會在國家級春節聯歡會上原音重現。我曾經是編故事的人,這次卻成為了故事里的人。
在同事們口中,我受傷原因的版本不下10個。最為傳奇,而且大家樂于接受的版本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到某年輕女性家中“國事訪問”,不幸時機沒把握好,跳窗出逃,腿摔斷了!還有一個大家同樣樂于接受的版本是,我去追一名高挑的美女,由于步幅比人家短,只好加快頻率倒騰,一著急,腿摔斷了!
這幫家伙還準備把諸多版本搬上聯歡會舞臺,名曰《腿是怎樣摔斷的》。不巧被總支書記緊急叫停,說不能把歡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其實,書記哪里知道,對于喜歡編排同事的我,豈會介意這些調侃?!
其實我更介意的,是受傷的真實原因!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墻。
我的介意是有道理的。兩年之后晉升正高職稱,我沒有因為援疆被加分,反而由于真實受傷原因被質疑而擱置一年。回頭看來風輕云淡,怨恨不再,但當時還是要求當地醫院寫了情況說明。當然,不可能改變結果。
打石膏的最后幾天,我的用拐技術已經爐火純青,不僅可以自由下樓,還去了菜市場和書店。我甚至有些相信,金庸筆下那些使用雙拐的武林高手,功夫真的可以出神入化。那段時間,我都有些喜歡這幅拐杖了。
然而不幸的是,如那位忠言逆耳的同事所言,拆除石膏后,我的右膝關節完全僵硬,稍微彎一點就會鉆心的痛。
最初的功能鍛煉異常艱難,沒有任何進展,我仍然需要借助雙拐才能上下樓,甚至不如解除石膏之前。我開始厭惡拐杖,看見它就煩,但又不得不用。
那段時間我幾乎崩潰。我一直認為,無論環境多么惡劣,只要身體好,我就能活下去,但現實卻如此殘酷!我打電話給骨科同事,得到的是科學而現實的回答:不行咱就再手術?!
老師郎景和主任建議我去物理治療科看看,當時理療科的主任是我師母。她和風細雨和我談了一個小時,舉了若干個熟悉的人的例子,目的是讓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回到傷前狀態,還親自給我示范膝關節功能鍛煉的關鍵動作。
看到從無戲言的師母如此堅定,我的天空終于有些放晴。后來,在與病人的交流中,如果需要,我都會堅定鼓勵,盡管我轉身會向家屬說明實情。當了病人之后我才知道,有些時候,病人最需要的是醫生毋庸置疑的安慰和鼓勵,甚至比藥物還管用!
我開始了正規的功能鍛煉,一點一滴,每天都有進步。終于,半個月之后,我可以不用拐杖上下樓了。再過了半個月,我差不多行動自如。但其實影響還是很大,現在受涼或勞累后,一站起來膝蓋就會疼痛,要靠止痛藥鎮壓。爬山之類的運動,只好被迫減少。至于滑雪滑冰之類,聽著我就腿疼。
丟掉拐杖之后沒有幾天,教學秘書說一位同事的媽媽受了傷要用拐杖。我歸還拐杖時開玩笑說,讓同事媽媽用完之后把拐杖扔了吧,這樣會更吉利些,否則還會有人接手。的確,拐杖的后任主人至少有4位。
其實我當然知道,就如得病一樣,誰都不想得病,但并不是繞著醫院走就會不得病。沒有人愿意受傷,但總會有人受傷。
是啊,拐杖不美也不招人喜歡,但卻能給需要的人提供幫助。
/ 北京協和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