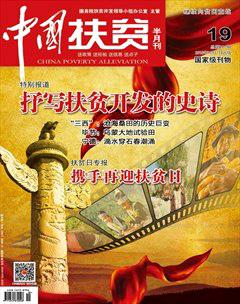滄海桑田的歷史巨變
馬麗文
“三西”扶貧今年32歲了。
“三西”是六盤山所處的寧夏西海固,與甘肅定西、河西的合稱,這里曾是中國最貧窮的地方之一。“三西”的窮,就窮在一個“旱”字,春播一粒麥,秋收一棵草。
什么叫窮?
“住的是窯窯洞洞,手拿的是放養棍棍,吃的是糠菜皮皮,穿的是稗草蓑衣。”
1982年底,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國家啟動“三西”扶貧開發計劃,首開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先河。自那時起,“三西”人民以“領導苦抓,社會苦幫,群眾苦干,以苦為樂,變苦變甜”的“五苦精神”,展開了一場歷時30多年的反貧困斗爭。
32年時過境遷,這塊千百年來被饑餓和貧困折磨的土地,真的變了。
也許,在世人眼里,“三西”扶貧開發之路是奇跡、坎坷與創新之路,而對于在這條路上奉獻過畢生精力和苦苦掙扎過的幾代“三西”人來說,這條路就是他們的人生。
記憶:干旱與饑餓
井干窖枯河斷流,
渴的麻雀喝柴油。
水吆……水吆……
老天爺……下點雨吧!
——隴原小曲
關于32年前的“三西”,人們這樣描述——
“鍋里沒糧,灶底沒柴,缸里沒水,身上沒衣,那才叫真窮。”
“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飯,天要下些雨就能吃飽肚子,天要不下雨就純粹沒有,只靠國家的供應糧。”
“十年九旱,困難啊,實在沒法形容。”
“全家只有一條爛棉被,冬夜里,七口人要睡成一個扇形,每人才能蓋上個被角兒。”
“一家五口人,窮得只有兩個碗。”
“穿的是黃衣服,吃的是救濟糧,喝的是泥湯湯,住的是茅草房。”
……
這是30多年前“三西”普通老百姓的真實生活寫照,他們飽嘗苦難卻無以言說,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對于這些生活在這一貧困地區的人們來說,山水已無從依憑,以定西為代表的甘肅中部干旱地區在1980年初,80%的人口缺糧半年以上,每年從省外調運救濟糧12億斤,人缺糧,畜缺草,人畜都缺水,構成了全國最大的貧困片帶。解決“三西”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已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
干旱與饑餓,至少是三代“三西”人的共同記憶。
20世紀70年代初,定西連旱3年,群眾衣食無著,紛紛扒火車逃荒。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聞訊后潸然淚下。他心情沉重地說:“我們一定要幫助那里的人民,扶持那里的生產,一定要把那里的貧困面貌改變過來。”很快,國務院8個部委組成的工作組來到定西,帶來大批救濟糧、救濟款。
機遇:困頓無著中迎來希望
“喝一口泉水潤一下嗓,
放聲唱,青山綠水的地方。
揉一下眼睛仔細望,
好風光,人世間賽過天上。”
——寧夏“花兒”
1982年底,為了徹底改變“三西”地區的貧困落后面貌,黨中央、國務院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決定把河西地區的農業綜合開發,和以定西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區、寧夏西海固地區的扶貧開發結合起來,成立了國務院三西農業建設領導小組,確立了興河西之利,濟中部之貧,有水走水路,無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和三年停止破壞,五年解決溫飽,兩年鞏固提高的扶貧戰略方針,開展了建國以來第一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跨區域的三西農業建設,改變了過去單純的臨時性救濟式扶貧方針,首開了全國區域性扶貧開發先河。
事實上,無論水路、旱路,還是另找出路,無非就是找一條活路。
于是,在窮山惡水間掙扎的“三西”人,憑著一只鐵锨、一把镢頭、一輛架子車,開始改變著命運。
甘肅探索治理水土流失新路子,緩坡耕地連片修梯田,陡坡耕地棄耕種草,荒山挖反坡梯田種草種樹,通過改革爐灶,供煤植薪,建沼氣池,推廣太陽灶等措施,從根本上建立遏制生態環境惡性循環的小流域綜合防護體系。
寧夏先后實施吊莊移民、揚黃灌溉工程大型移民區、國家易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中部干旱帶縣內生態移民工程,使百萬群眾搬離或正在搬離自然條件惡劣地區,開啟了貧困群眾幸福的新生活。“老家十年九旱,記得1982年全年幾乎沒降水,土地泛著白色,沒一棵綠草,牲口80%都渴死了。”從隆德縣搬到吳忠市紅寺堡區新莊集鄉楊柳村的馬國珍說,想想過去,西海固移民總能說上一段貧窮的辛酸往事。
30多年來,在甘肅中部地區以莊浪縣廣大干部群眾為代表,堅持不懈地開展以興修水平梯田為中心,以酷暑嚴寒嚇不倒,貧窮饑餓壓不跨的精神,征山不止,治水不休,終于將中部總耕地面積90%以上的土地建成水平梯田,數量達2104萬畝,1000多萬甘肅人用體力和意志進行了一場改造山河的壯舉。
如今,莊浪變了,昔日的梯田大縣正在向產業大縣轉變。
9月初的莊浪,很是壯美。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山頂沙棘戴帽,山腰梯田纏腰,地埂雪草鎖邊,溝底壩庫穿靴。”站在莊浪縣萬泉鎮邵坪塬的最高處向四周望去,滿眼盡是綠白之色,綿延的梯田宛如巨大的五線譜,在千溝萬壑中勻稱地展開。據莊浪縣扶貧辦主任徐克杰介紹,綠色主要是蘋果樹,白色主要是地膜玉米和地膜馬鈴薯。近年來,縣委縣政府加快推進由梯田大縣向產業大縣轉變,扶貧產業初具規模,形成了“南部果菜,北部畜薯”的格局,曾經水土流失嚴重的溝壑變成了效益綠溝,植被破壞嚴重的荒山禿梁變成了金山銀山。
今日的西海固,流青溢翠。滿目荒山變綠山,居者有新屋,耕者有良田,目睹一個個移民新村新變化的同時,“三西”人也見證著這一宏大而系統的扶貧工程背后的勇氣和決心。鄧小平同志曾說過:“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子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三西”扶貧工程的實施,就是憑著一種勇于探索的精神闖出來的,憑著一股奮起直追的勇氣攻堅克難得來的,更是憑著苦干實干干出來的。
轉身:脫窮皮 挖窮根
“牡丹的骨朵努嘴哩,
努嘴是有希望哩。
尕妹的眼睛里有水哩,
笑眼里是有指望哩。”
——三西“花兒”
天不能改,地能換!
脫貧的關鍵,往往在帶頭。30多年來,一個又一個帶頭人的傳奇故事,在“三西”流傳。
先說說年輕的一代,今年33歲的祁國梁是定西市通渭縣襄南鄉祁堯村村委會副主任、國梁農牧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平日里,村里人總喜歡稱他為“祁北大”,年少時的祁國梁品學兼優,懷揣北大夢,復讀數年,非北大不上。而立之年,為改變家鄉的貧窮面貌,祁國梁放棄高薪職業,回到家鄉,自立自強,大膽創業,帶領村民調整種養結構,切實幫助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在偏僻的荒山里播下致富的種子,在平凡的崗位上兢兢業業,無私地奉獻著自己的力量。
2013年以來,祁國梁充分利用政府扶持養殖業和雙聯貸款的有利時機,利用自己的承包地和流轉村里9戶村民的土地建設養殖場,投資600萬元,成立了通渭縣國梁農牧業專業合作社,在引進良種羊500只的基礎上擴繁羊存欄達1200只,推廣良種羊800只,年收入達60萬元,有效解決全村勞動力100多人,讓老百姓實現了家門口就業、增加經濟收入的愿望。
“一人致富不算富,帶動幫助更多人共同致富,才是我最高的理想和追求,也是我人生價值的最好體現。”祁國梁對記者說。
一個人富了,可以帶動一群人。而要想富,教育需先行,窮怕了的“三西”人,將讀書的信念融入血液,即使破爛的土坯房,門前也要寫上“耕讀第”——耕和讀,這是中國農民心中最為神圣的兩件事:耕作,一年之事;讀書,一生之計。讀書,是“三西”人的出路,更是希望。在通渭縣流傳著這樣的老話:家中無字畫,不是通渭人。在全國聞名的書畫之鄉甘肅通渭,沒有比讓孩子成為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事。
秦安縣劉坪鄉任吳村的果樹“土專家”吳王生,在2001年9月以乒乓球投票方式,向村里投出的第一個大項目就是建學校,大力發展教育。71歲的吳王生沒念過一天書,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他卻通過苦學苦干掌握了林果栽培技術,成為了村里遠近聞名的“土專家”。
任吳村位于秦安縣東部,屬淺山干旱區,農業生產主要以果品生產為主,林果產業是村里的支柱產業。然而,林果產業的發展,從注重產業規模,到更看重質量;從唯產量是從,到向產量要效益,是吳王生這樣的普通老百姓致富觀念轉變的最真實體現。在吳王生看來,每一顆果樹,從小樹苗開始,就需要進行精細化、標準化管理,比如有的果園在果樹行間套種了地茅草,因為它生長期間可以幫助疏松土壤,腐化以后還可以作為果樹很好的有機肥。在秦安,很多村民和吳王生一樣,林果管理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幾年來,通過整村推進項目的實施,任吳村的農業生產生活條件發生了很大改善,產業結構得到了合理優化,優質果品得到了大力發展,產業鏈條得到了進一步延伸,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比1982年的96元增加了近51倍。吳王生告訴記者:“現在1畝蘋果收入等于過去10畝的玉米收入,我今年種了10畝蘋果,預計收入20多萬,現在的生活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家家戶戶有了私家小汽車,種地種果全都是機械化、現代化,日子越過越有奔頭了。”
說起今年剛考入清華大學的孫子,吳王生笑得合不攏嘴,“村里的第一個清華哪,沒文化是不行的。吃不上飯,也得讓娃娃們上學,這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
村里富了,生活條件改善了,71歲的老人仍不敢懈怠。“說不定哪天我就走不動了,得趕緊打出自己的蘋果品牌,鼓勵村里成立果農合作社,建一個冷庫,再建一個物流中心。”期盼和堅毅的信念在吳王生的目光里閃動,為的是子孫后代徹底阻隔貧窮,將幸福延續。
“三西”人的致富路越走越寬,擴充的不僅是產量和腰包,更是思路和眼界。
從小小的土豆(馬鈴薯)出發,讓定西人有了現代農業和產業化的概念,更有了市場經濟的思維。自1996年始,定西馬鈴薯種植面積逐步擴張,近年來穩定在300萬畝以上,成為全國三大馬鈴薯集中產區之一和全國最大的脫毒種薯繁育基地。全市目前每年能加工馬鈴薯淀粉35萬噸,能培育種薯3600萬粒,能貯藏300萬噸。
小土豆創出大產業,定西的扶貧攻堅由此發生重大轉折,土豆成了“金蛋蛋”,一躍成為定西具有代表意義和獨特優勢的支柱產業之一,更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2008年,定西市又開始打造“中國薯都”。借此,定西市馬鈴薯產業步入科學化布局、集約化種植、標準化生產、精深化加工、品牌化營銷的新階段。曾經毫不起眼的“救命薯、溫飽薯”,現在正承擔著“脫貧薯、致富薯”的重大使命。目前,定西市農民人均從馬鈴薯產業中獲得的收入達1050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1%。
與此同時,更加令人興奮的是,2015年8月6日,引洮工程,這一甘肅歷史上最大的跨流域調水工程,宣告一期工程正式運行。早在20世紀50年代,甘肅就提出了引洮河水到中部地區的設想。但囿于當時的技術和經濟條件,1958年,第一次引洮工程啟動后很快以失敗告終。2006年,引洮工程再啟,經過8年艱苦奮戰,定西人民翹首企盼了半個多世紀的“圓夢工程”,終于實現了。
無論是苦干,還是巧干,找到破解貧困的路徑和方法才是智慧,定西人的觀念在變,思想在變,思路也在變,不變的是對脫貧致富的不懈追求。30多年來,定西貧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萬人下降到2014年底的63萬,貧困面從78%下降到23.6%,農民人均純收入從當初的105元提高到4600元。
同樣,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人,卻不再是原來的人了。
在西海固移民區,政府將產業培育作為大事來抓,因地制宜定方向,優惠政策做引導,資金技術給支持,一些移民區的產業也已漸成氣候。
如今,吳忠市紅寺堡區的釀酒葡萄產業初具規模。曾經,紅寺堡區嘗試的產業不少,但效果多不明顯。直到2007年,確定發展高效節水葡萄產業,并引進酒廠就地消化葡萄,紅寺堡才有了真正能挺起腰桿的“鐵桿莊稼”。但是,嘗試新產業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移民往往有顧慮。對此,紅寺堡區為農民種植葡萄開出了“誘人的禮單”:實行免費開溝、免費供苗、免費架絲、免費架桿、生活給予補助的“四免一補”政策。
李彩霞就是因種植葡萄產業受益的其中一人,3個孩子都在上學的李彩霞家里負擔很重,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在寧夏天德葡萄種植有限公司的帶動下,李彩霞將36畝土地流轉給公司種植釀酒葡萄,自己在葡萄園打工,年收入達2萬元。“以前買雙襪子,都得伸手向老公要錢,現在老公還得跟我要錢花。”自己賺錢了的李彩霞自豪地說。
攻堅:改革創新 向內而生
2015年9月19日 農歷八月初七星期六 晴
今天是愛妻歸真的日子,多想到她墳前看看,也讓她看看我。可是顧不上啊,愛妻離開我和孩子快三年了,每一個主麻日,每一個月齋,女兒都在家里請阿訇為她祈禱,然后再去老家給她上墳。但我總是忙工作,顧不上親自祭奠她,只能把對她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
今年除了移民工作,又多了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扶貧開發工作。任縣扶貧辦主任已經有半年時間了,有些工作還沒有新的局面,移民工作舉步維艱,天天都有群眾來訪,電話不斷,說句掏心窩的話,我特別著急。
只要一到移民村、移民工地,不知怎么回事,就是不知道餓,不知道累。農民從能夠吃飽肚子,穿一件新衣服的欲望開始,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也就越來越高了,我們的工作標準不能永遠定位在讓農民吃飽穿新上,要讓他們活得更加有尊嚴,活得更加有幸福感,就要撲下身子帶著他們干。把全部的心思用到工作上,忙一點,苦一點,活得就充實,實實在在干一點事情,大家雖然嘴上不說,但心里是很清楚的。我想,移民和扶貧工作將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次遠行,直到生命終結的那一天。
活一天,就要努力學習一天;組織讓干一天,就要踏踏實實干好一天。永遠保持頭腦清醒,永遠保持一身正氣,規規矩矩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勤勤懇懇為民。生,不能讓老百姓叫賊;死,不讓老百姓留罵名。
——同心縣扶貧辦主任馬希豐日志摘錄
馬希豐的網名叫“我是小草”,從上世紀70年代起,他就堅持寫日志,在網上開博至今,已寫下600多萬字的移民博客。目前,該博客點擊量累計超過200萬次。翻開他的所有日志,記錄的全都是移民和扶貧工作。
在網絡世界里,這部漸漸成形的“移民史記”的背后,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同心縣移民開發歷史畫卷。幾十年如一日,在馬希豐心里深深留下的印記,一定是那些生態條件極度惡劣的村莊,他清楚的知道走馬高莊鄉壕前門村的路有多難,去王團鎮白土崾峴的山有多險,田老莊鄉席家井、席家山遇到下雪進不去,鄉親們要與外界隔絕20多天……
2006年,一份調查顯示,同心縣以馬高莊、田老莊等干旱山區里,還生活著13萬貧困人口,農民人均純收入1300元左右,不足全區平均水平的1/3。如何讓貧困群眾從根本上拔窮根?
2007年,按“人隨水流,水隨人流”的思路,同心縣大膽實施縣內生態移民工程,用5年時間,把全縣居住在干旱缺水的3.13萬戶13.3萬人,搬遷到靠近水源的地方,從根本上解決貧困、恢復生態。“生態移民這個新名詞在同心首先提出來,得到了自治區認可。”馬希豐說。
然而,生態移民搬遷是個難事,老百姓知道住在干旱的荒山沒有發展前途,也知道生態環境的脆弱已經到了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地步,但故土難離,世代居住在這里的人們從感情上難以割舍。為了動員大家搬遷,馬希豐幾乎挨家挨戶和村民拉家常、算經濟賬、講政策、談未來,一趟不行跑兩趟、三趟。除了搬人、拆房,遷出區還有大量墳頭,埋的都是移民們的先輩,這些也需要遷移,但這是老百姓的感情所系,搞不好就要鬧矛盾。馬希豐實地查看了全部移民區的1200多座墳,悉心協調涉及到的人和事。
十多年來,馬希豐心里裝的最多的,就是移民群眾的利益。每個移民村搞基礎建設時,他都與工程承包方在合同中約定,工程用工必須用移民中的打工者,爭取讓移民一搬來就能掙錢。
馬希豐告訴記者,同心縣人命運的改變,始于2009年6月15日的萬人搬遷。
那一天,天蒙蒙亮,崎嶇的山上,上千輛農用車載著家當向著移民新村集結,上萬名村民扶老攜幼揮別故土,走出大山……追憶難忘時刻,馬希豐眼角有些濕潤。
萬人搬遷只是同心縣30年移民史畫卷上的一個片斷,而生態移民,從同心首創到經驗推廣,從產業配套,再到讓移民端上“金飯碗”, 同心人幸福得像花兒一樣。
2013年1月,寧夏潤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同心縣安溪同德移民新村開始建枸杞種植生產基地,流轉土地7500畝種植枸杞,年產800噸,預計2017年將達2000噸,枸杞產品出口歐洲等地,輻射帶動全村1379戶移民增收,公司還按每5年每畝土地增加流轉費100元的標準與移民簽訂25年的土地流轉合同。公司董事長郭嘉告訴記者:“我敢保證,這個村以后將是全縣收入最高的村。現在,村里的發展大戶每年能掙到10萬元,到2017年,這個村人均純收入將達到1萬元以上。”
生態移民之于同心來說,不僅是一場扶貧攻堅戰,更是一場改變形象的翻身仗。
30多年,是誰,改變了大地的容顏?又是誰,帶來了幸福的甘泉?
是一批又一批像馬希豐一樣的扶貧人,默默奉獻著自己的畢生精力,是一雙雙有形和無形的手,牽起“三西”千萬老百姓的雙手,扶起了定西的馬鈴薯產業、靜寧的蘋果產業、紅寺堡的葡萄產業、同心的枸杞產業……是他們,讓“三西”發生著美麗的嬗變。
如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三西”打響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攻堅戰,邁上了與全國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的新征程。但是,“三西”仍然是一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三西”的扶貧征程,仍然是路也迢迢。
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發生。相信,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下,在“三西”人民的艱苦奮斗中,”三西“一定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征程上,再譜扶貧攻堅新的壯麗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