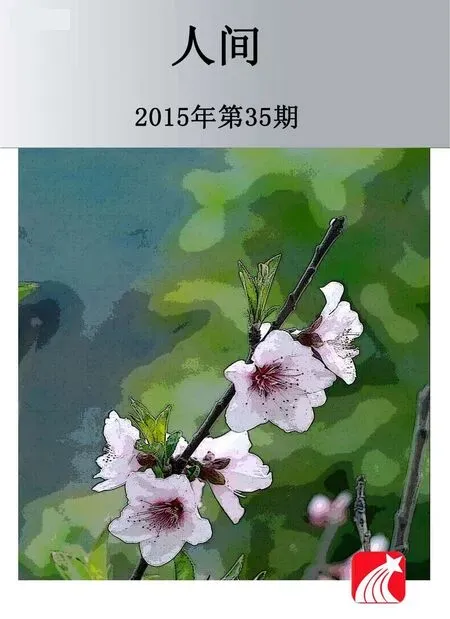用問題推開一扇窗
——讓學生在問題中享受語文
劉影珍
(四川省安岳縣啟明學校,四川 安岳 642350)
用問題推開一扇窗
——讓學生在問題中享受語文
劉影珍
(四川省安岳縣啟明學校,四川 安岳 642350)
享受思考的成果,更是在享受思考的過程,這是語文學習的最高境界。試想,當學生不再有枯坐冷板凳聽教師喋喋不休的無聊,不再有絞盡腦汁猜測所謂標準答案的無奈,當思考成為一種習慣,當閱讀成為一種對話,當表達成為一種傾訴,這就是語文帶給我們的樂趣。
問題設置;享受思考;享受語文
語文課堂的問題設置,最忌諱那些大而不當的問題,在學生的思維還未進入理想境界,提高的時機尚未成熟之際,就匆匆忙忙地提出一些較深奧的,帶有研究性質的問題,這自然很容易讓學生的思維陷入一種茫茫不知所以然的境地。同時,語文課堂提問也應杜絕那些“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的提問法,為提問而提問,提出一些滲離于課堂主題之外的小而瑣碎的難題,讓學生在一個個無聊的問號前疲于奔命而又難以實現思考的價值,這些問題也會使課堂陷入一種龐雜而無序的混亂狀態。理想的課堂提問應該是深與淺,遠和近的最佳結合,即問題應該有趣味性,挑戰性而又有充分的延展性。
我們可以嘗試以下的幾種提問方式:
一、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品的文學價值,是由讀者在閱讀鑒賞過程中得以實現的。任何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具有它的多義性,換言之,都如斷臂維納斯,有一種殘缺的美感,所以學生的閱讀鑒賞,既同文體對話的過程往往帶有更多的主觀性和個人色彩,對一部作品的解讀過程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每一個人的解讀都有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不僅表現對作品意義的認識,對人物的評價,還表現對語言材料所構的意象,意境的感受上。可以說,正是語言的這種“模糊性”和讀者的“創造性”,才使得枯燥簡單的語言變得如此神奇而富有魅力。所以教師絕對不能過早地拋出所謂的“標準答案”,而應該及時地設疑質疑,于無疑處生疑使學生在不拘泥于那些權威答案的基礎上能再推開一扇窗子,讓學生看到更美的風景。
例如,學習李白的《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時,名句“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就是把我的懷念托付給明月,讓它隨風伴你一直到遙的西南邊地,其中說到“明月”可以進一步提出問題,是否用了修辭手法,當然,無可非議,“把明月人格化了”但是我還不滿足于此,非要追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于是就進一步提出能誘發學生發散思維的問題:在以前,同學們是否學過“借明月”抒情的詩句呢?學生思考后說出了很多相關的名句,此時學生的思維不是足限在課本之中了,而是給學生打開了另一扇閃爍的大門。
二、橫看成嶺側成峰
教師既是與學生平等的對話者,又是課堂閱讀活動的組織者。因此在課堂提問時,也應抓住有利的時機,濃墨重彩讓學生根據自己的閱讀體驗,人生經歷等,進行個性化的解讀,將課內和課外和諧地融為一體。
比如在學習《期行》時,學生認為“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元方這樣做是否失禮。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有學生認為:元方失禮。他批評友人無理,自己更應做到有禮待之,而另外的同學卻認為:不失禮,友人失約在先,是無信;友人罵元方之父,是無禮;對七歲的孩子不應求全責備。兩種解讀,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據,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三、不畏浮云遮望眼
教師要主動創建一種開放的課堂結構。即在課堂上鼓勵學生自由組合,各抒已見,大膽討論,上臺陳述,要為學生的閱讀實踐創設民主的環境。提供自主條件,既要充分關注學生閱讀的主動性,閱讀需求的多樣性,閱讀心理的獨特性,更要高屋建瓴,敢于率先打破傳統,走出思維定勢,以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進一步“逗”起學生探究的熱情,讓他們能“仰而彌堅”,越堅,鉆得越起勁;“鉆而彌深”,越深就越鍥而不舍,充分享受鉆研思考過程的樂趣。
教《賣炭翁》時,讓學生盡情想象、發揮,賴以糊口的炭被搶走之后,賣炭翁會怎么做呢?他回家后怎么說呢?他的家人又會怎么說呢?他家以后的生活怎么樣呢?這就要求學生必須發揮創造性才能完成。而爭強好勝,樂于創造,勇于求新,正是初中學生的心理特征。所以對這樣的練習他們是很有興趣的。這些課堂練習,既有利于學生熟悉課文,又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口頭表達或寫作能力,還有助于發展他們的思維能力。經驗證明,學生對這種富有創造性的練習具有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真閱讀,積極思考,踴躍發言,課堂氣氛十分活躍。
四、山色空蒙雨亦奇
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挖掘教材中的“趣味因素”和“情感因素”,滿足學生好奇的心理需求。培養學生對語文本身的興趣,而語文課堂上教師如果能適時拋出一些“虛擬性”的問題,如“替換式”,給文章換一種表達,換一種構思“延伸式”讓學生續寫或補寫作品中省略的部分;“刪削式”,故意拿掉文本的一個或幾個片段;用這些“虛實結合”的方法給學生提供一些新穎的思維角度,一個嶄新的思維平臺,就更能讓學生體驗到語文的創新活動帶來樂趣,而當這種樂趣不再來自教師的表揚,而是學生發自內心創新成功后喜悅時,也就是學生創新情感形成之時。
在學習《木蘭詩》時,在理順文章的思路,簡析了詩的含義后,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請問如果花木蘭父親還能上戰場,花木蘭是否還會替他父親從軍?這個“虛擬性”的問題出現,立刻“挑”起了學生興趣,課堂氣氛隨之達到高潮。學生分為兩大陣營,一方認為他會替父親從軍必定父親已上高齡,在軍營時一定會吃不消,況且木蘭也對父母很孝順,他不忍心讓父親吃苦,所以他一定會代父從軍。而另一方同學則認為:不會,因為這是會犯欺君之罪,會給全家帶來殺身之禍,以及名門掃地的慘狀。
原作固然是有無窮魅力,假設的情節又激活了一個個體對原作的分析,真所謂“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五、動人春花不須多
語文教學講一個“拈”的工夫,即洪鎮濤老師所云:“全盤授予”為“拈精取要”,教師拈的好,拈出一點,帶出一個面;拈一葉而知天下秋,拈出一樹梅花,帶給學生的卻是整個春天。在學生常常忽略的文句中拈出重點,拈出矛盾,這樣駕雙課堂就能舉重若輕、游刃有余。比如學習魯迅寫的《風箏》拈出“風箏”兩字為線索。初一下冊的《白鵝》拈出“傲慢”,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拈出“詠雪送別”就能牽一發而動全身,綱舉目張,即所謂“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花不須多”。
綜上所述,適時適度、而且富于藝術技巧的提問,能加快把知識轉化為語文能力訓練的過程,更能激活學生的思維,從這扇窗里窺探廣闊的知識,在這種藝術中充分的感受語文,享受語文。
G64
A
1671-864X(2015)12-008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