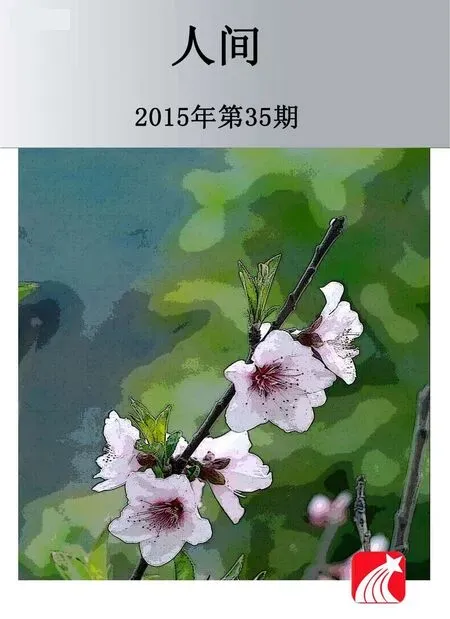淺析近年來日語借詞對漢語的影響
吳晶霞
(天津外國語大學,天津 300204)
淺析近年來日語借詞對漢語的影響
吳晶霞
(天津外國語大學,天津 300204)
中日兩國詞匯交流史源遠流長。提到日語借詞,人們往往想到的都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第一次日語詞匯借用高潮,關于第一次借用高潮的研究迄今已有大量成果問世,且中日兩國均已形成比較穩定的研究群體。實際上,近年來漢語也吸收了很多日語借詞,并且這些詞匯中有很多作為流行語正在被人們頻繁使用。在本文中,筆者將就近年來日語借詞在裝飾性作用、詞素化等方面對漢語的影響展開論述,并就日語借詞濫用的現象表達自己的看法。
日語;漢語;借詞;影響
中日兩國間的詞匯交流歷史悠久。在古代,日語從漢語中借用了大量詞匯,而到了近代以后,漢語從日語中借用的詞匯數量也相當龐大。我們認為,歷史上漢語從日語借詞共有兩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第二次是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0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并且,近年來隨著網絡的普及與發展,漢語又吸收了很多日語詞匯。在本文中,筆者將分別就近年來日語借詞對漢語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展開論述。
一、漢語中日語借詞的詞源
日語中的漢語詞匯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一)由古漢語傳入日語且詞義未被改動的。
(二)由和語詞匯改造而成的漢語詞匯。
(三)利用漢語的造詞規律創造的詞匯。
這主要是指從明治維新開始,大量外語涌入日本,使得日本人在翻譯時陷入無詞可用的境地。于是日本人利用漢語造詞規律創造了大量的漢語詞匯。
(四)取自中國古典但在日語中詞義發生改變的詞匯。
比如“政治”這個詞,“政”主要指國家的權利、制度、法令等,而“治”則是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政治”往往指的是君主和大臣們維護統治、治理國家的活動。現代漢語中的“政治”則是取自于日本人翻譯西方語言時創造出的“政治(せいじ)”一詞,它指的是有關國家及國家權力作用的人的各種活動。
二、日語借詞的裝飾性作用
前面提到,歷史上漢語從日語借詞有兩次高潮,這兩次高潮的產生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傳統的漢語已無法表達很多新事物,需要從日語當中借用大量詞匯以填補空白。近年來的一些日語詞匯的借用也是出于這樣的原因,不過也有許多事物在漢語中已有詞匯可以表達,借用日語詞匯只是為了追求時尚或是新鮮感。在這里,筆者將近年來的日語借詞分為以下三類。
(一)直接引用,詞形和詞義都無變化的日語借詞。即說不改變日語借詞原有的詞形和詞義。比如,“料理”這個詞,在漢語中“料理”原先有以下三種意思:第一是“照顧、照料”,第二是“安排、處理”,第三是“指點、教育”。而近年來,大街小巷的許多餐館的招牌上都出現了諸如“日本料理”、“韓國料理”甚至“中國料理”的字樣,這里的“料理”就是借用了日語中的“料理(りょうり)”一詞。其實其表達的意思和日語中的一樣,即“烹調;菜肴”。漢語中的“菜肴”一詞完全可以表達,但使用“料理”一詞卻顯得很時尚,更能夠引人注目。
(二)對日語詞匯詞形進行改造而形成的日語借詞。在漢語從日語借用詞匯的過程中,有些詞匯若直接引用,僅從字面意思難以理解。因此,人們對其進行了輕微的改造。比如“宅急送”一詞源于日語中的“宅急便”,日語中的“便”有“輸送、運輸”的意思,而漢語中卻沒有。因此如果直接使用“宅急便”一詞會不太方便,于是人們對這個詞進行改造,變成了“宅急送”。
現在隨著網絡的普及與發展也誕生了很多網絡詞匯,這其中也有對日語詞匯進行改造而形成的日語借詞。比如“食草男”一詞,這個詞源自日本,在日語中叫做“草食男子”,這里的“草食”就是“草を食べる”,即“吃草”。由于在日語語法中賓語在謂語之前,所以出現這樣的表達方式。但在中文里則恰恰相反,因而經過改造之后的“食草男”更符合漢語的語法規則,更能被大眾所接收。
(三)詞義發生變化的日語借詞。還有一部分的日語借詞雖然詞形未發生改變,但詞義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比如“人間蒸發”這個詞,借用的是日語中的“人間蒸発”。雖然兩者大致意思都是“消失了,不見了”,但實際上是有區別的。日語的“人間”是“人”的意思,所以“人間蒸発”表示的是“人不見了”;而漢語的“人間”是“人世間”的意思,所以“人間蒸發”表示的是“從人間蒸發”。
三、日語借詞的詞素化
如剛才所論述的那樣,近年來傳入我國的很多日語借詞在人們的改造下更加符合漢語的語言規范,這也方便了其更快地融入漢語中,人們也可以更靈活地使用這些日語借詞。在這其中,有一部分日語借詞已經形成了詞素。
比如日語“お宅族”中的“宅”這個詞就已經成為了漢語中的詞素。近幾年來人們常常可以看到“宅男”“宅女”“宅一族”等含有“宅”這個詞的說法。
現代漢語中經常提到的“族”這個詞也借用了日語。雖然漢語的“族”本身就帶有“有共同性的團體”的意思,但在使用時往往都是指“民族”“種族”等具有親緣關系的群體。而日語中的“族”所指代的范圍更大。近年來受到日語的影響,漢語中“族”的意思也開始擴大,“打工族、有車族、追星族”等帶有“族”這個詞素的詞匯屢見不鮮。
四、日語借詞的濫用
日語借詞的大量使用確實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增添了許多趣味性,但筆者認為日語借詞的濫用不可忽視。我們知道,在日本,隨著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大量新鮮事物涌入日本,日本人面對也很難再像明治維新時期那樣創造漢語詞匯來表達這些新鮮事物,因而產生了很多的外來語。這些外來語僅僅考片假名來記錄發音,從字面無法判斷其意義,且數量過多,變化又快,因此較難理解和記憶。筆者認為日語借詞過多也會導致這種情況,比如“蘿莉”“御姐”“耽美”這一類的詞匯,如果僅從字面很難理解其意義。
誠然,兩國間詞匯交流是好事,如前面論述的那樣,近年來的大量日語借詞對漢語起到了很好的裝飾作用,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式,這確實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但凡事都有“過猶不及”的原則,因此對日語借詞濫用的現象也當有所警惕。這樣才能營造更好的語言環境,更加利于中日兩國的語言交流。
[1]彭廣陸.從漢語的新詞語看日語的影響—說“人脈”[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6)
[2]吳侃.近年日語外來詞對中文的影響[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0(3)
[3]劉曉霞.從日語借詞看日語對漢語的影響[J].日語知識.2001(5)
[4]沈國威.回顧與前瞻日語借詞的研究[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3)
H136
A
1671-864X(2015)12-0168-01
吳晶霞(1991-),女,漢族,安徽合肥,天津外國語大學碩士在讀,天津外國語大學,日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