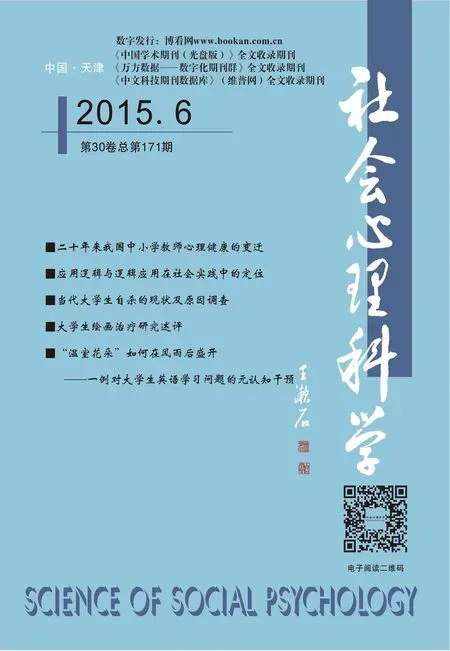二十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的變遷
趙云龍
(楚雄師范學院 民族教育研究所 云南 楚雄 675000)
1.引言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中明確提出:“振興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興教育的希望在教師。建設一支具有良好政治業務素質、結構合理、相對穩定的教師隊伍,是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根本大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有好的教師,才有好的教育。”
已有研究表明,教師心理健康狀況與學生心理健康程度呈顯著正相關,[1]教師職業倦怠對中小學生的健康成長有嚴重負面影響。[2]
2012年12月,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教師”和“心理健康”為主題進行搜索發現,30 多年(1979-2012)間,以“教師心理健康”為主題發表的論文總數為9107 篇,詳情見表1。可見,近7年間發表的以“教師心理健康”為主題的文章總數比之前20 多年的研究成果還要多。

表1 30多年來,我國教師心理健康研究文獻的發表時間分布情況
從研究工具的角度看,研究者通常采用與心理健康相關的量表進行研究,例如:癥狀自評量表(SCL-90)、艾森克個性問卷(EPQ)、卡特爾16 種人格因素問卷(16PF)以及自編問卷等,但使用最多的是SCL-90。
盡管研究方法相同且使用統一的研究工具(SCL-90),但研究結論卻存在差異。大部分研究者認為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很差,心理問題逐漸增多。[3]-[12]
對于上述研究結果的不一致,心理學領域一般采用元分析方法來解決。元分析是一種量化的文獻研究方法,是在總結多個單一研究結論基礎上,形成更為普遍的、更令人信服的定量結論。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研究樣本的來源區域、研究年代以及文獻類型(公開發表或非公開發表,一般期刊或核心期刊)都會對結果產生重要影響。以文獻“研究年代”為例,依新發(2012)等人對近18年間中國軍人心理健康元分析后發現,18年內,中國軍人心理健康狀況呈上升趨勢,即中國軍人心理越來越健康。[13]進一步統計分析發現,“年代”能夠解釋心理健康變化量的12%-44%,可見,對某一因子來說,其將近一半的變異是由“年代”這一變量引起的。辛自強(2012)等對25年來大學生心理健康元分析發現,大學生SCL-90 各因子均值與年代間呈顯著負相關。進一步回歸分析以后,發現“年代”(研究時間)可以解釋9 各因子4%-36%的變異。[14]可見,“年代”(研究時間)往往是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變量。但令人遺憾的是,傳統元分析方法經常將“年代”等變量視為“誤差”因素,在分析中需要嚴格控制,或者干脆選擇避而不談。例如,張艷麗(2009)對近10年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元分析中,文獻的研究時間這一因素直接就被忽視。[15]
為了彌補元分析方法的這一局限,美國圣地亞哥大學的Jean M.Twenge 教授提出了一種特殊的元分析技術——橫斷歷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簡稱為橫斷歷史研究。它是采用橫斷研究“設計”對大跨度時間、時代(或歷史發展)有關的差異或變異進行元分析研究的方法。這里的“設計”并非如關于個體發展的橫斷研究那樣預先構造好了方法,而是“事后追認”的,即將孤立的研究按照時間順序加以連貫,從而使得已有研究成為關于歷史發展的橫斷取樣。[16]
本研究運用橫斷歷史研究試圖確定1991年-2010年間,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變化的一般趨勢,具體內容包括:(1)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間的相關關系;(2)“年代”能夠解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變異量的多少;(3)不同性別(男教師和女教師)、學校類型(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家庭住址(城市和農村)教師近20年間心理健康變化情況是否存在差異;(4)不同性別(男教師和女教師)、學校類型(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家庭住址(城市和農村)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具有差異性。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癥狀自評量表(SCL-90)由Derogatis,L.R.編制(1975),包括90 個項目,可以評定一周以來的身心狀況。此表分為5 級評分,1=從無,2=輕度,3=中度,4=相當重,5=嚴重,也有的用0-4 級評分。SCL-90 包含9 各因子,分別是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和精神病性。
2.2 文獻搜集
2.2.1 文獻搜集標準
本研究選取文獻的標準如下:(1)所有研究必須使用相同的研究工具,即SCL-90 量表;(2)文獻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大陸的中小學教師群體,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被試;(3)研究文獻報告了被試(小學或初中或高中教師)SCL-90 量表9 個因子的描述統計結果(N,M,SD);(4)研究文獻的發表時間為:1993-2012年。把起始時間設為1993年,因為這是“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等數據庫中用SCL-90 研究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的最早時間。
2.2.2 文獻排除標準
本研究文獻的排除標準是:(1)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即文獻的研究背時是按某一特殊標準來選取的。例如民辦教師、體育教師、骨干教師、貧困民族地區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心理健康教育教師音樂教師、黨員教師、汶川地震災區教師等等;(2)研究時間的特殊性,即樣本測試的時間不在平時,而在考試之前,例如,高中教師施測時間為高考前一個月;(3)研究數據缺失或有明顯錯誤。文獻中沒有明確報告樣本SCL-90 量表的平均數或標準差,或文獻資料中提供了研究需要的數據(N,M,SD),但存在明顯錯誤;(4)數據的重復發表。相同作者、相同被試、相同結果但重復發表的文獻,選擇其中發表時間最早的一篇;(5)為了避免文獻數據的重復利用,采用元分析方法研究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的文獻被排除。
按照上述文獻選取和排除標準,在中國期刊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維普中文科技期刊、萬方學位論文及期刊等數據庫中,分別以“教師”、“心理健康”、“心理衛生”、“癥狀自評量表”和“SCL-90”等為檢索詞在題目、關鍵和摘要等項目下檢索,檢索的時間為1993年-2012年。符合標準的文獻共有195 篇,樣本總量為85574,文獻的具體情況如表2 所示。

表2 1991-2010各年度教師SCL-90數據組及被試數量分布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統計和編碼過程中,對數據資料做了如下基本處理;(1)SCL-90 量表有兩種計分方式:1-5 級和0-4 級評分方式,由于常模以及大多數研究多采用1-5 級評分方式,因此,本研究將在0-4 級計分方式因子均分上加1,統一轉換為1-5 級評分;(2)少部分文獻沒有提供總被試群體的因子均分,但是報告了子群體(例如,男教師和女教師)的因子均分(共6 篇),按照下列兩個公式(公式1,公式2)對子群體的研究結果進行加權合成:

(3)研究年代的確定。若文獻中清晰報告了樣本數據測查時間,則以此時間為準,對于未說明樣本數據選取時間的文獻,本研究沿用以往研究的做法(Twenge,J.M,2000),統一用發表時間減去2年。(4)若研究文獻中分別報告了小學教師、初中教師和高中教師SCL-90 量表因子得分(N,M,SD),則有幾組數據可算幾篇研究(共計4 篇文獻被拆分);(5)為了充分利用文獻數據資料,在數據錄入時,除考慮SCL-90 量表9 個因子均分的年代變化趨勢以外,性別、學校類型(中學教師或小學教師)、家庭住址(城市和農村)等變量也納入分析的范圍。具體來說,擬弄清兩個問題:一,性別、學校類型、家庭住址是否是引起教師心理健康差異的原因;二,不同性別、學校類型、家庭住址的教師心理健康狀況與年代間的關系如何。
3.研究結果
3.120 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逐漸下降,但下降速度比較緩慢
圖1 是中小學教師SCL-90 量表9 個因子得分與年代間的折線圖,從圖形可看出,20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得分隨著年代的增加逐漸升高。

圖1 中小學教師SCL-90各因子均值年代變化圖
圖2 是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間的相關散點圖,從圖形可看出,20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與年代間呈負相關。
為了更精確的量化我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隨時間的變化量,分別將年代與各因子均值及標準差進行相關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教師SCL-90各因子均值及標準差與年代呈非常顯著的負相關(P<0.001)。進一步回歸分析發現,年代可以解釋軀體化、敵對和精神病性三個因子的變異為34%、41%和30%,可以解釋抑郁和焦慮因子29%和25%的變異,可以解釋強迫癥狀、人際敏感、恐怖和偏執因子的變異為16%、10%、15%和9%。

圖2 中小學教師SCL-90各因子均值與年代的相關散點圖
20年來,中小學教師SCL-90 各因子得分隨年代增長呈逐漸上升趨勢,但究竟上升了多少?從統計結果可見,20年內,9 各因子均值的變化范圍是0.09-0.20,上升了0.15-0.33 個標準差(效果量d)。根據Cohen 對效果量d大小的區分,當d>0.80 時,稱為“大效應”,當時0.50<d<0.80,視為“中效應”,當0.20<d<0.50 時,視為“小效應”(Cohen,1992)。說明,20年來,雖然我國中小學教師SCL-90 各因子均值逐漸增加,但其增加的幅度非常小。
3.2 近15年來,男女教師心理健康的變化情況
本文195 項研究中,共有167 篇報告了男女教師心理健康的分數。1994、1995、1996 連續3年都沒有報告心理健康的性別分數,所以,分析的時間從1997年-2010年。
3.2.1 男教師的軀體化等3 個因子得分有上升趨勢,女教師的軀體化和焦慮因子有惡化趨勢,女教師心理健康相對男教師而言,變化緩慢。

表3 中小學教師SCL-90各因子均值、標準差與年代的相關及回歸分析

表4 中小學男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的相關及變化量
從表4 可以看出,男教師SCL-90 軀體化、敵對、恐怖等因子均分與年代相關顯著(P<0.01 或P<0.001),年代可以解釋的變量分別是29%、9%和13%。女教師的軀體化、焦慮等2 個因子得分與年代相關顯著(P<0.05),年代可以解釋的變異分別是9%和6%。
如前文所述,用效果量更詳細地量化男女教師SCL-90 各因子隨年代變化的大小。對于男教師來說,1997年至2010年以來,各因子增加了0.00-0.30 個標準差,女教師的變化范圍范圍在-0.01 至0.18 之間,均小于0.5。
3.2.2 元分析結果表明,男女教師軀體化等6個因子間存在顯著差異。
為了回答15年來男女教師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具有差異這一問題,分別對二者SCL-90 各因子的均值進行元分析,結果發現,在軀體化[-0.04(-0.02,-0.06);Z=7.13,P<0.00001]、抑郁[-0.02(-0.04,-0.01);Z=2.71,P<0.01]、焦慮[-0.05(-0.07,-0.03);Z=9.13,P<0.00001]和恐怖[-0.06(-0.09,-0.03);Z=11.69,P<0.00001]因子上,女教師得分高于男教師,在偏執[0.06(0.04,0.08);Z=10.01,P<0.00001]和精神病性 [0.02(0.01,0.03);Z=9.13,P<0.00001]因子上則剛好相反。

表5 中小學女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的相關及變化量

表6 中小學男女教師心理健康異質性檢驗和效應值估計
3.310 多年來,小學和中學教師心理健康的變化情況
在195 篇文獻中,有185 篇文章報告了小學和中學教師SCL-90 各因子的均值及標準差。由于1991年-1997年均沒有相關的數據資料,所以,對小學和中學教師心理健康變化趨勢的分析從1998年至2010年,時間跨度為12年。
3.3.1 10 多年來,小學和中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隨年代增加呈逐漸下降趨勢,但二者下降速度不一致。
統計結果顯示,除人際敏感、偏執等2 個因子以外,小學教師SCL-90 量表的7 個因子均與年代呈顯著相關關系(P<0.01 或P<0.001)。將年代和各因子均值進行回歸分析后,年代能夠解釋的變異量是3%-30%。盡管年代與小學教師個因子均值間有顯著相關關系且年代能夠解釋的最高變異量達30%,但年代引起小學教師各因子均值變化的效果量d在0.08-0.29 之間,屬于小效應。
將中學教師SCL-90 量表的9 個因子與年代進行相關和回歸分析發現,9 個因子都與年代呈顯著相關(P<0.001),年代可以解釋的變異量在31%-65%之間,年代引起均值的最大變化為0.52(軀體化)個標準差,屬于中效應,應引起重視。
總體上講,小學和中學教師的心理健康都有隨年代的增加而逐漸降低的趨勢,但相比小學教師而言,中學教師SCL-90 各因子與年代間的相關更緊密,年代對中學教師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明顯高于對小學教師的影響。
3.3.2 元分析結果顯示,出軀體化因子外,小學和中學教師的其余8 各因子均差異顯著(P<0.001)。
將10 多年來,小學和中學教師心理健康差異的研究進行元分析,結果發現,中學教師SCL-90的全部因子的得分均高于小學教師,除軀體化因子差異不顯著(P>0.05)外,其余8 個因子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說明中學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明顯低于小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

表7 小學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的相關及變化量

表8 中學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的相關及變化量

表9 中學和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異質性檢驗和效應值估計
3.418 年來,城市教師和農村教師心理健康的變化情況
家庭住址(城市或農村)被認為是影響教師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變量,在已發表195 項研究中,有92 篇文章報告了城市和農村教師SCL-90 各因子的均值及標準差,樣本包括21351 名農村中小學教師和11475 名城市中小學教師。
3.4.1 18年來,較農村中小學教師而言,城市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受年代影響很大,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速度也很快
為了揭示農村和城市教師心理健康隨年代變化的趨勢,分別對二者與年代進行相關和回歸分析。城市教師SCL-90 量表的軀體化等6 個因子與年代間相關顯著(P<0.05 或P<0.01 或P<0.001)。進一步回歸分析后,年代能夠解釋6 個因子的變異程度在12%-32%之間。農村中小學教師的軀體化和偏執因子與年代相關顯著(P<0.05),年代能夠解釋的最高變異量為12%。值得注意的是,農村教師SCL-90 偏執因子與年代呈顯著負相關(P<0.05),說明18年來農村中小學教師在偏執因子上的得分逐漸降低。
按前文所述,要回答18年來城市和農村教師心理健康的變化量,用d表示。本研究中,城市教師心理健康的變化量為0.14-0.59 個標準差,軀體化因子得分增加了0.59 個標準差,屬于“中效應”。農村教師心理健康的變化量為0.04-0.31 個標準差,屬于“小效應”,說明18年來農村教師心理健康水平變化幅度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3.4.2 元分析結果顯示,農村和城市教師心理健康水平存在顯著差異
元分析結果發現,城市教師SCL-90 各因子得分均高于農村教師,且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說明城市教師心理健康水平顯著低于農村教師。

表10 城市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的相關及變化量

表11 農村教師心理健康與年代的相關及變化量

表12 城市和農村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異質性檢驗和效應值估計
4.分析與討論
4.1 20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呈逐漸下降趨勢
研究表明,20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師SCL-90各因子與年代呈顯著正相關,年代能夠解釋的變異量在9%-41%之間,其中SCL-90 量表的抑郁、焦慮、敵對、偏執、精神病性等5 個因子變化的范圍為0.31-0.37 個標準差,屬于“小效應”。[17]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認為20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隨著年代的增加逐漸下降,即中小學教師心理問題越來越多,但其變化的速度比較緩慢。
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逐漸下降,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教師專業化的程度越來越高,教師角色已經由原來的知識傳遞者轉化為學習促進者、指導者和引路人,由單一型教師轉變為全能型教師,由經驗型教師轉變為研究型教師。教師角色的轉變,意味著社會對教師職業期望不斷增加,教師壓力會越來越大。另外,21 世紀以來開展的一系列課程改革,其本質是“適應性變革”,即要求教師從根本上對課改做出適應性的改變。因此,課改是對當前教育實踐活動的一種“否定性行為”。這種“否定”和“改變”給教師的行為方式、價值觀、情感態度等各方面都帶來了嚴峻挑戰和現實震撼,教師在重新界定自身角色和身份時也陷入了“危機”之中,具體包括以下幾種表現:職業方向感的模糊或偏離,教師教學成就感、創造性的缺失以及日常教學活動的去意義化等。[18](2)近年來,教師的工資待遇有了較大的改善,但與其他行業相比,屬于偏低水平。12 個行業中,教師平均工資在一直在倒數第一和倒數第三之間波動,在一些貧困和偏遠的農村地區,教師工資更低。付出和回報比例的嚴重失調,使得教師不僅要面對經濟的壓力,而且還要承受心理失衡帶來的壓力。另外,對于中小學教師來說,片面的評價機制以及機械的考核辦法不僅會挫傷教師工作的積極性,而且導致教師疲于奔命。還有,學校環境中,超負荷的教學、管理工作以及由于競爭而加劇的緊張的人際關系都會對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產生負面影響。
4.2 15年來,中小學男女教師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波動,但變動幅度較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近15年來,無論男教師還是女教師,二者的心理健康總體水平均隨著年代的增加呈逐漸下降趨勢,但下降趨勢非常緩慢。
令人欣喜的是,15年來,中小學男教師SCL-90 量表的抑郁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沒有變化(d=0),強迫癥狀和人際敏感因子得分有下降趨勢(d=-0.02 和d=-0.16)。對中小學女教師來說,人際敏感和偏執因子得分有所下降(d=-0.11 和d=-0.07)。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小學男女教師面對工作和生活的壓力時,“不自在感和自卑感”出現頻率有所降低,與以往相比。
另外,對15年來男女教師心理健康狀況進行元分析后發現,在軀體化、抑郁、焦慮和恐怖因子上,女教師得分高于男教師,在偏執和精神病性因子上則剛好相反,這與已有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5]可能的原因:(1)女教師是中小學教師群體的主力軍,她們更傾向于將心理問題與生理不適聯系在一起;(2)女教師除了應對工作壓力以外,相對于男教師而言,需要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教育子女等類似的“體力活”,加上女性在體力勞動方面的先天弱勢,使她們更容易表現出“軀體化”癥狀;(3)女性社會角色的多重化,使女教師在處理各種壓力事件時顯得力不從心,增加了焦慮和抑郁情緒。
4.3 近15年來,中學和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狀況呈下降趨勢,且中學教師下降的速度明顯快于小學教師
統計結果顯示:(1)中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隨年代的增加而逐漸下降,且下降速度明顯快于小學教師;(2)中學教師軀體化因子受年代影響的效果量為0.59,屬于“中效應”,應引起重視。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學教師越來越多的“感到身體不適”。
可能的原因有:(1)中學教師除了與小學教師一樣,必須承擔教學工作以及職業期望帶來的壓力以外,中考高考帶來的考試壓力是影響中學教師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雖然考試方式一直處于變革之中,但就目前來講,中考高考作為指揮棒的主體地位依然沒有受到動搖,處于其中的教師和學生承受的壓力是外人難以想象的。(2)中學教師工作壓力大、時間緊、任務重,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或者教師自己沒有興趣愛好,教師緊張、焦慮的情緒得不到宣泄和放松,長此以往,心理健康必然受到消極影響。有些教師性格內向,不喜歡交流傾訴,喜歡“宅”在家里,碰到負性生活事件時,應對方式單一且效果甚微。[19](3)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加入到教師行列,獨生子女自我中心等負面性格因素也會對其心理健康造成影響。
4.4 18年來,城市和農村教師心理健康水平向“相異”的方向發展,城市教師心理健康水平明顯下降,農村教師心理健康水平則有所提升。
統計結果顯示,18年來,城市教師心理健康狀況變化量在0.03-0.59 個標準差之間,其中,SCL-90 的軀體化因子變化最大,效果量為0.59。
農村教師SCL-90 的強迫癥狀等6 個因子的效果量小于0,說明農村教師心理健康水平有上升趨勢。可能的原因在于:(1)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農村教師的生活水平、經濟狀況以及和城市教師越來越接近。(2)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思想意識不斷提升,尤其是城市地區,社會、家長、學校對教師職業要求不斷增加,這會給身處其中的教師帶來巨大的職業壓力。還有,城市地區由于經濟達到、思想先進,在課改中,往往首當其沖,是課改的“示范區”,在課改不斷推行的今天,意味著教師必須付出更大的傷心代價適應教學工作。
[1]王加綿.(2000).關于教師心理健康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發展具有特殊意義的研究報告.遼寧教育,(11),20-21.
[2]朱姝,董莉萍,杜瑞紅,尹敏.(2010).教師職業枯竭及心理健康狀況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中國學校衛生,31(7),802-804.
[3]高峰,袁軍.(1995).上海市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現狀調查.上海教育科研,(3),40-45.
[4]薛晶玉,王鐵石.(2001).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現狀的調查.遼寧師專學報,3(5),41-45.
[5]李娟,李輝,黃高貴,李瑾,湯磊.(2006).貧困民族地區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狀況.中國學校衛生,27(12),1078.
[6]王麗君.(2005).中小學教師心理衛生問題及對策研究.河南社會科學,13(3),138-141.
[7]方紅麗,張桂青,楊建霞.(2007).西部地區大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現狀比較.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2,7887-7890.
[8]孫玲,俞瑞康.(2007).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江蘇教育研究,(3),41-44.
[9]李福業,劉繼文,劉斌,連玉龍.(2008).烏魯木齊市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狀況研究.新疆醫科大學學報,(5),53-56.
[10]楊伊生,張瑞芳.(2008).內蒙古小學教師成就動機與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漢文版),37(4),125-128.
[11]呂英.(2010).教師與非教師群體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與比較研究.教育與教學研究,24(4),49-52.
[12]胡衛平,馬玉璽,焦利英,汪華英.(2010).山西省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狀況調查.教育理論與實踐,(1),63-66.
[13]依新發,趙倩,蔡署山.(2012).中國軍人心理健康狀況的橫斷歷史研究研究,1990-2007.心理學報,44,226-236.
[14]辛自強,張梅,何琳.(2012).大學生心理健康搬遷的橫斷歷史研究.心理學報,44(5),664-679.
[15]張艷麗.(2009).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研究的元分析.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師范大學.
[16]辛自強,池麗萍.(2008).橫斷歷史研究,以元分析考察社會變遷中的心理發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6(2),44-51.
[17]Cohen,J.(1992).Statistic power analysi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3),98-101.
[18]李茂森.(2011).新課程改革背景下教師的身份認同危機,表現與實質.當代教育科學,(24),16-19.
[19]張蕾,孫凱基.(2001).青島市四方區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狀況的調查研.青島教育學院學報,14(l),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