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蕭蕭:詩歌是我的“宗教”,是我的“呼吸”
李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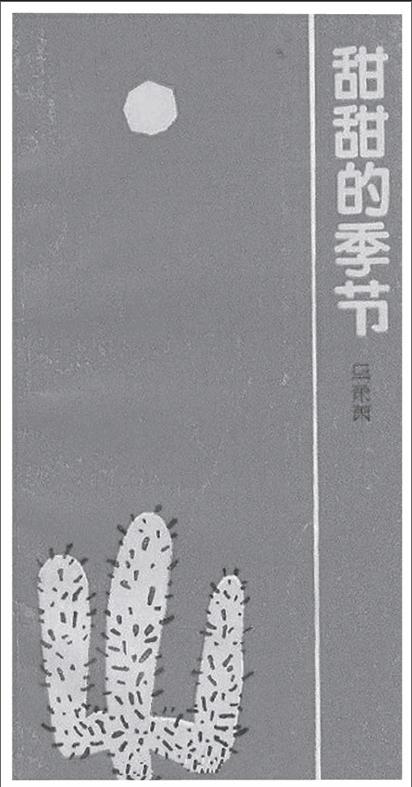

馬蕭蕭,湖南隆回人,1970年6月出生,1989年3月特招入伍。歷任炮兵、排長、干事、編輯、創作員等,現任蘭州軍區《西北軍事文學》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3歲開始發表作品,出版各類著作近20部,曾獲首屆中國十大校園詩人獎,首屆中國十佳軍旅詩人獎,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獎,第九屆全軍優秀文藝作品獎,第四屆全國優秀婦女讀物獎,第一、四屆黃河文學獎,《飛天》十年文學獎等,入選首批甘肅詩歌八駿。水墨作品多次參展并在國內外出版畫冊。
從校園詩人到軍旅詩人的華麗轉身
李 東:馬老師您好!您13歲發表作品,15歲創辦全國第一家中學生自辦詩報,更是被譽為八十年代中國校園詩壇領軍人物,成為詩壇“明星”,您能介紹一下當年的中學生校園詩歌創作概況么?現在回想起來會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馬蕭蕭:八十年代確實是一個詩歌的年代。黃河出版社出版的由姜紅偉編著的《八十年代校園詩歌運動備忘錄》一書中,我的名字出現了近200次。當年的校園詩人、現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評論家葛紅兵在序言中說:“20世紀80年代中學生校園詩歌運動是少數可以用輝煌和偉大兩個詞來形容的歷史事件,然而也是被遺忘甚至故意忽視的事件。20世紀80年代中學生校園詩歌運動是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啟蒙運動經歷了由高層知識分子而‘大學、‘中學、進而‘全社會的鋪展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學生校園詩歌運動處于新啟蒙運動全民化過程非常重要的環節上,是中國‘新時期文學誕生期最重要的文學事件之一。”那時節,全國各地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生詩歌學愛好者遙相呼應,在世界文學史上、中國校園內外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史無前例的中學生校園詩歌運動。它是中國當代詩壇繼“朦朧詩”、“第三代”之后又一場非常重要詩歌運動。當時,全國有數以千計的校園詩歌社團,和數以千計的校園詩歌刊物,我當時還創辦了全國第一家中學生自辦詩報《青少年詩報》;包括《詩刊》在內的各大報刊競相刊發少年詩人作品,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學生詩歌選集與個人作品專集,全國校園詩賽、少年作家筆會頻頻舉行;北京大學等名牌高校還破格免試錄取了中學生校園詩人、作家中的一二十名佼佼者。在上百萬名中學生詩愛者參與的投票活動中,姜紅偉、江熙(他現在叫江小魚,是電影導演、編劇)、馬蕭蕭、南島、葉寧等被評為首屆中國十大校園詩人。“神童詩人”田曉菲,15歲就被北京大學免試錄取,19歲就成為哈佛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現在是該校教授。著名詩人、《詩刊》原主編葉延濱對我們的評價是“洪燭、邱華棟、馬蕭蕭等少年詩人的作品,為過于沉重的八十年代詩壇增添了明麗的色調。”那是多么甜美的時節,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它甜美得有些荒唐,真不敢相信它曾在歷史上、在自己的生命中實實在在地閃現過。
李 東:自九十年代經歷社會轉型之后,這批校園詩人的近況如何?
馬蕭蕭:當年數百萬的少年詩愛者,只有我和少數人一直在文壇堅持至今。洪燭、李皓等十余人至今仍活躍于詩壇,而邱華棟則“轉業”為小說家了。其他人呢,有的成了學者教授、導演編劇、出版家、企業家、政府官員等等,在各行各業大都干出了一番事業。這些少年才子們仍如一顆顆明珠,在五湖四海乃至大洋彼岸,以不同的方式閃亮著各自的光澤。那光澤仍不乏浪漫與激情,卻也陡添了幾分沉重與滄桑。不知不覺,我們已在社會的逐步轉型和市場經濟的考驗中,走到了青春的尾巴,走在上有老下有少的空間里,走在生活與事業的雙軌上,走在詩與非詩的夾縫中。在我看來,一個一輩子從未愛詩、從未寫詩的人,是遺憾的;一個一輩子都只愛詩、都只寫詩的人,亦是遺憾。人生易老,世事紛繁,每個人都想開心,每個人都有詩之外的很多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已游離于詩壇之外的兄弟姐妹,我相信、我祝愿他們雖已不寫詩但心中還有詩,猶如一個不拜佛的人心中卻有佛一般。
李 東:少年成名,這對您后來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馬蕭蕭:一方面他給我帶來了較大榮譽,同時也給了沉重壓力。2010年1月,在西安舉行的首屆中國十佳軍旅詩人頒獎典禮上,陜西電視臺記者呂云要我談談獲獎感受。我說:這次頒獎,名稱沒用十大而用十佳,這個佳字,我很敏感。“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從16歲獲得首屆中國十大校園詩人獎,到今日又獲得首屆中國十佳軍旅詩人獎,這中間的23年里,一個“佳”字,一直是我的一塊心病。古人早說過,少年成名是人生的幾大不幸之一,甚至還說是人生的最大不幸。對此我深有同感,但卻一直不認此命。在西北從軍的20多年日子里,我一直擔心江郎才盡的故事在我身上重演,內心所承受的壓力一言難盡。這20多年,前十年我淡出詩壇,潛心于修煉詩外功夫,之后又繼續坐著十來年冷板凳,默默打造著自己的長詩《中國地名手記》等。而今,我是否已真正實現了自己從十大校園詩人到十佳軍旅詩人的成功晉級和華麗轉身?心中尚有疑問。但稍感欣慰的是,萬幸自己已不是那個被千夫所嘆的仲永。
詩歌左右了人生軌跡
李 東:當年有許多校園作家因為才華出眾被大學破格錄取,有一些至今仍活躍在文壇。而您卻是被部隊特招,這其中有什么故事嗎?
馬蕭蕭:我上中學時,地理、歷史、語文等成績尚可,其中,地理成績較突出。而數學、外語等就很差了,是全班的倒數。畢業前夕,市、縣文化部門還有省作家協會的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元洛把我向重點大學湘潭大學做了推薦。之所以沒有聯系北大、武大這樣的名校,當時是考慮到湘潭大學就在本省,似乎把握更大些。該校先后兩次派人到就讀的隆回二中對我進行了考察,并組織六位教授進行了面試,決定破格免試錄取。與此同時,邵陽市委也向湖南省委發去了“破格錄取了馬蕭蕭”的快報,省委副書記、省長劉正同志作了批示,無奈省招生辦礙于體制,考慮到本省尚無先例,未能“開口子”(湘潭大學雖然也是重點大學,但它由湖南省教委代管,自主權相對小一點)。我只好到湘潭大學自費就讀。第二年春,經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周玉清同志推薦,蘭州軍區駐陜某部徐興將軍破格接收我入伍,后來又破格提干,調到了蘭州軍機關從事文學編輯、創作工作。說起來很有意思,當年我拿著推薦信投奔徐興將軍時,從湖南老家帶給他的禮物是幾斤雪峰蜜橘。而將軍有所不知,這袋蜜橘原本是有十來斤重的,火車上我不知不覺吃掉了一小半。前幾年專程去西安看望他時,說起此事,兩人哈哈大笑。唉,如今社會,哪位詩人想要像我一樣遇他們這樣的貴人,恐怕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了。沒有他們的無私幫助和殷殷教導,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李 東:是否可以說寫詩改變了您的人生軌跡,詩歌(文學)在您生活中承擔著怎樣的角色?
馬蕭蕭:也許是自己少年時代內向、憂郁、敏感的性格決定了自己更適合寫詩吧,總覺得自己有話要說,總覺得說出來不如寫出來,就這么一路寫了下來。而且詩歌創作也不斷的給我帶來了一定的榮譽,也讓我在現實的紛繁生活中找到了一個情感的出口、一輪精神的月亮,詩歌待我不薄,詩歌對我有恩,我越來越喜歡它,越來越愛它,它成了我的“宗教”,成了我的“呼吸”,我與它融為一體了,再也分不開。詩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我的人生軌跡。
不斷打造詩外功夫
李 東:《中國地名手記》被認為您的代表作,您認同嗎?這部歷經十余年,反復修改、刪減的詩歌作品,也體現出您過人的才華和嚴謹的創作態度。那么,您創作該詩的動因是什么?
馬蕭蕭:算是我的代表作吧。我從小酷愛地理,上中學時,便能把中國地圖上的行政劃分、山川湖海、倒背如流。“寫遍中國”,一直是我的野心。另外,地名是歷史、文化、文明信息的載體,與姓名一樣,同屬名稱文化范疇,我多年研究姓名學,甚至被譽為取名專家,從地名里挖掘詩意,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兒了。自2000年開始,我用整整10年時間創作了一部詞典體長詩《中國地名手記》,這部長詩以中國三千多個地名為題,由兩千多首也可以獨立成篇的短詩組成,每首詩書寫一個地名或多個地名,主要從這個地名的文字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去書寫。當然,出版時我把它做了大幅度刪改。當時寫的時候是拼命往長里寫,一直寫了六萬行,出版的時候我是拼命把它往短里壓,一直壓到了六千行。這樣做的效果還不錯,長詩的質量得到了一定保證。書出來后反響還可以,很多著名詩人和評論家都給予了肯定。有的認為我這部長詩在恢復漢語詩歌創作的高難度寫作方面、恢復漢語詩歌創作的高技術寫作方面,起了一個帶頭作用。不過我覺得只是拋磚引玉而已。還有的認為這部長詩是“一部不可模仿、無法復制的奇書”,這個評價太高了,我認為是他對我的一種鼓勵。
李 東:我在網絡和您的博客讀到大量對您詩歌的評論文章,作者多為著名作家、評論家,也不乏知名詩人、普通讀者,而且評論幾乎全是贊揚,您的內心有沒有因此膨脹過?作為創作者,您如何看待外界這樣的評論?
馬蕭蕭:誰能不在乎外界對自己的評價呢?應該承認,我也有膨脹的時候,但總體上是淡然的,有足夠的理智和警惕。那些被“捧殺”和“美殺”掉的詩人,一直是我的反面教材。我是學周易的嘛,周易的核心理念就是天人合一、居安思危。
李 東:對于作家而言,都希望寫出傳世之作,這也就意味著創作中需要不斷自我突破。作為已經具有一定成就的詩人來說,您為此做過哪些努力?
馬蕭蕭:文學創作,一是要求作家有出色的天賦,要有對生活的敏銳的洞察力,要有對語言文字的超強的駕馭能力。二是要有旺盛的激情。要守住自己的童心,加強自己的愛心,鞏固自己的熱心。三是要有堅強的定力,要耐得住寂寞,要耐的住清淡甚至是清貧的生活,要耐的住長途跋涉的酸苦。30年來,我寫詩約3000首,自己略感滿意的不到300首,真正喜歡的恐怕也就30首。如若有人能喜歡其中三首,我便已知足。功夫在詩外,我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不斷打造詩外功夫。這,無非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豐富自己的學識。比如,這些年我研易、繪畫、賞石,受益匪淺。
李 東:是的,我知道您對易學頗有研究,這對你做人、寫詩有著哪些影響?
馬蕭蕭:一個詩人年過四十竟然還在寫詩,是可喜、不可恥,而一個詩人如果年過四十竟然還不會做人,既可悲、又可憐。做人與作詩的和諧關系,一直是中國詩人兩千多年以來都未能完全處理好的一大難題。多年前,我曾與詩人張后有過一次訪談。他問我:“我們一般都將周易稱為玄學,你研究周易最大的體會是什么?對詩歌有怎樣的助益?”我的回答是:不少人認為周易是用來算命和預測吉兇的,將其斥之為封建迷信,這種看法是極其錯誤的片面的,是會誤國誤民的。易經是群經之首,包涵“象、數、理、占”四部分,而“占”,只是其一。“封建迷信”這四個字非常可笑,其實迷信在封建社會以前就已出現啦。易學,重在對天地人三者和諧關系的辯證。用周易來作預測,確實很靈驗,但一個熱衷于算命的民族必將衰退,而一個能從易經中悟出天地人之和諧大道的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等,必可大成其功。遺憾的是,我們對天地無知無畏,對傳統自暴自棄,而國外對我們這些精粹就很感興趣:韓國國旗上,有太極圖;日本明治維新時,不通易者是不能入內閣的。君知否,人類目前還只能看到世界上百分之五的物質,此外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暗物質存在,科學還很嫩。我們國家,地大而物不博,人杰而地不靈,正是運用周易“趨吉避兇、居安思危”的和諧理念,才使幾千年的文化沒有中斷。與周易相比,詩歌實在是太小兒科了。周易是詩歌之源,易經里的爻辭,是中國詩歌的胚胎,是東方最古老最神性的詩篇。歷代大詩人中,通易者多多。易學修養,可以提升詩人的學習力、創造力和生活力。它不但能增強詩歌的神性、靈性、磁性和兼容性,實現詩人對語言自身功能的完善,還可以使詩人在紛繁生活中注重心靈的成長、行為的檢點,實現詩人與自然、詩人與社會、詩人與生活的自覺諧調。有人說,未來最富的人必是通“巫”之人,而我認為,內宇宙最博大最健美的詩人,必是有意無意的通易之人。
文學創作沒有程序性可言
李 東:當前文學環境不同了,因為一些詩歌事件,很多人一提到詩人,仿佛就是不正常的人,甚至有人以“詩人”作為諷刺,詩人的地位顯得有些尷尬,也引發許多關于詩人存在價值的討論,您認為在物欲橫流的當下詩人何為?
馬蕭蕭: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便是“出入”。一個擁有“出入證”的人,才是自由者。比如,你進我們戒備森嚴的軍區大院,就得辦出入證。有了這張出入證,你才能自由通行,才能找到我。一個詩人,只有辦好了屬于自己的那張出入證,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創作過程中,實現自己的自由飛翔;才能享受精彩的詩外生活,才能擁有扎實的詩外功夫,才能生活得脫俗而不清高,才能生活在浪漫之中而不是亂麻之中亂碼之中,才能為詩豐而不是為詩瘋。我贊同于堅所說的“像上帝一樣思考,像市民一樣生活”。
李 東:您的水墨畫也在文學圈和書畫界有了廣泛影響,受到追捧。您是什么時間開始畫畫的?您的水墨畫和詩歌一樣大氣開闊,這兩種藝術形式有怎樣的內在關系?
馬蕭蕭:應該說是一種互通、互補、互生的關系。在我13歲發表詩作的前一年,我在那座充當學校的馬氏宗祠里,忽發奇想,無師自通,“繪制”過連環畫《螞蟻戰》100多頁,保存至今。但此后便再未涂抹,雖然自己在編輯部也曾長期兼任過美術編輯。及至2006年我辦公室搬到了幾位專業畫家的對面,才于“詩情”之中重拾“畫意”,且一發而不可收拾。紛繁人世,我愈發堅信,詩情畫意乃吾輩的四字真言。詩為時間藝術,而畫當屬空間藝術;詩畫兼修者,左右大腦得以雙模雙待,靈與肉也在外宇宙里瀟灑聯通并自由移動。詩畫交融,時空在握;相比當初單純的詩人身份,自感對這個愛恨長存的世界又看清了幾分。無線時代,我對傳統國畫的所謂線條,不予全盤否定但從不完全依賴,一如我現在更多使用的是移動電話、無線上網卡、wifi一般。萬物類同,每個人、每一物,都是信息載體,都有接收與發射的號碼和密碼乃至開關;這世界的內芯,原本便是一股無形的元氣、真氣……我所做的,便是通過水與墨的協調,將這股生氣引入畫幅之中。在這個沒有國花國樹國石的國度,中國畫這個名稱看似榮光,實則衰矣危矣。那些拼命設計呀、重復呀、不讀書啊、迎合大眾與評委呀,不懂立意,不會命名,無力創新筆墨技法、水墨語言、材質性能,筆下鮮有文化味與學術性的畫家們,他們理不清歷史經典與時代風尚的遞進關系,弄不明個人經驗、國家經驗和全球經驗的交融秩序,一個個早已淪為十足的畫匠。大多只知營構出便于參展的大尺幅來追求視覺沖擊力的作品,似如光線(或沙粒)一般打入了觀眾眼里,難如光明一樣打亮觀眾心靈,在照相機、錄像機、顯微鏡、望遠鏡、航海潛海器、航空航天器等工具為人類所帶來的視界新關系面前,在西洋畫、現代水墨、實驗藝術與動漫等多路聯軍的夾擊下,傳統中國畫即使有九條命,我看也早已死掉了五六條。傳統中國畫的程式化問題,確己成為它發展的一大桎梏。它的前途,恰是一條與中國戲劇毫無二致的沒落之路。中國畫當屬水墨范疇,而水墨者,應以水為先。千百年來歷代名家已將筆法與墨法發揮到極致,唯有水法,尚有極大開拓空間。雖然單靠水法遠不能徹底拯救國畫,但它所造就的面目,確實煥然一新。多年來,我研之習之,略有收獲。文字與貨幣和度量衡一樣,有其國家甚至國際標準,乃神圣之物。所以我說,書法必須守法,只允許輕微違法,切不可胡抹亂畫。而世間景象,無奇不有,千變萬化,常態與非常態者,平視所見與俯仰所見者,肉眼所能見與肉眼所不能見者,乃至于夢境、幻覺、錯覺等等,均可入畫。所以我又說了,國畫萬勿循規,最好嚴重犯罪。或描具象,或舒氣韻,或述理念,或表技藝,只要能于紙上形成高于生活的新美視覺,無一不可。而能將其集藝術之美、哲學之理、人性之光等于一體者,當為巨匠。功夫在美院,而大功夫在畫外。我萬幸自己未有學院之緣未染學院惡習,一張白紙從心畫起,無法無天且自鳴得意。我的這些繪畫體會,既建立在自己的詩歌創作理念之上,同時也作用于自己的詩歌創作。
李 東:從您作品中明顯可以感受到西北大地的廣袤無垠,以及超越大地之上的情懷。請談談西部這片“精神地理”對您創作的影響。
馬蕭蕭:大西北,是“花兒”和“信天游”的故鄉,是“邊塞詩”與“新邊塞詩”的搖籃。這里有神奇壯麗的雪山、冰峰、草原、大漠,有深厚雄渾的歷史文化積淀,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有可歌可泣的軍旅傳奇,是文學創作的富礦。著名新邊塞詩人章德益說:“充滿靈趣,靈思與靈感的馬蕭蕭的詩,是一種由湘人靈慧的巧思與西北曠遠的山川悠然契合的產物。這種混融有綺思與野趣的小詩,一篇一篇都是意象的擷選、巧思的造型與人像的顯影,它們流自一個帶有童心的軍旅詩人內心深處,恰成為中國獷悍雄烈的軍旅詩的一個補充,一個在刀光劍影之外的多聲部的奇妙和聲。”章老師對我雖然是過獎了,但確實也道出了我的作品和我所在的大西北的聯系。感謝故鄉那一片山水里充溢的靈氣、神氣與巫氣,在我稚嫩的身體里安裝了最初的詩歌地理軟件。更慶幸,南國故土之秀雅與西陲軍旅之沉雄,逐步鑄就了我性靈的合金。
李 東:甘肅涌現出了許多優秀詩人,是詩壇的重要力量,繼“甘肅小說八駿”之后評選出的“甘肅詩歌八駿”也受到廣泛認可,并成為重要文化現象。這也使我想到曾引起中國文壇巨大震動的“陜軍東征”,以及“廣西三劍客”等等,作為“甘肅詩歌八駿”之一,您如何看待文壇這種“集群現象”?
馬蕭蕭:這是一種集團沖鋒的方式,是一種品牌意識的覺醒。事實證明,它既有利于贏得當地政府尤其是宣傳文化部門的支持,也有利于詩人作家自身的成長進步。但說到底,這只是一種文學現象、一種運作模式,任何詩人作家,最終都必須擁有自己獨立存在的實力。
李 東:在文化多元化的當前,詩歌寫作顯得異常龐雜:詩與非詩、好詩與壞詩的界定似乎越來越模糊,從編輯的角度來講,當前詩歌的評判標準究竟是什么?
馬蕭蕭:文學創作沒有程序性可言,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國家標準、國際標準。在我看來,什么形式、什么題材、什么手法、什么風格,都是可行的,也都是次要的,關鍵在于作品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體現與結合。好的詩歌,一要有語言的貢獻,詩人是普通人,但不能說普通話,要能從中看出詩人對語言藝術的求索與創新,看出詩人對語言自身功能的不斷完善;二要有人性的呈現,比如,傳遞真善美的情懷,給人以心靈的慰藉,等等;三要有全球的經驗,在文化既趨同又多元的當今,詩人應在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外宇宙(大我)與內宇宙(小我)的“婚配”過程中,培育出優良作物。
增強精英人物與團隊的權威引導力
李 東:新媒體加速了詩歌的傳播,特別是微信出現以來,詩歌以各種形式在朋友圈“刷屏”。有人說詩歌發展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對此您怎么看?您覺得當前詩歌創作環境怎么樣?
馬蕭蕭:微信對詩歌的推動作用,確實不可小瞧。從當初的網絡,到后來的博客,再到早幾年的微博,乃至發展到當下的微信(下一步肯定還會出現更新的媒介平臺),詩歌這個獨特的文學品種,很幸運地迎來了一個又一個愈加“宜居”的環境,便捷的閱讀分享,使得詩歌在日常時空中大有自由展翅之勢。但這種門檻較低、泥沙俱下的創作呈現,給人帶來的審美疲勞和客觀誤導亦不容忽視,如何增強精英人物與團隊的權威引導力,是當務之急。當今詩壇,平臺五花八門,詩會隔三差五,獎項多如牛毛,理論層出不窮,熱鬧的表現之下,詩人的自身修為和詩歌的藝術本質,大有“水土流失”之兆。普天之下,安安靜靜寫作的詩人,越來越少矣!
李 東:每一本雜志都有自己的辦刊理念,作為雜志主編,請您談談《西北軍事文學》的辦刊理念。受網絡和時代大環境的影響,紙質刊物面臨嚴峻挑戰,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讀者銳減、雜志發行量嚴重縮水,您認為紙質刊物的出路在哪里?
馬蕭蕭:《西北軍事文學》是在軍中擁有一定影響和地位的刊物,曾以長篇力作《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藏北游歷》《通向世界屋脊之路》等蜚聲文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在本刊兩次發表作品并向本刊推薦作品,茅盾文學獎得主李國文曾在本刊發表散文處女作,一大批詩人、作家從本刊起航。近幾年,我們在辦刊過程中,繼續堅持積極推進軍事文化發展,同時立志將其打造成文化戰略時代的開闊讀本,在欄目設置和稿件編發時也特別注重軍民文化融合,這使刊物既立足于軍旅,又走向了社會,發行量逐年上升,現已恢復到上世紀末前的水平。比如,我們2015年的訂數,就比去年增加了500多份,這個數字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全國大部分文學刊物發行量嚴重縮水的現狀下,我們這一點點進步,確實也來之不易,可喜可賀。說到紙質刊物的出路,大可不必過分悲觀,它自有其不可或缺的存在理由。現在的紙質刊物(尤其是內刊、民刊),比以前不是少了,而是更多。幾十年來,鮮有文學雜志停刊,雖然發行量難以復歸理想狀態。一些文學期刊,在上世紀為適應市場經濟的挑戰,在辦刊理念上往通俗類、情感類、都市類刊物上靠,最后幾乎沒有幾個成功的范例,逐步回歸到了文學本身。網絡時代、自媒體時代,大多數紙媒所做的應對,無非兩點:一方面盡力向新媒體延伸、與新媒體互動,同時強健自身的筋骨,求精求深打造產品,并死死抓住新媒體難以作為的那些領地來發揮自己的優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世界有陰陽二極互依互生之理,相對屬陰的網媒與相對屬陽的紙媒,其互存互動之道,也恰將展現出一種生機勃勃的和諧圖景。
李 東:您的回答無疑給創作者極大的鼓勵和信心。對于創作,您個人還有怎樣的規劃?
馬蕭蕭:我的詞典體《中國地名手記》,還將予以長期增補、修訂。另外,還有一部涉及周易、地理、藝術、宗教等內容的長篇隨筆,正在構思。至于其他的創作規劃,肯定會有,但目前還暫未考慮。
少年成名,無疑是所有初涉文學創作者夢寐以求的事情。此次訪談,我們走近昔日詩壇“明星”馬蕭蕭老師的內心世界,聆聽了他的成長故事、創作態度、辦刊理念,以及他對時代的看法。
作為少年成名并延續文學成績的優秀詩人,馬老師對創作談到三點:天賦、激情、定力。也許正是這三點,成就了他在作為優秀詩人的同時,還是一位出色的畫家、周易學者和奇石鑒賞家。
當前這樣一個“非詩歌”的時代,一個在西北大地構筑自己“詩歌地理”把詩歌當“宗教”和“呼吸”的人,我們有理由向他投去敬仰的目光。
責任編輯:閻 安 馬慧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