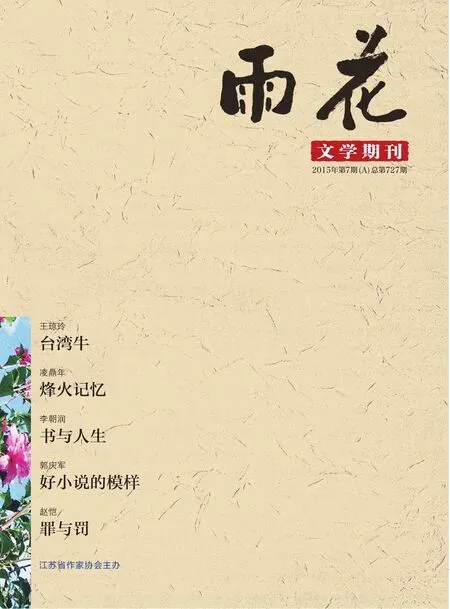臺灣牛
■王瓊玲
1943年,太平洋戰爭已經打得如火如荼,騰騰烈焰,炙烤著臺灣島上所有的住民。春光不再爛漫,厚厚的云層,阻擋一道道晨曦,天與地灰撲撲的,鎮壓著鉛塊般的重量。
阿里山山麓,梅仔坑小村莊,竹篁下、牛寮里,阿順伯公全家都在那兒。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是全家沒錯,包括被當成自家人的兩條牛。
兩條牛—大母牛以及它生的小水牛。
小水牛還沒斷奶,犄角也還沒長出來,只在頭頂上,露出了兩個小突,一雙牛眼亮汪汪,只看著自己的生身阿母。它緊緊挨著,不是低下頭,湊著鼻子,在阿母的肚下尋索奶頭;就是頂著兩個發癢的小突,抵著、拱著阿母的身軀,磨磨又蹭蹭。
任由小牛犢胡鬧著,那只龐大的母親,神情是全然的溺愛。它伸出紫紅色的長舌頭,一下又一下,舔著自己的親生寶貝。大舌頭舔過、掃過,小牛犢的一大片毛就潤了、濕了,乖順順倒伏下去;再逆個方向舔回來、掃過來,毛又換了邊,一根接一根、一片接一片,濕了,舒舒服服貼著,躺了下來。
阿順伯公全家圍著那一對牛阿母、小牛犢仔,安靜成一片,連十歲不到,平日愛鬧愛玩的曾孫子小阿桐,也緊緊閉上了大嘴巴。
牛寮地上,擺放著一大摞新割的青草,露水點點,像閃閃的淚珠。那要多早就去割呀!阿桐頑皮歸頑皮,上學前割草喂牛、放學后牽牛去泡水塘,小小年紀,多么盡責!
但是,這孩子現在怎么了?用力憋著氣,小胸膛一鼓一癟、鼻子一吸一張的,是要逼回快擠出眼眶的淚水?是要壓下拼命往喉嚨冒的抽泣?今天一大早,他的老曾祖就喊他過來,摟著他,聲聲告誡:失去心愛的東西,就在別人面前哇哇大哭的,絕對不是男子漢!
滿頭銀白的阿順姆婆,領著兒媳婦、孫媳婦,低著頭、垂著手站著,守在自己男人的身后。每一雙眼睛都紅腫多汁—她們不是男子漢,可以享有落淚的權利。
她們也全都是母親,都知道偶而溺愛一下孩子,有多幸福!多滿足!她們的勞動量、對這一家子的付出,也都不輸給那只大母牛。她們傷慟著、也惶駭著!會不會有一天,自己也會被拖走?或者,孩子們會被帶走?那樣,當母親的,就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失去溺愛孩子的機會了!
阿順伯公跨進柵欄,捧起一大把青草,再分成一小束一小束喂給大母牛。母牛張口銜了,磨著牙吃了。才咽下喉嚨去,濕厚的牛嘴,又探向伯公的大手掌,兩個鼻孔“噌!噌!”噴氣,討著再要。甚至,低下脖子,歪拱著牛頭,磨蹭伯公的腰和背。
一把又一把,慢慢地喂,阿順伯公那張方方正正的老黑臉,藏在白眉白須下,沒風沒雨,平靜到像橫了心、認了命。但是,每個人都瞄見了,他捧著青草的手指尖,哆哆嗦嗦在抖。
自從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日本旭日軍旗的十六道紅光,淌滴著人血的武士刀,已經讓整個臺灣陷入萬劫不復的煉獄,比起大自然的地震、刮臺風、崩土石流,還艱苦千倍萬倍。
現在,軍方又來了一道命令,說四處征戰的日本皇軍,需要優質的肉類蛋白質補充體力。所以,握有刀槍、掌管生殺大權的他們,不由分說地帶走全臺灣一只又一只的牛。他們扒了耕牛的皮,去制軍靴、做皮帶;他們切割、燉煮、醬燒耕牛的骨與肉,把農家相依為命的伙伴,變成一碗又一碗的飽腹菜肴。
今天,輪到阿順伯公家了,是最后一次的相聚與告別了。沒錯!它們雖然是牛,但也是人,是每個人至親至愛的家人呀!
大母牛的阿母、祖阿母、曾祖阿母,都養在他們家、也老在他們家、死在他們家。四五代生育,四五代留下小母犢仔,代代耕他們家的田、拖他們家的車。老了、耕不動、拖不了,就養在牛寮里,掛起大蚊帳,天天有青草吃,有幼嫩的甘蔗尾當點心;三不五時,還牽去涂泥漿、泡水塘。真的要永別時,全家老老小小哭紅了眼,圍著牛送終、抬著牛出殯,就只差沒誦佛經、沒披麻帶孝、沒有立牌祭拜而已……伯公說過:從十八代祖宗起,他們家就不吃牛肉。牛是家人,農家的大恩人,怎可以沒天沒良?
那只小牛犢仔還沒斷奶,今天,它的阿母就要被拖走了。它呢?跟著牛阿母去?或是留下來?跟了去,會不會也被殺被吃,進了日本兵的腸肚?留下來,還不太會吃草的它,能活嗎?就算活得下來,再大一些,肉長多了,會不會又被拖走,像它阿母一樣?
村里、山里的牛,都快被征召光了,世世代代靠天地生養、靠牛只犁田的人們,要怎樣活下去?
喔!阿順伯公現在不愁這個,他只在專心喂牛。青嫩的牧草,一把又一把,遞到母牛的嘴。它也吃得多專心呀!銅鈴大的牛眼,密稠稠的褐色睫毛,全是溫和與信任。它多乖順溫馴呀!好似天塌了也不怕,總會有老主人去頂著。
但,這一回,老主人還頂得住嗎?
青草喂完了,天也全亮了。
阿順姆婆捧著紅艷艷的彩帶,交給了伯公。太陽穿透密密匝匝的竹葉,反射出刺眼的血紅。
被征召的牛,跟“出征”的臺灣兵一樣,都要無條件將生命獻給天皇,用鮮血灌溉大和魂。所以,官方規定它們要披紅布、掛彩帶;牽進市街時,人們還要搖著日本國旗,夾道歡呼、列隊恭送。
老伯公細心細意,把彩帶繞過寬厚的牛肚子,綁好、系住了,一朵血紅大彩花,就端端正正開在牛背上。他拍拍牛脖子,像在夸贊孩子的乖巧。他雙手捧住牛頭,爬滿皺紋的臉頰,竟然偎了過去,牛鼻子呼喘出來的空氣,吹掀伯公的白胡須,一陣陣,像雪浪。
湊著牛耳朵,老伯公說了好一會兒的話。
說什么?沒人聽得見,或許是安撫、或許是致謝、也可能是訣別吧!
大母牛靜止著,停了嚼嘴、停了磨蹭,龐大又乖馴的身軀,似乎努力在傾聽著、理解著,連尾巴都停止甩動。
小牛犢依舊彎下脖子吸奶,溫熱又豐沛的乳汁,噗滋!噗滋!冒,它咕嚕!咕嚕!一口一口吞。來不及吞下的,還溢出嘴角,白了兩片翹嘟嘟的厚嘴唇。亮汪汪的牛眼睛瞇了下來,吸著、吮著!半睜半閉,睫毛微微抖,尾巴噗叭!噗叭!左搖又右甩,是小小囝仔被阿母溺著、寵著的那種愛嬌、那種歡喜……
淚水再也擋不住了,滑得眾人滿腮滿臉。
人與牛的話別,是那么寧靜、那么肅穆。
喜慶日子才敲的銅鑼,卻從遠遠的山嶺,一路響過來、近過來。
“匡嗆!匡啷!”“匡嗆!匡啷!”……
五、六個莊役場(臺灣日據時期的鄉公所)的公務員來了,他們要執行的,是連自己都痛恨的工作。
痛恨,又有什么辦法?有辦法,就不必這么卑微、這么無天良!他們不敢正眼看老伯公、不敢看阿桐、更不敢看即將變成孤兒的小水牛。
近幾個月來,他們奉日本人的命令,帶走一只只耕牛,砸碎了一家家生計、撕裂了一顆顆心肝。每一場生離死別,不管是默默相送、呼天搶地或憤怒攔阻,他們都只能概括承受。只因落地生根在梅仔坑,手中捧的,雖然是日本人的公家飯碗;嘴里吃的,卻都是臺灣牛與臺灣人耕作的心血。農家的悲與痛,只要還存著點良心,怎會沒感覺?
帶頭的人,名字叫阿隆,四十來歲,也是在老伯公眼皮下長大的。他一聲喝令,四五個跑腿的公務員,全部立正,對著老伯公、老姆婆一家子,深深鞠了躬。九十度的大彎腰,中規中矩的日本式禮敬。那是羞慚的道歉,也是根深柢固的生存習慣。
阿順姆婆轉過身、別過臉,用無感及無禮來反擊。在這節骨眼上,身為女人的最大好處,就是不必虛情假意。
但是,老伯公也沒虛情假意,他大度大量,點頭回禮了。當村長當了那么多年,替日本人當差的痛苦及無奈,他吞忍最多了,怎么忍心責怪這群小輩?
把牛繩交到阿隆手里,老伯公無言。
牛阿母也無言,卻死也不肯跟陌生人走。
它一被拉,牛頭就屈彎下來,脖子伸得長長的,像彈簧被扯到極限;四只腳蹄蹬住地,死命撐著,用頑強的拔河,進行最徹底的抗拒。
小牛犢傻頭傻腦的,搞不懂發生什么事?阿母的奶頭含不住嘴,滑掉了,吸不到奶汁,它有些怔忡,東張西望,焦急著:“哞!哞!”一聲聲稚嫩的抗議,驅趕不走降在母子倆身上的厄運。
人與牛的拔河僵持著,那是永不妥協的爭斗。它像黑色的巨巖。沒人拉得動龐大又固執的母親。
為了完成日本人下的使命,阿隆第二度向這一家人彎腰道歉,那是先禮后兵的宣告。
緊接著,官方的粗暴與蠻干就上場了:小牛還沒貫上鼻環,兩個人拽著它的一雙耳朵拼命拉;另兩個人再頂著、推著牛屁股,小牛犢就被迫推向前了。
小牛一起步,那只生身阿母,即便是要上刀山、下油鍋,也會緊緊跟著去的。
這一演變,太突兀、也太可惡了。
不想讓小牛犢也變成日本兵的嘴上肉,阿順伯公的大兒子走了出來,一臉的悲憤,也一臉的承擔。他一把搶過牛繩,按住脾氣,沒揮拳揍阿隆,只一步步導引著母牛走出牛寮;也示意阿桐去安撫那只小牛犢。
慢慢地,劍拔弩張的情勢松解了,黑色的巖石移動了。大母牛被熟悉的主人牽著、領著,不再頑強抵抗。四只牛蹄動了,一腳一腳踏向前。
是為了要保護親生孩兒?或只是聽從主人指揮慣了?它緩緩踏出去,一步又一步,走向既定的命運─臺灣牛的命運。
它沒回頭,也回不了頭。
所有的人,卻都清清楚楚看見,看見那一雙溫和又充滿信任的大眼睛,冒出、涌出清澈的淚泉,沿著粗硬的牛毛,一顆顆滑下來,滴落在主人家的泥土下。
阿順伯公在背后大喊:“阿隆!拜托一下,去到現場時,貫在牛鼻的鐵環,一定要替伊鉸開喔!”
“千萬要替伊鉸開喔!”……
聲音喑啞下來,重復著,最后,只嘟嚷在雪白的胡須里。
太陽高高升起了,烈得像刀子,扎刺所有的人。小阿桐沒哭,一滴淚也沒掉!他真的做到了。
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男子漢。
就這樣,牛阿母走了,小牛犢面臨生死存亡的大關卡,每一個人都拼足了勁想救它。
可是,要怎么救呀?
小牛犢還不太會吃草,日夜“哞!哞!”哀嚎著,呼喚它不見了的生身阿母!阿桐一放學,藺草書包往屋里一丟,人就跨進牛欄,頂著小牛犢的頭,摟它的脖子、拍它的背,努力輸送一點溫暖給饑餓的孤兒。阿順伯公的老妻、媳婦、大小孫媳婦們,用摏米的大石臼,一槌槌、一杵杵,磨碎嫩青草來喂它、哄它、強迫它。可是,喝不到母奶的小牛犢,還是一天一天消瘦下去、耗弱下去。全家老老小小愁眉深鎖,痛到捶心肝、急到頓腳蹄,也找不到任何好辦法。
那天中午,大地下著茫茫春雨。老伯公晃晃悠悠走向牛寮。再怎么硬朗的身體,也熬不太住大戰爆發后,日本人雷厲風行的限米限糧。他餓到膝蓋發酸,全身虛脫。然而,更虛脫的是那只沒了親娘的小牛犢。它已經瘦到皮包骨,側身躺在干草堆上了。看到老主人進來,有靈有情的它,牛頭挺了挺,四肢蹬了蹬,卻是怎么掙扎都起不來。
老伯公蹲坐落地,輕輕抱扶起牛犢仔的頭,枕在自己的大腿上。兩只黑硬的大手掌,在小孤兒瘦嶙嶙的身軀上,來來回回摩挲。黑褐色的牛毛,一浪浪一波波,在他手心手指間翻伏、滑流,他想起了那只乖馴的牛阿母、那雙溫和又信任的大眼睛、那片在牛犢仔身上舔來舔去的紫紅色舌頭、那兩行滴落泥土的清澈淚水……
阿順伯公垂著頭,哼哼冷笑!牛一只只牽走了,一家家小囝仔,餓到變成猴猻樣……他抬起老眼問蒼天,不言不語的天,只落著茫茫的雨。大男人不能哭,老男人更是哭不得!在生與死、臺與日的秋千上,悠蕩了快五十年,他也真的從來沒哭過!但是,現在,他好想放聲大哭一場!
出門去想想辦法吧!
一層層、一畦畦,汪著水的梯田,正灑落千萬條雨煉,阿順伯公漫無目的走著。天光水光,一大片銀白,銀白的恍惚里,卻站著另一個痛哭的老人──工頭阿財。
“阿財!落大雨哪!你為啥恍神恍神?”
男人與男人的對話,必須只有關心,不能問起尷尬的淚水。
“哦!阿順叔!是您喔!”
數百年來,阿里山梅仔坑山區流傳著好禮數,所有的人按輩分、照年齡,自動排出合情又合禮的順序,無論是喊公或喚叔、稱兄或叫名,都恭敬又誠懇,像親密的一家人。
“無啦!我閑閑無聊,出來巡田水看山園啦!”阿財披著蓑衣,卻忘了戴斗笠。他吸一吸鼻腔,仰起花白的頭顱,涼涼冷冷的雨珠,迸跳在他黝黑的、阡陌交通的老臉上,遮掩了赤紅的眼眶,也沖刷掉滿腮的淚痕。
“阿財呀!無牛,無要緊!用人拖犁,慢是有比較慢,但總拖得過難關呀!”
阿順伯公把油紙傘移過去,撐擋漫天的梅雨;黑硬的大手掌,也拍向老侄兒的肩膀。他知道就在昨天,阿財家的耕牛也被征召了。
“所有鐵做的農具,也繳去給日本人了!哪還有犁可用?”
阿財一臉憤恨。憤恨過后,卻是一臉愧疚。用這種態度回答,對長輩很不禮貌,他警覺到了。
“阿順叔呀!這十幾層的梯田,當初,原本是含水含不牢的土砂。為了要栽種水稻,使全家能吃香貢貢、甜滋滋的白米飯,我只好用老祖公最笨最直、厚工又厚力的辦法來改土儲水。”
阿財的淚水可以暫時止住,思念卻永遠停不了。兩個老男人固然都愛面子,但是,最痛苦的時候,有人能說說話,又聽懂每一句話,面子就沒那么重要了:
“我帶領著四個后生、四個媳婦、十幾個孫子,駛著一只大水牛、拖一個重鐵犁,吭吭嗆嗆!將所有的硬土切開、犁開,足足翻土二尺深,撿掉大粒小粒無用、無肥份的土塊及石頭,用牛車將挖起來的土,全部搬開,再把擋水擋得牢的白堊石灰,鋪墊進田底,完全鋪好了,人和牛就出死力去踏,踏得密密扎扎,確定勿會漏水泄肥了,再將那挖起來的田土,運返回來鋪落去。然后,再灌田水、種稻秧,一年三期收割的蓬萊米,就飼飽我全厝內三四十人的嘴坑!”阿財叨叨絮絮著,有對大自然的誠敬,也有全家拼斗的滿足。
“那只大水牛,陪我日出做到日落。后來,自己的田耕好了,我又牽伊去犁別人的田、運別人的貨。我真正是沒良心,只顧著愛賺錢,將牛操到半死……”身為工頭,阿財糾集的不只是勤奮的農工,還有任勞任怨的大水牛。
“阿財呀!全梅仔坑,誰人不知你疼惜牛?七八月天,你怕牛熱到中痧,就熬煮清涼退火的青草汁去苦勸牛喝。年頭年尾大寒天,你換煮黑砂糖加姜汁來侍奉牛;出門拖車前,你還用熱滾滾、燒噗噗,噴白煙的大條面巾,將牛全身軀拭透透。無人像你這樣愛牛,惜牛若惜命呀!”同樣是傷心人,阿順伯公用體諒的語句,安慰著雨中的老農。
“一想到我的水牛,拖著迭得半天高的甘蔗或米袋,翻村過莊,毒日頭曬、西北雨淋;爬崎路時,爬到哞哞叫,大氣小氣噼啪喘,我心肝就像針在刺……我是粗魯人,死無天良的,有時,還用皮鞭一下一下抽牛、打牛!現在,伊又被日本人牽去剝皮刣肉……”雨中的老農悔恨交加,淚水真的如雨下了。
“不是咱們不愛不疼,是伊們命運歹,出生做臺灣牛。”再怎么強忍,老伯公的淚也被誘出來了。
天,依舊落著茫茫雨,遠山近山,綿延不盡的濕綠,籠罩無休無止的悲哀。兩個老人都垂著頭,不敢對望彼此的淚眼。
啊!惹長輩傷心是大不敬的。阿財趕緊先掐住自己的悲痛,扭轉話開題:“阿順叔!您、您、您飼養的那小只牛犢仔,有好好的否?”
雖然很努力,還是失敗了,話題還是在臺灣牛上面兜兜轉。
“哪有可能會好!小小一只牛犢仔,無牛母疼惜,無奶水可吃,早就瘦巴巴,只存一把骨頭,早慢會……會活活餓死!”一講到無依無靠的小孤牛,老伯公的心都碎了。
“阿順叔!我……我……”不小心在長輩傷口上灑了大把的鹽巴,阿財心里七上八下,抓耳又撓腮。
“這雨,唉!透早落到透晚,真正是落未完!”阿順伯公抹一把臉,眨眨眼皮、擤一擤泛濫的鼻水。再怎樣,老男人的面子還是要顧的,尤其是在晚輩面前。
“那……那只小牛犢,可……可能是咱們阿里山最后一只了!”阿財鼻頭又酸了。昨天,自家大水牛被牽走的痛,也排山倒海淹過來:“咱們全都乖乖的繳稅金、按時納米谷,絕對不是日本人所罵的刁民呀!”想到這里,他心一橫,下了重大的決定:“阿順叔!我、我、我有……”決心是下了,但是,要吐出這天大的秘密,還是免不了緊張。
“你有啥?唉!什么世面沒見過,嘴須也長得可以打五六個結了!還吞吞吐吐、瘖瘖喔喔,講不輪轉?”
“我、我有辦法,救、救您家的牛犢仔!”長輩的淚,沖垮了阿財最后的心防,他豁出去了。
“啥?啥辦法?”是陰天要露曙光?或是天頂要劈雷電?阿順伯公眼睛瞪直了,整個人像要撲上去。
“我……我在雞胸嶺,無人所到的山壁后面,偷偷飼……飼幾十只山羊仔!”
“夭壽喔!你還大聲講!”阿順伯公反射動作,真的撲向前,一掌就封住老侄兒的大嘴巴。一想到并沒有日本人或臺奸在旁,又立刻放開手,尷尬地笑了笑。
“戰爭時,偷藏物資不繳出來,是會被捉去槍殺或斬頭的。你喔!真是戇大呆,竟然敢犯這天條?”
“我哪會不知死活,只是不甘愿交出羊仔送日本人!”莊稼漢硬頸、硬肩膀,脾氣一犟起來,也是茅坑里的石頭,臭烘烘又硬邦邦。
“牛有編戶口,也有身份證,一只一張,日本人管得硬死死,每個月派人來調查兼登記,咱們一點辦法也無,只好看牛一只一只去送死……”阿財的喉嚨又哽住了。啊!那只在毒日頭下拉車,在大雨中犁田,還被他一鞭鞭抽打的大水牛呀!
“羊沒有身份證,比較小只,就比較好藏!”他低下頭,穩住咬牙切齒的憤怒,也收斂了報復的眼神:“那群山羊,我偷偷飼養很久了。”
“阿財呀!你勿要再對任何人講。現此時,我啥事都無聽到!若有聽到,也全部卸入江洋大海,忘記到腦殼空空了!”老伯公一臉誠懇。在日本的武士刀下,這是尊重別人又保護自己的可愛方法、可信默契。
“阿順叔,我是講真的,我有辦法,使你的小牛犢仔,免活活餓死!”阿里山的最后一只牛了,怎能不救?阿財握住老伯公的手肘,也急切又誠懇。
“這……這……”老伯公心念一轉,立刻猜中老侄兒想用的辦法。他有些驚喜,也有些遲疑。驚喜與遲疑進行拉鋸戰,戰得天昏地暗。
那辦法─真的救得活小牛犢,老伯公確信。隔壁李家的大兒子,從阿里山上救了只死了阿母,奄奄一息的小猴崽子。一抱進院子,那只名叫“哈莉”的大花母狗,就搖著尾巴迎上來,直接叼了去,混著一窩剛出生、還沒睜眼的小狗仔,竟然一起奶活了。奶大了之后,陌生人一到李家,小猴崽立刻皺鼻肉、露尖齒,又撲又吠的,活脫是另一只小哈莉。想到這里,老伯公的眉頭舒坦了、嘴角也向上揚了。
但是,身為一村的村長,戰爭時期,帶頭抗命,肯定是死路一條,連累一家子是必然的,若害全村被搜、被查、被羞辱,就更凄慘了。問題是:再不出手搶救,那只可憐的小牛犢,也保證活不了。怎么辦?老伯公搓揉著太陽穴,眉頭又皺了起來。
“阿順叔,您免擔心啦!每一日的黃昏,叫小阿桐到寒水潭那棵大苦楝樹的樹下等我。我交羊奶給伊提回去,請阿順嬸煮滾后放涼,再用奶罐子喂那只小牛犢吃。”阿財邊講邊想辦法,一心一意要救小孤牛。
“這……會不會換小羊仔餓死呀?”阿順伯公冒出一頭熱汗。
“免操煩啦!小只羊仔已經加減會吃草啰!而且,我就不相信,六七只羊母,一只擠一些乳水,還救不活一只牛犢仔?”老農夫不識字,但是,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根本不必書本來教。
“按這樣做,不只勞累你,也會牽連一大堆人,冒真大的危險!”風里來、浪里去的老村長,不得不替大伙人擔憂。
“橫直我的牛已經被牽去剝皮割肉了,我也老啰!勿想要再拼命種稻、拼命繳糧了。”失去水牛的老農,像泄了氣的皮囊,什么都不來勁了。但是,一想到阿里山最后的牛犢仔,正需要拯救,也唯有他能拯救,一股動力,又從他一根根肋骨間冒出來,來回奔竄于手掌及腿腳了:“我入去深山內,找一些野果吃,順便擠羊奶,裝入木桶仔內,再用姑婆芋的大片葉子蓋住,用草絲綁好箍緊,以免羊奶溢出來,也避免閑人看到。”
方法真的是愈來愈周全、愈來愈可行。阿順伯公嘴唇哆嗦了!有可能賠掉別人身家性命的大事,要他點頭答應,實在是掙扎呀!
阿財看出老伯公的憂懼,淡定地笑了笑:“您老大人,再想就想過頭了。就算真正被閑人看到,除非是日本走狗,也應該勿會歹心污腸肚,真正去報官啦!”最后一只牛犢囝仔了,讓阿里山的好牛滅種,人蒙羞、天難容呀!
“阿財!真多謝、真多謝!‘人在做,天在看’,不只天公伯在看;那只牛犢仔的親生阿母,伊在天頂,也一定會看到、會感謝你的!”
灑落人間的雨絲,粗粗細細,一會兒急、一會兒歇,不管浩瀚的天空里有沒有神明、有沒有牛阿母,兩個老人都已準備好,要盡全力拼了。
分別前,面子問題又出現了。兩個老男人在雨中掉淚,不管理由多充足,總是羞死人!阿順伯公瞅著老侄兒,摸摸自己雪白的胡子:
“阿財!我看哪!還是要認真考慮。萬一,我的牛犢仔吃甚多羊奶后,一開嘴,就‘咩!咩!’學你的山羊仔亂叫,那就凄慘落魄了!哈!哈!哈!……”
兩個老人都笑開了,笑聲中夾帶著強烈的不安。但,心橫了、牙根也咬緊了,不管怎樣,先救小孤牛再說。救活了,邊養邊想辦法,不管是假報牛的死訊,不管是拿金戒指、金項鏈去賄賂臺奸,只要認真想,一定會想出好辦法來!
雨還是落,回家的路上,依舊天光水光,白茫茫一片。盡管黃梅雨下的沒完沒了,但阿順伯公覺得腰腿來了勁,有力量再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