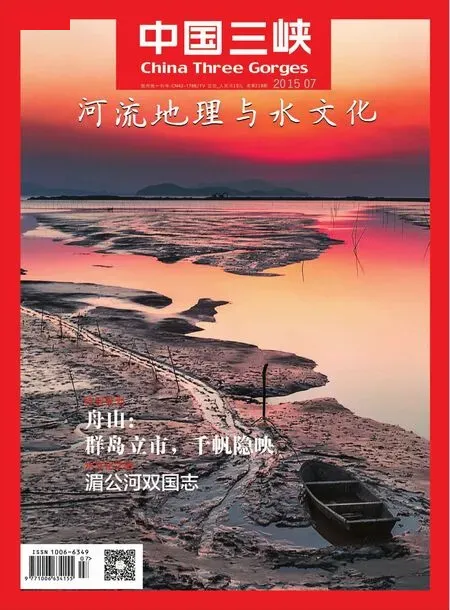上丁:靜水深流中的捉迷藏
文、圖/喻添舊 編輯/李顏岐
上丁:靜水深流中的捉迷藏
文、圖/喻添舊編輯/李顏岐
在遠離城市的河谷深處,清澈的河水倒映著白云和藍天,樹木在微波的晃動下成為幻象。涉禽悄無聲息地往返沙丘之間,只有馬達突突的聲音驚擾著無人的四方,白色的浪花在船尾翻起并很快消失不見。
這不是我第一次到達老撾了——我的意思是,我一天前曾從柬埔寨乘船逆流而上,到達邊境。湄公河寬闊且彎曲回折,我的手機信號一會兒顯示著柬埔寨電話公司,一會又收到了老撾電話公司的歡迎短信。我乘船出發的那座柬埔寨城鎮叫做上丁(Stung Treng),它是距離觀看江豚的地方最近的邊境落腳城鎮。
最近的幾十年來,上丁除了一條塵土飛揚著,如同街邊燒烤揚起的煙霧一樣的城鎮主干道,就沒什么值得自豪的了。但是它卻是通往湄公河最為原生態的一段的起點。通往北部的公路修建完成,使上丁成為柬埔寨到老撾的口岸近境,這比它的鄰居城市桔井更為便捷,后者一度是柬埔寨東部與越南老撾中轉的交通樞紐。
慢慢步行不用2個小時,就可以把上丁逛個遍,你需要留意的大約僅是一臺可以用VISA卡提取美金的ATM機,兩座小巧但有些殘破的寺廟,以及一家由中國人開設的超市。我驚訝于他千里迢迢地討生活,他驚訝于我風塵仆仆地背包行,一切都是因為相聚的這個城鎮太小了,小到鄉人偶遇也是一種奢侈。一座市場幾乎占據了整個城鎮,還有美得令人驚嘆的湄公河,對于上丁來說,或許這就已經足夠了。
河畔不知名的寺廟更像是一間寄宿學校,中午時分安靜無人。教室里桌椅簡陋陳舊,墻上掛著柬埔寨國旗和西哈努克的畫像。兩位身披僧袍的小沙彌正在教室里休息,我的“突然闖入”卻令他們開心。或許是對我手中的相機產生了興趣,他們拉著我登上教室外佛塔頂端的“藏經閣”,那里如今存放的是課本和資料。書中的文字我一個都讀不懂,只看明白了吳哥寺的圖案,這座柬埔寨的國家地標被印刷在課本上、啤酒上,國旗上、簽證上,以及一切用來代表柬埔寨出品的驕傲物件上。另一座臨河的寺廟中,正在修建新的大殿,辛勤勞作的都是僧侶,這與一些國家中充斥著的供人游覽的寺廟不一樣。沒有人“建議”我燒一炷香或拜一拜雕像,看起來好像是住持的老僧人關心的是我夜宿在哪里,似乎相當愿意為我提供一間免費的禪房過夜。我回答說就在主路旁的客棧里——那里的風扇對于如此悶熱的空氣來說簡直是神的恩賜。他點點頭,喃喃自語:“若不是這條大河,上丁會更加炎熱。Mekong(湄公)。”
他說的話頗有具象意義。上丁的湄公河,在灌溉堤岸上稀疏的農田,提供運輸的動力之外,更多地為人們提供了消遣和生存之外的價值。長長的棧道延伸至大河中心,沿線成為了人們的釣魚場、游泳池、觀景臺。水是不花錢的,亦是上丁永不窮盡的公共資源,當地人在這里洗去身上的塵埃,洗去衣服上的汗漬,也洗去車上的油污。湄公河洗去了上丁一切不干凈的東西,甚至連人們靈魂里的不潔都凈化掉了。所有人都以微笑面對他人,不論是市場里的商人,還是棚戶屋里的流浪漢。
從上丁出發去看江豚的價格不菲,船是單馬達的長尾木船,由一個當地船夫駕駛,到達柬老邊境的江豚出沒處,需要花費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高昂的費用和漫長的顛簸是相當值得的,要知道,沒有任何一段湄公河的風光如上丁邊境這般瑰麗與壯闊。在遠離城市的河谷深處,清澈的河水倒映著白云和藍天,樹木在微波的晃動下成為幻象。涉禽悄無聲息地往返沙丘之間,只有馬達突突的聲音驚擾著無人的四方,白色的浪花在船尾翻起并很快消失不見。
旱季的湄公河波瀾不驚,但從露出水面的樹干和樹枝形狀可以清晰想見季風時的河水兇猛。繁茂的樹根幾乎橫著生長,被流水拉扯著如同瘋人的亂頭發,也像被狂風吹襲的裙擺。水位下降之后,潮濕的樹根變得堅硬,與斜生的枝干葉一起,成為湄公河上傷痛的風景。少有人家住在沙丘之上,簡易的窩棚并不是他們的家。當河水蔓延的時候,他們不停地從一座島嶼搬遷至另一座島嶼,只有船,才是湄公河之子的唯一依靠。
在靜水深流的水下,生活著伊洛瓦底江豚,這種亞洲瀕危物種數量越來越少,據說在邊境只有不到70只存在了。當長尾船的馬達關閉,世界重新安靜的時候,你聽得到江豚的呼吸聲。順著水花輕輕被彈起的聲音搜尋,或許那灰藍色的可愛家伙就在眼前。在柬老邊境觀看江豚不會令人失望,這種即使曾經遭受大批獵殺卻依然親近人類的動物,從不吝嗇于將它光滑的背脊和鰭翻出水面,但是你需要做的是平心靜氣地等待,先與它玩一場有意思的捉迷藏。

上左:一些柬埔寨人仍然住在沙丘之上,他們是湄公河之子。

上右:簡陋的窩棚是他們暫時的家。

下:湄公河江豚的數量急劇減少,但是在邊境的河流中依然可以見到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