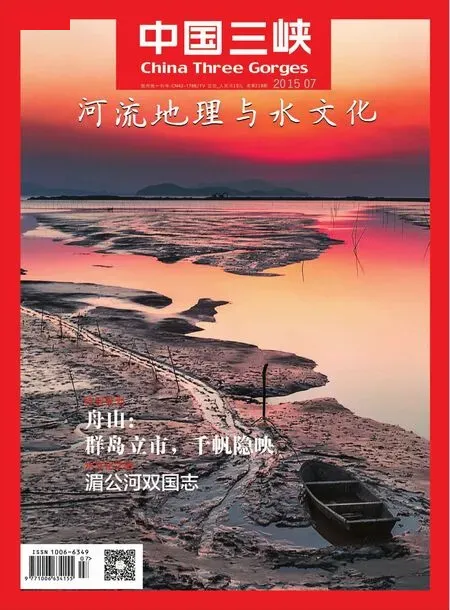金邊:向水而生
文、圖/喻添舊 編輯/羅婧奇
金邊:向水而生
文、圖/喻添舊編輯/羅婧奇
如今的金邊被認為是一座“時尚”的“現代都市”,我想這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起初金邊人放棄了吳哥式的建設規則:沒有站在高高的山上才可俯瞰全景的佛塔,沒有用巨石搭筑成的寺廟群,沒有紀錄國家歷史和君王功績的浮雕墻,亦沒有寬闊流淌并由神像守護的護城河——洞里薩河和湄公河在此匯聚就已經足夠了。
也許再沒有任何其他一座東南亞的首都如金邊這樣有著清晰的歷史脈絡和單一的城市傳說了。傳說一名叫做“Penh”的老婦人,在湄公河畔發現了四座佛像,仿佛是神明的引領,她將佛像供奉在附近的小山上,山下逐漸發展出的城鎮就是金邊(Phonm Penh,意為“Penh的山”)。
城市向水而生。
穿城而過的湄公河為積重難喘的國家帶來了活力與復蘇的可能。金邊這座曾被稱為“四面城”的新首都既可以接納洞里薩湖出產的豐富物產——魚貨和陶器,也可以控制通往河流上游老撾的貿易,更可以輕松囊括由越南三角洲地區中轉的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
農業生產再也無法成為國家的經濟支柱,盡管新首都的水利資源比起舊時代豐富了無數倍。你若是通過方便的陸路邊境由越南進入柬埔寨,會感覺到兩個國家農業發展水平的明顯差距。前者的農田一年收割2~3季,機械化助力著東南亞優良稻米的出口;而金邊的道路兩側卻大部分時間都是充滿凄涼感的白黃色,瘦弱的牛行走在田間,不是在耕地而是在覓食。這種眼前即視的情景變化跟氣候和地域無關,國界像一道閘門,毫無預兆地切斷了同樣接受湄公河水滋養的兩塊相鄰土地的聯系。
如今的金邊被認為是一座“時尚”的“現代都市”,我想這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起初金邊人放棄了吳哥式的建設規則:沒有站在高高的山上才可俯瞰全景的佛塔,沒有用巨石搭筑成的寺廟群,沒有記錄國家歷史和君王功績的浮雕墻,亦沒有寬闊流淌并由神像守護的護城河——洞里薩河和湄公河在此匯聚就已經足夠了。
在經過了命途多舛的600年之后,很難相信金邊人仍然會對宗教有真正意義上的虔誠,盡管祈禱和朝拜不停歇地在湄公河畔點燃城市的熱情。過去歲月里,泰國和越南的反復侵入令金邊人到今天都對這兩位鄰居感到不悅;法國人擁有的“印度支那”的“保護”范圍也包含了柬埔寨,他們曾經捏住了柬埔寨僅有的經濟咽喉——木材砍伐,但至少為金邊留下了今天仍在使用的城市格局體系;之后的“紅色高棉”幾乎摧毀了這個國家一切古老的榮耀,也包括人們的精神信仰和高棉民族本就羸弱的抗爭意識,這種如埋葬整個世界一樣的破壞比起吳哥帝國時期的任何一次變革都更加慘痛。現在的金邊人寧愿選擇遺忘或者閉口不談,傷痛正在愈合,就像湄公河上的航船駛過后合攏的波瀾。
沒有豪華的高樓大廈,即使是通常被認為是黃金地段的濱河路。高大的椰樹和保留殖民時期風格的酒店扼守著街道兩側,酒店屋頂的露臺安置著太陽浴躺椅,在雨季到來之前的日子里尤其受到歐洲游客的歡迎,他們在遠離喧囂的地方享受著與湄公河有關的優雅旅行。摩托車呼嘯而過,攪動著河上吹來的熱風,穿過一輛輛屬于權貴階層的大型汽車和屬于“金邊窮人”的腳力三輪。渡船往返于寬闊的河道兩岸,它們幾乎都不具有游覽功能,而只是構成城市公共交通的必要工具。

下:大朵的花蕾被整理準備,作為祭祀的獻禮。
當太陽偏西,灑下金色光輝的時候,河岸上聚滿了人,一場祈禱的儀式馬上就要開始。所有人都帶有鮮明的標簽,他們屬于不同的階級,不同的職業,懷著不同的目的,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們有著不同的精神狀態,享受不同的生活品質,他們每人都是組成新時代的金邊人的不可缺席的部分。農民或小商販將含苞待放的花朵捆扎,它們是粉色或白色的,并與削掉表皮的椰子和三支香束組合在一起。面色憔悴、泥垢滿身的孩子大多是無家可歸的乞丐,他們以低廉的價格售賣椰子蠟燈(確實也不值什么大價錢),以便換取一天的晚餐。“One dollar, let them free!”一位提著籠子的婦女向我推薦她的商品,籠子里裝滿撲騰亂蹦的活麻雀。金邊人認為買下兩只被困的麻雀拋向空中,可以借由“解救生命”來消除孽障或實現愿望,這個過程必須伴隨雙手合十的閉目祈禱才有效。不管實際效果如何,花費1美金尋求心理安慰對于城市中人來說確實不算什么,但基本上沒有外國游客參與到這個被稱作“放生”的游戲中來。
朝拜在河邊的亭子里舉行,無數鮮花和香支插入祭壇,再轉而通過神職人員的雙手堆滿亭子窗口外的垃圾箱,這看起來十分浪費。祈禱跪求之后,人們獲得的回饋是供過的水果,香蕉或龍眼居多,數量并不確定。這些虔誠的儀式參與者中,不乏染著紅發的時尚女孩,或塞著耳機用手機聽歌的青春少女,“放生”麻雀后,她們在Facebook上如日記一般寫下期待實現的愿望,她們與北京、首爾或是吉隆坡的年輕人沒有區別,盡管整個國家相比起來要衰弱得多。
在儀式的外圍,更加隨意的“對人生奧義的追尋”也在發生著,用寬大的帽子遮住整個頭臉的人以撲克牌占卜命運,她的客人也是漂亮的女士,在金邊這個城市里,女士尤其喜歡以看似傳統的方式改變令自己不滿意的生活現狀。
那些跟隨父母家人而來的孩子并不參與儀式,河邊的空草地是他們的游樂場。他們穿著鮮艷的衣褲和花裙子,根本不介意紅配綠的撞色搭配。一只氣球,幾個伙伴就能快樂地度過整個黃昏,直到夜幕下的街燈將影子拉長。無憂無慮的天性是什么時候被改變的呢?向身外之界祈禱是因為什么成為習慣的呢?或許心界與眼界有關,世界大了,心就變了,那一條條陳舊陰窄的巷道,遲早無法再承載人們作為“家”的期待。
金邊的許多老舊居民小區都如我們常說的城中村一樣存在。長久以來的隨意搭建令窄如胡同的樓間路變成了缺少出口的迷宮,看起來年代久遠的佛像浮雕豎立在小區入口,好像你正要進入一座寺廟。奇怪的物件組合到處都是,配電箱順著電線桿一路向上排列,仙人掌粗壯地生長,磚墻上的藍色玻璃窗從來沒有被打開過。但卻沒有人關門,家門口是人們最喜歡耗費掉一天無聊時光的地方。未完成的佛像堆滿院落——這里的許多人家正在政府的支持下,進行恢復傳統佛像制作工藝的工作,堆放更多的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摩托車。所有人都對到訪的陌生人無比歡迎,尤其是對中國人,因為這兩個國家從未有過交惡的歷史。剪刀手和微笑是世界通用語言,無論大人還是孩子,都毫不吝惜于自己的熱情。金邊的老城區里沒有欺詐也沒有騷擾,這與東南亞很多國家的今日狀況都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