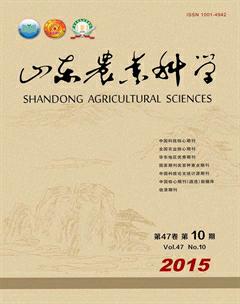中國家庭農場的功能和實施原則研究
楊永前 王文生 于曉翠 楊曉飛 江學淮
摘要:結合農業屬性和家庭農場特性及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新需求,深入剖析了中國家庭農場在21世紀前期應該具備的時代功能,并進一步分析了促進家庭農場功能實現而應遵循的實施原則,以期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參考,讓政策工具有效促進家庭農場時代功能的實現。
關鍵詞:家庭農場;功能;實施原則;糧食安全;邊際改革
中圖分類號:F324.1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1-4942(2015)10-0145-06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從國家政策層面以具體的支農措施來推進家庭農場發展。2014年2月24日,農業部下發了《關于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至此,發展家庭農場已經進入農業部及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目前,我國家庭農場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地方政府對家庭農場的界定標準和支持措施各異,有較多的家庭農場還處在微利和虧損狀態;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急需提高,家庭農場的發展動力急需鞏固,支持家庭農場發展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急需明確。為此,有待學者和業界在理論和實踐上深入研究我國21世紀前期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的家庭農場應該具備的時代功能和推進家庭農場發展的實施原則。
121世紀前期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賦予家庭農場的時代功能
農業的特有屬性和家庭農場的自身特性及社會特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現狀對農業所產生的相關需求共同賦予和呼喚著家庭農場特定時期的時代功能。家庭農場的功能是為了滿足所處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是所處時代通過制定的政策機制和基于農業的特有屬性和家庭農場的自身特性而實現的既定功能。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農業屬性和家庭農場的自身特性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會造就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家庭農場具有部分共同的特性和功能;但由于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不同,由此而對農業相關的需求有差異,導致各國的家庭農場在具有共同特性和功能的同時還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和功能。在同一個國家,由于所處的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不同,進而對農業的相關需求發生部分變化,會導致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家庭農場的功能隨之發生局部變化和調整。
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進入新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狀況、新問題和新需求。要應對農業比較效益較低、農業兼業化、農村空心化、農民老齡化,解決誰來種地、怎樣種好地的問題;我國不斷增加的人口對農產品總量的需求與我國農業資源稟賦的硬約束之間形成的對糧食安全的挑戰;農業資源的過度承載和傳統小農戶散亂差的耕作方式及其市場交易中的“隱匿交易者”身份造成的農業耕地資源環境惡化及農產品污染與消費升級中人們對食品質量的更高期待之間形成的食品安全的挑戰;城鎮化對二、三產業就業人員的需求及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對農村勞動力的解放和擠出形成的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問題和富余農村勞動力的農村就業保障問題;與“新四化”的短板農業現代化相關聯的“三農問題”;對當代農業科技成果的合理運用和實用性檢驗來探尋最適合我國現階段國情的農業生產組織結構和生產方式,對農業進行邊際改革和推動農業長期穩定發展的課題。21世紀前期,上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問題及需求以及農業的屬性和家庭農場的特性共同賦予我國家庭農場具有如下時代功能。
1.1運用家庭農場的規模效益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背景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迅猛發展,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戶的農業比較效益進一步降低,“種糧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嚴重挫傷了農民從事農業的積極性,導致很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就業,為家庭尋求二、三產業較高的比較效益。農村出現大量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及其粗放經營耕地和拋荒耕地的現象,浪費了稀缺的耕地資源。而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導致單個農戶耕地面積減少,農業機械化使得單個農戶農業生產能力大幅提高,單個農戶的耕地數量已無法吸納單個農戶全年的農業生產勞動時間,單個農戶耕地的平均產出也無法提供單個農戶全年生活生產等消費支出,導致對農業有明確職業傾向的農戶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而難以持續從事農業生產。可見,在這些問題的壓力下,原來傳統小農戶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農村生產關系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需要在承包戶自愿、公平和有償的基礎上,讓不愿耕種農地的承包戶把農村土地的經營權流轉給愿意耕種農地的農戶,讓愿意耕種農地的農戶獲得足夠吸納單個農戶全年農業生產勞動時間的規模耕地,進而讓流入農地的農戶獲得農業生產經營的規模效應,使農業的比較效益提高到與第二、三產業相當的水平,讓單個農戶規模耕地的產出能夠維持單個農戶的生活和生產的消費支出,讓流入農地的農戶愿意持續穩定從事農業生產。農業的規模效益可以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進而吸引更多年輕的新型職業農民帶領自己的農戶家庭成員專業從事農業生產,形成穩定高效的家庭農場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由此,要運用家庭農場的規模效益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進而培育家庭農場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來應對農業兼業化、農村空心化、農民老齡化,解決誰來種地和耕地資源浪費的問題。
1.2家庭農場對科技成果的轉化助力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農業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石。任何一個國家的農業都具有公共品屬性,都需要為本國人提供糧食安全保障。197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將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定義為“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糧食”。萊斯特.R.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人》給我國的糧食安全敲響了警鐘。
據《世界人口展望》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14億。隨著我國人口的不斷增加,面臨著國民對農產品消費總量不斷增加的需求與我國農業資源稟賦硬約束之間的矛盾,需要應對糧食安全的挑戰。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國人口總量已達到13.7億人,比2000年增長了5.84%。而我國耕地數量卻在逐年減少,2001~2008年,全國耕地面積由19.14億畝減少到18.26億畝。我國人均耕地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約相當于加拿大的1/16、俄羅斯的1/10、美國的1/7、印度的1/2。農業生產離不開水資源,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資料,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約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實施,高樓大廈在大片良田沃野上拔地而起,18億畝耕地紅線經受著沖擊和考驗。在這些農業資源稟賦的硬約束下,卻要不斷增加農產品產量來滿足13.7億及以后不斷增加的中國人對農產品總量的需求,這就需要提高農業生產中的科技要素。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傳統小農戶家庭分散經營,將土地劃分成小地塊,無法進行機械化生產,嚴重阻礙了農業發展。因此,需要創新比傳統小農戶更具活力和效率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引導新型職業農民通過耕地流轉集中建立家庭農場,來形成適合現代農業機械化和農業信息化等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成片見方的耕地,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從而增加農產品總量。這有利于消化國民對農產品總量上不斷增加的需求與我國農業資源稟賦硬約束之間的矛盾,助力解決中國糧食安全問題。endprint
1.3家庭農場的身份明確度和統防統治的耕作方式助力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我國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國民的消費升級,面臨著國民對農產品質量不斷提高的期待與我國農業生態環境惡化、農產品質量問題令人焦慮的矛盾,需要應對食品質量安全的挑戰。我國糧食自1998年至今已取得了十三連增,在人均耕地等資源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況下,用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但為此,掠奪性的農業復種指數的增加及化學肥料和化學農藥的大量使用已導致我國農業的耕地資源退化和污染,地表地下水資源污染嚴重。傳統小農戶短時期兼職從事農業生產,購買農資和銷售農產品都是在市場上隨機進行,導致傳統小農戶實際上是市場交易中的“隱匿交易者”。由于身份在市場交易中具有隱匿性,導致農產品質量問題難以追溯和追責到傳統小農戶,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傳統小農戶的擔當心態和加劇了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媒體經常曝光的“毒生姜”、“毒西瓜”等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都與無法有效追溯的小農戶散亂差的耕作方式及其消極的擔當心態相關。而家庭農場需要經過地方政府登記,家庭農場的家庭成員專業從事農業生產,要頻繁地在市場購買農資和銷售農產品,導致家庭農場具有市場中的“公開交易者”特性,這有利于農產品的質量追溯和追責。家庭農場為了獲得穩定的訂單,就有更多的動力去按照農產品質量要求進行農業生產,從而有利于食品質量安全。更為重要的是傳統普通農戶劃分的小塊田地在病蟲害防治時,相同區域的分屬于不同農戶的小塊田地耕種的作物品種及所生的病蟲不同,無法做到統防統治。病蟲利用不同田地施藥的時間差在相鄰的小塊田地之間來回遷徙躲避,直接導致施藥效果降低和施藥次數增加,帶來農產品農藥殘留增加的不利后果。而家庭農場為了提高病蟲害防治效果和節約用藥量,都會在成片見方的耕地上進行統防統治,這將減少施藥次數和施藥總量及降低農產品農藥殘留,助力食品質量安全。
1.4家庭農場助力解決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就業與農村就業保障問題
家庭農場的規模大小及使用的農業機械多少決定了所在農村區域的農業就業崗位的多少。家庭農場就業的彈性空間既要為城鎮化和工業化輸送就業大軍,又要為城鎮化和工業化階段性無法完全吸納農村待轉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提供農村的緩沖就業,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農村就業保障機會。一方面,為了讓中國從傳統的農業大國發展為農、工、商齊頭并進的發達國家,2014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解決好“三個一億人”問題,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這是對“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城鎮化戰略的進一步細化,這意味著要讓農村逐步提高的生產力所逐步解放出來的剩余勞動力逐步轉移到城鎮進入二、三產就業,為城鎮化和工業化輸送就業大軍。另一方面,受國內和國際多種經濟社會因素影響,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過程是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是漸進的、螺旋上升發展進步的,城鎮的二、三產業有時階段性還無法完全吸納農村待轉勞動力,有時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民工因宏觀經濟惡化或其它外界因素或個人原因又回流到農村生存,農村要為這些還沒有被城鎮化和工業化吸納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農業就業機會。
在現實生活中,工業化和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勞動力自發地從比較效益低的農業轉移到比較效益高的城鎮二、三產業就業。但是,我國城鎮一直面臨著就業壓力。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達5.1%左右。尤其是在我國勞動力、房地產等生產要素價格明顯高于東南亞及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導致一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東南亞及非洲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產業資本流動的背景下,農村的耕地需要發揮著為階段性還無法被城鎮二、三產業吸納的農村待轉的剩余勞動力以及從城鎮回流到農村生存的農民工提供農村就業的功能。在這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下,既要引導耕地向家庭農場流轉集中,創新規模農業,增加資金和農業科技及農業機械等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來發展農業生產力、解放農業勞動力,為城鎮化提供就業大軍;又要讓規模農業適度,不能不顧現階段國情而過度通過機械化來擴大單個農戶的大規模家庭農場的農業,導致單個農戶家庭農場的資本密集型的機械農業使用資本和機械等生產要素不合時宜的超前搶走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村的就業和生存機會。因此,家庭農場的規模要適度,要適合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吸納就業崗位的程度和農村勞動力富余狀況等基本國情;要契合我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與機械成本消化等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運用家庭農場規模化和機械化程度塑造農村就業的彈性空間,既要及時解放農業勞動力為城市有序輸送二、三產業勞動力,助力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實施;又要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農村就業和生存機會,保障農村穩定就業。
1.5家庭農場助力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穩定
2014年農業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農業現代化目前仍是我國“新四化”突出的“短板”。“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的重要問題,它直接導致了農業現代化成為“新四化”的短板。解決“三農”問題,最核心的內容應該就是農業要增產增效、農民要增收、農村要穩定。只有農業增產增效,農民才能增收;只有農業增產增效,農業對糧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對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撐作用才能得到鞏固和加強。只有農民增收,農村才能穩定。只有農村穩定,才能為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利的宏觀環境。因此,要通過流轉集中土地發展家庭農場,用適合農業生產特有屬性的家庭農場的家庭成員耕種方式和適合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高效管理的家庭農場規模農業來使農業增產增效。但要保留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不變和流出耕地的農戶的土地承包權不變,這樣,就使得流出耕地的原承包戶基于土地的農村集體所有權和承包戶的承包權不變的法律基礎來持續的獲得租金收入,而參與和分享到農業增產增效的收益。基于耕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離進行耕地流轉集中的制度設計,促使流入耕地的家庭農場與流出耕地的農民共同增收,持續鞏固農村的和諧穩定。運用家庭農場的效率和農村土地三權分離的制度設計共同造就農業增產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穩定的良好局面,助力解決“新四化”的短板和實現農業現代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