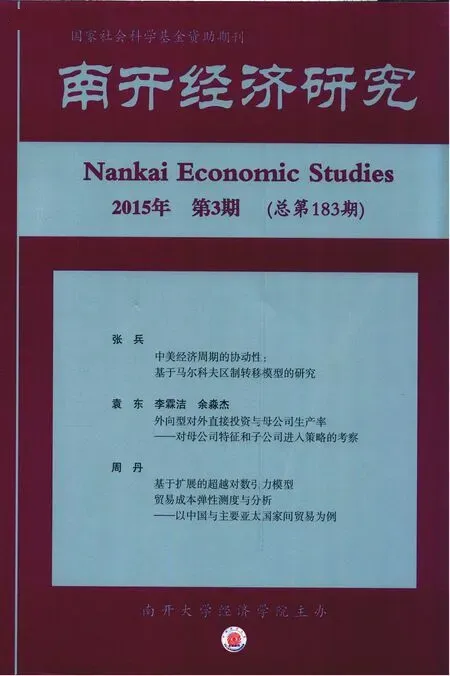外向型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公司生產率——對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進入策略的考察
袁 東 李霖潔 余淼杰
一、引 言
21 世紀初期,中國啟動了“走出去”戰略,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進行對外投資。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和企業數都有了迅速增加。各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我國2002 年①2002 年中國開始建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至2013 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年均復合增長率達37.57%,,從2012 年開始成為僅次為美國、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境內投資主體數存量從2003 年的1975 家到2012 年超過16000 家,分布在全球179 個國家(地區)。
不斷增長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影響本國經濟,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母公司的生產率。本文主要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母公司生產率的影響,并著重探討不同母(子)公司特征如何影響對外投資的生產率效應。
本文通過運用商務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庫以及作者搜集的子公司進入模式的微觀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我們發現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會提高母公司的生產率且這種提升效應從投資后第二年到第四年逐漸增強。我們還發現企業吸收能力和企業所有權屬性等母公司特征會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投資目的地、子公司進入模式的差異也會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此外,我們考察了避稅天堂等對于對外投資生產率效應的影響。雖然以前也有文獻探討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公司就業、產出、技術等帶來的影響(如Lipsey,1995;Blomstr?m et al.,1997;Branstetter,2006;Barba Navaretti et al.,2010;Chen and Yang,2013;趙偉 等,2006;常玉春,2011;毛其淋、許家云,2013;蔣冠宏等,2013 等),卻少有運用中國全國層面的跨多期的微觀企業樣本并深入探討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進入策略如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的文章。
首先,本文使用改進后的Olley 和Pakes(1996)方法(簡稱OP 方法)來度量企業的生產率①在穩健性檢驗部分我們也使用了Levinsohn- Petrin(2003)方法來度量企業的生產率。,特別是將是否有對外直接投資這一虛擬變量加入到生產函數的估計中,避免了因未考慮此因素而可能帶來的生產函數估計偏誤。由于選擇性偏誤和聯立性偏誤的存在,直接用OLS 方法估計索洛殘差得到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是有偏的,必須考慮到各個企業的特點,用修正后的OP 法才能準確度量企業生產率(如De Loecker,2011;Yu,2014)。其次,我們使用了2002—2008 年中國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年度調查數據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據來估計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企業生產率的即期和長期提升效應,可以有效避免宏觀數據帶來的統計誤差(Holz,2004)。為了控制生產率高的企業可能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自選擇效應,我們采用了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方法為對外直接的企業選取對照組。最后,本文不僅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整體層面的生產率效應,還著重考察了不同吸收能力、企業所有權屬性等母公司特征以及子公司所在國和進入模式等子公司進入策略對于生產率效應的異質性影響,這拓寬了對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生產率效應因素的認識。
事實上,在國內外已有相關文獻研究了外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即,OFDI)給投資企業、母國帶來的學習效應。Van Pottelsberghe 和Lichtenberg(2001)運用1971—1990 年美、日等13 個工業化國家宏觀層面的數據,得出在研發密集的國家進行投資會提高母國生產率,但研發密集的國家在其它國家投資不會提高東道國的生產率。Branstetter(2006)采用專利引用數據衡量知識外溢效應,得出了日本企業在美國投資既促進了美國本土企業知識的進步,也促使了日本母公司技術的進步。Pradham 和Singh(2009)使用印度汽車行業1988—2008 年的數據,說明印度汽車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使其母公司能夠獲得國外技術和市場信息,從而提升了母公司的研發密集度。Navaretti 等(2010)使用意大利1993—2000 年跨國公司的數據,發現OFDI 提高了意大利企業國內的生產率。Chen 和Yang(2013)使用中國臺灣地區制造業1992—2005 年的面板數據,發現中國臺灣地區制造業企業的OFDI 與其地區內的研發支出顯著相關,且在研發密集型行業中尤為明顯。基于1985—2004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宏觀層面的數據,趙偉等(2006)研究發現OFDI 對我國技術進步存在正向影響。利用我國國有大型企業2007—2008 年的數據,常玉春(2011)研究發現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的專利發明有顯著正向影響。基于2005—2008 年我國技術研發型對外投資的工業企業數據,蔣冠宏等(2013)研究發現企業的技術研發型外向FDI 顯著提升了企業生產率。
然而,并非所有文獻都證實了OFDI 生產率效應的存在。Braconier 等(2001)實證檢驗了外向型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會影響母國生產率。運用瑞典企業和行業層面的數據,他們并沒有發現由OFDI 引致的生產率提高。基于17 個OECD 國家1973—2000年的數據,Bitzer 和Kerekes(2008)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并沒有發現與OFDI 相關的技術外溢。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對于對外直接投資是否能帶來企業生產率提高這一問題,以往的研究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本文運用微觀企業層面的數據,不僅從總體上檢驗了外向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還分析了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進入策略對于對外投資生產率效應的重要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生產率效應異質性的研究是本文的重要貢獻,而且這有利于理解以前文獻在OFDI生產率效應上為什么會得出不同結論。
另外,本文的研究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雖然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最近幾年取得了巨大進展,但各種投資失敗的案例也經常見諸于新聞報刊。那么我們必然要問: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效究竟如何?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進入模式又會如何影響這種生產率效應?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增強對于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成效的理解,并對于引導國內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本文的主要創新點如下:其一,本文不僅研究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公司生產率的總體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考察了企業吸收能力、所有權屬性等母公司特征以及投資區位、進入模式等子公司進入策略對于這種生產率效應的影響。其二,相比于以前的研究,本文在生產函數估計方面更加精準,在估計生產函數時考慮了是否出口、是否進行了對外直接投資等可能影響企業生產函數的因素,從而有效避免了以前文獻未控制可能影響企業生產函數的因素而導致的生產率估計偏誤問題。
二、數 據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三個部分:一個是“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了全部國有企業和年銷售收入在500 萬元及以上的非國有工業企業①事實上《中國統計年鑒》的工業部分以及《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的基礎數據就來源于此數據庫。。本文采用的數據年份從2002 年到2008 年②雖然本文主要使用的是2002 年至2008 年的數據,但當考慮企業前一年生產經營狀況涉及到2001 年的數據時,我們也會使用2001 年該企業的數據,所以更確切地說,我們所使用的工業企業數據所跨年份為2001—2008 年。,工業企業樣本從2002 年超過18 萬到2008 年超過41萬,涵蓋了中國工業約40個兩分位行業,包括會計三大報表(即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上的財務指標、產品信息(生產的產品類別)等一百多個變量③由于數據中2008 年沒有工業中間投入值,我們參考韓國高等(2011)的方法,通過間接方法予以計算: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指標的解釋,工業增加值=工業總產值-工業中間投入+應交增值稅,從而推出,工業中間投入=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應交增值稅。在此我們假設2008 年工業增加值與工業總產值的比例與2007 年相同,則可以用每個企業2008 年工業總廠值與2007 年的工業增加值率計算出該企業2008 年的工業增加值,再結合本年應交增值稅額繼而可以計算出每個企業2008 年的工業中間投入。這種做法是為了更充分地利用2008 年的企業樣本,當然僅利用2001—2007 年數據進行估計,我們發現本文的結論并未發生顯著變化。。雖然該數據庫樣本量大、指標豐富,但由于部分企業會計報表不規范、上報登記錯誤等原因,數據存在一些異常值,需要在做分析之前對異常樣本進行剔除。本文先參考Feenstra 等(2014)的做法,將缺失主要財務指標(如資產總額、工業總產值和固定資產凈值)的樣本剔除,再將從業人員數少于8 人的樣本剔除,因為這些企業處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下(Brandt et al.,2012;Yu,2014);最后,按照一般公認的會計準則(GAAP)將存在以下情況的樣本剔除:(1)流動資產大于總資產,(2)總固定資產大于總資產,(3)固定資產凈額大于總資產,(4)企業的法人代碼缺失,(5)無效的成建立時間(如成立時間在1 月之前或12 月之后)。剔除掉無效數據后,在本文2002—2008 年的樣本中共有600,707 個企業,1,947,744 個觀測值。表1 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本文使用的第二個數據庫是來源于商務部提供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據,該數據包括所有在商務部登記注冊的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層面數據,變量包括母公司名稱、母公司所在省份、投資目的國、子公司名稱、核準日期④考慮到公司核準日期并不一定能十分精準的衡量子公司成立的年份,我們通過對每個公司的官網(如果有)進行檢索,使用母公司官網上的子公司成立年份來代替相應子公司的成立時間,最大限度地接近子公司真實的成立時間。、經營范圍等,涉及的樣本包括了從2002 年中國建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①2002 年,原外經貿部、國家統計局共同制定了中國第一份《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按統計制度的規定,年末境外直接投資企業個數是指境內投資主體在報告年度末直接擁有或控制10%或以上的投票權或其他等價利益的境外企業數目。以來所有中國大陸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公司,所以本文有利于從全國層面認識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公司的影響。

表1 描述性統計
本文使用的第三部分數據來源于地方政府的報告、商務部網站以及對外投資企業的官方網站,這部分數據主要用來構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模式,這部分數據的使用也是以前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文獻未曾涉及的。這部分數據的收集規則如下:首先,我們僅對能與工業企業數據庫匹配的子公司搜集其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信息;其次,信息搜集順序為,有公司(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網站的先在公司網站收集,若沒有公司網站就查找母公司當地商務部(廳、局)的官方報告,若仍然沒有,就會搜索相關新聞報道;最后,我們僅對確認性信息進行記錄,對可能、或許、傳言等非確認性信息不予記錄。如果信息中提及“成立”、“建立”、“創立”或“新建”子公司等相關字眼,則認為是“綠地投資”;如果信息中說的是“并購”、“兼并”或“收購”等字眼,則認為是“兼并收購”。如果沒有找到相關信息,則默認此指標缺失。
我們先將第一和第二部分數據進行合并。由于從第二部分數據并不知道進行對外投資的母公司是否屬于制造業,我們按照《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進行推算。在2008 年末時,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境內母公司中約有42.7%,來自于制造業,而2002—2008 年的境外企業為5820 家,故可推算其中大約有2485 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來自于制造業②此處我們假設按境外投資企業計數時,來自于制造業的比例也為42.7%,由于中國的跨國公司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在境外擁有超過2 家跨國公司的比例還非常低,故此假設在做粗略推算時問題不大。,合并后的數據有2033 家境外企業(共1516 家境內企業),故匹配率達到約81%,。基于匹配后的數據,我們對每家子公司的進入模式信息進行搜集,共找到1102 家子公司有進入模式信息,數據完整率約為54%,③由于子公司進入模式的信息缺失較多,我們將在分析進入模式時進行相應穩健性檢驗。。
三、實證策略與預先性分析
(一)企業生產率的度量
傳統的生產率的測度是通過企業實際產出與由OLS 計算所得的估計值之間的差額來實現的,這種方法簡單易操作,但由于受到聯立性偏誤和選擇性偏差的影響(Olley and Pakes,1996),簡單通過索洛殘差來估算企業生產率得到的結果是有偏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Olley 和Pakes(1996)(簡稱為OP 方法)假設企業投資額可以作為生產率的代理變量,并且考慮企業的生存概率以盡可能估計出無偏的企業生產率。
盡管傳統的OP 方法較為有效地解決了聯立性偏差和選擇性偏差問題,但是De Loecker(2011 & 2012)指出在估計生產函數時若不控制可能影響企業生產函數的因素,傳統的OP 方法所估計出的企業生產率仍然可能有偏。由于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可能會面臨不同的生產環境(De Loecker,2007;Yu,2014),故本文在估計生產函數時引入“是否有出口”這一虛擬變量以允許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擁有不同的生產函數。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會面臨不同的市場環境和資源配置過程(Markusen,2002),故在估計企業的生產函數時,需要將“是否有對外直接投資”的虛擬變量加入待估計生產函數,否則將出現未控制可能影響企業生產函數的因素而導致的生產率估計偏誤(De Loecker,2011、2012),而這一點也是以前研究對外投資與企業生產率的文獻所未考慮的。
(二)預先性分析
為了檢驗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是否有較高的生產率,本文設定了如下模型:
其中,ln T FPit、O F DIit分別表示企業i 在第t 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若當年存在對外直接投資OFDI 取1,否則取0);Xit包含一系列控制變量,如企業是否出口的虛擬變量、所有權類型、企業規模(用企業從業人數和企業資產總額來表示)等變量。為了控制出口企業的出口學習效應(Delgado et al.,2002;Lileeva and Trefler,2010 等)①出口學習效應最早可以追溯到Arrow(1962)提出的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效應,隨后許多學者將其運用到各個領域,這其中就包括國際貿易中的出口學習效應。,回歸中加入了企業是否存在出口的虛擬變量(在該年存在出口則為1,否則為0)。由于企業規模會影響到企業資源配置的能力,從而企業規模可能影響企業生產率(Leung et al.,2008;De Nagaraj,2014),故本文將其放入控制變量中,企業規模用企業從業人數來表示。αi和ηt分別表示企業和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
表2 給出了方程(1)的估計結果。


表2 對外投資企業和非對外投資企業生產率的差異
從表2 可知,在控制了企業所有者屬性、是否出口、從業人數和資產以后,對外投資企業較之于非對外投資企業有較高的生產率,但這只是一種偏相關關系;結合Helpman 等(2004)、田巍和余淼杰(2012)的研究可知,總體上來講企業對外投資存在著生產率的自選擇效應,所以如果不對這種自選擇效應進行控制,可能會高估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
(三)計量模型
為了控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自選擇效應的影響,我們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方法來估計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為了找出實驗組企業(有OFDI 的企業)生產率的反事實,我們采用最近鄰匹配的方法來構建對照組①匹配是分年、分行業按傾向得分向上、向下各找一個對照組。我們也嘗試了選取單個對照企業和更多的對照企業的匹配方式,但對本文結論沒有顯著影響。。我們采用Probit 模型對企業下一期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概率進行建模,參考以前文獻,解釋變量包括全要素生產率、企業所有權(由是否是國有企業、是否是外商投資企業來衡量)、企業規模(由從業人數和企業資產總額表示)、是否是出口企業,以及表示年份和行業的虛擬變量。
在得到了實驗組企業生產率的反事實以后,我們用下式(2)和式(3)來估算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用C 表示控制組,C (i )表示與實驗組企業i 匹配的企業集合,表示與企業i 匹配的企業的數量,各個與企業i 匹配的企業j 的權重為ω1、ωc分別表示實驗組和控制組的生產率,則對外直接投資在第s 期的生產率水平效應可表示為:


很明顯,式(3)估計的生產率效應實際上是實驗組企業在OFDI 后生產率變化情況和匹配后的對照組①本文中我們采用了從未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作為對照組。與此相對應的另一種做法是將當年未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作為對照組,顯然這種作法忽略了以前進行過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企業今后發展的影響,因此本文未將這些樣本作為對照組。企業在相同時期生產率變化的平均差異。
按照上述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表3 給出了成功匹配的比例。
表4 給出了匹配前后關鍵變量對比情況。從其中可以看出,在匹配前,與從未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相比,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會更大、生產率會更高,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確實存在自選擇效應;在匹配后,這種差異在統計上不在顯著,說明我們所找的對照企業能有效地控制對外投資的自選擇效應。

表3 新的對外投資企業數目與匹配比例

表4 匹配前后關鍵變量對比情況
四、估計結果
(一)工業企業整體層面
表5 給出了工業企業整體層面的估計結果。第(1)部分呈現的是對各期(s 期)生產率水平值的影響,第(2)部分呈現的是與對外直接投資前一期相比,各期生產率的增長效應。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公司企業生產率確實存在促進作用。從對外當直接投資當年開始①雖然生產率水平值的差異在對外直接投資當年并不顯著,但生產率的增長率在投資當年卻顯著為正,所以可以認為,總體上來說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公司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在對外投資第一年就開始顯現。,這些有對外投資的企業開始變得更加有生產力,到投資后第3 年(s=3),相比于其它企業,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率比其它企業平均高11.8%,。從第(2)部分可知,生產率的逐年增長效應并不是在每年都顯著,這意味著雖然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的生產率會變得比其它企業高,但并非每年生產率的增長率都會顯著高于其它企業②這個發現也和De Loecker(2007)關于出口的生產率效應的結論類似。。

表5 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工業企業整體層面③ 此表中,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樣本數少于合并后的企業樣本數,原因有三:一是匹配時需要用到企業前一年的生產經營情況,故前一年數據缺失的企業會被踢除;二是不滿足平衡條件,無法找到對照企業的樣本會被踢除;三是用OP 方法計算生產率時會用到中間投入的信息,此變量缺失的樣本也會被踢除。后文在估計時樣本情況與此類似。
(二)母公司特征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生產率效應的影響
1. 吸收能力與企業生產率
眾所周知,企業的吸收能力會影響企業對新的、外部有用信息的認知,從而可能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產生影響。參考以前的文獻(Cohen and Levinthal,1990;Griffith et al.,2004;Dai and Yu,2013),本文采用是否進行了研發來衡量企業的吸收能力。我們認為,在對外直接投資前進行了研發的企業,具有較高的吸收能力,能在對外投資后更好地利用外部信息,能更好地吸收已有知識、創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企業生產率。
為了證驗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是否會受到企業吸收能力的影響,本文按照是否有對外直接投資以及以前年份是否有研發將樣本分為四部分,然后將以前年份有研發的無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作為對照組,重新匹配后計算出有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的生產率效應,再將以前年份無研發的企業作為對照組,重新匹配后計算出無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的生產率效應。表6 給出了相應的估計結果。

表6 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分有無對外直接投資前研發① 有、無對外直接投資前研發兩個實驗組的樣本加總后小于表5 中的實驗組總樣本,這是因為根據以前年份有無研發將樣本細分以后,在某些年份、部分行業中由于樣本太少無法滿足平衡條件(balancing condition)從而不能給實驗組企業找到合適的對照組,故為了保持結果的準確性,在估計時將無法找到有效對照組的企業進行了剔除。各文分組匹配后出現的數量情況與些類似。從表6 可知,有對外直接投資前研發的企業所占比重接近50%,明顯高于不區分有無對外直接投資時有研發企業的比例,后者在2002—2008 年的比例約為12%。
由表6 可知:不論以前年份有無研發,對外直接投資都會促進母公司生產率的提高,但這種促進作用對于吸收能力不同的企業效果有顯著差異,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前研發的企業生產率提升作用更加明顯。從TFP 水平值來看,對于有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生產率的促進作用非常顯著:平均來說,投資當年其企業生產率會變得比無對外投資企業顯著高4%,,到對外投資后第3 年(s=3),其生產率已顯著高于無對外投資企業14.5%,。對于無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生產率獲益只在部分年份(對外投資后第1年和第2 年,即s=1和s=2時)顯著,并且生產率增長程度也低于有對外直接投資前研發的企業。
2. 企業所有權屬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比較
以往的研究表明,國有企業有更低的經濟績效,從而會有更低的生產率(Hsieh and Klenow,2009),為了檢驗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對于國有與非國有企業是否存在不同,我們按是否是國有企業、是否進行了對外直接投資將數據分成4 個部分。以未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作為對照組,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有企業的影響;以未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非國有企業作為對照組,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非國有企業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7。
從表7 可知,對外直接投資確實顯著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的獲益從對外投資當年的2.2%,提高到對外投資后第3 年的10.7%,。國有企業生產率的提升效應并不明顯,當然對待這個結論時要非常謹慎,因為數據中有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企業樣本非常有限①按《2008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截止2008 年末,國有企業占中國所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數量為16.1%,但這里面包括非金融類企業,考慮到有對外直接投資的金融類企業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故若將金融類企業剔除,國有企業所占比重還會下降,加之不滿足平衡條件的實驗組企業被剔除,以此導致數據中國有企業樣本數量有限。;從標準差來看,國有企業的標準差非常大,說明對外投資后,國企表現差異非常大,可能的原因是那些管理能力差、吸收能力不足的國企并沒有從對外投資中獲得技術、規模優勢,從而出現了“拖后腿”現象。

表7 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根據企業性質劃分② 事實上,雖然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非常大,但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公司數量并不多。
(三)子公司進入策略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生產率效應的影響
對于子公司進入策略,本文主要從投資區位(目的國)和子公司進入模式來研究。
1. 子公司投資區位與企業生產率
由于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生產技術,發達國家處于生產技術前沿,而發展中國家多處于世界科技和產業前沿以內(林毅夫,2012),故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給企業帶來的影響可能會有較大差異。為了檢驗這種差異是否真的存在,本文對只在OECD①由于OECD 國家絕大多數都是高收入的發達國家,故以此代表到發達國家的投資,本文的OECD 國家范圍為 2009 年以前加入 OECD 的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德國等在內的 30 個國家,詳見:http://www.oecd.org/about/membersandpartners/list-oecd-member-countries.htm。國家進行過投資和只在非OECD 國家進行過投資的企業分別進行檢驗②為了避免既在OECD 國家進行過投資,又在非OECD 國家進行過投資對估計結果所帶來的混淆效應,在進行估計時我們將對OECD 和非OECD 國家均進行了投資的樣本進行了剔除。,估計結果見表8。
從表8 可知,不論到OECD 國家進行投資還是到非OECD 國家進行投資,企業的生產率都會獲得顯著提升。考慮到非OECD 國家技術優勢相對不足,到非OECD 國家投資帶來的生產率獲益從側面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源分配效應和競爭效應。同時,表8 也反映了在多數年份,向OECD 國家進行投資能帶來更大的生產率提升效應,這也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公司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確實存在。

表8 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根據投資目的地劃分③ 此處向OECD 國家和非OECD 國家投資的樣本數之和小于工業企業整體層面的樣本之和還有一個原因,即此處將既有向OECD 國家進行了投資又有向非OECD 國家進行了投資的企業進行了剔除。
2. 子公司進入模式
總體來說進入國外投資的模式可以被分為兩類:綠地投資和兼并收購。這兩種投資模式下國外子公司可能會面臨不同的管理方式、企業文化以及技術獲益渠道,從而會影響國外子公司表現(Li,1995;Brouthers,2002;Kim and Gray,2008)。子公司的表現也會通過企業績效、技術外溢等渠道進一步影響國內母公司的表現。為了探討子公司進入模式對于母公司生產率有無影響,我們根據初次對外直接投資時企業的進入模式,分組探討了不同進入模式下對外直接投資生產率效應的差異,結果見表9。
從表9 可知,綠地投資和兼并收購均能夠促使母公司生產率的提高,但這種生產率的提升作用在到來時間上有所差異。綠地投資后第一年(s=1)就開始有明顯的生產率提升效應,且這種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強;而兼并收購在投資后兩年生產率雖有提高但統計上并不顯著,直到投資后第三年時生產率效應才開始顯著①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可能存在不能找到子公司進入模式信息的問題,但這種信息缺失一般都只存在綠地投資中(因為兼并收購國外公司一般都是有實力的大公司的行為,這些公司的信息公開情況更好,而且兼并收購國外公司一般會引起更大關注,這就導致這些信息的曝光率更高),為了檢驗文章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將進入模式缺失的子公司的進入模式替換為綠地投資,再按文中方法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本文有關子公司進入模式的分析仍然成立:綠地投資后第一年就開始有明顯的生產率提升效應,且這種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強。當然兼并收購的結論更不受影響,因為其樣本未發生變化。。這種現象的可能解釋是:相比于綠地投資,兼并收購給企業會帶來更多挑戰,例如企業文化融合、歷史包袱的處理等,能否有效整合被并購企業的資源將影響母公司生產率的表現。

表9 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根據進入模式劃分② 為了避免有綠地投資又有兼并收購進入模式帶來的混淆影響,我們將初次投資當年存在兩種進入模式的樣本予以剔除(初次投資當年同一公司可能有多次對外直接投資,從而可能存在不同的進入模式)。另外,部分不能確認進入模式的企業在此部分也被剔除。
五、穩健性檢驗與進一步分析
(一)生產率的度量
為了檢驗本文的估計結果對于不同的生產率估計方法是否穩健,參考Levinsohn和Petrin(2003)的做法(即LP 方法),分行業重新估計企業生產率。這種方法采用中間投入作為企業生產率的代理變量,用以控制企業生產投入決策和不可觀測的企業生產率的相關性,以此解決估計生產函數時的同時性偏誤問題。在估計出企業生產率后,我們按照第四部分的估計方法對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率效應進行了估計,結果顯示本文的主要結論并沒有因為生產率估計方法的改變而發生實質變化。限于篇幅,結果未在此報出。
(二)避稅天堂會有影響嗎?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相當大一部分投向了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美屬薩摩亞以及百慕大群島等避稅天堂①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可知,按投資目的地劃分,流向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經常位于前十位。。眾所周知,流向這些地方的對外投資很可能最終投資目的只是在此注冊以獲得稅收優惠。那么,這種投向香港和傳統避稅天堂的投資是否能促使母公司生產率提高呢?為了檢驗這個問題,本文將初次投資時只投向了避稅天堂和只投向了非避稅天堂的公司分開②基于對中國企業經常投資目的地的分析,我們使用的避稅天堂的名單為: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美屬薩摩亞、百慕大群島以及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考慮香港是因為香港經常被中國內地企業視為投資中轉地)。,分別按前文給出的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尋找對照組,然后再分別進行檢驗,估計結果見表10。
從表10 可知:向非避稅天堂進行的對外投資能顯著促進母公司生產率的進步,這種生產率效應從對外直接投資后第一年(s=1)的3.8%,,增長到第三年(s=3)的12.2%,;投向避稅天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帶來的生產率效應相對更小,但在投資后第二、三年這種生產率效應在統計上顯著。我們自然要問:為什么即使投向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其它避稅天堂的投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母公司生產率的發展呢?對此我們認為可能有以下幾種解釋:其一,雖然投向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其它避稅天堂的投資可能會以外資身份又回到內地,但相當一部分投資最終會流向其它國家和地區,這就會產生和其它直接投向非避稅天堂的投資類似的效果;其二,由于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良好的融資體系有助于解決國內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從而促進母公司的發展;其三,到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投資的企業,有許多是商務服務公司,能夠為母公司提供更準確及時的信息咨詢服務,促進母公司及時調整經營策略,同時促使母公司更好地融入到全球價值鏈中,增強母公司產品的進出口能力。

表10 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避稅天堂是否有影響?
(三)用一步系統矩估計方法估計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考慮到一步系統矩估計方法(One-step system-GMM)的靈活性,參考Yu(2014)等文章的做法,我們可以不用先估計企業生產率,而直接一步探究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企業生產率的作用①這種方法實際上是將對外直接投資看成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部分,顯示在相同的投入要素下對外直接投資是否能顯著提高企業產出。。也就是同時估計出生產函數的投入系數和對外直接投資系數,以作為額外的穩健性檢驗。其估計方程如下:

其中,Y、L、M 和K 分別表示產出、從業人數、中間投入和資本存量,ηt、θk和εikt分別表示時間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和擾動項,start 表示初次對外直接投資,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自選擇性,為了控制此內生性,我們采用滯后一期的對外投資變量,以估計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下一期企業產出的影響②對于存在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我們僅保留了初次對外投資當年(s=0)和投資后第二年(s=1)的數據。由于在估計方程中將start 變量取了滯后一期值,故實際上只估計了相對于未對外投資企業,初次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企業第二年績效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11。從表11 可知,總體來說對外直接投資確實會帶來顯著的生產率獲益;這種生產率又會受到企業吸收能力的影響,在有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生產率獲益更大,而對于無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這種生產率效應則更小(在此方法估計下也不顯著);此外投資目的地的差異也會影響對外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投向OECD 國家的投資更能促進母公司生產率的提高,而投向非OECD 國家的投資帶給母公司的生產率效應更低且顯著性也更低。

表11 包含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函數一步系統矩估計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盡管以前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比沒進行對外投資的企業有更高的生產率,但對于對外投資是否能提高母公司(母國)生產率這一問題沒有一致的答案。找到哪些因素影響企業對外投資的生產率效應將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之前的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從現實意義上來說,伴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膨脹,在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對企業對外投資成敗的質疑。本文從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入手,考察了不同母(子)公司的特征對于對外投資能否提高企業生產率的問題進行了實證檢驗,有助于大家加深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成效的理解。
本文通過利用2002 年到2008 年全國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調查數據、商務部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數據以及作者自己搜集的有關子公司進入模式的數據,實證檢驗了對外直接投資整體層面的生產率即期和長期效應,并考察了不同企業特征和東道國特征下,這種生產率效應的差異。我們使用擴展的Olley 和Pakes(1996)以及Levinsohn 和Petrin(2003)的方法估計了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并采用了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來控制生產率高的企業選擇對外投資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
研究結果表明:(A)整體而言,對外投資確實能夠促進母公司生產率的提高,根據TFP 估計方法的不同,這種提升效應在對外投資后第一年達4%,~7%,①前者是生產率采用OP 估計方法的結果,后者是生產率采用LP 估計方法的結果,下同。,到投資后第三年上升到12%,~18%,;但生產率的水平值的顯著提高并不意味著生產率的逐年增長率也會顯著高于無對外投資的企業。(B)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對于不同特征的母公司和子公司存在明顯的異質性:(1)對于有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這種生產率提升效應更加迅速且顯著,根據不同TFP 的估計方法,生產率的當年效應從4%,到6%,不等,投資后第三年的效應從15%,到31%,不等;而無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對外投資帶來的生產率提升作用要么不顯著,要么不持續且比有對外投資前研發的企業弱。(2)從本文的樣本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給國有企業帶來顯著的生產率提升。雖然估計出的對外投資的平均效應為正,但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對外投資后國有企業表現差異很大,存在部分企業“拖后腿”的現象。(3)投資目的國的特征也會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實證表明投向OECD 國家的企業生產率提高更多,且持續性顯著;而投向非OECD 國家的生產率效應更弱且并非持續性顯著。(4)區分子公司進入模式的估計結果表明,綠地投資給母公司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效應持續且統計上顯著;兼并收購會給母公司帶來更大挑戰,但對于能夠在較長期成功應對挑戰的母公司其生產率也會有顯著提升。此外我們對避稅天堂的考察表明,向非避稅天堂進行的投資從投資后第一年開始便能顯著提升母公司生產率;向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傳統避稅天堂進行的投資雖然生產率效應更弱,但在統計上也顯著。
本文的研究對于經濟理論也有相應貢獻。首先,我們驗證了吸收能力的作用(Cohen and Levinthal,1990;Griffith et al.,2004 等),從實證上證實了吸收能力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率效應具有調節作用,吸收能力強的企業,在對外投資后能更加有效地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從而有效提高企業生產率。其次,本文的結論支持了國有經濟低效的學說(Hsieh and Klenow,2009 等),國有企業由于受政府管制,其進行對外投資可能會更多地考慮政治因素,從而影響了其對外投資的效率。再次,我們在國家間發展差異的理論上,實證檢驗了這種差異如何影響對外投資的生產率效應。本文研究表明,東道國越發達,投向這些地區的投資對母公司的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就會越明顯,反之,投向欠發達地區進行的投資對母公司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可能就會越弱。最后,我們對跨國公司進入模式(Li,1995;Brouthers,2002 等)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了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對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的作用,這對于進一步了解展中國家對兩種跨國投資策略的選擇提供了經驗證據。
基于本文的研究,我們也能得出豐富的政策含義。其一,總體來說,我國應該堅持推進“走出去”戰略。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其它主要經濟體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的沖擊,歐洲陷入主權債務危機、日本經濟一直處于“失去”狀態,美國經濟也恢復緩慢,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減少以及人民幣升值的不斷推進,中國企業正面臨“走出去”的大好時機;本文的研究也表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后生產率還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這更從理論上表明,我們應該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其二,要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讓國有企業充分參與市場競爭。除了在關系國家安全的領域保持國有企業的相對優勢地位外,其它領域應該加大改革,降低行業進入門檻,為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創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應該進一步推進政企分離、特別是減少地方政府對地方國企經營決策的干預,讓國企回歸市場,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同時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造,或者允許更多的國有企業上市,讓其經營更加公開透明,接受民眾監督,以提高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其三,進入“十二五規劃”的后期,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逐漸加強,專利發明創新不斷增多,但相對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我國專業申請特別是實用價值高的發明專利的企業平均申請量還非常低。從本文研究可知,在企業“走出去”之前應該“修煉內功”,加大研發創新力度,要逐漸轉變過去單純的依靠模仿、仿造的發展思路,走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這樣才能在走出國門后擁有后續發展的強勁動力。其四,要創造企業家再學習的氛圍,鼓勵企業家學習海外投資(特別是兼并收購)方面的經驗。鼓勵培養有跨國背景的國際商務人才,特別要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懂得國際政治、國際法律的復合型經營管理人才。只有這樣,才能促使“走出去”戰略的益處得以更充分的實現。
當然由于樣本量的原因,我們無法對投資目的地和跨國投資進入模式的聯合效應進行更為細分的分析,但這個有意思的話題可以在將來進一步研究。
[1] 常玉春. 企業FDI 微觀績效的影響因素:一個文獻綜述[J]. 經濟評論,2010(4):154-160.
[2] 韓國高,高鐵梅,王立國,齊鷹飛,王曉姝. 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的測度、波動及成因研究[J]. 經濟研究,2011(12):18-31.
[3] 蔣冠宏,蔣殿春,蔣昕桐. 我國技術研發型外向FDI 的“生產率效應”——來自工業企業的證據[J]. 管理世界,2013(9):44-54.
[4] 林毅夫. 中國經濟專題[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第二版.
[5] 毛其淋,許家云.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否促進了企業創新[J]. 世界經濟,2014(8):98-125.
[6] 田 巍,余淼杰. 企業生產率和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基于企業層面數據的實證研究[J]. 經濟學(季刊),2012(2):383-408.
[7] 余淼杰. 加工貿易、企業生產率和關稅減免——來自中國產品面的證據[J]. 經濟學(季刊),2011(4):1251-1280.
[8] 趙 偉,古廣東,何元慶. 外向FDI 與中國技術進步:機理分析與嘗試性實證[J]. 管理世界,2006(7):53-60.
[9] Amiti,M. and Konings,J. Trade Liberalization,Intermediate Inputs,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5):1611-38.
[10] Arrow,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3):155-73.
[11] Becker,S. O. and Ichino,A.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s [J]. Stata Journal,2002,2(4):358-77.
[12] Bitzer,J. and Kerekes,M.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New Evidence [J]. Economics Letters,2008,100(3):355-58.
[13] Blomstr?m,M. et 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Home Country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7,107(445):1787-97.
[14] Braconier,H. et al. In Search of FDI-Transmitted R&D Spillovers:A Study Based on Swedish Data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2001,137(4):644-65.
[15] Brandt,L. et al.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97(2):339-51.
[16] Branstetter,L.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6,68(2):325-44.
[17] Brouthers,K. D. Institutional,Cultural and Transaction Cost Influences on Entry Mode Choice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2,33(2):203-21.
[18] Cai,H. and Liu,Q. Does Competition Encourage Unethical Behavior the Case of Corporate Profit Hiding in China [J]. Economic Journal,2009(119):764-95.
[19] Chen,K. and Yang,S. Impa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R&D Activity:Evidence from Taiwan'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Low-wage Countries [J]. Asian Economic Journal,2013,27(1):17-38.
[20] Cohen,W. M. and Levinthal,D. A. 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128-52.
[21] Dai,M. and Yu,M. Firm R&D,Absorptive Capacity and Learning by Exporting: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J]. The World Economy,2013,36(9):1131-45.
[22] Danny Leung,C. M. A. Y. Firm Size and Productivity[R]. Bank of Canada Working Paper,2008,No. 45.
[23] De Loecker,J. Do Exports Generate High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Sloveni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3(1):69-98.
[24] De Loecker,J. Product Differentiation,Multiproduct Firms,and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2011,79(5):1407-51.
[25] De Loecker,J. et al. Prices,Markups and Trade Refor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R]. Working Paper,No. 17925,2012.
[26] De,P. K. and Nagaraj,P. Productivity and Firm Size in India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4,42(4):891-907.
[27] Delgado,M. A. et al. Firm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Markets: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7(2):397-422.
[28] Feenstra,R. C. et al. 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4,96(4):729-44.
[29] Giorgio Barba Navaretti,D. C. A. A. How Does Investing in Cheap Labour Countries Affect Performance at Home?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Italy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2010,62(2):234-60.
[30] Griffith,R. et al. Mapping the Two Faces of R&D:Productivity Growth in a Panel of OECD Industri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4,86(4):883-95.
[31] Helpman,E. et al.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1):300-16.
[32] Holz,C. A. China's Statistical System in Transition:Challenges,Data Problems,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J].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4,3(50):381-409.
[33] Hsieh,C. and Klenow,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124(4):1403-48.
[34] Kim,Y. and Gray,S. J. The Impact of Entry Mode Choice on Foreign Affiliate Performance:The Case of Foreign MNEs in South Korea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48(2):165-88.
[35] Levinsohn,J. and Petrin,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70(2):317-41.
[36] Li,J. Foreign Entry and Survival:Effects of Strategic Choices on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5,16(5):333-51.
[37] Lileeva,A. and Trefler,D. 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Raises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for Some Plant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125(3):1051-99.
[38] Lipsey,R. 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U. S. Economy[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 1995.
[39] Loecker,J. 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Multiproduct Firms,and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2011,79(5):1407-51.
[40] Markusen,J. R.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 MIT Press,2002.
[41] Olley,G. S. and Pakes,A.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J]. Econometrica,1996,64(6):1263-97.
[42] Van Pottelsberghe,B. and Lichtenberg,F.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83(3):490-97.
[43] Pradhan,J. P. and Singh,N. Outward FDI and Knowledge Flows:A Study of the Indian Automotive Secto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es,2009,1(1):156-87.
[44] Yu,M. Processing Trade,Tariff Reductions,and Firm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14:Forth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