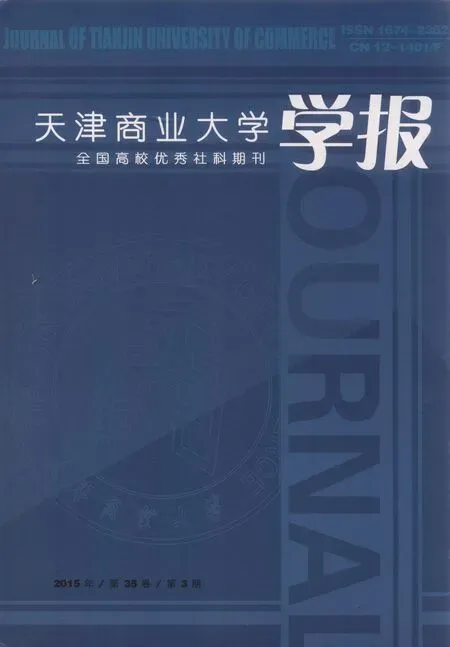對“居民遷出”式遺產保護路徑的效果評價和反思——以中山市翠亨村為例
謝春紅 ,于 玉 ,徐 虹,黃梓瑩
(1.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天津300071;2.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廣州510275)
長期以來,對于古村落的保護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古村落的古建筑上,而對古村落的村民、活態文化、社區發展等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古村落保護及其研究應該也必須注意它作為村落社區的一面。[1]早期的古村落、古建筑的保護通常是由文物局出錢買斷該地的產權,產權劃為國有,社區居民在與國家進行了產權交易后就遷出村落。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護了古村落完整的物質形態。但是,古村落作為傳統民俗文化和物質遺存的綜合體,居民遷出后失去了活力,成為空殼式的文物。在市場化背景下,社區居民也開始意識到了古村落的旅游價值,渴望參與到旅游經營中,居民的多元化利益訴求使得早期的“居民遷出”遺產保護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試圖回答:政府單一主導的“居民遷出”文化遺產保護模式的效果如何?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是什么?在旅游發展的背景下,社區參與的“集體缺位”對于旅游地的發展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本研究以文化人類學視角,從社區參與傳統文化保護、文化傳承來分析“居民遷出”對文化遺產帶來的影響,指出“居民遷出”文化遺產保護模式的局限和困境,對“居民遷出”式保護模式的效果進行評價和反思。
1 遺產保護、文化傳承與社區參與
1.1 遺產保護模式及問題
我國古村落與民居的旅游開發存在多種模式。從遺存形態來看,物質遺存的保護與開發模式有博物館式、大遺址式、文化遺產旅游開發式、城市歷史街區開發式和村落開發式五種基本類型;非物質遺存的保護與開發模式則有民俗博物館式、文化節慶保護與開發式、特色餐飲開發式、演藝開發式、主題公園開發式、物化產品開發式和影視開發式七種基本類型。從投資主體看,目前所采用的模式大致可以歸為兩種類型——外部介入性開發模式和內生性開發模式。[3]外部介入性開發是指以地方政府或企業從外部剛性介入的模式。這種開發模式忽視了作為村落主體的社區居民的利益,導致開發成本高及各利益主體間的矛盾沖突,旅游開發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內生性開發就是指古村落或傳統民居居民及其基層組織作為直接利益主體,對村落進行自我保護和開發的模式。
在對國內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實踐進行審視的基礎上,有學者總結了較為成功的文化遺產保護方式。“新天地”模式是對傳統保護區域進行改造,“整舊如舊”,將傳統舊區的空間形態進行合理重組和改造,傳統建筑融入新的都市風格,這種模式的特點是高投入、高回報、資金運轉周期長,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才能成功。麗江模式則是對傳統民居進行高原真性的修復,對遺產地居民進行教育和培訓,以旅游業的發展反哺遺產保護。麗江模式在某種程度上較好地保護了古城,但是旅游的過度開發導致商業化嚴重,文化的原真性受到威脅。平遙模式是在麗江模式的基礎上,對遺產進行旅游基礎設施投資,對居民進行教育和技能培訓,古城保護與新城建設相結合,解決社區居民生產生活、旅游開發和古城保護三者之間的矛盾。[4]在后兩種較為成功的模式中,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之間矛盾的協調解決離不開對居民利益的合理分配。
傳統村落兼有著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在村落里這兩類遺產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屬一個文化與審美的基因,是一個獨特的整體。[5]除此之外,古村落的整體性特征還表現于村民與村落的共生。[6]因此傳統村落的遺產保護必須是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和社區居民的整體保護。將居民遷出由文物保護單位進行博物館式的保護是遺產保護的一種慣用方式,這種保護方式對于單個的、小體量的文化遺產無疑是有效的,但對于那些體量大的、成規模的、無法移動的文化遺產卻無能為力;[7]其次,博物館式保護多依靠外部力量,缺乏有效的社區參與,一旦外部力量的援助退出,遺產的命運岌岌可危。古村落保護采取哪種模式要根據保護對象和社區生活的具體情況,但目前我國古村落保護多數的情況是“比較注重外觀、景點、路線,比較偏重于物質遺產”。目前對現有的文物保護和管理效果評價的實證研究不足,也缺乏以社區、居民、游客、管理方四維度系統分析的視角。
1.2 社區參與旅游與文化傳承
根據利益主體理論,社區是村落旅游開發的重要主體。與發達國家相比,國內的旅游社區參與仍處于注重單純的經濟利益訴求、被動參與地方旅游發展的初級階段。[8]如今的村落景觀保護是以學者、社會精英、政府為主開展的,當地社區仍處于缺位的狀態。[9]部分社區多數是少數民族型或村寨型社區,其居民大多遵循政府旅游規劃下的獎勵制度而對建筑方式予以保留以獲得獎金補貼。[10]社區參與是指社區居民自覺自愿參加社區各種活動或事務的行動。[11]除了使居民獲得經濟效益外,其積極作用還表現在居民自我文化認同、文化生存空間培育與拓展及精神內涵的展示等層面。社區居民始終是當地文化資源的親歷者、塑造者和所有者。[12]社區參與賦予社區居民接觸“他者”的機會,激發其自我文化價值認知,使其產生民族文化認同感,增加了相互間的親和力和凝聚力。[13-14]唯有社區居民參與,才能把與人不可分離的民俗風情轉化為旅游產品,才能讓游客在社區居民對民風民俗活動背后的民族觀念、思維模式、民族性格、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的詮釋、解讀中體味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內蘊。[13]
社區本應該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居民是村落遺存的創造者和延續者。[15]有學者[16]認為將歷史街區的原居民全部遷出、把民居全部改為旅游和文娛等設施會使街區失去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習俗,也就失去了“生活真實性”。社區參與旅游,既有利于突出地緣文化,讓游客體驗感知不同文化,也有利于保護和培育文化生存空間、保障其健康發展。[13]社區的參與有助于文化遺產地保持自身特性、維持“真實性”,增加自身魅力,社區居民是文化遺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良好的社區參與,不僅使居民受益,也會增加居民對遺產地日常經營管理的理解與配合,有助于提高遺產旅游地的經營管理效率。反之,處于弱勢地位社區如果無法從遺產中獲益,則不會主動對遺產進行保護,被動參與會引起社區居民的抵制情緒甚至是惡意破壞,如開山采石、破壞生態植被、砍伐樹木等。[18]
2 研究方法與案例說明
2.1 研究方法
對“居民遷出”式遺產保護路徑的效果評價,涉及村落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現狀與困境、社區文化變遷、游客感知等內容,較為全面與系統,需綜合社區、居民、游客、管理方多元視角收集資料,因此采用了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方法,具體如下:
(1)觀察法:通過對旅游目的地的深入觀察,詳細描繪目的地的保護和發展現狀,包括古村落建筑及周邊物質景觀的現狀、游客在目的地內的行為特點、社區居民與游客的互動情況等。(2)訪談法:訪談對象主要是當地社區居民和故居管委會人員。針對居民方面,主要關注翠亨村的居民遷出過程、社區記憶和遷出后的社會交往、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的變化。針對故居管委會,則主要了解翠亨村的遺產保護和村落管理的原則、方向與措施,發現遺產保護和管理自身的困境以及旅游發展帶來的問題。(3)問卷調查:以利克特量表形式,針對進入目的地的游客,了解游客的旅游體驗、主客交流程度、遺產保護感知、社區文化與孫中山精神感知等信息。(4)二手資料收集:主要獲取故居管委會歷年來對目的地社區的規劃和保護方案,用以補充對管理人員的訪談內容。
2.2 案例說明
位于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的翠亨村,是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的故鄉。1986年10月孫中山故居被國務院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6月翠亨村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孫中山故居、古村落民居等物質遺產保護、孫中山精神宣傳一直是景區管委會的核心工作,并取得很好的成效,目前孫中山紀念館是AAAA級景區和國家首批一級博物館。翠亨村的社區文化傳承、非物質遺產保護效果未得到政府部門與景區管委會重視與有效評估。
自20世紀80年代孫中山故居管理處陸續對核心保護區內的民居產權進行收購,翠亨村原住居民持續10年歷經3批次不斷遷出至新居,至今只有5戶左右居民住在原址。“遺產保護”、“旅游發展”、“孫中山”等詞打破了一個農業村的平靜,翠亨村在空間結構、社區居民構成、社區文化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見圖1)。

圖1 遷出后翠亨村的分區及雜居分布特征平面圖
翠亨村歷史文化名村由居民住宅區、孫中山故居保護區構成,是社區與景區相鄰而又截然分離。翠亨村產權收購后,居民從保護區內的翠亨村舊址遷入現在的居民住宅區。目前,古民居被收購或長期租賃,僅有幾處民居處于產權談判狀態,古村落的維護和管理也基本由故居管理處負責。對于居民來說,他們并無搬遷,只是遷入集體新房而已。居民住宅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翠亨新址,是居民“遷入區”。另一部分為翠亨新村,對外已正名。這部分土地是當年“遷入區”的多余土地,用于建設商品房屋和員工宿舍,因此居民并非本村居民,也不再由原村委會管轄。在本土居民概念中,翠亨新址才是翠亨新村。
3 “居民遷出”式遺產保護路徑的效果評價
3.1 社區:社區文化發生變遷
(1)居民更替呈雜居分布
20世紀80年代翠亨村總人口為80多戶人家,目前發展到100多戶。翠亨村舊址還剩5戶左右原居民,并以老人留守為主,其余居民當年遷出后基本在新址上建宅。隨著居民外出務工、出國等流動,翠亨村新址出現普遍的房屋空置和租賃現象。翠亨村新址附近建有小型工廠、靠近中山紀念中學和翠亨學校、故居旅游等因素引致許多外來非正規就業者、學生、家長等群體流入。翠亨新村住戶主要為水電廠和景區等單位員工。由于人杰地靈,名義翠亨新村有別墅、商品房等旅游地產,其戶主多為華僑和珠海、中山、澳門等第二居所購房者(見圖 1)。
本土村落居民流出,許多旅游勞工、學生、家長和第二居所購房者流入使得翠亨村的居民不斷更替,雜居分布特性明顯,社區人口構成復雜化,并重塑著社區文化與風氣。居民更替置換對社區文化的傳承、孫中山情感的維系都有著影響。
(2)居民生計模式改變
20世紀80年代前,村民主要以務農為生,后由于國家土地政策、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村落土地逐漸開始流轉,部分農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目前村落剩余農田約50畝,主要分布在景區的農業展示區及周邊,長期用于租賃。本村居民不再以務農為生,多外出打工,“以前人們有田種的時候就耕地,現在田地賣光了,就到工廠里面打工……剩下的田地也不夠給那么多居民分啦,已經出租了……大概是100元每平方米吧。”
極少數靠近景區的居民將房屋改造為商鋪做些小生意,“餐廳基本上都是外來人在經營,只有紀中旁邊有兩家檔口是我們村的人經營的,上層給自己住,下層賣冷飲、豬腸粉之類的。”景區管委會對翠亨舊村以及紀念館范圍內的經營活動管理更為嚴格,居民“有講過(到舊村開展經營活動),但是他(管委會)不給……說不讓那么多人進去里面經營。”實際只有少部分居民(一般為村委親屬)可獲得景區的管理、經營、后勤的工作。可見,文物保護單位開放給本村居民創造的就業機會和經濟盈利點相對較少,居民的社區旅游參與度極低,但遺產旅游的發展已經使得村落的生計模式發生改變。
(3)文化空間驟減,親緣關系松散化
“遷出”模式使居民交往空間得以重塑,公共游憩空間轉移,精神空間功能弱化。親友間交往頻率降低,組織松散,族人與鄰里間的情感維系淡化。目前,原居民的公共游憩空間轉移為翠亨大道邊上的本土居民經營的餐飲店與商鋪,基本不去景區游玩。
遷出前,居民多圍繞宗族祠堂而聚居,親緣關系的住戶比鄰相依,房屋布局緊湊相連,間距小且巷道窄。遷出后,居民通過抽簽獲地建房,在新的空間生產生活,居住格局打破,長期建立的鄰里關系被重組,舊村原有的公共空間也基本不被沿用。遷出前村落精神空間節點較多,有大小宗祠、北極殿、村口的大型土地神,幾乎每戶都有小型土地神。新村落的公共游憩空間減少,新建的籃球場、老年人活動中心利用率又很低,取代的是圍合的私家小院,同時居民新宅很少再建小型土地神,許多宗祠在文革期間已被破壞拆除,“現在是分開祭祖的,每一家自己都有活動。”“(以前)過節會聚在一起祭祖。但現在祠堂也拆了,沒有祠堂啦,還有個北帝廟遺址。”遷出后只有少部分居民會回到舊村,“(舊村入口土地神、北極殿)初一十五的時候,還會有人去拜的。”大部分居民仍保留神學信仰和拜祭習慣,社區文化空間的功能已越來越弱化。
3.2 居民:社區記憶模糊和情感淡漠
(1)居民旅游開發的參與度低
居民與故居景區缺乏互動,聯系薄弱,經濟與情感關聯都很弱。村落旅游引致效應不大,提供居民的間接就業機會不多,直接就業崗位有限,經濟聯系也多為一次性買賣關系。居民與景區雙方的互動極少,居民在遺產保護、旅游發展方面沒有話語權。居民如同是遺產保護之外的,處于邊緣化狀態。
大部分古民居已被景區一次性收購,少數民居與農業展示區的部分農田則處于長期租賃給景區的狀態。據翠亨居民回憶,當時集體性遷出進展順利,居民對遺產旅游的經濟價值認知也不高,所獲得的一次性經濟賠償、固定租金并不高,只有少數留守居民日后以市價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雖然“在評一級館的時候,是有具體雇傭多少當地人指標的”,但集中在景區的一線運營部門(包括環衛、閘口、維修、農業區等部門),這些少量的直接就業機會也多為村長及其親戚獲得。“非遺展示區打掃衛生的人就是本地人,老村長的兒子也是在維修組工作。新村長的媳婦也在這里工作,大概五六個人。”翠亨村的旅游發展所引致的餐飲、住宿、商鋪的發展很弱,集中在中山紀念中學附近的翠亨大道,只有少數居民有機會參與經營活動。
(2)居民的孫中山情懷不濃郁
孫中山精神與相關歷史本是翠亨歷史文化名村的核心遺產,但在本土居民看來,這些與翠亨村和自身關聯很弱,只是多了一個可接待親友的景區。居民長期的邊緣化且與景區互動匱乏,導致本土居民的孫中山情懷普遍較弱;故居景區與居民長期處于分離狀態,沒有形成翠亨社區的文化自覺。
景區管委會每年組織孫中山誕辰慶典等一系列節慶,“……很少(和村委會合作),節慶時他們(居民)會派代表過來”,但居民參與度極低。大部分居民對孫中山精神了解不深,“我們都不認識孫中山的。只是以前聽人講過,小日本打中國時不打翠亨村,他們會打隔壁村。因為他們敬仰孫中山,都不會打翠亨村的。”中年居民“很少(以孫中山為榜樣教育小孩),因為過了很久了,隔了好幾代了”。而年輕居民多數“不會(因為家鄉有孫中山這一偉人而自豪)”。可見孫中山及其事跡在代際間的傳遞頻率減弱,社區的孫中山情懷培育效果不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故居景區的旅游符號被翠亨居民高度認同,年長及年輕的居民都“會(帶到訪親友參觀孫中山故居),“以前有門票都會帶親戚進去孫中山故居(目前故居免費)”。
3.3 游客:空殼式的文化遺產感知
故居管委會介入較早,采用的是傳統的社區與景區分離式旅游發展模式。從游客旅游感知看,游客認為景區古村落的整體風貌保存完好;在孫中山精神、生平事跡等歷史的展示與宣傳效果佳。這不意味著游客有著非常好的文化遺產感知,靜態的物質遺產保護方式讓游客形成的是空殼式的文化遺產感知。
在實地調研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游客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逗留時間相對較長,逗留其他古民居的時間非常短。有些游客甚至抱怨:“這有什么好看的,和我們老家沒有人住的老房子差不多”;還有游客驚訝道:“還有個翠亨村?我只知道有孫中山故居,還以為就只是這個圍起來的小公園而已,翠亨村離這遠不遠,怎么走?”還有部分游客繞過景區想進入翠亨古村落進行深度體驗,頻頻被景區設置的自動閉合鐵門攔截。這些情境足以說明完好民國風貌的民居建筑并不足以讓游客有著完整的遺產體驗,活態的社區、社區文化在游客體驗中是缺失的。
在旅游體驗方面,游客普遍認為古村落的“古”風貌是吸引自己前來的重要因素,“走進故居的村落社區,了解村落風貌”、“與故居居民交流,了解當地文化及其對孫中山的情感”的意愿強烈。實際體驗是游客認為“在景區內,幾乎不能從當地人口中聽到孫中山家族相關故事,根本無法與當地居民交流”。“居民遷出”式模式使得主客交往機會匱乏,這對于文化旅游地,不利于體驗時代背景,不利于提高游客滿意度。
在旅游發展方面,游客十分期待與社區居民交往的機會,并支持開放更大的民居展示區。但基于旅游商業化的顧慮,游客在“讓本地居民回遷原村適當開展旅游商業活動(如旅游紀念品、餐飲、住宿等)”這個問題上總體支持居民回遷但又十分謹慎。但對于“雇傭更多的當地村民,增強居民與游客的交往”則持贊同態度,在“對游客開放更大的民居展示區域”則表現出十分贊同的態度。
3.4 管理方:社區缺位導致景區管理困境
因資金、人力受限和社區的集體缺位,遺產保護力度不足,旅游發展動力缺乏直接導致了翠亨村旅游發展滯后,推進受阻。居民淡出遺產保護視野,社區缺位,對于文化遺產地而言是缺失了文化傳承載體,這對物質遺產要素的保護、社區旅游的推動有著負面影響,使得景區陷入管理困境。
(1)古民居空置,保護有限
面向游客展示的故居每天都有專人負責環境維護和檢查,保護較為妥當,但未向游客開放的民居保護區內的房屋現狀不容樂觀。“現在有人住,但是不多,不到五戶人家”,盡管管理方“盡量安排員工到里面去住”,但多數房屋都是空置狀態。這些既不對外開放又無人居住的房屋沒有承擔任何實用功能,長期空置更加速房屋的破損。其次雖然民居幾乎被統一管理,但也只是選擇性優先保護。“因為現在人力和財力也不夠,所以不可能將所有的古民居都保護成像標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房屋那樣,只能對一些重點的建筑進行保護,以后旅游開發當然這些也會是重點。”
(2)社區旅游薄弱,就業供給有限
面對膨脹的大眾旅游需求,管理方也曾想開放更大的民居展示區和農業展示區以提高旅游體驗,但因維護資金不足、工資低難以招到員工而無法落實。民居展示區與農業展示區本是原居民的生活區,原居民無疑是最合適的管理主體或雇傭勞工。遷出后社區與景區分離,社區參與度極低,提供居民的就業機會很有限。景區內商業設施除了官方紀念店,僅存在三家居民經營的小店并且商品同質化嚴重。“這些商鋪在90年代就有了,一年年地簽合同”,至今景區內旅游商業未有所增加。民居展示區內有保存下來的商鋪建筑,管理方希望有商家能夠租賃開展相關商業活動還原真實生活場景,但商家“覺得賺不到錢,位置太偏,游客不會到那里去”,管理方在培育居民就業機會方面重視不夠。
(3)博物館型景區,旅游發展滯后
孫中山故居景區是博物館屬性,實行免票制度,沒有收入來源,一切資金全部靠上級撥款補貼,這不同于自負盈虧的景區,這一方面削弱了管理方推進旅游的動力,另一方面,博物館的非營利屬性使得故居即使作為4A級景區,在旅游商業方面(旅游活動、商品類型、商鋪位置)也有頗多限制,無法給予旅游經營者足夠的信心與盈利空間。翠亨遺產保護中忽略了居民這一重要的保護主體和文化載體,社區文化傳承效果不佳,社區旅游沒有被激活,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的能動性沒被激發,翠亨村的旅游發展滯后,推進效果并不顯著。
4 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居民遷出”式遺產保護路徑不利于社區文化傳承
本文以中山市孫中山故居所在地翠亨村為例,還原翠亨村的遷出過程,深入分析遷出模式的影響,從社區、居民、游客、管理方四個維度系統地對我國早期“居民遷出”式的文化遺產地保護路徑的效果進行評價與反思,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物質遺產保存完好。由于在“居民遷出”式保護方式之下,遺產要素的控制權和管理權被集中于管理方手中,古建筑和民居的改造和開發被嚴格控制。在該層意義上,“居民遷出”的保護措施具有一定合理性與有效性。(2)居民遷出后,原有的居住格局被打破,由于新居住區的公共空間和精神空間功能相對原有空間較弱,導致居民間親緣關系被稀釋減弱。原有的社區文化環境因缺乏社區居民的參與而空殼化,社區居民因缺乏原有的文化環境而出現文化缺位的現象,造成對孫中山精神的淡漠和村落文化認同的弱化。因此,“居民遷出”式保護路徑未能完好保存蘊含在孫中山故居內的精神文化遺產。
4.2 反思:文化傳承才是遺產保護的核心
“居民遷出”式這一遺產保護路徑使得翠亨村的物質要素得以很好的保護,但是對保護村落的文化、增強居民對孫中山的情感維系、活用物質遺產、增強社區參與方面的積極作用不明顯,甚至有負面影響。可以想象,當游客來到孫中山故居參觀,只是一種旅游形式,不再關注中山精神,不再關注古村文化;而居民與遺產旅游地脫節,沒有文化的認同感,對孫中山的情感不再重要時,這個古村落也在喪失其魅力。
本研究認為,對遺產地而言“居民遷出”式保護路徑應持慎用態度。“居民遷出”式是一種保“居”不保“民”的模式,游客的旅游體驗則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缺乏深度的觀光感知。“居民遷出”式保護路徑僅保護了遺產的物質形態,而忽視了其精神內核。尤其國內后期其他遺產案例地的開發過程日益凸顯的沖突問題更是強化了社區參與的重要性和“居民遷出”式的不適用性。對文化的保護才是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居民是文化傳承、社區凝聚的真正載體。
4.3 討論:社區參與旅游視角下遺產保護模式
從目的地的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角度看,遺產保護路徑還需結合實際進一步研究。而對于早期采用“居民遷出”式的遺產地而言,后續的旅游開發該如何轉型,社區如何參與旅游也需進一步探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為遺產保護、文化傳承和旅游發展提供了中間道路。國內眾多案例研究證實,適度的可持續的社區參與旅游對于促進社區居民認識自身的文化、增強文化認同感和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14]游客對于目的地原真性的追求使得居民將社區的傳統文化找回來,社區居民認識到了文化和資源的價值與重要性,保護意識也逐漸萌生,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復歸和保持。
遺產保護路徑的尋找將永無止境,旅游并非遺產保護的最佳選擇,但為適度化的選擇。文化遺產的保護活動因為有政府部門的大力倡導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實際運作中往往停留在專家學者以及政府的倡導層面,當地成員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極為有限,因而也在走向博物館化。[19]文化是活的生命存在,具有變動性和開放性,把文化當作固化的“遺產”來保護的強特性途徑難以實現。缺乏文化遺產保護的內生力量,這種外部力量的扶持所帶來的遺產保護效果時常是階段性的。一旦外部力量退出,文化遺產的保護便陷入困境。20世紀末我國在貴州、云南、廣西的少數民族社區建立了一批民族生態博物館的命運就是例證。整體看來,旅游的適度開發和有效控制,將有利于傳統文化的保護。[19]旅游可以作為遺產保護的一種選擇,在遺產保護和旅游開發中,為社區居民預留足夠的發展空間和選擇空間,他們才是真正的主體,外來者在任何時候都只是遺產保護的輔助力量。
致 謝:感謝劉岳林、譚靖敏、馮銳昌、李乾畢同學參與本文實地調研,感謝所有受訪者對本研究的信任和提供的寶貴信息。
[1]黃濤.古村落的文化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以浙江省楠溪江流域蒼坡古村為個案[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131-134.
[2] 傅才武,陳庚.當代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模式[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93-98.
[3] 齊學棟.古村落與傳統民居旅游開發模式芻議 [J].學術交流,2006(10):131-134.
[4] 康健.古村落保護與發展模式研究[D].太原:太原理工大學,2008.
[5]馮驥才.傳統村落的困境與出路——兼談傳統村落是另一類文化遺產[J].民間文化論壇,2013(1):7-12.
[6]魏成.路在何方——“空巢”古村落保護的困境與策略性方向[J].南方建筑,2009(4):21-24.
[7] 孫九霞.旅游作為文化遺產保護的一種選擇[J].旅游學刊,2010(5):10-11.
[8] 保繼剛,孫九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中西差異[J].地理學報,2006(4):401-413.
[9]劉夏蓓.傳統社會結構與文化景觀保護——三十年來我國古村落保護反思[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118-122.
[10]艾菊紅.文化生態旅游的社區參與和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云南三個傣族文化生態旅游村的比較研究[J].民族研究,2007(4):49-58.
[11]彭思濤,但文紅.基于社區參與的村落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模式研究——以貴州省雷山縣控拜社區為例[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09(2):94-98.
[12]曹興平.文化繪圖:文化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及實踐的新途徑[J].旅游學刊,2012(12):67-73.
[13]鄧小艷.文化傳承視野下社區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開發的思路探討[J].廣西民族研究,2012(1):180-84.
[14]孫九霞.社區參與旅游對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正效應[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35-49.
[15]陳庚.以居民為核心主體的古村落保護與開發——基于婺源李坑村的實證調查分析[J].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5):49-58.
[16]阮儀三,孫萌.我國歷史街區保護與規劃的若干問題研究[J].城市規劃,2001(10):2-9.
[17]AWORTH G J,TURNBRIDGE J E.The Tourist Historic City[M].London:Belhaven Press,1990.
[18]王濤,張立明,任亮平.基于社區參與的世界遺產地旅游開發與保護研究[J].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08(5):114-116.
[19]孫九霞.旅游拯救民族與文化?[N].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