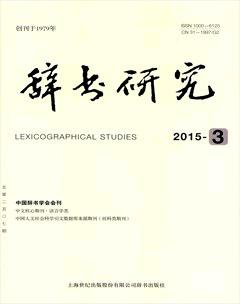揚雄《方言》的編纂宗旨與編纂方法論
錢榮貴
摘要 編纂思想是編纂活動的靈魂,研究編纂思想可以揭示典籍的生成機制和文化動因。作為我國第一部方言詞匯集,揚雄《方言》所蘊藏的編纂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的編纂宗旨,二是“即異求同,同中辨異”的編纂方法論。前者是揚雄繼承舊有的采風習俗而確立的,這一思想使其將“先代絕語”和“異國方言”同時納入《方言》采集和訓釋范圍。后者則是揚雄對《爾雅》“以義類聚”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方言》不僅以通語來訓釋被訓釋詞,還盡可能地揭示出被訓釋的一組詞之間的地域差異、時間差異和語轉差異。揚雄《方言》在方言研究史、方言辭書編纂史上是不朽的。
關鍵詞 揚雄 《方言》 編纂思想 編纂方法論
《方言》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方言詞匯集,成于西漢末年,凡十五卷,九千余字。后世傳本全稱《蝤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一萬一千余字,收詞1284個,詞條675個。《方言》分卷體例與《爾雅》相仿,但卷內條目不及《爾雅》有序。大體看來,《方言》卷一、卷二、卷三、卷六、卷七、卷十釋語詞,卷四釋衣服,卷五釋器物等,卷八釋動物,卷九釋兵器,卷十一釋昆蟲;卷十二、卷十三與《爾雅》“釋言”相似,但體例與其他各卷不同,只有“雅詁”沒有“羅話”,可見其為未竟之書。《方言》的編纂者為西漢揚雄。
揚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人,西漢著名天文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語言學家。訥于言辭,以文名世。40余歲,始游京師,任為郎官,給事黃門,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時,揚雄校書天祿閣,受劉棻獻瑞一事牽連,恐不自免,墜閣自殺。所幸未死,因年老久居一職,轉為大夫。揚雄一生“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仕途可謂平平,但其好古樂道,著述精豐,足可卓立千古。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云:“(揚雄)以經莫大于《易》,故則而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蒼頡》,故作《訓纂》;箴諫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賦莫弘于《離騷》,故反屈原而廣之;典莫正于《爾雅》,故作《方言》。”這些都說明,揚雄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皆能以歷代經典為坐標,其雄視古今的文化品格和學術精神實屬難得。
編纂思想是編纂活動的靈魂,典籍是“物化”了的編纂思想。研究編纂思想可以揭示典籍的生成機制和文化動因。作為我國第一部方言詞匯集,《方言》所蘊藏的編纂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的編纂宗旨,二是“即異求同,同中辨異”的編纂方法論。
一、編纂宗旨:“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故我國周秦時期即有農閑時節遣使采風之俗。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載,“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蝤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蝤軒”是一種輕便的車子,“輶軒之使”就是坐著“蝤軒”到各地采風的使者。蝤軒使者歸來后,便將采集的方言藏于秘室之中,天子憑借這些“奏籍”可以“不出戶牖,盡知天下”。贏亡以后,遣使采風之俗不復存在,藏于秘室的“奏籍”也已“遺脫漏棄”,幾不可見。至揚雄時代,能知此種風俗者,只有蜀郡的嚴君平、臨邛的林間翁孺二人。揚雄《與劉歆書》云:“獨蜀人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蝤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揚雄深受嚴君平、林間翁孺的影響,想在嚴君平“千言耳”、林閭翁孺“梗概之法”的基礎上編纂一部《方言》。為此,揚雄向成帝提出“愿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的請求。漢成帝深為感動,下詔“可不奪俸”,并“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室”。于是,揚雄利用“孝廉”與“衛卒”交會的機會,“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西京雜記》也曾記載揚雄采集方言的情形:“揚子云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揚雄收集、編纂《方言》的目的,正如揚雄本人所說的,“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可以說是揚雄編纂《方言》的主導思想。劉歆在《與揚雄書》中也曾說:“今圣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徭俗;適子云攘意之秋也。”東晉郭璞《方言注序》亦云:“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這里劉歆、郭璞、揚雄說法不盡相同,但意義是一致的。揚雄編纂《方言》與昔日周天子遣使采風“不出戶牖,盡知天下”的目的并無二致。
揚雄“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的編纂目的,直接影響和決定了《方言》的編纂內容。《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此名雖為后世所加,但很貼近《方言》的內容。從這一全稱也可看出,《方言》的內容大致有二,一是“絕代語”,二是“別國方言”。“絕代語”就是“先代絕語”,亦即古語詞,“別國方言”就是“四方之語”“異國俗語”。揚雄將“別國方言”作為編纂內容,頗好理解,因為“別國方言”可以使人君“不出戶牖,盡知天下”。但揚雄為何將“絕代語”也納入編纂范圍?在揚雄看來,“絕代語”雖然為先代語詞,但這些語詞,并未全部泯滅,有的還保留在當代的方言當中。正如李開(1993)所言:“‘絕代語是在時間中考察,以今通語為標準,古有而今無,但不排斥仍留存于方言中。……故它們既可能存在于古代通語中,也可能存在于古代方言中,且在今方言中仍可能存在,僅僅以今通語為標準,這些古語(通語或者方言詞)詞是‘絕代了。”也就是說,“絕代語”與今方言有著割不斷的聯系,想要真正了解民風民俗,達到“辨風正俗”的目的,就不能不知古語詞,特別是那些至今仍保留在方言中的古語詞。揚雄把“絕代語”和“別國方言”一并納入方言的收集和編纂范圍,可以充分實現“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的編纂宗旨。
二、編纂方法論:即異求同,同中辨異
揚雄《方言》的第二個編纂思想是“即異求同,同中辨異”,這直接體現在《方言》的釋例上。舉例如下:
臺,胎,陶,鞠,養也。晉衛燕魏曰臺,陳楚韓鄭之間曰鞠,秦或曰陶,汝潁梁宋之間曰胎,或曰艾。
此為揚雄《方言》的條目通例。《方言》釋例通常由兩個部分組成。前半部分,先列出被訓釋的詞,然后以通語釋之。這一部分可稱為“雅詁”,被訓釋的詞稱為“群詁例字”,“通語”稱為“詁訓字,即母題”。上例中的“臺、胎、陶、鞠”即為“群詁例字”,“養也”即為“詁訓字,即母題”。后半部分為“方言”部分,具體指出被訓詞所在地域。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方言》的條目通例,用公式表示為“雅詁(群詁例字+詁訓字,即母題)+方言”。
《方言》的“雅詁”部分集中體現了揚雄“即異求同”的思想。將字形不同、意思相同的詞放在一起,以一通語來訓釋,可以極大地節省辭書的篇幅。《方言》的“雅詁”部分大體相當于《爾雅》的釋詞通例。濮之珍(1987)曾從編排形式、母題雅詁兩個方面對《方言》和《爾雅》進行過詳細比較,得出了“《方言》一書的雅詁本之于《爾雅》”的結論。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方言》中的“雅詁”與《爾雅》釋詞通例的相似性。至少可以這么認為,《方言》“即異求同”的編纂思想是對《爾雅》“以義類聚”編纂思想的繼承。《方言》“雅詁”與《爾雅》通例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試舉兩例,便可知其大概:
例一:
如、適、之、嫁、徂、逝,往也。(《爾雅·釋詁》)
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方言》第一,14/1)
例二:
懷、惟、慮、愿、念、怒,畏也。(《爾雅·釋詁》)
郁、悠、懷、怒、惟、慮、愿、念、靖、慎,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郁悠。惟,凡思也;慮,謀思也;愿,欲思也;念,常思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靖;秦晉或曰慎。凡思之貌亦曰慎,或曰怒。(《方言》第一,11/1)
《爾雅》訓釋通例的局限性是沒能指出被訓詞之間的差異。而揚雄編纂思想的先進性就在于“即異求同”與“同中辨異”并舉,“同中辨異”是其編纂思想的主流。這種編纂思想體現在《方言》釋例中的“方言”部分。揚雄用27年時間進行口語調查,其主要目的是要一一揭示“群詁例字”之間的差異。揚雄《方言》對“群詁例字”差異的訓釋,至少包含“地域之異(空間)”“古今之異(時間)”“音轉之異(時空兼具)”三個方面:
首先,《方言》普遍揭示了“群詁例字”的地域差異。《方言》條目中標明“通語”“凡語”“凡通語”“通名”“四方之通語”者,均指沒有地域限制、普遍使用的共同語,如:“頷、頤,頜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頜。頤,其通語也。”(34/10)此條中“頤”就是指沒有地域限制的“通語”。《方言》中凡言“某地某地之間曰(謂)”者,俯拾即是,均為通行地域較廣的大區方言。如:“聳、(爿爫犬),欲也。荊吳之間曰聳,晉趙曰(爿爫犬)。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爿爫犬)。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凡相被飾亦曰(爿爫犬)。”(1/6)這里的“聳”“(爿爫犬)”即為范圍較廣的方言。《方言》中凡言“某地曰”者,為通行范圍較小的小區方言,這在《方言》中也占相當大的比重。如:“掩、丑、掍、綷,同也。……或曰掍;東齊曰丑。”(22/3)這里“棍”“丑”均為某地方言。當然,這三種情況只是大致的分類,《方言》中許多詞條的“方言”部分,往往同時指出“通語”“某地某地之間語”或“某地語”。《方言》中涉及的地名較多,林語堂(1933)曾據此歸納出西漢14個方言系。《揚雄方言研究》(劉君惠,李恕豪,楊鋼等1992)曾對《方言》中涉及的行政區劃名、自然地理名進行詳細研究,劃分出漢代的12個方言區,即“秦晉方言區”“周韓鄭方言區”“趙魏方言區”“衛宋方言區”“齊魯方言區”“東齊海岱方言區”“燕代方言區”“北燕朝鮮方言區”“楚方言區”“南楚方言區”“南越方言區”和“吳越方言區”。從中可以看出,《方言》所收方言覆蓋的地域之廣。
其次,《方言》指出了某些詞的古今差異。《方言》中凡言“古今語”“古雅之別語”“古謂之”者,說的都是古代方言。如:
敦、豐、厖、砎、幠、般、嘏、奕、戎、京、奘、將,大也。凡物之大貌曰豐。厖,深之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奔,或曰幠。宋魯陳衛之間謂之嘏,或曰戎。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為之作釋也。(12/1)
這里指出“奔”“幠”“嘏”“戎”“夏”“奘”“京”“將”等字皆為“古今語”,并指出“古今語”的產生是由于“初別國不相往來”,而現在可能已經相同了。從這個詞條中還可看出,揚雄之所以要對“古今語”進行解釋,就是因為“舊書雅記故俗語”,后人已難以知曉。再如:
假、佫、懷、摧、詹、戾、艘,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佫。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摧,詹,戾,楚語也。艐,宋語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13/1)
這里指出,“假、佫、懷、摧、詹、戾、艐”雖同為“至”義,但均為古代之方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到如今已經相同了。“古雅”之言為“古代之正言”,那么“古雅之別語”即為“古代之方言”。《方言》中還有一些詞條,直接寫明是古語詞,如:
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禪衣。有袌者,趙魏之間謂之褳衣;無袌者謂之裎衣,古謂之深衣。(1/4)
這里明確指出,“裎衣”古代稱為“深衣”,“深衣”即為古語詞也。
第三,《方言》揭示某些被訓釋詞的語轉之異,這是揚雄對語詞聲韻轉變規律的重大發現。方言之間為何有所不同,方言為何可以轉變成通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音轉造成的。《方言》中凡是注明“轉語”“代語”“語之轉”者,均指這種情況。標明“轉語”者,如“庸謂之倯,轉語也”(47/3);“粿,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娓,火也”(6/10)。標明“語之轉”者,如:“(扌亻美)、鋌、澌,盡也。南楚凡物盡生者曰(扌亻美)生。物空盡者曰鋌,鋌,賜也。鋌此(扌亻美)澌皆盡也。鋌,空也,語之轉也(49/3)”。標明“代語”者,如:“悈鰓、干都、耇、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間代語也。”(39/10)《方言》對“轉語”現象的揭示,實際上也體現出揚雄“同中辨異”的思想,“轉語”詞多為聲音之轉,聲音相近,但畢竟還是有細微差別的存在,正因為如此,才產生了不同的“轉語詞”和“代語詞”。
此外,《方言》中還注意到了近義詞之間的細微差異。如:
例一:
咺、唏、(忄勺)、怛,痛也。凡哀泣而不止曰咺,哀而不泣曰唏。于方:則楚言哀曰唏;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少兒泣而不止曰咺。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少兒泣而不止謂之唴,哭極音絕亦渭之唴。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唴哏,楚謂之噭咷,齊宋之間謂之喑,或謂之怒。(8/1)
例二:
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瑜,或謂之采,或謂之埌,或謂之壟。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壤,大者謂之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墓謂之墲。(162/13)
例一對“咺”“唏”兩個近義詞之間的細微差別進行了揭示,即“哀泣而不止曰咺,哀而不泣日唏”。例二指出了“填”與“丘”在大小程度上的不同。
綜上所述,“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的編纂宗旨是揚雄繼承采風舊俗而確立的,這一思想使揚雄將“先代絕語”和“異國方言”同時納入《方言》采集和訓釋范圍。“即異求同、同中辨異”的編輯方法論則是揚雄對《爾雅》“以義類聚”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方言》不僅以通語來訓釋被訓釋詞,還盡可能地揭示出被訓釋的一組詞之間的地域差異、時間差異和語轉差異。《方言》在我國語言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歷代學者對之褒譽有加。時人張伯松即稱之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晉代郭璞對之評價尤為全面和中肯,他認為《方言》“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俗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方言》為方言學的研究和方言辭書的編纂開辟了新境,對后世“方言地理學”“語轉學”的產生和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揚雄憑借一人之力對全國方言進行長達27年的口語調查,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種治學精神,尤為歷代學者所稱道。揚雄在方言研究史、方言辭書編纂史上是不朽的。
(責任編輯 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