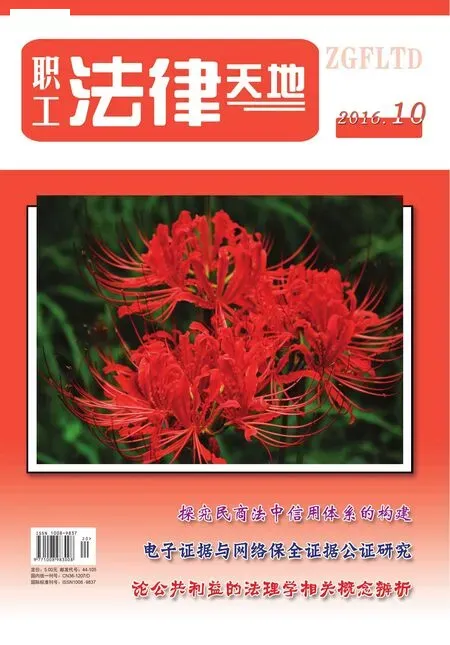以《折獄龜鑒》為視角淺談中國古代法律傳統
魏巧鳳
(250000 山東大學法學院 山東 濟南)
以《折獄龜鑒》為視角淺談中國古代法律傳統
魏巧鳳
(250000山東大學法學院山東 濟南)
《折獄龜鑒》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訴訟案例選編,由宋代鄭克編著。“折獄龜鑒”即為斷獄者提供借鑒。鄭克在本書中輯錄了從春秋至北宋大觀、政和年間歷代關于平反冤獄、辨別忠奸的故事,較為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古代司法官員在案件的審訊和判決等方面經驗,反映了中國古代人治為先、慎刑明德、禮法合一與重視證據的實用法律傳統。
折獄龜鑒 ;鄭克 ;法律傳統 ;實用主義
中國法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綿延不絕,從未中斷,由此而形成悠久而獨特的法律傳統。本文謹以成書于宋代的訴訟案例選編《折獄龜鑒》為視角,淺論中國古代法律傳統,提要鉤玄,探索中國古代法律的獨特之處。
一、人治甚于法治
在中國古代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行政權和司法權一直沒有明確的界限,所以地方行政官員也同時是司法審判官員,地方行政官員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審判各類的訴訟案件。從《折獄龜鑒》一書中也能看出,司法人員的心理品質對整個司法實踐活動的進行的具有重要的影響。[1]
司法人員良好的心理品質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即仁、智、勇。《折獄龜鑒》卷八列有“矜謹”專門,要求司法人員對于犯罪違法的人懷有憐憫謹慎之心,不要過于苛刻嚴峻。其次是“智”與“勇”,鄭克認為,如果司法者的智慧不足,就難以查明真相、辨別冤獄。《折獄龜鑒》中記載了大量關于用詐謀偵破案件的資料,如“陳述古祠鐘”、“蔣常留嫗”等。而在“智”與“勇”的衡量中,鄭克認為,“勇”比“智”更為可貴:如果是由于智慧不足而不能辨明,這還沒有什么可責備的;但如果是由于勇氣不足而不敢查辨,就應加以責罰了。[2]
二、慎刑明德,追求無訟
慎刑明德,是中國司法官員斷案的標準,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大夫在“德”與“刑”之間的價值取向。從周公的“明德慎罰”,到孔子的“為政以德”,到漢以后的“德主刑輔”,是一脈相承的。鄭克力主尚德緩刑,求實戒枉,提出“饑饉盜賊多”等觀點,要求司法人員對于犯罪違法的人懷有憐憫謹慎之心,不要過于苛刻嚴峻。在“寒朗廷爭”的按語中,作者更是把“仁者之情”作為司法人員的最重要的心理品質。[3]
慎刑明德的發展促進了無訟觀念的產生。在古代文臣階層看來,無訟即是統治者的德行得到了伸張,是政治清明的表征。由無訟的要求而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減少積案,和息糾紛的效果,然而其在實質上是與社會進步相徑庭的,它造成了人們缺乏運用法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觀念,并以訟為恥,進一步侵害了百姓的私權。《折獄龜鑒》中亦不乏司法官員為追求無訟而多方調解的案例。
三、禮法合一,綜合為治
禮在中國古代社會具有著“序尊卑、明貴賤、定親疏、別同異”的功能,對中國古代法律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禮指導著法律的制定,“出于禮則入于刑”。禮的規范也被用于補充法條的不足。
《折獄龜鑒》中也處處體現禮治對司法官員判案的影響。“賈黯案”與“殷仲堪案”體現了禮對法律的直接影響。[4]注重利用人際關系的親愛與憎惡,來偵破某些案件。“高楷留靴”和“包拯密喻”就是利用愛惡心理偵破案件的兩個例子。在封建制度下,統治者立法含禮,司法用禮,為的是維護宗法家族等級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最終目的。
四、重視證據、情理斷獄
中國古代法律很早就發展出重視證據的傳統,很早就脫離了神判法的桎梏。正如梁治平在《法意與人情》中寫到的那樣:“自有信史以來,法律即完全不受神明的支配與干預,它的道德基礎是倫常與人情,它的形而上學的根據是天理和自然。”[6]《折獄龜鑒》記載的許多案件都能為這一傳統提供佐證。蔡州知州高防通過驗布為疑犯洗刷冤屈即體現了古人對證據的重視。而在在李惠案及傅琰案中,雍州刺史李惠巧判羊皮歸屬;山陰縣令傅琰明析絲的所有,“鞭絲擊皮,事異理同,皆以物為證者也”,更是提出物證優于人證的觀點。[7]
情理斷獄是中國古代另一典型法律傳統。這一理念是從偵查和判決進行考察。在偵查階段,司法官員運用情理作為審理的原則和方式,排除疑點,避免產生冤假錯案。《折獄龜鑒》在“鞫情”與“辨誣”中用了大量筆墨講情理斷獄,子產由婦人哭聲懼而不哀而懷疑其中另有隱情,裴度按兵不動追回印鑒即是其中典型案例。
本文從考察具體案例出發,從人治為先、慎刑明德、禮法合一與重視證據這四方面的角度挖掘《折獄龜鑒》中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法律傳統。《折獄龜鑒》作為封建社會的案例匯編,有自身的歷史局限,但這并不影響它成為一部不朽的法律著作,書中所闡明的以實用主義為中心的法律傳統,對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仍有重要意義。
[1]張晉藩,論中國古代法律的傳統,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4
[2]鄭克,《折獄龜鑒·議罪·陳男守正》,南宋
[3]鄭克,《折獄龜鑒·矜謹·陳朗廷爭》,南宋
[4]鄭克,《折獄龜鑒·議罪·賈黯》、《折獄龜鑒·議罪·殷仲堪》,南宋
[5]梁治平,法意與人情,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1
[6]鄭牧民,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研究,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