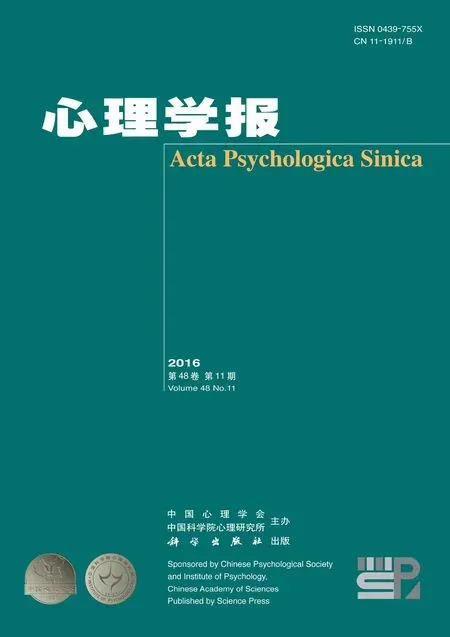低階層者的系統合理化水平更高嗎?
——基于社會認知視角的考察*
楊沈龍 郭永玉 胡小勇,2 舒首立,3 李 靜
(1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人的發展與心理健康湖北省重點實驗室, 武漢 430079)(2西南大學心理學部, 重慶 400715) (3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蕪湖 241000)
1 引言
貧富分化問題已成為當今很多國家共同面對的挑戰, 而社會階層的固化常常使這一困境雪上加霜(Davidai & Gilovich, 2015)。在中國, 情況同樣如此。一方面, 連年居高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顯示著我國巨大的分配不平等與貧富差距現象; 另一方面,階層的固化、代際之間的流動凝滯, 使得經濟分配的矛盾得以進一步突顯。很多研究顯示, 近年來底層民眾的向上流動正在變得愈發困難(e.g., 李春玲,2014; 余秀蘭, 2014), 即使完成了高等教育, 出身低階層家庭的個體上升的通道依然相對狹窄(岳昌君, 張愷, 2014)。在此背景下, 當代低階層者對于社會系統的態度值得高度關注。他們對于當前社會體系的公正性、合理性作何感受?其感受有著怎樣的心理基礎?又是否會在某些條件下有所變化?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僅是維護穩定的需要, 還將有助于我們從建設性的角度出發, 深入了解低階層民眾的心理特點與心理需求, 進而可以為社會治理提供有益的參考。
那么在已往研究中, 心理學對此做過怎樣的探討?這里不能不提到系統合理化理論(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中的一個觀點, 即低階層者比高階層者更認為社會系統是合理的, 更支持現存體系(Jost, Pelham, Sheldon, & Sullivan, 2003)。然而, 此觀點也一直存在著很大爭議(楊沈龍, 郭永玉, 李靜,2013), 因為很多的研究結論恰恰相反, 發現低階層比高階層更反對系統(e.g., Brandt, 2013a)。那么與高階層相比, 低階層到底是否更認為系統合理呢?本研究將以此問題為理論出發點, 以中國的不同社會階層者為現實關注點, 考察高低階層者認可系統合理性的差異, 并且基于系統合理化理論的最新理論發展, 采用社會認知視角進一步探索該效應的心理機制與邊界條件。
1.1 社會階層與系統合理化
社會階層(social class)是一種用來反映個體在社會層級階梯中相對位置高低的社會分類, 一個人的社會階層代表了他(她)所占有的客觀社會資源,以及其主觀上所感知到的自身社會地位(Kraus, Piff,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Kraus, Tan, & Tannenbaum, 2013)。系統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指的是個體維護、支持現存社會體系,并認為其公平、合理、正當的一種傾向(Kay & Jost,2003, 2014)。一般意義的系統合理化水平可以通過系統合理化量表(system justification scale, Kay &Jost, 2003)測得, 此外系統合理化也有一些具體的心理和行為表現(Jost et al., 2014)。立足于理論目的,本研究重點關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系統合理化。
系統合理化理論認為, 個體天然地會將自己所處的社會系統視為合理、正當的(Jost & Banaji, 1994)。基于此框架, Jost等(2003)在一次調查中發現, 與高階層相比, 低階層者有著更高的系統合理化水平,也即更認為系統是合理的。可以看出, 這一結果對于系統合理化理論來說有比較特殊的價值, 因為它說明個體對系統合理性的感知是可以超越其個人得失的(低階層在系統中處境不利卻仍然認為系統合理), 所以“低階層更認為系統合理”很快成為系統合理化理論中一條重要的觀點(e.g., Jost, Banaji,& Nosek, 2004)。然而隨著研究的積累, 越來越多更有說服力的數據顯示了恰恰相反的結論, 即低階層似乎是更反對系統的(e.g., Brandt, 2013a, 2013b;Kraus & Callaghan, 2014; Lee, Pratto, & Johnson,2011), Brandt (2013a)甚至直接地提出了對于Jost等(2003)的數據可重復性的質疑。
更關鍵的是, 認為低階層者系統合理化水平更高的觀點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 Jost及其同事(2003)曾試圖從緩解焦慮的角度解釋為什么低階層會如此, 但此解釋也沒有得到直接的研究支持(e.g.,Brandt, 2013a)。Jost團隊最近也承認了這一點, 他們表示, 低階層是否更覺系統合理, 這一問題是復雜的, 不僅關乎焦慮, 也需要充分考慮其他心理過程(Kay & Jost, 2014)。但是對于所謂“其他心理過程”, Kay和Jost (2014)暫未做出充分闡述。而同樣令人遺憾的是, 以Brandt (2013a)為代表的“反對派”也并沒有從理論上詳細闡明為什么低階層會更反對系統。也就是說, 爭論雙方都更多地關注階層對系統合理化直接的預測關系, 但缺乏對其機制做更細致的理論闡述。
1.2 社會認知視角的引入:高低階層者系統合理化的差異及其機制
就在這種情況下, 最近有學者(Hussak & Cimpian,2015)基于認知途徑(cognitive pathway), 對于系統合理化理論提出了一個補充解釋。此解釋雖然并沒有直接關注階層與系統合理化的關系, 但其思路卻恰好可以回應Kay和Jost (2014)上面所說的“其他心理過程”。
該認知途徑的解釋也同意系統合理化理論最基本的主張, 即人會自然地認可社會系統的合理性,但它對系統合理化理論做了一點重要的補充, 就是強調個體生來固有的認知傾向是系統合理化最主要的心理基礎:個體在知覺外物時更多關注其內在特征, 也更多對其結果進行內部歸因, 當以這種方式去感知社會經濟差異(socioeconomic disparity)(如窮人和富人)時, 就會自然地認為事物間之所以存在差異是因其內部因素不同(如之所以有貧富差異是因為富人和窮人自身固有的特征不同), 從而對社會經濟差異產生理所當然之感, 也就因此認為社會系統中的事物都是公正合理、應該被支持的(Hussak & Cimpian, 2015)。在其研究中, Hussak和Cimpian (2015)告知被試Blarks遠比Orps富有(兩人均為虛構), 發現被試確實更傾向于對此差異做內歸因解釋(因為Blarks比Orp聰明、能干), 而且內歸因強度正向預測系統合理化。相關領域研究如Ng和Allen (2005)也發現, 個體越傾向于將貧富差異歸結于內因(如人與人能力不同、努力程度不同)而非外因(如體制、偏見), 則其公平感就越強, 而且個體的貧富歸因甚至比個體自身是否獲益更能有效預測其公平感。這充分地體現了認知因素(貧富歸因)在此問題中的關鍵作用, 說明從認知途徑來理解系統合理化的成因, 確是值得借鑒的。
不過, 認知途徑解釋(Hussak & Cimpian, 2015)對系統合理化的理解似乎還是有一定局限, 因為它默認所有人在歸因時都是更注重內部因素, 卻忽略了個體差異。而恰恰對于我們所關注的低階層, 其歸因傾向可能是正相反的——作為社會階層心理學(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領域最有影響理論之一的階層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就明確闡述過:低階層的認知模式是情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 即更多認為人的行為會受到外部情境因素的影響; 而高階層更注重自我本身, 更多認為人的行為主要是由個體內部因素決定(Kraus et al, 2012; 胡小勇, 李靜, 蘆學璋, 郭永玉,2014)。很多研究也都顯示低階層的歸因傾向確實較為忽略內部因素而更注重外部因素(e.g., Grossmann& Varnum, 2011), 包括對貧富的歸因(Kraus, Piff,& Keltner, 2009; 李靜, 2014)。這說明對于低階層者來說, 系統合理化的認知基礎相對來說并不存在。換言之, 認知途徑解釋(Hussak & Cimpian, 2015)將個體對于貧富的內歸因傾向作為系統合理化的形成機制, 這一視角是可取的, 但它卻沒能充分考慮低階層者所具有的不同歸因傾向, 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系統合理化結果。
現在讓我們回歸研究問題, 低階層者系統合理化水平更高嗎?基于上述理論推導, 本研究認為低階層者的歸因傾向與形成系統合理化的認知基礎是恰恰相反的, 因此會傾向于更少地認為系統合理。再從研究上看, 更多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大樣本(e.g. Brandt, 2013a; Lee et al., 2011)和跨文化(Whyte& Han, 2008)的數據都顯示低階層更為反對系統。最后從現實上看, 低階層者也確實面臨更多的不公(e.g., 李春玲, 2014)。因此基于理論、研究和現實的多重考慮, 本研究提出:
假設1:與高階層者相比, 低階層者的系統合理化水平相對較低。
此外, 上述理論分析顯示, 對于貧富差距的歸因傾向可能是低階層者系統合理化水平較低的中介因素:階層社會認知理論(Kraus et al., 2012)揭示了階層與貧富歸因的關系, 系統合理化的認知途徑解釋(Hussak & Cimpian, 2015)又闡述了貧富歸因對于系統合理化的重要作用, 當我們將這兩個立足于社會認知的理論框架相結合, 可以看出個體的階層水平、貧富歸因傾向和系統合理化之間, 也許存在著階層—歸因—合理化的邏輯鏈條關系。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2:貧富歸因在社會階層與系統合理化間起到中介作用, 社會階層越低, 就會越少地對貧富差距做內歸因解釋, 并基于此表現更低的系統合理化傾向。
1.3 社會認知過程的邊界:控制感的調節作用
在假設2的基礎上, 研究還將進一步考察上述中介模型成立的邊界條件。為此我們還是要借助社會認知的理論框架, 看什么因素能對低階層者的這一認知機制產生影響。而根據上述階層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Kraus et al., 2012), 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恰能起到這一作用。
控制感是個體對于自己掌控事件能力和受到外部限制程度的感知(Lachman & Weaver, 1998;Skinner, 1996), 它既是個體差異變量, 又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Turiano, Chapman, Agrigoroaei, Infurna,& Lachman, 2014)。在階層社會認知理論中, 控制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Kraus等(2012)指出, 低階層者之所以在認知過程中更重視外部因素, 與他們成長過程中體驗到更多的限制有關, 而一旦低階層者的控制感升高, 他們也會傾向于表現出類似高階層的認知模式。Kraus等(2009)的研究可以為此提供支持:低階層者在認知活動中比高階層更多地關注背景性線索, 但啟動高低階層都暫時體驗到高控制感后, 兩階層的差異消失, 低階層也開始更多地注意前景物, 轉入了“高階層認知模式”, 而高階層則受控制感的影響不大。還有很多研究從不同角度顯示了控制感對于低階層者的積極作用 (Lachman &Weaver, 1998; McCoy, Wellman, Cosley, Saslow, &Epel, 2013; Turiano et al., 2014)。
對于這些理論觀點和研究結果, 我們可以將其集中歸納為低階層者對控制感的依賴。表現在社會認知中, 就是在控制感較低時, 他們的認知傾向是更注重外部背景因素的; 但當控制感較高時, 他們就傾向于切換到“高階層模式”, 表現出更偏重于內部特征的認知傾向。因此具體到本研究, 可以推測:如果低階層者擁有更多的控制感, 也許就可以改變既有認知模式, 彌合與高階層在此認知過程中的差異, 繼而改變系統合理化水平。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3:控制感會調節階層—貧富歸因—系統合理化的中介關系, 而且控制感是通過調節階層預測貧富歸因這一路徑來實現對中介模型的調節(調節前半路徑):當個體控制感較低時該模型成立; 而當控制感較高時, 該中介模型不成立, 高低階層者貧富歸因的差異不顯著。

圖1 研究總假設模型
本研究總的假設模型如圖1所示。為了使結果更穩健, 我們設計了兩個研究。兩研究都將對上述3個假設依次進行檢驗, 它們除了樣本不同以外,主要是對社會階層和控制感這兩個關鍵變量都將使用兩種不同的操作性定義。先說社會階層, 目前比較能代表研究主流的主要是兩種思路:一種認為被試對于自身或自己家庭在社會中所處位置的主觀感知(也即主觀社會階層, subjective social class)是最能反映階層水平的, 也是對于預測不同階層的心理差異最為有效的(Kraus et al., 2013); 另一種則是將主觀階層與能反映個體對于社會資源占有狀況的客觀指標(也即客觀社會階層, objective social class)相結合來體現社會階層水平(e.g., Dubois,Rucker, & Galinsky, 2015; Tan & Kraus, 2015)。這兩種做法都很常見, 因此我們擬在兩個研究中分別采用主觀指標和主、客觀合成指標來反映被試的階層。再說控制感, 前文提到它兼具個體特質性和情境可變性, 所以對其進行問卷測量和實驗操縱也都很普遍, 很多研究(e.g., Kay, Gaucher, Napier, Callan,& Laurin, 2008)還在不同子研究中綜合考慮二者,以此互為驗證。因此研究1擬對控制感進行實驗操縱, 研究2將采用相關法對其加以測量。
這樣總的來看, 兩個研究可以形成一定的互補關系。研究1能更好地揭示控制感與其他變量的因果關系, 但既然是實驗操縱, 其效應能否在一般的生活中得到體現尚有待檢驗; 而且因為是在實驗室進行, 樣本量相對較小, 被試代表性相對較低。而研究2通過更大樣本的調查, 選取不同來源的被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上述不足加以彌補。
2 研究1
2.1 方法
2.1.1 被試
招募華中師范大學在校學生作為被試, 排除有相關研究經歷和未能完成研究過程的被試后, 得到有效數據241份, 其中男性110人, 平均年齡21.77歲(SD
=2.37)。2.1.2 研究程序和研究工具
研究的自變量為社會階層, 用量表測得, 以連續變量計入統計; 調節變量為控制感, 采用實驗操縱。研究流程參照Kraus等(2009)的設計。被試來到實驗室后, 首先測量其基本信息和家庭社會階層水平。之后隨機將被試分入高控制感啟動組或低控制感啟動組, 操縱其形成較高或較低控制感的狀態,繼而測量被試的貧富歸因與系統合理化水平。全部完成后, 發放禮品, 講解研究目的。
階層的測量采用國內外同類研究常用的階梯量表(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 給被試呈現圖2中所示階梯, 讓其想象這個梯子代表了中國不同的家庭所處的不同的階層, 等級越高,表示其所處的階層地位越高。讓被試報告他覺得自己出身的家庭位于1~10中的哪一層。

圖2 階梯量表
控制感操縱采用該領域常用的回憶任務(e.g.Friesen, Kay, Eibach, & Galinsky, 2014; Kay et al.,2008)。這個任務就是讓被試自由回憶并寫下一件他們體驗到完全掌控(啟動高控制感)或者無能為力(啟動低控制感)的事件, 來使他們暫時體驗到不同控制感的狀態。遵照之前學者(e.g., Shepherd, Kay,Landau, & Keefer, 2011)建議, 研究通過預實驗來考察操縱效果, 66名大學生被試(與研究1樣本不同,其中男性27人, 平均年齡21.0歲)被隨機分入這兩個啟動組, 之后采用Lachman和Weaver (1998)編制的控制感量表對其啟動后的控制感水平進行測量(α=0.83)。結果顯示高控制感啟動組的控制感顯著高于低控制感啟動組,t
(64)=2.92,p
< 0.01,d
=0.73, 證明該實驗操縱確實可以影響被試即時的控制感水平。貧富歸因的測量采取李靜(2014)編制的具有良好信效度水平的貧富差距歸因問卷, 包括了內部歸因和外部歸因兩個維度, 各有8個項目。問卷基于廣泛地城鄉調查和項目分析, 列出了可能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原因, 內歸因的條目如“個人勤奮或努力程度不同”、“個人的能力不同”等; 外歸因的條目如“有無關系或門路”、“家庭背景或出身不同”等內容。對于每一種歸因, 讓被試報告其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采取7點計分。在計算總分時, 由于研究在理論上更強調的是內歸因傾向, 依照前人研究(Hussak & Cimpian, 2015)做法, 也是工具編制者(李靜, 2014)的建議, 取被試在內歸因分量表上的8道題總分與外歸因量表上8題總分的差值, 作為貧富歸因的得分, 得分越高, 表示被試的內歸因傾向越高。在本研究中, 內、外歸因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65、0.78。
系統合理化的測量采用該領域研究中常用的系統合理化量表(Kay & Jost, 2003)。該量表測查被試對系統是否公平、是否惠民等問題的感知, 如“中國政府的大多數政策都給民眾帶來了好處”、“中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糟糕(反向計分)”, 量表共8道題目(2道反向計分), 采用7點計分。計算所有項目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代表被試系統合理化水平越高(α=0.75)。
統計分析通過SPSS18.0完成。對于是否需要對一些因素如人口學變量做統計控制(statistical control), 研究遵循了心理統計學者最新的建議(e.g.,Becker et al., 2016; Bernerth & Aguinis, 2016), 因為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關注上述變量本身在現實社會中的真實關系, 而不存在明確理論目的需要排除某些協變量的干擾, 所以本研究在數據處理時未考慮統計控制(研究2同理)。
2.2 結果
2.2.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矩陣如表1示,其中性別和控制感采用虛擬變量, “1”為男性, “0”為女性; “1”為高控制感組, “0”為低控制感組, 后同。可以看到社會階層與系統合理化存在顯著正相關(r
=0.15,p
< 0.05), 假設1得到支持。階層和貧富歸因(r
=0.15,p
< 0.05)、貧富歸因和系統合理化(r
=0.37,p
< 0.001)的正相關關系也均顯著。2.2.2 中介效應檢驗
將所有被試數據代入假設2的中介模型中加以檢驗, 根據心理統計學者(Hayes, 2013)建議, 使用偏差矯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檢驗(抽取1000個樣本)。結果顯示, 社會階層對系統合理化總的預測效應顯著(B
=0.09,SE
=0.04,p
< 0.05), 95%的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為[0.01, 0.16], 假設1得到驗證; 社會階層對貧富歸因的預測作用顯著(B
=0.76,SE
=0.32,p
< 0.05), 95%CI為[0.12, 1.40];同時納入社會階層和貧富歸因后, 社會階層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不顯著(B
=0.06,SE
=0.04,p
> 0.05),95%CI為[–0.01, 0.13], 貧富歸因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作用顯著(B
=0.04,SE
=0.01,p
< 0.001),95%CI為[0.03, 0.06]。貧富歸因的中介效應為0.032,95%CI為[0.006, 0.069], 占總效應的35.9%。以上結果表明貧富歸因在階層預測系統合理化中起中介作用(但不作為完全中介作用, 參見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a), 研究2同理), 假設2得到支持。2.2.3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假設3的理論模型是控制感對中介模型前半段的調節作用, 因此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b)所建議的檢驗方法, 應對如下3個方程進行檢驗(如表2所示, 下列結果通過bootstrap檢驗得出, 抽1000個樣本)。首先檢驗的回歸方程為系統合理化=c+c社會階層 + c控制感 + c社會階層×控制感 +e(方程1)。結果表明, 社會階層與控制感的交互項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不顯著(B
=–0.15,SE
=0.08,p
>0.05), 95%CI為[–0.31, 0.01]。接下來檢驗方程貧富歸因=a+ a社會階層 + a控制感 + a社會階層×控制感 + e(方程2)和系統合理化=c’ + c’社會階層 + b貧富歸因 + e(方程3)。方程2的檢驗結果表明, 社會階層與控制感的交互項對貧富歸因的預測顯著(B
=–1.58,SE
=0.67,p
< 0.05), 95%CI為[–2.90, –0.26]。方程3的檢驗結果表明, 貧富歸因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顯著(B
=0.04,SE
=0.01,p
<0.001), 95%CI為[0.03, 0.06]。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b)提出的標準, 本研究預期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為了深入了解有調節的中介模型的實質, 進一步通過簡單斜率檢驗來考察不同控制感條件下階層對貧富歸因的預測效應。結果顯示, 低控制感條件下, 社會階層對貧富歸因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B
=1.39,SE
=0.44,p
< 0.01), 95%CI為[0.52, 2.25]; 但在高控制感條件下, 低階層的貧富歸因與高階層并無顯著差異(B
=–0.20,SE
=0.51,p
>0.05), 95%CI為[–1.20, 0.81] (如圖3)。最后考察在調節變量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應的不同情況, 結果顯示在低控制感的情況下, 中介效應模型成立, 非標準化的中介效應為0.06, 95%CI為[0.02, 0.11],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50.6%; 而在高控制感條件下, 該中介模型不成立, 非標準化的中介效應為–0.01, 95%CI為[–0.06, 0.03], 由于置信區間包括0, 所以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可以忽略。以上結果共同支持了假設3的成立。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N =241)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N=241)

圖3 控制感對社會階層預測貧富歸因的調節作用(研究1)
2.3 討論
研究1的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3個假設。首先,來自于越低社會階層的個體, 其系統合理化水平也相對越低, 這與系統合理化理論的觀點不符(e.g.,Jost et al., 2003), 但與大多數該領域的研究相一致(e.g., Brandt, 2013a)。進一步考察發現, 借助于貧富歸因這一社會認知視角可以比較好地解釋這一效應, 也即低階層者系統合理化水平相對較低,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對于人與人為何產生貧富差距的解釋更偏向于外部, 而較少地感到人可以基于能力或努力等自身因素實現富裕。更進一步來看, 這種階層—歸因—合理化的中介邏輯又會受到其控制感水平的調節, 若低階層者體驗到較高的控制感則可以彌合與高階層在歸因上的差異, 改變此中介過程。該結果支持了本研究基于社會認知視角提出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說明從認知機制的角度來理解此問題是可行的。
3 研究2
3.1 方法
研究1支持了全部3個假設, 但基于本研究的總體考慮, 為使結論更加可靠, 研究2將采用基于更大樣本的相關法再次檢驗上述假設。
3.1.1 被試
采取分層整群抽樣法選取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江漢大學、湖北商貿學院在校學生為被試, 共得到有效問卷829份。其中男生357人, 平均為20.71歲(SD
=2.12)。3.1.2 研究工具
社會階層測量, 綜合考慮主觀階層與客觀階層兩方面指標, 并參照同類研究做法(Tan & Kraus,2015), 將主、客觀兩個指標分別轉化為標準分數然后相加, 來反映被試所在的社會階層。主觀階層的測量同研究1。客觀階層采用陸學藝(2002)提出的基于中國本土化的, 以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為依據劃分的十大階層, 從高到低包括了從國家和社會管理者到城鄉無業半失業者共10個等級, 分別賦值1~10, 讓被試報告其父母分別屬于哪種職業, 反向計分后取父母中較高的分數來代表其家庭的客觀階層水平。
控制感測量, 采用Lachman和Weaver (1998)編制的控制感量表的中文版(李靜, 2014), 包括掌控感和限制感(反向計分)兩個可相加維度, 共12個項目, 7點計分, 得分越高代表被試控制感越高。本研究中的數據顯示, 量表結構效度良好, χ/df
=3.49, RMSEA=0.06, SRMR=0.05, CFI=0.92, GFI=0.96,α
系數為0.77。貧富歸因測量同研究1。研究2結果顯示, 量表結構效度良好, χ/df
=6.37, RMSEA=0.08,SRMR=0.06, CFI=0.84, GFI=0.91。內、外歸因的α
系數均為0.78。系統合理化測量同研究1。研究2結果顯示, 量表結構效度良好, χ/df
=5.78, RMSEA=0.07,SRMR=0.04, CFI=0.96, GFI=0.97,α
系數為0.80。3.2 結果
3.2.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與檢驗
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根據相關建議(周浩,龍立榮, 2004), 研究從程序方面進行了相應控制,如采用匿名方式進行測查、部分條目使用反向題等。數據收集完成后,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 結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9個, 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13.73%, 小于40%的臨界標準。此外, 還使用Mplus7.0軟件對階層、控制感、貧富歸因、系統合理化4個構念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并將擬合指數與單因子模型進行比較。結果顯示, 四因子模型的擬合指數明顯好于單因子模型。以上結果都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中的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它們的相關矩陣如表3所示, 可以看到社會階層與系統合理化存在顯著正相關(r
=0.08,p
< 0.05), 假設1得到支持。社會階層和貧富歸因(r
=0.16,p
< 0.001)、貧富歸因和系統合理化(r
=0.31,p
< 0.001)的正相關關系均顯著, 與研究1結果一致。3.2.3 中介效應檢驗
中介效應檢驗步驟同研究1, 只是參照Hayes(2013)的建議和做法, 增加考慮了學生對學校的嵌套關系。分析結果顯示, 社會階層預測系統合理化總效應顯著(B
=0.05,SE
=0.02,p
< 0.05), 95%CI為[0.01, 0.08], 假設1得到驗證; 社會階層對貧富歸因的預測作用顯著(B
=0.73,SE
=0.15,p
<0.001), 95%CI為[0.44, 1.01]; 同時納入社會階層和貧富歸因后, 社會階層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作用不顯著(B
=0.01,SE
=0.02,p
> 0.05), 95%CI為[–0.02,0.05], 貧富歸因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作用顯著(B
=0.04,SE
=0.004,p
<.001), 95%CI為[0.03, 0.05]。貧富歸因的中介效應為0.03, 95%的置信區間為[0.017, 0.045], 中介效應占到總效應的67.6%。以上結果驗證了假設2的成立。3.2.4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見表4)步驟同研究1,只增加考慮了學生對學校的嵌套關系(Hayes, 2013)。方程1中, 社會階層與控制感的交互項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不顯著(B
=–0.03,SE
=0.02,p
> 0.05),95%CI為[–0.08, 0.02]。方程2中, 社會階層與控制感的交互項對貧富歸因的預測顯著(B
=–0.41,SE
=0.18,p
< 0.05), 95%CI為[–0.77, –0.05]。方程3中,貧富歸因對系統合理化的預測顯著(B
=0.04,SE
=0.00,p
< 0.001), 95%CI為[0.03, 0.05]。據此, 本研究預期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溫忠麟, 葉寶娟, 2014b)。進一步通過簡單斜率檢驗來考察不同控制感條件下(取正負一個標準差)階層對貧富歸因的預測效應, 結果顯示, 低控制感條件下, 社會階層對貧富歸因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B
=0.89,SE
=0.20,p
< 0.001), 95%CI為[0.49, 1.29]; 但在高控制感條件下, 低階層的貧富歸因與高階層的差異不再顯著(B
=0.29,SE
=0.19,p
> 0.05), 95%CI為[–0.08,0.66] (如圖4)。最后考察在調節變量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應的不同情況, 結果顯示在低控制感的情況下, 中介效應模型成立, 非標準化的中介效應為0.04,p
< 0.05, 95%CI為[0.02, 0.06], 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71.8%; 而在高控制感條件下, 該中介模型不成立, 標準化的中介效應為0.01,p
> 0.05,95%CI為[–0.01, 0.03]。以上結果共同支持了假設3的成立。
表3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N=829)

表4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N=829)

圖4 控制感對社會階層預測貧富歸因的調節作用(研究2)
3.3 討論
在研究1的基礎上, 研究2通過更大樣本的調查, 同樣驗證了社會階層預測系統合理化的效應和社會階層—貧富歸因—系統合理化的中介關系, 并且結果再次表明這一關系會受到控制感的調節。因為研究2關注的是更廣泛的樣本, 測查的也是一般化的狀態, 所以比研究1更具有說服力; 但研究1因為操縱了控制感, 能夠更好地體現它與貧富歸因和系統合理化的因果關系。總之, 兩個研究可以互為驗證, 共同為上述3個假設提供了比較堅實的支持。
4 總討論
4.1 社會階層與系統合理化的關系
本研究的兩組數據都表明, 個體社會階層越低就會越少地支持現存系統。顯然此結果并不符合系統合理化理論中“低階層更認為系統合理” (Jost et al.,2003)的觀點; 但從系統合理化理論最近的表述來看, 其觀點也并非一味強調這一效應必然成立(Kay& Jost, 2014)。因此, 基于中國樣本對此效應進行檢驗是很有必要的。而且, 對于系統合理化理論和本問題來說, 中國的低階層者具有其獨特的研究價值。因為系統合理化理論起源于美國, 而“美國夢”的盛行使得美國人普遍認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Kraus & Stephens, 2012), 即便低階層者也對向上流動有樂觀的預期(Kraus & Tan, 2015), 因此可以說“低階層更認為系統合理”的提出, 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但是在中國, 階層固化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低階層者向上流動的信心(余秀蘭,2014), 這種差異是較為明顯的。因此, 本研究的數據對于系統合理化理論來說是寶貴的, 而且研究結果也并不支持“低階層更認為系統合理”的觀點, 充分說明系統合理化理論有必要更多考慮不同的人群和文化(e.g., Cichocka & Jost, 2014)。
顯然, 本研究結論遠不足以推翻Jost等(2003)的理論觀點, 但可以為進一步探索該問題提供啟示:階層與系統合理化的關系也許不可避免地與具體的文化和群體有關, 也就是說, 在某些特定的社會體系中, 低階層可能確實會更認為系統合理; 在另一些體系中則可能恰恰相反。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Jost團隊也提出, 階層與系統合理化的關系可能并不是確定的, 這取決于低階層者權力感的高低和對系統經濟結果的依賴程度, 當然在研究中他們只是重點考察了權力感與結果依賴對于系統合理化的影響而沒有真正涉及到階層(van der Toorn et al.,2015), 但這一思路與本研究還是有著一定的共通性, 即都是考慮要將此問題做更全面、細致的區分, 而不再籠統地強調低階層一定更認可系統的合理性。這也許是未來更深入地考察此問題的一個研究方向。
4.2 貧富歸因的中介作用
在假設1的基礎上, 研究結果進一步支持了貧富歸因是階層預測系統合理化的中介變量, 體現了認知途徑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 系統合理化理論更多強調人們這種對系統合理性的認可是為了緩解因無法改變系統而產生的焦慮(e.g., Jost& Hunyady, 2005), 而較為忽略認知因素的作用(Hussak & Cimpian, 2015)。我們并不否認緩解焦慮這一思路的理論價值, 但是具體到社會階層預測系統合理化的問題, 即使Kay和Jost (2014)也承認緩解焦慮這一解釋思路并不完善; 而且Hussak和Cimpian (2015)的研究表明即使控制了焦慮因素,內歸因傾向依然可以很好地預測系統合理化。因此本研究將理論視角定位于認知途徑, 讓階層社會認知理論(Kraus et al., 2012)和系統合理化的認知途徑解釋(Hussak & Cimpian, 2015)這兩個立足于社會認知的理論形成了一次對話, 構建起“階層—歸因—合理化”這一更完整的邏輯鏈。可以說, 本研究是利用了系統合理化理論的最新思路(認知途徑觀點), 對于該理論的一個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給出了一種解釋。
此外研究結果也支持和擴展了上述兩個社會認知理論。對于階層社會認知理論來說, 其核心觀點就是高低階層有根本性的認知傾向差異, 而且該差異可以作為高低階層許多方面差異的解釋機制(Kraus, Piff, & Keltner, 2011), 本研究將這種認知差異的解釋力擴展到系統合理化層面, 進一步擴展了該理論的外延。同時, 本研究也部分地支持并發展了系統合理化的認知途徑解釋(Hussak & Cimpian,2015), 因為該理論主要強調的是高階層的典型認知傾向(內歸因), 而我們更強調低階層者不認為系統合理是因為他們貧富內歸因傾向較弱, 可以說是針對此理論的偏頗之處做了必要補充。
4.3 控制感的調節作用
那么對于如上中介過程, 何時又會有所變化?或者說如何改變低階層者外歸因—反對系統的模式?本研究發現提升控制感可以起到這一作用。這再次支持了階層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 即控制感的升高可以改變低階層者的認知傾向(Kraus et al.,2009, 2012)。不過該理論并未直接考察過控制感對低階層者歸因的影響, 本研究對這一點給予了補充,并且還考察了這一作用的后效——系統合理化水平, 延伸了控制感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 社會階層心理學領域另一重要理論——社會文化視角(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也非常重視控制感對于低階層者的作用, 并且也強調了控制感升高時低階層可以轉入“高階層模式” (Stephens, Markus, & Phillips,2014)。其實, 如何幫助低階層轉變固有的心理模式以促進其更好地向上流動, 已成為社會階層心理學新的發展方向(e.g., Stephens et al., 2014), 未來這一領域可以更多考慮控制感在其中的作用。
當然, 促進階層流動, 既關乎低階層個人因素,也關乎社會系統因素, 恰如本研究中控制感的操作性定義, 既包括主體對外界的掌控感, 也包括外界對主體的限制(Lachman & Weaver, 1998), 將這兩點結合來看, 本研究中控制感的調節作用成立可以帶來很好的啟示:要想讓低階層改變歸因模式, 進而認為系統合理, 這需要個體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一方面, 個體可以通過簡便易行的自我調節方式來提升控制感, 例如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執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等策略都被發現具有這種積極作用(e.g., Arbour & Martin Ginis, 2009;Harris, Mayle, Mabbott, & Napper, 2007)。另一方面,社會系統的影響也非常重要, 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通過改變客觀社會條件來增進民眾的控制感, 可能比單純強調個體進行自我調節來提升控制感更有建設性意義。例如趙志裕, 區穎敏, 陳靜(2008)通過情境模擬實驗, 發現外部環境對個體的制約越少,被試的控制感就越高; 李靜(2014)則運用趙志裕等(2008)的實驗范式, 進一步發現環境制約程度還會影響被試對于自己在實驗中所得代幣的歸因。這些結論可以為社會治理提供有益的參考——在低階層自身進行適度自我調節的同時, 社會也應盡可能減少對底層群體的限制壁壘, 來進一步幫助其提升控制感, 讓他們感到自己在這樣一個社會里面, 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財富和成功。這也許是本研究最重要的一點實踐啟示。
4.4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需要未來研究繼續深入。首先, 本研究樣本為大學生, 盡管從現有研究來看, 出身于高(低)階層家庭的學生所具備的很多心理特點與已經步入社會的高(低)階層者并無明顯差別(Kraus et al., 2012), 而且以學生作為被試來反映社會階層的效應也是研究中常用的做法(e.g.,Na & Chen, 2016; Stephens, Fryberg, Markus, Johnson,& Covarrubias, 2012), 但在將本研究結論推廣至更大范圍的群體時, 還是應該謹慎, 未來研究可以更多采用不同的群體來驗證本研究的結論。其次, 本研究采用系統合理化量表來反映因變量, 代表了最一般意義的系統合理化, 但其實, 系統合理化還可以體現在一些具體細節方面, 如政治保守主義(Jetten,Haslam, & Barlow, 2013)、社會支配傾向(Carvacho et al., 2013)等, 未來可結合不同的操作性定義對此問題進行更豐富的探討。最后, 本研究更多的是借鑒了系統合理化理論中最新提出的認知途徑解釋, 重點考慮了貧富歸因的中介作用, 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數據上來看, 都不能認為貧富歸因是階層預測系統合理化這一效應中唯一起作用的機制, 正如Kay和Jost (2014)所說, 這一過程可能很復雜, 未來還可從更多其他心理因素入手, 更細致地探索不同階層形成系統合理化的根源。
5 結論
第一, 個體的社會階層對其系統合理化水平具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
第二, 對貧富分化做出內歸因解釋是社會階層預測系統合理化的中介變量, 社會階層越低, 就會越少地對貧富分化做內歸因解釋; 而這種內歸因越少, 其系統合理化也越弱。
第三, 社會階層—貧富歸因—系統合理化的中介關系, 受到了控制感的調節, 在低控制感的情況下, 該中介模型成立, 高低階層的貧富內歸因傾向差異顯著; 而在高控制感的情況下, 中介模型不成立, 高低階層貧富內歸因傾向無顯著差異。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Health Psychology,19
, 586–592.Arbour, K. P., & Martin Ginis, K. A. (2009).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on women's walking behaviour.Psychology & Health, 24
,49–65.Becker, T. E., Atinc, G., Breaugh, J. A., Carlson, K. D., Edwards, J.R., & Spector, P. E. (2016). Statistical control in correlational studies: 10 essential recomme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er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7
, 157–167.Bernerth, J. B., & Aguinis, H. (2016). A critical review and best-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rol variable usage.Personnel Psychology, 69
, 229–283.Brandt, M. J. (2013a).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04
, 765–785.Brandt, M. J. (2013b). Low status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business: A reanalysis of Brandt (2013). Available at SSRN 2275189.
Carvacho, H., Zick, A., Haye, A., González, R., Manzi, J.,Kocik, C., & Bertl, M. (2013).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rejudice: The roles of education, income,and ideological attitude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 272–285.Cichocka, A., & Jost, J. T. (2014). Stripped of illusions? Exploring system justification processes in capitalist and post-Communist societ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
, 6–29.Davidai, S., & Gilovich, T. (2015). Building a more mobile America—one income quintile at a time.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 60–71.Dubois, D., Rucker, D. D., & Galinsky, A. D. (2015). Social class, power, and selfishness: When and why upper and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behave unethicall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
, 436–449.Friesen, J. P., Kay, A. C., Eibach, R. P., & Galinsky, A. D.(2014). Seeking structure in social organization: Compensatory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vantages of hierarch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
, 590–609.Grossmann, I., & Varnum, M. E. W. (2011). Social class,culture, and cognition.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
, 81–89.Harris, P. R., Mayle, K., Mabbott, L., & Napper, L. (2007).Self-affirmation reduces smokers' defensiveness to graphic on-pack cigarette warning labels.Health Psychology, 26
,437–446.Hayes, A. F. (2013).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Hu, X. Y., Li, J., Lu, X. Z., & Guo, Y. Y. (2014).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7
, 1509–1517.[胡小勇, 李靜, 蘆學璋, 郭永玉. (2014). 社會階層的心理學研究: 社會認知視角.心理科學, 37
, 1509–1517.]Hussak, L. J., & Cimpian, A. (2015). An early-emerging explanatory heuristic promote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
, 739–752.Jetten, J., Haslam, S. A., & Barlow, F. K. (2013). Bringing back the system: One reason why conservatives are happier than liberals is that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gives them access to more group memberships.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4
, 6–13.Jost, J. T., & Banaji, M. R.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 1–27.Jost, J. T., Banaji, M. R., & Nosek, B. A. (2004). A decad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ccumulated evidence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olstering of the status quo.Political Psychology, 25
, 881–919.Jost, J. T., Hawkins, C. B., Nosek, B. A., Hennes, E. P., Stern,C., Gosling, S. D., & Graham, J. (2014). Belief in a just God (and a just society): A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pective on religious ideology.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4
, 56–81.Jost, J. T., & Hunyady, O. (2005).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 260–265.Jost, J. T., Pelham, B. W., Sheldon, O., & Sullivan, B. (2003).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sonance on behalf of the system: Evidence of enhanced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e disadvantaged.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 13–36.Kay, A. C., Gaucher, D., Napier, J. L., Callan, M. J., & Laurin,K. (2008).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 18–35.Kay, A. C., & Jost, J. T. (2003). Complementary justice:Effects of "poor but happy" and "poor but honest"stereotype exemplars o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implicit activation of the justice motiv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 823–837.Kay, A. C., & Jost, J. T. (2014).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motivational sci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s one of many“autonomous motivational structure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7
, 146–147.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4). Noblesse oblige?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maintenance among politicians.PLoS One, 9
, e85293.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 992–1004.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11). Social class as culture: The convergence of resources and rank in the social realm.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 246–250.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 546–572.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
, 642–656.Kraus, M. W., & Tan, J. J. X. (2015). Americans overestimate social class mobili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 101–111.Kraus, M. W., Tan, J. J. X., & Tannenbaum, M. B. (2013).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Psychological Inquiry, 24
, 81–96.Lachman, M. E., & Weaver, S. L. (1998).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4
, 763–773.Lee, I. C., Pratto, F., & Johnson, B. T. (2011). Intergroup consensus/disagreement in support of group based hierarchy:An examination of socio-structural and psycho- cultural Factor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 1029–1064.Li, C. L. (2014).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mong the post-80s generation: With comments on “The Silent Revolentio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4), 66–77.[李春玲. (2014). “80后”的教育經歷與機會不平等——兼評《無聲的革命》.中國社會科學,
(4), 66–77.]Li, J. (2014).Study on the tendency of attribution 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different social strara
.Guangzhou, China: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李靜. (2014).不同社會階層對貧富差距的心理歸因研究
.廣州: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Lu, X. Y. (Ed.). (2002).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lass research report
.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陸學藝 (Ed.). (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McCoy, S. K., Wellman, J. D., Cosley, B., Saslow, L., & Epel,E. (2013). Is the belief in meritocracy palliative for members of low status groups? Evidence for a benefit for self-esteem and physical health via perceived control.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 307–318.Na, J., & Chan, M. Y. (2016).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lower social-class enhances response inhibit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0
, 242–246.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3
, 435–454.Shepherd, S., Kay, A. C., Landau, M. J., & Keefer, L. A. (2011).Evidence for the specificity of control motivations in worldview defense: Distinguishing compensatory control from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nd terror management process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7
(5), 949–958.Skinner, E. A. (1996). A guide to constructs of control.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 549– 570.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Markus, H. R., Johnson, C. S.,& Covarrubias, R. (2012). Unseen disadvantage: 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ce undermin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 1178–1197.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Phillips, L. T. (2014). Social class culture cycles: How three gateway contexts shape selves and fuel inequalit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65
, 611–634.Tan, J. J. X., & Kraus, M. W. (2015). Lay theories about social class buffer lower-class individuals against poor self-rated health and negative affec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
, 446–461.Turiano, N. A., Chapman, B. P., Agrigoroaei, S., Infurna, F. J.,& Lachman, M. (2014). Perceived control reduces mortality risk at low, not high, education levels.Health Psychology,33
, 883–890.van der Toorn, J., Feinberg, M., Jost, J. T., Kay, A. C., Tyler, T.R., Willer, R., & Wilmuth, C. (2015). 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fosters system justif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 hierarchy, and government.Political Psychology,36
, 93–110.Wen, Z. L., & Ye, B. J. (2014a).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 731–745.[溫忠麟, 葉寶娟. (2014a). 中介效應分析: 方法和模型發展.心理科學進展, 22
, 731–745.]Wen, Z. L., & Ye, B. J. (2014b). Different methods for testing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s: Competitors or backups?.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6
, 714–726.[溫忠麟, 葉寶娟. (2014b).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方法: 競爭還是替補?.心理學報, 46
, 714–726.]Whyte, M. K., & Han, C. P. (2008).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
, 29–51.Yang, S. L., Guo, Y. Y., & Li, J. (2013). Whether lower social class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the social system to be justified.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 2245–2255.[楊沈龍, 郭永玉, 李靜. (2013). 低社會階層者是否更相信系統公正.心理科學進展, 21
, 2245–2255.]Yu, X, L. (2014). Can education still promote the social mobility.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5
, 9–15.[余秀蘭. (2014). 教育還能促進底層的升遷性社會流動嗎.高等教育研究, 35
, 9–15.]Yue, C. J., & Zhang, K. (2014). Research on job-hunting result and starting salary of college graduate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Educational Research, 35
, 72–83.[岳昌君, 張愷. (2014). 高校畢業生求職結果及起薪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2013年全國高校抽樣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教育研究, 35
, 72–83.]Chiu, C-y., Au, E. W-M., & Chen, J. (2008). How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ety, culture and thought? The contributions of shared implicit theories.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
, 147–170.[趙志裕, 區穎敏, 陳靜. (2008). 如何研究社會、文化和思想行為間的關系?——共享內隱論在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貢獻.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 4
, 147–170.]Zhou, H., & Long, L. R. (2004). Statistical remedies for common method biase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 942–950.[周浩, 龍立榮.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統計檢驗與控制方法.心理科學進展, 12
, 942–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