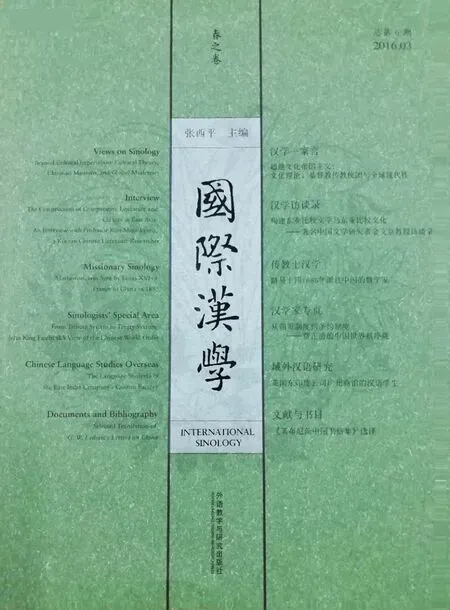超越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理論、基督教傳教使團與全球現代性*
史 凱 譯
譯者按:中國基督教研究是歐美學術界持續關注的所在,21世紀以來,海外學者陸續提出中國基督教研究中的范式轉移問題,本文即是其中一篇代表性論述。原文刊發于2002年10月《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41期,第301—325頁。作者唐日安(Ryan Dunch),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歷史與古典系教授,東亞研究系主任,著有《福州新教徒與現代中國的形成》(Fuzhou Protestant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1857—1927],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唐日安在這篇長文中敏銳地指出文化帝國主義視角內在的邏輯悖論和學理缺陷。作者以來華傳教士研究為例,詳述如何基于跨文化接觸的具體過程,通過轉換焦點,把民族性、現代性和歷史性相結合,從而更加透徹地理解人類文化的交融與碰撞。全文論證縝密,被歐美學者引用頻次破百,在西方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譯者不揣淺陋,譯出全文,舛誤之處,敬請讀者批評賜教。
“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用途寬泛的奇妙詞語。它首見于20世紀70年代的學術批評話語,針對美國媒體在拉丁美洲的影響而言;事實上,它也一直以媒體研究為基本參照系,主要指向全球范圍內美國娛樂產品和文化形象的統治地位。①Emile G.McAnany and Kenton T.Wilkinson, “From Cultural Imperialists to Takeover Victims? Questions on Hollywood’s Buyouts from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 No.6 (1992), pp.724-748.它還被諸多領域的學術論文和通俗讀物使用,涵蓋歷史事件和當下議題。例如,近年來人們頻頻使用“文化帝國主義”解釋(并抨擊)西方數學的普世結論(西方數學是殖民地時期帝國霸權“強加于人”的文化帝國主義的“秘密武器”,它蠱惑人心,破壞本土的概念系統);英語通行全球的語言現象;從社會性的角度將身體“殘障”定義為偏離“正常”的人體屬性(“體格健全論”的文化帝國主義);臨床醫學上把永久性意識喪失(“腦死亡”)等同于死亡;20世紀50年代英國人熱捧“貓王”(Elvis Presley,1935—1977)和他的美國伙伴,以及足球和板球各自在巴西和印度盛行不衰。②Alan J.Bishop, “Western Mathematics: The Secret Weapon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Race and Class 32, no.2 (1990), pp.51-65; Lennard J.Davis, “J’accuse! Cultural Imperialism—Ableist Style,” Social Alternatives 18, No.1 (1999), pp.36-40; Nicholas Tonti-Filippini, “Revising Brain Death: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 Linacre Quarterly (1998), 內容概要參見 Issues in Law and Medicine 14, No.2 (1998), pp.225-226; Laura E.Cooper and B.Lee Cooper, “The Pendulum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Popular Music Inter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943—1967,”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7, No.3 (1993), pp.61-78;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上述案例的背后大多存在同一個看似合乎情理的驅動力—批判某種形式的文化霸權。然而,批判的沖動并不必然構成說服力。本文的焦點不在“文化帝國主義”何以應用于特定領域,作者更為關心的是,作為一種解讀文化影響的分析工具,尤其在切入近代史上的傳教士活動時,“文化帝國主義”呈現出哪些優勢與不足。作者把“文化帝國主義”視為一種觀念模型而非“現實”,通過考察其效用(utility)厘清它所彰顯的亮點和遮蔽的問題。①“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說存在類似的問題,有關論述詳見Timothy Brook and B.Michael Frolic, “The Ambiguous Challenge of Civil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ed.Timothy Brook and B.Michael Frolic.Armonk, N.Y.: M.E.Sharpe,1997, p.8.就此而論,本文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概念受困于兩大主要缺陷:第一,它未能跳出民族和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本質論話語;第二,它把復雜的文化影響過程簡化為施動者與受動者的二元對立,還剝奪了后者的能動性(agency)。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將考察“文化帝國主義”和類似術語怎樣描繪19—20世紀的基督教傳教士,中國的個案尤其值得參考。本文結語部分初步構設“文化帝國主義”的替代模型,以期助推人們深入理解傳教士的歷史角色。
一、“文化帝國主義”及其問題
鮮有學者精準界定何為文化帝國主義。多數情況下,學術界使用這個術語時遵循的暗合之意是:某些文化產品(例如社會廣泛接受的看法、觀念和娛樂產品)通過強制手段—往往表現為利用自身與政治經濟權力之間的聯系—在其他文化中占據統治性地位。由是觀之,其核心在于對另一種文化產生的影響和該過程的強制性。
以“文化帝國主義”為題旨的學術討論首先包含著這樣一個前提,即認同過往幾十年來成型的知識與權力關系的觀點。接受那一套觀點,就把文化帝國主義與后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聯系在一起(盡管早在后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引發論戰之前,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即已出現)。眾所周知,此派陣營的里程碑,正是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的那部《東方主義》(Orientalism)。追溯該書強大影響力的源頭,乃是薩義德把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等學者的洞見套用于一個相對具體和普遍的現象。薩義德稱,19世紀的學者和小說家苦心追求的所謂抽象和非政治化的知識,實際上與殖民權力的擴張存在共謀關系。他說,他們生產的關于“東方”的作品構成一套話語,把不同的非西方社會雜糅一起,并貼上一組負面屬性的標簽,與“西方”的正向特質截然對立。這套話語建構“自我”與“他者”,使西方對“東方”的政治統治顯得理所應當,注定如此。②Edward W.Said, Orientalism.New York: Pantheon, 1978.
薩義德的大作贏得廣泛影響實在情理之中,它尤其有助于破解現代知識體系的“中立性”(neutrality)。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堅稱西醫“正確”,本土傳統療法“錯誤”;斷然否認西方數學是特定文化產物的聲音也日趨式微。總體說來,我們必須承認西方文化產品的影響遍及全球,這種影響通過強制性的歷史進程發生(此處暫不討論強制進程的行為主體)。顯而易見的還有,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轉變,不僅涉及政治關系、工業生產和經濟貿易的全球化,也包括文化產品、民族國家、理性主義與科學、政治世俗主義、憲政國家、大眾教育(突出某些教育形式和科目)在全球范圍的擴張與蔓延,它們無不與權力統治結構,特別是殖民主義緊密相連。
與此同時,批評者指出,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文化帝國主義”存在若干問題,這些問題沖擊著它的基本效用。
最不客氣的聲音說,文化帝國主義的論點缺乏基本說服力,不過是用一種不成熟的文化決定論替換知識系統和文化產品的“中立性迷思”(myth of cultural neutrality)。這種文化決定論主張,文化產品“攜帶”著內在價值觀,它們被“強加”給面目麻木、消極被動的目標受眾。有人就曾這樣評價西方數學知識:“西方數學映射著非人化、客體化和意識形態化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必然通過殖民地的舊式數學教育得以顯現。”③Bishop, op.cit., p.58.(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諸如此類的表述通過使用被動語態(“教育本地民眾并幫助他們適應歐洲主導的世界結構,其必要性已得到重視”),或者想當然地把動機歸結為抽象因素(“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包藏兩大禍心,一為經濟,一為政治……”),往往遮蔽了歷史能動性的問題—換言之,由誰、如何、向誰傳遞所謂的價值觀。①Ibid.,p.55;James Petras,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3, No.2 (1993), pp.139-148; 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4-108.E.Richard Brown 就以這種決定論思維牽強附會地分析一通中國,參見E.Richard Brown, “Rockefeller Medicine in China: Profess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 Found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ed.Robert F.Arnove.Boston: G.K.Hall, 1980.
當然,批評者并不諱言,確定文化產品的受眾反應與意見絕非易事,并且它不可與分析文化產品本身混為一談。②Tomlinson, op.cit., pp.51-64; McAnany and Wilkinson, op.cit..仍以數學為例,即是說,探討數學作為一種認知系統所具備的屬性,并不能幫助我們看清公式另一端的接受方:殖民地學校體系里的學習者怎樣理解、闡釋、重建、使用,甚至排斥西方數學知識。再如,后殖民研究者已經意識到,剖析“殖民話語”(殖民者社會有關被殖民對象的敘事話語,薩義德的著述堪稱此研究領域的先鋒之作)與探究被殖民對象自身的文化體驗是兩個不同的命題。③例如,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17.因此,必須指出,縱使西方社會的“他者”形象研究如何豐富,也不能完全揭示“他者”社會的成員個體面向歐洲社會時的遭遇和經歷。我們甚至不可以想當然地斷言,殖民者社會的海外代理人在其所在國與“他者”進行日常接觸時,秉承著殖民話語描述的立場。
不少被劃入“文化帝國主義”之列的現象實則表征著市場的力量,由此引出了文化商品的市場需求,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卻常常被那些不夠嚴謹細致的討論忽視。有人認為,市場對文化產品(通常是美國的文化產品)的需求充分證明文化帝國主義引導著全球趣味,協助美國企業漁利。同質化的社會興趣與強制性的作用力再一次被概括為“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至于接收一方,則被視為極少甚至根本不具任何能動性。持此論調的著述尤其喜歡用年輕人的時尚潮流作證。按照他們的說法,青年人“對消費主義—個人主義(consumerist-individualist)的宣傳攻勢毫無免疫力”可言。④Petras, op.cit., p.139.的確,世界各國的年輕人都喜歡穿耐克鞋,聽邁克爾·杰克遜(Michael Jackson,1958—2009)的音樂,然而如何評論這一現象卻并不簡單。有人把全球消費美國的文化產品解讀為大眾沉醉于新型的麻醉劑中不能自拔,認為它標志著一個以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為特征的同質化的世界文化正在興起,這個過程受到西方傳媒公司全程操控,后者不斷破壞階級團結,削弱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斗志。⑤例如上引書。反對這一觀點的人則試圖證明美國發生的口號和形象其實并無固定意義,無論從文化視角抑或階級立場看待,它們都只是漂移的符號,在新的條件下不斷重新組合、再度語境化。“美國符號是全球視覺通用語的源頭,但它們的意義和用法早已突破美國本土。”一位研究青年時尚的當代歐洲學者如是說。⑥Rob Kroes, “American Empir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A View from the Receiving End,” Diplomatic History 23, No.3 (1999),pp.500-521; 另見 Francis X.Rocca, “America’s Multicultural Imperialism,” American Spectator 33, No.7 (2000), pp.34-38.他尖銳地指出,歐洲人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抨擊其實夾帶著精英文化對流行文化的傲慢心態。于是,原本痛斥本國青年追捧美國明星麥當娜(Madonna Ciccone)的法國人,一旦看到年輕人推崇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或者巴爾托克(Bartok Bela,1881—1945)即刻喜笑顏開,盡管后者同樣是外來文化的代表。
考察“文化帝國主義”如何解釋兩段不同時期的歷史,即帝國主義時代的基督教傳教士活動和二戰后北美與西歐富庶的工業國家間的文化交流,我們看到更多的問題。“文化帝國主義”把不同類型的“權力”雜糅在一起:披頭士樂隊興起前美國流行音樂在英國文化市場的“權力”;20世紀90年代美國商標在歐洲的“權力”;二戰前帝國主義國家在殖民地或者權治虛弱的中國等地所擁有的更加直接和壓迫性的“權力”。20世紀50年代美國流行音樂果真奴役(colonize)了歐洲人的潛意識嗎?倘若事實如此,我們該如何比較這種文化變異與殖民地時期非洲部族遭遇的文化變異?①Cooper and Cooper, op.cit..由是觀之,我們或許不得不說,一個可以浮泛地套用于各種語境的概念,其效用大概極為有限。
一些討論已經指出定義的困境。“文化帝國主義”把“文化”和“帝國主義”兩個詞語捆綁在一起,界定任何一方都是公認的棘手難題。②Andrew N.Porter,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y Enterprise, 1780—1914”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5, No.3(1997): 367-391; Tomlinson, op.cit., pp.2-8; Guttmann, op.cit., chap.9.不少嘗試性或隱晦的定義,例如我在本節開始給出的松散解釋,往往引出更多的問題。比如,如何判定“文化的統治地位”(cultural dominance)?定義之難還涉及文化和國家的本質論。如若把文化帝國主義解釋為外來文化的統治,言外之意即是存在一個可以回溯的文化原點,它不受內部沖突的影響,若非遭遇外來作用絕無變化的可能。這一論調的荒謬之處顯而易見。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又譯“庶民研究”。—譯者注)學者早有共識:我們根本無法還原(retrieve)前殖民時代“真實”的文化聲音。③參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專文 “Can the Subaltern Speak?”,載 Williams and Chrisman, op.cit., pp.66-111.此文影響甚大。遺憾的是,大量的討論依舊嵌置著謬論,尤以借民族主義之名批判外來文化時最為明顯。那些批判者恰恰忽視了一點:現代民族國家的身份本身就包含著建構和霸權的屬性。④后殖民研究學者已經認識到,以先天論和/或民族主義為工具批判殖民話語,潛藏著本質主義的危險傾向。參見Williams and Chrisman, op.cit., pp.15-16, 23.民族主義研究的新近成果已經揭示,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s)的合法性建立在這樣一種論調上:聲稱代表“真實的”民族群體和文化、根本有別于“外來的”和區域性的以及其他次民族(sub-national)的元素。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各式論著其實都充斥著民族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巧言令色,它們一遍又一遍地強化著民族國家的概念。⑤Prasenjit Duara, “Response to Philip Huang’s ‘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26, No.1(2000), p.36; Tomlinson, op.cit., chap.3.
立場的矛盾是文化帝國主義概念的又一塊短板:如何能找到一個立足點,既從認識論上識別文化帝國主義,又對其進行道德批判。批評者指責薩義德無法自圓其說。這一意見的代表人物當屬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1925—1995)。蓋爾納生前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撰文批判薩義德,論點之一是薩義德的道德評判純屬無緣之木。他這樣寫道:“薩義德輕巧地擺好姿態,發表一通道德評判,教育我們該怎么想,卻絕口不談自己的立場何以能夠成立。”⑥Ernest Gellner, “The Mightier Pen? Edward Said and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Inside-Out Colonialis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690 (February 19, 1993), p.3.盡管薩義德及其擁護者矢口否認蓋爾納的指責,但后殖民研究領域內的學者已經注意到其中的問題。如果話語在建構和分類對象的過程中無不對應著權力關系,如果前殖民的“本真”(authenticity)不過是幻象,我們焉敢輕言后殖民研究話語的正當性?一家重要的后殖民研究期刊的編輯就曾借致謝之際吐露心聲:他們“希望”那些已經認識到“權力和知識之間互蘊關系”的學者日后生產出“不一樣的知識,更好的知識……以實際行動回應薩義德的核心命題—‘我們怎樣了解并尊重他者’”。⑦Williams and Chrisman, op.cit.,p.8; 另見 Santiago Castro-Gómez, “Latin American Postcolonial Theories,” Peace Review 10,No.1 (1998), pp.27-33.可惜這般謙遜的姿態較之大量粗糙炮制的論著著實鮮見。在后者那里,“更好的知識”就等同于“進步”知識分子群體口中的解放性(emancipatory)知識,與所謂強制性(repressive)知識相對。依照某些人的說法,當今批評界的主要代表—“雷蒙德·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愛德華·薩義德、貝爾·胡克斯 (Bell Hooks)、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等人士”—他們的著作被奉為新一代正典,還有人不假思索信口開河,稱這些人是“全天下的進步人士”。①Davis, op.cit., p.36.我們不禁想起上一版的大師名單:毛澤東、切·格瓦拉(Che)、卡斯特羅(Fidel Castro)、胡志明—盡管舊版名單同樣有自說自話之嫌,至少看上去更具國際性!
“文化帝國主義”的最后一個問題來自文章開篇所列的那些五花八門的用法。我們已經指出,它們背后的邏輯是:人們之所以接受外來文化蓋因強制力所賜。言下之意文化乃意識形態主宰的場域。依據本模式,文化變遷系外力作用所致。假定“正常”人體的標準、青年時尚的含義和死亡的臨床認定三者都是文化帝國主義的產物,它們所構成的觀念的三角形里,每一個內角無疑都是權力的一次操練,每一例觀念的變化顯然都是強權的勝利—無論文化內外。那么,強制力的終點在何處?每個人都棲居于文化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伴生的文化產品,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已然被“殖民化”?我們承認(我本人深信不疑)抽象的社會力量,如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以及/或者現代性(modernity)深刻地重構了人類的主觀經驗,然而把重構簡化為強制外力的獨舞,個體只能消極順從,卻是典型的決定論式的社會觀。進一步講,把文化變遷解釋為外界強制力的結果終將把我們的跨文化研究帶向這樣一種近代史觀:西方主宰著全球文化的決定性影響,現代性就等同于西方化。②Nicos Mouzelis探討了其中的謬誤,參見“Modernity: A Non-Eurocentric Conceptual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No.1 (1999), pp.141-159.亦可參見Theodore H.von Laue的個案分析: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lobal Perspectiv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如此一來,原為反對文化霸權而生的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話語,卻因為無視非西方世界的能動性和自主性而催生出一個十足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結論,真可謂滑天下之大稽。
二、基督教傳教活動、本土代理人與觀念的殖民化
有一個群體頻頻被用于證明近代歷史上文化帝國主義的淫威,那就是基督教傳教士。早在文化帝國主義的話語興起之前的幾十年里,傳教士是帝國主義幫兇的言論就已甚囂塵上,源頭大概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等地出現的民族主義批判。③我尚未發現民族主義者對傳教士帝國主義的批判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媒體研究領域的文化帝國主義討論之間有何直接關聯,也沒發現1949年之前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攻擊傳教團時明確使用過“文化帝國主義”這一術語。在當時以及后世的文學作品與學術著作里,傳教士是清一色的狹隘沙文主義者,他們的活動破壞本土文化,為殖民者打開侵略的大門。④近來備受關注的一部新作,Barbara Kingsolver所著The Poisonwood Bible: A Novel(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8 )即為典型代表。另一部多年前問世的小說也歸為此類,即Chinua Achebe所著Things Fall Apart (London: Heinemann, 1958),盡管后者對西非的伊博人(Igbo)與傳教士的相遇分析更為細致。但是,這種形象基調遮蔽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文化帝國主義是否適用于解讀傳教士對非西方社會的影響。⑤例如,Yunseong Kim, “Protestant Missions as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Early Modern Korea: Hegemony and its Discontents,”Korea Journal 39, No.4(1999), pp.205-234.
從文化帝國主義的角度理解基督教傳教活動,不但容易落入使用該術語的常見陷阱,而且制造了兩個新問題。第一,傳教士文化帝國主義的討論大多涵蓋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這一百年,即現代帝國主義時期。當我們談論更晚的當代話題時,文化帝國主義一般指向一個不直接涉及政治控制的文化統治的過程,但文化帝國主義與傳教士一經結合,人們就開始激辯傳教士與帝國主義政治和經濟勢力之間存在的直接關聯。即是說,傳教士文化帝國主義的討論對應著這樣一種帝國主義模型:帝國主義多方位的目的性活動表現在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政治、經濟和文化。研究者竭力尋找傳教士與政治帝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的直接關系,試圖證明傳教士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代理人。⑥例如,Lewis Pyenson在討論帝國主義和西方科學的關系時就把“文化帝國主義”解釋為與帝國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直接聯系。參見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the Exact Sciences.New York: Peter Lang, 1985, pp.312-316.還有的研究索性一口咬定傳教士就是帝國主義的共謀。日前問世的一本教科書便把傳教士(missionary)、商人(merchants)和軍人(military)并稱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制造的三座大山(three ‘M’s),他們“被宗教使命一般的沖動所驅動,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國傳播資本主義、基督教真理和國家武力構成的西方福音書”。①R.Keith Schoppa,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2, pp.45, 58-62.
這些觀點的缺陷顯而易見。從“文化帝國主義”切入不同領域的研究,核心命題原本是本土文化受到的影響。比起剖查傳教士對本土文化造成的沖擊,盯著傳教士與政府和商業利益之間的瓜葛不但學術價值有限,經驗主義色彩過濃,還偏離了文化帝國主義研究的焦點。雖然存在例外,但總體而言,差會和傳教士很難影響原籍國政府及其殖民地代理人的既定政策,與原籍國的商人和商業利益也沒有多少直接聯系。②參見科馬洛夫夫婦的細致論述,“Christianity and Colonialism in South Africa,” American Ethnologist 13 (1986), pp.1-22.事實上,傳教士的利益常與他們在政府部門和商業行當的同胞截然對立,傳教士、領事/殖民官員和商人之間的現實關系時冷時熱忽好忽壞。③中國基督教史提供了豐富的例證。例如,英國領事同意中國官員驅逐英國傳教士,前提條件是,中方準許英方修建賽馬場。參見Ellsworth C.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1974, pp.140, 163.澄清這一點并非替傳教士鳴冤叫屈,為他們洗白文化帝國主義的指控,但它提醒我們不要模糊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焦點:它絕不簡單地等同于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映射,而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沖擊。
這里有必要指出,把傳教士與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的人明顯受到一篇流傳廣泛的文章的影響,正是它拋出一個片面且含混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定義。文章問世于20世紀70年代。杰出的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回顧了主要的帝國主義理論模型和它們對傳教士的定位。他指出把傳教活動解釋為帝國主義政治和經濟利益使然不足以說明問題。史列辛格相信當時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等人探討帝國主義文化和心理影響的新作提供了解碼傳教士的鑰匙,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理論所不能及的。史列辛格的分析細致且有建設性,但是他把“文化帝國主義”解釋為“一種文化刻意侵犯另一種文化的思想和價值觀”,卻無疑犯了忽視受眾能動性和偏離焦點的錯誤:誰的“目的”?我們談論的是意圖還是后果?“侵犯”“思想和價值觀”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兩種文化是否真的像這個定義標稱的那樣迥然不同?④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ed.John K.Fairbank.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63.史列辛格的研究視角導致他提供的定義偏離有關影響的命題。而影響研究,如我所言,較之臆斷傳教士的行為動機或者“侵犯”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焦點,蘊含著更多的學術發現。⑤Paul W.Harris注意到史列辛格的觀點存在不足,他主張“拓寬武力和侵略的定義”,試圖以此提出一個更加妥當的“文化帝國主義”定義。參見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ollaboration and Dependenc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acif i c Historical Review 60, No.3(1991), pp.309-338, 313.
我們要反思的第二個問題是,評論傳教士文化帝國主義的言論眾口一詞:傳教士帶著居高臨下的種族主義的眼光俯視身邊的非基督徒群體。傳教士出版物和檔案似乎都在印證這一觀點的合理性。其實并非所有的傳教士都像萬為(Erastus Wentworth,1813—1886)那樣狹隘。這個1860年前后生活在福州的美以美會傳教士不堪忍受福州菜“粗鄙的準備工作”,眼巴巴地盼著蛋糕和咖啡。他甚至大放厥詞說“讓天朝的中國人信奉上帝,學著像基督徒那樣用刀叉吃飯比登天還難”⑥R.S.Maclay引用了傳教士萬為的私人書信,參見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New York: Carlton and Porter, 1861, p.278., 好在他不能代表全部的傳教士。很多傳教士的性格品質、神學思想、外部環境、適應能力以及至關重要的一點,中文水平,都在萬為之上,因此跨越文化障礙的表現遠遠強于后者。我們不難從教堂的中文史料中尋獲證據,它們記錄著傳教士如何以言行贏得當地搭檔的信任和尊重。我們不能否認,帝國時代的傳教士踏上宣教地區的土地時,堅信他們智力、道德和精神優越感的源泉不是“文化”(culture),而是獨有的“文明”(civilization)的象征。有人甚至認為自己的“種族”也優人一等,這像極了19世紀末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t)向西方文化滲透時的情狀。①Brian Stanley, The Bible and the Flag: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Leicester, Eng.: Apollos, 1990, chap.7.
傳教士的專斷作風自有其歷史喻義,卻并非因為它是赤裸裸的“文化帝國主義”。誠然,在傳教士恩賜姿態的另一端,是本地基督徒和教會學校學生的忍辱負重,這是理解基督教民族主義、獨立教會和本土教會運動何以興起的要點。②參見Daniel H.Bays,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Daniel H.Bay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essie G.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 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Notre Dame, Ind.: Cross-Cultural Publications, 1988; Susan Billington Harper, “Ironies of Indigenization: Some Cultural Repercussions of Mission in South India,”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9, No.1 (1995), pp.13-20; Lamin Sanneh, Translating the Messag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New York: Orbis, 1989, pp.167-172, 182-190.盡管如此,論及傳教士如何影響本土文化這一關鍵命題,糾結于傳教士的態度實則離題甚遠。遺憾的是,批判傳教士文化影響的論著,并不總能分清不同的概念,經常把傳教士改變所在國文化的意圖(intent)與其實際行為(actuality)混為一談。
類似的問題還存在于如何評價傳教士為原籍國讀者所作的出版物(比起用宣教對象國語言寫成的出版物更加通俗易懂)。人們常以它們為例證明傳教士傲慢、粗暴和東方主義的立場。這種邏輯忽視了文本產生的語境和目的,也沒有充分考慮文本與實際活動的關系(不要忘了,傳教士與薩義德筆下的東方主義者不一樣,前者浸淫于所在國文化數十載,常常因此被改變)。③試舉幾例:Stuart Creighton Miller, “Ends and Means: Missionary Justif i 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Fairbank,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249-282; James L.Hevia, “Leaving a Brand on China: Missionar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Movement,” Modern China 18, No.3, 1992, pp.304-332.頗具反諷意味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福音派”(social gospel)傳教士,自認為比前人更加同情宣教對象國,但其神學思想又意欲掀起全面的社會變革。較之早前神學保守的同行,他們表現出更強的文化侵略性。畢竟,前者至少努力把傳揚福音和政治文化訴求區分開來。
批評者著重指出“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剝奪了受眾在文化變遷過程中的能動力。有人辯解說,“帝國主義”文化的消費者就扮演了主動角色,他們可以抗拒、選擇甚至重塑自己吸收的文化產品,前文所舉的媒體和青年文化兩例就是證據。關注非西方世界基督教的近作也開始有意凸顯本土能動性,把傳教活動的研究焦點從作為帝國宗主文化參與者的傳教士轉移到遭遇基督教的本土一方。④Norman Etherington, “Missions and Empire,”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ed.Robin Winks, Vol.5,Historiograph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09ff.; Andrew F.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Edinburgh: T&T Clark, 1996; J.D.Y.Peel, “For Who Hath Despised the Day of Small Things? Missionary Narratives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 No.3, 1995, pp.581-607; Harper, op.cit..稍顯滑稽的是,傳教史研究正沿著底層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軌跡發展,追蹤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移植過程中經歷的落差、抗拒、混雜和選擇。⑤Piers M.Larson將底層研究的成果移用于研究傳教團和本地教友,參見“‘Capacities and Modes of Thinking’: Intellectual Engagements and Subaltern Hegemony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gasy Christia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No.4,1997, pp.968-1002.
盡管如此,正視非西方社會的基督徒在這場遭遇中所呈現的能動性,似乎無法從根本上彌補文化帝國主義的先天缺陷。美國學者科馬洛夫夫婦(Jean & John Comaroff)長期關注茨瓦納人與英國基督教傳教士(衛斯理宗和公理宗)的交流(19世紀20年代以來),成就不俗。他們認為,即使文化參照系發生不可逆轉的重構,本土受眾的能動性也不會消失。他們批評前人的研究忽視了這個維度。因此自己特別注意考察茨瓦納人的能動角色,以此辨證地分析傳教士與茨瓦納人的接觸。①Comaroff and Comaroff, op.cit., pp.1-2; Jean Comaroff and John Comaroff,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6-11.不過他們也承認,就算拒絕接受傳教士的宣教信息,茨瓦納人也不可能徹底斷絕與傳教士的關系。那些“漫長的交往”改變了茨瓦納人對自我、文化、語言、工作、土地、時間等生活要素的認識。二人尤其重視前人忽略的兩個維度,即符號的運用和日常世俗行為對殖民地文化的重塑作用。通過分析茨瓦納人的生活元素,包括祈雨口號、耕作農具、服裝和建筑的式樣功能、計時方法、書面語言等等,他們得出結論“傳教團把塔石第人(Tshidi)帶入一場必須直面的對話”。他們相信(其理論基礎是采用還原論式的描述,將衛斯理宗解讀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這場對話“為茨瓦納人注入理性個人主義世界里的公民色彩……在那個世界里,個人進步所收獲的回報是福祉增加,德行提升”。這場對話其實是一次觀念的變遷之旅,終將沿著資本主義社會殖民秩序的軌道把茨瓦納人和其他非洲黑人帶往無產階級化。②Comaroff and Comaroff, “Christianity and Colonialism,” pp.15-16; idem,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John and Jean Comaroff, Ethnography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58-260.塔石第人是茨瓦納人的一個亞群。
科馬洛夫夫婦稱該過程為“觀念的殖民化”,以此響應以法農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義批判者。但他們并未將觀念的殖民化視為對原生文化粗暴的露天采掘,毫不擔憂殖民地人民文化殘缺、心性腐化等后果,這一點完全不同于法農,也有別于近年人們在還原主義語境下賦予“觀念的殖民化”一詞的新意。③有關殖民化的心理研究和批判,參見Williams and Chrisman, op.cit., Part One.科馬洛夫的觀點暗含著這樣一層含義:文化之間如同相互撞擊的臺球,上演著占位和取代。換言之,殖民主義的后果不是文化變質或者文化雜糅,而是某種文化的退場。④Achebe的小說Things Fall Apart試圖傳達這一訊息。Achebe否認小說意在揭露英國人破壞伊博人文化。他強調外來的巨大沖擊并不會遏制文化的流動性和適應性,這也是其續作No Longer At Ease (London: Heinemann, 1960)的中心思想。參見Conversations with Chinua Achebe, ed.Bernth Lindfors.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7, pp.66-67, 118.科馬洛夫伉儷富于洞見,敏于察思,充分考慮了被殖民者遭遇殖民勢力時的能動角色。他們還表示,傳教士并非直接的政治意義上的殖民代理人。因為在傳教士的神學思想里,宗教和政治相互分離,他們的政治角色“實屬模糊”。⑤Comaroff and Comaroff, “Christianity and Colonialism,” p.17.而且,在夫婦二人看來,殖民化的基本載體乃是“日常行為”而非政治權力—“把文化帝國主義的種子播撒在日常生活的田壟里方能實現大豐收”。以此而論,所謂殖民化,其精髓與實質其實是“自視歐洲文明信使的基督教傳教士發起觀念體系的大舉進攻”。⑥Comaroff and Comaroff,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pp.293, 258.
科馬洛夫夫婦的研究深刻獨到,“觀念的殖民化”簡潔有力,然而究其本質,他們乃是以另一種方式提出如何理解現代文化的命題。他們記錄的那些變化并非茨瓦納人獨有的經歷。時鐘計時法、私人財產概念、個體勞動、財富積累(無論在農場莊園還是在工廠礦山)、建筑和住宅內飾的形式、理性、人體醫學知識、民族國家、經濟發展、讀寫能力等等,都意味著全新的世界秩序,它們規定著西方社會的現代性體驗,正如它們影響了茨瓦納人一樣。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霸權是它的特征,即是說,這個世界秩序一方面展示出強權和精心統治,另一方面又被置身其中的人擁抱、批駁甚至顛覆。⑦Guttmann特別區分了強制(imposition)與霸權(hegemony)。參見Games and Empires, Introduction.說到傳教士、傳教活動的歷史頗似世俗理性主義(secular rationalism)的發展。為了奪取國家空間里的話語權,后者把宗教打入人類社會演變進程中的舊事物之列。類似地,傳教活動(以及傳教士關于基督教文明和“異端”社會的話語)也可以被理解為基督徒為了保持在原籍國的文化優勢所作的努力。這里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都被殖民化了嗎?換言之,我再次提請讀者注意,我們正在探討某些抽象概念作為思考工具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明辨“觀念的殖民化”是否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杠桿,是否有助于我們理解現代性帶來的文化變遷。.
我們不妨換一種更加清晰直白的表達:不應把傳教士與非西方社會的相遇以及這些社會經歷的殖民變化當作自成一格的孤立事件,它們從屬于更高層面內19世紀、20世紀的全球變化。研究的難點在于選擇準確的語言充分描述概念世界所發生的復雜、多維和整體性的變化。從什么到什么?變化是否僅僅意味著壓迫和征服?比如說,現代非洲的混合型社會形態果真如一些學者所言僅僅張揚著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調教”的勝利嗎?①G.K.Kieh Jr., “The Roots of Western Inf l uence in Africa: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ing Proces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9,No.1, 1992, pp.7-19.如是解讀折射出怎樣的邏輯?我們絕非意欲粉飾殖民主義的剝削、虛偽和殘忍,更不敢大放厥詞,謬稱既然一切統治權都是強制性的,殖民地國家遭受的強制力在類型和程度上都與現代國家和現代話語并無二致。我們也不難預想,自己的主張可能觸發棘手的論爭:何謂現代性?怎樣確定一個本質上非資本主義、非歐洲中心主義和非宗教神學的現代性定義?盡管如此,我們相信本文倡導的基本觀點將有助于推動人們在更加開闊的語境下認識文化帝國主義和/或觀念的殖民化。②有關現代性與文化帝國主義的討論,參見Tomlinson, op.cit., chap.5;有關現代性的一般性討論,參見Williams and Chrisman, op.cit., p.130, 181-189.(節選自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 Eng.: Polity Press,1990.)
三、傳教團、觀念與中國的現代性
我們把目光集中于傳教團與中國的現代性這一個案為我們提供了積極的啟示。當然,19世紀的中國是個龐大的官僚國家,與茨瓦納社會大為不同。科馬洛夫夫婦把諸多元素歸入傳教士帶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性—犁、讀寫能力、貨幣、私產、遠距離商業活動、家庭財富、通過正規教育實現個人成就的迷思、稅收、協議勞動、城市生活—它們其實早已出現在中國大地。不僅如此,雖然中國實實在在地遭受到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沖擊,卻從未淪為殖民地。此外,盡管英國傳教士在面向茨瓦納人的現代性傳遞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根據科馬洛夫的觀點),在華傳教士群體的影響(更為多樣的影響)卻離不開其他渠道—商業行為、出版活動、官場交往、中日接觸—正是經由它們,外來思想和制度才得以向天朝帝國滲透。
從《平凡的世界》看路遙創作史詩性追求的得失 ………………………………………………… 張文哲(1.68)
盡管如此,中國社會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經歷的巨變絲毫不亞于茨瓦納社會。傳統的歷史著述多稱這些變化為“傳統”向“現代”的過渡,其中西方的沖擊和影響,無論好壞,起到決定性作用。人們對近代在華基督教傳教團的評價就投射著這種看法。20世紀前50年,傳教士及其支持者的著述聲稱傳教團“功不可沒”,它們驚醒了一個渾渾噩噩的中國,把它拉進現代世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相反的情形:1919年之后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傳入中國,受此影響,20世紀20年代起民族主義者以帝國主義或“文化侵略”的罪名痛批傳教士,斥責宣教活動和教會教育麻痹中國人、充當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統治的幫兇。③如前所述,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者批判傳教士活動時使用了文化帝國主義的邏輯,但當時尚未出現文化帝國主義這一措辭。他們用類似的表達,如“文化入侵” “精神侵略”,把傳教士和“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更多例證參見朱有瓛、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武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705—712、742—761頁。對這一時期的詳盡分析,另見Lutz, op.cit..其他社會在批判基督教傳教團時(例如,印度甘地的觀點),大多把歸化受眾的目標與“造福民眾”的教育和醫療貢獻,中國人卻一直將傳教士的教育和醫療工作劃入隱性侵略之列。中國人普遍認為,利他主義的表象恰恰說明欺騙的隱蔽和高明。④有關甘地的觀點,參見Schlesinger, op.cit., pp.366-367.毛澤東就曾在1949年用其直言不諱的風格表達了這種觀點。他單獨挑出美國,一個對中國的政治侵略不及日本和歐洲國家,寫道:“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①毛澤東:《“友誼”,還是侵略?》,見《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年,第448頁。
雖然傳教士推動“提升中國”的說法與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傳教士帝國主義的批判針鋒相對,二者卻反映出相同的參照框架:現代主義的世界歷史敘事。在這種敘事下中國是一個統一的歷史整體,它需要經過政治、經濟、技術和社會的“發展”,從過去“解放”出來,在民族國家的世界新秩序中占據一席之地。②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35, 1996, pp.96-118;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兩派陣營的另一點共識是,傳教活動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無論好壞都是深遠的。所以,盡管早前中國人攻擊傳教士的目的在于維持晚清帝國的現狀,到了20世紀20年代民族主義者批判傳教士帝國主義的行為,則在本質上與傳教士和中國教友一樣,體現著觀念的現代轉變。
過去30年西方史學界的研究不斷沖擊著即有觀點:晚期的中華帝國其實比人們想象的更具活力,徹底顛覆了僵化的“傳統”社會的形象;區域研究表明中國社會內部豐富多變;變化的動力來自內源性因素而不是西方的介入等外來壓力;最新的學術前沿是考察19世紀末以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公民身份和代表意識(representation)等觀念如何得以建構,繼而打破國家是自然形成的傳統看法。③Paul A.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這些研究工作突破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法,重新評估基督教傳教團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盡管如此,大多數新近的研究依然沒有給予傳教士和中國教友足夠的重視,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出自對熱炒“西方沖擊”的矯枉過正式的反動,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傳教士研究“已無新意”。還有一種可能,人們仍心存敬畏,不愿妄議前人的虔敬之舉。當然,亮點依然存在,若干個案研究就很有意義。例如,兩部討論義和團運動的專著贏得一片贊譽(它們對傳教士的解讀和評價令人耳目一新),近年問世的數個專題成果也意義不俗。④例如,Kathleen L.Lodwick, Educating the Women of Hainan: The Career of Margaret Moninger in China, 1915–1942.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Lawrence D.Kessler,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Joseph W.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aul A.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Bays, op.cit..以羅杰·湯普森(Roger Thompson)的論文為例,此文內容豐富,交互式解讀(interactive interpretation)的研究視角啟人深思。文章聚焦于如下歷史:1861年傳教士進入陜西農村,不久即想方設法關閉寺院、沒收寺產充公,這個大膽的舉動前無古人,卻為1900年后卷入現代化進程的中國官員效仿。⑤Roger R.Thompson, “Twilight of the God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hristians, Confucians, and the Modernizing State,1861–1911,” in Bays, op.cit..國家權力的延伸與世俗現代性話語之間的關系另見 Prasenjit Duara,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1, 1991, pp.67-83.雖然以上個案值得我們關注,但總體而論,西方學術界的主導性意見依然認為,傳教活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位置不那么重要。我們有理由相信,融合前沿理論、整合史學論著、在中國近代史脈絡中充分定位傳教士的綜合性研究成果仍需時日。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過去20年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者投入極大的熱情探討在華傳教士的歷史角色。他們比西方同行更樂于承認傳教士的歷史意義,不拒絕使用正面的積極語詞。在毛時代的數十年里,中國人對傳教士的評價是負面和消極的。1979年以來帝國主義和階級斗爭的話語逐漸淡出,官方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由此打開正面評價傳教士的意識形態空間。以王立新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一書為例,該書在近年出版的同類專著中可謂翹楚。作者指出,美國傳教士并非文化帝國主義或其他類型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致力于“文化交流”,為清末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貢獻。作者也不掩飾問題,他批評傳教士為達到宗教目的選擇性地介紹西方文明甚至不惜欺騙,比如,刻意淡化法國大革命和達爾文進化論的歷史價值。①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Dan Cui在其英文著作The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British-American Cooperation to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20s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一書中呈現了相似的寫作結構,對英國傳教士的評價更加正面。
王立新的論著嚴謹細致,堪稱中國學術界傳教士研究的里程碑。本書也像此前的一些研究一樣,把現代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框架作為歷史評價的標準:傳教士的角色是正面的,他們推動了看上去必然的和線性的“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也應批判他們試圖將這一進程引入“歧途”的做法。有趣的是,在王立新和其他一些中國學者的近作里,“帝國主義”一詞的含義有別于西方學者討論文化帝國主義時的語義。中國學者往往把(面目可憎的)文化帝國主義和(有益的、至少是中性的)文化交流兩相比照,并且越來越多地將傳教士活動納入后者的范疇。這一傾向傳遞的基本立場是,傳教士與外國政治經濟利益沒有直接關聯,他們大多對中國心懷善意。不過,前文已經指出,從廣義的文化帝國主義層面考察,何種動機、有無直接的政治聯系都不是傳教士研究的核心命題。科馬洛夫夫婦(還有毛澤東)就不曾刻意區分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交流。對傳教士的各種評價對應著帝國主義的不同含義:在中國歷史學者筆下,帝國主義指一定歷史時期內西方政治勢力的擴張,而在后殖民讀本的編輯眼中,帝國主義是一個正在發生的進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逐漸全球化,侵入其他非資本主義地區,破壞前資本主義或者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②Williams and Chrisman, op.cit., p.2.如果說第一個定義明顯狹隘,第二個定義卻流于寬泛(然而它把“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作為唯一的基準線也很片面,不得不說是一個悖論)—即便包羅萬象是“文化帝國主義”一詞得以廣泛應用的主要原因。
上述研究提醒我們,評價傳教士的影響必須回答另一個更為宏大的問題:如何把民族主義、現代性和歷史性結合起來思考。中國近代史的書寫深受發展主義思維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謂“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的影響,影響到人們對傳教士的定位。③Duara, “Response to Philip Huang,” p.36.近代中國經歷的變化頗似科馬洛夫夫婦筆下所謂“觀念的殖民化”。例如,引進西醫;反對纏足、吸食鴉片和封建迷信;引入理性至上的、進階式的和(在理論上)適用全民的教育制度;倡導婚姻自由;爭取政治表達的權利—都與傳教士存在不同程度的關聯—在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里,它們一直被視作民族解放和“覺醒”的歷史表現。④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探討了民族“覺醒”的話語,參見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薩義德忽視了亞洲參與者在建構東方主義過程中充當的角色,德里克把中國知識分子擁抱發展主義的言論稱為“自我東方化”⑤Dirlik, op.cit..(self-orientalization)。這個術語與“觀念的殖民化”面臨著相同的困境,但是,畢竟賦予當代知識分子界定變化的權力,這種變化對今天的亞洲參與者而言首先應當是解放性的。當然,如果把緊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而出現的變化解讀為“觀念的殖民化”,那么我們必須看到,“觀念的殖民化”是一種普世現象。
四、基督教傳教團與全球現代性
19世紀和20世紀世界發生的變化是深刻和無可逃避的,時至今日任何人也無法與這場巨變剝離開來,這使得評價歷史變得更為復雜。人們一度把這場變化理解為“西方化”(westernization),認為它是一場以歐洲為中心勢不可擋地向外擴張的連鎖反應。然而,這種看法遮蔽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千姿百態的本地化變異并未簡單復制西方的組織結構和典型行為。①J.Boli和F.J.Lechner回顧總結了“全球化導致文化同質化”之說受到的主要質疑。參見“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ulture,”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Neil J.Smelser and Paul B.Baltes.Amsterdam: Elsevier,2001, Vol.9, pp.6261-6266.無論我們怎樣理解這種變化,有一點確鑿無疑:19世紀和20世紀的基督教傳教活動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讓西方的概念和制度傳播到非西方社會(在有些情形下尤為明顯)。評價傳教士的歷史角色,我們需要超越一味吹捧或者貶損的單極化傾向,這種傾向的源頭是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交織而成的二元目的論。
因此,我們有必要越過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如前所述,無論分析一般性的文化接觸還是聚焦世界歷史上的傳教士活動,它都算不上一個令人滿意的模型。要之,其主要癥結如下:第一,它沒有跳出本質主義的民族/文化本真性話語想象;第二,它沒有充分考慮甚至忽視了受動者的能動性;最后,它用強制行為解釋文化變遷,把復雜的文化影響簡化為施動者和受動者的二元對立,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征服、合作或抵抗,以及毫無意義的動機之爭和文化交流與文化壓迫之間牽強附會的區別。科馬洛夫夫婦的研究令人難忘,但是他們用于描述文化變遷的術語“觀念的殖民化”同樣存在缺陷。他們記錄的茨瓦納人兩百年來經歷的變化究其本質而言是全球性的,若以此反證“文化帝國主義”和“觀念的殖民化”,則意味著“被殖民化的觀念”是一種普世經歷。
這種洞見提供了一個思想基礎,有望推動我們融合宏觀的全球視角與微觀的個案立場,重新評價作為近代世界史要素的傳教活動。在宏觀層面,我們能否嘗試勾勒傳教士的整體角色:他們傳播現代秩序里那些建基于“普世性”的規范性的概念范疇—國家、理性、科學與技術、個人自主、宗教—從歐洲傳向非西方社會。在微觀層面,透過考察具體的信息移植(appropriations)及其后續反應,我們能否澄清傳教士通過怎樣的方式在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生產文化差異?第一個問題指向一幅全球場景,引導我們比較傳教士與非西方社會里其他的變化矢量;第二個問題對應翻譯活動,重視本土語境下的能動力,即接受、本地化再現、改造或拒絕傳教士的宣教。誠然,許多工作有待展開,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經為上述兩個問題提供了肯定的答案。
長久以來存在一種臆想,認定宗教與現代性水火不容,前者屬于“傳統”世界,注定將被“現代”意義的理性、世俗民族國家和作為消費者的個體(individual-as-consumer)取代。這一想當然的看法干擾了我們的判斷,妨礙我們把傳教士視為全球現代性的傳播者。過去十年里,越來越多的人提出不同意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探討宗教身份與現代民族主義關系的學者。薇思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指出,在19世紀和20世紀都有一些印度人和英國人選擇歸附少數民族宗教信仰,這一事實挑戰著世俗現代性和民族身份的二元邏輯。她本人反對把宗教身份歸入前現代和前民族范疇的學術話語。③Gauri Viswanathan, Outside the Fold: Conversion, Modernity, and Belief.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薇思瓦納珊借鑒了塔拉爾·阿薩德(Talal Asad)的觀點,阿薩德認為,宗教被視為人類社會的普世特征,但宗教概念本身實為近代西方話語的產物。①Talal Asad,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范彼德(Peter van der Veer)和萊曼(Hartmut Lehmann)提醒學者們注意“宗教和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體現著西方現代性話語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二人主張“分析宗教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位置時……應當結合現代國家概念的出現與傳播”。②Peter van der Veer and Hartmut Lehmann, “Introduction,” in Nation and Relig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 and Asia, ed.Van der Veer and Lehman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4.
前述成果對于剖析近代史上的基督教傳教團而言啟示良多。各宗派的傳教士都自視為當地教友的領路人,引領他們加入超越國家和族群邊界的普世團契(a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communion)。具體到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團,即表現為教會的管轄權和代表權(representation),涵蓋宣教區(mission field)的新興教堂(速度和形式因宗派不同而異)。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這樣的聯合教派傳教團或者弟兄會(Brethren assemblies)一類的反教權(antiecclesiastical)運動組織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也秉持同樣的原則:存在一個普世的跨國家和民族的基督教教會。這種基督教國際主義(在一個更宏大的本體論基礎上)對應著現代社會里民族國家保持自治獨立又彼此關聯的國際秩序。二者的確多有契合,正如在贊美詩里,“喚醒”異教徒投入基督教的懷抱常常被描繪為“喚醒”異教徒的國家和民族加入基督教國家的世界大家庭。③參見John Fitzgerald,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0年,第389頁。因此,我們也許有理由相信,傳教士國際主義(以及19世紀中期以來形成的更加世俗的國際非政府機構一起④參見Boli and Lechner, op.cit., p.6261.)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奠定世俗國際主義的思想基礎。
準確地講,傳教團因其組織結構成為跨文化傳播的管道。傳教士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非西方社會分布最廣的西方人,由于他們的工作性質而挑起跨文化傳播的重擔。新教和羅馬天主教傳教團征募特定文化、教育和宗教背景出身的人。他們到達宣教地區后,通過私人接觸、信函往來、文字出版和召集會議等渠道,與所在國社會以及來自其他傳教團和國家的傳教士交流。通過圣事(orders)或布道會(mission board),傳教士與原籍國和家鄉教會以及同派的其他傳教士保持聯系,聯系的渠道還是信函、出版物和會議。由此可見,傳教士個體接受的影響是多樣和高度國際化的,各種形式的內外聯絡利于教派之間以及宣教對象國之間相互比較,規范工作,至少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團的情狀如此。
借助布道、教學和文字出版,傳教士向讀者、聽眾和學生源源不斷地傳遞現代全球體系的諸多特質。以中國為例,他們用地理和歷史著作破除中華帝國自視文明源頭和世界中心的觀念,提醒中國人他們的國家只是萬國之一,世間各國皆有歷史。傳教士還創制大量漢語新詞,從相對具體的“碳” “機車”到抽象的“民主” “義務” “新聞”,不一而足,以此傳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思想。⑤劉禾(Lydia H.Liu)的著作中列舉了大量此類概念。參見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ppendix;劉禾還論述了日本在西方術語的漢譯中如何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傳教士又印制不同語言的《圣經》和重要譯名手冊,此舉意義非比尋常。⑥Norma Diamond探討了傳教士翻譯的《圣經》對少數民族身份和權力的意義。參見“Christianity and the Hua Miao:Writing and Power,” in Bays, op.cit..仍以中國為例,學術界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傳教士世俗出版物,對《圣經》和其他宗教文獻的關注有限。宗教出版物的術語選擇對中國讀者的影響其實是一個重要課題,有待進行深入研究。
科馬洛夫強調日常行為的重要性,這一點提醒我們,符號可以與文本一樣傳遞現代世界秩序的元素。我在其他場合提過一個例子。1895—1920年間傳教士聯合中國基督徒推動建立福州地區的公共政治制度。他們采取的手段包括懸掛國旗(中外國旗)和唱原始國歌(proto national anthem)(中外歌曲)。①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特別是第4章。當然,傳教士本身就意味著差別意識和外部視角,對本土生活來說意義特殊。例如,本文第三節提到,羅杰·湯普森考察了正當的“宗教”與無益的“迷信”之間的所謂區別如何經由中國人與傳教士的接觸進入中國的國家話語,成為現代派官員手中華麗的幌子,他們以此為由關閉當地寺院,收繳寺產。②Thompson, op.cit..
傳教士在傳播全球共性特質時扮演的角色還引出另一個問題,即信仰的歸附需要并且建構現代意義的自主個體觀念。范彼德主編的一部會議文集—書名很是引人注目—《歸附現代性:基督教的全球化》 (Conversion to Modernities:The Glob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就正式探討了這一問題。范彼德在序言中表示,現代的個人概念“對資本主義和新教主義都至關重要”,也與“傳教士的歸附事業”密切相關。③Peter van der Veer, “Introduction,” p.9, in Conversion to Modernities: The Glob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ed.van der Veer.New York: Routledge 1996.John Fitzgerald在“Lands of the East Awake”一文討論了中國的個案。他的話再次提醒我們反思那種把現代性與宗教對立起來的慣性思維。長期研究五旬節教派(Pentecostal Christianity)在非西方世界傳播的學者也顯然注意到同樣的問題。所以,盡管五旬節教派一度被視為對現代性的反動,如今卻因為它強調個人體驗而成為現代性的典型范例。④Andrew Walker, “Thoroughly Modern: Sociological Ref l ections on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from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Stephen Hunt, Malcolm Hamilton, and Tony Walter.London: Macmillan, 1997, p.36; 參見Martin Percy, “The City on a Beach: Future Prospects for Charismatic Movements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ibid.;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0.
至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傳教士擔當著重要的中介,他們推動構建普世的全球現代性。他們的影響也存在于伴隨全球化同步進行的文化分化的進程中。為了闡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厘清傳教士與所在國文化的關系。首先有必要考察某些廣為流傳的原型。出于福音工作的現實需要,即便最保守和粗魯的傳教士也必須與所在國的民眾維持良好的工作關系。事實上,他們不大敢于端出一副全盤否定所在國文化的姿態。然而流行的傳教士形象卻是這樣的:他們擺弄著手指,把所在國文化批得一無是處,處心積慮地想要建立起一個完全的替代品。這種形象,即使用最謹慎的措辭形容,也是不可想象的。倘若哪個傳教士果真如此狂躁,無須多久就將淪為失敗的教士,只剩下被召回國一條路。
接著要討論一個重要的事實:他們的傳教事業要求使用所在國的語言傳遞信息,翻譯因此成為傳教活動的一個核心議題。今天人們已有共識,翻譯絕非把文本的“意思”從一種語言平移到另一種語言,就像文本的內核可以輕巧地從生產它的具體語言中抽離出來一樣。傳教士在翻譯時為了表達本地語言里不存在的概念,無論神學概念或者其他領域的概念,必須使用已有的語詞或者發明新的語詞。無論作何選擇,問題都會隨之而來:沿用既有語詞,原詞已經負載著本土文化的語義;創制新詞則可能令讀者不甚明了,往往又得退回原路,思量如何以受眾熟悉的語言解釋那些陌生的概念。不僅如此,假如他們的口語表現不足以抓住聽眾的耳朵,文字的風格和形式無法吸引讀者的注意力,那么任憑如何翻譯也是枉然。如若在一個文獻典籍汗牛充棟的國家,憑借文字打動讀者就更加不易,盡管這個國家悠久的閱讀傳統看似降低了操作的難度。以中國為例,中國人的書面語言之難非同尋常,讀者的眼力之高堪稱少有,傳教士一般選擇與中國人合作著書。如此一來,他們的傳播行為必然受到極大限制,不易隔絕所在國社會文化的操控。
傳播行為的一條顯著特征是講話人/作者無法控制文本或話語在受眾一端產生的意義,跨文化傳播尤其如此,講話人/作者可能并不充分了解受眾的文化框架,也難以準確預知自己的話語/文本將怎樣被置于其中并作何解讀。這再一次引出了跨文化傳播活動中受眾的能動性話題。前文已有論述,文化帝國主義模式的一個主要缺陷,就是輕視了受眾社會的能動力。今天學者們之所以把文化的分化與趨同均視作全球化的內容,就在于看到了受眾社會的能動性:每一條所謂的“共性”被引入既有的文化主體之后,可能衍生出不同的意義和用途。①Boli and Lechner, op.cit..
重點考察本土受眾的能動性,分析他們如何使用當地的文化語言解讀傳教士的信息,這種研究理路提示我們,外來的文化壓力可能消亡或征服本土文化,也可能激發創造的潛能,至少對受眾社會的部分成員如此。②這里涉及Mary Louise Pratt提出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之說。參見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London: Routledge, 1993。Dirlik將此概念應用于研究中國,參見“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不同于Dirlik筆下“自我東方化”的描述,另外一些學者積極評價受西方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參見Philip C.C.Huang,“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26, No.1, 2000, pp.3-31.既然現實中并不存在一個外在的本真的標準供人們衡量文化變遷,那么評估具體的文化變遷時,我們需要首先考察的是經歷文化變遷過程的人怎樣自我理解,同時也要看到文化的流動性,充分肯定歷史參與者面對語境張力有所作為。這就要求我們跳出民族國家的排他性話語(例如,中國基督徒是帝國主義“走狗”、否認少數群體的“合法性”等成見)。說到中國,最近的研究成果正在帶領我們超越晚清官方檔案里標簽化的中國基督徒形象,跳出20世紀民族主義者的論戰和早期學界的主流觀點。當代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已經闡明,從中國北方鄉村的天主教徒到香港新界的客家新教教徒再到美國的華人移民,基督教完全可以成為一些中國人群體的身份標志。③Richard A.Madsen,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這種破除舊識的思維反映出文化的內涵由結構主義轉向更加強調流動性和歷時性的模式,跨越“西方”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簡單二分法因此成為可能。
非洲學學者、耶魯大學教授拉明·桑納(Lamin Sanneh)專業從事基督教和傳教士研究,他在分析傳教士翻譯對非西方文化產生的影響時指出,傳教士把基督教經典譯成所在國語言其實鞏固了本地文化。桑納教授說:“《圣經》翻譯基于一個前提,那就是本地語言與福音話語之間相互通約,用本地的術語和概念描述《圣經》的核心范疇就是證明。”作為對比,他舉出伊斯蘭教的翻譯。伊斯蘭教只承認阿拉伯語的《古蘭經》是唯一神圣的權威經典,就此而言,西非的伊斯蘭教比基督教更加排斥本土文化的宗教價值。桑納教授考證發現,傳教士在西非的翻譯活動不僅生產了一批辭典和語法手冊,還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當地諺語、成語、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因此,“傳教士對非洲語言和文化的公開興趣”增強了非洲民族的“自我意識”,強化了他們的民族身份。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能因為當地人在本土語言世界遭遇福音書后歸附了基督教就認定其結果必然意味著告別非洲世界的“心理移民”。把基督教文獻譯成本土語言還催生了宗教處境化運動,畢竟,基督教經典一旦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出版,傳教士便很難左右人們的解讀。④Sanneh, Translating the Message,特別是第5章;引自第166、170、184頁。他的后續著作更加精深,參見Encountering the West: Christianity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Process, The African Dimension.Maryknoll, N.Y.: Orbis, 1993.
綜上所述,如若我們可以改換視角,不再視傳教士為西方文化霸權的代理人,轉而考察跨文化交流的具體過程,就不難理解傳教活動何以通過傳播宣稱“普世”的概念達到鞏固文化差異的效果,無論那些概念屬于宗教范疇還是所謂全球現代性的組成要素。受眾社會的能動性表現在宣教對象的諸多具體角色中—作為語言教師、合作者、聽眾和讀者,基于自身的文化語境理解和移植傳教士的信息。傳教士必須筆耕不輟,堅持翻譯,于是,從日常慣例到至圣的奧秘,亦即在上帝名號之下全部的所謂“共性”,都逐漸進入不同語言系統里業已存在的意義網絡。不僅如此,既然翻譯活動或顯或隱地呈現著本土語言的結構特性及價值觀念,翻譯的終極效果或許比民族國家的影響更符合文化多元性的要求。以中國為例,傳教團和教堂一度用方言組織宣教、敬拜和出版,可惜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這一做法迅速消失,因為民族國家更加青睞國家的“共同話語”而非千姿百態的地方語言。
1996年德里克在本刊撰文呼吁學術界“歷史地看待資本主義現代性,同時積極尋找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現代性……但長期受其霸權壓制的其他現代性。”①Dirlik, op.cit., p.118.我相信,重新評價作為近代世界史有機成分的傳教活動,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王立新告訴我們,傳教士帶給中國的現代性既包括20世紀興起的現代秩序的內在元素,也有它最終淘汰的內容。②Ibid.,p.316.傳教士傳遞了怎樣的現代性,它們在非西方的文化語境下如何被接受、排斥和改造,這些問題都將啟發我們認識文化全球化。前文已經闡明,文化帝國主義不足以成為剖析這一過程的精準工具,“觀念的殖民化”也無力引領我們走得更遠。我們需要一種更富活力和互動性的理論框架,新的框架既要承認文化接觸中存在的壓迫、缺失和抵抗,更應展現多樣的可能性、邊界的流動性和潛在的創造性。方法論的關鍵在于焦點的轉換,從傳教士與本地文化相遇時的傳播者轉向接收端的本土能動性。跨文化的相遇刺激著文化的分化與趨同,全球化就在這兩個同步的維度上行進,明辨這一要點有助于學界適時調整研究方向。由此我們將更加透徹地理解塑造現代秩序的全球文化進程中人類所做的選擇與放棄。
【漢學家風采】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1951— )教授現為拉特羅布大學亞洲研究學院博士生導師,西方學術界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著有《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998年,該書獲享譽甚高的美國亞洲研究協會“李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J.Nathan)教授評價“這部杰出的著作基于開闊而敏銳的學術眼光,對20世紀初期中國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進行了綜合研究。”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保爾·蒙克(Paul Monk)認為:“這是一本非常優秀的著作。任何想要了解中國崛起及其政治自由斗爭的人,都有必要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