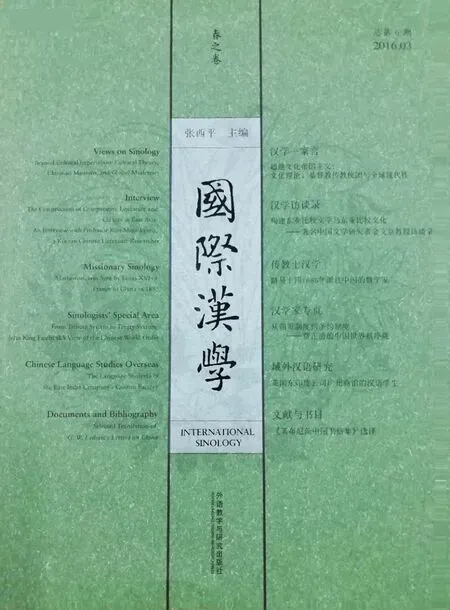《萊布尼茨中國書信集》選譯
楊紫煙 譯
譯者按: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德國數(shù)學家、哲學家,與牛頓先后獨立發(fā)明微積分,并對二進制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萊布尼茨中國書信集》[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missionaren (1689—1714),F(xiàn)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1990]中收錄了1689年至1714年間萊布尼茨與多位耶穌會士之間的通信。作為唯理論者,萊布尼茨在中國文化中找到了共鳴,書中他與入華傳教士白晉、閔明我、洪若翰、杜德美、劉應等的70封書信都表露出他對中國文字、歷史、醫(yī)藥、天文、數(shù)學等各方面的濃厚興趣和敬意。其中他與數(shù)學家白晉有關《易經》的通信,則提供了二進制的發(fā)明與伏羲八卦究竟有無關系的側面資料。從此處節(jié)選的書信片段中,讀者不難窺見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熱忱,以及初期入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獨到見解。
17.萊布尼茨致安多—韋珠(Antoine Verjus,1632—1706)
漢諾威(Hannover) 1697年12月2日
巴黎尊敬的韋珠神父收
尊敬的神父大人:
您給我的上一封信,以及您好心地讓我結識了尊敬的白晉神父(Joachim Bouvet,1656—1730),使我能通過他學到不少有關中國的知識,都讓我繼續(xù)感受到您的好意,長久以來您對我的恩惠就不曾中斷過。我十分贊賞和關心您在中國的傳教事業(yè),因為我覺得它是如今最偉大的事業(yè),不僅為著上帝的榮耀,為著福音的傳播,更有利于人類的幸福,有利于我們歐洲與中國各自科學與技藝的成長,這就像文明之光的交換,能在短時間內讓我們掌握他們奮斗幾千年才掌握的技能,也讓他們學會我們的技藝,豐富雙方的文化寶庫。這都是超出人們想象的光輝偉業(yè)。
麻煩神父大人派人將我內容龐雜的回信轉交給白晉神父,希望別人不要覬覦他那些寶貴的資料。我還希望他能給我提供更多的東西,當然只能慢慢等。我相信有人手中已經有很多相關資料的樣本了,我希望管理資料的您也能為我提供一些您認為合適的,我可以向您保證我決不會濫用它們。我很希望能有一些寄往中國或從中國寄來的資料的梗概,簡介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地理情況、韃靼地區(qū)語言的材料,盡可能多的各種語言寫成的天主經(附有逐字對照的譯文),比現(xiàn)有的更出色的講解中文字的說明和對中國歷史及編年表的考證,這樣我們不僅能了解我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中文史料,更重要的是能知道中國為科學與文藝所做的最大貢獻是什么。
神父大人日理萬機,很難有空回答我的問題,滿足我的好奇心。而白晉神父又正準備回到那龐大的帝國,也很少有空。我希望神父大人能委托您一位細心的朋友給我提供現(xiàn)有資料中我想要的那些,我也很希望他能請白晉神父以后仍給予我?guī)椭?/p>
神父大人,我很希望自己能為您神圣而美好的事業(yè)做點貢獻,但我覺得我能為您做的可能只有我比較籠統(tǒng)概括的研究工作了。撇開與之無關的歷史、公共事業(yè)與人權問題,單談科學與技藝的進步,我覺得重要的有兩點:首先是發(fā)展創(chuàng)新(這是藝術中的藝術),不僅包括通過樹立新方法來創(chuàng)新,也包括創(chuàng)新地使用某些邏輯推論;第二是確立一套可靠的哲學思想,這既有利于培養(yǎng)人們的虔誠之心,也有利于探求真理。以前在報紙和其他地方我都談到過這一點,我甚至在給白晉神父的信中也說起過,因為我了解到有關人士計劃在中國宣傳哲學思想,而且我相信借助我的動力學說或力學知識,我們能夠證實古代的哲學思想,并在不破壞對神學有利的已有學說的前提下,使我們今天看來無用或無法解釋的東西變得有用而容易理解。
借此機會,我還想告訴神父大人:我給我的朋友阿弗朗什(Avranches)教區(qū)主教寫了一封信,說我認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傳播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某些哲學思想,這封信被登載在巴黎的《學者報》(Journal des savants)上并遭到駁斥,駁斥者認為我在攻擊新近去世的笛卡爾先生及其擁護者們的偉大學說。確實,我發(fā)現(xiàn)笛卡爾先生有些論點可能引出違背神意倒向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學說的結論;但我同時也聲明:我并不將這些結論歸咎于學說創(chuàng)建者或擁護者,基督教的仁愛讓我相信他們不曾覺察到這些危險的后果。我提到笛卡爾先生有一個論點:同一物質可以連續(xù)表現(xiàn)為各種可能的不同形式,從這一論點我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論哪種可能出現(xiàn),其中原因既不是選擇也不是神意。關于這一點有反對者駁斥我偽造笛卡爾論點,于是我補充標注此論點出處為笛卡爾的《定律》(Principes)一書第3冊第47條,還在今年第32、33期《學者報》上論證了我的觀點。最近在第37期報紙上又有人反駁,他們無視我的聲明,指責我攻擊笛卡爾學說,這完全沒有依據。我對神父大人提起這個是想讓您了解我良好的本意以及我謹慎委婉的態(tài)度。
我還有一個年輕時就開始醞釀的計劃(在我1666年出版的一篇演講稿里公開過),我覺得它不僅對宣傳我們信仰的傳教事業(yè)有非凡的作用,還十分有利于在公共生活與藝術及其他行業(yè)中發(fā)現(xiàn)并檢驗思考與實踐的自然真理。可是由于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專心一意協(xié)助我的幫手,我還沒能將這個計劃付諸實踐。這個計劃就是我發(fā)現(xiàn)可以通過一個與數(shù)學不同的方法發(fā)現(xiàn)建立真理,并借助算術的檢驗使之與數(shù)字和代數(shù)一樣確鑿無疑。在這個奇妙的領域里,獨立于任何語言的新的哲學計算能讓彼此相隔最遙遠、語言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比方說我們和中國人—共同理解自然界最重要最抽象的真理。這不同于建立新的萬能文字或萬能語言,既不會有建立新語言的不便與困難,還有更多其他優(yōu)點:因為它不僅僅用于解釋事物(抽象符號也可以解釋事物),更可以用于揭示真理,甚至用于口頭表達、化解紛爭,這些都是抽象符號所無法比擬的。這種特別的計算應該還有更多其他令人驚異的用途,我無法簡單描述,而且沒有實踐也很難讓人信服。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機會把它付諸實踐,也找不到任何與之相近的觀點,我很擔心這個計劃就這樣流產會給傳教事業(yè)帶來巨大損失。不過,我們應該完全相信主的神意,在全知全能的主認為合適的時候,實踐這個計劃的時機自然會出現(xiàn)。
神父大人是偉大的主的光輝旨意的強大執(zhí)行者,懇請您為了公眾的利益,為了基督教信仰的傳播,幫助我保存這個計劃。向您致以我崇高的敬意與深深的感謝。
您卑微順從的仆人 萊布尼茨
附言:有沒有人請幾個中國人來歐洲作活字典幫助我們做相關研究?
18.萊布尼茨致白晉
漢諾威1697年12月2(12)日
巴黎尊敬的白晉神父大人收
尊敬的神父大人:
我本以為尊敬的神父大人還在中國腹地,與那龐大帝國的皇帝談論哲學和數(shù)學,以便將基督教的福音傳給皇帝和他的臣民,卻驚喜地收到您客氣無比的來信,在此向您致以深深的謝意。我出版的書里講述的是拜主所賜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您不必向我致謝。何況您與同行的傳教士都不顧偏見與反對,義無反顧地參與了這項偉大事業(yè),我覺得你們的虔誠與熱情才真值得稱道。您若能給我提供北京紀行里沒有涉及的資料,我會非常高興,如果像您上封信里說的那樣,您對書中某些內容,或是序言,或是增補部分有什么意見或建議,請不吝賜教,我會非常感激。可能是有人壓縮了《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里這短短的一段而添加了其他東西,造成了一些問題。您說要寄給我您已出版的有關中國皇帝的作品,能在我的書里增加這樣一段中國皇帝的小傳,真是太完美了。我也十分期待您關于中國皇帝頒布容教令并允許自由傳教前因后果的新作。我對您給予我的恩惠深表感謝,唯愿自己不致辱沒您對我的好意。希望您的大作不僅用法語,也用拉丁語出版,讓更多的民眾都能拜讀、受益。
尊敬的韋珠神父大人告訴我,您正準備回到為上帝的傳教事業(yè)出色工作的國度,也轉告我隨時可以向您要一些資料梗概,我會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向您請教,但愿您別出發(fā)得太早。我認為以后我們還將從中國得到有關其歷史、道德、政治、數(shù)學和物理的資料。在歷史方面,我認為首要的是得有某種考證材料,用它來檢驗我們能夠和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信賴中文歷史典籍。而這種檢驗需要一部中國文學史,有一部內容詳盡、確鑿可信的文學史至關重要。證實工作應該節(jié)錄原文并盡可能地附上適當?shù)淖g文。
對中文書寫與語言的說明闡釋可說是文學史的基礎,也是打開一切知識寶庫的鑰匙。現(xiàn)存有好幾本有關中文字符的手抄字典,分別有中文版、葡萄牙文版、佛拉芒文版,等等。好像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0—1689) 神父曾對我說中國也有這方面的字典,中文字符是與各種東西的不同外觀緊密相連的。不論中國字典是什么樣的,我堅信通過諸位神父大人我們一定能得到最精準的中文字典,我也相信一定已經有人帶來了一些出色的字典與語法資料,這樣我們就可以判斷新近去世的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先生的期望是否有憑有據,米勒先生在東方語言研究上造詣頗深,他曾斷言能夠有一種開啟中文奧秘的鑰匙,我特別想知道神父大人您對此的感想。要深入研究中文,出版一些中文書很有必要,這些書不僅應有逐行對照的譯文,還應配有語法來分析解釋文字本身的規(guī)則,如果是早期古文字的話,就應該專門闡釋那些改變字符含義的細小筆畫。
借助對中文的研究,我們有望得知其周邊民族語言的大致情況,希望開始能得到少量例詞、有關通信的梗概,以及用我們懂的語言或當?shù)卣Z言寫成的天主經與主禱文,這些都配上逐行對照的譯文。對各種語言的研究調查最能揭示各民族的起源和遷徙情況。且不說朝鮮、日本、暹羅、阿瓦(Ava)及印度部分地方的語言,研究這些語言需要慢慢搜集相關資料,現(xiàn)在我只研究中國北部、印度大部與波斯使用的韃靼語。搜集部分詞匯和語法常識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這些語言寫成的天主經經文。因為哪怕天主經里只有一個我們認識的字,通過逐行對照的譯文,我們也有辦法把這種語言同其他語言相比較。我希望能有用中國的韃靼文寫成的天主經,我想您應該有辦法幫我拿到吧,如果能夠,我懇請您幫我這個忙,我打算將它同更靠西邊、通常稱為蒙古文的韃靼文天主經作個比較。有人從荷蘭寫信告訴我莫斯科公國副大使(就是那位簽署尼布楚和約的大使,簽約時張誠神父[Jean-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大人也在場)的隨行人員中有一些蒙古農奴,我想從他們那里應該可以拿到一本天主經。有人寫信告訴我說蒙古語和更靠西的卡爾梅克人(Kalmuc)的語言很相近,因此我特別想知道中文會不會也近似于蒙古文。我也聽說蒙古人崇拜唐古特語及其文字,因為大喇嘛在唐古特。我很期待能夠了解唐古特文字到底是怎樣的。還有人寫信告訴我不久前去世的波蘭國王曾向閔明我神父詢問一些中文字,想把它們同自己懂的克里米亞韃靼文作對比,可是除了兩種語言中都用Marah或類似單詞表示“馬”以外,沒什么別的值得報告的發(fā)現(xiàn)。然而,幾乎與之一樣的詞在德語和威爾士地區(qū)留存的古高盧語中也表示相同的意思,這一發(fā)現(xiàn)意義重大,它說明這個詞從歐洲大陸的一端傳到了另一端。總之,我希望我們能夠抓住一切機會深入了解各民族語言,這既有利于我剛才提到的各方面,也有利于傳教事業(yè)的進行。
要研究中國歷史剩下的問題,需要仔細構建一個歷史年表,以便解決其古代時間的大問題,同時還可以判斷是否如我們所見的那樣,《圣經》的希伯來文70子版更為可信。這一切工作都應該誠實地進行,不應因為可能損害到我們所堅信的權威而有所隱瞞,因為我們發(fā)現(xiàn)的一定會是相互呼應的事實,《圣經》不會受到任何沖擊。除了研究中國歷史過去的王朝交替,以及雖有不少昏君仍一統(tǒng)江山的當今王朝外,還應仔細考察中國的發(fā)明、技藝、法律、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歷史。比方說我很想知道他們古時候是否有接近于我們的幾何學一樣的科學,是否知道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于斜邊的平方,他們得知這條定律的途徑是前人的研究,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實踐經驗,還是通過自己或其他民族的論證。
說著說著就說到了歷史以外的其他主題上,我現(xiàn)在就談談中國的倫理道德與政治問題。他們應該有很完善的規(guī)章制度保證國內的安定,希望有一天我們能掌握其中的細節(jié)。因為真正的實用哲學是為教育和公眾社交服務提供良好秩序,而不是對美德和義務空泛的訓誡。在這一點上我們能從中國人那里學到不少東西,他們值得我們欽佩。他們約定俗成、在重要場合使用的格言和慣用語都值得配上解釋以中文出版。
我堅信他們的思辨與數(shù)學無法與我們的相媲美;但他們在悠久歷史里的長期實踐活動一定使他們有數(shù)不清的機械發(fā)明和其他創(chuàng)造,這些都是我們所缺乏的。雖然我們在理論原則上比他們進步,但我們的相遇和交流意義重大,它會孕育千萬美好成果,千萬發(fā)明創(chuàng)造。我本人也是天天都驚異于我們在某些領域的匱乏,驚異于我們有那么多東西可以借來充實各方面的實踐:有些是對日常生活作用非凡的,有些是與計數(shù)、圖像、機械、航行、軍事科學、地理等等息息相關的。中國人一定有許多古老的天文觀測資料,我們應該盡力搜集出版,這樣既可以把它們同當今的天文資料相比對,還可以把它們和喜帕恰斯(Hipparchus,約前190—前120)與托勒密(Ptolemy,約100—170)的天文記載及記有亞歷山大在巴比倫發(fā)現(xiàn)的天文記載的資料相比對。同時,借助他們有關中國及周邊地區(qū)的地圖和相關記載,我們的地理學研究也能得到相應完善。我很想知道您對威特森(Nicolaes Witsen,1641—1717)先生所制地圖的看法,還想知道您和您的神父們是否有韃靼最東部的地圖可以對威特森先生所制地圖作修正與補充。總有一天我們會弄清楚美洲與亞洲是否屬于同一大陸。
現(xiàn)在來談談物理方面,物理研究的是地理和機械原理無法解釋、通過實驗得出的、某種實物的規(guī)律。所以我們不可能先驗地或通過論證來得出這些規(guī)律,只能通過實際經驗或慣例獲得。我堅信中國人在這方面遠遠地超過了我們,因為他們的實踐時間比我們久,傳統(tǒng)經驗比我們更連貫更精細。但這些物理規(guī)律覆蓋面太廣,因此我認為了解它的最好辦法就是將中國的各種職業(yè)與技能做一番描述。由于描述對象眾多,我們事不宜遲,要想從中得出成果,必須盡快開始著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國人在我們之前發(fā)明了羅盤、火藥,掌握了簡單卻了不起的知識,其中有一些我們今天才明白,但我相信他們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醫(yī)學方面,這是自然科學中最必不可少的學科。神學是靈魂層次上認知的最高點,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涵蓋了良好的道德與優(yōu)秀的政治,同樣,醫(yī)學可以說是肉體層次上知識的結晶與最高點,因為醫(yī)學是將人的肉體與完整的人相對照作研究的。但一切自然科學包括醫(yī)學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人類的最高幸福,治病與養(yǎng)生都是為了讓人類為上帝的榮耀繼續(xù)服務。對不起,神父大人,請原諒我又偏題了。
剛才跟您說的都是我希望以后慢慢能拿到的資料,但是如果能現(xiàn)在就給我們提供這些資料的部分樣本是最好不過了,比方說用少數(shù)幾種語言寫成的天主經、一些帶有語法分析的中文書、還不錯的字典、中國歷史年表的一些考據、好的規(guī)章、發(fā)明創(chuàng)造、細致的觀測或實驗報告等等。既然已經有人帶了其中的一些東西回來,我非常希望能得到那些資料的介紹,也希望今后能得到更多的相關資料。
我還特別希望得到閔明我神父大人的消息,我曾榮幸地獲準與他通信,我想他那里應該也有準備給我的東西。不過無論如何,正當壯年的您一定能在這方面給予我?guī)椭槲覐浹a不足。我還很想知道中國人對由羅梅爾(Ole Romer,1644—1710)先生發(fā)明、迪雷(Duret)先生制造的天文觀測儀有什么感想。聽說觀測儀由你們親自運送,以便將它完整地送到且不致生銹。要想比從前更準確地預測日食月食等天象,掌握月亮的運行周期十分重要,因此我很想了解觀測儀在 卡 西 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先生、皮卡爾(Jean Picard,1620—1682)先 生、德 拉 伊 爾(Philippe de la Hire,1640—1718)先生等人的周密照管下運行得如何,也想知道有關人士是否已經至少獲得了一段時間內可信的觀測記錄表。
您如果能告訴我一些有關從中國帶來或是已經或將要運往中國的東西的具體情況,那就太好了。我對這些很感興趣,因為我非常希望這樣的交流能順利進行,我認為這在當今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我們歐洲,都是意義最為重大的事。如果有機會,我會很高興地為之作貢獻。因為我們能夠幾乎像注射一樣把我們的知識技能一瞬間傳授給他們,我們也一樣能從他們那里一下子認識一個嶄新的世界,若不通過這種交流,我們不知道要用多少世紀才能掌握這些知識。雙方彼此獲益才算公平,因為如果光讓他們學習我們的知識而不作交換,我們便會落后于他們。這也是我常常向閔明我神父宣傳的。盡管如此,中國人能給予我們的一切都無法與我們帶給他們的信仰之光相提并論。
剛去世不久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神父承認,您與各位神父也發(fā)現(xiàn):在中國宣傳哲學意義重大,有助于使他們的靈魂更接近真正的宗教從而接納它。正因為如此,研究如何教授哲學也變得重要起來,要讓教授的哲學更有根據、更有說服力、更適合達到這樣的效果。我注意到許多有學問的人認為應該廢除經院哲學,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哲學取代它,不少人主張用笛卡爾哲學。但在作了各方面的權衡之后,我認為古代的哲學根基牢靠,現(xiàn)代的哲學應該用來豐富它而不是摧毀它。我與機智的笛卡爾主義者們在這個問題上有過不少爭論,我甚至用數(shù)學向他們表明他們完全不認識真正的自然法則,要認識它們不僅要在自然界研究實物,更要研究力,物體從前(或是隱德來希[entéléchie]—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用語,意謂“完成”)的形式就是它的力。通過這個,我相信可以恢復為神學服務的古老經院哲學的地位,而不違反現(xiàn)代發(fā)現(xiàn)與力學原理,因為力學本身就是研究力,而正好就身體現(xiàn)象而言,研究力最能引起對精神問題的考慮,因此,最能將迷失于物質概念的中國人引入精神層面。這樣也算我為我們的宗教出了一份力,不僅如此,我還希望這有助于阻止一種過度物質化的哲學侵吞人類靈魂,在我提出的各方面,力的準則都來自于一個最高的支配者。
我得停筆了,不然這封信就要被我寫成一篇演說辭了。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與根基堅實的科學的發(fā)展,我們能更好地領悟智慧真諦,體會萬物之主的強大,造福人類;我對這項傳播主的榮耀、利于人類最高幸福的事業(yè)懷有極大的熱忱,正是這股熱忱促使我寫下了以上冗長的話。希望在這項事業(yè)上與我懷有相同觀點的您不致覺得我的啰唆讓您心煩。既然您在準備長途旅行,想必時間寶貴,沒時間將您打算和能夠告訴我的東西全部告訴我。不過如果您認為合適,我希望能有一些比較空閑一點的神父能補充您與韋珠神父為我提供的援助。我衷心祝愿您神圣而美好的目標得以順利實現(xiàn),并祝您身體健康。
附言:因為信上還空出這么一塊位置,我再補充幾句:著名的開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曾發(fā)表過幾頁論文,其內容是針對同屬耶穌會的提倫提烏斯(Terentius)神父從中國的來信,他在文中提出了研究中國天文、歷史年代、地理等方面的建議與其他方面的想法。我十分肯定您所在的巴黎的圖書館里一定有這份資料。如果您手頭沒有,我懇求您想辦法把它找出來,把它當成開普勒現(xiàn)在寫的一樣好好研究;因為如今我們如此幸運,能更好掌握他那時想要了解的一切。現(xiàn)在我這里沒有他的這份書稿,否則我一定會把它讀完,以便告訴您值得研究的地方。我不知道中國歷史是否有證據證實我們所說的古老的中國曾進行過遠征。塞德蘭(Zeilan)島的名字似乎是從塞里斯人,也就是中國人那里得來的,有發(fā)現(xiàn)證明古代的地理學家把該島稱為“Seran diva”,可以證明Diu或Diva在波斯語中的意思是島。“Seran diva”的意思就是“塞里斯人(或中國人)的島”。可能從前那里是很多塞里斯人的停泊口岸。不過中國人確實曾進行過遠征,他們極有可能曾在塞德蘭或賽朗(Seran)或賽朗島(Seran diva)建立過殖民地。
法國有關人士正竭力翻譯大量中文書籍,請您告訴我翻譯工作是如何進行的,是通過懂得中文的歐洲人,還是請來中國人幫忙?
21.白晉致萊布尼茨
拉羅舍爾(La Rochelle) 1698年2月28日
先生:
您在三個月不到的時間里給我寫來了4封信,我無法向您表達這對我來說是多大的榮幸。我到12月2日才同時收到您寄出的前兩封,很抱歉那時才回復您,也很遺憾無法回答科獻斯基(Adam Adamandy Konchanski,1631—1700)神父信中的問題。因為我能力有限,不過在我?guī)湍@些忙之前,我會請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1653—1708)神父大人代替我給您幫忙。郭弼恩神父正在韋珠神父身邊作有關中國傳教及其他東方事務的錄事,此后我們所有的有關論文都會寄給他。他答應我會定時給您寄他編輯出版的論文集,我想他一定不會食言,好好協(xié)助您。
至于您委托羅齊埃爾(Rosieres)先生轉交給我的第三封信,我對曼茲里烏斯(Menzelius)先生的書一無所知,這對雙方都是損失,十分遺憾。而您的第四封信寄到時我已出發(fā)上船了。與我同行的有8位耶穌會士,他們各有專長,這使得他們能在中國得心應手地工作,既有助于使中國人改信基督教,也能為像您這樣好奇而學識淵博之士提供有關中國的一切知識,以利于科學與文藝的發(fā)展。您給我們美好而客氣的來函,我會給他們看,希望您以后繼續(xù)和我們通信。您自己或您的友人提出的各點建議,我們都會慎重而仔細地考慮,既然您的觀點和我們一致,相信您對此一定很滿意。我還可以提前向您保證,法國的耶穌會士,無論是正身處中國的還是那些正準備去中國的,或是以后要去中國的,他們都會和我們一樣努力工作,并以此為樂,以此為豪。這是我請您務必相信的,也希望通過您,讓您那些對中國多少有興趣的朋友們,包括曼茲里烏斯先生、美名遠揚的斯克羅齊烏斯(Schrokius)先生、尊敬的科獻斯基神父都確信這一點,在此請允許我向他們表達我微不足道的敬意。我會榮幸地給他們每個人單獨寫信,雖然我正準備乘船出發(fā),但總還有點空閑時間。
如果我們到達巴達維亞,我一定會去拜訪克萊耶(Andreas Cleyer,1634—1698)先生,親自將斯克羅齊烏斯先生的信交給他。我還會叫人制作一份復本,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把信中提到問題的解釋盡快寄給您。如果有空,我會馬上開始著手這方面的工作。
閔明我和張誠神父知道了您讓我向他們轉告的祝福后一定十分感激,我會提醒他們最初對您做的承諾。
您所說的有關您新型計算器的事,閔明我神父和所有法國耶穌會士聽了都十分高興。不過他們或許還要等好幾年才能知道這計算器的機械結構,這一定會讓他們感到很沮喪。
我剛剛把您寄給我的文辭美妙、內容豐富的第一封信又讀了一遍,著迷程度比我頭一次讀它時更深。令我特別欣喜的是,您在信中建議我們弄清楚的各方面,恰恰和我們鑒于其巨大影響而決定更為重視的問題不謀而合。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在中國的神父里對中文與漢字造詣最深的劉應神父(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決定編纂一部字典,這本字典會讓您覺得在這一方面已經做得無可指摘。附在書中的語法及其他注釋將使這部著作完美無缺。不論米勒先生所說的中文鑰匙是什么,我堅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對中文做出完美的分析,或許能將它們作為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來解讀,由此確認究竟它們中哪一種是大洪水之前學者們使用的文字。我們已經想辦法了解了您想知道的中國鄰國的語言情況,會盡快把相關資料寄給您。信中還會加入要重制的地圖,特別是韃靼東部地圖所需要的專門資料。不久以后我可能會有機會到韃靼東部,一直到所謂的阿尼安(Anian,即今白令海峽。—譯者注)海峽附近去作一次短途旅行。
我們打算側重研究的是中國的歷史編年表,我們會盡最大可能建立一個依據確鑿、清晰明確的編年表。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們打算按您的想法,對撰寫中國歷史、編寫年表的主要作者作全面的考證;之后,我們再研究他們的自然史與社會史、物理、道德、法律、政治、藝術、數(shù)學和醫(yī)學,我相信醫(yī)學一定是中國能教給我們最多寶貴知識的學科之一。我這么說是因為我最關注的就是醫(yī)學方面。我甚至已經弄到了這方面許多論著,只是一直沒有時間好好研究。我只給了比尼翁(Bignon)教士一份《脈經》的譯文,《脈經》節(jié)錄自我?guī)Ыo皇家圖書館的《本草綱目》。郭弼恩神父有這篇譯文的草稿與《本草綱目》序言的譯文,《本草綱目》記載了中國自然史的主體部分,而它的序言揭示了整部作品的主題與結構。
如果我有多一點的空閑時間,我會寫一本中文解密,或一本最初漢字的分析,最初的漢字由或斷開或完整的橫線構成,據說為伏羲所創(chuàng),我自認為已經找到了學習它的真正秘訣。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神父在他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一書序言中將這些古漢字列進表格里。創(chuàng)造漢字的人巧奪天工,漢字以一種簡單自然的方法展現(xiàn)了一切科學原則,換言之,這是一套完美的理論體系,但似乎在孔子之前很久,中國人就不認識這套體系了。不過,雖然中國人已不再懂得這語言,他們對這體系,或這些文字的真正奧妙卻仍懷有特別的尊崇,這奧妙所在不僅能幫助我們重建中國古人真正的法則,使全國人認識真正的上帝;還能幫助我們樹立在一切科學中都應遵守的自然法則,或更確切地說,重新找出理性之光最為純潔時古人所遵循的古老法則。先生,您看,我很高興自己完全贊同您的想法,我清楚,要讓中國人接受這真正的宗教,應該只教他們古代哲學,乃至中國古代哲學,我覺得中國古代哲學在所有方面都與我們認為最可信的古代哲學相似,我們的古代哲學只研究物質與形式,中國的則只重視自然中的物質與運動,運動同于形式,或同于所謂的力或自然物的活動原則。
我沒有找到您說開普勒提議在中國研究天文、歷史年表和地理的那幾頁資料,如果您找到了,先生,請幫我們看看有哪幾點最重要,然后通知我們,感激不盡。
您找我要一份韃靼文天主經的譯文,隨信附上我匆忙之中翻譯的譯文,由于我忘了一些日常用的詞匯,所以譯文里會有些紕漏。
我真心希望還有幾小時的空閑時間來滿足您各方面的好奇心。上帝保佑,不久之后我們在中國能夠給您寄去一些詞匯與完整的語法研究。在此,千萬次感謝您對我順利抵達目的地的祝福,愿您生生世世永遠蒙受上帝的恩寵。我為您的善良向您致以誠摯的敬意與深深的感謝。
您卑微順從的仆人 白晉
22.郭弼恩致萊布尼茨
巴黎 1698年5月15日
先生:
尊敬的白晉神父大人告訴我他離開之前給您寫了信。3月6日他從拉羅舍爾出發(fā)直接去中國,風向正好。雖然出發(fā)已經遲了一個月,他仍希望在今年抵達。如果上帝保佑他今年抵達,他的旅行一定十分順利,更有利于基督教在這個龐大帝國的傳播。聯(lián)系是世上最重要的,正是基于這一點,韋珠神父—您了解他的虔誠—才在今年派出了他可能范圍內最多的傳教士,自薦者超過100名,若不是神父無法負擔如此龐大的費用,他會將他們全派出去。神父在這些人中挑選了18名,并讓他們從不同路線出發(fā)。白晉神父船上有9名,個個德才兼?zhèn)洹F渲羞€有一名技藝高超的意大利畫師,中國皇帝一直想要一名西洋畫師,這次白晉神父打算把他推薦給皇帝。
先生,我們多么期待這新的一批傳教士為信仰、為科學技藝的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直到現(xiàn)在我們幾乎沒有從在北京的傳教士那里收到任何東西,盡管他們曾給我們寄出很多論著與細致的調查報告,可這些都不幸因為戰(zhàn)爭散失殆盡。特別讓我感到可惜的是張誠神父寄給我的有關他在韃靼旅行的報告,那其中有許多我們完全不曾知曉的新鮮知識。為彌補這些損失,白晉神父答應會寄給我們中國書籍里更新鮮有趣的資料。先生,神父大人為您的美德及您曾給予他的幫助而感動不已,希望我今后和您保持聯(lián)系,將我們從中國收到的一切消息都轉告您。我會很高興并且準確無誤地做這些事。因為萊布尼茨先生在整個歐洲美名遠揚、德高望重,為我們這個時代做出了偉大貢獻,但凡對科學有點興趣的人,無不為能與您交流感到興奮,而且這種交流也會為今后的日子留下珍貴的回憶。神父大人囑咐我撰寫傳教史,并發(fā)表從中國寄來的資料,希望我今后的這些工作也能滿足您的好奇心。我已將《中國皇帝頒布容教法令的歷史》(L’histoire de l’Ed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faveur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一書送去印刷,這本書白晉神父也和您說過,比您在《中國近事》書中譯成拉丁文的蘇霖(Francisco Suarez,1548—1617)神父所寫的內容更豐富,印刷完畢后我會立即給您兩本,一本送給您表示我對您的敬意,另一本請您寄給您的朋友科獻斯基神父大人。我會將書交給布羅索(Brosseau)先生。書中有一些關于中國不同教派、中國物理和道德的有趣介紹。這些都是過去僅僅被泛泛觸及的領域,今后我們會更深入地研究它們。最后還有一段對中國人祭祖祭孔儀式的闡釋,是為那些不明就里卻對這些儀式大放厥詞的頑固人士指明錯誤的。非常希望您讀了這本書后,能來信告訴我您的感想。如果我也有一本您的《中國近事》,我就會把您寫在開頭的出色序言譯成法文,去年冬天我將您這書的部分節(jié)錄與中國來信的一些片段一起出版了,大家都非常希望看到完整的原作。
白晉神父把您與科獻斯基神父的論文都帶走了,他會詳細給你們回信的。韋珠神父將斯帕根斯菲爾德(Spargensfeld)先生的問題托付給我回答,我在此附上給他的回信,請您讀完后幫我把給他的信封好轉交。他好像沒有讀過剛去世不久的柏應理神父所著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這本書1687年在巴黎出版,值得一讀。白晉神父似乎很想要曼茲里烏斯先生的中國編年表,他特別囑咐我向您要。劉應神父精通中文與漢字,我已寫信給他請他盡快給我們寄來這個聲名遠播的帝國精確的編年表和詳細的歷史,我還請他著手編一本新的中國地圖集,盡管衛(wèi)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神父所編的地圖集很出色,但其中有不少錯誤,新地圖集能對我們所了解的韃靼及其鄰國的情況作一補充,關于這些情況我們還有許多東西需要研究。我?guī)缀蹩梢源_信美洲與烏皮國(Vupi)接壤并屬于同一大陸;或許日本也與之接壤,或許日本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種島嶼,因為我們并不知道其北方的情況。希望不久之后就能有這些方面的重大發(fā)現(xiàn)。也希望能榮幸地將這些情況盡快告知您,向您致以崇高的尊敬與敬佩之情。
您卑微順從的仆人 耶穌會士 郭弼恩
附言:韋珠神父大人告訴我您想知道白晉神父帶了些什么去中國,他給皇帝帶去了各式各樣的數(shù)學儀器、一些擺鐘、鑲嵌工藝品、分支吊燈和一面大鏡子。國王陛下還從自己的珍藏中拿出了一整套盔甲送給中國皇帝,包括一頂頭盔、一副制作考究的護胸甲、一把軍刀、幾把手槍、一支火槍和一支短筒火槍,還另附了一些銅版印刷的精美書籍與王家圖書館的圖畫。白晉神父還帶去了大部分技術工具的樣品和模型以便將其與中國的作比較。
23.郭弼恩托萊布尼茨轉致科獻斯基
巴黎 1698年5月15日
尊敬的神父大人:
白晉神父在巴黎收到了您給他寫的信,他本來很樂意回答您提出的問題,也非常想向您的好意表示感激,但他實在太忙無法做這些事。于是打算到拉羅舍爾再給您回信,但我也不知道那時他是否會有時間。由于無法確定是否有空,白晉神父讓我向您的友善表示感謝,并讓我用有限的學識代他回答您的問題。神父大人,這正是我下面要做的,以此向您表達我對您的尊敬與仰慕之情。
1.我們中有些神父已經編寫了中文字典與語法書,幫助歐洲人學習中文。其中有一本字典里所有的中文字都用西歐字符拼寫,每個字都有葡萄牙文解釋。還有一本字典里的葡萄牙文單詞按字母順序編排,都配上中文解釋。另外還有一本字典非同凡響,其中所有中文字均為手寫,并被分為三類:簡單字、復合字和雙字合成字。這本字典極其出色,但法國沒有任何復本。
2.中國人熱愛詩歌。其詩歌押韻而優(yōu)美,有一些戲劇也是由詩歌構成,不過當然與我們的戲劇風格迥異。他們的文學作品嚴肅而充滿訓誡,風格接近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5—117),并與中國人的才華相得益彰。他們的語言里沒有像您提到的“grandisonus”“magnanimus”一類的復合詞。
3.中國的編年表非常出色而且連貫。柏應理神父在他那本受到眾多學者欣賞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中讓我們了解到這一點。有關我主耶穌受難那天的日食有很多可以研究,我想這在中國并未造成很大影響,因為日食發(fā)生時中國已是傍晚或入夜。如果您有空具體算出在中國觀測到這次日食的時間,我們將不勝感激。如果中國的編年史提及這次日食,我們的神父們也會仔細查明情況。
4.中國人并不用星期劃分月份。他們使用陰歷,并根據太陽運行情況加以調整用來紀年。
5.有關人士發(fā)現(xiàn)在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有很大的磁偏角。我們的神父十分精確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今后還會寄來這方面的觀察報告。
6.瓷器上的釉是用與制瓷相同的材料經過進一步摻水攪和制成的。法國已經有人掌握了有關訣竅,能制造出與中國瓷一樣精致半透明的瓷器。不過只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奧秘。只要他能掌握好燒瓷時爐內應該的溫度,其他的就都不用操心,這種瓷器也很快就會變得很普遍。但是由于溫度過高會燒壞許多瓷器,因此現(xiàn)在他仍可以將制成的瓷器賣得和從中國進口的一樣昂貴。至于那些莫斯科人帶來的半透明的甕,我們既不知道是什么,也從未聽說過。
7.中國人懂得用稻子制像玻璃一樣透明物質的秘方,還會用蕨草制這種東西。他們還會用稻米釀制美酒,釀造方法幾乎與我們釀葡萄酒的方法一樣。
8.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飲茶的風氣正在淡化。
9.大多數(shù)在歐洲能看見的鳥在中國也有,特別是那里有許多與歐洲相似的烏鴉和麻雀。那里也有荊棘、薊等類似的東西。但我想那里沒有蘑菇和塊菰。
10.在中國神職人員并不比歐洲的高明,那些江湖術士對自己長生不老藥的鼓吹都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不值得浪費時間來介紹。
神父大人,剛才我已盡力回答了您給白晉神父提的問題,等白晉神父到達中國以后,他一定還會再做更詳細的補充說明。他是5月6日從拉羅舍爾出發(fā)的,風向正好,他乘坐的是一艘配有40架火炮的王家三桅戰(zhàn)艦,戰(zhàn)艦名叫“安菲特利特”(Amphitrite)快帆。如果風向合適,明年8月底會抵達中國。將這艘船直接派到中國的那些商人準備在11月再派出一艘船去中國。有一位波蘭的耶穌會神父曾打算加入法國神父的行列一起去中國,如果他還有此計劃,這會是個好機會,希望您能寫封信通知他。因為韋珠神父對使中國皈依基督教的傳教事業(yè)懷有無限熱忱,他對我說如果有波蘭或德國神父愿意與我們法國神父一起去中國,他將非常歡迎而且高興。向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派多少傳教士也不算多,試想30—40個傳教士在2億中國人中算什么?如果我們真對我們的信仰無限忠誠的話,就應該抓住中國皇帝明確表示歡迎我們的機會,向中國派成百上千名傳教士。我已將中國皇帝頒布容教令的歷史一書送去印刷,我會寄一本給您的朋友萊布尼茨先生讓他轉交給您,書中應該會有您感興趣的東西。請允許我滿懷熱忱地向您表示我深深的崇敬與尊敬之情。
您卑微順從的仆人 耶穌會士 郭弼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