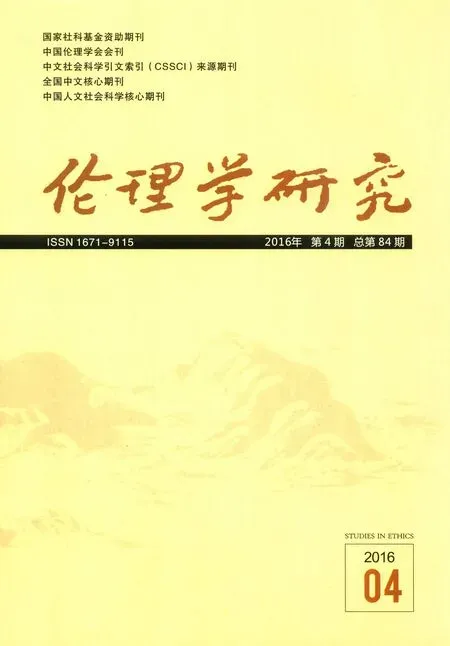民國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道德價值訴求
王芳芳
民國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道德價值訴求
王芳芳
民國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成立是傳統(tǒng)中醫(yī)生們的一場自救運動,這一過程折射出傳統(tǒng)士大夫在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從意圖倫理轉(zhuǎn)向責(zé)任倫理的一種嘗試。但此轉(zhuǎn)型并非一帆風(fēng)順,更非完全徹底,就其轉(zhuǎn)型困境而言,它甚至也成為了困擾當(dāng)代中國社會醫(yī)患關(guān)系緊張的原因之一,即從醫(yī)生的視角看,傳統(tǒng)士大夫(確切來講是傳統(tǒng)中醫(yī)師)從意圖倫理向責(zé)任倫理的轉(zhuǎn)型尚未完成。在當(dāng)代多元的倫理空間中,以“善的框架”和道德“方向感”為特征的職業(yè)認(rèn)同在今日中國醫(yī)生那里并未得到良好呈現(xiàn)。
意圖倫理;責(zé)任倫理;中國士大夫;現(xiàn)代轉(zhuǎn)型;醫(yī)患關(guān)系
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身兼“居官者”和“文人”雙重角色,位居“四民”之首。傳統(tǒng)士大夫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不為‘良相’即為‘良醫(yī)’”,這二者都體現(xiàn)的是主觀性的意圖倫理。民國時期出現(xiàn)的中醫(yī)師則受到現(xiàn)代西方專業(yè)精神的影響,開始接受客觀性的責(zé)任倫理,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出現(xiàn)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目前學(xué)界對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角色認(rèn)同等主題有所觸及,但尚未對中醫(yī)師這一具體人群給予倫理關(guān)照。本文擬從意圖倫理向責(zé)任倫理的轉(zhuǎn)換這一視角切入,揭示中國士大夫現(xiàn)代轉(zhuǎn)型所形成的新道德資源和面臨的倫理困境。
一、“意圖倫理和責(zé)任倫理”的界分及其問題意識
“意圖倫理與責(zé)任倫理”的界分是德國社會學(xué)家馬克思·韋伯在《以政治為業(yè)》的著名演講中提出的①,韋伯指出:“我們必須明白一個事實,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都可以是受兩種準(zhǔn)則中的一個支配,這兩種準(zhǔn)則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并且勢不兩立。指導(dǎo)行為的準(zhǔn)則,可以是‘意圖倫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責(zé)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這并不是說,意圖倫理就等于不負(fù)責(zé)任,或責(zé)任倫理就等于毫無意圖的機(jī)會主義。當(dāng)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恪守意圖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jié)果’,同遵循責(zé)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后果,這兩者之間卻有著極其深刻的對立”[1](P107)。
上述“意圖倫理”與“責(zé)任倫理”的界分,是韋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確切來說,是在批判“意圖倫理”②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所謂“意圖倫理”,是以行為者主觀意圖的純潔性為要義,受先驗性意圖植入的影響,運用自己的思維邏輯去處理各種關(guān)系,不關(guān)注行為手段的正當(dāng)性與否,將行為后果推給他者的一種純主觀傾向的倫理準(zhǔn)則。正如帕森斯所言,“意圖倫理(價值合理性)把行動條件僅僅當(dāng)作獲致特定絕對價值的手段和條件,但是他并不關(guān)心他的行動成功與否。他能否成功與他是否應(yīng)當(dāng)努力沒有關(guān)系——因為沒有其他價值與之匹敵,不能成功也無其他價值可以補(bǔ)償。如果客觀情況使得成功不可能,那么,‘受難’就是唯一可接受的道路”[2](P721)。然而,韋伯并沒有僅僅停留于簡單描述“意圖倫理”與“責(zé)任倫理”的沖突,而是基于對政治與道德的吊詭關(guān)系③的分析,提出了融合“天職”精神和現(xiàn)代理性于一體的“責(zé)任倫理”精神。所謂“責(zé)任倫理”,不僅要求行動主體意圖的良善,還要求行為主體在做出行為選擇時,顧及可能的行為后果并為之負(fù)責(zé)的一種兼顧主、客觀傾向的倫理準(zhǔn)則。“責(zé)任倫理(目的合理性)行動者不僅必須要選擇達(dá)到一種特定目的的手段,而且還必須把諸價值即諸終極目的加以權(quán)衡比較;他不僅必須關(guān)注一項特定行動過程對于獲致其本身直接目的或終極目的可能直接造成的后果,還必須關(guān)注該行動過程對于其他價值直接或間接可能造成的后果”[2](P721),以至于瑞士學(xué)者G.恩德利指出韋伯的“意圖倫理與責(zé)任倫理是一種假對立”[3]。
在韋伯看來,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祛魅”的理性化社會。在理性化社會,工具理性盛行、宗教力量式微,那么,前現(xiàn)代社會的倫理價值何以與現(xiàn)代社會進(jìn)行對接?韋伯相信,只有這樣一類人才可以承接這一重大歷史使命,即“具有古代傳教士的‘激情’和‘信仰’卻又有現(xiàn)代‘理性’精神并負(fù)有‘政治責(zé)任感’,即融信仰與理性、激情與責(zé)任感、判斷力與行動力于一身的克里斯瑪型的政治家”[4]。真正的政治家不同于政客、官吏、傳教士等,而是“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因為“能夠深深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齡大小),他意識到了對自己行為后果的責(zé)任,真正發(fā)自內(nèi)心地感受著這一責(zé)任。然后他遵照責(zé)任倫理采取行動,在做到一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動的表現(xiàn)。我們每一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須明白,我們都有可能在某時某刻走到這樣一個位置上。就此而言,意圖倫理和責(zé)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bǔ)充的,唯有將兩者結(jié)合在一起,才構(gòu)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dān)當(dāng)‘政治使命’的人”。[1](P116)
韋伯的“責(zé)任倫理”提出以后,后世學(xué)者從學(xué)理上對之進(jìn)行了從政治領(lǐng)域向社會領(lǐng)域的拓展。質(zhì)言之,上述“意圖倫理與責(zé)任倫理”的界分,實際上反應(yīng)了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古代人(前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人在倫理實現(xiàn)方式上的差別,這是韋伯的一大重要貢獻(xiàn)。不過,針對這個差別,韋伯并沒有給出更加細(xì)致的論述。筆者以為,從倫理的實現(xiàn)方式上看,古代人(前現(xiàn)代人)所信奉的意圖倫理,僅靠行為主體單個人就可以實現(xiàn),因為它僅關(guān)乎行為主體意圖的良善與否。而現(xiàn)代人所秉承的責(zé)任倫理,是需要團(tuán)隊來實現(xiàn)的,因為它與責(zé)任的特性及現(xiàn)代社會的倫理屬性相關(guān)。其一,從責(zé)任的特性來看,它具有延及性、擴(kuò)展性。在韋伯提出“責(zé)任倫理”之后,德國學(xué)者漢斯·憂那思以“憂患啟迪”的方式對韋伯的責(zé)任概念進(jìn)行了擴(kuò)展。針對傳統(tǒng)“近距離倫理”的困境以及現(xiàn)代哲學(xué)對“自然的遺忘”,憂那思提出了奠基于亞里斯多德自然目的論基礎(chǔ)之上的“遠(yuǎn)距離倫理”,“把責(zé)任的對象由鄰人轉(zhuǎn)向后代,把對人的責(zé)任擴(kuò)展及自然”[5]。此外,從責(zé)任的主體來看,現(xiàn)代技術(shù)文明提出的重大問題就是“個人的權(quán)力也許從比例上看甚至變得更加渺小,而變得更加偉大的無疑是集體的權(quán)力”[6]。易言之,個體性倫理將在技術(shù)文明時代失語,“我”將被“我們”、整體及作為整體的高級行為主體所取代,決策與行為將“成為集體政治的事情”[7]。其二,在前現(xiàn)代社會(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時空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靜態(tài)穩(wěn)定狀,監(jiān)控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surveillance)是“內(nèi)在于所有人類活動的、對行動的反思監(jiān)控”,靠血緣、地緣、宗教團(tuán)契來維持[8](P18-19),工作領(lǐng)域里的社會關(guān)系靠個體的角色意識來范導(dǎo)。現(xiàn)代社會以降,隨著“時空分離”的“暈旋感”④、公共領(lǐng)域的“浮”[8](P17)出以及社會分工和分層的完成,人們的流動性大大增加,時空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動態(tài)的不穩(wěn)定性。在現(xiàn)代陌生人社會,個體的人逐漸轉(zhuǎn)化為組織人。責(zé)任的承擔(dān)與監(jiān)管就無法再依賴個體內(nèi)在的主觀性反思,而是要依托于外在的、客觀的公共空間。中國古代社會比較缺乏這樣一個公共空間,中國社會大量存在的是私和公,但是沒有“公共”。“公”,是道德意義上的大道,有別于此的“公共”(public),中國社會是缺乏的。
可見,以專家團(tuán)隊為責(zé)任主體的風(fēng)險共擔(dān)機(jī)制,是現(xiàn)代社會實現(xiàn)責(zé)任倫理的主要形態(tài)。上述專家團(tuán)隊的出現(xiàn)一方面顯示個人私德式意圖倫理的衰微,另一方面也預(yù)示著公共空間開始成為社會事務(wù)以及社會倫理的主要作用領(lǐng)域。民國時期中醫(yī)師團(tuán)體就是這樣一支醫(yī)療領(lǐng)域的社會公共力量。而傳統(tǒng)中國士大夫,是以個體主觀意圖的良善作為其行事準(zhǔn)則;并且,在傳統(tǒng)中醫(yī)師群體內(nèi)部還存在著同行相輕這一陋習(xí)。傳統(tǒng)中醫(yī)師的這種執(zhí)業(yè)環(huán)境,實際上是用醫(yī)家的個體理性來凌駕和解構(gòu)醫(yī)學(xué)救死扶傷之學(xué)科理性,懸置了醫(yī)者職業(yè)倫理,傳統(tǒng)中醫(yī)師責(zé)任倫理精神的闕如,也就成了邏輯上的必然。
二、傳統(tǒng)中國士大夫的意圖倫理及其缺失
總體上,在家國同構(gòu)的宗法社會,中國士大夫作為儒家學(xué)說的踐行者,雖意圖倫理凸顯,但以責(zé)任為核心的現(xiàn)代職業(yè)倫理則明顯缺失。
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出“家國同構(gòu)”的形態(tài)。在宗法制下,“國”是擴(kuò)大化的血親,以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依附于皇權(quán)體制下的士大夫,秉承著“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政治意圖,有強(qiáng)烈的入仕精神和淑世情懷,在科舉入仕的正途上孜孜以求,“雖九死其猶未悔”,即使以布衣終老也不放棄對政治的關(guān)懷與投入[9](P116)。傳統(tǒng)社會并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社會分工(如現(xiàn)代的司法與行政的社會分工),更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職業(yè)分化(如行政官與法官這樣的職業(yè)區(qū)分),地方行政官的日常事務(wù)更多的是在判案,因而又可說基本是法官。[10]因而,傳統(tǒng)士大夫從“灑掃應(yīng)對”中所學(xué)的格致之知,并不具有以責(zé)任為核心的職業(yè)倫理意蘊(yùn)。
傳統(tǒng)士大夫上述倫理特征落實到醫(yī)者這一具象上也有明顯的體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較之于儒者,醫(yī)術(shù)被視為技術(shù)之流,醫(yī)者社會地位低下。不論是世醫(yī)、儒醫(yī),還是“世儒醫(yī)”,他們始終在“醫(yī)”與“儒”之間徘徊與掙扎。宋代偃文息武的政策,使得“不為良相,則為良醫(yī)”的價值觀念得以流行。儒醫(yī)的實質(zhì)是用儒學(xué)幫助、改造醫(yī)學(xué),而非僅僅是既通儒又通醫(yī)。儒醫(yī)認(rèn)為,醫(yī)學(xué)不獨能治身,亦可以實現(xiàn)修齊治平之抱負(fù)。他們以儒道言醫(yī),以儒行“正當(dāng)”化其醫(yī)療知識與技藝[11](P73-74),而非從醫(yī)療專業(yè)角度去鉆研醫(yī)術(shù)。所以,在傳統(tǒng)社會,“尊德性”之主觀性意圖始終處于主導(dǎo)地位,醫(yī)者也始終沒有放棄“攀援于儒”的努力[11](P68-69)。
此外,士大夫這種強(qiáng)調(diào)主觀性意圖、忽視后果責(zé)任的倫理屬性,也可以從醫(yī)療實踐中窺其一斑,其突出表現(xiàn)就是在病家⑤頻繁擇醫(yī)、試醫(yī)甚至“執(zhí)脈以困醫(yī)”的情景下,各自為政的醫(yī)家⑥出于“見機(jī)自保”而做出“擇病而醫(yī)”之不負(fù)責(zé)任的舉措[12](P49-57)。正如民國時期上海改革派中醫(yī)師代表秦伯未(1901—1970)指出:“今世之所謂名醫(yī)者,有三術(shù)焉。見病勢較重即多防變推諉之辭。為后日留愈則居功,變則諉過之地,此其一也。專選平淡和平之藥。動曰某方所增損,以博穩(wěn)當(dāng)之名,可告無罪于天下,此其二也。和顏悅色溫語婉詞,動效奴仆之稱,求媚于婦女庸愚之輩,使其至死而不悟,此其三也。觀此世之所謂名醫(yī),但不負(fù)診治之責(zé)任。”[13]名醫(yī)尚且有如此不負(fù)責(zé)之“術(shù)”,一般的“走方醫(yī)”、郎中更不必說。病家頻繁試醫(yī)、擇醫(yī),固然突出了醫(yī)療實踐中病患的參與權(quán),但同時也孳生了故意迎合病家、沒有治療最終決定權(quán)的非專業(yè)性醫(yī)家。在此境況下,建立醫(yī)家在醫(yī)療文化領(lǐng)域的權(quán)威,當(dāng)是形塑負(fù)責(zé)任醫(yī)家的重要舉措。而這種醫(yī)療權(quán)威的確定,依賴于醫(yī)家對于特定疾病之“真確診斷”與“合理治療”[14]之專業(yè)共識的形成。民國中醫(yī)師團(tuán)體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同僚權(quán)威”(colleague authority)[15]的公共空間,是現(xiàn)代醫(yī)療領(lǐng)域責(zé)任倫理踐行的主體。
三、轉(zhuǎn)向責(zé)任倫理的嘗試:民國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產(chǎn)生及其作用
民國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成立是傳統(tǒng)中醫(yī)的一場自救運動,是內(nèi)憂外患的產(chǎn)物。這一方面是來自西醫(yī)的刺激。至民國時期,西醫(yī)在醫(yī)療舞臺上基本打破了中醫(yī)一統(tǒng)天下的醫(yī)療格局,繼而也引發(fā)了20世紀(jì)30年代長達(dá)10年的中西醫(yī)之爭。這場爭執(zhí)始于學(xué)術(shù)界,延伸至政治界,最終導(dǎo)致了撼動全國的“政治大地震”[16],嚴(yán)重危及中醫(yī)師群體的生存,于是原來老死不相往來、一盤散沙的傳統(tǒng)中醫(yī)師大受刺激并空前地團(tuán)結(jié)起來,被迫進(jìn)行從價值觀到組織形式的自我更新,從醫(yī)術(shù)評價標(biāo)準(zhǔn)到同業(yè)互動模式的重構(gòu),以更好地爭取生存空間。另一方面病患大量流失,病家不再篤信中醫(yī),而是將信將疑,頻繁擇醫(yī)、試醫(yī)。與此同時,醫(yī)家“擇病而醫(yī)”和傳統(tǒng)中醫(yī)師內(nèi)部的同行相譏等因素也加重了傳統(tǒng)中醫(yī)從業(yè)者的危機(jī)。為了有效地回應(yīng)當(dāng)時的醫(yī)療情境,原本各自為政的傳統(tǒng)中醫(yī)師,通過弱關(guān)系⑦連接起來,責(zé)任倫理開始超越意圖倫理,民國時期中醫(yī)師團(tuán)體引領(lǐng)其成員迎接現(xiàn)代社會挑戰(zhàn),塑造新的中醫(yī)師群像。
如前所述,傳統(tǒng)儒醫(yī)之身份介于儒與醫(yī)之間,雖有徘徊猶豫,但作為意圖倫理的踐行者,其終極關(guān)懷在儒不在醫(yī),其支撐性價值系統(tǒng)始終是儒家的德性價值觀。近代以降至民國時期的部分中醫(yī)師們開始將醫(yī)術(shù)從儒家思想及其價值系統(tǒng)中剝離出來,在成立中醫(yī)師團(tuán)體之后更加注重醫(yī)術(shù)的實際療效及責(zé)任承擔(dān),其支撐性價值系統(tǒng)是對醫(yī)學(xué)這一職業(yè)的倫理認(rèn)同。
“認(rèn)同”(identity)來源于拉丁詞根idem,意即“同樣的”[17],哲學(xué)意義上的“認(rèn)同”研究,源起于近代的笛卡爾;之后,相關(guān)的“自我認(rèn)同”和“社會認(rèn)同”理論在心理學(xué)和社會學(xué)領(lǐng)域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與此有關(guān)的理論學(xué)派和學(xué)說也異彩紛呈。筆者在此文中借鑒加拿大學(xué)者查爾斯·泰勒的觀點,他將認(rèn)同理解為自我的同一性,包含了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個體的獨立。泰勒提出“認(rèn)同”關(guān)涉“善的框架”和在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18]。那么,就醫(yī)者而言,其職業(yè)認(rèn)同就意味著以維護(hù)醫(yī)者職業(yè)這一倫理實體為“方向感”,在“善的框架”中開展醫(yī)療實踐。這樣的醫(yī)療實踐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職業(yè)生涯的倫理認(rèn)同,是“特殊性”的醫(yī)者個體對具有普遍性的醫(yī)者職業(yè)共同體的心理認(rèn)同和行為認(rèn)同;它要求任何個體性醫(yī)者的行動與現(xiàn)實,都必須從醫(yī)者職業(yè)這一倫理實體出發(fā),維護(hù)其利益和榮譽(yù)[19]。不論是病家頻繁的“擇醫(yī)”“執(zhí)脈以困醫(yī)”,還是醫(yī)家的同行相輕,實際上反映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傳統(tǒng)中醫(yī)師“業(yè)界”觀念的缺乏和醫(yī)者職業(yè)共同體認(rèn)同的闕如。民國初年,通曉西醫(yī)倫理的翻譯大師丁福保提出了中醫(yī)師“對同業(yè)的義務(wù)”[20],強(qiáng)調(diào)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是專業(yè)團(tuán)體中的一員,與其他成員共享“病家信任”這個資產(chǎn)。20世紀(jì)30年代的中醫(yī)師們開始強(qiáng)調(diào)自身的主體地位。“對患者意見存疑”之共識的確立,以及對“醫(yī)界”整體性的強(qiáng)調(diào)使得中醫(yī)師間的惡意攻擊逐漸減少。從“中央國醫(yī)館”到地方的各中醫(yī)協(xié)會、國醫(yī)公會等[12](P70-73),無不強(qiáng)調(diào)中醫(yī)師業(yè)內(nèi)的團(tuán)結(jié)與互助,倡導(dǎo)建立同行業(yè)的行為規(guī)范,用價值而非僅僅用利益來作為行醫(yī)的信條,用敬畏和責(zé)任來詮釋自己的醫(yī)療實踐。此外,該時期以保障醫(yī)師職業(yè)權(quán)益為中心的職業(yè)公會(如上海國醫(yī)學(xué)會等)的成立,還表明“醫(yī)界關(guān)注的重心從單純的學(xué)術(shù)過渡到職業(yè)本身,彰顯出醫(yī)師群體愈來愈明晰的職業(yè)定位和身份認(rèn)同,也是醫(yī)師群體專業(yè)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現(xiàn)”[21](P61)。如1932年上海國醫(yī)學(xué)會主持編纂的《國醫(yī)名錄》的發(fā)行,可視為中醫(yī)師資格準(zhǔn)入機(jī)制建立的首次嘗試。由此可見,中醫(yī)師們的自我定位已然從傳統(tǒng)的“儒醫(yī)”“世醫(yī)”“走方醫(yī)”等向現(xiàn)代性的、有組織聯(lián)絡(luò)和基礎(chǔ)學(xué)歷與職稱的職業(yè)化轉(zhuǎn)變。雖然這種轉(zhuǎn)變距西方社會學(xué)家定義的專業(yè)化體制還離得非常遠(yuǎn),但無論如何,它已經(jīng)明確地表明,中醫(yī)師群體走上了以專業(yè)團(tuán)體為業(yè)界基礎(chǔ)的方向了[12](P75),而這正吻合了責(zé)任倫理精神勃興的時代氣象。此外,為了切實促進(jìn)中醫(yī)師專業(yè)精神的培養(yǎng),各中醫(yī)學(xué)社、學(xué)會均圍繞“聯(lián)絡(luò)感情、交換知識”這一團(tuán)體宗旨開展社交活動和學(xué)術(shù)活動。如在當(dāng)時上海中醫(yī)界的舞臺上便活躍著三個中醫(yī)師團(tuán)體——杏林社、春在社和醫(yī)林社,三者沒有派別之分,只有社員年齡之異;以每月一次的“聚餐”為契機(jī),團(tuán)體成員互相交流感情、切磋醫(yī)療機(jī)能[22]。這種運行機(jī)制,極大地促進(jìn)了中醫(yī)師對醫(yī)者職業(yè)這一倫理實體的認(rèn)同,其背后折射出來的就是對責(zé)任倫理精神的彰顯。
在韋伯看來,“工作”是踐行責(zé)任倫理的平臺,是禁欲主義天職的一種人間形式,它通過舍棄天生形態(tài)的自我而使自我的現(xiàn)實存在合法化,并產(chǎn)生一種獻(xiàn)身于終極價值或目標(biāo)的新的、更高的自我。它使人在奉獻(xiàn)中得到凈化,從而在一個已被理性化耗盡了意義的世界上創(chuàng)造一種意義感、目的感與個人價值感[23]。中醫(yī)師團(tuán)體成立以后,作為一種新興的醫(yī)療性社會組織,積極地參與貧病救助與時疫救治等社會事務(wù),共同推動公共衛(wèi)生體系的建設(shè),推進(jìn)了當(dāng)時的社會治理。例如,在貧病救助方面,民國時期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出現(xiàn)使得組織化的救助力量得以彰顯,彌補(bǔ)了以往中醫(yī)師在公益救助中個體施診不足的窘?jīng)r。以上海國醫(yī)公會為例,為了便于貧民就醫(yī),該公會把上海中醫(yī)界所開設(shè)或參與的數(shù)十處施診地點、施診時間和施診辦法在報刊上公之于眾[21](P269)。在時疫救治方面,為了在現(xiàn)代衛(wèi)生體制內(nèi)取得話語權(quán),中醫(yī)師團(tuán)體在盡力改變其自身傳統(tǒng)行醫(yī)方式的同時,還注重運用組織策略,聯(lián)合西醫(yī)共同開展時疫救治。這些內(nèi)容經(jīng)常在《申報》等諸多民國時期重要媒體上有所反映。中醫(yī)師團(tuán)體在公共衛(wèi)生領(lǐng)域里的積極作為,一方面彌補(bǔ)了國家孱弱之供給不足,另一方面通過實施貧病救助和時疫救治,充分展現(xiàn)了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意義感、目的感和價值感。
四、當(dāng)代醫(yī)患關(guān)系的糾結(jié):中國士大夫轉(zhuǎn)型之困
在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大背景下,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不得不接受自身角色及身份的轉(zhuǎn)變。一方面,科舉入仕途徑的終結(jié),使得他們被拋出權(quán)力體系之外,多數(shù)人開始從單純的一種人格蛻變成政治家、軍事家等各個職業(yè)的領(lǐng)袖;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淑世情懷,使其心系政治變革、情牽社會發(fā)展,集結(jié)民間社會,以民間結(jié)社的形式重構(gòu)政治與社會的新公共空間,以社會團(tuán)體的形式架設(shè)作為國家與個人中介的公民社會[9](P117)。反觀當(dāng)代中國緊張的醫(yī)患關(guān)系,筆者以為,從醫(yī)生的角度可歸結(jié)于傳統(tǒng)士大夫(確切來講是傳統(tǒng)中醫(yī)師)從意圖倫理向責(zé)任倫理的轉(zhuǎn)型尚未完成所致。
傳統(tǒng)中醫(yī)師群體雖然具有濃厚的意圖倫理意識,但是缺乏西方社會啟蒙運動以來的公共理性——這種公共理性具體表現(xiàn)為以風(fēng)險共擔(dān)、契約精神、相互保障等為特質(zhì)的責(zé)任倫理精神。民國時期正值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轉(zhuǎn)型期,民國時期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成立,可視為傳統(tǒng)中醫(yī)師尋求公共理性的一種自組織嘗試⑧。
民國時期開啟的中國醫(yī)師的職業(yè)化、責(zé)任倫理的轉(zhuǎn)向是在一個十分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xiàn)的,當(dāng)時的中國四分五裂,國家權(quán)力極度羸弱,無力提供有足夠涵蓋面的公共衛(wèi)生服務(wù),同時借助教會、西醫(yī)等方式人們開始接受了明顯有別于傳統(tǒng)身份觀念的醫(yī)療觀念,這就為公共領(lǐng)域的“浮”出、社會團(tuán)體的出現(xiàn)并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某種成長的裂縫,使得“改造傳統(tǒng)政治結(jié)構(gòu)和權(quán)威形態(tài),使其在新的基礎(chǔ)上重新獲得合法性和社會支持力量”[24]成為可能。在理想化的民主治理理論中,“權(quán)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zhuǎn)化也取決于不同社團(tuán)、群體和組織共同建立具有對彼此都具有約束力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共識”[25]。這樣一種民間社會與政治權(quán)威之間的良性互動關(guān)系,反而在政局亂象紛呈的民國時期,通過民間團(tuán)體參與社會治理而展現(xiàn)出某種端倪。
盡管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意圖倫理意識對于激發(fā)革命熱情、堅定革命信念,功不可沒;然而,在和平時期,因其動機(jī)至上的道德追求,勢必會帶來不計后果的非經(jīng)濟(jì)主義后果,尤其是在高度流動性的現(xiàn)代陌生人社會,責(zé)任倫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遺憾的是,在士大夫轉(zhuǎn)型過程中,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意圖倫理并沒有完成與責(zé)任倫理的恰切對接。具體而言,由于戰(zhàn)亂、革命等歷史因素,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并沒有完成,又加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建立起了對社會組織采取全面管控的超強(qiáng)政府模式,社會空間幾近萎縮至零,致使民國中醫(yī)師團(tuán)體成員所展現(xiàn)出來的“意義感、目的感和價值感”等端倪,只是曇花一現(xiàn),其歷史傳承并沒有得到延續(xù)。這種轉(zhuǎn)型困境造就了現(xiàn)代中國醫(yī)生以職業(yè)認(rèn)同感不足為核心的角色意識游弋、倫理意識模糊和責(zé)任意識不清。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又進(jìn)一步惡化了中國醫(yī)生的職業(yè)化發(fā)展環(huán)境。以市場經(jīng)濟(jì)和資本意識為重要特征的現(xiàn)代化語境,導(dǎo)致了傳統(tǒng)歸屬感斷裂等嚴(yán)重的社會價值問題,作為社會成員的中國醫(yī)生難以免俗,為數(shù)不少的醫(yī)者執(zhí)業(yè)理念錯誤并喪失崇高意識、價值認(rèn)知扭曲并缺少人文關(guān)懷、精誠意識缺失,這成為今日醫(yī)患關(guān)系錯位的主因。質(zhì)言之,許多中國醫(yī)者身處當(dāng)代多元的倫理空間,就個體而言沒有能夠恰當(dāng)區(qū)分意圖倫理和責(zé)任倫理,就群體而言沒有確立起相互間以“善的框架”和道德“方向感”為特征的職業(yè)認(rèn)同,結(jié)果,他們迷失在價值轉(zhuǎn)換的開局中:自己既非傳統(tǒng)懸壺濟(jì)世的仁者⑨,又非西方意義上的專業(yè)人士⑩。要求現(xiàn)代醫(yī)生同時扮演好上述兩個角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
不必諱言,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修齊治平的情懷的確可以彌補(bǔ)責(zé)任倫理在境界上的不足;但是,其“正心誠意”“反求諸己”“人人皆可為堯舜”的信念具有強(qiáng)烈的不確定性,而且完全訴諸當(dāng)事人的主觀意愿,缺少有效的客觀制裁和約束力量,容易淪為說教。應(yīng)該說,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普通公眾對醫(yī)生的道德期待還是傳統(tǒng)的,但是又部分鉸接著、夾雜著現(xiàn)代意義的內(nèi)容。這種道德期待要求醫(yī)生在認(rèn)同社會身份和個人身份間取得平衡:既期望醫(yī)生提高其專業(yè)化的水準(zhǔn),又要求醫(yī)生不忽視其自己和病人的個人身份[26],希冀醫(yī)療實踐在“善的框架”中進(jìn)行。遺憾的是,在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期,“意圖倫理”和“責(zé)任倫理”并沒有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社會倫理精神建構(gòu)之兩翼,這直接導(dǎo)致了諸多社會倫理問題的產(chǎn)生。筆者以為,困擾當(dāng)代中國的眾多辱醫(yī)殺醫(yī)事件之原因,固然有現(xiàn)行醫(yī)療體制的弊端,但我們亦可從中國士大夫的轉(zhuǎn)型之困中窺其一斑。因此,要對中國式醫(yī)患關(guān)系問題提出一個基于責(zé)任倫理的解決方案指南,關(guān)乎兩點:其一,從個體層面來講,現(xiàn)代社會理想的醫(yī)生角色應(yīng)該是以恰當(dāng)區(qū)分意圖倫理和責(zé)任倫理為行醫(yī)要旨,“融合信仰與理性、激情與責(zé)任、判斷力與行動力于一身”的、“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集仁心和仁術(shù)于一體的人;其二,從群體層面來講,確立起相互間以“善的框架”和道德方向感為特征的職業(yè)認(rèn)同,惟其如此,身處當(dāng)代多元道德空間,中國醫(yī)生們才能樹立正確的職業(yè)理念、恪守精誠意識,“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注 釋]
①關(guān)于“意圖倫理”,目前學(xué)界的譯法尚未統(tǒng)一,中譯本比較通行的譯法有“信念倫理”、“意圖倫理”,此外還有“心志倫理”;英譯本有“ethic of ultimate ends”、“ethic of conviction”、“ethic of intention”,日譯本有“心情倫理”等。參見(德)馬克思.韋伯.學(xué)術(shù)與政治[M].錢永祥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260.為了突出其主觀性且便于行文,本文統(tǒng)一采用“意圖倫理”的譯法。
②“‘意圖念倫理’就是寧愿被殺乃至國家失敗(后果)也不以武力抗惡(意圖);或者寧愿不和平而再打幾年戰(zhàn)爭(后果)也要實行社會革命的理想(意圖);寧愿多數(shù)暴政、文化倒退(后果)也要實行普選(意圖、例見韋伯評論俄國革命文);寧愿國家利益受損(后果)也要公布外交文件等等”參見何懷宏.政治家的責(zé)任倫理[J].倫理學(xué)研究,2005(1):11。韋伯認(rèn)為,“意圖倫理的信徒所能意識到的‘責(zé)任’,僅僅是去盯住意圖之火,例如反對社會制度不公正的抗議之火,不要讓它熄滅。他的行動目標(biāo),從可能的后果看毫無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燒。這種行為只能、也只應(yīng)具有楷模的價值”。馬克斯·韋伯.學(xué)術(shù)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108.
③韋伯認(rèn)為,“政治的決定性手段是暴力”,目的和手段的緊張關(guān)系,使得“在利用目的為手段辯護(hù)這個問題上,意圖倫理必定會栽跟頭,……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惡果者惟惡出之’,而是恰恰相反,任何不能理解這一點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馬克斯·韋伯.學(xué)術(shù)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108-110.
④“時空分離”,來源于吉登斯的《現(xiàn)代性自我認(rèn)同》,被吉登斯視為現(xiàn)代性的三種動力之一;“暈旋”是汪暉等人在《文化與公共性》一書中描述現(xiàn)代性時的用語。參見田海平.日常生活轉(zhuǎn)型與公共倫理意識[J].求是學(xué)刊,1999(4):18.
⑤學(xué)界之所以用“病家”之稱謂,就是因為參與診療的主體,不僅僅是病人自己,甚至病人的整個家庭都參與“擇醫(yī)”、“試醫(yī)”。
⑥為了呼應(yīng)“病家”之說法,這里根據(jù)學(xué)界現(xiàn)有的原則,筆者采用“醫(yī)家”之說法。
⑦在“關(guān)系取向”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形成的是一種內(nèi)向式強(qiáng)關(guān)系,即以各自的家族、宗族為單位的強(qiáng)關(guān)系,而在廣大的社會領(lǐng)域則是弱關(guān)系。弱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功利性與自愿性及個體的聯(lián)合與合作,強(qiáng)關(guān)系則強(qiáng)調(diào)義務(wù)和規(guī)范、以滿足內(nèi)部成員歸屬感和個體安全感為要的。參見:李林艷.弱關(guān)系的弱勢及其轉(zhuǎn)化——“關(guān)系”的一種文化闡釋路徑[J].社會,2007(4):187-188.民國時期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內(nèi)部關(guān)系顯然不屬于依靠家庭倫理來調(diào)節(jié)的強(qiáng)關(guān)系,而應(yīng)當(dāng)屬于依靠醫(yī)家與病家的醫(yī)病關(guān)系來調(diào)節(jié)的弱關(guān)系。
⑧民國時期的中醫(yī)師團(tuán)體,是中醫(yī)師個體以遵守公約宣言為基礎(chǔ),在理性參與的前提下將行業(yè)共同利益顯性化的結(jié)果。在此過程中,中醫(yī)師個體以讓渡自身部分權(quán)力意志的形式實現(xiàn)依公約宣言而行的職業(yè)自由。自成立之始,中醫(yī)師團(tuán)體就具有超越中醫(yī)師個體私利之性質(zhì),并具有一種超越具象生命的法的存在形式,其價值訴求是中醫(yī)師團(tuán)體的公共意志和公共理性。在此語境下,中醫(yī)師成員們以公約宣言為基礎(chǔ)來協(xié)商事宜、相互合作、采取行動,以維護(hù)中醫(yī)行業(yè)的共同利益。在這個過程中,中醫(yī)師個體要以限制自身權(quán)力意志為基礎(chǔ)來規(guī)范言行,使個體理性盡可能地接近公共理性,在摒棄同行相輕之陋習(xí)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公約宣言所規(guī)范的中醫(yī)師行業(yè)中的其他成員及其權(quán)利。這樣,中醫(yī)師團(tuán)體內(nèi)部便結(jié)成了交互主體之網(wǎng),達(dá)致共生共在之道德境遇、社會倫理之維度。
⑨以“隨訪患者”為例,現(xiàn)代醫(yī)生中保持這一重要的良好職業(yè)習(xí)慣者并不多見。“看病是一個過程,必須要隨診,適度提醒,開始怎么想的,后來發(fā)生了哪些變化,變化的根據(jù)是什么,從中找出原因。現(xiàn)在大家只是盯著結(jié)果,而不注重過程”,出身醫(yī)學(xué)世家、如今70歲高齡的心血管專家胡大一先生在談及母親對他行醫(yī)實踐的影響時說:“沒有電話的年代,我母親會把患者的地址記在本子上,患者不按時來,她就寫信去提醒。我現(xiàn)在記得,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都是地址,后來就變成了電話號碼,再后來又變成了手機(jī)號碼。她記不住我手機(jī)號碼,但是會記住病人的”。引自:安然.大醫(yī)胡大一:為醫(yī)患關(guān)系“點穴”[N].中國新聞周刊,2016-06-7(744).
⑩這大概是日本倉敷中央病院醫(yī)師教育研修部最近在中國網(wǎng)紅的主要原因。“他們改變了傳統(tǒng)筆試的入學(xué)考試規(guī)則,為年輕外科醫(yī)生設(shè)置了新的挑戰(zhàn),以此檢驗學(xué)生的實際技能。檢測包括三個環(huán)節(jié):15分鐘內(nèi)完成一只5mm的千紙鶴、15分鐘內(nèi)重新組合所給昆蟲、15分鐘內(nèi)在一粒米上制作壽司。這場地獄測試最終僅有5名學(xué)生勝出,而倉敷中央醫(yī)院也完美地制作出自己的宣傳片”。v_movier.日本外科醫(yī)生選拔要考這個?簡直喪心病狂![EB/O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w NTk0MA==&mid=2653036836&idx=1&sn=733027da7cb7d6255c9cc2cb8a665c32&scene=5&srcid=0507d0OcdN1d8Pfh4S kU6SAE#rd,2016-05-06/2016-06-13.
[1][德]馬克斯·韋伯.學(xué)術(shù)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
[2][美]T.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jié)構(gòu)[M].張明德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轉(zhuǎn)引自葉笑云.現(xiàn)代政治的困境及其“救贖”——析韋伯的政治家“責(zé)任倫理”思想[J].道德與文明,2013(2):93-94.
[3][瑞士]G.恩德利.意圖倫理與責(zé)任倫理——一種假對立(上)[J].王浩、喬亨利,譯.國外社會科學(xué),1998(3):13-17.
[4]葉笑云.現(xiàn)代政治的困境及其“救贖”——析韋伯的政治家“責(zé)任倫理”思想[J].道德與文明,2013(2):93.
[5]李喜英.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責(zé)任倫理基礎(chǔ)——約納斯責(zé)任倫理學(xué)的現(xiàn)代效應(yīng)[J].江蘇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2008(5):33.
[6][德]憂那思.技術(shù)、醫(yī)學(xué)與倫理——責(zé)任原則的實踐[M].張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7]甘紹平.憂那思等人的新倫理究竟新在哪里?[J].哲學(xué)研究,2000(12):55.
[8]田海平.日常生活轉(zhuǎn)型與公共倫理意識[J].求是學(xué)刊,1999(4):18-19.
[9]俞祖華、趙慧峰.清末新型知識群體:從傳統(tǒng)士大夫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轉(zhuǎn)型[J].人文雜志,2012.
[10]龔群.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職業(yè)及其倫理[J].孔子研究,2001(6):17.
[11]王敏.世醫(yī)家族與民間醫(yī)療:江南何氏個案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xué),2012.
[12]雷祥麟.負(fù)責(zé)任的醫(y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J].新史學(xué),1995(6).
[13]胡安邦.國醫(yī)開業(yè)術(shù)[M].胡氏醫(yī)室,1933.
[14]范守淵.范氏醫(yī)論集(下冊)[M].上海﹕九九醫(yī)學(xué)出版社,1947.
[15]Lei,Sean Hsiang-lin.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10-1949[D].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67.
[16]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y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6:252.
[17]GleasonP.IdentifyingIdentity:A Semant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83,69(4):910-931.方文.群體資格:社會認(rèn)同事件的新路徑[J].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8(1):89.
[18][加拿大]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xiàn)代認(rèn)同的形成[M].韓震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19]何昕.醫(yī)患關(guān)系視角下的傳統(tǒng)醫(yī)德倫理認(rèn)同研究[J].中州學(xué)刊,2014(4):109.
[20]丁福保.醫(yī)士之義務(wù)[N].中西醫(yī)學(xué)報,1910(1):7.雷祥麟.負(fù)責(zé)任的醫(y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J].新史學(xué),1995(6):70.
[21]尹倩.民國時期的醫(yī)師群體研究(1912~1937)——以上海為中心[D].華中師范大學(xué),2008.
[22]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
[23]哈維·戈德曼:自我的禁欲主義實踐[A].(德)哈特穆特.萊曼、京特.羅特.韋伯的新教倫理——由來、根據(jù)和背景[C].閻克文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24]鄧正來、景躍進(jìn).構(gòu)建中國的市民社會[A].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視角[C].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25]楊念群.近代中國研究中的“市民社會”——方法及限度[A].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視角[C].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26]趙志裕、溫靜、譚儉邦.社會認(rèn)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范例[J].社會學(xué)研究,2005(5):218.
王芳芳,中國人民大學(xué)哲學(xué)院與日本愛知大學(xué)國際中國學(xué)研究中心(ICCS)雙博士學(xué)位培養(yǎng)項目交換生。
中國人民大學(xué)“統(tǒng)籌推進(jìn)世界一流大學(xué)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專項經(jīng)費項目(15XNLG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