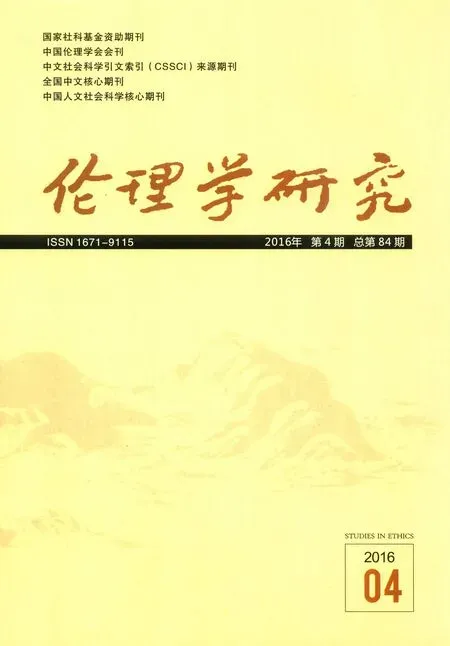論哈貝馬斯商談民主的德性之維
王軍
論哈貝馬斯商談民主的德性之維
王軍
自由主義強調私人的自主權利,主張通過公民選舉精英的民主模式來治理國家。在對個人自由的看護上,它寄希望于精英們的德性。相反,共和主義把民主視為一種整合社會的政治性組織,這種組織以全體公民的道德和倫理自覺為基礎。哈貝馬斯指出,自由主義賦予民主的規范性意義太弱,而共和主義賦予民主的規范性意義則太強,不具有事實上的生命力。據此,他提出了商談民主概念。商談民主是一種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對自由主義的私人自主權利保持開放,同時也積極吸納共和主義的公民道德和倫理主張。這種中立的德性姿態,使商談民主有效地調和了存在于自由主義、共和主義民主中的事實性與規范性之間的張力。
自由主義;共和主義;商談民主
托克維爾曾經斷言:“民主政府盡管還有許多缺點,但它仍然是最能使社會繁榮的政府”[1](P265)。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采取民主制度的西方社會普遍遭遇了貧富差距、維權運動、罷工游行等社會危機,民主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傳統的民主理論對此卻束手無策。在這種背景下,哈貝馬斯于20世紀末提出了商談民主①的概念,這種程序民主的理論一經提出,就立即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學界熱烈的探討,它也被視為西方民主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②不同于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的民主理論,哈貝馬斯指出,商談民主的核心是一個商談和談判的網絡,這個網絡使得有可能對實用問題、道德問題和倫理問題作合理的解決。[2](P395)但是,這個商談網絡本身具有何種性質與品格?或者商談民主應當具有何種德性?是像自由主義一樣認為民主僅有保障私人自主的工具性價值,還是效法共和主義將民主內化為一種公民道德和國家的生活方式?
廓清商談民主的德性維度十分必要,因為這關系到其制度構建的可能性與規范合法性。如果偏離自由主義太遠,商談民主就難以在復雜社會中建立起一套有效導控社會的合理機制,并且極易走向以自由主義為主流價值的現代西方社會制度的反面,其理論的現實說服力將大大縮減。反過來,如果完全拋棄共和主義的民主主張,商談民主則無法獲得公民個人的內心認同與來自社會的廣泛支持,從而造成規范空心化的尷尬,這種將合法性建立在沙灘之上的商談民主理論,勢必在突破規范性問題的道路上崩塌,淪為一種對現實的無聊辯護。哈貝馬斯看到了這一點,他主張,商談民主是一種中立性的民主程序[2](P375),它既對共和主義的道德綁架保持警惕,又防止自己滑向自由主義過分懷疑的深淵,它擁有一種中立的品質,持一種中立的德性態度,這種德性維度是在對自由主義民主和共和主義民主的德性批判的繼承上逐漸形成的。
一、自由主義民主與精英德性
自由主義者將人權擺在首要位置,他們認為,人權,也即人的基本自由和私人權益是國家和政府組織起來的目的。這種理論來源于洛克“有限政府”的經典闡述。洛克認為,人類在組成特定的政治社會時,放棄“為了保護自己和其余人類而為任何事情的權力”以及“處罰和執行違反自然法行為的權力”,但是,個人依然保有其余的自然自由,而且,政府的目的也在于保護個人的自由、安全、財產和公眾福利不受侵犯[3](P59,77-80)。這段被奉為“自由主義”
圭臬的古典論述表明,不同于共和主義將個人自由完全交給國家和政府,自由主義遵循個人自由不完全轉讓的原則,強調國家和政府只不過是個人與社會的“守夜人”。因此,自由主義從來不像共和主義一樣奢望公民能從靈魂深處對政府予以信任,相反,它極度珍視個人在私人生活領域內的自由,時刻提防“多數人暴政”的社會悲劇。基于此,在國家制度的建構上,自由主義表現得極為謹慎,它主張通過一種理性化的制度設計,由間接民主、政黨政治和公民選舉組成代議制政府來管理國家,這種理論在密爾的《代議制政府》中得到系統的闡釋。[4]可是,主張選舉少數精英來治理社會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雖然可以防止政府的擴張和暴政,但它有一種將精英與市民社會對立的傾向,甚至它在一開始就是精英式的。密爾就強調杰出的人士可以得到兩票的選舉權,而不會書寫的人則應當被取消選舉權,這顯然違反了民主就是“全體人民治理的全民政府”的樸素理念。
自由主義強調通過“代議制”政府來治理國家實際上意味著將國家的管理權交到精英手中,本質上,這種理論將政府的合法性寄托在少數政治精英的道德擔當和倫理上的自我約束。關于國家治理的具體方略,自由主義則認為,通過法治化的治理,即精英們的家長式立法,能夠確保對公民個人自由權利的保障。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這些主張,之后雖然被不斷修正,在“二戰”后以經驗主義、多元主義和經濟民主理論等不同的形式出現,但其核心觀點和基本原則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5]在哈貝馬斯看來,對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理解,必須放在特定的視域和假設上進行。首先,自由主義認為所有人平等并能夠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公民個人通過投票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選舉代表來治理國家,從而保護自己的基本權利。其次,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進一步假定,通過政黨之間相互競爭而組成的政府,從長遠來看,在有關社會利益之間或多或少是平等地分配的,個人權益能夠盡可能平等地得到滿足。個人的基本權利能夠得到保護并且等到平等滿足的假設,為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提供了最終的規范性、合法性基礎。
然而,隨著理論的不斷發展,自由主義民主“個人權利能夠被平等地滿足”的假設很快被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證偽了[6]。這主要是因為,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另一個假設,即個人利益訴求能夠得到合理表達并被尊重,在機制上是不可能的。在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下,選民將自我利益轉化為選票,而政治家則用特定的政策許諾來換取這些選票,合理的決策就建立在選民和政治精英之間的這種交易之中。因此,哈貝馬斯說,“根據自由主義觀點,政治本質上是一場爭奪人們可借以控制行政權力的職位的斗爭。決定公共領域和議會中政治性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是為保住或獲得權力職位而進行策略性行動的集體行動者之間的競爭”[2](P375)。在這種策略性行動和集體競爭的背后,主導政治決策過程的不再是公民個人的利益和權利,而是精英和團體之間的利益妥協。哈貝馬斯尖銳地指出:“既然利益團體的成員實際上是相當有選擇地組成的,是相當消極、對于團體政策的是影響甚微的,那么就假定,權力斗爭本質上是在精英之間進行的。”[2](P412)這種僅僅關注自身權力獲得的精英政治,使自由主義民主最終退化為“相互競爭的領導群體的國民選舉,也即選擇領袖”。因此,把個人利益轉化為選票的民主設計看似是公民個人訴求的自主表達,但實際上,通過普選、辯論和政黨政治等相關運作,民主制度淪為了精英才華的秀場。在這個秀場里,雖然公民的個人權益在口頭上是重要的,但是缺乏法律上的保障,而僅僅通過精英個人的道德義務和政治忠誠來兌現選舉口號往往難以實現對公民個人權利的最終維護。所以,在厭倦了精英們輪番登場的民主舞臺上,公眾普遍地缺席了,用哈貝馬斯的話說,他們以抗議投票和不參加投票的方式來表達其對民主制度的不滿,這就使得自由主義民主面臨基礎喪失和合法化取消的危險。[2](P413-414)
自由主義過分重視私人的自主權利,僅僅承認民主有保障公民個人自由的工具性價值,而且,在對這種價值的看守上,它寄希望于選舉出來的精英們的德性,即精英們的道德和他們自身的倫理約束。“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意見和意志的形成過程僅僅表現為不同利益之間的妥協。在此過程中,妥協原則得到了自由主義基本原理的證明,它們應當通過普選權、代議制及其運作程序來確保結果的公平。”[7](P286-287)但是,由于政黨政治在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導作用,利益妥協主要是在精英和政黨團體之間達成的,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個人權利在民主決策中的缺位。這表明,那種靠精英德性來保障私人自主權利的理想化設計最終導致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對立,自由主義民主的規范性、合法性被消解了。
二、共和主義民主與公民自覺
與關注私人自主的自由主義者不同,首先映入共和主義者眼簾的,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國家和社會,以及在這個社會中分享共同倫理價值的公民。共和主義認為,正如亞里士多德的名言所說,“人類自然是傾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8](P7),“我們確認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個人,就因為(個人只是城邦的組成部分),每一個隔離的個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必須共同集合與城邦這個整體(才能讓大家滿足其需要)。”[8](P9)因此,與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個人的私人自主權利相反,在共和主義看來,國家和社會才是政治的最高目的,雖然它在個人和家庭之后產生,但是,在本性上,它是先于個人和家庭而存在。與此同時,在國家和個人的關系上,共和主義強調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是國家的組成部分,二者相互融合,社會與國家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盧梭也指出,“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并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P20)這意味著,與自由主義強調權利的有限轉讓完全不同,共和主義認為是個人完全為共同體所吸納,不僅在政治上,也在道德上、倫理上,同時,這個共同體包含了社會的所有成員,它不允許個人游離在共同體之外,它要“強迫游離的個人自由”。
在民主的界定上,共和主義主張,公民的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構成了社會借以將自己建構為一個政治性整體的一種媒介,民主就等同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政治性自我組織。[2](P368)在共和主義看來,民主并不是一種利益的協調機制,它是政治共同體全體公民自覺的政治自決實踐,通過公民的集體意志做出決策。因此,共和主義所關心的,是國家如何才能變得更好,國家和集體公共善如何能實現的問題,而這種實現,與自由主義寄希望于精英的德性不同,共和主義強調公民的倫理自覺,即分享共同道德和生活價值觀的公民能夠在公共事務做出合理和統一的決策。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實,那么,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裂縫如何彌合?
針對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分裂的現實情形,以斯金納和佩迪特為代表的新羅馬共和主義求助于對“自由”概念的重構。從否定自由主義“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和傳統“自由”概念出發,斯金納和佩迪特分別提出了“第三種自由”,即“非支配自由”的概念。[10]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新的自由觀,將完成國家事務需要的“積極自由”與從事私人生活需要的“消極自由”協調起來,化解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但是,正如帕頓、拉莫等人批評的那樣,新羅馬共和主義對自由概念的重構,必須回到新雅典共和主義的傳統上去,強調公民的共同倫理生活和道德自覺,即“積極自由”;相反,如果他們模糊使用自由概念,將難以與自由主義進行區別,因而也不具有哲學上探討的價值與意義。[11]新羅馬共和主義希望通過一種綜合的自由觀來消解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對立的理想破產了。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仍然兩分的背景下,共和主義關于“公民自決”的民主理論根本無從構建,因此,新羅馬共和主義實際上并未涉及到對民主理論的深入探討。
對國家與市民社會對立的更重要的拯救,源自于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倫理傳統,這種傳統將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結合起來。亞里士多德強調,政治家應當研究德性,以使公民具有德性并服從法律,更進一步地,政治家還需要對人的靈魂的本性有所了解,以使我們能更好地追求人的善和人的幸福,因為善和幸福都與靈魂有關。[12](P32)這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公民對政治的認可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策略性選擇,而是發自靈魂深處的道德認同。通過公民這種自覺的倫理贊同,自由主義主張的國家與社會、公民與市民之間的對立被消解了,個人、社會和國家被統一起來,而民主就成為公民自決的政治行動,它以追求共同體的最高善為目標,是一種共同體全體公民對全體公民的決策建制。但是,哈貝馬斯批評道,以國家整體為中心的共和主義政治觀是一項認為國家可以超越有能力進行集體行動的全體公民的不合實際的假定。[2](P369)根據系統論,現代社會已經變成一個由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子系統構成的網絡,而且各自有其特殊的代碼,雖然它們之間不至于彼此隔離,并通過法律語言能夠實現各自的相互溝通,但是,那種根植于公民靈魂深處的共同倫理認同顯然已經失去了其實現的條件。另外,共和主義一直堅持對“至善”的追求,對人來說,至善是自我實現,也即,他愛護和滿足他的存在的最高部分,即有理性的部分,為高貴的動機所推動,促進別人的福利,為祖國服務。[13](P95)但是,為國家服務和利他的要求完全抹平了公民作為個體的自主利益,在利益多元和分化的現代社會往往很難實現。所以,雖然“公民自決”的共和主義的民主理論在合法性、規范性理念上具有頑強的說服力,可在現實制度建構面前,卻顯得力不從心。
從國家整體出發的共和主義,把民主視為一種整合社會的政治性組織,這種組織以全體公民的道德和倫理自覺為基礎,以實現國家的共同善為最高目標,通過公民大會、直接選舉等形式來保證公民的政治自決實踐。但現實中系統分化、價值多元的復雜社會,不僅瓦解了共同體公民的道德和倫理價值,而且使試圖通過公民大會、直接選舉來治理國家的方略也成為一種紙上談兵。共和主義的民主理論與主張,雖然能夠喚起公民內心深處對民主的贊同,但它必須由公民的倫理和道德自覺來保障,不關注個人的私人自主和權益,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而被作為一種理想束之高閣了。
三、商談民主:一種中立的德性維度
1.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視域下的商談民主概念重構
哈貝馬斯指出,商談民主是在批評與吸收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和共和主義民主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直言道,“在比較了不同的實質性規范的民主模式之后,我提出了一個程序性的民主過程概念。”[2](P358)商談民主理論,哈貝馬斯將之與“話語政治”相連,而“話語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實:它提供了一種對成問題的信念進行質疑的、可合理地論證的方式。”[14](P49)可以說,話語與商談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通過語言、論辯的方式達成共識,對爭議問題予以解決。值得注意的是,商談民主吸收了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雙方的元素,是一種調和性的理論,用哈貝馬斯的話說,“話語理論吸收了兩方面的因素,用一種理想的商談和決策程序把他們融合了起來。”[7](P286-287)哈貝馬斯進一步強調,“商談論賦予民主過程的規范性涵義,比自由主義模式中看到的要強,比共和主義模式中看到的要弱。”[2](P369)具體來說,商談民主的概念,應當從以下兩方面來把握。
首先,商談民主意味著一種高層次主體間性的交往。一方面,與自由主義強調對私人自主權利的不可通約性不同,商談民主主張通過交往把各個孤立的個體團結起來。也即在“高層次主體間性”去主體化的背景下,各種無主體的交往過程,往往能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討論問題的論壇和達成合理的意見的場所,進一步地,通過對這種討論和合意達成進行建制化,就能使得這種無主體的交往之流和交往權力轉換為行政權力,進而保障真實的共同利益和私人自主。[2](P371)而另一方面,共和主義認為民主是以國家整體為核心,由公民全體進行決策的政治性組織在商談民主看來也是不成立的。哈貝馬斯強調,與商談的民主理論相對應的社會觀是一種非中心化的社會觀,它放棄了主體性哲學的概念架構[2](P371),所以,強調國家中心和人民主權至高地位在這里并沒有被考慮進來。在高層次主體間性中,“人民主權不再體現在一種自主公民的有形聚集之中,它被卷入一種由論壇和議會團體所構成的可以說是無主體的交往循環之中。”[2](P168)通過這種交往循環,國家層面的整體考量被放到一個較低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被共和主義忽略的公民個人自主利益能夠和公共利益勾連起來并達致平衡。
其次,商談民主表現為人權和人民主權的相互統一。在論述人權與人民主權關系時,哈貝馬斯總結道:“私人自主性和公共自主性,人權和人民主權,是同源產生的,是互為前提的東西。”[2](P106)在人權和人民主權的價值選擇上,自由主義民主強調“人權”的重要性,認為民主制度不過是保障人權不受侵犯的工具;而共和主義民主則主張“人民主權”的至高無上性,它將民主界定為分享共同道德、倫理價值的公民共同體的政治自決機制。但在商談民主的視野中,人權與人民主權則是相互統一的,通過非中心化的交往,人權在意見形成或意志的形成過程中獲得真實的保護,人民主權則在交往程序的現實運作中得到真實實現。哈貝馬斯強調:“人民主權——即使它變成無人稱的東西——之所以退卻為民主的程序和對這些程序之高要求交往預設的法律執行,僅僅是為了使它自己被感受為交往地產生的權力”[2](P373),所以,商談民主認為,人民主權實際上是一種由法律建制化的交往權力,在這種交往權力中,“人權”并不被排斥,相反,個人自主權利通過交往能夠被充分尊重。這樣,通過商談、交往,分別為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民主所強調的“人權”和“人民主權”就被統一了,并在商談民主中得到協調。
2.商談民主的中立德性
不同于自由主義民主寄托于精英德性、共和主義民主強調公民倫理,作為一種調和性的政治理論,商談民主在本性和品質上保持一種中立的德性態度。哈貝馬斯強調:商談民主“突破了把國家當作中心的整體論社會模式,聲稱對彼此競爭的世界觀和生活形式是保持中立的”[2](P358-359)。這種中立,具體地表現為商談民主居于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間,并不偏向于“精英德性”、“私人自主”或者“公民倫理”、“國家中心”的任何一方,而是對二者都保持開放的姿態。
首先,商談民主的高層次的主體間性交往就意味著一種中立的姿態。一方面,它對公民個人的自主權利保持開放,而另一方面,非中心化的主體間關系取代了國家核心的價值導向。所以,在主體間性的交往中,精英被化為與大眾平等的交往主體,精英德性不再是商談民主關注的內容,而同時,非中心化祛除了對分享共同道德、倫理價值公民的依賴,道德、價值相異的個人與群體亦可以通過交往達成合理意見。
其次,商談民主的中立維度也體現在人權和人民主權的統一之中。將交往權力建制化的商談民主,一方面可以保證個人的自主權利被尊重,人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通過交往和論辯,共同的意見和意志得以形成,國家的共同利益能也夠得到保障。同時,寄托于精英德性的國家的治理將通過建制化的交往權力來完成,這顯然受到個人自主權利的約束,而強調由共同道德、倫理價值的公民共同體共同決策的民主概念,也將被化解在通過交往而達成的一次又一次的合理決策中。
商談民主的中立性姿態,使其能夠超越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固有的價值堅守與傾向,因而也就具有了更強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傳統民主理論已經無法解決現實危機的社會境況中。但是,商談民主這種既放棄個人自主權利的首要地位,又擺脫國家的中心作用的中立德性,遭到了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兩方面的反駁。
共和主義強調:“沒有一種據說中立的原則可能是真正中立的。每一種表面上中立的程序都反映了一種特定的有關好的生活的觀念。”[2](P383)而且,處于自由主義國家之中的中立程序也不能隱晦地服務于那些國家中的優先價值,不然的話,對具有其他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公民就是不公平的。哈貝馬斯指出,共和主義這種將中立原則當成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方式是站不住腳的。中立程序實際上是一種普遍的論辯規則,這條規則的目的在于保證發生分歧的各方能夠交談并解決問題,因此,它必須不屈從于任何一種倫理信念,以保證持不同道德態度的人能夠達成合理意見。
商談民主的中立性同樣為自由主義所質疑。自由主義擔心,商談民主向任何人想要提出的任何問題和任何論據都敞開大門,這必然會破壞對私人領域的法律保護,危及個人的人格完整。[2](P386)對此,哈貝馬斯澄清到,商談民主所涉及的討論議題確實是非常廣泛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私人領域的干涉,也就是說,私事可能在民主程序中被討論,但是這種討論僅僅是一種討論,要對其進行政治調節還必須符合一系列條件,而那時,它所涉及的范圍和對象已經不是私事了。所以,商談民主對所有的論題仍然持一種中立的開放態度,但這并不會干涉到私人領域的隱私和權益。
在商談民主的概念以及與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的辯論中,商談民主的中立態度得到了澄清。更重要的是,商談民主將這種中立德性根植在商談民主的雙軌制商談之中,對自由主義民主的規范性缺失和共和主義的事實上無力作了一個調和性拯救。
哈貝馬斯指出,“根據商談論,商議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決于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于相應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預設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協商過程與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2](P370)。他進一步強調:“商議性政治是在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不同層次上沿著兩個軌道進行的——一個是具有憲法建制形式的,一個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2](P388)。也就是說,在哈貝馬斯看來,商議民主是在兩個軌道上同時而且從不同方向上展開的。首先,具有憲法建制形式的民主程序,通過國家層面議會、政府或者法院中的交往、論辯程序的正式運作,達成民主決議,從上而下影響國家和社會。其次,不具有正式形式的意見形成與意志形成過程,由下而上,通過相互交往討論社會中的一些問題,形成公共輿論,進而形成共同合理建議,為國家所接受。前一種民主過程,可以看作是自由主義的程序制度,后一種合意的形成,則更符合共和主義的觀點。商談民主對這兩種程序同時保持中立和開放的姿態,并不倚重于其中的任何一種,對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進行了調和。
需強調的是,商談民主的中立性調和,合理地消解了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民主理論中各自存在的規范性與事實性之間的緊張。在雙軌制的商談背景下,具有憲法建制化的意見形成與意志形成過程,通過議會中固定化的民主論辯、商議形成民主決策。這種決策的動因與來源,在于普通公民在非正式化的交往論辯中產生集體建議或公共輿論,在此,公民個人的意見能夠進入國家決策的環節,契合自由主義的現實民主程序獲得了規范性意義。反過來,非正式的公眾交往形成的共同建議和合理主張,最終都會反映到正式的政治建構中,在議會中得到承認并形成決策,從而現實地影響整個國家。也就是說,一種在通過公眾交往而達成的共同決策,能夠在整個國家范圍內得到遵守與實行,在此,烏托邦式的共和主義民主主張獲得了真實的生命。
至此,在“精英德性”與“公民自覺”、“私人自主”與“國家中心”中持中立姿態商談民主,通過雙軌制商談以及交往程序的建制化,一方面,能夠使公民個人的利益與意見進入國家決策,消除了自由主義民主規范性缺失的尷尬;另一方面,則可以將共同建議與決策擴散至整個國家,解決了共和主義民主事實上無力與導控匱乏的難題。與此同時,居于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間的商談民主,融合了自由主義民主的事實性與共和主義民主的規范性,為自己尋找到了事實性與規范性上的支持與根據。
[注 釋]
①商談民主,英文為“Deliberative Democracy”,中文則譯為“商議民主、協商民主、審議民主”等概念,但考慮到哈貝馬斯主要強調的是商談論框架下,通過商議、協商、審議、談判等程序來達成對問題的共同決策或解決,因此,本文采用“商談民主”的概念。
②Stephen K.White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Rene von Schomberg&Kenneth Baynes,Discourse and Democracy: Essays on Habermas’s Between Norms and Fact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Erik Oddvar Eriksen & Jarle weigard,Understanding Habermas: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London& New York:Continuum,2003;高鴻鈞等著.商談法哲學與民主法治國[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王曉升.商談道德與商議民主[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鄭永流主編.商談的再思[M].法律出版社,2010.
[1]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童世俊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3]洛克.政府論(下篇)[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4]J.S.密爾.代議制政府[M].汪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5]劉鋼.超越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哈貝馬斯的程序民主[J].現代哲學,2004(3):46-53.
[6]朱德米.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興起[J].復旦學報,2001(3):107-113.
[7]哈貝馬斯.包容他者[M].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9]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0]昆廷·斯金納:“第三種自由概念”,應奇、劉訓練編.第三種自由[A].東方出版社,2006.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義:一種關于自由與政府的理論[C].劉訓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11]艾倫·帕頓.共和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M].《中西政治文化論叢》(第四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See,CharlesLarmore,“ACritiqueofPhilip Pettit's Republicanism”,in Social,Political,and Legal Philosophy:Philosophical Issues 2,ed.Ernest Sosa and Enrique Villanueva,Boston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1.
[12]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3]梯利、伍德.西方哲學史(增補修訂版)[M].葛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14]安德魯·埃德加.哈貝馬斯:關鍵概念[M].楊禮銀、朱松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王 軍,中共深圳市光明新區黨工委改革辦(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