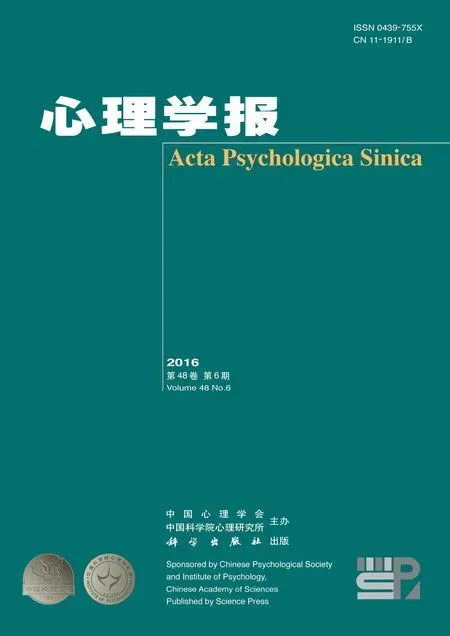互動公平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心理授權的中介作用與權力距離的調節作用*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1 引言
盡管中西方的哲學家和文學家對人類幸福的本質早有探討與描述,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對幸福感的研究才開始從哲學思辨走向實證科學之路,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Diener,1984;Ryan&Deci,2001)。尤其是近些年來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發展,使得學者們開始從積極的視角探討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等相關概念(Seligman,2002)。后來,隨著Luthans等為代表的學者們提出的積極組織行為學(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發展,使得對幸福感的研究擴展到了管理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Luthans,2002),組織中員工幸福感(employee well-being)的研究才逐漸受到更多的重視(Sonnentag&Ilies,2011)。
縱觀員工幸福感的研究,我們發現公平是與其密不可分的一個概念,在組織研究中,盡管已有學者從公平的視角來研究員工幸福感(e.g.,Cassar&Buttigieg,2015),但更多是從組織公平(organizational justice)這一整體構念來研究的,卻沒有進一步探討某種特定的公平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作用(Prilleltensky,2013)。這使得我們對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沒有深入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從管理實踐的角度來看,幸福的員工會有更好的績效和更低的離職率(Wright&Cropanzano,2004);員工幸福感可以降低職業倦怠感,提高工作效率,員工幸福感對組織的生存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Danna&Griffin,1999;Spreitzer&Porath,2012)。因此,以某種特定的公平為切入點來分析如何提高員工幸福感更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本研究將主要關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探討互動公平如何以及何時會影響員工幸福感。眾所周知,組織公平一般包括3種不同的公平類型,即與結果相關的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與資源如何分配相關的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以及在資源分配過程中人們人際交往時所感受到的互動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Colquitt,2001)。根據Greenberg(1993)提出的分類方法,前兩種屬于結構性公平,主要是指規章、制度、機制等方面的公平;而最后一種屬于社會性公平,主要關注的是個體在與他人相處的過程中或者在交換信息的過程中,所受到他人對待的公平程度(Ambrose,Seabright,&Schminke,2002)。由于幸福感本身就是一種人們在人際交往或交換關系中的情感體驗和感受,與交換關系密切相關(H?usser,Mojzisch,Niesel,&Schulz-Hardt,2010;Schmitt,Branscombe,Postmes,&Garcia,2014),因此,從定義上來看,互動公平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最為緊密。其次,相對于其他兩種公平來說,互動公平在組織中最為常見,是人們在組織中每天都要經歷的一種公平(Bies,2001,2005;汪新艷,2009)。而且實證研究也表明,在人們每天所經歷的不公平事件中,只有極其小的一部分可以被歸結于分配公平或程序公平,而絕大部分的不公平都是由于人際交往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對待所導致的(Mikula,Petri,&Tanzer,1990)。最后,相比起結構性公平(如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來說,社會性公平(如互動公平)更加可控,可以進行調整,從而對企業實踐更有意義(Ambrose,Schminke,&Mayer,2013;Loi,Yang,&Diefendorff,2009)。但是,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什么互動公平會影響員工幸福感?這種影響作用在什么情況下會出現?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值得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將主要以公平理論為主體,并結合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Deci&Ryan,1991)這一整體框架,探討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內在影響機制、以及這種關系成立的邊界條件。本研究主要有以下3點理論貢獻。首先,本研究從互動公平的視角探索了其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鑒于現有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公平的整體概念,很少關注某種特定的公平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并且,以往研究主要也是從結構性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視角出發,而忽略了更為常見的互動公平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擴展了現有的公平與幸福感關系的研究。其次,本研究以公平理論為主體,并結合自我決定理論(Deci&Ryan,1991),從心理授權的視角來分析互動公平影響員工幸福感的內部作用機制,這不僅闡明了互動公平為什么會影響員工幸福感,而且也進一步將相關理論和公平研究聯系起來,加深了我們對于公平與幸福感之間關系的理解(Prilleltensky,2013)。最后,本研究還基于公平作用效果的個體差異,進一步探索員工自身的權力距離這一個體的文化價值觀導向對整個作用機制的調節作用。這不僅系統地分析了互動公平通過員工心理授權進而影響員工幸福感這一機制的邊界條件,使得理論模型更加完整,而且也回應了學者們提出的應關注對個體權力距離的研究(Daniels&Greguras,2014)。
2 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2.1 員工幸福感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員工幸福感這一構念,并且對其定義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剛開始,一些學者將員工幸福感僅僅定義為一種工作上的心理與健康狀態,用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情緒耗竭、或工作壓力等相關概念來衡量員工幸福感(Katariina&Nurmi,2004;Kausto,Elo,Lipponen,&Elovainio,2005;Wright&Cropanzano,2004)。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以往的定義缺乏對工作情感部分的關注,于是采用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來衡量員工幸福感(Diener,Smith,&,Fujita,1995;Schaufeli&Bakker,2004)。隨后,一些學者提出,員工幸福感的定義過于狹窄,不能僅僅關注工作上的狀態,還應該關注非工作方面的所有心理感受與健康狀況。例如,Vanhala和Tuomi(2006)認為員工幸福感應該包含整體性幸福感、工作滿意度以及情緒耗竭;Ilies,Schwind和Heller(2007)則認為員工幸福感可以從個人和環境兩方面來考慮,并將這兩方面又分為工作面與非工作面;Lu,Gilmour,Kao和Huang(2006)將員工幸福感劃分為工作滿意度、家庭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和正向情感;而Diener及其合作者認為,員工幸福感還應該包括消極情感(Diener&Ryan,2009;Diener&Seligman,2002)。隨著討論的逐漸深入,員工幸福感的定義和內涵不斷得到擴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應該把員工的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工作滿意度和正負向情感進行有機整合(鄒瓊,佐斌,代濤濤,2015)。最近,Zheng,Zhu,Zhao和Zhang(2015)基于整合的視角,提出員工幸福感既是員工對工作層面與生活層面滿意程度的認知與感知,又是在工作層面與非工作層面所表現出來的情感的心理體驗和滿足狀態,主要包括員工生活幸福感、員工工作幸福感、以及員工心理幸福感這3個構面。另外,鑒于以往研究中測量工具的缺乏,Zheng等(2015)在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基礎上,開發了一個有效的測量工具,從而彌補了現有研究的不足。因此,本研究將采用Zheng等(2015)對于員工幸福感這一構念的操作性定義來進行相關研究。
2.2 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
在現有的幸福感研究中,組織公平是與其密不可分的一個概念(Cassar&Buttigieg,2015;Moliner,Martínez-Tur,Ramos,Peiró,&Cropanzano,2008)。組織公平主要是指員工在工作場所中所感知到的組織對待他們的公平程度(Greenberg,1990)。學者們將組織公平至少分為3種不同的類型,包括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以及互動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Colquitt,2001)。正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是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互動公平被定義為人們在組織中的人際交往過程中所感知到的被對待的公平程度(Bies&Moag,1986;Moorman,1991),主要是指決策者(如領導)用尊重的方式對待下屬(Baron,1993;Bies&Moag,1986;Cropanzano,Prehar,&Chen,2002),并給下屬提供充分的理由來解釋自己的行為(Bobocel&Farrell,1996;Shapiro,Buttner,&Barry,1994;Sitkin&Bies,1993)。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到互動公平在組織中的重要作用(Colquitt,Conlon,Wesson,Porter,&Ng,2001;Colquitt et al.,2013)。例如,Moorman(1991)的研究表明,互動公平能夠促進員工采取組織公民行為;Ambrose和Schminke(2003)的研究表明,互動公平能夠讓員工感受到組織的支持、對領導產生信任;而何軒(2009)的研究則主要關注了在中國的情境下,互動公平與員工沉默行為之間的關系。最近,朱其權和龍立榮(2012)則對互動公平的部分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進行了綜述,并認為互動公平的研究將帶來組織公平研究的第三次浪潮。
本研究認為,互動公平能夠提高員工幸福感。當員工感受到高水平的互動公平時,意味著員工在與領導的交往過程中得到了更多的信任、重視和尊重(Cropanzano et al.,2002),這些經歷會讓員工感覺到自己在組織中的重要性(Lind,Greenberg,Scott,&Welchans,2000),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積極的心理和情緒感知(Judge,Scott,&Ilies,2006;Loi et al.,2009),提高員工幸福感(Moliner et al.,2008)。相反,如果員工在與領導的交往過程中沒有得到足夠的信任和重視,甚至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員工就會覺得失去了尊嚴和歸屬感,從而降低積極的心理和情緒體驗(Tyler,1999),降低員工幸福感,甚至產生消極的情緒和態度(Tepper,2000,2007)。另外,互動公平不僅僅體現在人際交往過程中所受到的對待,還體現在領導是否就某一決策或程序向員工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解釋(Colquitt et al.,2001,2013)。如果領導能夠及時與員工溝通,向員工們解釋清楚做出某項決策的原因,那么員工不僅會認為領導非常真誠、公開、透明、值得信賴(Colquitt et al.,2001),也會感受到領導對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從而提高積極的心理和情緒體驗(Loi et al.,2009),提高員工幸福感。相對來說,如果領導在與下屬交往的過程中沒有對一些關鍵信息進行充分的解釋和說明,就會讓員工對領導或組織的信任度降低,并且有可能會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從而降低員工幸福感,甚至產生負向的情緒。與此同時,研究還表明,互動公平會影響員工在工作場所中所感受到的壓力(Judge&Colquitt,2004),從而影響員工幸福感。當員工所感受到的互動公平水平較低時,往往會覺得自己受到了排斥(Lind&Tyler,1988;Tyler&Lind,1992),體會到較大的壓力,對身心健康產生負向的影響作用(Fox,Spector,&Miles,2001;Kivim?ki et al.,2004;Tepper,2000),使得員工幸福感也較低。相比來看,高水平的互動公平可以被視為一種重要的資源,能夠讓員工積極地、從容地應對工作中的各種壓力和挑戰(Kausto et al.,2005),從而讓員工有較高的幸福感。綜上所述,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呈現正相關關系。
2.3 心理授權的中介作用
心理授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Spreitzer,1995)是衡量個體在工作場所中所體會到的一種綜合的心理感知,主要包括工作意義、勝任力、自主性和影響力這4個方面。工作意義主要是指個體根據自己的標準對工作目標的重要性或價值的判斷或認知(Thomas&Velthouse,1990);勝任力(或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于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項工作的認知(Gist,1987);自主性是指個體對于自己的行為或工作方式是否有控制權的認知(Deci,Connell,&Ryan,1989);影響力是指個體對于自己對組織戰略或管理工作的影響程度的認知(Ashforth,1989)。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影響心理授權的因素有很多,不僅僅來源于對工作任務本身的評價,也會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曾永青,2014)。根據公平的多元需求框架理論(multiple needs framework of justice;Cropanzano,Byrne,Bobocel,&Rupp,2001),員工與領導的交往過程中所受到的公平對待(互動公平)是影響心理授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Deci et al.,1989;Li,Wu,Johnson,&Wu,2012)。
公平的多元需求框架理論(Cropanzano et al.,2001)從個體基本的心理需求出發,提出公平會通過影響員工的內心需求進而對其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該理論主要討論了三方面的需求,包括:對外部環境的控制力的感知、在交換關系中所感受到的自我價值和影響力、以及體會到的自身的尊嚴和意義。因此,結合公平的多元需求框架理論和心理授權的基本內涵,我們認為,互動公平能夠滿足員工的心理需求,從而影響員工心理授權。具體來看,高水平的互動公平意味著領導在日常的管理中公平地對待員工,重視并尊重員工的意見;在做決策過程中也會充分考慮員工的利益,并且讓員工了解或參與決策的整個過程。這些行為會讓員工體會到自身的尊嚴,認為自己得到了尊重,并且感受到工作的意義(Leventhal,1980)。同時,領導對員工的意見的認可和尊重還會提升員工對外部環境控制力的感知,從而認為自己有能力完成相應的工作任務,對自己有更強的信心,也會感覺到自己在工作中有一定的控制權和自主性(Li et al.,2012;Tepper,Lockhart,&Hoobler,2001)。另外,領導讓員工直接參與到決策的過程中會讓員工在交換關系中感受到自身的影響力,并認為自己對組織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因此,從公平的多元需求框架理論(Cropanzano et al.,2001)的角度來看,高水平的互動公平能夠滿足員工的多元需求,提升員工在工作意義、勝任力、自主性和影響力方面的心理認知,從而提升員工的心理授權。相對來說,低水平的互動公平意味著領導在日常管理中沒有公平地對待下屬,不考慮員工的利益和意見,不讓員工了解或參與決策的整個過程,員工就會感覺自己的內在心理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在工作意義、勝任力、自主性和影響力方面的心理感知較低,從而有較低的心理授權。基于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互動公平與員工心理授權呈現正相關關系。
進一步來看,我們認為,當員工感受到較高的心理授權時,其幸福感也會隨之提升。這與自我決定理論(Deci&Ryan,1991)相一致。自我決定理論是幸福感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Deci&Ryan,1991;苗元江,朱曉紅,2009)。該理論認為,從本質上來講,個體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有機體,因此,對幸福感來說,內在需要的滿足比起那些物質、金錢等外在需要的滿足更為重要(Ryan&Deci,2000)。一般來說,決定幸福感的3種基本心理需要主要包括自主需要(autonomy)、勝任需要(competence)以及歸屬需要(relatedness)。自主需要是指個體要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定的控制權和自主性,能夠根據自己內心的意愿來選擇自己的行為;勝任需要是指個體要有能力去完成某項任務,有一定的影響力,并且受到大家的認可;歸屬需要是指個體要感覺到外部環境中的他人的關心、尊重和認同,從而體會到與群體之間的聯系(Ryan&Deci,2000)。基于現有文獻,本研究提出心理授權這一構念能夠從自主需要、勝任需要和歸屬需要這三方面來衡量員工的心理感知,并影響員工幸福感。
具體來講,當員工的心理授權水平較高時,員工會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項工作任務。同時,員工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也被授予了一定的自主性,能夠自己選擇或控制自己的行為或工作方式。并且,員工也會認為自己對于組織戰略或管理工作有重要的影響作用。這些心理感知都反映出員工的基本內在需要(即自主需要、勝任需要、歸屬需要)得到了滿足。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可知,員工幸福感會隨之得到提升(Patrick,Knee,Canevello,&Lonsbary,2007;Reis,Sheldon,Gable,Roscoe,&Ryan,2000;Sheldon,Ryan,&Reis,1996)。相反,如果員工感受到的心理授權水平較低,員工會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太大的意義,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完成工作的過程中自主性相對較低,并且對組織戰略或決策并不能產生較大的影響作用。這種情況下,員工的基本內在需要(即自主需要、勝任需要、歸屬需要)并沒有得到滿足,幸福感水平就會較低。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心理授權與員工幸福感呈現正相關關系。
從公平的多元需求框架理論(Cropanzano et al.,2001)的視角來看,當領導在與員工交往過程中充分尊重、重視員工,認可員工付出的努力,并在決策過程中聽取員工的意見或披露相關的信息時,員工的內在需求能夠得到滿足,在工作意義、勝任力、自主性和影響力這些方面的心理感知都會有所提高,有更高的心理授權。從自我決定理論(Deci&Ryan,1991)的視角來看,員工心理授權的提高表明其基本內在需要(即自主需要、勝任需要、歸屬需要)能夠得到滿足,從而會進一步提高員工幸福感。另外,自我決定理論也指出,個體內在需要的滿足是通過與外部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實現的(Deci et al.,1989;Deci&Ryan,1991;Ryan&Deci,2000;劉靖東,鐘伯光,姒剛彥,2013)。當外部環境給予了充分的支持(如互動公平)時,員工的內在需要(包括自主需要、勝任需要和歸屬需要)能夠得到滿足,從而影響員工的心理感知(心理授權),并進一步影響員工幸福感。因此,高水平的互動公平會提高員工的心理授權,并進一步提高員工幸福感。相反,如果領導與員工之間的互動公平水平較低,員工感知到的心理授權較低,內在需要得不到滿足,就會進一步降低員工幸福感。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2.4 權力距離的調節作用
互動公平通過心理授權來影響員工幸福感的這一機制有什么邊界條件呢?回顧現有的文獻可以發現,公平的影響作用并不是對每個人都會產生相同的效果,而是具有個體的差異性。研究表明,擁有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導向的個體對公平的敏感程度不同,會在心理上產生不同的感知(Kim&Leung,2007;Mueller&Wynn,2000)。其中,權力距離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價值觀導向,可能會影響個體對公平的敏感程度(Liu,Yang,&Nauta,2013)。基于此,本研究將主要探討權力距離對上述機制的調節作用。
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這一概念源于Hofstede(1980)對國家文化的研究,一般是指在一個國家或社會中,人們對不平等的權力分配的接受程度。在最初的研究中,權力距離主要關注的是國家或社會層面,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個體的權力距離這一文化價值觀導向的影響作用(Kirkman,Chen,Farh,Chen,&Lowe,2009;Lian,Ferris,&Brown,2012;Yang,Zhang,&Tsui,2010)。在個體層面,權力距離被定義為個體對于組織的、制度的、或社會的權力分配不均衡的接受程度(Clugston,Howell,&Dorfman,2000;Hofstede,1980)。權力距離越高,表明個體對權力分配不均衡的接受程度越高;相對來說,權力距離越低,表明個體對權力分配不均衡的接受程度越低。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由于個體自身對權力分配不均衡的接受程度不同,權力距離不同的個體對公平或不公平的敏感程度就不同,會在心理上產生不同的感知。具體來說,高權力距離的個體會接受權力的不均衡分配,把不公平視為理所應當,對公平或不公平更加不敏感;而低權力距離的個體會更加在意權力的均衡分配,無法接受不公平的對待,對公平或不公平更加敏感(Liu et al.,2013)。與此同時,不同權力距離的員工對于領導的行為和權威的認識和接受程度也會不同,這會使得在領導—下屬的社會交往過程中,即便領導表現出相同的行為,對不同權力距離水平的個體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作用(Ensari&Murphy,2003;Gelfand,Erez,&Aycan,2007;Tsui,2007)。研究表明,擁有高權力距離的員工可能并不會把領導不公平的對待視為冒犯或侵犯的行為,從而會產生較低的負向影響;而擁有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對權力的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程度更低,對領導不公平的對待更加敏感,反應更加劇烈(Brockner et al.,2001;Kirkman et al.,2009;Lian et al.,2012;Tyler,Lind,&Huo,2000)。另外,Farh,Hackett和Liang(2007)也指出,高權力距離的下屬對于領導行為的反應并不取決于領導如何對待他們,也就是說,領導是否以公平的方式來對待下屬,對高權力距離的下屬的心理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相對來說,低權力距離的下屬認為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因此,領導對待下屬的方式就會在更大程度上影響到員工。也就是說,領導是否用公平的方式來對待下屬,對低權力距離的下屬的心理會產生更加顯著的影響作用。
基于上述邏輯,我們認為,員工的權力距離會負向調節互動公平與員工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來講,他們對公平或不公平更加不敏感,且他們會認為領導應該有更大的權力,應該在做決策時不考慮員工的意見,因此,當領導與下屬的互動公平水平較低時,即領導并沒有尊重、重視員工,在做決策時也沒有充分地考慮員工的利益和意見時,高權力距離的員工更可能表現出理解和接受的姿態,其內心的需要并不會受到那么大的沖擊,心理授權也就不會受到那么大的負向影響。當領導與下屬的互動公平水平較高時,即領導會尊重、重視員工,充分考慮員工的利益和意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員工的內心需要,從而提高心理授權的水平。但是,由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對是否受到公平對待并不敏感,也并沒有那么在意權力的分配是否公平,領導是否公平地對待下屬,因此,對其心理授權的正向影響也相對較小。相對而言,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來講,他們對公平或不公平更加敏感,且他們也認為領導不應該有過多的權力,領導和下屬之間應該是平等的關系,領導應該尊重和重視員工。因此,當領導與下屬的互動公平水平較低時,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方式就會在更大程度上沖擊低權力距離員工的內心需要的滿足,從而大大降低其心理授權的感知;而當領導與下屬的互動水平較高時,由于低權力距離對公平更加敏感,領導對下屬的關心和重視就會在更大程度上滿足其心理需要,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該員工的心理授權。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5:員工的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這一關系對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強,而對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弱。
本研究的假設4提出了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在假設5中提出由于不同權力距離水平的個體對公平或不公平的敏感程度不同,會使得互動公平對心理授權的影響作用產生差異。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提出整合的被調節的中介模型,即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這一中介作用的大小取決于員工的權力距離水平。
對高權力距離的員工來說,他們能夠接受領導的權力更大,也愿意遵循領導做出的各項決策和安排(Chen&Aryee,2007)。他們對不公平的敏感程度更低,對不公平的接受程度更高(Kim&Leung,2007)。因此,與領導交往過程中的互動公平程度的不同,并不會顯著地影響這些員工對工作意義的判斷,對自身勝任能力的認知,對工作自主性的評價,以及對自身影響力的認識,對其心理授權的影響相對較弱,進而對其感受到的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也較弱。相對而言,對低權力距離的員工來說,他們更加重視與領導之間平等的交往,更加看重領導是否考慮或尊重他們的利益或意見(Chen&Aryee,2007)。他們對不公平的敏感程度更高,對不公平的接受程度更低(Kim&Leung,2007)。因此,對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他們與領導交往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互動公平的高低,即是否得到尊重,領導是否對決策給出了充分的理由和解釋,想法和意見是否被充分考慮或采納等,都會影響他們在工作意義、勝任力、自主性和影響力方面的判斷和內心需求,對其心理授權的影響相對較強,進而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也相對較強。綜上所述,我們提出以下被調節的中介作用假設:
假設6:員工的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心理授權對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關系的中介作用,表現為被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型。具體而言,這一中介作用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強,而對于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而言相對較弱。
圖1描繪的是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圖1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樣本與問卷收集過程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北方的一家制造型企業。該企業在日常運營中非常關注員工的幸福感,希望通過各項措施來提高員工幸福感,從而提高組織的績效。因此,本研究得到了該企業高層管理者的全力支持與配合。此次調研項目共邀請了489名一線員工參與其中。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的干擾(Podsakoff,MacKenzie,Lee,&Podsakoff,2003),我們共進行了3次問卷調研。在每次現場調研之前,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都為我們提供了參與調研的人員名單,以便我們進行編碼匹配等工作。同時,人力資源部每次都會通過內部信息網絡,提前把調研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通知到每位參與者,從而保證現場調研的有序進行。另外,為了提高數據的質量,研究者提前準備好了相應的問卷,直接帶到現場進行分發,并在被試填答完畢之后立刻收回裝箱。在被試填答問卷前,研究者向被試承諾所有數據的保密性,并強調數據的真實性對研究結果的重要意義。
在第一次調研時,我們邀請所有的一線員工(共489人)參與調研,請他們根據自己與領導交往過程中的真實感受和想法,對互動公平水平進行評價。此次調研共收回有效問卷376份,有效回收率為76.89%。兩個月以后,我們邀請所有參與第一次調研的員工(共376人)參與第二次調研,并請他們對自身的權力距離和心理授權進行評價。此次調研共收回有效問卷294份,有效回收率為78.19%。再過兩個月以后,我們邀請所有參與第二次調研的員工(共294人)參與第三次調研,并請他們對自身的幸福感進行評價。此次調研共收回有效問卷199份,有效回收率為67.69%。因此,3次調研最終成功匹配的問卷為199份,總回收率為40.70%。在征得被試允許的情況下,人力資源部為我們提供了被試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領導的共事時間。另外,為了檢驗樣本是否受到響應偏差的干擾,我們將只參與了第一次調研(82人)和3次調研均參加(199人)的被試進行對比之后發現,兩個樣本在人口統計特征方面并沒有顯著的差異,主要研究變量(互動公平)也沒有顯著的差異(t
(279)=0.21,n.s.
);我們也將參與了前兩次調研(95人)和3次調研均參與(199人)的被試進行對比之后發現,兩個樣本在人口統計特征方面沒有顯著的差異,其主要研究變量也沒有顯著的差異(互動公平:t
(292)=0.74,n.s.
;權力距離:t
(292)=0.17,n.s.
;心理授權:t
(292)=0.65,n.s.
)。總的來說,在最終的樣本中,78.40%為男性,93.00%的被試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水平的教育培訓,平均年齡為23.58歲(SD
=4.50),與領導的共事時間平均為1.19年(SD
=1.04)。3.2 測量工具
在調研之前,我們遵循標準的翻譯和回譯(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程序,把所有的英文測量工具準確地翻譯為中文(Brislin,1986)。除了特別說明,本研究一律采用7點Likert計分法(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互動公平:
我們選用了Moorman(1991)開發的6個題項的量表來測量員工與其領導交往過程中的互動公平。其代表性題目如“我的直接領導考慮我的觀點”“我的直接領導對各種決定提供及時的反饋”“我的直接領導對我很友好并為我著想”。在本研究中,其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2。心理授權:
本研究選用了Spreitzer(1995)開發的12個題項的量表來測量員工的心理授權。該量表包含4個維度,分別是工作意義(“我的工作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自我效能(“我對自己完成工作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工作自主性(“在決定如何完成我的工作上,我有很多的自主權”)、以及工作影響(“我對發生在本部門的事情有很大的影響力和作用”)。我們采用了5點Likert計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進行評價。在本研究中,其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5。權力距離:
與以往研究一致,我們選取了8個題項的量表來測量員工的權力距離(Earley&Erez,1997;Kirkman et al.,2009)。其代表性題目如“在大多數情況下,領導應該不咨詢下屬而做出決定”“員工不應該表達與領導不同的意見”“讓員工參與決策的領導會失去威信”。在本研究中,其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3。員工幸福感:
本研究中,我們采用了Zheng等(2015)開發的18個題項的量表來測量員工幸福感。該量表是在中國的情境中開發的,并且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它主要包括3個維度,分別是生活幸福感(“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工作幸福感(“總體來說,我對我從事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以及心理幸福感(“總的來說,我對自己是肯定的,并對自己充滿信心”)。在本研究中,其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3。控制變量:
在本研究中,我們控制了員工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與領導的共事時間(年)。4 研究結果
4.1 描述性統計與驗證性因子分析
表1報告了本研究中所涉及變量的均值、標準差、相關系數、內部一致性系數。從該表總結的數據中可以看出,所有變量的內部一致性系數都較高。同時,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這3個變量中兩兩之間都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我們的理論預期一致。
另外,我們運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技術評估了變量之間的區分效度。考慮到我們的樣本量較小,而測量的題項較多,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擬合指數的有效性。因此,我們遵循以往研究的處理方式(Williams,Vandenberg,&Edwards,2009),用心理授權的4個分維度分數和員工幸福感的3個分維度分數分別作為其觀察指標,同時按照題項?構念平衡法(item-to-construct-balance approach)將互動公平和權力距離的題項分別打包為3個指標,最后再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表2報告了假設模型以及其他5種替代模型的擬合指數。結果顯示,觀測數據與假設模型(四因子模型)之間的擬合度相對最好(χ(59)=104.68,RMSEA=0.06,CFI=0.97,TLI=0.95,GFI=0.93),而其他5種替代模型的擬合指數都明顯變差。具體來看,將權力距離和心理授權并入一個因子時,其擬合指數為χ(62)=386.53,RMSEA=0.16,CFI=0.75,TLI=0.69,GFI=0.76;將互動公平和心理授權并入一個因子時,其擬合指數為χ(62)=229.64,RMSEA=0.12,CFI=0.87,TLI=0.84,GFI=0.84;將互動公平和權力距離并入一個因子時,其擬合指數為χ(62)=391.28,RMSEA=0.16,CFI=0.75,TLI=0.68,GFI=0.76;將互動公平、權力距離和心理授權并入一個因子時,其擬合指數為χ(64)=515.43,RMSEA=0.19,CFI=0.65,TLI=0.58,GFI=0.70;最后,當把所有變量并入一個因子時,其擬合指數為χ(65)=783.96,RMSEA=0.24,CFI=0.45,TLI=0.33,GFI=0.61。上述結果表明互動公平、心理授權、權力距離、以及員工幸福感這4個變量之間有非常好的區分效度。

表1 均值、標準差以及變量間的相關系數

表2 模型的比較
4.2 假設檢驗
主效應檢驗。
假設1提出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呈現正相關關系。表3中模型5的結果顯示,互動公平對員工幸福感的正向影響顯著(β=0.17,p
<0.01)。因此,假設1得到了支持。假設2提出互動公平與員工心理授權呈現正相關關系。表3中模型2的結果顯示,互動公平對員工心理授權的正向影響顯著(β=0.11,p
<0.01)。因此,假設2得到了支持。假設3提出心理授權與員工幸福感呈正相關關系。表3中模型6的結果顯示,心理授權對員工幸福感的正向影響顯著(β=0.46,p
<0.001)。因此,假設3也得到了支持。中介效應檢驗。
假設4提出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表3中模型7的結果顯示,當加入心理授權后,互動公平對員工幸福感的正向影響作用從0.17(p
<0.01)減小為0.13(p
<0.05),而心理授權對員工幸福感的正向影響仍然顯著(β=0.41,p
<0.001)。根據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可知,心理授權部分中介了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另外,我們采取了Tofighi和MacKinnon(2011)的RMediation的方法對中介效應進行更加準確的檢驗。結果顯示,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的估計值是0.05,并且在95%的置信區間上顯著[0.01,0.08]。因此,假設4得到了支持。調節效應檢驗。
假設5提出員工的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為了更加準確地檢驗這一假設,我們根據Aiken和West(1991)的建議,首先將相關變量進行了中心化,從而降低多重共線性對結果的干擾。表3中模型3的結果顯示,此負向調節效應顯著(β=?0.07,p
<0.05)。此外,交互效應圖(圖2)和簡單斜率檢驗(simple slope test)的結果顯示:對低權力距離(低于平均值1個標準差)的員工來說,互動公平對心理授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β=0.18,p
<0.01);而對高權力距離(高于平均值1個標準差)的員工來說,互動公平對心理授權沒有顯著的影響作用(β=0.04,n.s.
)。因此,假設5得到了支持。
表3 回歸分析結果

圖2 權力距離對互動公平?心理授權關系的調節作用

表4 被調節的中介模型的分析結果
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假設6提出員工的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關系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運用Edwards和Lambert(2007)提出的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分析在不同權力距離水平下,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所起的中介作用的大小。該方法要求計算出5種不同情況下(即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的影響系數。這能夠使得模型估計更加清晰完整,并且能夠充分展示出調節變量具體的調節作用(Edwards&Lambert,2007)。表4的結果表明,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的間接效應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β=0.09,p
<0.01)和高權力距離的員工(β=0.01,n.s.
)這兩組的組間差異為0.08,達到了顯著性水平(p
<0.05)。因此,假設6得到了支持。為了進一步顯示心理授權的中介效應在不同的權力距離水平下的大小,我們將權力距離對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這一中介機制的調節作用展示在圖3中。如圖所示,當心理授權作為中介變量時,權力距離的水平越高,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越弱。另外,表4的結果也表明,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和高權力距離的員工,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一階段調節效應)存在顯著差異(Δβ=0.14,p
<0.05),進一步支持了假設5。
圖3 權力距離對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這一中介機制的調節作用
5 討論與結論
5.1 結果分析與理論貢獻
本研究旨在從互動公平的視角來研究員工幸福感這一重要構念,探索互動公平如何及何時會影響員工幸福感。通過對多時間點的數據的分析,本研究得到的結果主要包括:(1)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2)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3)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4)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互動公平通過心理授權進而影響員工幸福感的整個中介機制。對上述研究結果的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互動公平能顯著促進員工幸福感的提升。員工幸福感是員工對生活、工作、心理方面的滿意程度的主觀感受。幸福感較高的員工有更好的績效表現,更低的職業倦怠感,會主動為企業出謀劃策,因此,對企業的生存和長期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作用(Spreitzer&Porath,2012)。然而,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外部環境的競爭加劇,企業及其員工經受了巨大的沖擊和壓力(Lu,Kao,Siu,&Lu,2011;Siu,Spector,Cooper,&Lu,2005)。企業中充斥著壓抑、焦慮等負面情緒,使得員工工作投入下降、生產率降低、離職上升、甚至還頻繁發生跳樓等惡性事件。這不僅給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負面作用(Danna&Griffin,1999;Ilies et al.,2007),也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非常不良的影響。基于此,對員工幸福感的關注在我國的組織情境中顯得尤為重要。縱觀以往的研究,公平與幸福感是密不可分的兩個概念,目前也已經有研究探討組織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e.g.,Cassar&Buttigieg,2015)。但是,現有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組織公平這一整體構念,而對某種特定的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的探索仍然不夠(Prilleltensky,2013),這會使得現有研究過于局限,且無法深入了解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從公平的文獻來看,現有研究更多關注的是結構性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在組織中的作用(Colquitt et al.,2001,2013),卻忽略了人際交往過程中感受到的社會性公平(互動公平)對員工心理和行為的影響。考慮到員工幸福感本身就是一種人際交往過程中的情感體驗和感受(H?usser et al.,2010;Schmitt et al.,2014),且人們每天所經歷的不公平事件絕大部分是由于人際交往中的不公平所導致的(Mikula et al.,1990),因此,本研究認為,從互動公平的視角研究員工幸福感更為契合,關注員工幸福感這一話題在我國的組織情境中有重要的價值。同時,本研究還突破了現有文獻的關注點,將員工幸福感與互動公平相結合,探討并發現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結果不僅拓寬了員工幸福感與組織公平這兩方面的研究范圍,做出理論貢獻,也進一步推動了積極組織行為學的發展,促使更多的學者關注員工幸福感這一重要課題。
第二,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心理授權在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在明確了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之后,我們進一步探索這一關系背后的內在機制和心理過程。本研究以公平理論為主體,并結合自我決定理論(Deci&Ryan,1991),提出并發現心理授權是一種有效的傳導機制,將互動公平的正向影響傳遞至員工幸福感。由公平的多元需求框架理論(Cropanzano et al.,2001)可知,公平是通過影響個體的內心需求進而影響其態度和行為的。高水平的互動公平意味著個體對外部環境的控制力的感知、在交換關系中所感受到的自我價值和影響力、以及體會到的自身的尊嚴和意義都有很高的水平。這些內心需求的滿足會提升員工在工作意義、勝任力、自主性和影響力方面的心理感知,從而形成高水平的心理授權。進一步由自我決定理論(Deci&Ryan,1991)可知,當員工有高水平的心理授權時,員工的自主需要、勝任需要以及歸屬需要都會得到滿足,從而有高水平的幸福感(苗元江,朱曉紅,2009)。從自我決定理論的整體框架來看,員工在外部環境中與領導之間的互動公平會影響員工內部的心理授權,這一影響作用又會進一步影響員工幸福感。這一過程清晰地展示了互動公平影響員工幸福感的內在機制,并將組織公平和員工幸福感這兩部分研究通過心理授權有機地聯系在一起。與此同時,盡管在提出自我決定理論的早期,學者就運用該理論來預測幸福感(Ryan&Deci,2000),并且后來也有實證研究運用該理論的論述來做幸福感的相關研究(e.g.,Patrick et al.,2007),但是在國內關于自我決定理論的研究仍主要以論述類的研究為主,而實證研究卻相對較少(劉靖東等,2013)。因此,本研究對自我決定理論在中國人群的實際運用有著重要的貢獻。另外,本研究表明互動公平能夠提高員工的心理授權,這一結果不僅擴展了組織公平研究的影響范圍,也進一步擴展了關于心理授權前因的研究。
第三,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以及互動公平通過心理授權進而影響員工幸福感的整個中介機制。從公平理論的研究來看,公平效果存在個體差異,不同的個體對公平有不同的敏感程度。從以往文獻可知,擁有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導向的個體對公平的敏感程度不同,會在心理上產生不同的感知(Kim&Leung,2007;Mueller&Wynn,2000)。其中,權力距離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價值觀導向,可能會影響個體對公平的敏感程度(Liu et al.,2013)。基于這一考慮,我們進一步探索并發現權力距離對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起著負向的調節作用,對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這一中介機制也起著負向的調節作用。具體來看,對高權力距離的員工來講,他們對公平的敏感程度較低,因此互動公平的高低對他們的內心需求的影響都較小,對心理授權的影響較小,進而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也較小;而對低權力距離的員工來講,他們對公平的敏感程度較高,因此互動公平的高低變化會對他們的內心需求產生較大的影響,對心理授權的影響較大,進而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也較大。這一推論得到了數據分析結果的支持,如表4所示,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的間接效應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β=0.09,p
<0.01)和高權力距離的員工(β=0.01,n.s.
)確實存在顯著的差異(Δβ=0.08,p
<0.05)。另外,表4的結果也顯示,對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和高權力距離的員工,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一階段調節效應)存在顯著差異(Δβ=0.14,p
<0.05),而心理授權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二階段調節效應)并沒有存在顯著差異(Δβ=?0.22,n.s.
)。這些結果進一步表明,擁有不同文化價值觀導向的個體對公平的敏感程度確實不同,使得心理授權受到的影響不同,并最終體現為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也不同。綜上,本研究系統地分析了互動公平—心理授權—員工幸福感這一中介過程的邊界條件,并發現這種影響作用對低權力距離的員工更為有效,而對高權力距離的員工相對無效。這一發現拓展了組織公平與員工幸福感的相關研究,厘清了互動公平通過心理授權進而影響員工幸福感的這一機制的邊界條件。同時,由于整個中介機制是在自我決定理論的基礎上推導得出的,本研究的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我決定理論的應用是有適用條件的,對不同的個體所產生的影響作用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未來的研究在應用自我決定理論時也應該注意其適用范圍。另外,本研究也表明,從文化價值觀導向的角度來探索公平影響效果的個體差異是非常有意義的,能夠更加清晰地展示出不同情況下的具體影響作用,值得未來的研究進一步關注(Daniels&Greguras,2014)。第四,現有大部分對互動公平和員工幸福感的研究采用的都是橫截面數據,這會使得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擾(Podsakoff et al.,2003),影響實證結果的說服力。因此,從實證研究設計的角度來講,本研究的多時間點采樣設計所得到的結果更加可信,能為假設檢驗提供更加充分的證據,值得未來的研究參考借鑒(Colquitt et al.,2001,2013;Zheng et al.,2015;朱其權,龍立榮,2012)。
總的來講,本研究在理論方面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義:(1)以互動公平為出發點,為員工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Prilleltensky,2013),明確了互動公平這種特定的組織公平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作用,同時擴展了互動公平研究的影響范圍,也對組織公平理論有所延伸(Colquitt et al.,2013);(2)以公平理論為主體,并結合自我決定理論(Deci&Ryan,1991),從心理授權的視角分析了互動公平影響員工幸福感的內部作用機制,本研究有效地回答了“互動公平如何影響員工幸福感”這一研究問題;(3)從公平感知的個體差異角度出發,探索員工權力距離這一文化價值觀導向的調節作用,確定了互動公平影響心理授權以及互動公平通過心理授權進而影響員工幸福感這一中介機制的邊界條件,構建了更為完整的理論模型。
5.2 實踐啟示
本研究對管理實踐有著三方面的重要啟示。首先,研究結果顯示:領導與員工之間的互動公平對員工幸福感有非常顯著的影響。這表明,企業可以通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來提高領導與下屬之間的互動公平,從而提升員工幸福感。例如,企業可以定期開展培訓課程,讓領導在日常管理實踐中更多從員工的切身利益和內心需要出發,重視員工為企業的付出,尊重員工的個人意愿。另外,企業在制定人力資源政策時,也可以對領導下屬互動公平進行更多的關注和考評。其次,互動公平是通過心理授權來對員工幸福感產生影響的。所以,企業領導者應該關注員工的內在需求,在做決策時要多聽聽員工的意見和想法,從而增強他們的心理授權,提高幸福感。最后,本研究結果也表明,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對互動公平更加敏感。如果領導不能尊重、信任他們,他們的心理授權會受到更大的沖擊,幸福感也會更低。如果企業沒有管理好這部分員工,這些“負能量”很可能在組織中蔓延,從而最終阻礙企業的長期發展。因此,企業管理者應該更加關注擁有低權力距離的員工,給予他們更多的信任和尊重,這對于管理新生代員工有著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
5.3 研究局限與展望
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了解這些不足能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方向。第一,本研究在對現有研究的深入考察的基礎上,選取互動公平這一特定的組織公平概念出發,探討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對幸福感與公平的研究均有貢獻。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組織公平也包含分配公平和結果公平這兩種類型。為了進一步拓展公平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關注其他兩種特定的公平類型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亦或是將互動公平、分配公平以及結果公平都納入到討論的范圍,比較這3種不同的組織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關系的強弱。
第二,本研究以公平理論為主體,并結合自我決定理論(Deci&Ryan,1991)這一整體框架,進一步探索了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內在影響機制,有較強的理論貢獻。然而,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心理授權僅僅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結合其他理論視角(如社會交換理論),繼續探討互動公平影響員工幸福感的其他中介機制,從而進一步豐富現有的研究成果。
第三,本研究從公平感知的個體差異角度出發,提出并發現員工權力距離這一文化價值觀導向對整個中介機制的調節作用。然而,從公平的研究來看,公平的作用不僅有個體差異,也會受到外部情境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礎上考察相關的情境變量對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影響作用,如團隊公平氛圍(team justice climate)(Liao&Rupp,2005)、團隊權力距離(team power distance)(Yang,Mossholder,&Peng,2007)等。
第四,從自我決定理論的視角來看,決定幸福感的3種基本心理需要主要包括自主需要、勝任需要以及歸屬需要(Ryan&Deci,2000),這是本研究的核心理論基礎。然而,本研究并沒有對上述3種需要進行細化區分。因此,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進一步探索影響員工幸福感的主導需要是什么,不同內心需要對員工幸福感是否有不同的影響作用,是否會有交互影響,具體的影響方式和機制是什么?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五,本研究采取了與現有文獻一致的做法,關注的是員工幸福感這一整體的構念(e.g.,Zheng et al.,2015),然而從定義上來講,員工幸福感包含了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這3個構面。為了推動員工幸福感研究的縱深發展,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將這3個維度進行區分,研究特定的影響作用或機制。例如,互動公平是否會對這3個構面產生不同的影響作用?是否會有不同的內在影響機制?
第六,本研究主要關注了員工幸福感的前因部分,而沒有探索其結果部分。如今,我們都認為員工幸福感在組織中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但是我們尚不清楚它對個體的行為表現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作用。因此,在本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繼續探索互動公平影響員工幸福感之后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個體的行為表現(如任務績效、組織公民行為等)。這對員工幸福感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對組織管理實踐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最后,從方法的角度來看,本研究采用的是問卷調研的方法,可能無法為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提供充分的證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在多個時間點收集數據來檢驗我們的理論模型。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因果關系,并且有效解決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Podsakoff et al.,2003)。但是,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采用實驗法來探討互動公平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以此提高結果的內部效度。例如,研究者可以對互動公平水平進行操控(例如讓被試觀看不同的領導下屬交往過程的視頻),然后檢驗對被試心理授權和幸福感的影響作用,從而建立因果關系。
5.4 結論
本研究采用多時間點的研究設計,從互動公平的視角研究了員工幸福感這一重要課題,結果表明: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心理授權中介了互動公平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作用;權力距離負向調節了互動公平與心理授權之間的關系,以及員工心理授權對互動公平與員工幸福感之間關系的中介作用,表現為被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型。這些發現為推進員工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重要啟示。通過本研究可知,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應該公平地對待下屬,尊重員工的意見,考慮他們的內心需要和感受,這些行為不僅可以有效提升員工幸福感,而且能幫助企業在改善員工的心理健康、發揮員工的潛能、增進競爭力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
Aiken,L.S.,&West,S.G.(1991).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Ambrose,M.L.,&Schminke,M.(2003).Organization structure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interactional justice,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and supervisory trust.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8
,295–305.Ambrose,M.L.,Schminke,M.,&Mayer,D.M.(2013).Trickledown effects of supervisor perceptions of interactional justice:A moderated mediation approach.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8
,678–689.Ambrose,M.L.,Seabright,M.A.,&Schminke,M.(2002).Sabotage in the workplace: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njustic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89
,947–965.Ashforth,B.E.(1989).The experience of powerlessness in 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43
,207–242.Baron,R.A.(1993).Criticism(informal negative feedback)as a source of perceived unfairness in organizations:Effects,mechanisms,and countermeasures.In R.Cropanzano(Ed.),Justice in the workplace:Approaching fairnes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p.155–170).Hillsdale,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Baron,R.M.,&Kenny,D.A.(1986).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1
,1173–1182.Bies,R.J.(2001).International(in)justice: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In J.Greenberg&R.Cropanzano(Eds.),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justice
(pp.89–118).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Bies,R.J.(2005).Ar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nceptually distinct?In J.Greenberg&J.A.Colquitt(Eds.),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85–112).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Bies,R.J.,& Moag,J.S.(1986).Interactional justice: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In R.J.Lewicki,B.H.Sheppard,&M.H.Bazerman(Eds.),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pp.43–55).Greenwich,CT:JAI Press.Bobocel,D.R.,&Farrell,A.C.(1996).Sex-based promotion decisions and interactional fairness: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account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1
,22–35.Brislin,R.W.(1986).The wording and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instruments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Brockner,J.,Ackerman,G.,Greenberg,J.,Gelfand,M.J.,Francesco,A.M.,Chen,Z.X.,...Shapiro,D.(2001).Culture and procedural justice:The influence of power distance on reactions to voi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37
,300–315.Cassar,V.,&Buttigieg,S.C.(2015).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emotional well-being.Personnel Review,44
,217–235.Chen,Z.X.,&Aryee,S.(2007).Delegation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ediating processes in China.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0
,226–238.Clugston,M.,Howell,J.P.,&Dorfman,P.W.(2000).Does cultural socialization predict multiple bases and foci of commitment?Journal of Management,26
,5–30.Colquitt,J.A.(2001).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6
,386–400.Colquitt,J.A.,Conlon,D.E.,Wesson,M.J.,Porter,C.O.L.H.,&Ng,K.Y.(2001).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A metaanalyticreview of25 yearsoforganizationaljustice research.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6
,425–445.Colquitt,J.A.,Scott,B.A.,Rodell,J.B.,Long,D.M.,Zapata,C.P.,Conlon,D.E.,&Wesson,M.J.(2013).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a decade later:A meta-analytic test of social exchange and affect–based perspective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8
,199–236.Cropanzano,R.,Byrne,Z.S.,Bobocel,D.R.,&Rupp,D.E.(2001).Moral virtues,fairness heuristics,social entities,and other denizen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58
,164–209.Cropanzano,R.,Prehar,C.A.,&Chen,P.Y.(2002).Using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o distinguish procedural from interactional justice.Group&Organization Management,27
,324–351.Daniels,M.A.,&Greguras,G.J.(2014).Exploring the nature of power distance:Implications for micro-and macro–level theories,processes,and outcomes.Journal of Management,40
,1202–1229.Danna,K.,&Griffin,R.W.(1999).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kplace: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Journal of Management,25
,357–384.Deci,E.L.,Connell,J.P.,&Ryan,R.M.(1989).Selfdetermination in a work organization.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74
,580–590.Deci,E.L.,&Ryan,R.M.(1991).A motivational approach to self:Integration in personality In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1990: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
(pp.237–288).Lincoln,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Diener,E.(1984).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ical Bulletin,95
,542–575.Diener,E.,&Ryan,K.(2009).Subjective well-being:A general overview.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39
,391–406.Diener,E.,&Seligman,M.E.P.(2002).Very happy people.Psychological Science,13
,81–84.Diener,E.,Smith,H.,&Fujita,F.(1995).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affec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9
,130–141.Earley,P.C.,&Erez,M.(1997).The transplanted executive:Why you need to understand how workers in other countries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Edwards,J.R.,& Lambert,L.S.(2007).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Psychological Methods,12
,1–22.Ensari,N.,&Murphy,S.E.(2003).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attribution of charisma to the leader.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92
,52–66.Farh,J.-L.,Hackett,R.D.,&Liang,J.(2007).Individuallevel cultural values as moderator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employee outcome relationships in China: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distance and traditional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0
,715–729.Fox,S.,Spector,P.E.,&Miles,D.(2001).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CWB)in response to job stressors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Some mediator and moderator tests for autonomy and emotions.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59
,291–309.Gelfand,M.J.,Erez,M.,&Aycan,Z.(2007).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8
,479–514.Gist,M.E.(1987).Self-efficacy: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2
,472–485.Greenberg,J.(1990).Organizational justice: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Journal of Management,16
,399–432.Greenberg,J.(1993).The social side of fairness:Interpersonal and informational classe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InJustice in the workplace:Approaching fairnes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p.79–103).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H?usser,J.A.,Mojzisch,A.,Niesel,M.,&Schulz-Hardt,S.(2010).Ten years on: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job demand-control(-support)mode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Work&Stress,24
,1–35.He,X.(2009).Could interactional justice cure silence?An indigenous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oderation of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Management World,
(4),128–134.[何軒.(2009).互動公平真的就能治療“沉默”病嗎?——以中庸思維作為調節變量的本土實證研究.管理世界,
(4),128–134.]Hofstede,G.(1980).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CA:Sage.Ilies,R.,Schwind,K.M.,&Heller,D.(2007).Employee well-being:A multilevel model linking work and nonwork domains.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6
,326–341.Judge,T.A.,&Colquitt,J.A.(2004).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stress: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family conflict.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9
,395–404.Judge,T.A.,Scott,B.A.,&Ilies,R.(2006).Hostility,job attitudes,and workplace deviance:Test of a multilevel mode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1
,126–138.Katariina,S.A.,&Nurmi,J.E.(2004).Employee’s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and well-being at work.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17
,471–489.Kausto,J.,Elo,A.L.,Lipponen,J.,&Elovainio,M.(2005).Moderating effects of job insecurity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employee well-being:Gender differences.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4
,431–452.Kim,T.Y.,&Leung,K.(2007).Forming and reacting to overall fairness: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04
,83–95.Kirkman,B.L.,Chen,G.,Farh,J.-L.,Chen,Z.X.,&Lowe,K.B.(2009).Individual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and follower reactions t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A cross-level,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2
,744–764.Kivim?ki,M.,Ferrie,J.E.,Head,J.,Shipley,M.J.,Vahtera,J.,&Marmot,M.G.(2004).Organisational justice and change in justice as predictors of employee health:The Whitehall II study.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58
,931–937.Leventhal,G.S.(1980).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fairnes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In K.J.Gergen,M.S.Greenberg,&R.H.Willis(Eds.),Social exchange: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27–55).New York,NY:Plenum Press.Li,C.W.,Wu,K.K.,Johnson,D.E.,&Wu,M.(2012).Moral leadership and psychologicalempowermentin China.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7
,90–108.Lian,H.W.,Ferris,D.L.,&Brown,D.J.(2012).Does power distance exacerbate or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abusive supervision?It depends on the outcom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7
,107–123.Liao,H.,&Rupp,D.E.(2005).The impact of justice climate and justice orientation on work outcomes:A cross-level multifoci framework.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0
,242–256.Lind,E.A.,Greenberg,J.,Scott,K.S.,&Welchans,T.D.(2000).The winding road from employee to complainant:Situ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wrongfultermination claim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45
,557–590.Lind,E.A.,&Tyler,T.R.(1988).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New York,NY:Plenum Press.Liu,C.,Yang,L.Q.,&Nauta,M.M.(2013).Examining the mediating effectofsupervisorconflicton procedural injustice-job strain relations:The function of power distanc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18
,64–74.Liu,J.D.,Chuang,P.K.,&Si,G.Y.(2013).The applic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1
,1803–1813.[劉靖東,鐘伯光,姒剛彥.(2013).自我決定理論在中國人人群的應用.心理科學進展,21
,1803–1813.]Loi,R.,Yang,J.X.,&Diefendorff,J.M.(2009).Four-factor justice and daily job satisfaction: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4
,770–781.Lu,L.,Gilmour,R.,Kao,S.F.,&Huang,M.T.(2006).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work/family demands,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ellbeing:The Taiwanese vs British.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11
,9–27.Lu,L.,Kao,S.F.,Siu,O.L.,&Lu,C.Q.(2011).Work stress,Chinese work values,and work well-being in the Greater China.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51
,767–783.Luthans,F.(2002).The need for and meaning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3
,695–706.Miao,Y.J.,&Zhu,X.H.(2009).Self-decision theory and wellbeing research.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Natural Science Edition),4
,6–9,49.[苗元江,朱曉紅.(2009).自我決定理論及其幸福感研究.北京教育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4
,6–9,49.]Mikula,G.,Petri,B.,&Tanzer,N.K.(1990).What people regard as unjust:Types and structures of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injustic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
,133–149.Moliner,C.,Martínez-Tur,V.,Ramos,J.,Peiró,J.M.,&Cropanzano,R.(2008).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extrarole customer service:The mediating role of well-being at work.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7
,327–348.Moorman,R.H.(1991).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Do fairness perceptions influence employee citizenship?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76
,845–855.Mueller,C.W.,&Wynn,T.(2000).The degree to which justice is valued at the workplace.Social Justice Research,13,
1–24.Patrick,H.,Knee,C.R.,Canevello,A.,&Lonsbary,C.(2007).The role of need fulfillment in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92
,434–457.Podsakoff,P.M.,MacKenzie,S.B.,Lee,J.Y.,&Podsakoff,N.P.(2003).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8
,879–903.Prilleltensky,I.(2013).Wellness without fairness:The missing link in psychology.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43
,147–155.Reis,H.T.,Sheldon,K.M.,Gable,S.L.,Roscoe,J.,&Ryan,R.M.(2000).Daily well-being:The role of autonomy,competence,and relatednes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6
,419–435.Ryan,R.M.,&Deci,E.L.(2000).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social development,and well-being.American Psychologist,55
,68–78.Ryan,R.M.,&Deci,E.L.(2001).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emonic well-being.Annual Review Psychology,52
,141–166.Schaufeli,W.B.,&Bakker,A.B.(2004).Job demands,job resources,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burnout and engagement:A multi-sample study.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5
,293–315.Schmitt,M.T.,Branscombe,N.R.,Postmes,T.,&Garcia,A.(2014).The consequenc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A meta-analytic review.Psychological Bulletin,140
,921–948.Seligman.M.E.P.(2002).Authentic happiness: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
New York,NY:Free Press.Shapiro,D.L.,Buttner,E.H.,&Barry,B.(1994).Explanations:What factors enhance their perceived adequacy?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58
,346–368.Sheldon,K.M.,Ryan,R.,&Reis,H.T.(1996).What makes for a good day?Competence and autonomy in the day and in the pers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2
,1270–1279.Sitkin,S.B.,&Bies,R.J.(1993).Social accounts in conflict situations:Using explanations to manage conflict.Human Relations,46
,349–370.Siu,O.L.,Spector,P.E.,Cooper,C.L.,&Lu,C.Q.(2005).Work stress,self-efficacy,Chinese work values,and work well-being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12
,274–288.Sonnentag,S.,&Ilies,R.(2011).Intra-individual processes linking work and employee well-being:Introduction into the special issue.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32
,521–525.Spreitzer,G.M.(1995).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 workplace:Dimensions,measurement,and valid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8
,1442–1465.Spreitzer,G.,& Porath,C.(2012).Creating sustainable performance.Harvard Business Review,90
,92–99,152.Tepper,B.J.(2000).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3
,178–190.Tepper,B.J.(2007).Abusive supervision in work organizations:Review synthesis,and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Management,33
,261–289.Tepper,B.J.,Lockhart,D.,&Hoobler,J.(2001).Justice,citizenship,and role definition effect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6
,789–796.Thomas,K.W.,&Velthouse,B.A.(1990).Cognitive elements of empowerment:An"interpretive"model of intrinsic task moti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5
,666–681.Tofighi,D.,&MacKinnon,D.P.(2011).RMediation:An R package for mediation analysis confidence intervals.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43
,692–700.Tsui,A.S.(2007).From homogenization to pluralism: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0
,1353–1364.Tyler,T.R.(1999).Why people cooperate with organizations:An identity-based perspective.In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21,pp.201–246).Stanford,CT:Elsevier Science/JAI Press.Tyler,T.R.,&Lind,E.A.(1992).A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 in groups.In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25,pp.115–191).San Diego,CA:Academic Press.Tyler,T.R.,Lind,E.A.,&Huo,Y.J.(2000).Cultural values and authority relations:The psychology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cross cultures.Psychology,Public Policy,and Law,6
,1138–1163.Vanhala,S.,&Tuomi,K.(2006).HRM,company performance and employee well-being.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anagement Studies,17
,241–255.Wang,X.Y.(2009).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tructure and re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China.Management Review,21
(9),39–47.[汪新艷.(2009).中國員工組織公平感結構和現狀的實證解析.管理評論,21
(9),39–47.]Williams,L.J.,Vandenberg,R.J.,&Edwards,J.R.(2009).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anagement research:A guide for improved analysi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3
,543–604.Wright,T.A.,&Cropanzano,R.(2004).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job performance:A fresh look at an age-old quest.Organizational Dynamics,33
,338–351.Yang,J.X.,Mossholder,K.W.,&Peng,T.K.(2007).Procedural justice climate and group power distance:An examination of cross-level interaction effect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2
,681–692.Yang,J.X.,Zhang,Z.X.,&Tsui,A.S.(2010).Middle manager leadership and frontline employee performance:Bypass,cascading,and moderating effects.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7
,654–678.Zeng,Y.Q.(201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Journal of Jiangsu Teach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
,57–63.[曾永青.(2014).心理授權研究綜述.江蘇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
,57–63.]Zheng,X.M.,Zhu,W.C,Zhao,H.X.,&Zhang,C.(2015).Employee well-being in organizations:Theoretical model,scale development,and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36
,621–644.Zhu,Q.Q.,&Long,L.R.(2012).Interactional justice:A critical review and its future agenda.Management Review,24
,101–106.[朱其權,龍立榮.(2012).互動公平研究評述.管理評論,24
,101–106.]Zou,Q.,Zuo,B.,&Dai,T.T.(2015).Happiness at work:Definition, measurement levels and causal model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3
,669–678.[鄒瓊,佐斌,代濤濤.(2015).工作幸福感:概念、測量水平與因果模型.心理科學進展,23
,669–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