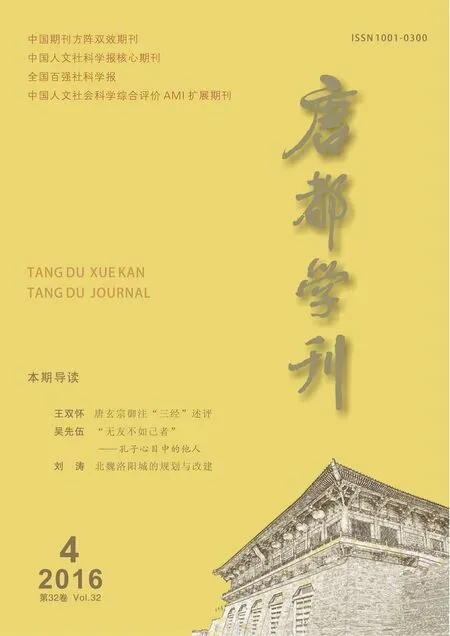王船山對張載“太虛即氣”本體論議題的承續與開新
陳力祥, 王志華
(湖南大學 岳麓書院,長沙 410082)
?
【關學研究】
王船山對張載“太虛即氣”本體論議題的承續與開新
陳力祥, 王志華
(湖南大學 岳麓書院,長沙410082)
王船山以張載為宗師,“希橫渠之正學”,其哲學思想是張載哲學思想的延續與價值開新。以“太虛即氣”為議題,由張載之“太虛即氣”到船山之“太虛一實”,由張載之“氣化”到船山“氣之化也”,彰顯出船山哲學本體論對張載哲學本體論的承續。由船山氣之化的差異性導致宇宙萬物的層級性,彰顯出船山對張載之超越。
張載;王船山;氣;本體;太虛即氣
王志華,男,山西臨汾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宋明理學研究。
船山哲學乃是張載哲學基礎上的正學與開新,學術界已成定論。如嵇文甫先生認為船山“宗師橫渠,修正程朱,反對陸王”[1];船山兒子王敔在其所作的《大行府君行述》中這樣來概括他父親船山的學術淵源:“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說,則參伍于濂、洛、關、閩,以辟象山、陽明之謬,斥錢、王、羅、李之妄。”[2]73船山在自撰的墓志銘中也明確說道:“希張橫渠之正學。”而且船山在晚年于67歲完成了《張子正蒙注》一書,又于72歲進行了修定[3]283,可見其對張載的推崇。清人鄧顯鶴評論船山說:“生平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而原本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為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捄來茲之失。”[2]410足以說明船山對張載之學的正學與開新。
一、由表入里:從張載之“太虛即氣”到船山之“太虛一實”
船山對張載氣本論思想的繼承與發揮主要體現在他的《張子正蒙注》一書,此書由船山通過對張載《正蒙》做注而成。在張載的整個思想體系中,“太虛”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范疇。“事實上,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張載之標舉太虛,亦有獨特之地位。”“張載之前,沒有思想家以‘太虛’做為其思想體系的重要概念。所以,張載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位以太虛作為重要概念的思想家。”[4]59因為張載堅持氣本論,所以“太虛”一詞經常與“氣”連用,比如在《正蒙·太和》中就提到:“虛空即氣”[5]8。張載乃氣本論者,與宋明理學的主流理學觀或心學觀不同,雖然這是學界的共識,但對張載氣本論的解讀卻并不一致。出現這種分歧的關鍵在于對“即”字的理解:一種觀點把“即”理解為“是”,那么“虛空即氣”也就可以理解為“虛空是氣”。“虛空”“太虛”雖然是氣,但卻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所說的氣,而是“氣的本來存在狀態,他稱這本然狀態為本體”。我們一般意義所說的氣“不過是這種清稀微細的太虛之氣凝聚而成并可以看到象狀的暫時形態”[6]。另一種觀點把“即”理解為“不離”之意,牟宗三先生就堅持這種解讀,他在《心體與性體》一書中說:“‘虛空即氣’,順橫渠之詞語,當言虛體即氣,或清通之神即氣。此‘即’字是圓融之‘即’,不離之‘即’,‘通一無二’之即,非等同之即,亦非謂詞之即。”[7]牟先生之所以堅持如此解讀,因為在他看來,只有把“即”理解為“不離”,才可以避免張載哲學的唯氣論傾向[4]141。而如果一旦把張載哲學理解為唯氣論的哲學,在牟先生看來,價值也就無法得到安頓。
對張載“虛空即氣”之氣本論的解讀大體呈現為以上這兩種觀點,那么船山對張載“虛空即氣”之氣本論的解讀又是如何呢?只有通過對比解讀,才能進一步彰顯船山對張載“虛空即氣”之氣本論解讀的獨特性。船山明確說道:“太虛,一實者也。”[8]402“人之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8]30首先,船山在這里用了“太虛,一實者也”、“太虛者,氣也”的句式,這種句式在古代漢語中就是要明確表示一種主謂關系,說明“太虛”是一種實(在),這種實(在)不是別的,就是氣。其次,“虛涵氣,氣充虛”并不是說“虛”作為空間包涵著“氣”、“氣”作為物質充滿著“虛”,而是對張載原文“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所作的注,所以應該理解為“虛”作為本體始終涵攝著“氣”,“氣”作為運動的物質(之用)不斷擴充著“虛”(之體)。“散而歸于太虛,復其缊之本體,非消滅也。聚而為庶物之生,自缊之常性,非幻成也。”[8]19因為這句話是對“氣之為物,散入無形”原文的注,顯然是說“氣”返歸于“太虛”,意味著又回到了它缊的本體狀態,不是如道家所說的消失與滅無;而當“氣”聚為萬物時,也就必然會將其缊的性實實在在地賦予萬物,不是如佛家所說的皆是幻象。從這一角度來講,“太虛”或者“太虛之氣”就是指“氣之清虛至極的狀態”[4]66,“太虛”終歸還是“氣”。
船山從“體—用”的角度說明了太虛與“氣”的關系*此處的“氣”包括由“太虛”而凝聚的氣以及由氣而凝聚的萬物兩部分,相對于“太虛”之“體”而言,無論是“氣”還是萬物,都是一種“用”。。“聚而成形,散而歸于太虛,氣猶是氣也。神者,氣之靈,不離乎氣而相與為體,則神猶是神也。聚而可見,散而不可見爾,其體豈有不順而妄者乎!”[8]23無論是“氣”聚而成物,還是散而歸于“太虛”,作為最根本的“氣”始終沒有發生改變。作為“氣之靈”的“神”隨著“氣”的聚散也始終與氣相為體用而時刻在起作用,對于可見的物是如此,對于不可見的虛氣也是如此。所以船山才會接著在后一條注文中說:“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神化者,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然而有跡可見。”[8]23我們感官所能感覺到的一定是變化所留下的“痕跡”,“痕跡”的所以然也即是“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神化”),雖然不能為感官所捕捉到,但其同樣也是“順而不妄者”,因為體—用的一致性必然要求“虛氣”不二。氣聚成物為顯,稱其為“有”;物散歸氣為隱,稱其為“無”。但船山一般不喜歡用“有—無”而是用“顯—隱”來說明這種體—用關系,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他反對道家“無中生有”與“有化為無”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他徹底堅持氣本論的必然結果,“氣”才是宇宙得以永恒的最終維系者,“其(引者按:指氣)聚而出為人物之形,散而入于太虛則不形,抑必有所從來”[8]23。“抑必有所從來”說明了氣化的根據,也就引出了頗為關鍵的一個問題:既然太虛是氣,是否二者之間就不存在著區別呢?“太虛即氣,缊之本體,陰陽合于太和,雖其實氣也,而未可名之為氣;其升降飛揚,莫之為而為萬物之資始者,于此言之則謂之天。氣化者,氣之化也。陰陽具于太虛缊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蕩……”[8]32太虛雖然是氣,但卻是一種作為缊的本體之氣。嚴格來講,太虛還不可以被命名為氣,因為只要言氣就已經落到了物的層面。從狹義上來說,可以認為太虛只是氣化(為萬物)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也可被稱之為“太和”。“太和”之中具有陰陽二氣以及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蕩”的作用,這種二氣交感的作用正體現了宋儒所說天道之生生不息的生命狀態,不是有意為之于萬物的蓬勃,但卻又可以造就萬物的生死輪回。“天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5]63天不息地賦予萬物以性,萬物又無時地循當然之則相感。就此一層意義來講,“太虛”又可名為“天”。毫無疑問,船山的這一思想正是對張載“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5]9之思想的繼承與展開。“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其聚而出為人物之形,散而入于太虛則不形,抑必有所從來。”[8]23虛空、太虛既然作為本體的氣,也就意味著必然要化生萬物。船山稱氣聚為物為顯,稱物散為氣為隱,隱顯交替顯示出太虛本身氣化的復雜環節。“升降飛揚,乃二氣和合之動幾,雖陰陽未形,而已全具殊質矣。‘生物以息相吹’之說非也,此乃太虛之流動洋溢,非僅生物之息也。”[8]27氣化一系列的復雜環節顯示了太虛作為本體的巨大生命力與創造力。太虛之中蘊含著二氣生化的微妙征兆(“二氣和合之動幾”),雖然還沒有顯露出明顯的陰陽功能,但已經具備了造化的全部殊質。為了說明此種問題,船山還批評了莊子“生物以息相吹”的說法,認為這不僅僅只是局限于生物的相互吹息,同時也是整個太虛內部流動洋溢的狀態。“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9]1044太虛本身是運動不息的,從無停滯。作為氣的太虛,尤其又是作為宇宙本體的太虛,里面充滿了渾淪的陰陽之氣,“陰陽異撰,而其缊于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8]5。陰陽之氣因為功能、性質的差異(“陰陽異撰”),二者缊于太虛之中,屈伸往來,相摩相蕩,異質而同趣,歸一而分殊,彌綸于太虛、萬物之中,天地、宇宙之間(“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既是一種宇宙原初的和諧,也是萬物最終所要達到的最高和諧。整個大秩序的順理無妄有條不紊,一方面固然需要有湛然清通的本體太虛之氣,一方面也需要有神妙精微的氣化過程。船山的本體太虛之氣,太虛之氣猶如江河的源頭,想要真正展示這一源頭的活力與能量,就必須呈現江河的全幅景觀,在這里也就是要把神化之氣氣化的整個過程揭示出來。
二、由淺入深:從張載之“氣化”到船山“氣之化也”
“船山把宇宙演化分為兩個基本的階段,即變合以前的氣體階段與變合以后的氣化階段,氣體即氣之體,亦即氣之實體、氣之本體。”“氣化即氣之用,在氣化階段陽變陰合,生成萬物。”[3]189,189-190船山對張載“虛空即氣”之氣本論的解讀其實就是在討論變合以前的氣之實體,明確了這一點,也就可以進一步討論船山的“氣化”思想,即氣化過程中生成萬物的問題。
船山首先指出:“氣化者,氣之化也。”[8]32“時行物生,不窮于生,化也。”[8]80時節運行萬物產生而又不窮盡于生就是“化”。“萬有之化,流行成用。”[9]979萬有法象的生生不已,正是天道流行以成其妙用的體現。所謂的“氣化”,歸根到底就是“氣”的一種作用表現,船山的這個思想顯然是對張載“氣化”思想的繼承與展開。所以這里就有必要先討論一下張載對“氣化”的闡釋:“天道四時行,百物生。”[5]13“道”對張載而言,就是“氣化”,上面曾引述過他的一條表達:“由氣化,有道之名。”“化”是與“變”相對而言的,“變,言其著;化,言其漸”[5]70。“變”揭示的是一種明顯的改變,“化”則暗示著一種不明顯的變化,二者之間的區別只在于顯隱的不同,在于人是否可以用感官來把握。感官可以體會到四時的運行與百物的生生,但卻不能察知到這種運行的不息之處與生生的流行之處。天道之“化”雖難以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并不妨礙其本身作為“氣”的功能形態而發生作用,因此張載說道:“天之化也運諸氣。”[5]16太虛(“由太虛,有天之名”)之化的作用完全是氣的運行與擴展而已。實際上,在張載看來,“氣”—“化”的關系正是一種體用關系的呈現,“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于氣而已”[5]15。單看這里的論述,似乎是在說德體道用,但只要將“德體道用”的思維往前推論,就會不難得出“神體化用”的結論。在張載的體系中,“神”始終是與“天”“不測”“一”相聯系的,而這三者在根本上又是一而不二的,我們可以看一下他下面的幾條論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5]16“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5]9鬼神就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之妙合變化的良能,這一功能就“天”的意義上來講被稱之為“神”。因為陰陽二氣的作用總是精妙細微的,無法明顯地捕捉,但其作用卻是顯而易見并且是遵循法則而有常,所以才說:“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5]14但“神而有常”之所以可能的根本保證卻在于“一”。“氣有陰陽,推行有漸有化,合一不測謂神。”[5]16這里明確提到“合一不測謂神”,陰陽之氣的漸化推行,只能說是不測的妙用,但這種妙用之所以顯示出“神”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合一”,“合一”就是“一于氣而已”。“神”“化”與“一”在張載的思想體系中是很重要的哲學范疇,關于它們之間的關系他的論述比較多,我們可以再看兩則經典的表達:“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5]10“若一則[有兩],有兩亦[一]在,無兩亦一在,然無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5]233此處的討論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氣(之體)”的層面,也就是終極本源的問題,除了氣的存在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存在。一個層面是“氣化(之用)”的層面,就在“兩化(之用)”過程中始終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一(之體)”而言,即“神”;就“一(之體)”的作用必須展開為“兩化(之用)”而言,即“化”。“一”(體)之“神”與“兩”(用)之“化”合而言之就構成了天之“參”*“參”字既可讀作“參加”之“參”(cān),也可讀作數字之“參”(叁)(sān),行文此處讀作數字之“參”,這樣與“兩”相互一致,比較符合張載思想的原意。。但實際上,天并不真的就顯示出是“參”,而自始至終都是“氣”而已。以上通過對張載氣化思想的考察,大體可以得出船山“氣化者,氣之化也”的思想是對張載氣化思想的繼承。
以上述張載“氣化”思想的理解作為基礎,下文再來看船山本人對“氣化”的承續。船山之“氣化”有兩大特點:一是側重于論“氣”的材質性,即作為構成萬物的質料,注重一貫動態的整體呈現;一是側重于“化”的類別性,即在萬物之化中有物之化與人之化的區別,注重靜態結構的細微分疏。先看他從“氣”之材質性的角度對氣化的論述。“天之所以為天而化生萬物者,太和也,陰陽也,聚散之神也。”[8]369“而”字在此處不宜被理解為表示并列關系的連詞,而是同《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10]一句中“而”字的用法一致。天之所以為天就在于天能夠化生萬物,而天之化生萬物的根據則是太和、陰陽與天之聚散的德性(張載原文:“神,天德。”)。三者之中,“太和”又是“陰陽”與“聚散之神”的根本。“天無體,太和缊之氣,為萬物所資始,屈伸變化,無跡而不可測,萬物之神所資也。”[8]50“資”就是依靠,依據,主宰。“天”本身就是作為體而存在的,也就是“太和缊之氣”,它是萬物之存在所依靠的根據(“所資始”),也是萬物之變化神妙的主宰(“所資”)。“陰陽者,二氣缊,輕清不聚者為陽,雖含陰氣亦陽也;其聚于地中與地為體者為陰,雖含陽氣亦陰也。凡陰陽之名義不一,陰亦有陰陽,陽亦有陽陰,非判然二物,終不相雜之謂。”[8]57陰陽之作用的體現就是陰陽二氣缊的結果。實際上,陰陽只是表示兩種不同性質的力量,作為存在層面的“氣”來講,并不存在著陰陽兩種不同性質的氣(“非判然二物,終不相雜之謂”)。陰陽二氣通常是渾淪無間的,否則就不可能發揮出太和缊的效果。“五行之化氣合離融結,彌綸于地上,而與四時之氣相為感通,以為萬物之資,是亦天地陰陽相交之所成也。”[11]562太和缊的陰陽二氣進一步聚為五行之氣與四時之氣,五行之氣充滿天地之間,又與四時之氣相感通相生生,成為萬物得以形成的直接質料。從太和缊之氣、陰陽二氣到五行之氣、四時之氣,再到萬物的產生,這一過程就被稱之為“氣之化”。“化者,天地生物之事。”[8]355“天以神御氣而時行物生。”[8]78“化”的過程既是天地生物的過程,同時也是“天以神御氣”的過程,兩者作為同一氣化過程中的隱顯兩個層面,并行交錯,相感通而生生不已。
以上是從一貫的動態過程來把握“氣化”的生生流行,下面將從靜態的層面來論述萬物的“氣化”結構。“天地之法象,人之血氣表里、耳目手足,以至魚鳥飛潛,草木華實,雖陰陽不相離,而抑各成乎陰陽之體。”[8]27-28張載在談到“法象”時說:“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5]9船山注言:“日月、雷風、水火、山澤固神化之所為,而亦氣聚之客形,或久或暫,皆已用之余也。”[8]34“糟粕”原意為造酒之后所剩渣滓,引申為陳跡。日月、雷風、水火、山澤、人之血氣表里、耳目手足,以至魚鳥飛潛、草木華實在內的天地法象都屬于“已用之余”,是經過神化作用之后所遺留下的可以把捉到的陳跡。盡管它們作為短暫的客形(相對于氣化而言),但在維持其形質的階段中,陰陽之氣的兩種功能一直在起著作用。“形之撰,氣也。”“形無非氣之凝”[8]407,408。“撰”為實在意。形體作為實在的承載者,無非是由氣凝聚而成,氣構成了形體的全部材質。“天地之產,皆精微茂美之氣所成。”“氣之所自盛,誠之所自凝,理之所自給,推其所自來,皆天地精微茂美之化,其醞釀變化,初不喪其至善之用。”[8]420*船山此處雖言“至善之用”,但此處的“至善”并不具有通常所說的與“惡”相對的倫理價值這一層意義,這里只是要說明萬物本身的自然變化可以被歸結為“氣”之用。“誠”也是實在意,也就是形體。凡是由天地所產生的法象形體,要推究它們(在發生學意義上)最根本的來源,最終都可以歸為一種“精微茂美之氣”;而且其形體之結構性功能的發揮即理之作用的彰顯也是來源于“精微茂美之氣”最初的“至善之用”。“天之化生萬物,人與禽獸并生焉。皆二氣五行之所妙合而成形者也。”[12]511天地化生萬物,不但要經歷如前面所說的從太和缊之氣、陰陽二氣到五行之氣、四時之氣,再到萬物之產生這一復雜的“氣化”過程,而且萬物形體本身也是由“二氣五行之所妙合”而直接構成的。整個“氣化”的過程不存在階段性的中斷,而是整體涵攝性地擴充并被賦予萬物。“太虛之氣,無同無異,妙合而為一,人之所受即此氣也。”[8]123在萬物稟賦“氣化”的過程中,幾乎無一例外,就連人的稟賦都是如此,因為本源的太虛缊之氣并不存在差異性(“太虛之氣,無同無異,妙合而為一”)。“人物之生,莫不受命于天。”[11]1115“天地人物之氣,其原一也。”[8]328“人物同受太和之氣以生,本一也。”[8]221人與物的現成生命形態歸根到底都是天命的結果,作為本原所稟賦的氣是一樣的,因為本一的太和之氣具有絕對的同一性。在這一點上,不僅人與物沒有差異,就是圣人所稟賦的氣也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人物之生,皆缊一氣之伸聚,雖圣人不能有所損益于太和。”[8]44“日月之發斂,四時之推遷,百物之生死,于風雨露雷乘時而興、乘時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來謂之客。”[8]18“唯萬物之始,皆陰陽之撰。”[9]42萬物生死輪回的不息,日月發光于外,收斂于內,四時循環推移,風雨露雷這些自然現象興息有時,它們對于作為真正開端之實在的陰陽而言都是短暫的有去有來的客體呈現,唯有那缊之氣的伸聚才是永恒的“主形”。
三、崇“本”開新:船山氣化差異性層面彰顯出對張載之超越
船山認為,雖然太虛之氣作為萬物的“本”與“原”是一,沒有差異,但在氣化為萬物所稟賦的過程中卻是有差異的,而且這種差異顯得很懸殊,這樣也就可以合理地解釋天地世界的豐富性與人之性命的虛靈性。“一方面肯定氣化流行這個自然宇宙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則亦強調人是此氣化流行而摶聚成之最優秀者,人實是天地之心,人能詮釋宇宙,潤化宇宙及締造者,而且宇宙經由人之詮釋、潤化及創造之后方成其為人的宇宙。”[13]這是船山論氣化獨有的兩個層面,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下文將重點討論船山論氣化的差異性,以彰顯船山于氣化過程中對張載的超越性。
氣化的過程就是氣之聚而成物,物又散而歸氣,這是一個客觀的流行過程,沒有一息的停滯。“氣之聚散,物之死生,出而來,入而往,皆理勢之自然,不能已止者也。”[8]20正是在基于氣之聚散,造成了萬物品類之間的差異。“植物根于地中,而受五行已成形之氣以長。陽降而陰升,則聚而榮;陽升而陰降,則散而槁。以形而受氣,故但有質而無性。”“動物皆出地上,而受五行未成形之氣以生。氣之往來在呼吸,自稚至壯,呼吸盛而日聚,自壯至老,呼吸衰而日散。形以神而成,故各其含其性。”[8]101植物的生命稟賦與成長來于五行之氣,受陽氣影響時,就呈現為欣欣向榮的狀態;受陰氣影響時,就表現為保藏含蓄的收斂狀態。因為主要是(植物的)形體受氣之作用的影響,所以植物只有氣聚以成的質料,而沒有氣聚以凝的靈性。動物則不同,所稟賦的是比五行之氣更為精微的還未成五行之形時的氣,生命形態的盛與衰取決于所呼吸之氣的聚與散,在呼吸之氣的聚散過程中,一方面形體得以茁壯,另一方面在形體茁壯的同時,由形而來的神逐漸成為各自的性。“草木有氣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理,兼情與理合為一致,乃成乎人之生。”[12]218草木只有氣而沒有情,禽獸雖有情但缺乏理,二者都有偏頗,將情理合為一體,于是就有了人的產生。“人者,兩間之精氣也,取精于天,翕陰陽而發其冏明。”[14]與動植物都不同而又更為精微的是人所稟賦的精氣,這種精氣直接取自太虛湛一的清氣(“取精于天”),妙合陰陽兩種神化作用而顯發出人的炯炯靈明。“人者,陰陽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陰陽以協天地萬物之居者也。”[8]369人既然作為陰陽神妙化合之聚的產物,當然也就可以配合天地成就萬物。“天以神御氣而時行物生,人以神感物而移風易俗。神者,所以感物之神而類應者也。”[8]78天地以氣化之神造就了萬物與四時的運行,人借氣的神妙之用應運四時而感通萬物以改變風尚而成一代良法美俗,這也正是船山所說的“感物之神而類應”。“陰陽之始本一也,而因動靜分而為兩,迨其成又合陰陽于一也。如男陽也而非無陰,女陰也而非無陽。以至于草木魚鳥,無孤陽之物,無孤陰之物,唯深于格物者知之。時位相得,則為人,為上知;不相得,則為禽獸,為下愚;要其受氣之游,合兩端于一體,則無有不兼體者也。”[8]37與萬物的稟賦一樣,何以人的稟賦獨特而茂美?這是船山需要回應的一個問題。為此他提出了“時位”的概念。人禽之別不在于陰陽之始的本一,因為二者都以太虛缊的和合之氣為本源,同時也以太虛渾淪湛一的清純之氣為依歸。所不同者就是時位相得與否,“相得,則為人,為上知;不相得,則為禽獸,為下愚”。“萬物之生,莫不資于天地之大德與五行之化氣,而物之生也,非天地合靈善之至,故于五行之端偏至而不均,唯人則繼之者無不善,而五行之氣以均而得其秀焉。”[11]564“時位相得”使人之所繼者無不善,所稟賦的五行之氣均勻而秀麗;禽獸則不然,不僅稟賦的五行之氣有偏頗不均勻,而且本身也沒有繼承天地的欣和靈善的本性。“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于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于此。”[12]510“時位相得”還使人稟得了正氣,氣正使得形正,形氣之正使人可以保全其固有的善性。盡管這種分別只是極為細微的差距,但卻是人物之所以分的關鍵。盡管“時位”很重要,但也只是造就人之特殊的眾多因素之一。“五行之氣,用生萬物,物莫不資之以生,人則皆具而得其最神者。”[11]561五行之氣作為萬物生生所必須要依據的質料,對人而言亦是如此,唯一的細微差異在于人還具備萬物所沒有的五行之氣的神妙功能。“二氣構形,形以成;二氣輔形,形以養。能任其養,所給其養,終百年而無非取足于陰陽。是大造者即以生萬物之理氣為人成形質之撰,交用其實而資以不匱。”[9]892船山此處雖言“二氣”,但實際上并不存在著真正的二氣,這里只是就功能而言。對于萬物生生所依據的質料是“五行之氣”,對于人而言,不僅只有“五行之氣”,還有陰陽二氣。而且二者相比,陰陽二氣對人的影響更為廣大重要。陰陽二氣不僅只是在初級階段構成形體,更為重要的是還能輔養形體。無論是養氣還是養體都是人所獨有的,實際上養體的根本在于養性,養性又要落到養氣上。
在船山本體論哲學中,船山對張載的超越之處在于其本體論哲學更為精細、深入。如果說張載哲學關于化生萬物只是停留在重了悟、獨斷論層面,那么船山關于氣化流行、化生萬物則進入了重論證、重邏輯層面。
船山“希橫渠之正學”,就張載“太虛即氣”這一觀點而言,船山對張載之學既有繼承之處,亦有創先之處。從張載之“太虛即氣”到船山之“太虛一實”,船山的繼承更多地表現為由表入里的深入過程;從張載之“氣化”到船山“氣之化也”,船山更多表現出由淺入深的細化探究;船山氣化差異性層面彰顯出對張載之超越,崇“本”開新。
[1]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1962:109.
[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6冊[M].長沙:岳麓書社,2011.
[3]陳來.詮釋與重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4]朱建民.張載思想研究[M].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
[5]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
[6]陳來.宋明理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47.
[7]牟宗三.心體與性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93.
[8]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2冊[M].長沙:岳麓書社,2011.
[9]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冊[M].長沙:岳麓書社,2011.
[10]朱熹.朱子全書:第6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3.
[11]王夫之.船山全書:第4冊[M].長沙:岳麓書社,2011.
[1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8冊[M].長沙:岳麓書社,2011.
[13]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M].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1988:18.
[14]王夫之.船山全書:第3冊[M].長沙:岳麓書社,2011:447.
[責任編輯王銀娥賈馬燕]
Wang Chuan-shan’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Zhang Zai’s Ontological Issue That “Tai Xu is Qi”
CHEN Li-xiang, WANG Zhi-hua
(YueluAcademy,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Wang Chuan-shan, one of Zhang zai’s disciples, inherited his master’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expanded his own. The issue under discussion is that Tai Xu was Qi, proposed by Zhang Zai, and that Tai Xu was an entity, proposed by Wang Chuan-shan. All revealed the inheritance of Wang Chuan-shan’s ontology from Zhang Zai’s, as a result, Wang’s differentiation led to the gradability of the universe, showing that Wang Chuan-shan’s thought had really transcended Zhang Zai’s.
Zhang Zai; Wang chuan-shan; Qi; entity; Tai Xu is Qi
B249.2
A
1001-0300(2016)04-0057-06
2016-03-14
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王船山遵禮之道研究”(15YBA094)的階段性成果
陳力祥,男,湖南邵陽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后,主要從事宋明理學和船山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