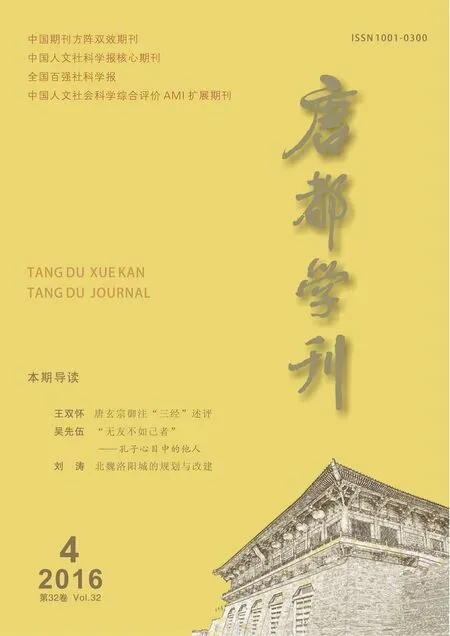《冷山》的深層生態(tài)解讀
付小蘭,夏 喆
(空軍工程大學(xué) 理學(xué)院,西安 710051)
?
【文學(xué)藝術(shù)研究】
《冷山》的深層生態(tài)解讀
付小蘭,夏喆
(空軍工程大學(xué) 理學(xué)院,西安710051)
查爾斯·弗雷澤在作品《冷山》中,以逃兵英曼艱辛漫長(zhǎng)的回家之路為明線,描繪了戰(zhàn)爭(zhēng)對(duì)人性的摧殘與對(duì)自然生態(tài)的破壞。同時(shí)又以艾達(dá)與魯比相互幫助,在農(nóng)場(chǎng)中求生存的故事為暗線,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與土地的交融共生關(guān)系。從深層生態(tài)學(xué)角度對(duì)小說(shuō)進(jìn)行解讀,在探索作者渴望人類融入自然、返璞歸真,實(shí)現(xiàn)人性“歸化”的生態(tài)追求之外,呼吁人類學(xué)習(xí)印第安先民樸素的生態(tài)智慧,以期達(dá)到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相處。
查爾斯·弗雷澤;《冷山》;深層生態(tài)思想;印第安人
夏喆,男,陜西西安人,空軍工程大學(xué)理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軍事文學(xué)研究。
《冷山》是美國(guó)作家查爾斯·弗雷澤的處女作,該書于1997出版后便榮登《紐約時(shí)報(bào)》暢銷書榜首,并在當(dāng)年以“描寫了人與土地復(fù)雜感情與關(guān)系”[1]341榮獲美國(guó)國(guó)家圖書獎(jiǎng),次年又成為全美十大暢銷書之一。各大報(bào)紙雜志、知名作家更是不吝溢美之詞,《紐約圖書評(píng)論》評(píng)論其為“一部絕佳的小說(shuō),令人驚異”[1]1,《華盛頓郵報(bào)》贊譽(yù)其為“一本令人激動(dòng)的小說(shuō)”[1]1,兩屆“歐·亨利短篇小說(shuō)獎(jiǎng)”得主里克·巴斯則認(rèn)為它“是美國(guó)文學(xué)中最輝煌的成就之一”[1]2。小說(shuō)中,作者以詩(shī)意般細(xì)膩的筆觸,以雙線式的敘事結(jié)構(gòu),穿插講述了內(nèi)戰(zhàn)末年,身負(fù)重傷的南方士兵英曼逃離戰(zhàn)場(chǎng),歷盡千難萬(wàn)險(xiǎn),回歸家園冷山,與愛人艾達(dá)團(tuán)聚的傳奇,以及艾達(dá)·門羅在孤女魯比的幫助下辛苦勞作,等待心上人歸來(lái)的故事。
深層生態(tài)學(xué)作為生態(tài)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理論基礎(chǔ),其概念最早由挪威哲學(xué)家倫·奈斯1972年在《淺與深——長(zhǎng)期的生態(tài)運(yùn)動(dòng)》一文中提出。作為一種生態(tài)智慧,深層生態(tài)學(xué)要求深入到人類的價(jià)值觀念與社會(huì)的價(jià)值體制進(jìn)行根本改造,以破除人類中心主義價(jià)值觀念的積弊,并最終建立一種無(wú)等級(jí)差別的和諧生態(tài)文明。因此,深層生態(tài)學(xué)的“目的不是為我們現(xiàn)存社會(huì)的輕微改變,而是對(duì)我們整個(gè)文明的根本性轉(zhuǎn)向”[2]。為了尋找超越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及工具理性價(jià)值觀的精神資源,深層生態(tài)學(xué)者們轉(zhuǎn)而將目光投向土著文化、東方文化等一切被西方現(xiàn)代文明邊緣化的傳統(tǒng)文明,如印第安人生態(tài)智慧、東方佛教文化等,而這些正是深層生態(tài)學(xué)智慧的直接思想來(lái)源。弗雷澤在《冷山》中并未過(guò)多著墨于戰(zhàn)爭(zhēng),而是通過(guò)對(duì)戰(zhàn)爭(zhēng)中生態(tài)、人性危機(jī)的描繪來(lái)表現(xiàn)其反戰(zhàn)主題與生態(tài)追求,因而也蘊(yùn)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深層生態(tài)思想。正因如此,弗雷澤在小說(shuō)的卷首特別引用了中國(guó)唐代著名隱逸詩(shī)僧寒山的詩(shī)句:“人問(wèn)寒山道,寒山路不通”[1]3,不僅暗含了自己對(duì)田園生活的追求,使全書帶上了東方禪宗的意境和生態(tài)觀,更表達(dá)了對(duì)戰(zhàn)爭(zhēng)中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不再的失落無(wú)奈與對(duì)戰(zhàn)爭(zhēng)血腥暴力的強(qiáng)烈批判。
在人類文明的畸形發(fā)展導(dǎo)致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和自然資源枯竭日益加劇的今天,品讀弗雷澤的《冷山》,領(lǐng)悟小說(shuō)中的生態(tài)智慧,對(duì)人們樹立正確的生態(tài)觀念,建立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生態(tài)關(guān)系有著特別的意義。
一、作家的深層生態(tài)思想來(lái)源
弗雷澤成長(zhǎng)于北卡羅來(lái)納州山區(qū),即小說(shuō)中冷山的所在地。兒時(shí)的山區(qū)生活賦予了弗雷澤一個(gè)快樂(lè)自由的童年,也使他對(duì)大自然充滿了熱愛與依賴。成人后,他依舊憧憬著一種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渴望著在原始自然之美中“詩(shī)意的棲息”*“詩(shī)意的棲息”:美國(guó)著名環(huán)境倫理學(xué)家羅爾斯頓在其著作《環(huán)境倫理學(xué)》中將生態(tài)倫理最后歸結(jié)于人在自然中的詩(shī)意棲息,即心懷熱愛與感激之情地去融入自然,將個(gè)人的生命融合進(jìn)自然整體之中。。然而,在繁華的大都市里,他卻目睹著青山綠水被鋼筋水泥所替代,生態(tài)環(huán)境受到嚴(yán)重破壞,人們?cè)跓艏t酒綠中紙醉金迷、在利益驅(qū)使下變得諂媚貪婪。雖然這些都使人們獲得了短暫的感官愉悅和滿足,但是信仰的缺失、心靈的空虛與道德的淪喪卻彌漫于整個(gè)社會(huì),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guān)系也因此愈發(fā)疏遠(yuǎn)和對(duì)立。面對(duì)著令人失望的現(xiàn)實(shí),作者懷著對(duì)自然原始之美的熱愛以及對(duì)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向往,毅然決然地帶著全家人離開城市,回到故鄉(xiāng),回歸自然,從此以牧馬為娛,以寫作為生,過(guò)著隱士般的生活。
作者的家鄉(xiāng)風(fēng)景獨(dú)特,一直以來(lái)都是印第安人的家園。印第安人按照古老的方式生存繁衍、生產(chǎn)生活,雖然土地貧瘠,但仍過(guò)著自給自足的幸福生活。弗雷澤從家人朋友那里聽說(shuō)了一個(gè)從高祖父起就世代相傳的故事:一個(gè)叫英曼的逃兵在內(nèi)戰(zhàn)中拖著受傷的身體踏上漫漫回家路,最終卻慘遭民兵槍殺。為記錄下這個(gè)奧德賽式的傷感回鄉(xiāng)之旅和當(dāng)年家鄉(xiāng)的風(fēng)土人情,作者親自上山去尋找英曼及其他遇害者的墳?zāi)梗⒅販亓擞⒙?dāng)年走過(guò)的艱辛歷程。小說(shuō)中,作者把目光聚焦在原始的自然之美,追憶那個(gè)時(shí)代樸素、天然的生活方式,懷念人與人之間的純真善良;在批判人類社會(huì)文明中的積弊與血腥的戰(zhàn)爭(zhēng)對(duì)自然與人性的摧殘和破壞、在表達(dá)對(duì)先民生活方式逐漸消逝的遺憾的同時(shí),也抒發(fā)了他對(duì)人類回歸本性、融入自然,共同構(gòu)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的生態(tài)追求以及對(duì)人類如何在工業(yè)文明高度發(fā)達(dá)的今天“詩(shī)意的棲息”的深刻思考,而這正是對(duì)深層生態(tài)學(xué)思想的思考與回應(yīng)。
二、《冷山》中的深層生態(tài)思想
(一)人類精神的“異化”
人類因?yàn)樨澙范l(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參戰(zhàn)者以主宰者的姿態(tài),在瘋狂蹂躪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之時(shí),也給卷入其中的人們帶來(lái)無(wú)盡的苦難。小說(shuō)中,弗雷澤多次將鏡頭聚焦至戰(zhàn)爭(zhēng)摧殘下人與人、人與自然支離破碎關(guān)系的現(xiàn)狀:環(huán)境受到污染,原本和諧美麗的自然家園不復(fù)存在,野戰(zhàn)醫(yī)院外一片灰蒙的天空、充斥著泡沫垃圾的污濁河流——“這條寬闊的水溝,只是大地上的一條污漬……堆滿了泡沫的黃色垃圾……和茅坑一般骯臟”[1]63,被焚毀后房屋的斷壁殘?jiān)取?zhàn)爭(zhēng)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更導(dǎo)致了人類巨大的精神危機(jī),它激發(fā)了人類內(nèi)心潛藏已久的征服欲,使人失去了理智與人性,成為一臺(tái)臺(tái)冷血的殺人機(jī)器;它侵蝕著人的精神,泯滅著人的善良,扭曲著人的精神,迫使卷入其中的人們終日被血腥與死亡圍困。小說(shuō)中多次出現(xiàn)了描繪戰(zhàn)場(chǎng)上慘烈場(chǎng)面的情節(jié),如弗雷德里克斯堡戰(zhàn)役中,北軍一整天都在進(jìn)攻,士兵們一個(gè)接一個(gè)倒下,但仍舊前赴后繼,“北軍尸橫遍野,到處是一堆堆血肉模糊的尸體”[1]8;受傷的士兵也未能幸免一死,被排列整齊,一錘一個(gè)砸死;即便是號(hào)稱正義之師的北軍,也因吃了敗仗而氣急敗壞,到處燒殺搶掠,連婦女和兒童也不放過(guò)。戰(zhàn)爭(zhēng)中的征服與統(tǒng)治行為,會(huì)使人獲得暫時(shí)的感官刺激與欲望滿足,但卻加劇了人類精神生態(tài)的“異化”,強(qiáng)化了人對(duì)人、人對(duì)自然的征服與控制欲,導(dǎo)致人與自然的天然聯(lián)系被割裂,人身心的內(nèi)在自然與作為生存家園的外部世界被隔絕,使人類喪失對(duì)信仰和對(duì)生命的敬意,從而帶來(lái)最終的結(jié)果:人類與自然在文明發(fā)展道路上愈加疏遠(yuǎn)并逐步走向?qū)αⅰ?/p>
(二)人類精神的“歸化”
“只有實(shí)現(xiàn)了價(jià)值觀向生態(tài)中心主義轉(zhuǎn)向,才能有效解決生態(tài)危機(jī)。”[3]人類的精神生態(tài)是地球生態(tài)圈的最高組成部分,因此,人類精神與自然生態(tài)協(xié)調(diào)一致才是生態(tài)和諧的理想境界。弗雷澤敏銳地覺察出生態(tài)問(wèn)題本質(zhì)上是人類精神世界的“異化”,因此,他強(qiáng)烈渴望將人類文明中的積弊進(jìn)行徹底清理,使人類精神生態(tài)得到新生,實(shí)現(xiàn)內(nèi)心世界自然回歸,重返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即人類精神世界的“歸化”。
1.回歸荒野
在深層生態(tài)學(xué)學(xué)者們看來(lái),荒野是生命的源頭,也是人們找回在文明劣根中喪失的自我的場(chǎng)所,只有在荒野中,人類才能恢復(fù)真正的自我。弗雷澤將英曼的回家之旅描繪為他心靈的救贖之路:厭倦了冷酷的殺戮與毀滅后的英曼逐漸從最初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盲目狂熱中清醒過(guò)來(lái),懷著對(duì)心上人無(wú)盡的眷戀,最終選擇逃離戰(zhàn)場(chǎng),踏上了漫長(zhǎng)而艱辛的重返家園之旅。他的返鄉(xiāng)之旅兇險(xiǎn)異常,危機(jī)四伏,他一路風(fēng)餐露宿,跋山涉水,在忍受著饑餓、病痛的折磨的同時(shí),還要時(shí)刻提防山林猛獸的襲擊、民兵的屠殺、同伴的背叛與惡霸的迫害。因此,他本能地渴望在大自然中,在心上人濃烈的愛里尋求庇護(hù),獲得慰藉。對(duì)記憶中冷山上自然之美的眷戀和與艾達(dá)未來(lái)生活的憧憬,成為了他苦難返鄉(xiāng)路上唯一的心靈寄托與精神家園。“憑記憶勾畫家鄉(xiāng)熟悉的綠色田野。……生長(zhǎng)著水晶蘭的潮濕的小河岸,……聆聽牛蹄踩踏塵土發(fā)出的噗噗聲,直至消失在蟈蟈兒和青蛙的叫聲里。”[1]2英曼向往著冷山上的一切,憧憬著與家鄉(xiāng)的自然美景融為一體。深層生態(tài)運(yùn)動(dòng)最終要深入到人的內(nèi)心世界,它的任務(wù)是“把人類文明重新放置于自然的母體中”[4]37,使人類重獲內(nèi)心世界、文明觀念與外在生態(tài)韻律的和諧統(tǒng)一。而正是這種渴望回歸自然的和諧之光在撫慰著英曼的心靈創(chuàng)傷,減輕其精神折磨的同時(shí),也讓他始終保持著人性的善良。
回歸荒野、融入自然使英曼在其心靈救贖之路上得到重生,而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生態(tài)則與艾達(dá)和魯比的生存息息相關(guān):她們?cè)谏掷锎颢C;在農(nóng)場(chǎng)中養(yǎng)殖牲口;在周邊的田地上耕耘,“田垅上的卷心菜、蘿卜、芥藍(lán)菜和洋蔥還很稚嫩,艾達(dá)和魯比在給他們鋤草,這些就是他們過(guò)冬的主要蔬菜了。幾個(gè)星期前,她們開始精心準(zhǔn)備,先用犁耕一遍,然后用爐灰和牲口糞施肥。”[1]101艾達(dá)和魯比在農(nóng)場(chǎng)中生產(chǎn)生存,依靠自然所賜予的生活所需免遭饑餓與寒冷。在這里,人與自然合二為一;人與土地渾然一體;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和睦融洽。雖然艾達(dá)擁有農(nóng)場(chǎng),但她和魯比之間并沒(méi)有主仆關(guān)系,她們彼此尊重、相互關(guān)愛、同甘共苦,像姐妹一般親密。魯比教會(huì)艾達(dá)認(rèn)識(shí)土地,獲得求生技能;艾達(dá)也會(huì)在閑暇時(shí)為魯比閱讀小說(shuō),豐富她的精神生活。同時(shí),土地上收獲的一切也使她們有能力去給予更多身處困境中的人無(wú)私幫助。
2.返璞歸真與“自我實(shí)現(xiàn)”
與很多生態(tài)作家一樣,兒童承載著弗雷澤對(duì)人類善良本性的贊美,依托著自己所追求的和諧生態(tài)世界。兒童形象以及兒童的視角,既是作家追憶逝去的美好童年的生動(dòng)文學(xué)再現(xiàn),更具有深刻的生態(tài)隱喻及內(nèi)涵。
小說(shuō)中的二號(hào)女主角魯比,從小就被毫無(wú)責(zé)任心、懶散無(wú)能的父親拋棄,整日處于“放養(yǎng)”的狀態(tài)。“在野外覓食,挖掘草根,用柳枝編網(wǎng)捕魚,并用類似的方法捕捉飛鳥。”[1]267特別是一天夜里,小魯比被困在森林里,起初,她對(duì)周圍陌生的一切都充滿了惶恐,然而,漸漸的,在與自然的交融中,在自然之美的感召下,她感受到了溫暖與慰藉,變得不再恐懼。而且從那以后,她在大自然中“能知道別人永遠(yuǎn)不知道的東西”[1]81。作家筆下的小魯比向往自然、熱愛自然、親近自然,更沉醉于其中,沉醉于細(xì)膩地聆聽自然萬(wàn)物的聲音,敏銳地感知生態(tài)野性之美。孩子保有著人類最本能的純真善良,這也賦予了其與大自然超驗(yàn)溝通的能力,他們能用感官與心靈體驗(yàn)自然,避免了用理性來(lái)分隔自然。而這正是魯比能夠敏銳地洞察自然界的規(guī)律,獲得人類最原始的寶貴生存技能的原因。弗雷澤通過(guò)對(duì)魯比童年時(shí)與自然和諧交融的描繪,以兒童的視角表達(dá)了自己呼喚人類天性復(fù)歸的追求與對(duì)自然的敬畏。
童年時(shí)期的魯比與自然的和諧交融也傳遞了奈斯深層生態(tài)學(xué)的智慧——“自我實(shí)現(xiàn)”(Self-realization)論,它是深層生態(tài)理論的基點(diǎn),也是深層生態(tài)運(yùn)動(dòng)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實(shí)現(xiàn)途徑為“通過(guò)自我與多樣豐富的生命世界的認(rèn)同,從而超越人類個(gè)體小我的局限性,在廣博的生命世界融合的過(guò)程中獲得個(gè)體生命的拓展和心靈世界的超越”[4]14。在奈斯看來(lái),“自我實(shí)現(xiàn)”已經(jīng)超越了人類社會(huì)范疇,達(dá)到了人與生態(tài)中所有存在物的認(rèn)同,因此“自我”應(yīng)是大寫的(Self)。在“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過(guò)程中,人類需要“自身內(nèi)在潛能的激發(fā)”[5]18。小魯比那晚在荒野中富于神秘色彩的“頓悟”經(jīng)歷,激活了她在生態(tài)中“自我實(shí)現(xiàn)”的潛能,使小魯比對(duì)自我與廣袤自然中一切存在物的認(rèn)同范圍不斷擴(kuò)大與加深,對(duì)它們的恐懼感與疏離感逐漸縮小,最終達(dá)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5]31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心理狀態(tài)與精神境界。在奈斯看來(lái),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復(fù)雜性與多樣性能夠最大限度地促進(jìn)“自我實(shí)現(xiàn)”。這也正解釋了為什么魯比在面對(duì)被傳統(tǒng)定義為邪惡與死亡象征的烏鴉時(shí),卻對(duì)其有著特別的親近與崇拜之感。作為艾達(dá)的精神導(dǎo)師和最好的朋友,魯比在幫助她恢復(fù)農(nóng)場(chǎng)生產(chǎn),適應(yīng)自然的過(guò)程中,也使她逐漸認(rèn)識(shí)了土地,融入了自然,獲得了感悟自然之美的能力:“逐漸地她開始感覺到不可計(jì)數(shù)的細(xì)小生命在忙碌著,從一簇簇的花冠……他們對(duì)能量的積聚是生命善良的律動(dòng)。”[1]106因此,魯比在小說(shuō)中也扮演著喚醒人類內(nèi)心深處生態(tài)意識(shí)的角色。
(三)印第安人的生態(tài)智慧
弗雷澤描寫了印第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始生活方式。生態(tài)思想家克里考特指出:“在生態(tài)文學(xué)思想普及和環(huán)境危機(jī)的意識(shí)深入人心的時(shí)代,傳統(tǒng)的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成為一種象征,它象征著我們失去了但還沒(méi)有忘記的人與自然的和諧。”[6]在生態(tài)方面,美國(guó)印第安文化近乎“成熟”,有著豐富的生態(tài)智慧。他們尊重自然,敬畏生命,遵從自然的規(guī)律進(jìn)行生產(chǎn)生活,僅向自然索取自己的基本生活所需。這正是今天深層生態(tài)學(xué)學(xué)者們所追求的,他們渴望從這些原著居民那里汲取營(yíng)養(yǎng),獲得智慧。
1.生態(tài)中心主義
印第安人將自己視為生態(tài)之網(wǎng)中的一部分,這種樸素原始的自然觀為與自然矛盾越發(fā)尖銳的人類和被人類中心主義支配許久的西方文明指明了一條自我拯救之路。正因如此,奈斯在其深層生態(tài)學(xué)思想中將印第安人樸素的自然觀作為生態(tài)中心主義觀點(diǎn)的理論來(lái)源。在《西雅圖宣言》中,印第安人向世界宣告了他們傳統(tǒng)的生態(tài)中心自然觀:“我們是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也是我們的一部分。”[7]印第安人從未將自己放置于自然界的中心位置,認(rèn)為自己有優(yōu)于其他物種的任何特權(quán)。在他們看來(lái),自然生態(tài)中的一切都具有內(nèi)在價(jià)值,自然萬(wàn)物互相聯(lián)系,互相連結(jié),彼此平等,統(tǒng)一于一個(gè)和諧整體之中。他們認(rèn)為盡管殺生是必須的,因?yàn)槿祟惖纳嫘枰澄铮侨祟惐仨氁鹬貏?dòng)物的生命,對(duì)其心存感激之情。這一思想可以從一位印第安老婦人殺羊的情節(jié)中看出:“老女人繼續(xù)撓著它的下巴,撫摸它的耳朵……一眨眼便深深地割開了山羊額下的動(dòng)脈……她繼續(xù)撓著它的毛,撫弄它的耳朵。羊和女人都凝神看著遠(yuǎn)方。”[1]208老婦人殺羊的過(guò)程平靜而詳和,更像是一場(chǎng)神圣的宗教儀式,表現(xiàn)出了印第安人對(duì)自然的敬畏與對(duì)生命的尊重。這也是生態(tài)學(xué)家利奧波德在《大地倫理》(Land Ethic)中所追求的重要生態(tài)思想之一,“大地倫理是要把人類變成這個(gè)共同體中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duì)每個(gè)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duì)這個(gè)共同體本身的尊敬”[8]。而與印第安人對(duì)生命的敬畏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暴虐的民兵在搶奪了寡婦家的牲口后,卻進(jìn)行了一場(chǎng)屠殺,“他們必然要飽餐一頓,哪怕把那頭豬的腿生生割下來(lái)……擰斷兩只雞的脖子,拔掉雞毛,掏出內(nèi)臟”[1]244。在戰(zhàn)爭(zhēng)摧殘與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影響下,征服、殺戮的邪惡觀念再度占據(jù)了人類心靈。他們瘋狂地藐視,踐踏著自然,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高唱?jiǎng)P歌,殘暴地宰殺生靈,表現(xiàn)出一種病態(tài)的狂妄。弗雷澤渴望人類向古老的先民學(xué)習(xí),恢復(fù)對(duì)自然界中一切生命的敬畏之心,并與其休戚與共,以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心靈的和諧關(guān)系。
2.尊重自然,簡(jiǎn)單生活
印第安人的作息方式并不像所謂的文明人認(rèn)為的那樣是野蠻和愚昧的。相反,印第安人創(chuàng)造了一種和諧美好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并且也擁有了人類寶貴而深遠(yuǎn)的生態(tài)思想。他們的勞作僅僅以滿足基本生存為目的,他們自由地生活,擁有心靈的安寧祥和與精神世界的豐富完整。小說(shuō)中,那位印第安婦人住在簡(jiǎn)陋的帳篷里,餓了,就吃自然賜予的食物;渴了,就喝飼養(yǎng)的羊奶;病了,就用山上的草藥。即便是將要死亡,她也希望重新歸入自然,“往石崖上一躺,讓渡鴉把她的尸體啄碎,帶著她飛向遠(yuǎn)方”[1]207。同樣,魯比在幫助艾達(dá)經(jīng)營(yíng)農(nóng)場(chǎng)時(shí),也始終沿襲著印第安人的這種簡(jiǎn)單的生活方式:“一切事情——給籬笆打樁、做泡菜、殺豬——都得聽從天意的指示”[1]102。“很少有她想要,而自己又不能制造,種植或在山上找到的。”[1]189魯比所遵從的這種天然生產(chǎn)與生活的方式加深了人類對(duì)土地與自然萬(wàn)物的依賴,并且以生存需要為指向的物物交換將生產(chǎn)從金錢利益的鐵鏈中解放出來(lái),強(qiáng)化了人與自然休戚與共的關(guān)系,更促進(jìn)了生態(tài)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在生態(tài)危機(jī)日趨嚴(yán)峻的今天,深層生態(tài)學(xué)學(xué)者們更加確信,把人類的物質(zhì)需求限制在生態(tài)的可承受范圍內(nèi),并追求簡(jiǎn)單的物質(zhì)生活是人類應(yīng)盡的責(zé)任。人類對(duì)物質(zhì)的強(qiáng)烈追求是以內(nèi)在自然的極度萎縮,自然資源的加速耗盡為代價(jià)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將物質(zhì)享受的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nèi)。但是,這種樸素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要求人類重新回到刀耕火種的原始混沌狀態(tài)。“我們不可能說(shuō)服所有的人拆除高樓而重新搬到山洞里去住,拋棄鐘表而重新滴漏計(jì)時(shí),銷毀電腦而重新結(jié)繩記事。”[4]78樸素的生活實(shí)際上是一種心靈的回歸,一種生態(tài)思維模式的回歸:像那些原著居民一樣,不再熱衷于物質(zhì)需求的滿足,日益關(guān)愛我們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樹立人類應(yīng)有的生態(tài)責(zé)任意識(shí)。在小說(shuō)的高潮部分,弗雷澤亦將艾達(dá)與英曼這對(duì)患難情侶的重逢設(shè)定在了印第安人的古村落,暗示著只有人類融入自然,簡(jiǎn)單生活,達(dá)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tài)時(shí),才會(huì)得到幸福。
三、結(jié)語(yǔ)
弗雷澤在《冷山》中展示了自己渴望人類融入自然、返璞歸真,實(shí)現(xiàn)人類精神“歸化”的生態(tài)追求,呼吁人類向古老的先民學(xué)習(xí),尊重自然,簡(jiǎn)單生活,與萬(wàn)物休戚與共。然而,由于長(zhǎng)期深植于人類內(nèi)心的征服、占有的劣根,人類要真正實(shí)現(xiàn)回歸自然,返璞歸真,達(dá)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有很漫長(zhǎng)的一段“奧德賽”之路要走。正因如此,弗雷澤并未給小說(shuō)設(shè)置一個(gè)圓滿的結(jié)局:英曼在與民兵槍戰(zhàn)時(shí),對(duì)一位男孩心懷憐憫卻最終慘遭其殺害,這也呼應(yīng)了作品的卷首語(yǔ)——“人問(wèn)寒山道,寒山路不通”[1]3。
[1]查爾斯·弗雷澤.冷山[M].周玉軍,潘源譯.南寧:接力出版社,2004.
[2]Eric Katz,Andrew Light,and David Rothenberg.Beneath the surface[M].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5:8.
[3]Berry T.The Viable Human[G]∥ in G.Sessions,eds.,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5:18.
[4]王茜.生態(tài)文化的審美之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雷毅.深層生態(tài)學(xué):闡釋與整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12.
[6]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203.
[7]Lisa M.Benton,John R.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 Reader[M].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12-13.
[8]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xiāng)年鑒[M].侯文慧譯.長(zhǎng)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2.
[責(zé)任編輯張敏]
Interpretation of Cold Mountain
FU Xiao-lan, XIA Zhe
(CollegeofScience,AirForceEngineeringUniversity,Xi’an710051,China)
ColdMountain, written by Charles Frazier, is about Inman’s long and hard walk home as an army deserter, describes the ravages of the war to human nature and natural ecology. Besides, the novel tells of the mutual help between Ada and Inman, and their survival in the countryside, portraying the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ecology, the pursuit of the writer’s eagerness to blend into the nature and recover the original simplicity, and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pursuit of human naturalism, this paper aims at appealing us to learn Indian ancestors’ simplicity so as to seek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themselves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harles Frazier;ColdMountain; deep ecological thought; Indians
I106.4
A
1001-0300(2016)04-0124-05
2016-02-28
付小蘭,女,重慶人,空軍工程大學(xué)理學(xué)院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軍事文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