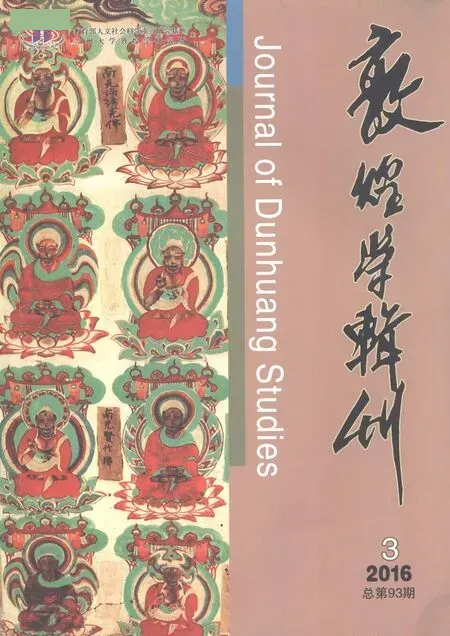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出世論考(下篇)
——兼對古靈寶經出世時間下限的考定
王承文
(中山大學 歷史系,廣東 廣州 510275)
五、《靈寶經目序》與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內在關系
敦煌本《靈寶經目》與現存《靈寶經目序》之間是否存在直接關系,將直接決定敦煌本《靈寶經目》究竟是元嘉十四年(437)的《靈寶經目》,還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陸修靜所編《三洞經書目錄》中的洞玄部靈寶經的目錄。我們認為現存陸修靜《靈寶經目序》與敦煌本《靈寶經目》是兩個相互關聯亦高度倚存的文本。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所說的《靈寶經目》,其實就是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為此,我們有必要對其中一些最具有關鍵意義的問題展開討論。
(一)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所稱“《舊目》所載”和“篇章所見”涵義辨析
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專門記載了他在整理古靈寶經之前古靈寶經的混亂狀況,其文稱:
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學士宗竟,鮮有甄別。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尋覓,甫悟參差。
究竟什么是陸修靜所說的“或是《舊目》所載”,什么是“或自篇章所見”呢?學術界一般認為這里的“或是《舊目》所載”,是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元始舊經”,即“十部妙經三十六卷”;至于“或自篇章所見”則是專指“新經”。不過,近年來,劉屹博士對此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觀點。他認為“或是《舊目》所載”,是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元始舊經”;而“或自篇章所見”,則是指在“元始舊經”和“新經”之外單獨流傳而后來卻又失傳了的一批“斷簡殘章”。其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還有“一些靈寶經,現已沒有完整篇章傳世,但卻在某些現存的古靈寶經中被轉引或提及過”[注]劉屹《“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的先后問題——以“篇章所見”的古靈寶經為中心》,《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第11頁。。由于這一問題對于理解敦煌本《靈寶經目》的結構等十分關鍵。對此,我們試作簡要討論。
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前后所說的“《舊目》”以及“十部《舊目》”意義應完全相同。《靈寶經目序》所稱“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如前所述,所謂“《舊目》所載”,其“《舊目》”就是是特指元嘉十四年(437)陸修靜著手整理古靈寶經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專門著錄“元始舊經”的《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陸修靜將其簡稱為《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因為,無論是古靈寶經本身,還是陸修靜,其所說的“《舊目》”都是特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而這里的“或是《舊目》所載”,是與“新、舊五十五卷”中的“舊”經即“元始舊經”相對應的;至于“或自篇章所見”,則是與“新、舊五十五卷”中的“新”經相對應的,是專門指“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近年來,小林正美亦指出所謂“或自篇章所見”,是“指代葛仙公所受的‘新經’”[注][日]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譯《新范式道教史的構建》,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第134頁。。
那么,陸修靜為什么要用“或自篇章所見”來專門指代這批“新經”呢?這是因為在陸修靜編纂《靈寶經目》之前,“元始舊經”已有《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這樣一個專門的目錄。然而,這些“新經”的情況卻完全不一樣,尚處于一種分散無序的狀態,并沒有一個專門的目錄將它們編纂在一起,因此陸修靜特地將它們稱之為“或自篇章所見”。與此相關的表達方式還有很多。例如:(1)《靈寶經目序》稱:“慮有未悉,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注解意疑者略云爾。”其中“并仙公所授事”即專指“新經”,而且是與“今條《舊目》已出”相并列的;(2)敦煌本《靈寶經目》逐條列舉了全部“元始舊經”和“新經”之后,稱“十部《舊目》及新名錄記如前”。其中“十部《舊目》”,就是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著錄的“元始舊經”。而“新名”則是指所有“新經”的經名;(3)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稱:“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其中“并仙公所稟”即指“新經”,并與“今見出元始舊經”是相并列的;(4)《云笈七簽》卷三《靈寶略紀》稱:“(葛)孝先(即葛玄)凡所受經二十三卷,并語稟請問十卷,合三十三卷。”其“并語稟請問十卷”就是指“新經”,而且是與“(葛)孝先(即葛玄)凡所受經二十三卷”即“元始舊經”相并列。可見,陸修靜所稱“或自篇章所見”,本身是與“或是《舊目》所載”相并列的。否則,大批“新經”的存在將會無所指歸。也正因為如此,陸修靜所稱“或自篇章所見”,并不是指在“元始舊經”和“新經”之外還有單獨流傳的“斷簡殘章”。
其次,劉屹博士所提出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古靈寶經“新經”(他將其稱之為“仙公新經”)是在“元始舊經”之前出世這樣一個結論為前提的。他認為“‘新經’不僅沒有稱引任何一部‘舊經’經名和內容,而且表現出與‘舊經’建構的經教體系有所不同”。對此,我們經過重新研究,證明古靈寶經“元始舊經”一般都比“新經”更早出世,“新經”不但大量征引了“元始舊經”的經名及其內容,而且從整體上來看,古靈寶經“新經”也主要是對“元始舊經”的詮釋和進一步發展。[注]王承文《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和“新經”出世先后考釋——兼對劉屹博士系列質疑的答復》,《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最后,陸修靜所稱“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是指原《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元始舊經”,再加上《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之外的“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即“新經”,總共為55卷。然而,陸修靜認為這55卷的“舊經”和“新經”中,各自都存在十分嚴重的真偽不分、魚龍混雜的情況,所以陸修靜通過仔細甄別,去偽存真,最終才形成了這部《靈寶經目》。而原來的“新、舊五十五卷”,變成了敦煌本《靈寶經目》所說的:
(“新經”)右十一卷,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都合前元始[舊經],新舊經見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為三十五卷,或為三十六卷。
因此,陸修靜編成的這份《靈寶經目》,既包括了經過他確認的由《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元始舊經”,也包括了經過他確認的真正可信的“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
(二)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所稱“十部《舊目》”,究竟是“出者三分”,還是“出者六分”?
1.從《靈寶經目序》看“元始舊經”之“出者六分”的可能性
陸修靜《靈寶經目序》記述了古靈寶經“元始舊經”的出世數量,其文稱:
但經始興,未盡顯行,十部《舊目》,出者三分。雖玄蘊未傾,然法輪已遍于八方,自非時交運會,孰能若斯之盛哉!
所謂“十部《舊目》”,如前所述,是專門指陸修靜《靈寶經目》中“《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元始舊經”,即“十部妙經三十六卷”。而陸修靜所稱“但經始興,未盡顯行,十部《舊目》,出者三分”,是說“元始舊經”并沒有全部出世。而其中一個最為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這里究竟是“十部《舊目》,出者三分”,還是“十部《舊目》,出者六分”呢?近三十多年來,這一問題一直是嚴重困擾國際學術界的難題,亦是導致各種爭議紛紜最主要的根源。因為,如果是在“十部妙經三十六卷”中“出者三分”的話,那么,當時就只有大約11卷“元始舊經”出世。然而,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卻稱:
……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今分成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
其稱“元始舊經”中“二十一卷已出”,顯然與《靈寶經目序》中“十部舊目,出者三分”,即11卷不相符合。也正因為如此,小林正美、劉屹等研究者判定敦煌本《靈寶經目》是泰始七年(471)陸修靜所編《三洞經書目錄》中洞玄靈寶經的經目。如果小林正美等學者的說法能夠成立的話,那么,在公元437年陸修靜寫定《靈寶經目序》之時,必然還有大量“元始舊經”尚未出世。也就是說,作為“元始舊經”系列主體為數眾多的古靈寶經,其實都是在公元437年到471年之間才被創作出來的。[注][日]小林正美著,李慶譯《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劉屹《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41-142頁;王皓月《再論〈靈寶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85-90頁。
1997年,大淵忍爾和柏夷(Stephen R.Bokenkamp)在其各自的著作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出敦煌本《靈寶經目》就是元嘉十四年的經目,并且都認為《靈寶經目序》中的“出者三分”,是《云笈七簽》在流傳過程中因為抄寫等原因所導致的錯誤,其原文本應是“出者六分”。[注][日]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東京:創文社,1997年,第88頁;Stephen R. Bokenkamp,“The Wondrous Scriptures of the Upper Chapters on Limitless Salvation”,in Bokenkamp,Early Daoist Scriptur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396-397.Bokenkamp,Stages of Transcendence: The Bhūn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s,” in Robert E.Buswell,Jr.ed.,Chinese Buddhist Apocraph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140.如果是“出者六分”的話,那么,“元始舊經”之“十部妙經三十六卷”中“已出”的數額,則應為21.6卷。這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中“元始舊經”的數量21卷基本符合。為了更能說明問題,我們對此稍作引申。因為如果是“出者五分”,則應為18卷;如果是“出者七分”,則應為25卷。所以“出者六分”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數目。也就是說,在劉宋元嘉十四年(437)之后,不再有新的古靈寶經典問世。
從小林正美等學者所列舉的相關證據來看,陸修靜《靈寶經目序》中的“十部《舊目》,出者三分”,應是其整個立論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證據。[注]小林正美所列舉的另外兩條主要證據包括:第一,鳩摩羅什所譯大乘佛教經典在江南的影響,開始于公元420年左右。因此,古靈寶經中的大乘佛教影響,必定在此之后。而柏夷所發表的多篇論文,證明了古靈寶經中的大乘佛教思想,主要源于孫吳時期支謙所譯佛經的影響(見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 Strickmann ed,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A.Stein,Vol.2.Brussel.,1983, pp.434-486,1983);第二,小林正美從《道教義樞》卷2《三洞義第五》所引古靈寶經“新經”《真一自然經》中,出現了劉宋后期南岳道士徐靈期的名字,從而認為古靈寶經的創作應延續到了劉宋中后期。不過,敦煌文書P.2452“新經”《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即《真一自然經》有關古靈寶經的傳授,卻只有東晉建元二年(344)葛洪在羅浮山傳經的記載。并沒有其后包括劉宋后期徐靈期等人的記載。而大淵忍爾和柏夷的結論,則主要建立在他們對古靈寶經的整體把握上,并不局限于某一孤立性的證據,因而也具有較大的合理性。然而,這兩位學者所稱“出者六分”的說服力則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因此,我們試對此作進一步討論。
首先,我們認為中國古代文獻典籍包括道教經書在流傳過程中,“二”、“三”、“六”、“七”、“八”等這些數字發生誤寫的現象確實比較常見。[注]例如,“二”與“七”字就容易相混淆。唐代閭丘方遠《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稱葛玄卒年曰:“仙公以吳赤烏二年八月十五日,于天臺山白日升天。”(《道藏》第6冊,第376頁)然而,陶弘景撰《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卻稱“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長往不返”(陳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2頁);元代譚嗣先《太極葛仙公傳》記載其于“赤烏七年八月十五日”升仙。又稱“于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上升,徑赴闕庭”,“仙公上升時年八十一”(《道藏》第6冊,第847頁);元代趙道一《歷代真仙體道通鑒》卷23《葛玄傳》稱“于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飛升,徑赴闕庭”(《道藏》第5冊,第229頁)。而“甲子歲”即為吳大帝赤烏七年(244)。因此,《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中的“吳赤烏二年”必定是“吳赤烏七年”的錯誤。我們試圖通過一些相關例證來進一步說明。敦煌文書P.2452號《靈寶威儀經訣上》,即古靈寶經“新經”《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的殘卷,該經記載從太極真人徐來勒以來靈寶經的傳授過程,其文稱:
……抱樸子君建元六年三月三日,于羅浮山付[葛]世,世傳好之子弟。
以上敦煌文書的字體屬于行書。其“建元六年”應是“建元二年”的錯誤。因為東晉康帝司馬岳在位并以“建元”紀年,總共就是兩年(343-344),因此,以上敦煌文書中的“建元六年”,必定是抄寫者錯誤抄寫所致。[注]王承文《葛洪晚年南隱羅浮山事跡釋證——以東晉袁宏〈羅浮記〉為中心》,載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編《首屆葛洪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3年11月),第253頁。刊載于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21輯,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158-184頁。另外,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道藏通考》中也指出了這一點,見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The Taoist Canon :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236.而與此類似的訛誤實際上也同樣出現在收錄有陸修靜《靈寶經目序》的《云笈七簽》中。我們試舉有關靈寶經傳承的資料來說明。
唐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第五》所引《太玄都四極盟科》稱:
……(葛)洪號抱樸子,以晉建元二年三月三日,于羅浮山付弟子海安君望、世等。至從孫巢甫以晉隆安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之徒,相傳于世,于今不絕。[注][唐]孟安排《道教義樞》卷2《三洞義第五》引《道藏》第24冊,第813頁。對這一資料的來源,我們將另有專門討論。
《云笈七簽》卷六《三洞經教部·三洞并序》引《四極盟科》稱:
……(葛)洪又于晉建元二年三月三日,于羅浮山付弟子安海君望世等。后從孫巢甫,晉隆安元年,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遂行于世。[注][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云笈七簽》卷6《三洞經教部·三洞并序》,第90頁。
而《云笈七簽》卷六《三洞經教部·三洞品格》所引《太玄都四極盟科》卻又為:
……抱樸[子]以建元六年三月三日,于羅浮山[付弟子安海君望、世等。至從孫巢甫,以晉]隆安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之徒,相傳于世,于今不絕。[注][宋]張君房編《云笈七簽》卷6《三洞品格》,《道藏》第22冊,第34頁。按:《正統道藏》本此段殘闕較多,據[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云笈七簽》校補。
如前所述,東晉康帝“建元”年號,前后總共只有兩年。因而“建元六年”亦必然是“建元二年”書寫的訛誤。至于前引《云笈七簽》引《四極盟科》所稱“隆安元年”,亦僅屬于一個非常孤立的個案,與其它所有記載都不合,因而也完全可能是“隆安末年”的訛誤。因為“元”與“末”字的書寫亦確實很容易造成混淆。
近年來,劉屹博士判定敦煌本《靈寶經目》屬于泰始七年(471)經目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認為“《云笈七簽》本《靈寶經目序》是經過北宋官方組織編纂的傳世文獻,其文字的整齊規范程度要大大超過敦煌寫本”;并進而認為“除非能找到別本證據來參校,否則無法讓人相信‘出者六分’或‘未出者三分’才是正本”。[注]劉屹《敦煌本〈靈寶經目〉研究》,《文史》2009年第2輯,第66頁。應該說,劉屹博士對這一問題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確實值得肯定和贊賞。然而,現存《云笈七簽》在其第六卷中對《太玄都四極盟科》一書的前后兩次征引,竟然存在“建元二年”和“建元六年”兩種完全不同的寫法。而且“建元六年”又必然屬于該書在流傳過程中的訛誤。因此,不能因為《云笈七簽》在宋代以來道門內部流傳廣泛亦很權威,就排除形成這種訛誤的可能性。但是,以上這種明顯的訛誤卻又可以肯定并不是北宋官方編纂《云笈七簽》時所出現的,而是該書在其后來流傳過程中因為抄寫所出現的錯誤。這種錯誤出現的時間,應該在明代《正統道藏》編纂之前。因此,結合其它證據來看,我們認為《云笈七簽》所收陸修靜《靈寶經目序》原文中的“出者六分”,在后來流傳過程中被誤為“出者三分”,應該說是完全有可能的。
2.從《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看“元始舊經”之“出者六分”的必然性
陸修靜的《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明確說明此前經過整理后的古靈寶經數目是“三十五卷”,從而也證明了敦煌本《靈寶經目》就是公元437年編成的經目。由于有關古靈寶經出世的記載本身極其匱乏,因而這一條材料也是最能說明古靈寶經出世的極少數關鍵證據之一。《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稱:
臣修靜依棲至道,翹竚靈文……自從叨竊以來一十七年,竭誠盡思,遵奉修研,玩習神文,耽味玄趣,心存目想,期以必通,秉操勵情,夙夜匪懈。考覽所受,粗得周遍,自覺神開意解,漸悟理歸,宛義妙致,本自仰絕,其粗跡近旨,謂可彷佛。伏尋靈寶大法,下世度人,玄科《舊目》三十六卷……但正教始興,天書寶重,大有之蘊,不盡顯行。然即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根末表里,足相輔成;大乘之體,備用不少。[注]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道藏》第9冊,第839頁。
陸修靜所稱“自從叨竊以來一十七年”,大淵忍爾考證是指陸修靜入道之后17年,為元嘉二十一年(444),也就是其編纂《靈寶經目》并撰寫《靈寶經目序》之后的第七年。[注][日]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第74頁。按國內外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所稱“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與敦煌本《靈寶經目》對“元始舊經”和“新經”的記載符合。學術界只是對《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的成書年代存有爭議。小林正美先是提出《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成書于“元嘉之末”即公元453年(見[日]小林正美著,李慶譯《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36、170頁)。然而,小林正美在其新著《新范式道教史的構建》的《前言》中,則提出《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成書于“元嘉十八年(441年)”(見[日]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譯《新范式道教史的構建》,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第8頁)。不過,小林正美的新觀點實際上對其自己最初的核心觀點作了極為重要的修改。因為小林正美一直堅持元嘉十四年的《靈寶經目序》中“十部《舊目》,出者三分”是正確的。如果其新提出的《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作于“元嘉十八年”的觀點能夠成立,則意味著大量新的“元始舊經”都寫成在“元嘉十四年”到“元嘉十八年”僅三至四年間。而不是原來的從“元嘉十四年”到“泰始七年”(471)的長達三十四年之間。同時也就意味他否定了自己在《六朝道教史研究》中所列舉的古靈寶經創作延續到劉宋中后期的證據。近年來,劉屹博士則提出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與《靈寶經目序》一樣,均為公元437年所作(見其《古靈寶經出世論——以葛巢甫和陸修靜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劉屹博士一方面并未說明其將該書確定在公元437年的理由,另一方面則會使其前后觀點相抵牾。因為如果劉屹博士此說能夠成立的話,則應該明白無誤地確證了敦煌本《靈寶經目》必然是屬于元嘉十四年的《靈寶經目》。因為《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已非常清楚地說明“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所著錄的“元始舊經”和“新經”的數量,即“今為三十五卷”正好相符合。不過,劉屹博士在此前所撰《敦煌本〈靈寶經目〉研究》(《文史》2009年第2輯)等一系列論文中,亦將敦煌本《靈寶經目》看成是陸修靜于劉宋泰始七年(471)所編《三洞經書目錄》中靈寶經的目錄。認為陸修靜《靈寶經目序》中的“出者三分”不可能是“出者六分”的抄寫錯誤。進而認為有大量“元始舊經”都是在元嘉十四年(437)《靈寶經目》編成之后直至公元471年之間才出世的。劉屹博士最近顯然已經意識到了其前后觀點存在抵牾和矛盾之處。一方面他雖然仍然堅持敦煌本《靈寶經目》是泰始七年所成經目,大量“元始舊經”是在元嘉十四年之后作成,但是,另一方面則對《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所稱“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又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解釋,稱“是后人根據陸氏471年的目錄所做的改寫,因為那時的靈寶經卷數在很長時期內已是一個比較固定的最終卷數”(見其《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第141頁)。即“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是后人甚至可能是明代人改寫而成的。不過,從現存資料來看,這種觀點目前恐怕還很難加以證實。以上“伏尋靈寶大法,下世度人,玄科《舊目》,三十六卷”,所謂“玄科《舊目》,三十六卷”,就是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三十六卷“元始舊經”。而陸氏所謂“正教”與敦煌本《靈寶經目》中宋文明所作注釋中的“正文”一詞具有相同的涵義,都是特指“元始舊經”。而所謂“并仙公所稟”之“并”字,當為“合在一起”的意思。所謂“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是說經過他甄辨并確認可信的古靈寶經是“三十五卷”,應指“二十三卷”的“元始舊經”,加上“十二卷”的“新經”,總共三十五卷。有關其具體計算方法見后面的討論。
在《靈寶經目序》中,陸修靜一方面強調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出世的不完整性,其稱:“期運既至,大法方隆。但經始興,未盡顯行。”而其《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亦稱:“但正教始興,天書寶重,大有之蘊,不盡顯行。”二者都是說“元始舊經”沒有完全披露出來。然而,另一方面,陸修靜卻又非常強調現有已出“元始舊經”所具有的度人救世的重大意義。其《靈寶經目序》稱:“十部舊目,出者三(六)分。雖玄蘊未傾,然法輪已遍于八方,自非時交運會,孰能若斯之盛哉!”而《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亦稱:“然即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根末表里,足相輔成;大乘之體,備用不少。”而敦煌本《靈寶經目》陸修靜即明確稱:
……都合前元始[舊經],新、舊經見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為三十五卷。或為三十六卷。
因此,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實際上已經證明了敦煌本《靈寶經目》就是元嘉十四年的經目。而這一條材料也非常確切地證明了敦煌本陸修靜《靈寶經目》,應屬于陸修靜撰寫《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之前的經目,而不是泰始七年(471)陸修靜奉宋明帝敕編成的《三洞經書目錄》中靈寶經的目錄。
3.從陸修靜著作的整體論述看“元始舊經”之“出者六分”的必然性
還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之所以將敦煌本《靈寶經目》確定為公元437年的經目,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出者三分”,并不真正符合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上下文的表述。因為陸修靜在該《序》中,一方面對于在他之前和與他同時代的人偽造古靈寶經的行為,都給予了極其嚴厲的譴責,并嚴厲禁止道教中人繼續創作任何新的古靈寶經典;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在公元437年之后,無論是“元始舊經”抑或“新經”,還在繼續增加擴充。也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能夠證明陸修靜本人以及“他身邊的天師道道士們”直接參與了古靈寶經的創作。而堅持敦煌本《靈寶經目》作成于公元471年的研究者,在某種意義上說,似乎都有意地忽略了這樣一個最重要的前提。
為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靈寶經目序》這一特定文本中,看看陸修靜整理之前的古靈寶經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尤其是要理解陸修靜甄別和整理古靈寶經究竟包括了哪些具體內容。其《靈寶經目序》稱:
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學士宗竟,鮮有甄別。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尋覓,甫悟參差,或刪破上清,或采搏余經,或造立序說,或回換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圖,或以充舊典,或別置盟戒。文字僻左,音韻不屬,辭趣煩猥,義味淺鄙,顛倒舛錯,事無次序。考其精偽,當由為狷狂之徒,質非挺玄,本無尋真之志,而因修窺閱,假服道名,貪冒受取,不顧殃考,興造多端,招人宗崇。敢以魚目,廁于隋侯之肆;輒將散礫,托于和氏之門。衒誑愚蒙,誣誷太玄。既晚學推信,弗加澄研,遂令精粗糅雜,真偽混行。視聽者疑惑,修味者悶煩。上則損辱于靈囿,下則恥累于學者。進退如此,無一可宜。徒傾產疲力,將以何施?夫輕慢之咎既深,毀謗之罪靡赦。
所謂“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學士宗竟,鮮有甄別”,均是指古靈寶經存在大量魚目混珠的情況,“元始舊經”和“新經”的總數已達到55卷之多。而陸修靜所稱“既加尋覓,甫悟參差。或刪破上清,或采搏余經,或造立序說,或回換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圖,或以充舊典,或別置盟戒”,則是說當陸修靜對這些經書加以整理研究之后,他也才明白了這些經書所存在的問題。他認為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1)有些經書是從上清經典剽竊而來的;(2)有的是依據對其他各種經書的摘錄而形成的;(3)有的是偽造了經書的序言;(4)有的是替換了原來的篇目;(5)有的增加了章句;(6)有的經書制作了新的符圖;(7)特別是所謂“或以充舊典,或別置盟戒”,是說有人用虛假的經文去充當“元始舊經”。而有的則在經書中添置了其它的盟誓文字和戒律;(8)這些偽濫的經書內容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文字僻左,音韻不屬,辭趣煩猥,義味淺鄙,顛倒舛錯,事無次序”。
陸修靜對于出現這樣嚴重偽濫情況的原因也作了專門分析。他認為,一方面是“狂狷之徒”,不懼怕因果報應而膽大妄為地加以粗制濫造。他說:“考其精偽,當由為狷狂之徒,質非挺玄,本無尋真之志,而因修窺閱,假服道名,貪冒受取,不顧殃考,興造多端,招人宗崇。敢以魚目,廁于隋侯之肆;輒將散礫,托于和氏之門。衒誑愚蒙,誣誷太玄。”然而,另一方面,則也是因為后來的修道者真偽不分,盲目崇信所造成的。他說:“既晚學推信,弗加澄研,遂令精粗糅雜,真偽混行。視聽者疑惑,修味者悶煩。”而靈寶經書真偽不分所導致的嚴重后果,則是“上則損辱于靈囿,下則恥累于學者。進退如此,無一可宜。徒傾產疲力,將以何施?夫輕慢之咎既深,毀謗之罪靡赦”。所謂“上則損辱于靈囿”,“靈囿”在中國古代指供帝王狩獵和游樂的園林。《詩經·大雅·靈臺》記述了最早的周文王靈囿,稱“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此代指帝王的大業。可見,陸修靜認為偽濫的經書不但損害污辱了帝王的大業,也嚴重敗壞了道教的聲譽。
正因為如此,陸修靜既表現了對有意造偽者行為的極端深惡痛絕,又對眾多信奉者被蒙蔽感到極為痛心疾首。同時也表明陸修靜自己是堅決反對偽造靈寶經的。其稱:“余少躭玄味,志愛經書,積累錙銖,冀其萬一。若信有可崇,何茍明言,坐取風刀乎!”意即自己從年少之時就開始崇信道教,敬奉靈寶經書,而且盡力做經書的搜集和積累。如果道教信仰本身是值得尊崇的,那么,我為什么還要隨隨便便地公開來說,以招致死后下地獄的惡報呢?所謂“坐取風刀”,在古靈寶經中常見,代表地獄惡報。顯然,陸修靜在此是以極其虔誠的道教信仰,來向天神誓言其自己的所作所為均符合靈寶經本身的實際情況。
歷史資料證明,陸修靜本人與江南“葛氏道派”之間并沒有明確的傳承關系。而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批判道門內部偽造古靈寶經的同時,也強調“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尋覓,甫悟參差”,“余少躭玄味,志愛經書,積累錙銖,冀其萬一”。這些都顯示陸修靜所整理的古靈寶經經書,主要源于他自己長期以來對古靈寶經的搜集和信仰。[注]王承文《陸修靜道教信仰從天師道向靈寶經轉變論考——以陸修靜所撰〈道門科略〉為起點的考察》(上篇、下篇),《宗教學研究》2014年第2期、第3期。所謂“甫悟參差”,“甫”是指方才,剛剛,意即雖然他對古靈寶經的搜集研究的過程很長,但是真正領悟并能分清其中真偽混雜情況,卻是在其撰寫《靈寶經目序》之前不久。而其撰寫《靈寶經目序》之時,距離東晉安帝隆安(397-401)末年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注][梁]陶弘景《真誥》卷19《翼真檢第一》,《道藏》第20冊,第604頁。,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而此時有大量“元始舊經”和“新經”已經流傳于世。《靈寶經目序》稱:
元嘉十四年某月日,三洞弟子陸修靜敬示諸道流。相與同法,弘修文業,贊揚妙化,興世隆福。每欣一切,遭遇慈澤,離彼惡道,入此善場,逍遙長樂,何慶如之!
以上都是陸修靜對當時道門中人共同修奉靈寶經盛況的描述。而且陸修靜又進一步強調,此時古靈寶經“雖玄蘊未傾,然法輪已遍于八方,自非時交運會,孰能若斯之盛哉!”也證明此時道門內已經有大量道士正在修習靈寶經。也就是說,在公元437年之前,古靈寶經早已成為道門內部普遍修奉的經典。陸修靜作為道門領袖,他對前人和同時代的人大量偽造古靈寶經的行為作了極為嚴厲的批判和譴責,并把他認定為偽造的大量假古靈寶經排除在其《靈寶經目》之外,而且又以其道教信仰來誓言他自己甄別古靈寶經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似乎很難想象,此后他自己卻又明目張膽地鼓動“葛氏道派”中人或者“他身邊的天師道道士們”繼續創作新的古靈寶經,甚或自己還親自動手來創作古靈寶經。并且直到公元471年編纂《三洞經書目錄》時,他卻又將這些經典名目堂而皇之地都編在一起。
《正統道藏》和敦煌遺書共保留有陸修靜著作八種,即《陸先生道門科略》、《靈寶經目序》、敦煌本《靈寶經目》、《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洞玄靈寶說光燭戒罰燈祝愿儀》、《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太上洞玄靈寶眾簡儀》、《洞玄靈寶五感文》等。根據我們的研究,陸修靜對古靈寶經嚴謹而忠實的態度,也貫穿在其一系列現存著作中。除了《道門科略》專門闡述天師道的宗教傳統、制度和教義思想之外,陸修靜的其它所有著作,則都是通過大量直接征引古靈寶經并且按照古靈寶經教義思想編撰而成的。在這些著作中,陸修靜把對古靈寶經原文的征引與他自己的發揮和論述都作了相當清晰的區別。也證明了他自己不可能參與古靈寶經的創作,同時也決不可能容忍其同時代的其他人創作新的經典以冒充古靈寶經,然后他自己還特地加以征引。例如,其《太上洞玄靈寶眾簡儀》稱:
《明真》、《玉訣》并有其詳,而晚學暗惰,志性淺略,遇見一科,不加精尋,率意施用,遂致矯錯,亡首失尾,永不悟非。若斯之徒,常為痛心,視其淪溺,懼傷慈教,謹依舊典,撰投簡文次第,復為甲乙,注解法度,以啟昧者之懷,自為門人成軌,豈茍施悠悠者哉。[注]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眾簡文》,《道藏》第6冊,第563頁。
我們將陸修靜的《太上洞玄靈寶眾簡儀》,與相關古靈寶經的原文逐字逐句地核對,可以發現陸修靜這一著作95%的內容,其實都能在古靈寶經中找到原始出處,而陸修靜本身也將其出處作了盡可能明確的說明。至于陸修靜自己的注解,則以小字加以區別。[注]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17-534頁。而這就恰恰證明了陸修靜對待古靈寶經極其嚴肅和恭敬的態度。其《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亦稱:
自靈寶導世以來,相傳授者,或總度三洞,同壇共盟,精粗糅雜,小大混行。時有單受洞玄,而施用上法,告召錯濫,不相主伍。或采博下道,黃赤之官,降就卑猥,引屈非所,顛倒亂妄,不得體式,乖違冥典,迷誤后徒。臣每晨宵嘆惋,內疚泣血。既真師渺邈,不可希期鉆求,世學永無其文。事要急用,實宜充備。[注]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道藏》第9冊,第840頁。
以上一方面對靈寶經真偽混亂的情形給以嚴厲批判,另一方面則表明要加以糾正。按照陸修靜自己的說法,其在編撰該書的過程中,“執筆戰栗,形魂交喪,懼以謬越致罪,又慮造作招考,進退屏營,如蹈刃毒。繕治雖竟,不敢擅用,謹潔身清齋于三寶御前,誦讀一過。恩惟太上眾尊、玄中大法師,垂神照鑒,矜察所啟。若萬有一毫之補,合請施行。如其不允,輒當毀除。可否之宜,要以靈瑞為證,愿特賜告效,伏須感應”。以上足見其態度極其虔誠真摯。同時陸修靜亦是要人們相信其編撰此書,是完全忠實于古靈寶經經典本義的。
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中,陸修靜也說明了自己編撰該書所依據的主要經典及其對待靈寶經典的態度。其文稱:
臣敢以囂瞑,竊按《金》、《黃》二箓、《明真》、《玉訣》、《真一自然經訣》,準則眾圣真人授度之軌,敷《三部八景神官》,撰集登壇盟誓,為立成儀注。執筆戰栗,形魂交喪,懼以謬越致罪,又慮造作招考,進退屏營,如蹈刃毒。繕治雖竟,不敢擅用,謹潔身清齋于三寶御前,誦讀一過。恩惟太上眾尊、玄中大法師,垂神照鑒,矜察所啟。若萬有一毫之補,合請施行。如其不允,輒當毀除。可否之宜,要以靈瑞為證,愿特賜告效,伏須感應。謹啟:臣修靜誠惶誠恐,稽首再禮以聞。臣陸修靜謹進。
陸修靜稱其“撰集登壇盟誓,為立成儀注”,明確提到所依據的最主要材料,包括這樣一些古靈寶經:(1)“《金》、《黃》二箓”,是指“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寶經金箓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2)“《明真》”是指“元始舊經”《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3)“《玉訣》”是指“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4)“《真一自然經訣》”則是指“新經”《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5)所謂“敷《三部八景神官》”,是指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錄的“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三部八景自然神真箓儀》,《道藏》本稱為《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
根據我們的研究,該書90%以上的內容均源自其對13部古靈寶經的征引。其中“元始舊經”包括:《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太上洞玄靈寶經金箓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洞玄靈寶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圖經》等。而其所征引的“新經”包括:《太上玉經太極隱注寶訣》、《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等。在這部著作中,陸修靜亦盡可能地將其所征引的古靈寶經經文的出處加以說明,并使之與自己的論述區分開來。
陸修靜在劉宋元嘉三十年(453)撰寫的《洞玄靈寶五感文》,是其以靈寶經法思想為基礎對漢晉以來道教齋法的第一次總結。其文稱:
至道清虛,法典簡素,恬寂無為,此其本也。而世物浮偽,鮮能體行,競高流淫,信用妖妄,倚附邪魅,假托真正,君子小人,相與逐往,昏迷長寢,曾莫甄悟。致上危神器,下傾百姓,滅身破國,猶不以戒。至乃濁亂正炁,點染清真,毀辱大道,可為痛酷。[注]陸修靜《洞玄靈寶五感文》,《道藏》第32冊,第618頁。
以上也反映了陸修靜將道教齋戒儀式是否真正符合“法典”即道經原典,看成是極其莊嚴神圣的大事。并認為偽濫的經書以及齋法,將會“上危神器,下傾百姓,滅身破國”,“濁亂正炁,點染清真,毀辱大道”。從該書所記載的靈寶齋法即金箓齋、黃箓齋、明真齋、三元齋、八節齋、自然齋六種齋法來看,陸修靜對以上六種齋法概括性的論述,都能在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包括《無上秘要》齋法對相關古靈寶經的征引)中找到原始出處和相關對應。
需要指出的是,小林正美先生其實也認為陸修靜本人并沒有直接參與古靈寶經的創作。[注][日]小林正美著,李慶譯《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30頁。然而,從現存陸修靜著作與古靈寶經之間的關系來看,我們很難想象陸修靜一邊對前人偽造古靈寶經的行為加以嚴厲譴責和批判,一邊卻又允許甚或鼓勵身邊的道士們繼續大量創作古靈寶經。學術界近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種新的觀點,認為陸修靜雖然表面上嚴厲譴責道教中人偽造靈寶經,而他自己卻一方面續寫完成了人間實際存在的元始系《靈寶經》,另一方面又大量親自創作了原本未出的“元始舊經”。[注]王皓月《再論〈靈寶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5-90頁;王皓月《靈寶經の研究—陸修靜と靈寶經の關系を中心に》,早稻田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從現存的各種資料來看,我們認為這種觀點還需要重新斟酌。
總之,從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整個文本的結構和前后語境來看,很顯然,他的目的決不是為“葛氏道派”的道士們抑或“他身邊的天師道道士們”繼續創作古靈寶經張目,也決不是為他自己對古靈寶經進行大規模修改、續寫甚至親自來重新創作而張目。其真正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批判和譴責業已存在的古靈寶經真偽混雜的情況,并要努力做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另一方面也是要堅決遏止禁絕道教內部繼續偽造古靈寶經的行為。
(三)《靈寶經目序》末尾所稱“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與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對應關系
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的末尾,實際上已經指明了其《靈寶經目序》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對應關系。而這一點恰恰也是前人比較忽略的一個重要證據。其文稱:
慮有未悉,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注解意疑者略云爾。
所謂“慮有未悉”,是指陸修靜一方面憂慮道教中人不能知曉和分辨古靈寶經魚目混雜的情況,另一方面則是擔心在經過他甄別整理之后,這種情況又重新出現,所以他特地要加以逐條說明。以上的“條”字是一個動詞,古代有“條陳”、“條寫”、“條具”、“條述”、“條列”、“條白”等表達方式,還有“條分件系”的表達。而這里的“條”就是指逐條梳理校核之義。所謂“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就是指陸修靜在《靈寶經目》中,既逐條陳述了“《舊目》”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各經“已出”或“未出”的情況,也逐條敘述了各“新經”已出世的情況。而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對《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元始舊經”之“已出”或“未出”,以及“新經”的出世情況都有非常明確的說明,證明《靈寶經目序》所述與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實際狀況是完全符合的。
小林正美先生在其新著中,一方面根據《靈寶經目序》所稱“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認為其中“并仙公所授事”是指“仙公新經”,并強調這一種表達能夠證明“仙公系《靈寶經》在元嘉十四年都已經被編纂了”。[注][日]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譯《新范式道教史的構建》,第134頁。然而,另一方面他似乎又過于執著于“出者三分”這樣一種非常孤立的表達,堅持認為大量“元始舊經”都是在元嘉十四年以后才被創作出來。不過,這一點卻與他新提出的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成書于“元嘉十八年(441)”的觀點又是相矛盾的。[注]見本文前面對《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年代的討論。
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理解,陸修靜所稱“今條《舊目》所出”,實際上也能證明真正出世的“元始舊經”都已經通過《靈寶經目》列舉齊備了。不存在用新創作的古靈寶經來繼續補充這份經目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靈寶經目序》所稱“十部《舊目》,出者三分”,完全有可能就是“出者六分”。至于陸修靜所稱“注解意疑者略云爾”,是指陸修靜除了在《靈寶經目》中逐條陳述“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出世情況之外,還對“元始舊經”和“新經”各自出世和分卷總的情況作了概括性的說明,對靈寶經“十二部”的名稱及其含義也作了簡約的注解。而這一點也是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的情況相符合的。
我們還要特別強調的是,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既然明確說正是因為“慮有未悉”,所以他才“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一方面表明他已經將古靈寶經“已出”和“未出”的情況在當時道門內部廣而告之;另一方面,他自己對道門內部偽造靈寶經的現象作了如此嚴厲的批判,也就表明了他要禁止道門內部繼續偽造或重新創作古靈寶經的事情再次發生。因此,可以確定,在《靈寶經目序》最末的這一句話之后,緊接著的應該就是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至于《三洞經書目錄》中洞玄部靈寶經部分,應該仍然是按照公元437年編定《靈寶經目》時的原貌來編纂的。反之,如果他在公元437年甄別整理古靈寶經之后,卻又將新增加的古靈寶經重新編入《三洞經書目錄》的話,一方面他必須要重新修改他在437年《靈寶經目》中對相關“元始舊經”所作出的“已出”或“未出”的具體說明;而另一方面,也就意味著他完全背信棄義,公然也公開地違反了他自己此前的誓言和承諾。
至南朝中期,宋文明所作《靈寶經義疏》除了輯錄陸修靜《靈寶經目》之外,又注稱:“后有三十五卷偽目,仍在陸《源流》卷末,不錄入此也。”以上是指在陸修靜編成《靈寶經目》之后,曾經另有一部關于偽古靈寶經的“三十五卷偽目”。因為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稱“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而陸修靜認為這“新、舊五十五卷”中恰恰都是真偽混淆的。因此,在被陸氏確定為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之外的經書,原則上都屬于“偽經”,其數額大致是23卷,再加上在元嘉十四年之后至宋文明重新整理古靈寶經之前新出的12卷偽古靈寶經,它們共同構成了所謂的“三十五卷偽目”。而這也證明了自陸修靜于元嘉十四年確立《靈寶經目》后,任何未被陸修靜《靈寶經目》著錄的古靈寶經,都被視為“偽經”。因此,宋文明所稱“三十五偽目”的存在,恰恰證明了陸修靜作為道門領袖,其在公元437年所進行的“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等做法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并且在道門內部具有非常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宋文明本人也堅持了陸修靜所確立的原則。他在注解《靈寶經目》時稱:“正文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二卷見行于世,余十四卷猶隱天宮。”所謂“正文有三十六卷”,就是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錄的“十部妙經三十六卷”即“元始舊經”。而“其二十二卷見行于世,余十四卷猶隱天宮”,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對“元始舊經”的著錄情況相符合。[注][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云笈七簽》卷6《三洞經教部·三洞品格》稱:“元始天王告西王母曰:‘《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有十部妙經,合三十六卷。’是靈寶君所出,高上大圣所撰,具如《靈寶疏釋》,有二十一卷已現于世,十五卷未出。”(第93頁)按以上《靈寶疏釋》就是宋文明《靈寶經義疏》。
至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甄鸞上《笑道論》三卷,該書“道經未出言出者”條稱: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檢今《經目》,并云見在。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并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勅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余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注][北周]甄鸞《笑道論》卷下,載道宣《廣弘明集》卷9,《大正藏》第52冊,第151頁。
可見,從宋文明到南北朝末期的甄鸞寫成《笑道論》之間,原《靈寶經目》中注明“未出”的一批“元始舊經”亦已經出世。所謂“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與宋文明稱“余十四卷猶隱天宮”含義相同。至于其“一十五卷”和“十四卷”的區別,僅僅是對相關經典卷數的計算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四)《靈寶經目序》與敦煌本《靈寶經目》所稱古靈寶經數目的計算方式
中外學術界有關古靈寶經出世的分歧和爭論,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因為對這些經典數量計算方式的不同而引發。因此,我們不妨將《靈寶經目》中幾種計算方式詳列如下。
(1)敦煌本《靈寶經目》陸修靜原文稱:“都合前元始[舊經],新舊經見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為三十五卷,或為三十六卷。”以上所謂“三十二卷真正之文”,應是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即“二十一卷已出”的“元始舊經”,再加上“十一卷”已出的“新經”,共32卷。
(2)敦煌本《靈寶經目》陸修靜所謂“今為三十五卷”,應是指“今分成二十三卷”的“元始舊經”,再加上分成十二卷的“新經”。因為在這種計算中,《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序經》已不是原來的一卷本,而是“仙公在世時所得本,是分為二卷”,共為35卷。
(3)敦煌本《靈寶經目》陸修靜所稱“或為三十六卷”,指“元始舊經”和“新經”總數為36卷。在這種計算方式中,“元始舊經”已經變成了“今分成二十三卷”,加上十三卷“新經”。因為《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序經》為“今人或作三卷”。因此,共36卷。
(4)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稱:“然即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所謂“并仙公所稟”,這里的“并”是指再加上“仙公所稟”的“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即“新經”。陸修靜認為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經典中真正可信的,加在一起為35卷。根據我們前面的考證,“新經”和“舊經”共35卷,是指“今分成二十三卷”的“元始舊經”,再加上分成十二卷的“新經”。此與敦煌本《靈寶經目》所稱“都合前元始[舊經],新舊經見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為三十五卷”相符合。
六、結論
有關古靈寶經的出世年代,一直是近三十多年來國際道教學界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國內外靈寶經研究者群體的擴大,相關爭議和分歧不是在逐步縮小,而是在越來越擴大。在相關討論中,敦煌本《靈寶經目》本身的結構及其成立年代具有最為關鍵的意義。在目前和未來不可能有更多新材料發現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更加重視對現有文本資料的深入解讀和內在理解。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早在公元437年陸修靜編撰《靈寶經目序》和《靈寶經目》之前,古靈寶經的創作者實際上就已經編制了最早的經目——《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這個經目與《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等一批最早的“元始舊經”的創作基本上是同時完成的,并且是按照“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的結構來設計的。在古靈寶經的創作者看來,“元始舊經”在名義上均為元始天尊所說,而且均由《靈寶赤書五篇真文》直接演化而來,因而具有“新經”所遠不能比擬的神圣性和崇高地位。而《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的存在,也證明“元始舊經”在本質上是一批具有統一性經教體系和內在邏輯結構的經典。而相關“篇目”則代表它們在闡述靈寶經教體系中承擔不同的使命,因而每一部經書的內容和側重點雖然有較大的不同,但是在一些最根本性的教義思想等方面卻又是相同和相通的。《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既是陸修靜《靈寶經目》中《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的直接來源,也是陸修靜在公元437年完成甄別和整理“元始舊經”最主要的依據。陸修靜對“元始舊經”的甄別和整理,一方面是依據這個經目對真偽混雜的“元始舊經”進行去偽存真,另一方面則明確標明各部“元始舊經”之“已出”和“未出”的狀況。至于古靈寶經“新經”在本質上應是對所有“元始舊經”的詮釋、補充和進一步發展。除了《太上靈寶五符序》之外,“新經”的出世一般都是在“元始舊經”之后。
我們的討論也證明,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所說的《靈寶經目》,其實就是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這兩個文本之間具有內在的不能分割的關系。而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最核心的教義思想具有高度的連貫性。與陸修靜《靈寶經目序》一樣,敦煌本《靈寶經目》亦作成于劉宋元嘉十四年(437)。而《靈寶經目》所著錄的所有“元始舊經”和“新經”,其最晚成書也應在元嘉十四年之前的劉宋前期。而且,現存敦煌本、《道藏》本由陸修靜本人所撰寫的多部經書,其內容大都是在大量而直接地征引古靈寶經的基礎上形成的。陸修靜本人及其身邊的道士們都屬于古靈寶經的信奉者,并未直接參與過古靈寶經的創作。同時,我們還認為“元始舊經”和“新經”均為“葛氏道派”所創作。該經目中“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劃分,保存的就是古靈寶經問世之初的本來面目。陸修靜并未“變更”相關古靈寶經的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