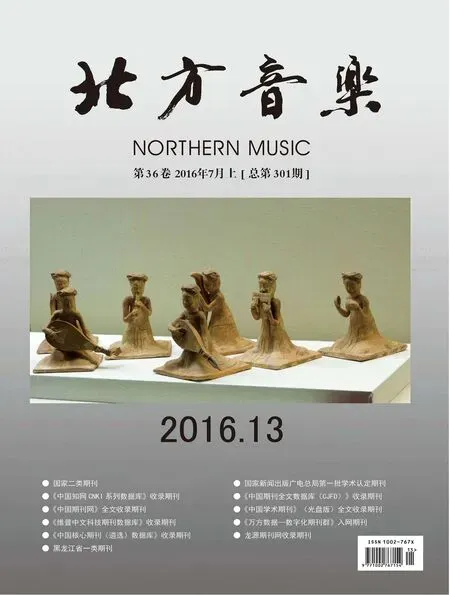20世紀西方音樂變化之“鐘擺現(xiàn)象”
王夢熠(漢口學院音樂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20世紀西方音樂變化之“鐘擺現(xiàn)象”
王夢熠
(漢口學院音樂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20世紀的西方音樂流派紛爭,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態(tài)勢:印象主義音樂、表現(xiàn)主義音樂、新古典主義音樂、序列主義音樂、偶然音樂、電子音樂、具體音樂、噪音音樂、簡約派音樂、新浪漫主義音樂等等,形成如此眾多的流派。除了其社會環(huán)境、思想觀念、個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之外,筆者將借用物理學中“鐘擺理論”的觀點,以表現(xiàn)主義音樂和新古典主義音樂、序列主義音樂和偶然音樂為例,來闡釋20世紀西方音樂經歷著從一端走向另一端兩極并存且相互交替的發(fā)展規(guī)律,正如鐘擺從一端走向另一端,周而復始的運功。
20世紀音樂;流派;思想觀念;鐘擺理論;對立
20世紀西方音樂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由于多元化的音樂語言及風格的呈現(xiàn),致使其形成了諸多不同的流派,如印象主義、表現(xiàn)主義、新古典主義、序列主義、偶然音樂、電子音樂、具體音樂、噪音音樂、簡約派、新浪漫主義等等。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有很多,研究者往往將其歸因于社會環(huán)境、思想觀念、個人性格等因素,筆者竊以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并值得我們學界普遍關注、值得玩味的原因,那就是“鐘擺理論”。
一、鐘擺理論釋義
“鐘擺理論”即一個鐘擺,時而朝左,時而朝右,周而復始,來回擺動。其中,鐘擺總是圍繞著一個中心值在一定范圍內作有規(guī)律的擺動,所以被冠名為“鐘擺理論”[1]。這原本是一個物理學名詞,筆者認為同樣也適用于音樂領域。
戴維·伊文說過,“一種風格被引入極端之后,作曲家必然要以另一種極不同的音樂風格與之對抗。”[2]這從西方音樂的發(fā)展脈絡上看是顯而易見的,就拿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新古典主義音樂為例,它的出現(xiàn)有社會的原因、戰(zhàn)爭的原因,心靈上受到巨大摧殘的聽眾們希望有簡明、清晰、樸素、自然的音樂來安撫內心的傷痛,因此新古典主義就應運而生。實際上這僅僅是社會方面體現(xiàn)的一個原因,若從音樂本身來看,新古典主義的出現(xiàn)也是音樂發(fā)展的必然之路。自晚期浪漫主義音樂以來的各種作曲技法,都對傳統(tǒng)的作曲技法進行了突破,進入20世紀后,這種對傳統(tǒng)的突破更為突出,比如歌唱性的旋律被不流暢、零碎的旋律片段取代;功能和聲被新的和聲理論替代;明確的調性被無調性替代;配器上各種新花樣的出現(xiàn)無不彰顯出音樂上的現(xiàn)代特點。一種音樂要素的突破,在聽覺上便會產生與傳統(tǒng)較大的不同,更何況是對音樂各要素的突破必然最終會走向極端,所以才有了新古典主義音樂的誕生。
因此,筆者認為這種物極必反的發(fā)展規(guī)律正是符合鐘擺理論的特點,這體現(xiàn)的是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音樂史的發(fā)展也同樣遵循著這個規(guī)律。
二、鐘擺理論中的兩極在20世紀西方音樂中的體現(xiàn)
20世紀絢麗多彩的音樂文化中,鐘擺理論清晰地體現(xiàn)于其中,最為對立的要數表現(xiàn)主義音樂和新古典主義音樂、序列主義音樂和偶然音樂。
(一)表現(xiàn)主義音樂與新古典主義音樂
這兩種音樂大致出現(xiàn)在20世紀早期。從音樂觀念上看,勛伯格認為,“藝術的本質與人的情感密切相關。藝術價值所要求的禮節(jié)性并非僅僅為了理想上的滿足,同時也是為了情感上的滿足。然后無論創(chuàng)作者要激發(fā)的情緒是什么,他的想法一定要表達出來。‘一件藝術品,只有當他把作者內心激蕩的感情傳達給聽眾的時候,他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聽眾內心情感的激蕩’。”[3]因此,他創(chuàng)立十二音音樂的目的就是更清晰表現(xiàn)所要表現(xiàn)的內容。與他相反,斯特拉文斯基卻說過一段話:“據我看來,音樂從它的本質來說,根本不能表現(xiàn)任何東西,不管是一種感情、一種精神狀態(tài)、一種心理情緒、一種自然現(xiàn)象……表現(xiàn)從來不是音樂的本性,表現(xiàn)絕不是音樂存在的目的。即使音樂看起來在表現(xiàn)什么東西,那只是一種幻想,而不是現(xiàn)實。那僅僅是由于長期形成的默契,作為一種標簽、一種慣例,我們所給予、所強加于音樂的一種附加的屬性——總之,是我們不自覺地或由于習慣勢力對音樂的本質所誤解的一面。”[4]從上述對立的觀點就清晰地體現(xiàn)了二人不同的音樂觀念。勛伯格倡導音樂的“表現(xiàn)”作用,而斯特拉文斯基卻強調音樂的“非表現(xiàn)”功能。在兩種不同音樂觀念的指導下,音樂風格的不同更是自然而然的事,表現(xiàn)主義音樂怪誕、不協(xié)調、帶有刺激性、情感上的宣泄、缺乏邏輯力,而新古典主義音樂清晰、簡明、樸素、情感上的節(jié)制、注重內在的邏輯性。從音樂創(chuàng)作手法上來看也有很大的區(qū)別,西方音樂的調性音樂在浪漫主義晚期遭到了極大突破,勛伯格的十二音音樂更往前進了一步,采用無調性作曲技法。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雖然里面有著清晰可辨的現(xiàn)代氣息,但總體上說是有調性的。斯特拉文斯基認為自己的事業(yè)是修補舊船,而不是向勛伯格那樣開辟新航線。由此可見,從音樂觀念、音樂風格、音樂創(chuàng)作手法三個方面,就可以看到兩種音樂風格如同是鐘擺的兩個極端,呈現(xiàn)出對立的狀態(tài)。
(二)序列主義音樂與偶然音樂
這兩種音樂出現(xiàn)在20世紀中期。它們也如同鐘擺的兩端,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偶然音樂是“作曲家把一些偶然的、不確定的或沒有預先設計好的因素,帶進了作品的創(chuàng)作或表演之中。”[5]例如施托克豪森在一張大樂譜紙上寫上幾個音樂片段,在演奏過程中,演奏者可以在順序上作自由的選擇,這就是偶然音樂作曲家們常使用的一種方法。偶然音樂中的不確定性實際上在巴洛克時期就有明確的體現(xiàn),回顧巴洛克時期的“通奏低音”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作曲家只寫出高低兩個聲部,并在低音聲部的上方、下方或旁邊標記相應的阿拉伯數字,演奏者根據數字即興的表演,可是這種不確定性逐漸被明確的記譜法所取代。從西方音樂的發(fā)展來看,作曲家們更多追求的是音樂記譜的精確性。各種音樂記號的出現(xiàn),甚至加上文字對音樂的解釋,都是試圖更全面地控制音樂,而序列主義音樂將這種控制走向了極端。在這里又要提及勛伯格,序列主義音樂是來源于勛伯格的十二音音樂,十二音音樂一方面是對調性音樂的瓦解,另一方面是在理性思想指導下,對音高排列的嚴格控制,隨后對節(jié)奏、力度、音樂等各要素都要控制的時候,序列主義音樂完全確立。因此,序列主義音樂的出現(xiàn)也有其必然的歷史規(guī)律。序列主義音樂將音樂中的理性推向了極端,偶然音樂的出現(xiàn),正是對這種處處都要進行精密設計的作曲技法的一種突破。
總之,表現(xiàn)主義音樂與新古典主義音樂、序列主義音樂與偶然音樂共同存在于一個時期,出現(xiàn)了兩極并存的現(xiàn)象,并且在20世紀音樂中,兩極并存的現(xiàn)象比先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顯而易見,并且到達兩極的時間周期較短。由此鐘擺理論在20世紀音樂的發(fā)展規(guī)律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但是,筆者認為,戴維·伊文的觀點①只能體現(xiàn)鐘擺理論兩級的一面,他只是從橫向上來看待事物交替發(fā)展的規(guī)律,卻沒有從縱向上來看待事物發(fā)展的前續(xù)后繼。鐘擺理論不僅僅只有從一端擺向另一端的發(fā)展,還要有一個來回擺動的中心軸,筆者下文稱其為“中心值”,也就是說它的擺動始終脫離不了中心。放在音樂領域來看,這應該是指在同一個時代作曲家在音樂中所保留的共同特點。因此,事物發(fā)展過程中物極必反的同時,必然還存在著共性,筆者認為,這才是鐘擺理論的雙層內涵。
三、鐘擺理論的中心值在20世紀西方音樂中的體現(xiàn)
從表現(xiàn)主義音樂到新古典主義音樂的轉變,從序列主義音樂到偶然音樂的出現(xiàn),都體現(xiàn)著兩級的規(guī)律,那么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共性?是否像鐘擺理論所講的,有一個中心值?
首先來看表現(xiàn)主義音樂和新古典主義音樂,上文已列舉這兩種音樂在觀念、風格、創(chuàng)作手法上的不同,但他們卻無法超越這個時代的限制。勛伯格創(chuàng)立的十二音音樂,在對音高的嚴格控制中體現(xiàn)的理性思維與新古典主義音樂強調客觀、理性是一致的,也正是因為這種相通性,使得斯特拉文斯基晚年也采用十二音音樂作曲技法。這種理性的思維使得二人十分注重結構的數理關系。例如勛伯格十二音作曲技法中的一些做法,讓人覺得他像是在做數學題。斯特拉文斯基在晚年也談到“音樂在任何情況下都更接近于數學而不是文學。……音樂的本身之所以是數學,是因為它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形式總是抽象的概念。”[6]表現(xiàn)主義音樂很大程度上是對晚期浪漫主義音樂的繼承,甚至是更進一步,但是勛伯格并沒有繼承馬勒那樣龐大的樂隊編制,相反他在配器上偏重小型室內樂,這一點與斯特拉文斯基的創(chuàng)作是一致的。斯特拉文斯基在早期的芭蕾舞劇《火鳥》《彼得魯什卡》《春之祭》中采用了較為龐大的樂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就已表現(xiàn)出偏向小型創(chuàng)作上的特點。代表性的作品如1918年創(chuàng)作的《士兵的故事》,可能是受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所限,但這與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追求是不謀而合的。他只使用七件樂器:小提琴、低音提琴、單簧管、大管、短號、長號,以及打擊樂器,并且表演者僅僅需要五位,一位朗誦者和四位演員。在之后的創(chuàng)作中斯特拉文斯基的這種偏重小型室內樂形式的做法更為明顯。他們二人的這種做法又共同的體現(xiàn)了對19世紀晚期浪漫主義音樂的逆反。同時,他們都用單一主題代替之前復雜的主題結構。十二音音樂采用單一的音高序列,通過倒影、逆行、倒影逆行的發(fā)展手法來推動音樂的發(fā)展。斯特拉文斯基最喜愛的形式就是賦格,他一直對古老的對位法具有很大的興趣。
其次,再來看序列主義音樂與偶然音樂,兩者之間的不同前文已討論過,但對作為非西方音樂史專業(yè)的學習者來說,聽這兩種音樂單單從音響上似乎聽不出來有什么不同,均有怪誕、不協(xié)調、難以捉摸的特點,似乎感覺它們最終呈示給聽眾的音響都是一樣的,除非另做譜例分析。而正是這兩種音樂所體現(xiàn)的共同特點又是作為20世紀音樂的一個重要特征。
由此可見,對于序列音樂與偶然音樂來講,這兩種音樂在音響上的共同特點、所共同體現(xiàn)的時代文化氛圍,好比是鐘擺理論的中心值,而這兩種音樂在理性與感性思維上的兩個極端就好比鐘擺理論的兩極。
這種理性與感性的交替發(fā)展也成為西方音樂發(fā)展中的一大規(guī)律。古希臘注重精神文化,崇尚理性,而古羅馬卻是一個注重感官享受,崇尚感性的國家。進入中世紀后,在基督教思想上建立起來的音樂強調“禁欲”主義,用理性的思想控制音樂的發(fā)展。進入文藝復興時期,隨著人文主義思想的提倡,這個時期的音樂豐富多彩,在中世紀被壓抑的各種情感在這個時期有了釋放,直到巴洛克時期亨德爾提倡的情感原則,使得感性因素在這兩個時期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但是,隨后新興階層的出現(xiàn),要求用“理性”作為武器,因此作曲家們在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著理性的原則。在浪漫主義時期,作曲家們卻反叛一切“理性的”束縛,音樂再次回到“感性”的時代,到20世紀新古典主義音樂又強調客觀理性,序列主義音樂強調理性控制。
由此可見,西方音樂史的發(fā)展總是經歷著從一端走向另一端的發(fā)展歷程,正像是鐘擺從一端走向另一端,周而復始。20世紀社會環(huán)境的高度變化發(fā)展,使得鐘擺理論成為在這個世紀音樂不斷變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樣變化,這個時代總是會有它獨有的特征,這也是整個社會音樂文化的共性。筆者認為鐘擺理論是20世紀音樂,甚至整個西方音樂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也是20世紀音樂多元化發(fā)展的趨勢。
注釋:
①戴維·伊文的觀點參見第一頁。
[1] http://baike.baidu.com/view/541482.htm。
[2]保·朗多米爾.《西方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
[3][美]彼得·斯·漢森.《二十世紀音樂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64.
[4][美]彼得·斯·漢森.《二十世紀音樂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150.
[5]于潤洋.《西方音樂通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6:389.
[6]方之文.《雙s.異同論——勛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之比較研究》.《中國音樂學》,1990(3):102.
[7][美]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
[8]楊燕迪.《二十世紀西方音樂分析理論評述》.《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1995(3).
王夢熠(1987—),女,漢口學院音樂學院教師,音樂學研究生學歷。
——評《勛伯格與救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