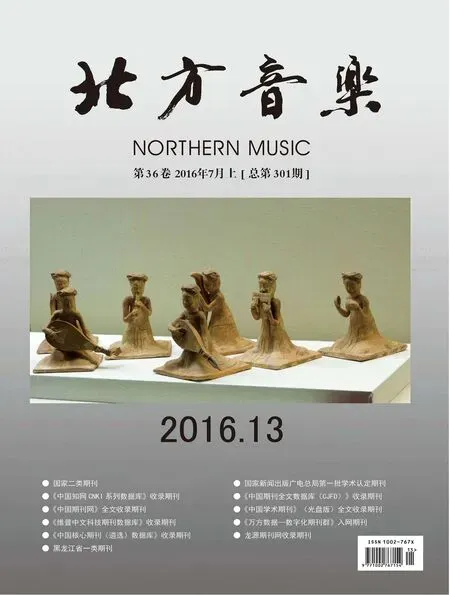巴托克鋼琴作品的民族特色分析
遲 冰(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音樂學院,河南 新鄭 451150)
巴托克鋼琴作品的民族特色分析
遲 冰
(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音樂學院,河南 新鄭 451150)
巴托克是近代西方音樂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音樂家,而鋼琴則是其創作的一個重要領域,并以鮮明的民族風格著稱。鑒于此,本文從其鋼琴創作經歷談起,就這種民族特色進行了具體分析,并就所獲得的啟示和借鑒進行了總結。
巴托克;鋼琴作品;民族特色;分析啟示
一、巴托克鋼琴創作經歷概述
巴托克(1881年—1945年),匈牙利著名音樂家,也是世界音樂巨匠,曾先后創作出了數百部經典之作。縱觀其整個創作歷程,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889年至1907年的萌芽期。1889年,巴托克開始了音樂創作歷程,該時期的作品顯然深受貝多芬、李斯特等古典和浪漫主義作曲家的影響,主要以模仿為主,但是仍然表現出了對民族民間音樂的關注。主要作品包含《四首鋼琴小品》、《管樂和鋼琴狂想曲》等,作品中初次使用了一些民族民間音樂素材,彰顯出了巴托克強烈的民族意識。第二個時期是1908年至1924年的形成期。從1906年開始,巴托克就開始了自己的田野考察之旅,曾帶著留聲機走遍了匈牙利各地,廣泛收集和整理各種民族民間音樂素材,并有意識的將這些素材運用于作品中。包含《獻給孩子們》、《兩幅肖像》以及最為著名的《野蠻的快板》,通過對大量民族民間音樂素材的運用,巴托克已經初步形成了個性化的民族風格。第三個時期是1926年到1940年的變化期。該時期的巴托克受到斯特拉文斯基等音樂家的影響,嘗試在作品中表現出新古典主義風格,包含《第一鋼琴協奏曲》、鋼琴曲集《小宇宙》、鋼琴組曲《在戶外》等,雖然風格上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其實這是巴托克在探索民族民間音樂在鋼琴中新的表現形式。第四個時期是1940年至1945的晚年期。1940年,受到政局的影響,巴托克來到美國定居,雖然經常遭受病痛的折磨,但是巴托克仍然堅持著音樂創作,寫出了《第三鋼琴協奏曲》等。1945年9月,巴托克在紐約病逝。
二、巴托克鋼琴作品的民族風格表現
(一)調式方面
調式是音樂的骨架,對于音樂風格有著決定性影響。在對民族民間音樂數十年的研究中,巴托克發現了兩個特點:一個是民族民間音樂是有調性的,而不是當時十分流行的“無調性說”;另一個則是民族民間音樂多使用中古調式和匈牙利調式,而不是大小調式體系。在此基礎上,巴托克采取了創新的運用,即在原有調式調性的基礎上加入了半音,從而使作品兼具民族性和現代性兩種風格。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利用調式轉換來實現預期的效果,如《獻給孩子們》,這是巴托克早期的作品,其中第31首的開始部分,有個同屬于G宮系統的樂句,左手部分開始是多利亞調式,隨后又變為了愛奧尼亞調式,同時加入了半音。同樣是《獻給孩子們》,第53首《快板》,巴托克采用了二部對位的方式,上下兩個聲部采用了不同的調式,一個是多利亞小調,一個是利第亞大調,兩者是同主音二重調式的重疊,利用民族調式產生了小二度關系。可以看出,巴托克在調式調性方面,是一種典型的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既能夠保留民族民間音樂中調式調性的特點,又能夠使作品體現出現代感,可謂是一舉兩得。
(二)和聲方面
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音樂創作的整體發展,和聲的作用和價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確和重視,也成為了音樂家彰顯個人風格的又一個重要渠道。對巴托克來說,在發現民族民間音樂在調式方面的特殊性之后,他意識到不能再沿用傳統的三度疊置法。另一方面,民族民間音樂中經常出現的四度音程和二度半音,也給了他以新的啟示和借鑒,所以在具體的創作中,他更多使用了四度疊置的和弦結構。如《十四首鋼琴小曲》中的第11首,該作品的右手旋律全面使用了四度疊置和弦,且采用了平行進行的方式,音樂風格十分鮮明。后來在《小宇宙》中,巴托克還專門寫了一首《四度音》,可見對這種和弦的偏愛。除此之外,巴托克也將二度疊置和弦結構視為民族性和現代性的標志。用大二度來表現民族風格,用小二度表現現代風格。如《小宇宙》第132首《大二度的分解與結合》中,全曲多次出現了大二度疊置和弦結構,然后在低音部中利用小二度對大二度進行分解,使兩者有機融合為一個整體。所以在傳統面前,巴托克絕不是機械地照搬照抄,而是靈活地創新運用,獲得了個性化的民族風格。
(三)節奏方面
節奏是民族民間音樂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多數民族民間音樂都有一種或多種獨特的節奏形式,同時也是區分于其它民族或地區音樂的標志。巴托克為了獲得更加新奇的節奏效果,曾對素材中的節奏進行了系統地歸類和研究,然后創造出了多種新的音型和組合方式,再予以大膽運用。比如自由節奏。這是匈牙利民歌中常見的節奏形式,意在給演唱者以極大的自由表現空間,多運用于一些個性化的情感抒發。比如在《小宇宙》這部以孩子們的幻想為主題的作品中,自由節奏就經常出現,以此來表現孩子們幻想的無拘無束。又比如附點節奏,這是匈牙利民間舞曲中經常出現的節奏形式,能夠表現出灑脫、隨意的情緒。而巴托克在具體運用中,突出了附點節奏的模仿性特點,如《狐貍之歌》中,就通過大量附點節奏的運用,形象刻畫出了狐貍陰險、狡詐的形象。而且為了實現不規則的節奏效果,巴托克還善于使用混合節拍和重音變化。前者是指頻繁地進行拍號變換,后者則是指將原有的重音規律轉移到相對較弱的拍子上。比如在《鋼琴奏鳴曲》第一樂章中,有兩個樂段都是每小節就變換一次拍號,同時重新標注重音記號,由此突破了傳統的節奏束縛,獲得了更加靈活和豐富的音樂表現效果。其在節奏方面的創新,對于20世紀的音樂創作技法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啟發和借鑒。
三、巴托克鋼琴創作的啟示
巴托克被譽為最具有民族色彩的鋼琴創作者,為匈牙利乃至整個歐洲的民族民間音樂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此給我們的啟示和借鑒也是十分豐富和深刻的。從19世紀末鋼琴傳入中國開始,中國的音樂創作者就開始了中國鋼琴作品的創作歷程,至今已經走過了百年的發展歷史。在這一百年中,雖然走過彎路,但是最終的收獲卻是巨大的。眾多創作者或對民歌、民間器樂進行改編,或廣泛運用各種民族民間音樂素材,創作出了大量的中國鋼琴佳作,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鋼琴音樂特有的風格,以及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追求和思想內涵,以此為基礎,也涌現出了眾多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演奏家,民族民間音樂也由此獲得了全新的傳承渠道,可謂是一舉多得。進入21世紀后,世界文化呈現出了明顯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創作者的創作理念也更加超前和個性化,這無疑是鋼琴文化發展的一種見證。但是正所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在這種多元文化背景下,越應該認識到民族民間音樂的價值和意義,將創作出具有民族風格的鋼琴作品視為己任,而不是沉浸于某些技法上的創新實驗中不能自拔。而且還有一點需要更進一步明確的是,從當下的中國鋼琴作品來看,改編曲占據了較大的比例,在中國鋼琴作品創作初期,通過對一些耳熟能詳的作品進行改編,能夠有效拉近聽眾和作品的距離,有利于作品的普及和傳播。但是這并不是使作品表現出民族風格的唯一方法,民族風格的表現也不能僅局限于對傳統作品的改編,而是要樹立起現代意識,關注國家和民族發展,關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變化,使作品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彰顯出當代華夏兒女的精神氣質和風貌,這不但是所有音樂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也是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綜上所述,近年來,伴隨著世界各國對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視和推動,一些始終秉承民族化創作理念的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得到了新的對待和研究。巴托克正是其中之一。在20世紀初現代主義音樂風起云涌之際,巴托克并沒有選擇盲從,而是堅定地走民族化發展道路,或許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但是在今天看來,其價值和意義已經得到了彰顯。由此獲得的啟示和借鑒也是十分深刻的,即在中國鋼琴創作中,也應該始終堅持民族化風格,為這門外來的藝術注入民族的審美、情緒、思想和情感,并由此為民族化的演奏和欣賞打下堅實的基礎,直至中國鋼琴學派的形成。這是巴托克其人其作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和借鑒,也是所有中國鋼琴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1]尤·霍洛波夫,羅秉康.巴托克和聲的現代化特點[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7(01) .
[2]金毅妮.表現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交點——巴托克中后期作品[J].音樂愛好者,2007(03).
[3]尤·霍洛波夫,羅秉康.巴托克和聲的現代化特點[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7(02).
[4]伊·馬爾蒂諾夫,羅秉康.巴托克和現代音樂[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