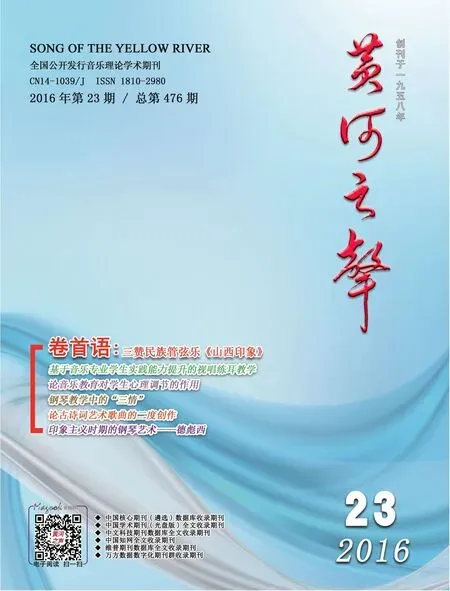鳴角一聲當三聲
——湘西土家族梯瑪牛角號的音樂文化研究
向清全
(中國音樂學院,北京 100101)
鳴角一聲當三聲
——湘西土家族梯瑪牛角號的音樂文化研究
向清全
(中國音樂學院,北京 100101)
牛角號,是用天然水牛角制成的吹奏樂器,早期用于狩獵、戰爭、祭祀等。它在湘西地區主要“存活”于土家族的祭祀、巫法等活動之中,為土家族梯瑪(土家族法師)所“操控”。本文首先從樂器本身和音樂本體層面入手,探討作為樂器的牛角號,所涉及到的形制、形象、曲調形態特征等方面的問題。其次從文化層面切入,探究作為法器的牛角號,它在儀式中被賦予的特殊功效和所達到的功能效應;以及作為身份象征的牛角號所涉及的一些性別“禁忌”問題。通過對兩個層面、三個問題的探討,試圖展現湘西土家族梯瑪牛角號的音樂文化全貌。
土家族;梯瑪;牛角號;功能;身份象征;禁忌
牛角號是廣泛流傳于西南少數民族中的一件吹奏樂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牛角號除形制不同外,用途也有所不同。“在廣西融江流域瑤族的牛角,以天然水牛角制作,瑤語稱‘姜’,用于喪樂;貴州彝族牛角,叫‘孩過’,用于喜慶、喪樂;湘黔邊界苗族牛角,發音悲壯,用于集會;布依族牛角發音低沉,用作集合信號。此外,還有的地區用銅、錫等金屬仿制‘牛角’,用于宗教法事。”①
土家族作為西南少數民族中的一員,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重慶、貴州的部分地區。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土家族主要聚居地之一,湘西州與貴州省、重慶市、湖北省接壤,是湖南的西北門戶,常被稱為湖南的“盲腸”地帶。較為閉塞的地理環境,為湘西增添了神秘色彩,巫楚文化影響著湘西地區的總體文化氛圍,后由于各種原因,周邊地區的漢族人口遷入,使得當地的巫楚文化與漢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土家族人民在該地長期生活,并創造出自己獨具特色的音樂文化,包括民歌、說唱、戲曲、器樂等多個類別。“土家族樂器分為吹奏樂和打擊樂兩種。吹奏樂器有咚咚奎,木葉、土笛、噴吶、牛角、莽號等。牛角,很早用于戰爭和狩獵,后來成為土老司的主要吹奏樂器。如擺手舞和銅鈴舞都要吹牛角。”②而擺手舞和銅鈴舞又與土家族的祭祀、巫法活動相關聯。
綜上可知,在湘西,牛角號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常作為溝通人神的法器,“存活”于土家族祭祀、巫法等活動之中,被儀式的執儀者梯瑪(又稱土老司,主要指土家族法師)所“操控”。還值得一提的是,苗族和土家族在湘西這片土地上長期共同生活,雖兩者族屬不同,但兩族人民在生活習慣、風俗等方面并非完全“涇渭分明”,常有相互交融之處,這在他們進行的巫法活動中也有所體現。據筆者觀察、了解,湘西地區苗族巴代(苗族法師),與土家族的梯瑪在裝扮、法器的使用上存在相似之處。除了司刀、銅鈴外,牛角號則是他們在儀式中必備的法器。因此,需要說明的是,牛角號在湘西并不獨屬于土家族,而是土家族和苗族所共有。
一、作為樂器的牛角號
土家族梯瑪常將牛角號稱之為牛角,他們將其視為法器。而“局外人”要將作為樂器或響器的牛角與作為器物的牛角(不用來吹奏的牛角)相互區別開來,便把它稱之為牛角號。從稱謂上可知,牛角號常常被“局外人”視為一件能發音的吹奏樂器,將其作為一件樂器,就不得不涉及到它的形制、形象、發音、曲調等各方面問題。
牛角號主要用天然水牛角制成,由于直接取材于水牛角,所以形制的大小、長短各不相同,沒有一定之規。由于現在水牛角越來越少,因此也出現了銅制的“牛角號”(與牛角號外形相同,只是制材不同)。
牛角號有一吹孔,無指孔。吹奏時發出類似“嗚、嗚、嗚”的聲音,聲音較為粗狂,但具有穿透力,所以在某些地方或民族常將它作為集合信號。因為形制的不同,牛角號音域的寬窄也有所不同。吹奏牛角時,常用右手握住牛角號靠近吹孔處的位置,吹奏(圖三)。
“玉皇角”、“老君角”是湘西土家族梯瑪在進行儀式時,經常吹奏的曲調。筆者所采錄的,湘西土家族梯瑪周光交吹奏的曲調“玉皇角”主要是由兩個呈近似大二度的音級構成。考慮到湖南湘西土家族的歌腔多為徵、羽調式,(《中國土家族民歌調查及其研究》中對湖南湘西土家族111首民歌進行了調式統計,得出:“湖南湘西土家族的民歌調式排列為:徵、羽、宮、角、商”③),因此,筆者將此呈近似大二度的音級用“sol”和“la”來表示(見譜例1)。
譜例1:
由譜例1可知,“玉皇角”全曲由“sol”和“la”兩個音構成,最后以“la”音結束。吹奏時,“la”的持續時間相對較長,“sol”常常以“la”的倚音形式出現,呈現出前短后長的節奏型。值得一提的是,劉嶸老師在《土家族祭祀儀式音樂研究(下)—以家祭儀式“還土王愿”為例》一文中,對“玉皇角”、“老君角”的曲調進行了細致的記譜、分析,并得出:“兩個曲調實際上就是一個曲調的變體形式,沒有顯著的區別,主要圍繞一個基本音程進行反復。這個音程比純四度略微偏窄一點,可以記作sol-do的進行。”④由此可以確定的是,土家族梯瑪牛角號的曲調,主要由兩個音級構成,但由于吹奏者(梯瑪)的不同,兩音級間呈現的度數也有所不同,如筆者采錄的曲調為近似大二度;劉嶸老師所采錄的曲調為“音程比純四度略微偏窄一點。”
二、作為法器的牛角號
牛角號在梯瑪的觀念里,不僅僅是一件會發聲的樂器或響器,它在梯瑪儀式中常被視為一件具有特殊功效的重要法器。所以,對于牛角號在儀式中運用的方式和所產生的功能效應的探討十分必要。“‘信仰體系’一個由‘信仰’、‘儀式’、‘儀式中的音聲’組成的三合一整體,儀式的展現過程,其中一個重要有機因素是儀式展現過程中的各種‘音聲’行為(其中包括一般用意的‘音樂’)。作為儀式行為的一部分,‘音聲’對儀式的參與者來說是一個增強、延續、扶持和輔助的儀式行為及氣氛的重要媒介和手段。我們對‘儀式中音聲’的研究,從‘音聲’切入,置‘音聲’于儀式和環境中探尋其在信仰體系中的內涵和意義。”⑤
筆者曾親歷了一次梯瑪所主持的“解洗”儀式。“解洗”儀式,是梯瑪為一些所謂見到“鬼”以致于神經錯亂的人解掉邪氣的一種儀式,分三天進行。除了前期的準備工作外,主要的儀式程序有:請師—開壇—早朝—踩碗—中朝—晚朝—過紅山—上刀梯。梯瑪主要在請師前和上到刀梯頂端唱完《送神》歌調后吹奏牛角號,雖然梯瑪在請師時也手持牛角號跟隨步伐晃動,但并沒有進行吹奏。除牛角號外,梯瑪儀式中還會出現一些在民俗活動中常用的樂器,如嗩吶、鑼、鼓、鈸等。
嗩吶、鑼、鼓、鈸主要作為梯瑪歌唱時的伴奏樂器,在儀式中使用。嗩吶伴奏有兩種方式:其一,一直跟著曲調的旋律,如一些常用的歌腔,就有嗩吶一直伴奏。其二,梯瑪在演唱實詞時不伴奏,而在實詞結束后的拖腔時伴奏。嗩吶伴奏時,一般要比演唱音域高一個八度,這與嗩吶聲音高亢的特點有一定的關系。鑼、鼓、鈸(有頭鈸和二鈸之分),則是一個組合,四件樂器相互配合,常在梯瑪演唱的每一句歌腔間進行伴奏,根據歌腔的不同,鑼、鼓、鈸在伴奏時的打法和伴奏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據筆者觀察,嗩吶、鑼、鼓、鈸在儀式中的使用次數,要比牛角號更為頻繁。雖然它們使用較為頻繁,但這些“與民俗活動共享”的樂器與作為儀式法器的牛角號相比,功能效應卻不相同。“認識儀式音樂功能的兩種角度;一種角度是分析儀式音樂可能達到的功能;另一種角度是研究儀式行為者希望音樂達到的功能。這兩種不同的認識角度也可以理解為兩種不同的立場和觀念:前一種是從儀式局外人立場用‘客位觀’去分析儀式音樂的功能效應;后一種是從儀式局內人立場用‘主位觀’去理解儀式希望者對音樂的功能去向。”⑥嗩吶、鑼、鼓、鈸作為梯瑪歌唱時的伴奏樂器,在儀式中出現。梯瑪認為,他們在做儀式時念唱的書卷較長,樂器的伴奏主要起到讓自己換氣休息的作用。筆者曾作為整個儀式的觀察者,感受到嗩吶、鑼、鼓、鈸在渲染和烘托歌腔的同時,也使得儀式音聲更為“豐滿”。因此,不管是在梯瑪的觀念中,還是筆者的觀察感受中,這類“與民俗活動共享”的樂器都不具備一些特殊(溝通神靈)的功能。
但牛角號的使用,在梯瑪的眼里卻有不一樣的功能效應。他們認為,在儀式前只要吹奏牛角號,神靈就會被請到他們做法的地方,來協助或幫助他們解決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儀式結束后吹奏牛角號,可以將請來的神仙送回去。牛角號的這種特殊功效,不但體現在梯瑪的口述文本當中,也體現在梯瑪神歌的唱詞當中。如梯瑪在《請師》中唱到:“鳴角一聲當三聲,聲聲拜請請何神。”以及梯瑪在上完刀梯后唱的《送神》(譜例2)。由譜例可見,《送神》為a、b上下句歌腔,反復五次,反復時歌腔變化不大,只是歌詞按照“東、南、西、北、中”變化,主要用來拜送“東、南、西、北、中”五方神,后再接類似尾聲的“最后一板”(局內人稱謂)歌腔結束全曲。“la、do、re”和“la、do、mi”(或“la、do、re、mi”)構成歌腔旋律的基本語匯,“sol”除了作為結束音外,很少作為旋律的骨干音出現。a、b上下句的唱詞幾乎是一字一音或一字兩音,總體唱詞節奏較為密集,旋律主要圍繞“la、do、re”三個音或“la、do”兩個音展開,起伏不大,風格接近“朗誦性”;“最后一板”的歌腔,雖主要圍繞“la、do、mi”三個音展開,但常有“sol”的加入,點綴旋律,并出現四度、五度小跳和八度大跳,旋律起伏相對較大,且唱詞中的某些字的拖腔較長,旋律風格接近“詠唱性”。從譜例中還可以看到“最后一板”的唱詞為:“道國今日現,鳴角走師神,大圣結界大天尊。”需要指出的是,《請師》、《送神》唱詞中的“鳴角”二字,皆指的是吹牛角號,這說明牛角號在梯瑪信仰體系中具有“請神”和“送神”的功能。
此外,這種特殊功能也體現在梯瑪對于牛角號曲調的解讀之上,梯瑪周光交告訴筆者:“‘玉皇角’代表了24玉皇,主要向師傅報告去哪里做法。”在他用哼唱的方式為筆者解釋這句話的時候,筆者發現,上述呈近似大二度的“sol”和“la”可分別代表“玉皇”二字,如(譜例3)。需要說明的是,“玉皇”二字并非該曲調的唱詞,只是梯瑪對這兩個音背后含義的解讀,然而從這些解讀中不難發現,牛角號的曲調與梯瑪信仰之間的關聯。
譜例2:
譜例3:
相對而言,牛角號的曲調對于儀式參與者則更像一種“信號”。梯瑪在儀式前吹響牛角號,儀式的幫助者或協助者(主要指儀式的幫手)和受儀者(主要指需要解決問題的事主),紛紛就位進入儀式狀態,儀式的觀看者(主要指事主家附近的一些民眾,包括筆者)紛紛趕到儀式現場,這就充分體現了儀式參與者常將其視為儀式開始的“信號”。
綜上所述,作為法器的牛角號,被梯瑪賦予了溝通神靈的功能,在儀式中雖沒有嗩吶、鑼、鼓、鈸這些樂器使用頻繁,但是可以說它對于儀式具有更特殊的意義。梯瑪在儀式中吹牛角號“請神”、“送神”這種行為,同樣也體現了梯瑪對自己所信奉神靈的尊重。對于儀式的部分受儀者、觀看者而言,牛角號的被吹響,宣告著儀式的開始或者結束,對儀式的起始和終止具有結構性的功能。同樣,它也給受儀者、觀看者一種心理暗示:接下來在該場域的活動要從世俗轉向神圣。這就要求在場的人們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懷揣著敬畏之心。可見,不管以何種角度去觀察、分析、理解作為儀式中法器的牛角號,它的功能性意義都要遠遠大于它作為一件樂器的意義。
三、作為身份象征的牛角號及性別“禁忌”
樂器演奏者及他們的身份和性別常常是民族音樂學樂器學關注的焦點之一。(美)布魯諾·內特爾在《民族音樂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中,第26個論題“尤八的創造物:樂器”的開篇就談到:“在民族音樂學中,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研究樂器是非常重要。最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什么人演奏什么樂器,以及那樣演奏一味著什么,這些一直是我們研究的內容。”⑦并在接下來的論述中繼續指出:“樂器對性別研究以及社會部分相互關系的其他研究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⑧可見,民族音樂學樂器學,不僅僅關注樂器的本身,還為我們提供了多種視角,如對樂器演奏者的研究,這就涉及到了演奏者身份、性別等各方面的問題。
筆者上述已經提到,牛角號被土家族梯瑪所“操控”,在儀式中是一件具有特殊意義的法器。當然,梯瑪與牛角號的關系,遠遠不止這么簡單。梯瑪周光交曾告訴筆者:“每一代梯瑪死后,牛角號要和梯瑪在一起,一并下葬。牛角號也可以傳給下一代,有些梯瑪使用的牛角號已有幾代的歷史。”牛角號與梯瑪一起下葬或被代代相傳,這都體現了牛角號與梯瑪的密切關系,它逐漸成為梯瑪的身份象征。眾所周知,牛角號在古代的戰爭中,也被士兵所“操控”,號角聲常被視為指揮戰斗的信號。隨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衛星、無線電等先進通訊設備在軍事當中的使用,現代戰爭已經不需要牛角號來傳輸戰斗信號,士兵也不再是牛角號的主要“操控”者。但如今在湘西,牛角號仍被作為土家族梯瑪的身份象征,筆者認為:
社會在發展,但牛角號作為梯瑪的身份象征在湘西并無變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牛角號的主要“操控”者仍然是土家族梯瑪,而且這種“操控”和“被操控”的關系在不斷地被強調和認可。土家族梯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雖受到過打壓,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評定政策的出臺;民族音樂學的引入對儀式音樂的關注;旅游業的興起和發展等多方面的原因,湘西土家族梯瑪可謂是“求大于供”,他們除了作為一些事主家的求助對象,也常被作為政策的保護對象、學者的研究對象、游客的“獵奇”對象。梯瑪穿著法衣、吹著牛角號、唱著神歌進行各種儀式,不管是在事主面前展現“法力”,還是在學者面前展示文化或是在游客面前展演文化,他們在進行對外“表達”的同時也在“強調”著牛角號與梯瑪或是與土家族巫法活動之間的關聯。當然有時這種強調并非他們刻意去做,只是他們祖祖輩輩都是這樣進行儀式的。在對外的展現、展示、展演中無意識的不斷“強調”,且不斷被認可,都使得牛角號仍作為梯瑪的身份象征而存在。
綜上所述,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樂器“操控”者長期演奏著自己的樂器,使得樂器與“操控”者的身份產生關聯,樂器“操控”者身份的變化也影響著樂器對于“操控”者身份的象征意義。
樂器不僅可以作為身份象征而存在,它還具有“性別”。這包括樂器制作者或演奏者賦予它的“性別”,如廣西部分地區的銅鼓有“公母”之分;也包括樂器“操控”者的性別要求。因此,對樂器被賦予的“性別”及樂器“操控”者的性別要求的觀察與闡釋相當必要。湘西牛角號的“操控”者均為男性法師,這與土家族梯瑪的傳承有密切的關系。因為湘西土家族梯瑪的承襲一般都是祖代相傳,并只傳本族宗親的男丁,從不外傳。有些梯瑪班子在傳承時可不受到本族的輩份限制,可父傳子也可子傳父,可兄傳弟也可弟傳兄,每一代梯瑪都有自己相應的法號,法號輩份的高低由“入門”的先后而定。彭德榮在《梯瑪與梯瑪歌》一文中提到:“梯瑪的傳承一般是父傳子、子傳孫的親血緣系統家族遞續。我們在采訪中,凡梯瑪,皆說是十代相傳、九代師承之類。因此,做一場祭祀活動的梯瑪群體,多是由親血緣系統的父子幾兄弟組成而由一位巫法大、輩份高、年齡長的梯瑪作掌壇師。”⑨筆者的考察對象梯瑪周光交,已是周氏梯瑪第十二代傳承人,在他梳理自己的傳承譜系時,筆者同樣發現周氏每一代的梯瑪與他均有親屬關系,且都為男性。由此可見,在土家族的歷史文化中,我們似乎很難找到一些關于牛角號“操控”者性別的“明文規定”,但牛角號主要“操控”者在傳承時對于性別的要求,造就了牛角號在湘西多為男性吹奏的“約定俗成”。這種隱性的性別“禁忌”,使得牛角號與男性法師關聯起來。
四、結語
就樂器本身和音樂本體而言,牛角號在制作中的天然取材,以及曲調多以兩個音級構成,使得它在樂器制作和音樂形態上不似某些樂器那樣繁瑣和復雜,但它所承載的文化卻又是相當厚重。牛角號在儀式中被梯瑪所“操控”,梯瑪給予它音聲,賦予它特殊意義,這樣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而這些文化內涵、象征意義與牛角號的本身及音樂的本體,共同“勾勒”出牛角號的音樂文化全貌。
注釋:
①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研究所《中國音樂詞典》編輯部.中國音樂詞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10:286.
② 黃柏權.土家族樂器一覽.民族藝術,1991,04:155.
③ 徐旸,齊柏平.中國土家族民歌調查及其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35.
④ 劉嶸.土家族祭祀儀式音樂研究(下)--以家祭儀式“還土王愿”為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9,02:19.
⑤ 曹本冶.儀式音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11:44.
⑥ 薛藝兵.神圣的娛樂:中國民間祭祀儀式及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94.
⑦ [美]布魯諾?內特爾著,聞涵卿,王輝,劉勇譯.民族音樂學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8:328.
⑧ [美]布魯諾?內特爾著,聞涵卿,王輝,劉勇譯.民族音樂學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8:332.
⑨ 彭榮德.梯瑪與梯瑪歌.鄂西大學學報,1989,01:65.
[1]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研究所《中國音樂詞典》編輯部.中國音樂詞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
[2] [美]布魯諾?內特爾著,聞涵卿,王輝,劉勇譯.民族音樂學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8.
[3] 曹本冶.儀式音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11.
[4] 薛藝兵.神圣的娛樂:中國民間祭祀儀式及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5] 徐旸,齊柏平.中國土家族民歌調查及其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6] 蔣廷瑜,廖明君.銅鼓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7] 彭榮德.梯瑪與梯瑪歌.鄂西大學學報,1989,01.
[8] 黃柏權.土家族樂器一覽.民族藝術,1991,04.
[9] 劉嶸.土家族祭祀儀式音樂研究(下)--以家祭儀式“還土王愿”為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