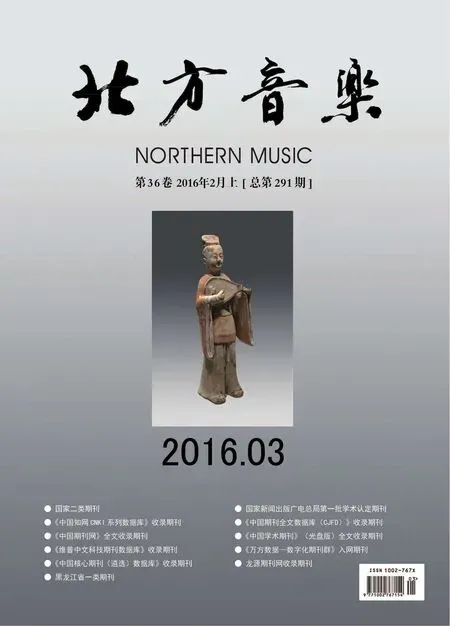音樂藝術中情和理怎么統一
葉思博
(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
音樂藝術中情和理怎么統一
葉思博
(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摘要】本文對音樂學習及演奏中關于理性和感性的均衡性和相互之間的統一性入手,進行逐步深入的分析。意圖來解決在音樂實踐中理性練習和分析與感性表現與演奏之間的矛盾。
【關鍵字】意識;抽象;情感;理智
所謂情感和理智,自人類文明開始至今都是一個無法融合的問題。近代心理學的建立才使得關于情感和理智的原理得以慢慢的延展在人類的知識視界之中。
一,心理學中關于意識的劃分與音樂藝術的關系
(一)心理學中的情感與理智
心理學中首先將人類的心理做了一個基本的劃分:人類的心理世界分為兩個部份,其一是意識,泛指人類的一切心理活動,這里是指可以被感知的,或是可以被模糊感知的一切心理活動和心理反應;第二類是無意識,根據當代的心理學研究數據和結論可以得出,無意識的心理狀態要比有意識的心理狀態涵蓋的心理空間大的多。
意識被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情感,指人的情緒和情感反應,而不是思考反應,是對一系列主觀認識經驗的統稱,是多種感覺、思想、行為的綜合產生的心理狀態;第二類是理智,被認為是一種思考、計算、衡量、推理與邏輯的能力。
(二)藝術與情感和理智的關系。
從學術角度不帶有情感傾向來分析。情感與理智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識活動。兩者從根本上來說是絕無融合的可能性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卻是,人就是一個這樣的合成有機體。人同時用理性和感性的對生命整個過程進行精確的把握,對環境和自身無時不刻的進行理解、分析和感受,這種有機結合的極致就是人類文明中最璀璨的結晶——藝術。
對于藝術的定義,我們這里有必要給予明確的限定:“藝術,指憑借技巧、意愿、想像力、經驗等綜合人為因素的融合和平衡創作隱含美學的器物、環境、影像動作或聲音的表達模式,以指和他人分享美的或是深意的情感與意識的人類用以表達既有感知的且將個人或群體體驗沉淀與展現的過程。”(維基百科2014年4月15日22:55分最后修訂版本定義)。
二、以聲音做為表現媒介媒介的藝術形式
而人類所創造的所有藝術中,最為抽象的、難于給出確定定義的藝術形式就是——音樂。音樂是聲音的藝術。同樣以聲音為媒介的藝術,有詩歌,或是文學作品,但是這些藝術作品與音樂藝術有著完全不同的本質特點,以下做一簡述比較:
(一)文學、詩歌,固定的發音組合代表固定的含義,這就是語言——文字系統的特征,并且語言文字藝術是一種邏輯的藝術,整個一套體系,是以理性為基礎思維的體系。非常的具象,而且不借助聲音,同樣可以將需要表達的含義表達的非常清晰。并且做為不同的語言體系,其組織結構完全不同,是一個個獨立的近乎于封閉的體系。
(二)音樂,固定的發音組合沒有固定的含義,并且無重復的可能性。符號——樂音體系的特征在于,音樂是一種非邏輯的藝術,整個一套體系,是以感性——靈感框架建立起來的。完全的抽象體系,不借助聲音則完全無法存在。無法表達任何情緒、情感或任何音樂所能表現的內容。雖然全世界有不同的音樂組合和樂音體系,但是,其組織結構卻在人類的聽覺進化過程中,達到了驚人的一致性。雖然大家都選用了不同的樂音體系,如:五聲樂音體系、六聲樂音體系、七聲樂音體系,到近代的十二音體系,或者說是微分音體系。但是其內部的樂音數學體系都是完全重合的。并且其組織結構雖然不同,但完全是跨越文化圈的共同的,可明確感受的。
由此可以看出,音樂是一種近乎于純感性的文明藝術形式(所以用近乎于這個詞,是因為樂譜是一種理性的邏輯結構)。音樂的抽象性、情感性、靈感性、瞬時性、不可重復和復制性、無法測量性、共通性、不可準確描述性明確了音樂本體與理性的無關。這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幾乎是可以確鑿的。
三、情與理在音樂藝術中如何統一
理性是與音樂完全格格不入的一種意識形態,理性要求具象性、邏輯性、可分析性、可持續性、可重復性和可復制性、可測量性、具有某些不可共同特征性、可明確描述性、甚至是經驗性的可預測性。
理性與感性的根本區別在于理性以邏輯、分析為根基;感性以感受、感覺為基礎。這兩者看似不可融合和調節。但是他們就融合在我們的意識世界之中。人所以為人,所以是自然界目前看來最能夠認識世界的動物,就在于我們是一種融合感性和理性的動物。這種動物被稱之為高級動物。
而人類所創造出的精神文明中最為貼近人的意識本質的藝術類型筆者認為就是音樂。原因之一就在于意識是抽象的,音樂也是抽象的。抽象的存在是取消了某種事物的具體形象,而保留其本質特征和運作規律,也就是保留了其核心實質的一種意識方式。音樂正是如此。而音樂的媒介又是一種具有物理特性的(理性——物質系統)沒有可見形象的(感性——精神系統)聲波。
在比較清楚的了解了音樂本質和物質世界的理性和感性的相互關照之后,我們就建立了一個能夠進入音樂存在狀態的一個基礎或是一種較為茁壯的框架。
現在我們開始進入音樂的產生環節,也就是音樂表演或者稱之為演奏環節,這個環節才是音樂實際存在的意義。
前文所述的所有篇幅重點分析了音樂的性質,現在我們來看音樂產生的現象:眾所周知,所謂音樂是用不同的樂器(這里把人的聲帶也歸入樂器類型中),發出約定俗成的固定的音高,建立一種音響模型,并以某種節奏、音色、速度,結合而成的樂音系統來完成其自身的現象。從以上筆者對音樂的定義可以看出,音樂產生的現象就現象本身而言是一種純理性的建構,無論從音高、節奏、音色、速度還是音樂模型都是一種純理性的產物,但是有一個奇詭的結論卻從中誕生:這一切的理性的結合完全是為了表現人對于音樂感性的激動(此處的激動是廣義的激動:包含喜怒哀樂都屬于激動的范疇。因為悲哀等情緒也是一種感性激動的現象,所以從心理學角度來講任何情緒的性質都是一種感性體系的激動)而建立的體系。由此可以演繹出一個匪夷所思的結論:理性是為了感性而建立起的一種結構!這一結論似乎是有問題的,但是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音樂中這一結論是完全成立的。
理性是有序的,而感性是無序的。但由于人類的邏輯思考和歸納演繹的本性,人們是通過理性的有序結構而通達了感性無序的大門。
從事音樂演奏的人都會有著這一一個過程:感受音樂(感性)——技術訓練(理性)——認識音樂(理性)——感受音樂(感性)——演奏音樂技術階段(理性)——演奏音樂演繹階段(感性)——演奏音樂欣賞階段(理性、感性結合)。
這個過程并非如筆者所列出的這樣絕對,在學習和演奏的過程中,也可能不按照以上的序列步驟來進行,也有可能會跳過某個階段或者是亂序的進行。但是關鍵的問題在于,自始至終音樂學習和演奏過程始終都是一種理性和感性共同運作的過程。
在音樂的產生過程中絕對的是理性的訓練,其目的在于,對控制體系的一種敏感和精確的把握。因為只有這種控制的把握才可能將音樂推向表現的道路。才可以有呈現音樂的能力和可能。這種理性的控制是必須的環節。這也正是理性的強項,在這個環節一定注意的是三個原則:分析、理解、準確。冷靜的分析自己的能力和音樂所要求的之間的差距,分析自己的錯誤和提升自己的可能性;充分理解音樂所需要的條件和自己所能達到的“界限”,充分的理解音樂的各種可能性;準確的做到音樂所需要的要求,準確的進行技術的訓練。準確的對自身進行“絕對”的控制和把握,將所有的意外情況都處理掉。這就是理性的意義,也是理性之所以在音樂中的重要性的體現,音樂中如果沒有這種理性的存在,音樂本身的存在從基礎上就會完全的消解,而導致音樂的解構。
但是這種理性的存在同時又是非常致命和危險的。如果將這種理性在音樂中貫徹到底,音樂就變成為一種機械的存在,內在的生命力和精神力將完全的死亡。取而代之的將是一種死氣沉沉的聲音現象,一種技術的堆砌,一種演奏者的酷刑,一種聽眾的折磨。類似于一個“行尸走肉”。這種情況類似于二十世紀出現的某些近現代音樂類型,大量的技術手段和設備的運用,演奏者對技術的掌握常造成一種手足無措的的心里障礙,同時又由于旋律的機械化或是理性化而導致一種徹底的理解無能的情況,感性又無處進入,這正是近現代音樂的一個困境,試想:一個演奏者連最起碼的旋律走向都無法把握、無法記憶、甚至是無法感受的話,憑借理性的記憶又根本不可能。那么這樣的音樂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演奏)狀態?如果作為演奏者是這樣的感受的話,那么聽眾將如何去反應?這也許就是現代音樂的為難之處:突破了,卻失去了精神的家園,如果回轉,卻又掉進了理性的桎梏。
因此,理性有其不可替代性,但同時又有著非常明確的缺失性,這是作為存在的屬性,本質屬性不可改變。所以在音樂的演奏和學習過程中,對于理性的缺陷必須非常清楚的意識和感受到,并且要有所調整,切不可為了音樂而技術,為了技術而精確,為了精確而理性。這是所有的音樂學習和演奏者所需要引以為戒的。
感性是貫穿于音樂始終的一條“隱”(抽象)線。卻是音樂的靈魂所在,雖然看不到,卻決定了音樂的核心性質及輻射出的屬性。這就是“情”。
情,是一種自發的感性現象,人對于任何事物都自發的產生情的主觀感受,情是一種主觀的不可名狀的心理狀態持續現象。這種現象有其特殊的性質:主觀的客觀性,也就是說,雖然情感的產生是由于主觀產生了一種持續的心理狀態,但是這種心里狀態是由于客觀事物的刺激而出現的。并且這種客觀引起的主觀感受會有一種共通性,會在相同的環境中馬上傳播給共同環境的每一個主觀的主體,雖然在每一個主體身上的反應不同,但其性質卻是幾乎完全相同的。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中被稱為“集體無意識現象”,這種現象最早是被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發現并命名的。其含義為:“集體無意識的內容是原始的,包括本能和原型。它只是一種可能,以一種不明確的記憶形式積淀在人的大腦組織結構之中,在一定條件下能被喚醒、激活。”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中積淀著的原始意象是藝術創作源泉。一個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體無意識”領域中找到,它使人們看到或聽到人類原始意識的原始意象或遙遠回聲,并形成頓悟,產生美感。”
從原型批評的角度來理解這段話,就是藝術家所創造的形象是某種文化原型的以無意識的方式世代相傳的結果。由無意識所體現出來的個體的文化特征,是由作者童年時所生存的文化環境決定的。這個環境就是由符號構成的風俗與行為方式,世代相傳的童年生活保持了某一文化的延續性。
由此,可以明確一點,就是“情”也就是感性是“美”產生的契機,只有情有著如此的功能,讓人從理性的層面,通過其自身領悟審美的現象而達到“美”,這種“美”是抽象的存在,而這種抽象的存在通過音樂進行最直接和完整的傳播,這就是音樂藝術中情與理的完美結合的產物。
綜上所述,在音樂藝術中情與理的統一就是音樂情感與音樂現象的統一,就是核心與實質的統一,就是物質世界與靈魂世界的統一,這種統一必須要有感性的主觀感受和理性的主觀理解與分析,做為音樂學習和演奏者,必須在保持感性豐富情感的同時,理性的進行訓練和控制,這樣才能進行兩者合二為一的嘗試和熟練。這種嘗試和訓練其實又是人類賴以生存和觀察世界的本能反應,所以并非是一種強制性的困難的實現。中國古代早有思想家對其進行了精準的研究和描述:《樂記,樂本篇》開篇明義寫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行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聲音,在時間的長河中給我們后來的音樂學習和演奏者一個告誡,音樂是情與理的統一體。偏情而忘理,音不成也;偏理而忘情,音無魂也;唯情理相成,而音生也。
參考文獻
[1](德國)雷納特·克洛佩爾.《演奏藝術的生理心理學津要》[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2](美國)羅伯特·C·所羅門.《哲學導論》(第9版)[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12月第一版
[3](美國)Aniruddh·D·Patel.《音樂、語言與腦》[M].上海: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4](美國)本杰明·萊希.《心理學導論》(第9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作者簡介:葉思博,男,漢族,助教,藝術學碩士,單位: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研究方向:音樂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