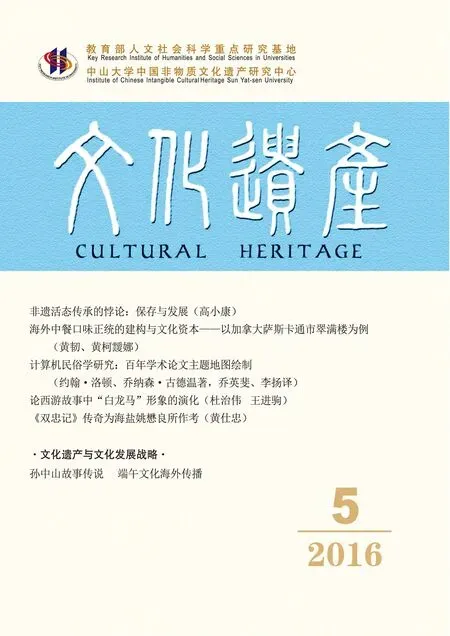從字說創(chuàng)作看元代冠禮的傳承與變遷*
——兼論儒家的成人觀念
賀少雅
?
從字說創(chuàng)作看元代冠禮的傳承與變遷*
——兼論儒家的成人觀念
賀少雅
字說是一種應用性文體,其源于古代冠笄之禮中的祝辭,興起于宋代,發(fā)展于元代,興盛于明清,衰落于民國以后。元代是宋代理學發(fā)展的重要階段,也是傳統(tǒng)禮儀走向復興的重要發(fā)展時期。從元代字說的寫作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代冠禮的“加冠命字”儀節(jié)正在重建,另一方面,冠禮儀式各環(huán)節(jié)之間正發(fā)生著轉(zhuǎn)化和分離,主要表現(xiàn)在:字說寫作逐漸盛于加冠祝辭、“加冠”和“命字”儀節(jié)發(fā)生分離、賓者與冠者之間的關系更加多元化。同時,字說文體中對冠者名字內(nèi)涵的解說折射出了當時儒家的成人觀念和價值導向。
元代字說冠禮成人觀念
字說作為一種應用性文體,敘述為某人命名取字的緣起,闡釋名和字的內(nèi)涵或論述儒家道統(tǒng),并寓以祝福、勉勵和警戒之意。明代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對其文體來源作出解說:“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后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仿古辭而為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故近以說為主,而其他亦并列焉。至于名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今雖不行,然于禮有據(jù),故亦取之,以備一體云。”*(明)吳訥、徐師曾《文章辨體序說 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47頁。關于字說與字敘、字辭、名(字)說等文體之間的關系,當代學者作了辨析。*學者劉成國認為,字說與字序、字解等基本等同,但與字辭有一定區(qū)別,而且字說與名說有密切關系,可能還融合了歷代皇帝改名詔及誡子書的文體內(nèi)容。參見其《宋代字說考論》,《文學遺產(chǎn)》2013年第6期。
字說發(fā)軔于中唐,興起于兩宋,發(fā)展于元代,興盛于明清兩朝。*關于字說的歷史發(fā)展,學者劉成國認為“字說發(fā)軔于中唐,蔚興于兩宋,而泛濫于元、明、清三朝”。但本人認為,用“發(fā)展期”代替“泛濫”一詞比較合適。首先,若僅從數(shù)量上來看,劉氏一說可行(據(jù)本人的統(tǒng)計,字說創(chuàng)作在宋代以前為1篇,兩宋遼金約460篇,元代490篇左右,明清兩代分別在500篇和200篇以上),但字說寫作在元代初期并不多,一些儒學大家如姚樞、許衡等均僅有幾篇,而到元代中后期,字說作品才得以大肆發(fā)展。再者,元代字說寫作相對集中,如僅理學家吳澄一人即有85篇。最后,元代享國時間不長,字說在民間社會的真正影響有多大,實不敢定論,所以“泛濫”的提法似可商榷。部分文體學家將其列專章論述,如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匯編》中就收錄了宋代蘇洵、蘇軾、黃庭堅等創(chuàng)作的19篇字說。學者郭英德認為,這些類似于冠禮祝辭之類的“辭”“禱”“誄”等都是適應不同的言說行為的文辭樣式,屬于“作為行為方式的分類”。*參見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學術研究》2005年第1期。其具有強烈的應用色彩,文學性則往往為人們所忽視。但是,近年臺灣學者葉國良提出,中國古代的很多文體都與儀式有關,而且“因禮儀而產(chǎn)生的文體,比起其他語言的文學來得特別多,乃是中國文學的特色之一”*葉國良:《禮儀與文體》,《中國文化研究》2015年夏之卷,第106-107頁。,他認為字說是古代冠笄之禮的一種變體,字說文體的興衰與冠笄之禮的衰微具有一致的關系。*參見葉國良《冠笄之禮的演變與字說興衰的關系——兼論文體興衰的原因》,《臺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5年5月。葉氏的字說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不少學者從此開始關注字說研究,但多是從文體的角度集中對宋代字說創(chuàng)作進行探討。*請參見葉國良《冠笄之禮的演變與字說興衰的關系——兼論文體興衰的原因》(《臺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5年5月),劉成國《宋代字說考論》(《文學遺產(chǎn)》2013年第6期),張海鷗《宋代的名字說與名字文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鄧錫斌《宋代名字說的文體淵源》(《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等文章。誠然,宋代是字說的初步發(fā)展階段,尤其是南宋理學興起之后,理學家借助字說闡述儒家義理,重振傳統(tǒng)禮儀,使得字說創(chuàng)作逐步繁榮。但實際到了元代,隨著理學作為官學的確立,字說創(chuàng)作也甚為可觀,數(shù)量竟與兩宋的創(chuàng)作總量相當。元代儒生秉承著強烈的儒家道統(tǒng)觀念,邊參與冠禮實踐,邊寫作字說,闡發(fā)儒家義理,“對兩宋儒學向明清儒學過渡起了傳遞、定向的作用”*韓鐘文:《中國儒學史(宋元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字說如一面鏡子,折射出了元代冠笄之禮的傳承與變遷,反映了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和成人觀念。
一、元代冠禮的復興
元代儒士們承續(xù)兩宋新儒學的發(fā)展,除了在理論上繼承程朱理學外,也將禮儀實踐付諸行動。理學家吳澄在《曾尚禮字說》中說:
古之經(jīng)禮……于僅存之中最易行者,冠禮也,而其廢也久矣。司馬公及程子、朱子惟恐人之憚其難,故又斟酌古禮而損益之,庶其便于今而可行,然人亦莫之行也。故其在吾鄉(xiāng),惟蜀郡虞氏及予二家猶不廢此禮,他蓋鮮有聞焉。翰林應奉曾巽初在京冠其子,有賓有贊,有三加,若醮若字,其儀一仿朱子所定。古禮久廢之余,而獨行人之所不能行,可謂篤志好學之君子已。*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卷49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頁。
吳澄在這里肯定了司馬光、二程和朱熹在整飭和復興禮儀中的作用,也提及本人與虞氏、曾氏的禮儀實踐。從文獻來看,當時民間社會禮儀遵行者并非如吳澄所說的“莫之行”,比如當時江南大族鄭氏家族就是嚴格執(zhí)行家禮的典范,其子弟多有行冠禮者,僅字說中就見柳貫《鄭泳冠字祝辭》、戴良《鄭梴冠子祝辭》、朱震亨《鄭湜加冠祝辭》和陳旅《鄭濤字序》,且家族中人鄭泳著有《鄭氏家儀》對冠禮作了具體規(guī)定。如陳旅《鄭濤字序》中提到:“初,予讀《浦江鄭氏家范》,嘆其扶導之有方,意必多佳子弟出于其間,恨未之見。一旦列宴于祭酒之堂,忽鄭深仲幾自外至,且謂予曰:深弟名濤,已嘗筮賓,行三加之禮,字之曰仲舒矣。濤慕先生之風,當深來燕時,濤再三為深言,欲求先生之文以自勖。”*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37冊,卷1172,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頁。后來鄭氏家族被明朝廷命名為“江南第一家”,成為民間禮儀實踐的樣本,明代大儒宋濂和方孝孺等均曾為鄭氏家族子弟作冠禮祝辭和字說。吳澄在《陳壵伯高字說》中也提到:“夫冠而字,禮也;字而有辭,亦禮也。……及考《大戴禮·公冠》篇所記,亦有別為冠辭者,近世彌多。而予為人作字說,殆不啻數(shù)十。”*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卷49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反映出當時民間舉行冠禮者有之。
關于元代字說的繁榮,一般認為,原因有二:一是理學家借用這種文體,宣揚理學思想,以復興古禮,他們將冠禮對成人的期待,與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的德性修養(yǎng)聯(lián)系起來,為古老的命名取字風俗,注入了新的哲學內(nèi)涵*劉成國:《宋代字說考論》。,促進了字說的創(chuàng)作。再者,有的學者推斷,字說創(chuàng)作的繁盛恰恰說明元代冠禮的衰頹,由于冠禮不得倡行于世,所以文人以字說創(chuàng)作來取代冠禮儀式。*參見葉國良《冠笄之禮的演變與字說興衰的關系——兼論文體興衰的原因》、李隆獻《歷代成年禮的特色與沿革——兼論成年禮衰微的原因》的相關論述。的確,與冠禮直接相關和闡述冠義的字說只是大量字說中的一部分*依照字說與冠禮關系的緊密程度,有的指明冠義和字義,標題上就有體現(xiàn),如冠禮祝辭、冠辭、冠說、冠贊;有的在標題上沒有體現(xiàn),但是文中有對冠義的闡述;有的只是闡發(fā)名字的含義和儒家的成人觀念;有的與冠笄禮關系不大,如名(字)說、改名說。古代女子由于“十五始嫁,笄而字”,所以名字說多是加笄命名字或者加笄命字,前者如宋陳著《名女洸字汝玉說》《名女沖字汝和說》《名女清字汝則說》和游九言《上官氏女甥名說》《黃氏三女甥名說》,后者如劉克莊《陳倩玉女》。,且關于民間舉行冠禮的直接記載所見不多,所以何中《猶子養(yǎng)正字說》發(fā)出感嘆:“今方辮發(fā)垂髫,下及公卿百執(zhí)事,以至于薄海內(nèi)外,冠且贅矣,奚以字為。雖然冠而字,禮也,未忍以今廢禮,是亦不可無說。”*(元)何中《知非堂稿》卷7,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4冊,影印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02頁。本文作者校點。
二、延續(xù):舉行冠禮的年齡基本穩(wěn)定
古代男子加冠的年齡中并無明確規(guī)定,雖然《禮記》中有“男子二十,冠而字”之說,但文獻中所見,士及以上階層的加冠年齡有“十二歲”“十五歲”“二十二歲”“二十三歲”等不同記載。漢魏六朝時期,冠齡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二十等*參見李隆獻《歷代成年禮的特色與沿革——兼論成年禮衰微的原因》,《臺大中文學報》第18期,2003年6月。。至宋代,司馬光、朱熹對民間冠禮年齡作了規(guī)定,《書儀》謂“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其注云“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jīng)》《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后冠之,斯具美矣”。*(宋)司馬光:《書儀》卷2,《叢書集成初編》第104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頁。司馬光在遵從舊俗的基礎上,提出了加冠的年齡段,又根據(jù)當時社會要求,尤其是儒家對于人的塑造和成人的規(guī)定,以“十五歲”作為理想的冠齡。朱熹《家禮》基本遵從《書儀》,也作“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92頁。。
元代民間基本遵從朱子《家禮》規(guī)定,十五歲左右加冠,比如,戴良《唐林字說》載“句章唐起賢之冢子林,從予游久,今年十有五矣。起賢將責之以成人之道也,乃行三加之禮”*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53冊,卷1632,南京: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下同,從略)2004年版,第335頁。;鄭玉《弟璉名字說》曰“玉生十有五年,先君子命名以易其小字”*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46冊,卷1430,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頁。。也有人對冠齡作出解說,如劉岳申的《劉昕字賓旭字說》中云:“昔者,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學,有不待二十者矣。夫子以十有五為旭日,此夫子之寅賓也。古以七十為稀年,則十五為旭日,有不信可惜乎?安成劉氏子昕,字賓旭。……蓋旭日甚可愛而不可玩,故加敬焉,兢兢焉,業(yè)業(yè)焉。”*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1冊,卷66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0頁。其以孔子“十有五年而志于學”的言說來引導和鼓勵冠者,為其樹立了圣人孔子的標桿,并對“十五歲志于學”“不待二十”作了更細微的年齡區(qū)分。當然,也有其他年齡加冠者,如元代鄭泳《鄭氏家儀》載:“吾家子弟年十六,許行冠禮,皆要誦背四書五經(jīng)正文,講說大義,否則延至二十一歲。”*(元)鄭泳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jīng)部)第114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頁。何中《猶子養(yǎng)正字說》:“祖生年十七而冠,儼然成人而父命之字也。”*祖生,即養(yǎng)正之名。(元)何中:《知非堂稿》卷7,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4冊,第503頁。本文作者校點。
可見,這一時期的加冠年齡基本沿襲了前代,年齡范圍彈性又相對統(tǒng)一,符合人的生命發(fā)展規(guī)律,也契合時代的要求。
三、變遷:冠禮儀節(jié)的細微調(diào)整
除了冠禮年齡的基本穩(wěn)定以外,宋代以后,隨著冠禮的重振,一些儀式得以恢復。但是也呈現(xiàn)出與前代不同的特點。比如,字說的出現(xiàn),其在闡釋名字涵義時把儒家傳統(tǒng)價值觀和成人觀念貫穿于冠禮之中,部分代替了祝辭的功能*從目前的材料中,還很難看到元代民間社會的冠禮儀式,所以不能判斷儀式中是否還有規(guī)范的祝辭,字說與冠禮上的祝辭之間的關系等,留待以后討論。,延續(xù)了冠禮中取字儀式的象征意義。但字說之于冠禮的功能在弱化,而且祝辭寫作者已由傳統(tǒng)的無血緣關系的鄉(xiāng)老和師長,變得更為多元化。
(一)冠禮儀式的記敘和解釋性文體——字說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
字說作為記敘冠禮過程,解釋名字涵義的一種文體,自宋代已經(jīng)形成一定規(guī)制,元代時繼續(xù)完善和發(fā)展。其中一類為字辭、祝辭,形式上或韻或散,或韻散結(jié)合,直接體現(xiàn)出與冠禮祝辭之間的淵源關系。韻文類的,如吳澄《虞采虞集字辭》:
著雍困敦,相月六蓂。虞氏二子,丱突而成。既加元服,乃敬其名。字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爾字,用勖爾德。孰采孰受,忠信于禮。孰集孰生,道義于氣。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zhì)以素粉。義在夫集,生者其効。如耘之熟,苖以長茂。予告汝采,自誠而明。行有余力,一貫粗精。予告汝集,自明而誠。及其誠功,四體充盈。念念一實,表里無偽。言動威儀,浸浸可備。事事一是,俯仰無怍。盛大周流,進進罔覺。采匪詞華,集匪辯博。希賢希圣,爾有家學。相門有嗣,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元)吳澄:《吳文正集》卷7,收入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7冊,第88頁。
韻散結(jié)合的,如柳貫《鄭泳冠字祝辭》: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筮得穆日,始用三加之禮,冠其諸孫泳,而責之以成人之道焉。不鄙戒賓,過采衰陋。夫既席開酌醴,字實予責。予惟泳以潛行為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毎以適道譬之,有自來矣。而順卿又方敦泳以學。予聞諸《易范》,潛之為用,不既大哉!乃為制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為辭祝之。……辭曰:
……字尓仲潛,戒尓驕輕,非伏扵潛,欲抵其平。滄浪之歌,有濯斯纓,爾慎持之,如承佩珩。尓世孝義,視尓門旌,黍稷維微,神歆德馨。由微至著,有聞無聲,棄爾孩孺,揚尓翹英。式祗訓辭,以無忝所生。*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5冊,卷80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453頁。
按《儀禮·士冠禮》記載,三次加冠皆有祝辭,且為四字韻文,初加緇布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皮弁冠,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爵弁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正所謂“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頁。漢以降,至隋唐五代,史書中雖有士及以上階層的加冠記載,但加冠祝辭所見不多。兩宋時期庶族階層上升,迫切要求禮儀下行,宋司馬光整飭冠禮作《書儀》,冠禮儀節(jié)、祝辭和字辭以《儀禮·士冠禮》為本,基本保持不變,論及受禮者接受祝辭以后的言行時提到:“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禮辭,許,乃入,設酒饌延賓及儐贊如常儀。”*(宋)司馬光:《書儀》卷2,《叢書集成初編》第1040冊,第19頁。后朱熹《家禮》在司馬氏基礎上,增加“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7冊,第892頁。。元代鄭泳《鄭氏家儀》基本沿襲朱熹《家禮》載:“賓字冠者,字之曰:‘令月吉日,禮儀既備。以某爾名,以某爾字。爰字孔嘉,于士攸宜。宜之于嘏,福祿永綬。’……賓自作冠辭亦可。”*(元)鄭泳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jīng)部)第114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頁。說明,宋元時冠辭(字說)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比較普遍。這些冠辭不僅有具體的韻語類祝辭,還會敘述加冠前后的冠禮儀節(jié),將儒家“忠君信友事親”的成人觀念寓于名字的解說之中,處處體現(xiàn)著長者們對冠者的殷切期望,這或許便是朱熹的“命以字之之意”。
還有一些字說,名為“冠說”“冠贊”,多散文議論體,雖不是祝辭,但與冠禮也有著密切關系,如王義山《猶子希文冠說》,文字語言平易,類似于論說文,通篇沒有太多關于冠禮儀式過程的敘述,只是提到“汝父以元服加汝”,然后就開始論述冠禮于成人之意義,“古者重以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焉”,并以大學之道,“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3冊,卷8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58頁。之語對冠者予以諄諄教誨,具體解說儒家對于“人”的要求、如何成人等。
(二)儀式核心要素“加冠”和“命字”的分離
古人有名有字,字作為成年之后的一種身體符號,刻印在成年人的身體之上,伴隨其終生,作為字義的解說的字說文體,在宋代興起以后,通過與冠禮結(jié)合,解說冠義,闡釋儒家義理,在冠禮重建和傳承中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我們看到,“加冠”和“命字”作為冠笄之禮的兩個核心要素,在元代已呈現(xiàn)分離之勢,字說雖然發(fā)揮著部分儀式功能,但意義已很有限,比如其寫作時間本應在加冠之后,但此時于冠禮前后均可。
1.儀式舉行與否及儀節(jié)的先后并不嚴格
一般來說,加冠在前命字在后,比如元代字說中多有“既冠字之某某”而后求字說之語,如蒲道源《劉伯受字序》:“劉福……今年逾弱冠,鄉(xiāng)里之先輩共與進之,欲美其稱呼,請字于余。”*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1冊,卷65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頁。但也有未加冠而提前命字者,如吳澄《吳肜文明字說》:“學子吳肜,年未弱冠,就孫先生受學。肜字文明,問其字學于予。”*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卷49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更有為幾個未加冠者同時命字者,如汪克寬《吳氏三子字說》:“友人吳仲實甫,年且耆艾,見三子長次皆就外傅而受學矣,請余字之,以敘其義而告之。余曰:‘冠而字,則祝之以辭,禮也。今尚幼,盍俟其稍長而命之字,可乎?’仲實答曰:‘生非欲使之尊其名以夸于人也,實欲使之敬其名與字,而亟責以成人之道,俾昭然知所以示訓而永久不忘也。’”*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52冊,卷1595,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頁。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更加強調(diào)字說之于一個人終生的教誨訓誡意義,而不太在乎是否與冠禮儀式合一,也并沒有嚴格遵循加冠命字儀節(jié)的先后。
2.重視字的涵義而忽視儀式的舉行
元代民間不論加冠與否,均強調(diào)命字之舉,但是多注重字的解說而未提及儀式的舉行。比如,安熙《趙氏子名字序》中記載:
方齋趙君為予言:“二子守中、居中既冠而有室,亦既抱子矣,而字尚闕焉。余三子則又成童而未名也。子盍為我名而字之?”予應之曰:“古之人,生子三月,父咳而名之。二十成人,加冠于首,鄉(xiāng)先生醴而字之。此禮之正也。今成人者已冠,而字之固無可疑,余則非所當及也,奈何?”方齋曰:“老夫末疾侵凌,亦既耄矣,及今少康,且幸時得與吾子相周旋于此焉,字而戒之,使他日既冠,睹其字而惟其義,若古人之佩韋弦者而自警焉,以不忘父師平昔之誨,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可乎哉?”*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4冊,卷76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頁。
可見,為人父者為兒子請字重視的乃是字之含義,而非命字的儀式,雖然也提到冠禮的儀式,但其前兩子是否舉行冠禮以及后三子會否舉行冠禮,都不得而知。相較之下,“字”會伴隨一個人終生,其警戒意義似乎更重于一時舉行的冠禮。
對于字的重視,還體現(xiàn)在有的儒者在加冠命字后請多人申說字義,如黃溍《李生字說》:“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為之說以繹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厭其欲,復來征予言。夫冠而字,古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之字辭,一而已。一字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黃溍集》(全4冊)第1冊,卷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頁。這與冠禮的儀式意義有所偏差,字說已成為一種人際交往的中介,失去了具體的儀式功能。
3.字說與儀式的同步關系減弱
冠禮在周代以后除了皇家貴族以外,民間多不行,但只是部分儀節(jié)的衰落,取字儀節(jié)在民間幾乎沒有中斷。*庶人階層取字,據(jù)史料看,至少在明代以前不多見,明代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1《佞幸》“伶人稱字”條載:“丈夫始冠則字之,后來遂有字說,重男子美稱也。惟伶人最賤,謂之娼夫,亙古無字……雖至與人主狎,終不敢稱字。后世此輩儕于四民,既有字且有號,然不過施于市廛游冶兒,不聞稱于士人也。”(楊萬里校點,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56-457頁)。宋初,社會上又興起請字、更字、改字之風,字說創(chuàng)作通常有四種場合:一、行冠禮,聘賓命字,然后請撰字說。二、請字,然后請求命字者撰寫字說,闡釋其意。三、請字之后,別求他人撰寫字說。四、直接請求對方撰說闡釋名字之意。其中,第一、四兩種情況相當少見。*劉成國:《宋代字說考論》。元代的情況也大致如此,理學家借助字說和人生日用之冠禮,通過創(chuàng)建書院和社會講學等一系列教化之舉,將“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等一套倫理綱常之說和禮儀實踐滲透到全社會。
字說本為加冠和命字的注解,應與儀式同步進行,但是從元代字說創(chuàng)作來看,兩者的關系不再有章可循。一般而言,應該是加冠命字的同時或者之后有冠辭進行解說。但在元代,有的是加冠命字前請字說,上文已有論述。有的舉行冠禮與否不可知,但已有名和字,專為請字。比如,虞集《趙孟昌以順字說》:“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為之說焉。”*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6冊,卷838,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頁。再如,方回《潘友文渙字說》:“武夷潘君早中童子科,今年已成人,回同年乙科進士陳此竹天應建寧鄉(xiāng)前輩引之來見,其名易風行水上之卦也,其字曰友文,就求字說。……二十曰弱冠,君今年二十一,則不可無學問之力。”*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7冊,卷21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245頁。還有幾個人一起求字的,如王禮《陸氏四子字辭》和《張氏五子字辭》等,其中所涉及之人年齡不等,加冠與否也不甚明了,只為請字。
具體說來,時人請字的目的大致有二:一為重視字之訓誡之意。如吳澄《余淵字說》所言:“吾郡余氏子名淵,弱冠及吾門,而字深道,屢請予書訓戒之辭為字說。”*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卷49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二來通過字說,申說古禮,遵而行之。像王禮《吳彥琚彥瑀字說》:“居所二子既冠矣,求字于予。……于是字其伯曰彥琚,仲曰彥瑀。二子拜而受之,復求其字之說,庶幾聞古禮之仿佛,遵而行之,不猶賢于求之野乎。”*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60冊,卷185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624頁。的確,字說在闡釋字的涵義時經(jīng)常要提到古之冠禮及冠禮的儀式和意義,所以借請字和字說之機以求遵行古禮者應有之。當然,從客觀上來說,求字說也有借此編織人際關系網(wǎng)絡之嫌。*劉成國:《宋代字說考論》。
(三)賓者與冠者之間的關系更加多元化
賓是為冠者加冠命字之人,《儀禮注疏》曰:“賓,主人之僚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全三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頁。在冠禮中,主人要“筮賓”“戒賓”“宿賓”,即對賓者要經(jīng)過選擇和幾次邀請,可見其之于冠禮和冠者的重要性。但至宋代時,儀式已經(jīng)省減很多,朱熹《家禮》載:“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7冊,第892頁。元代《鄭氏家儀》也曰:“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為之。”*(元)鄭泳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jīng)部)第114冊,第396頁。
賓者在冠禮中的作為也有不同。有的賓者為冠者加冠命字且作字說,如吳澄《鄧衍字說》中提到,“往年虞子及之子集冠,予辱為賓,嘗辭而字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卷49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頁。,即《虞采虞集字辭》。有的賓者為冠者加冠命字但不作字說,而由朋友或者既冠者再另請字說,如王禮《劉仲恂字說》:“禾州劉君子衡……既冠,字曰仲恂,欲聞其義于余。”*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60冊,卷185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4頁。
另外,按照古禮,“父命子名,而朋友字之”*(元)謝應芳:《子京字說》,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43冊,卷1348,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頁。,命字者應為賓者,且賓者與受字者本沒有血緣關系,但到宋元時期多有族內(nèi)長輩或者父親給晚輩命字者,至于其是否舉行冠禮大多沒有提到。如陳櫟《族侄孫子敬子襄字說》:“族兄八府君二孫,長曰翼,年逾弱冠,次曰贊,年亦幾弱冠矣,字猶龂龂未定,決于予。”*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8冊,卷57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頁。
而且字說創(chuàng)作者與冠禮儀式也沒有直接關系,只是為其命字或衍說字義。如蒲道源《陳逢吉字說》:“陳提舉之子名佑……今冠而未字,鄉(xiāng)人以為闕典來請。奉字曰逢吉,且申其義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1冊,卷65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頁。按照理學家吳澄的說法,加冠命字應為賓者所為,且必須在儀式上一起進行,他人的字說不合禮數(shù),但當時這種做法已經(jīng)很多,吳澄也勉強為之。正如其在《宋誠字說》中說:“古之冠者,賓字之,有辭以致祝頌,載在《儀禮》。后世因此,或別作字說以寓規(guī)戒焉,然必出于所師尊之人而后可。非冠之賓而祝頌,諂也;非教之師而規(guī)戒,瀆也。”*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卷49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
盡管元代冠禮與前代相比,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遷,但是“字”所具有的成年符號意義依然存在,而且伴隨著字說創(chuàng)作的繁盛,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部分儀式功能,對于個體成長仍然具有標志性意義,對其做人和成人也具有督促和提醒的作用。
四、字說中儒家成人觀念的變遷
字說作為與冠禮關系緊密的文體創(chuàng)作,承載著時人對于成人的規(guī)定和“人”的觀念。中國社會以儒家倫理為本位,男子二十“冠而字之,成人之道”*楊天宇:《禮記譯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13頁。,最看重的“人”的倫理道德要求。《禮記·冠義》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成人者,將則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焉。”*楊天宇:《禮記譯注》(下),第814頁。五倫所構(gòu)成的禮義,正是成人的基本標準。
對成人品格,儒家也作過具體解說。孔子在《論語·憲問》中提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第149頁。意思是,像臧武仲般充滿智慧,像孟公綽般清心寡欲,勇敢似卞莊子,才藝如冉求,再輔以禮樂,才能成為一個完美的人。同時,在孔子看來,成為完美的人要終生學習,“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第12頁。。荀子在《勸學》中也提出:“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shù)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yǎng)之。……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蔣南華等注譯:《荀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頁。荀子所主張的這種具有“全、粹、美”的人格主體,真與求知、善與意志、美與情感就集注于“成人”一身*朱義祿:《論儒家的“成人之道”》,《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把孔子所說的成人進一步具象化,成為后世儒者所追求的成人之道。
這種傳統(tǒng)儒家所規(guī)定的成人標準和人格標準在元代字說中多有表現(xiàn)。比如,時人命字多取“善”字,因為是理想人格所應具備的。比如,胡炳文《伯善字說》和《李孟善字說》、王禮《嘉善字說》、虞集《易至善字說》等。胡炳文《伯善字說》曰:“明經(jīng)十三世孫成章之孫,性美而嗜學,名元,字伯善。予訓之曰:《論語》善人之上有君子,有圣人。《孟子》善人之上有信,有美,有大,有圣,有神。予與爾祖、爾父所望于爾者非止為善人而已也,況爾之名曰元,而字曰伯善。自元而言善,大善也,純粹至善也。”*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7冊,卷55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頁。文中引述《論語》《孟子》等儒家經(jīng)典和大儒對“善“的解析和要求,將“純粹至善”作為對一個年輕人畢生所追求的境界和成“人”的理想。
“仁義禮智信”“孝悌忠順”等儒家所強調(diào)的德性在字說闡釋中也有體現(xiàn)。如王禮的《劉仲恂字說》中載:“予嘗以謂士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必有其基也。基者何?信實之謂也?人能信實,無往而不恂恂矣。有謙退,無浮夸。有持重,無淺躁。若人也,吾知其可大受也。人至于圣神,極矣。然功未有不基于恂恂之信實,茍無恂恂信實之資,則雖有賁、育之勇,儀、秦之辨,良、平之智,猶五味之本非甘,五色之先無素,未必有所就于天下也。”*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60冊,卷185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5頁。吳澄《黃玨玉成字說》:“予嘉其志,而勖之以學。予所謂學,非欲其學記誦以夸博,非欲其學辭章以炫文也。其學在處善循理,在信言謹行,在孝弟忠順,在睦姻任恤。于家而一家和,于族而一族和,于鄉(xiāng)而一鄉(xiāng)和,于官而一府和。推而廣之,無施不宜”*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5冊,卷49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均強調(diào)了成為一個人應該學習和到達的標準。
但是,我們知道,宋元之際的儒學與前代儒學已有一定差別,元代字說所反映的成人觀念在承襲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同時,也體現(xiàn)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來看王義山《猶子希文冠說》:
先儒教人,八歲小學,十五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成人之謂也。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夫子且然。大學自物格以至天下平,其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為國,國之外為天下。此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有所謂意。意者心之運動,非心之外別有意也。由意有所謂知。知者心之讖悟,非心之外別有知也。由知有所謂物。物者心之天理,非心之外別有物也。貫一心于誠意致知物格之中。此四者,不可以等級言也。故《大學》之道,自正心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3冊,卷8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頁。
寫作者將《大學》之義與冠齡結(jié)合在一起,將儒家對于十五歲成人的標準和要求具象化,使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體的大學觀,作為一種成人觀念深入人心。
結(jié)論
字說在宋代出現(xiàn)以后,歷經(jīng)元明清幾百年,儒者和民間士人在促進冠禮復興的同時,通過字說傳遞和凝固著儒家相對統(tǒng)一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觀念,塑造和規(guī)范著大多數(shù)群體的成人觀念,保證了整個社會在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上的相對穩(wěn)定,從而維護了整個社會的秩序。
我們知道,成年禮是為承認年輕人具有進入社會的能力和資格而舉行的人生儀禮。*鐘敬文主編:《民俗學概論》(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頁。按照楊寬先生所說,周代成年男子三次加冠后,便獲得了統(tǒng)治者、軍人和祭者的身份,具有了參與政治、軍事和祭祀的權(quán)利。*楊寬:《“冠禮”新探》,《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52頁。命字之后,除了“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外,同輩之間均以字相稱,標志著一個人已經(jīng)進入成年人的交際圈,要以成年人的要求來培養(yǎng)、塑造和規(guī)范自己。但是周代以后,冠禮逐漸衰微,其儀式意義也未得到強調(diào)。至清末,隨著劇烈的社會變遷,社會不再需要諱名稱字,“取字”習俗也逐漸衰落。如今,命字之俗只在文人中有部分存在。當前社會又開始成年禮的重建,比如中學的18歲成人儀式、社會上舉辦的仿古成人禮等,但這些儀式均缺失“命字”這一文化符號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和意義。那么,在重構(gòu)的成年儀式中,如何來重構(gòu)一種儀節(jié)體現(xiàn)“加冠命字”所體現(xiàn)的功能存在,又應該構(gòu)建怎樣的成人觀念?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責任編輯]劉曉春
賀少雅(1981- ),女,漢,河北深州人,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民俗學專業(yè)在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K890
A
1674-0890(2016)05-047-09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人生禮儀傳統(tǒng)的當代重建與傳承研究”(項目審批號:14AZD120)的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