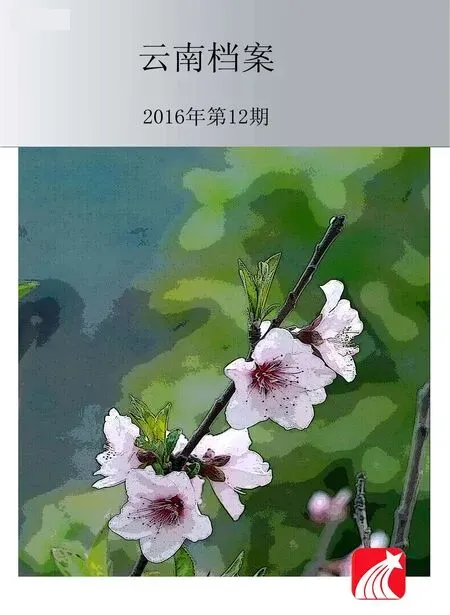康熙朝起居注制度設立考
■冉虎 崔杰 牛麗丹
康熙朝起居注制度設立考
■冉虎 崔杰 牛麗丹
清代起居注制度,始于康熙年間。清入關以前,已有圍繞后金汗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的言行、按時間順序用滿文逐日記載的記事性檔冊,也即現存的《舊滿洲檔》。其記載形式早期多為事后追述,從天命六年起基本形成了按日記事的方式[1]。但是正如喬治忠先生所說,清入關前的這種記事性滿文檔冊“內容廣泛龐雜,不僅記錄君主言行,而且舉凡戰爭過程、族內紛爭、經濟生活、民情風俗、對外交涉、臣僚事跡等等無不收載,是入關前的綜合記錄,與起居注根本不同。[2]”太宗時期還有漢文《太宗文皇帝日錄》的編修,然而它只是依據滿文檔編譯而成[3],性質與《舊滿洲檔》一樣,也不能稱之為起居注。
研究清代的起居注制度,在《康熙起居注》出現以前最值得關注的文獻莫過于《多爾袞攝政日記》了。1933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根據清末江蘇寶應劉啟瑞所藏《皇父攝政王起居注》的副本排印出版了《多爾袞攝政日記》。在此書“敘”中出版者說明了本書發現及出版的大概情形:“多爾袞攝政日記為清內閣大庫藏物,宣統間清理庫檔流落于外,后歸寶應劉氏(即劉啟瑞——筆者注)食舊德齋。原冊起五月二十九迄七月初九而不紀年。茲因中有閏六月,檢勘歷書及實錄,知為順治二年事。原書初無名稱,每日記事后均書記者銜名,與清代起居注體例略同,故劉氏于其所錄副冊題曰《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考清代起居注康熙間始置館,當時尚無其制,今劉氏囑本院刊行,爰改題曰《多爾袞攝政日記》。[4]”1959年,此書的原鈔本被四川師院(今四川師范大學)圖書館購得。該鈔本卷末附有劉啟瑞之子劉文興所做《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其文略謂:“清季宣統初元,內閣庫垣圯,時家君方任閣讀,奉朝命檢庫藏。既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攝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馬可書稿等,遂以聞于朝,……時又在起居注檔上,見有《皇父攝政王起居注》一冊,黃綾裝背,面鈐有弘文院印……是書紀大學士剛林等入見攝政王議政諸事……每日各自為記,末署記者銜名,與起居注體例合。其事皆清初史料,與滿文老檔同一可貴。特書式博大,與康熙立館后所修起居注式不合。[5]”由該跋可知,《多爾袞攝政日記·敘》中所言“原書初無名稱”并不符合實情,實際情況是該文獻被發現時就不僅有《皇父攝政王起居注》的名稱,而且還被昭然列于起居注檔,因此并不能以康熙以前清代沒有起居注館的設立,就否定了該文獻起居注的性質。
現存《皇父攝政王起居注》共計有五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九(閏六月)之間共十二日的記事。從其內容來看,主要記載多爾袞與大學士等議政的情形,如六月初四記:
大學士等入啟事,王上賜坐,叩謝。大學士讀章奏,各隨事處分訖,賜茶。王上問:“殿工大木產于何處?”大學士等對曰:“川廣”。又問:“大木可常有否?”對曰:“極大者亦甚難得,殿柱間有三合四合六合者。”王又問曰“聞皇極一殿費至六百萬金,果否?”對曰:“誠然,其兩廠見貯木料尚不在數內。”王上曰:“一殿之工至六百萬,何太奢耶。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況六百萬乎?然漢文帝吝惜百金亦覺太儉,大凡天下事自有中道,大過與不及俱都不是,如堯之茅茨不剪,亦過于儉,帝王所居,豈宜如此?”大學士等回:“太古之時,原自渾樸。”吏部、兵部各啟事畢,退。
侍讀陳其慶恭記
與入關前的滿文檔冊相比,《皇父攝政王起居注》不再是龐雜的綜合記錄,而是專記“王上”多爾袞的言論,已接近傳統漢族史學“起居注者,錄記人君言行動止之事”[6]的起居注概念。考每日記事人員,由學士李若琳,侍讀陳具慶、朱之俊,侍講高爾儼,檢討成克鞏、高珩、羅憲汶、劉肇國、白胤謙九人,“皆明末天啟訖崇禎間進士”[7],他們很有可能按照明代起居注制度取媚多爾袞,按帝王規制,為其記注起居。
以上通過對《皇父攝政王起居注》的發現過程及本身內容的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多爾袞攝政時代曾經設立過起居注制度,再據私人著作《養吉齋叢錄》所載:“天聰三年,命儒臣分為兩直,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顧爾馬渾、托布戚翻譯漢字書籍,此即日講之義。巴克什庫爾禪同筆帖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記注本朝政事,此即起居注之義。順治十二年,設日講官……康熙九年,復設起居注官(原注:國初有起居注,后裁)……[8]”此處注文很值得注意,“國初”顯然并非指康熙朝,也不是指太宗天聰三年命儒臣分兩直的文館之制,對于順治朝,則從順治十二年講起,專講日講官之設,并未涉及起居注,那么此處所言“國初有起居注”就極有可能是指多爾袞攝政時期起居注之設。至于何時裁撤,難以考證,很有可能是在順治親政后被裁去。
盡管清代官書沒有明言在多爾袞時期曾經有起居注制度的設立,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以上史料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而在順治親政之后不久,起居注制度立刻成為朝廷很受關注的話題。
順治八年九月庚寅,刑科給事中魏象樞奏言于臨御之際,“即召滿漢輔臣二人,講說治道,以弼成圣德。仍擇滿漢詞臣文學雅重者數人,備顧問,記起居。[9]”順治十年正月庚辰,工科給事中劉顯績奏言:“自古帝王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期昭示當時,垂法后世。我皇上種種美政,史不勝書,乞仿前代設立記注官,凡有詔諭及諸臣啟奏,皇上一言一動,隨事之書,存貯內院,以為圣子神孫萬世法則。[10]”兩件奏疏未被采納,僅僅“報聞”而已。顧治十二年二月壬戌,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奏言:“……抑臣更有請者,垂休典謨,光照令德,莫要于設立史官。皇上統一中原,事事以堯舜為法,但起居注官尚未設立……今宜仿古制,特設記注官置諸左右,凡皇上嘉言善行—一記載,于以垂憲萬世,傳之無窮。亦治道之一助也。[11]”順治“嘉其言”。順治十七年六月丁亥,掌翰林院事學士折庫訥條奏八事,其中之一為“起居注宜設,古之盛世,右史記言,左史記動,其善者記之以為法,不善者記之以為戒。乞選方正博學之士授為起居注官,俾隨侍左右,凡一言一動,俱令書記,以垂后世[12]”或許是由于多爾袞攝政時期僭越設立起居注,使順治皇帝對起居注心存惡感,所以盡管滿漢官員多番奏請(甚至包括地位尊貴的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在順治親政時期,起居注制度未再設立。
順治十八年正月,順治病逝,康熙帝即位,以輔政四大臣為首的滿洲保守勢力主張“率循祖制,咸復舊章”。順治十五年仿明朝體制設立的翰林院、內閣也被裁撤,退回到了太宗時期的內三院體制。在這樣的背景下,起居注制度的設立更是無從談起。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清除了鰲拜集團,徹底掌握了國家權力。熱衷于傳統漢文化的康熙帝繼續沿著順治時期封建化的政治道路前行。康熙九年八月,“命改內三院為內閣,其大學士、學士官銜,及設立翰林院衙門等官。俱著查順治十五年例議奏。[13]”恢復了內閣、翰林院的建制,是康熙朝政治進一步漢化的重要步驟。而在此前后,漢族大臣們也在緊鑼密鼓地為圣祖皇帝籌劃著經筵、日講制度。
康熙六年七月吏科給事中藺挺達、康熙七年三月福建御史李棠、康熙七年九月內秘書院侍讀學士熊賜履、康熙八年四月兵科給事中劉如漢等紛紛奏請開經筵日講[14]。在眾多漢官的連番奏請下,康熙于九年十月,諭禮部:“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孟。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爾部詳查典例,擇吉具儀奏聞。[15]”康熙十年二月丙午,命吏部尚書黃機、刑部尚書馮溥等充經筵講官[16]。康熙十年二月已亥,康熙帝第一次舉行了經筵大典[17]。康熙十年四月辛卯,“命日講官進講[18]。”至此,經過眾多漢官多年的努力,最具傳統中原政權特色的皇帝教育制度在康熙朝建立了起來,這表明康熙帝已決意效法漢族政權,以儒治國。因此,并不需要多少人奏請,起居注制度馬上便建立了起來。
《圣祖實錄》關于設立起居注的奏請只有康熙七年九月壬子,內秘書院侍讀學士熊賜履所奏“皇上一身,宗廟社稷所倚,中外臣民所瞻仰。近聞車架將幸邊外,伏乞俯采芻言,收回成命。如以農隙講武,則請立遴選儒臣,簪筆左右,一言一動,書之簡冊,以垂永久。”奉旨“是,朕允所請,停止邊外之行,所稱應設起居注官,知道了。[19]”熊賜履的這件奏疏主要目的是在于請康熙皇帝停止邊外之行,設立起居注官只是附帶一提,而康熙對起居注制度的態度則顯然非常積極。時隔三年之后,康熙十年八月甲午,康熙帝下旨“設立起居注,命日講官兼攝[20]”。
需要說明的是,關于清代起居注創立的時間,清代官書多記載為康熙九年,如《康熙會典》載“康熙九年,置起居注館于太和門外西廊[21]”。此后清代幾部會典以及《欽定日下舊聞考》、《皇朝文獻通考》等書均同,然而正如研究者所說“將起居注館始設時間記載為康熙九年的史籍雖多,但卻同出一源,即康熙朝《大清會典》[22]”。實際上,康熙朝起居注館的設立時間,應以《圣祖實錄》所記康熙十年八月甲午為準。其理由條列如下:一、起居注官既然以日講官兼攝,而在康熙十年三月,才正式以翰林院掌院學士折庫納、熊賜履等充起居注官[23],《康熙起居注》后所附記注官也正是這些人,因此康熙朝起居注館不可能先于日講官而設立。二、從現存的康熙起居注冊看,無論滿文本、漢文本,皆始自康熙十年九月[24],未見有康熙九年至十年八月的記載。三、王士禛《池北偶談》也記載“康熙十年復設起居注館,在午門內之西,與實錄館相對[25]”。王士禛是康熙時人,曾任翰林院侍讀、侍講,并入直南書房[26],他的記載應該有相當的可信度。
綜上可知,康熙朝起居注的設立時間應以《圣祖實錄》為確,即康熙十年八月甲午,并于轉月開始正式記注康熙起居。《康熙起居注》第一條記載為康熙十年九月,“朔已酉。上以寰宇一統,躬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形告成禮。”而在《圣祖實錄》中相同的記載卻在初二日庚戌。啟行日期,兩書相同,均在初三日辛亥。值得注意的是,在起居注中,初二日庚戌缺載,這在已出版的《康熙起居注》中絕無僅有。觀察整個起居注,即使某一天無事可載,也要寫明日期,不使中綴,如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六壬戌二十一日丁卯,均沒有任何記載,但日期卻未缺失。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康熙做出告祭祖陵的決策,正如實錄的記載,是在初二日庚戌,起居注將其系于初一日已酉,只是為了追求記載的完整性。這一方面更加說明康熙朝起居注的記載始于十年九月,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起居注正式詳細記載康熙言動始于十年九月初三日辛亥,這一日的記載為“卯時,駕出午門,素服,不奏樂,不設鹵簿。在京王、貝勒以下及文武大小各官跪送,王、貝勒以下文武大臣出城遠送。是日,上出朝陽門,駐蹕三河縣。地方文武官員來朝。”
[1][2]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頁、159頁。
[3]莊吉發:《清代起居注冊的編纂及其史料及其史料價值》,載《清代史料論述》(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4]《多爾袞攝政日記·敘》,北平故宮博物院編,鉛印本,北平:故宮博物院,民國二十二年(1933)。
[5][7]轉引自熊克:《清初〈皇父攝政王起居注〉原本題記》,四川學院學報,1981。
[6]唐魏征等:《隋書·經籍志》,《隋書》卷三十三,第966頁,中華書局1973年8月。
[8](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第15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
[9]《世祖實錄》卷60,順治八年九月庚寅。
[10]《世祖實錄》卷71,順治十年正月庚辰。
[11]《世祖實錄》卷89,順治十二年二月壬戌。
[12]《世祖實錄》卷136,順治十七年六月丁亥。
[13]《圣祖世錄)卷33,康熙九年八月乙未。
[14]《圣祖實錄》卷23、卷25、卷27、卷29。
[15]《圣祖實錄》卷34,康熙九年十月丁酉。
[16]《圣祖實錄》卷35,康熙十年二月丙午。
[17]《圣祖實錄》卷35,康熙十年二月已亥。
[18]《圣祖實錄》卷35,康熙十年四月辛卯。
[19]《圣祖實錄》卷27,康熙七年九月壬子。
[20]《圣祖實錄》卷36,康熙十年八月甲午。
[21]《康熙會典》卷155《翰林院·起居注館》
[22]喬治忠、王鴻雁:《清代官修史書與〈大清會典事例〉》,載《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3]《圣祖實錄》卷35,康熙十年三月癸丑。
[24]參看中華書局1984年版《康熙起居注》書前《說明》與莊吉發《清代起居注冊的編纂及其史料價值》載《清代史料論述》(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25](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勒斯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1997重印
[26]《清史稿·王世禎傳》,第9952頁
作者單位:天津外國語大學綜合檔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