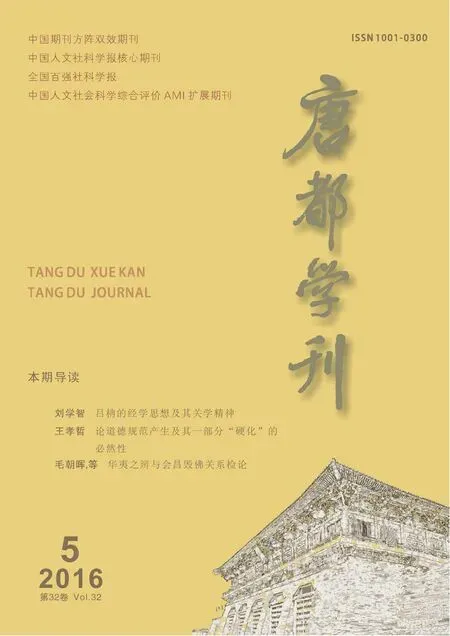憶忠實
王仲生
(西安文理學院教授,文學評論家)
?
憶忠實
王仲生
(西安文理學院教授,文學評論家)
忠實走了,永遠離開了這個紛擾的塵世,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2015年春節剛過,忠實打來電話,要我們陪他去西京醫院看病。
這很不容易。在這之前,我老伴從電話里聽出忠實說話有些口齒不清,問他怎么回事,他說是口腔潰瘍。我們勸他看病,他說不要緊,很多朋友都給他拿了各種藥,只是吃了不見好,等他忙過這一陣再說看病的事。
一連幾個禮拜,我們一催再催,他一推再推,總有忙不完的事。
這次是他打電話主動要我們聯系看病。不一會兒,他說又有事,這就又往后拖了一個禮拜。
從三月底開始,到病情確診。一年多時間里,我們與忠實的子女,投入到為忠實尋醫問藥,檢查、治療的痛苦日子。每一天都在十分期望、十分焦慮中度過。忠實的子女,特別孝順,這也與忠實的家教分不開吧。他們竭盡了全力。
而忠實呢,一旦看起病來,他就十分尊重醫生。只要他同意的,絕對做到。他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雷醫生感慨地跟我們說:“老頭兒太堅強了,老頭兒太堅強了。”
他雖然沒有說,但我們感覺得到,他不相信他會得這種病。他那創造文字“奇跡”的自信,頑強的生命自覺,都使忠實不肯也不愿相信,他會在病魔前倒下。
他堅信,他能戰勝頑疾惡癥,這在很大程度上,為他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強大精神力量。
整個治療過程中,忠實表現得特別頑強。
他說話越來越不方便,吞咽也一天比一天困難。他居然一改整天吃面條、面食的習慣,要求子女天天為他做米飯、炒菜。不難想象,每次進餐,他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我老伴為鼓勵他、安慰他,開玩笑說,忠實變南方人了。忠實會心地嘿嘿一笑。
2015年10月6日,忠實還主動來我家要老伴給他包餃子吃,他說好久沒有吃餃子了。那時他剛治療出院不久。
忠實有一個習慣,或是情緒好,或是情緒特別不好時,會到我們家,吃我老伴包的餃子。我老伴餃子做得可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們家,忠實總會遇到常來我家的中年人、青年人,他們都是文學工作者、文學教學者,或是《白鹿原》愛好者。無拘無束的笑談中,忠實會爆發出他少有的暢懷大笑,不是嘿嘿嘿,而是暢開心懷的大笑,感染人的笑。響亮得哈哈哈,回蕩在客廳。
忠實吃過飯,常常會坐到客廳長沙發上,一邊抽著雪茄(這也是特許,通常抽煙都得到陽臺長廊上),一邊抿著茶(他只喝陜青),徹底放松了他的身軀和情緒。
談話往往沒有主題,是河水漫過淺灘,漫無邊際,隨意聊天。
偶爾,扯到忠實感興趣的話題,他會興奮,那是河水激起了浪花。忠實沉浸在他的思緒里了,眼望著對話人,或站在陽臺,望著遠方。那犀利、銳智而透著狠勁的雙眼,有了閃電驚雷,有了春風旭日。
更多的時候,忠實會舉起夾著雪茄的瘦骨嶙峋的右手,細聲慢語,回答大家的提問。或是他經歷中的一個片斷,或是《白鹿原》里某個細節。是一個老者,對著晚輩的家常談話,樸實而誠懇。談著談著,忠實會把眼光轉向我,似乎是征詢我的看法,我們會心一笑。河水緩緩流淌,在時光的流逝里,煙霧的繚繞里。
2015年10月6日那天,忠實情緒似乎特別好,健談,開玩笑。說到寫字,他說我老伴才是書法家,又補了一句“真正的書法家”。在座的人滿堂歡笑,向力趕快打開“ipad”,可惜,忠實不再重復,只錄下了一片笑語和忠實憨厚的嘿嘿聲。他好像有些得意。
忠實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但他仍堅持隔天去石油大學工作室。
一天,我們去石油大學工作室看忠實(事先電話聯系好的)。
我們在客廳沙發上坐定,忠實泡上了陜青茶。
無語的對視中,他雙手撐著沙發,對我發出了長長的一聲苦笑,笑得開放、持久,又很坦然、無奈。我明白他,他的苦笑,告訴了我,在與病魔的頑強對抗中,他竭盡了全力,但他并不會放棄絕望中的抗爭。他雙手交叉合十,緊緊地、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我想起了魯迅先生,魯迅于絕望中仍堅持渺茫的希望。
忠實終于躺倒在病房,他仍堅持每晚回家,他不愿住在病房,他以這種方式,宣告他的生命不可戰勝。
一次,我們去探望忠實。
我說:“你別說話,你只需表示一下就行了。”我接著說:“春天來了,你可以走出去,曬曬太陽。過幾天,天氣好了,我們陪你去你西蔣村的老屋看看。好嗎?”
躺在病床上的忠實,點了點頭。
我說:“我們還可以陪你去1989年酷熱的暑天,你在郭李村君利家寫下《白鹿原》第十一章的那孔窯洞。”
他沒有點頭,只是默然,我懂他的默然。一個將軍會回到他奪得輝煌戰績的昔日戰場嗎?
2016年4月27日上午,我們去醫院探望忠實。他極度虛弱,靜臥在床。
聽到我們的問候,他突然睜開了緊閉的眼,睜得那么大,那么圓。他努力把眼皮往外轉,還往外轉,幾乎要把頭昂起。那雙鷹瞵鶚視的大眼,此刻,是一片溫柔、溫暖,明凈如一汪泉,平和、寧靜;如一片海,浩瀚、祥和;如狂風暴雪肆虐后,一輪白日,照耀在莽莽雪原;如疾風驟雨掃蕩后,一盤滿月,把大地照亮得晶瑩剔透。美麗,美麗得讓我驚訝!一個年過七旬的老人,竟然擁有如此美麗的慧眼、巨眼。美麗的大眼,定定地看著我。
我緊緊握住忠實的手,無語。
我80年的生命中,從來不曾看到過這樣大而美麗、仁愛的眼。一絲不祥的預感掠上心頭。
忠實悄聲問:“王老師有啥事?”他仍在為我操心。
勉力細聲說:“啥事沒有,來看看您!”
忠實安靜地合上了眼。病室悄然。
4月28日上午,忠實的妹妹電話告訴我們,忠實病情穩定,他哥還在看手機,我們的心平靜了點。
誰會想到,4月29日晨,得到噩耗,董寶綏開車,我們匆匆趕到醫院,與忠實作最后的告別。
巨大的悲痛讓我哭倒在沙發上。
種種往事,影像般從心頭掠過……
1990年9月23日。
我與忠實八九人一行赴成都參加四川文聯與作協組織的成都軍區某作家的作品研討會。
坐的是硬臥,忠實與我正好上、中鋪,我們徹夜長談。忠實興奮地壓著嗓子,向我講述他正在寫的《白鹿原》。談得高興了,坐到車窗另一邊,邊抽煙邊聊。
他講到,戲臺下,田小娥如何勾引了白孝文……
他講到,白靈與鹿兆海用丟銅錢來決定是加入國民黨還是共產黨……
我被這些離奇的講述吸引。
我對農村素不了解,聽了如同天方夜譚。
我明確表示,丟銅錢,可以理解,對于北伐前后那段歷史,我比較熟悉。
我理解忠實。一個作家沉浸在長篇創作的構思里,那是一個人的世界。他也需要傾訴。
這年10月,我去南京,第一次參加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理事會,會議間隙,完成了近萬字的長篇文章,《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評陳忠實八十年代后期創作》,刊于《小說評論》1991年第2期。這篇文章,分析了忠實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中、短篇小說,指出忠實正在實現他創作生涯中巨大的轉變。如果是,此前,忠實的創作基本上是站在農民的角度,寫政策調整后農村的變革;而現在,忠實已從民族反思的高度,從歷史與文化,從道德與心理,以審美創造書寫中國社會變革在農村激發的巨變。這篇文章,在省作協引起不同反響。但它為《白鹿原》的出現,提供了一個讓人信服的說明和闡釋。
社會上,甚至文學圈內,往往有一種錯覺、誤解,認為《白鹿原》橫空出世,對忠實來說,不可思議。如果他們讀過忠實這批作品,讀過《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他們將會釋然、了然。
《白鹿原》的問世,實在是忠實20世紀80年代后期創作的必然,是80年代我國思想解放、文學發展的必然。
1992年3月29日,忠實來我家,親自送來《白鹿原》手稿,他有些拿不準,讓我看看能行否?4月7日,我讀完手稿,4月21日,忠實邀我去他家做客,在座的有李星。我們一致肯定了《白鹿原》,認為忠實獲得了巨大突破。
1992年底,《白鹿原》在《當代》問世,1993年,《白鹿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白鹿原》一書難求。
1993年3月23、24日,陜西省委宣傳部、省作協聯合召開《白鹿原》研討會,我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
《小說評論》1993年第4期刊發了長篇小說《白鹿原》評論專輯,我的《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詢和構筑》為專輯頭條。
看《專輯》不難發現,這是當時國內第一篇全面論述《白鹿原》的評論。
1993年第6期《文藝理論與批評》刊發了我的另一篇長篇評論:《人與歷史、歷史與人——再評陳忠實的〈白鹿原〉》,刊在《商榷與爭鳴》專輯,這個專輯同時刊發了付迪先生的《試評〈白鹿原〉及其評論》,對我的文章進行商榷。
1993年7月14日,我與忠實、田長山一行,赴北京參加中國作協召開的《白鹿原》研討會。15日入住大雅寶空軍招待所北樓316室,16日在文采閣研討會一天。與會評論家一致高度評價了《白鹿原》,我在會上發言。17日上午陪忠實在王府井新華書店簽名售書。排隊的人,從店門直延長到街道,盛況空前。21日與忠實乘車離京。其間,我與忠實先后訪問過許覺民、鄭伯農等先生。當時,社會上傳言,《白鹿原》有傾向性問題,爭議較多。10月21日,陜西省委宣傳部王巨才部長、文藝處處長孫豹隱召集了六位先生(王愚、李星、蕭云儒、劉建軍、暢廣元與我)入住西北大學留學生樓,以封閉方式,討論了陜軍東征作品,主要是討論《白鹿原》與《廢都》兩部作品,一致認為兩部作品都是了不起的作品。
會后形成了一個紀要,呈中宣部。
《白鹿原》開啟了一個文學新浪潮。這時,評論文章紛起,各位名家的評論先后見報。
1993年,忠實當選為省作協主席,他忘我地投入到作協管理工作,對全省文學創作極力推動。
1995年4月,我與忠實應耶魯大學東亞文學系主任孫康宜博士邀請,去耶魯、哈佛燕京學社、波士頓華人文化中心講學,5月轉加拿大溫哥華華人文化中心講學。
一個多月的朝夕相處,忠實的人格魅力讓我有了進一步了解。
在紐約,應邀參加一個宴會。不料,大廳里,聲光、攝影設備早已布置完備,原來是“美國之音”要現場采訪。半個小時,很高的酬金,我們斷然拒絕。忠實表示了義憤,指出,這是突然襲擊,強人所難。對方再三表示,不設框框,隨意聊聊來美觀感。幾經磋商,我們決不妥協,對方只好作罷。
席間,宴請方自己起了沖突,激烈的爭論搞得氣氛緊張,我們只好勸住了雙方。
宴席是《中央日報》《世界日報》兩家搞的,兩位報社駐美國主編在政治立場上顯然不一致,說著說著,吵得臉紅脖子粗,不歡而散。有趣的是,《世界日報》主編又從紐約追到波士頓,找到我們。他說的是東西文化差異,中國文化的魅力,這是一個有趣的媒體人。
記得剛從溫哥華機場出關,一大批記者圍了過來,“請問您如何看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被抓?”我脫口而出:“這是我們反腐……”話還沒落音,記者們一轟而散,走得光光的。忠實哈哈大笑,“這幫家伙,自討沒趣。”
忠實訪美的口頭禪是:“狗日的美國,啥好的都搞到它這來了。”
忠實在美國吃不到家鄉的面條,急不可耐。后到一華人家,媳婦是丹鳳人,專門給他做了一頓燃面。忠實吃得那個香啊,抹抹嘴,再來一碗。臨了,還要喝一碗面湯。這個習慣,在以后的交往中,我發現,幾乎終生難改。
我的外孫女兩三歲時,每次忠實招待,她也學忠實,要油潑面。后來,她回了美國,油潑面成了她思鄉的一道不忘的記憶。
一次,席間大家議論起了《白鹿原》,小外孫女突然高聲說:我知道了,陳爺爺有兩個名字,一個叫陳忠實,一個叫《白鹿原》,滿堂哄笑。忠實更是高興:“這娃聰明扎咧。”
每次我們去美國探親,忠實都要為我們餞行。這次忠實住院,每當我們去看他,他都要問:“啥時去美國啊?”我們只好說:“還沒定呢。”我們總在想,等忠實康復了或穩定了再定。
契訶夫說:“我懼怕托爾斯泰離開人世。如果他死了,那么我的生命將出現巨大的空白。”
忠實的離去,讓我們的生命同樣出現了巨大的空白。今生今世這個空白,無法彌補。它不只是文學的空白,作家道義擔當的空白,更是真誠友誼的空白。
忠實忠實于生活。他的作品,尤其《白鹿原》絕不粉飾生活。小說《白鹿原》創造了我國20世紀文學的高峰,捍衛了文學的良知和責任。
忠實忠實于文學,他說文學依然神圣。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保留一份神圣,這對于人類太可貴了。
忠實忠實于友誼。他絕不褻瀆友誼。他珍視他作品的讀者,一律平等相待,忠誠相待。即使他臥床不起,他仍然堅持為讀者簽名。一旁的我,唯有尊重、敬重。
陶淵明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小說《白鹿原》將與地域概念的白鹿原同在。
[責任編輯王銀娥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