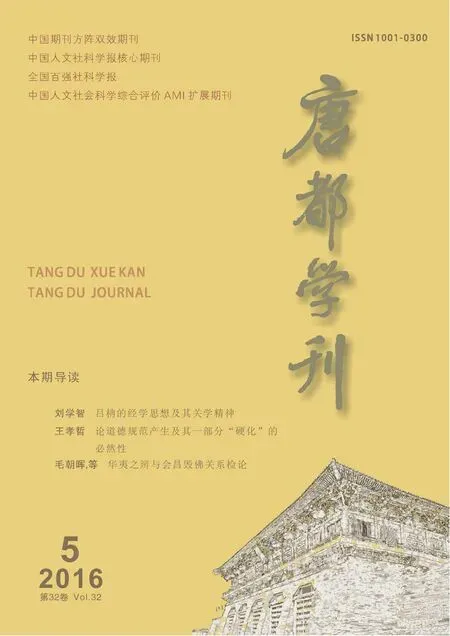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綜述
王興鋒
(貴州師范大學 歷史與政治學院,貴陽 550001;陜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西安 710062)
?
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綜述
王興鋒
(貴州師范大學 歷史與政治學院,貴陽550001;陜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西安710062)
匈奴是北方草原上一個歷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影響了當時歐亞大陸的歷史進程。最早開啟匈奴歷史地理研究的是清末學者丁謙。自此以后,關于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越來越引起學界關注。百年來,研究范圍涉及匈奴族的相關地名考證、城址考證、人口數量、行政區劃以及民族遷徙與分布等方面,成績斐然,其中,在匈奴族筑城問題等方面學界已達成共識,但仍需借助新發現、新技術、新觀點,加強匈奴族歷史地理的研究。
匈奴;歷史地理;民族地理;民族史
匈奴族是中國歷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數民族之一。它興起于戰國末年(公元前3世紀前后),西漢中期以后,在漢朝大規模軍事打擊下日益衰落。直至東漢前期(公元1世紀),匈奴族分裂為南、北兩支,南匈奴附漢內徙,其屬部在中原地區活躍了近兩百年;北匈奴逐漸西遷,其后裔在此后的幾百年間不斷向西征服,直達地中海西岸,引起歐洲大陸民族大規模遷徙。縱觀匈奴族歷史,其活動區域涉及歐亞大陸,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進程。長期以來,匈奴族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筆者就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的研究狀況略作梳理,以供學界參考。
一、匈奴族相關地名研究
最先開啟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的是清末著名地理學者丁謙。他專治邊疆及民族地理,先后對《漢書》《后漢書》做了較為詳細的地理考證,撰寫了《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后漢書南匈奴傳地理考證》(其文收錄丁氏著《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全四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丁謙的研究僅限于地理名詞考證,未參考出土文獻,也未做過實地考察,所以他考證的諸多地名有待商榷,但是這些著作對后世學者研究匈奴族的源流及地理分布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祁連
“祁連”一詞最早出自《史記·大宛列傳》:“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關于“祁連”的地望,學術界存在較大爭議。
一說指今祁連山。
《史記·大宛列傳》張守節《正義》:“祁連山在甘州西南”為此說張本。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烏孫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巖波書店,1970年版)為此說之代表。中國學者戴春陽《祁連、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認為祁連山在河西走廊。
一說指今天山。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顏師古注:“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為此說張本。日本學者內田吟風《關于月氏遷移大夏的地理年代考證(上)》(《東洋史研究》3~4,1938年)、中國學者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中華書局,2004年版)為此說代表。
余太山《烏孫考》(《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認為《史記》和《漢書》所載烏孫的故地是一致的,區別在于前者略而后者詳。張騫所謂“祁連、敦煌間”應指天山、祁連山以北廣大平原,東起河套,西達準噶爾平原。余太山著《塞種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認為祁連即今天山。劉文性《“祁連一名天山”質疑》(《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認為天山是一條基本上呈東—西走向的山脈,它的地理位置“在西域”,所以必須“出敦煌”。它橫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全境,但并不同甘肅的什么山體相連接。王建新《中國西北草原地區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新進展—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載于《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三輯,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也認同此說。
綜合兩說的有陳世良《渾邪考》(《新疆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認為祁連山應包括今甘肅祁連山和新疆東部天山。臺灣學者劉義棠《祁連天山考》(《政治大學民族學報》1994年第21期)一文從歷史地理與語言學的角度考證出驃騎將軍所攻者為甘肅境內之祁連山,貳師將軍與竇固所攻者為新疆蒲類附近之天山。
此外,探討“祁連”一詞語源的論文有:賀德揚《論“祁連”》(《文史哲》1990年第3期)認為“祁連”一詞是上古漢語固有的詞匯。王雪樵《古匈奴人呼天為“祁連”本出漢語考》(《晉陽學刊》1994年第4期)認為匈奴語中原本并無“祁連”這個詞,匈奴人將漢語“天”字讀作了“祁連”,于是漢人所說的“天山”,在匈奴人口語中便成了“祁連山”。林梅村《祁連與昆侖》(《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收入《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考證,祁連一詞源于吐火羅語,后被匈奴沿用。匈奴人稱敦煌南山為祁連山。王玨《“祁連”一詞是漢語詞還是匈奴語詞》(《周口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1期)也認為“祁連”一詞是一個地道的漢語詞,是“天”或“乾”的古老的緩讀分音形式。
2.蹛林
《史記·匈奴列傳》載:“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司馬貞《索隱》引服虔云:“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鄭氏云:“地名也。”《正義》引顏師古云:“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關于“蹛林”為匈奴的祭祀之地,史學界并無異議。如我國學者方壯猷《匈奴語言考》(《國學季刊》第2卷第2號,1930年12月)一文運用比較語言學方法考釋了26個匈奴族名號,認為蹛林即“祭所”。主要分歧集中在蹛林的地望。
岑仲勉《跋突厥文闕特勤碑》(《輔仁學志》第6卷第1、2期,1937年6月;又載于林幹編《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認為蹛林為北方民族之圣地塔米爾河之臺魯爾倭赫池。日本學者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黃舒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9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原載江上波夫著《匈奴文化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1948年版)論證匈奴祭祀的“蹛林”是以自然林木為圣所,于該處聚會,行祭祀、宴樂、或豎樹枝、或積之為祭壇,會眾繞其周邊,以祭祀天地諸神的習俗,東起太平洋,西迄東歐,北自西伯利亞,南至喜馬拉雅山,至今仍為歐亞諸民族最普遍實行的宗教活動之一。
3.甌脫
“甌脫”出自《史記·匈奴列傳》,其傳載:“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邊為甌脫。”司馬貞《索隱》引漢代人服虔曰:“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地。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裴骃《集解》引三國時人韋昭曰:“界上屯守處也。”唐人張守節《正義》按:“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唐人顏師古注云:“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舍〕也。”自漢唐以來,諸家對“甌脫”的解釋不盡相同。當代學者對“甌脫”一詞的理解提出多種看法,有“(土)室”、“邊界”、“哨所”、“空地”、“領地”、“中立地帶”諸說。
清末學者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全四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認為“甌脫”指兩部族、兩國之間的“棄地”而言,大意不過謂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1923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發表《匈奴起源考》(巴黎《亞洲雜志》第202卷,后改名《蒙古民族起源考》于同年復載日本《史學雜志》第18期,中國學者何健民于1936年將此文譯成中文《匈奴民族考》,收錄于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一文利用語言學博稽群籍考訂了諸多匈奴族名詞,其中與地理相關的名詞有甌脫、祁連。他認為甌脫系指“室”。方壯猷《匈奴語言考》(1930年12月《國學季刊》第2卷第2號)一文認為甌脫即“土室”。三位學者先后對“甌脫”一詞做了解釋,但仍承襲傳統觀點,未對甌脫作深入解析。
改革開放后,中國學者對“甌脫”給予極大的關注。首先,林幹《匈奴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認為甌脫是匈奴語邊界的意思。何星亮《匈奴語試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一文認為甌脫為哨所之意。劉文性《“甌脫”釋》(《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認為甌脫的實質是“中立地帶”。他進一步分析了“甌脫”產生的原因。張云《“甌脫”考述》(《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認為甌脫有兩層含義:一為本意,一為引申之意。他認同韋昭的解釋,即“界上屯守處”,此為本意,而引申之意是因在邊界上有軍事防守作用,自然要設立哨所之類,故而有時又可作候望或斥候之所講。
鑒于劉、張二文對甌脫的不同解釋,何星亮又發表《匈奴語“甌脫”再釋》(《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何先生充實了自己的邊防哨所說,認為“甌脫”為邊界上的防衛設施。隨后,劉文性發表《“甌脫”再認識——與張云、何星亮同志商榷》(《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對二人關于甌脫為邊防設施的說法提出異議。既不贊同何星亮的“甌脫”為“ordu”的音譯,也不贊同張云的“匈奴與其他國家臨界處應當都有甌脫”的說法。他認為討論“甌脫”一語的關鍵,是首先弄清詞義。只要把詞義搞清了,也就抓到了問題的實質。至于語源問題,是第二步的、次要的問題。大家可以在對詞義共同認識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我國北方各民族的語音,從中找出最理想的答案。
陳宗振《古突厥語的otar與“甌脫”》(《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利用比較語言學方法認為“甌脫”有一個較抽象的、深層的意義,即“臨時住所”。“土穴”、“土室”、“界上屯守處”、“境上斥候之室”、“境上候望之處”可說是“甌脫”一詞的引申意義。胡·阿拉騰烏拉、高玉虎《簡論“甌脫”的起源與發展》(《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1990年第3期)否認“甌脫”是邊界、防守地的意思,認為“甌脫”在匈奴時代作為社會組織的行政基本單位,蒙元時期被用作游牧營地或狩獵時的輔助名詞,即鄂托克。胡和溫都爾《甌脫義辨》(《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認為“甌脫”是領地的意思,并論述了“甌脫”一詞在歷史上的演變過程。臺灣學者逯耀東《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載于《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華轉變的歷程》中華書局,2006年版)認為漢匈間確有甌脫存在,即為漢匈非武裝之緩沖地帶,并進一步指出甌脫為漢匈民族交往的媒介。李煥青、王彥輝《匈奴“甌脫”考辯》(《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2期)認為“甌脫”一詞的語意,應從蒙古高原特有的生存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的角度思考,最初是指匈奴族對本民族的祖居地、發祥地和自己母性部落的稱謂和記憶,后來又指稱分地、宮帳(龍庭)、軍營或營地。提出理解甌脫含義的關鍵點,首先必須理解游牧民族的生存環境、生產方式與生活習慣,只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所有關于甌脫的記載也就迎刃而解了。
4.瀚海、北海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漢武帝元狩四年春,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攻擊匈奴左賢王,進而“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裴骃《集解》引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異志》云:“在沙漠北”。關于瀚海,史學界有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瀚海是沙漠。如林劍鳴在《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中寫道:“大軍出代二千余里,在狼居胥山翰海沙漠(今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旗北)大敗匈奴左賢王。”張志坤《漢代匈奴北海之考辨》(《史學月刊》1994年第2期)認同林劍鳴關于瀚海即沙漠的觀點,但對于翰海沙漠在今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旗北的觀點提出質疑。此外,還有趙永成《“瀚海”不是海》(《咬文嚼字》2002年第10期)亦認為瀚海即沙漠。
第二種觀點認為瀚海是湖澤。如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79年版)把今貝加爾湖標明為北海、瀚海,并標明霍去病進軍路線直達湖邊。傅金純、紀思《“瀚海”、“狼山”應何在?》(《固原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認為《史記》所言瀚海,當在蒙古高原東北境,可能即今呼倫湖和貝爾湖。南北朝史文中,“瀚海”仍為北方的海名,只是記載的方位有異,其中又疑指今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應曉琴、黃珅《瀚海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考察了“瀚海”一詞的演變。認為原指貝加爾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時具三種含義:貝加爾湖、天池、沙漠。和談《“瀚海”本源辨正》(《蘭臺世界》2012年第12期)認為“瀚海”源出《三國志·魏書》,是東海中一處海域的名稱。
第三種觀點認為瀚海是山脈。岑仲勉在1958年改定的《自漢至唐漠北幾個地名之考定》(載于《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2004年版)通過考證,認為“瀚海”是音譯,即“杭海”、“杭愛”,是阿爾泰山的支脈。
第四種觀點認為瀚海是山隘。柴劍虹《“瀚海”辨》(《學林漫錄·二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認為兩千多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民族稱高山峻嶺中的險隘深谷為“杭海”。霍去病率大軍登臨峻嶺險隘,聽當地居民稱之為“杭海”,遂以隘名山,后又將這一帶山脈統稱為“杭海山”、“杭愛山”,泛稱變成了專有名詞。
“北海”一詞出自《漢書·李廣蘇建傳》,其傳載:“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將北海標在今貝加爾湖。張志坤《漢代匈奴北海之考辨》(《史學月刊》1994年第2期)對史學界公認的北海即貝加爾湖提出質疑,認為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幾個湖泊如庫蘇泊、烏布蘇諾爾湖、吉爾吉斯湖都有可能是漢時所謂的北海,而其中的烏布蘇諾爾湖較有可能成為北海。
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焉支與祁連》(藤田豐八著、楊煉譯,載《西域研究》,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也對祁連進行了考證。佐藤長《關于匈奴的若干地名》(《東洋史研究》,1990年)考證了與匈奴族相關的窴顏山、趙信城、姑且水、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等諸多地名。
二、關于匈奴族的遷徙與分布研究
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收錄于《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運用音韻、考據等傳統史學方法把匈奴名稱的演變做了系統的概括,認為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后世所謂的匈奴。其文梳理了先秦時期中國北方諸戎、狄、胡的分布方位、支流、流變情況,以及他們參與構成匈奴部落聯盟的情況,具有開創性意義。
1.通史性論著
馬長壽著《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年版),作者首先論述了與匈奴有密切聯系的北狄,討論了北狄的意義、分布、種類以及與華夏諸國的關系。認為當春秋、戰國之時,北狄在中國史上的位置十分重要,所以講匈奴必須先講北狄。其次,第三章探討了匈奴的人種、語言、文化和社會制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第四章對匈奴人入居中國內地也做了比較詳細的討論。
林幹著《匈奴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書作者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和方法,對匈奴族的經濟生活、社會結構、政權組織、文化習俗、部族興衰、政治演變及與其他各族、特別是漢匈關系,做了比較全面而系統的敘述。
安介生著《歷史民族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是目前國內第一部研究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的系統性著作,對中國歷史民族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學科性質、研究現狀、研究方法等諸多問題提出初步的認識與研究構想。其第二章《秦漢三國民族地理》第一節《秦漢至三國時期匈奴民族分布區的演變及相關問題》,首先論述了秦至西漢北方匈奴分布區與變遷,其次探討了東漢至三國時期匈奴族的南遷與匈奴分布區的南拓。
2.匈奴諸王駐牧地
《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又載“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遷徙。”所謂各有分地,即匈奴單于以及左右賢王等各部諸王所管轄的地域有一定界限,而左右賢王以下的諸王將,也在相對固定的草場放牧。1964年,林幹發表《匈奴諸王駐牧地考》(載于《匈奴史論文選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考證了包括單于在內的匈奴諸王駐牧地,其成果為諸多學者所引用。此后,王宗維《匈奴諸王考述》(《內蒙古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從匈奴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管理體制入手,全面考察匈奴諸王的性質、地位和分布等問題。王可賓《匈奴左地與姑夕王駐地》(《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年第2期)一文考證了匈奴左地,同時對林幹關于姑夕王駐地可能是在今內蒙古哲盟、昭盟和錫盟一帶提出質疑,認為姑夕王的駐地,只能在今錫林郭勒盟一帶。
3.匈奴內徙研究
關于匈奴內徙的論著除了安介生《歷史民族地理》,主要有:宋慶嵩《漢人北徙與匈奴南遷》(集美學校校董事會編《集美校友論著》第二輯,1948年)通過分析史料歸納了漢人北徙的原因,其次著重分析匈奴內遷原因及漢朝對內遷匈奴的安置等問題,最后將匈奴內遷與西晉末年的徙戎論聯系起來,認為西晉政府不能采納郭欽、江統的建議致使內遷匈奴成為西晉一大禍患。楊東晨《論從葷粥至匈奴的遷徙和融合》(《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6期)探討了從葷粥至匈奴的遷徙及其與漢族的融合。李吉和《匈奴的內徙及其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探討了匈奴由于各種原因從漢朝開始不斷向內地遷徙,并論述匈奴內徙之后因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遷而加速匈奴部落制的解體,最終促進民族整合和匈奴生產方式的變遷以及文化的變動。薛海波《南匈奴內遷與東漢北邊邊防新論》(《內蒙古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論述了南匈奴內遷后并沒有在東漢解決北邊邊患的戰爭中發揮多大作用,而且至東漢后期,南匈奴又成為東漢北部邊疆的一大邊患。
4.北匈奴西遷研究
西漢晚期,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公元73年至91年,北匈奴在東漢政府的軍事打擊下被迫西遷。此后,北匈奴西遷直至頓河、多瑙河流域,其后裔不斷向西征服,直達地中海西岸,引起歐洲大陸居民的大范圍遷徙。北匈奴西遷的經過,中國史書語焉不詳,因此,關于北匈奴西遷的研究,西方學者首先提出并得到廣泛關注,相關研究可以參見林幹《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匈奴述評》(上、下)(《內蒙古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1990年第1期)、賈衣肯《匈奴西遷問題研究綜述》(上、下)(《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9、10期)。
在歐洲學者的影響下,我國學者于20世紀初也開始關注這一問題。最早是清代內閣學士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商務印書館,1936年),其文首先引入西方學者有關公元前后至三、四世紀歐亞草原中部諸族分布及活動情況的論述,詳細介紹了阿提拉西征歐洲始末。此后北匈奴西遷問題引起中國學者的極大關注。相關研究有:章炳麟《匈奴始遷歐洲考》(收錄于《太炎文錄初編·別錄》,《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丁謙《漢以后匈奴事跡考》(《地學雜志》1919年第7、8合期)、金元憲《北匈奴西遷考》(1935年6月《國學論衡》第5期上)、何震亞《匈奴與匈牙利》(1937年2月《中外文化》第1期)、佟柱臣《匈奴西遷與歐洲民族之移動》(1942年1月《學藝》第2輯)、閻宗臨《匈奴西遷與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學術通訊》1962年第2期)
改革開放以后,相關論著層出不窮。中國學者主要關注匈奴西遷的原因和路線。如齊思和《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歷史研究》1977年第3期)、肖之興《關于匈奴西遷過程的探討》(《歷史研究》1978年第7期)、林幹《北匈奴西遷考略》(《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舒順林《略論北匈奴西遷的原因》(《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郭平梁《匈奴西遷及其一些相關問題》(《民族史論叢》第1輯,1987年)、王彥輝《北匈奴西遷歐洲的歷史考察》(《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吳興勇《論匈奴人西遷的自然地理原因》(《史學月刊》1991年第3期)、馬駿騏《略論匈奴西遷》(《貴州文史叢刊》1999年第4期)、馬利清《關于北匈奴西遷的考古學新探索》(《內蒙古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白莉《北匈奴西遷至中亞及繼續西遷之原因》(《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5期)、李英龍《簡論北匈奴西遷》(《河北工程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閔海霞、崔明德《略論北匈奴西遷的原因》(《齊魯學刊》2008年第3期)、吉晶玉《匈奴西遷與歐洲中世紀文學的多元融合》(《新疆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張繼淵《試論北匈奴西遷的原因》(《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9期)。
國內學者大多受歐洲普遍流行的匈奴、匈人同族論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的影響,并接受了這種觀點。然而,在西方史學界,這一觀點已受到挑戰,國內學者關注不多,僅有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文史》第33輯,中華書局,1990年)、《關于Huns族源的臆測》(《文史》第34輯,中華書局,1992年)。
三、匈奴族人口推測
關于匈奴族人口的數額,史無明確記載。胡君泊首先提出這個問題,胡先生在《匈奴源流考》中專設《匈奴之人口》一節(《西北研究》第8期,1933年2月)。文中僅抄錄了史書對兩漢、西晉時期有關匈奴正丁(控弦、精騎、黨眾)數額的記載,卻未作深入研究。但他所謂“然吾人觀冒頓時代用兵之數,則其人口可以相見矣”;“然欲求當時人口,亦帷從此可以推計耳”值得注意。此說首倡以匈奴用兵之數,推計其當時人口的設想。隨后,呂思勉《匈奴文化索隱》(《國學論衡》第5期上,1935年6月),其中《六匈奴人口》一節認為冒頓單于時期的總人口數量為300萬。
新中國成立后,史學界主要關注冒頓單于時期的總人口數量。馬長壽在《論匈奴部落國家的奴隸制》(《歷史研究》1954年第5期)一文中認為匈奴控弦的戰士約30萬之眾,而他們出兵的單位是以家族為標準的,即賈誼《新書》所謂“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以此推算極盛時代的匈奴總人口共有150萬。
改革開放后,史學界關于匈奴族人口的討論逐漸增多。
1983年,林幹發表《匈奴社會制度初探》(載于《匈奴史論文選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以公元前200年冒頓單于平城之圍時有精兵40萬,并依照賈誼的說法“五口而出介卒一人”,認為匈奴總人口大約為200萬。
劉淑英《我國古代匈奴族人口初探》(《人口與經濟》1993年第1期)認為冒頓單于時期匈奴人口大約為180~200萬,至多不會超過220萬。
袁祖亮《略論冒頓單于時期的匈奴人口》(《南都學壇》1998年第4期)首先肯定匈奴最盛時兵力為30萬,其次以中行說言匈奴之人眾在漢文帝時不過漢之一郡為根據,推算出漢文帝時人口最多的汝南郡和潁川郡,進而推測出冒頓單于時期的匈奴總人口應在130萬至140萬之間。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認為匈奴直到漢文帝時才由中行說將“計課其人眾畜物”的辦法傳入匈奴,并且冒頓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匈奴對漢軍作戰的兵力從未超過十幾萬,因此,冒頓之世有控弦之士30余萬的說法是不可信的。他估計匈奴的人口總數不過五六十萬,絕不會達到100萬。
王慶憲《匈奴人口的計算方法與其社會形制》(《黑龍江民族叢刊》2004年第3期)一文雖未明確給出一個匈奴人口的具體數字,但已對傳統的計算方法產生了質疑。他認為因為史書缺載,需要認真搜集文獻及考古資料,才有可能研究出匈奴人口數額的相對準確的結果。
尚新麗《西漢時期匈奴人口數量變化蠡測》(《人口與經濟》2006年第2期)一文對西漢時期匈奴人口的增減做了全面推測,認為冒頓單于時期匈奴人口在110萬~130萬之間;老上單于至軍臣單于中期,匈奴人口達到了鼎盛時期,由130萬增長到150萬以上;漢武帝到漢宣帝年間匈奴人口有60萬左右,不超過80萬;西漢末年恢復到西漢初年的110萬左右。
孫危、李丹《匈奴族人口研究的再思考》(《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一文結合考古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來說明冒頓前期匈奴民族的主體在構成上存在著差異,進而認為不能把匈奴族和匈奴人混為一談。雖未給出匈奴族人口的數額,但提出了另一種計算匈奴族人口的方法。
阿爾丁夫《關于匈奴戶口估計原則和冒頓單于當政前期匈奴族人口》(《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一文認為《史記》所載“縱精兵四十萬”是不準確,認為30萬較為合適,同時他又認為對匈奴人來說,不能以一家或一戶五口論,最多只能以四口論,最后推測匈奴人即匈奴國人口約為100萬出頭,其中匈奴族人口不過80萬出頭。
此外,日本學者內田吟風(《北亞細亞研究·匈奴篇》東京同朋舍,1975年)認為西漢時期匈奴人口約在30萬左右。袁延勝《東漢時期匈奴族的人口》(《南都學壇》2007年第1期)一文根據有關記載推算出東漢時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數是在漢和帝永元年間,是時南、北匈奴的人口總數約有140萬,同時又對南、北匈奴的民族分布作了考證。
在匈奴史研究中,探索其人口數額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百年來史學界多有論述,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史料的缺乏以及計算方法運用的差異等原因,各家學者對匈奴族總人口數額推測的結果差異很大,該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
四、關于匈奴單于庭的研究
匈奴單于庭是匈奴單于行政機構所在地。
秦末漢初,匈奴單于國盛極一時。據《史記·匈奴列傳》載,這時的匈奴“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云中”。《漢書·地理志》五原郡條載:“稒陽,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匈奴頭曼的單于庭即頭曼城(單于南庭)。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年版)認為頭曼城在陰山之中或其北麓,即今內蒙古固陽縣城以北一帶。
冒頓單于在位時,除了漠南的單于南庭,在漠北也設有王庭,即單于北庭。1941年,黃文弼發表《前漢匈奴單于建庭考》(《責善半月刊》第2卷第5期,1941年)對西漢時期匈奴單于北庭與南庭進行了一番考證,認為單于北庭在鄂爾渾河畔、杭愛山之東麓的哈拉和林西北70里。單于南庭在陰山附近,具體在何處未定論。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認為單于北庭在蹛林水(塔米爾河,即匈奴龍城)以東的安侯水(今鄂爾渾河)一帶,即今蒙古國碩柴達木湖附近。日本學者內田吟風《關于單于的稱號及匈奴單于庭的位置》(《東方學》第12卷,1956年)認為初期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至兒單于(前105—103年在位)以后移至外蒙古鄂爾渾河流域的哈拉和林附近。兩者觀點基本吻合。
林幹《匈奴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根據在今色愣格河上源、烏蘭巴托北70英里處的諾顏山發現的上百座匈奴墓葬,認為單于庭可能在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附近。龔蔭《匈奴單于疏證》(《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亦認同此說。
邱樹森《兩漢匈奴單于庭、龍庭今地考》(《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2期)一文,對兩漢時期的匈奴頭曼城、南北單于庭及龍城進行了考證,認為單于北庭在蒙古國前杭愛省哈爾和林北百里的一處廢墟中。
南匈奴單于庭是東漢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族分裂為南、北兩部時南匈奴呼韓邪單于的行政機構所在地。建武二十六年(50)正式設立南匈奴單于庭帳于五原西部塞80里處,隨后單于庭遷入云中郡,最后遷至西河郡的美稷縣。美稷縣即南匈奴單于庭駐地。關于南匈奴單于庭駐地的論文主要有史念海《鄂爾多斯高原東部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跡探索記》(載于《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認為,今內蒙古準格爾旗沙圪堵鎮納林村古城可能為漢代美稷故城,即南匈奴單于庭駐地。邱樹森《兩漢匈奴單于庭、龍庭今地考》(《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2期)承襲史念海的觀點。王興鋒《漢代美稷故城新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對于納林村古城為南匈奴單于庭駐地提出質疑,并通過文獻史料、實地調查和考古資料,認為內蒙古準格爾旗暖水鄉榆樹壕古城實為美稷縣故城,即南匈奴單于庭駐地。
陳峰《南匈奴附漢初期單于庭的設立與變遷及其歷史地理考察》(《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雖未指明南匈奴單于庭的具體位置,但是作者以歷史地理學的視角考察了南匈奴部落在公元48—50年間將單于庭先后設在五原塞地區、云中郡及西河美稷的過程。認為這樣的變化體現出空間發展過程和地域特色,同時也包含匈奴族與漢政府之間復雜的政治關系、地理格局以及兩族之間的和戰與相互影響。
五、關于匈奴族筑城問題的研究
《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同傳又載:“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鹽鐵論·備胡》載:“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匈奴族以畜牧為主業,兼營狩獵,過著往來遷徙不定的游牧生活,表明匈奴沒有必要修筑可以定居的城郭。但是另一方面,《史記·匈奴列傳》載“五月,大會蘢城”。前129年,衛青出塞擊匈奴,“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其明年春(元狩四年,前119)……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裴骃《集解》引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筑城居之。”《漢書·匈奴傳》記載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筑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后衛律穿井數百,伐木數千,但因有人言“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而作罷。《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與匈奴族有關的“城”,我們并不清楚其城池的形制、布局、結構等。此外,在今陜西靖邊縣城北的白城子村,考古工作者發現一座古代城址,此城為東晉時南匈奴貴族后裔赫連勃勃所建都城——統萬城。因此,關于匈奴族筑城問題的研究愈顯重要。
匈奴族筑城問題的研究最早是隨著俄國學者發掘匈奴墓葬的考古工作而展開的。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蒙古和外貝加爾地區發現和發掘的匈奴時代的城塞和村落遺址可確定近20處。蒙古國境內有十多處,分布于中央省、后杭愛省、布爾根省、肯特省、喬巴山省和東方省,1955年曾試掘幾處。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發現兩處,即伊沃爾加城址和都連村遺址。史學界通過百余年匈奴考古的探索,根據大量實物遺存的發現,逐漸認識到在匈奴族活動的區域筑是有定居的遺址和城郭的。
1956年周連寬發表《蘇聯南西伯利亞所發現的中國式宮殿遺址》(《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利用中國漢代考古和文獻,判斷蘇聯南西伯利亞地區阿巴坎市發現的宮殿遺址年代相當于王莽時期,是由中原工匠參與建造的,這是中國學者最早對匈奴筑城問題的綜合研究。1962年,林幹《匈奴城鎮和廟宇遺跡》一文根據蒙古學者策·道爾吉蘇榮著《北匈奴》一書中的《北匈奴的城鎮》一章及和·普爾賚著《匈奴三城的遺址》的發掘報告,對他們認為是匈奴的城鎮和廟宇遺跡做了介紹。文章對中國學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對于《史記》《漢書》提到的龍城、趙信城、范夫人城、頹當城和郅支城等,馮恩學著《俄國東西伯利亞及遠東考古》(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認為這些以人名而稱之城,反映出城的性質不是匈奴國家設立的行政機構的城,而帶有私城的性質。馬利清《匈奴的城塞及相關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一文論述了匈奴境內不斷發現的城塞和定居遺址,并提示我們著重關注匈奴社會存在的定居生活方式以及有關農業、手工業的經濟成分。
潘玲《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及相關匈奴考古問題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概括介紹了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的重要匈奴遺存——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的考古發現,在充分的科學依據基礎上,綜合運用國內外考古資料判斷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的主體年代在西漢中期至中晚期,并且分析當地以西漢中期為主體和以東漢前期為主體的兩個時期匈奴遺存的器物群的時代特征。
烏恩岳斯圖著《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匈奴時期》(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認為匈奴重要的行政中心龍城的規模和建筑是否與一般概念中的都城一樣,由高大城墻環繞的宏偉宮殿,是值得懷疑的。他推測所謂龍城很可能是由旃帳構成的聚居點。
1998年,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在陜西神木縣大保當鄉任家伙場村老米圪臺附近發掘一處城址,根據出土遺物判斷該城址興盛時間為東漢中晚期,其上限可能到西漢晚期。隨后出版了發掘報告,認為該城址可能是漢代上郡屬國治所龜茲縣城。(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神木大保當——漢代城址與墓葬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中國境內唯一一座兩漢時期具有匈奴族遺存的城址。王煒林《試論神木大保當發現的漢代城址》(載于《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2006年版)根據歷史地理方面的考證,按大保當與榆林的相對位置,認為該大保當城址很可能即是漢代所設的上郡屬國治龜茲縣。王興鋒《漢代上郡屬國都尉府駐地——龜茲縣故城新探》根據《漢書》《水經注》有關龜茲縣域范圍的記載,以及對昂拜淖爾古城的考古調查,否認大保當城址為漢代龜茲縣故城,推定漢代龜茲縣故城當在今內蒙古烏審旗北部的昂拜淖爾古城。
此外,日本學者對匈奴族筑城問題的研究也有關注,如內田吟風《古代游牧民族的土木建造技術—特別是以在トランスバイカリア發現的匈奴營壘遺址為中心》(《東洋史研究》11-2,1951年)、手冢隆義《關于匈奴的城郭》(《史苑》19-1,1955年6月)、江上波夫著《歐亞大陸古代北方文化》(全國書房、1948年)和《亞洲文化史研究·要說篇》(東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
六、結語
綜上所述,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表現如下:(1)研究內容廣泛,涉及地理名詞考證、城址考證、人口數量、行政區劃以及民族遷徙與分布等等;(2)某些觀點史學界已經達成共識,如關于匈奴活動區域的筑城問題。以上是筆者對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成果做了一個大體的回顧和總結,雖然成果豐富,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和薄弱環節,如缺乏整體系統的研究。今后隨著匈奴考古工作的深入,筆者認為,應繼續加強野外實地考察,采用GPS定位、測距儀等技術手段,取得可信的第一手資料。結合比較語言學等方法的同時,注重外文相關論著的翻譯,廣泛吸取國內外研究的最新成果,進一步提高匈奴族歷史地理的研究工作。
[責任編輯朱偉東賈馬燕]
Summary of Research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un Nationality
WANG Xing-feng
(SchoolofHistoryandPolitics,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The Hun Nationality belongs to nomadic people with a long history very active on the northern grasslands in China, having exerted much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course of history in Asia and Europe at that time. Ding Qian, a scholar in the late Qin Dynasty, was the first to star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un Nationality. Afterwards, its research has arous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mong scholars. Over a century, notice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about its research, ranging from verifying relevant names of places, town sites,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o its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like. Scholars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ir city fortific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un Nationality still needs strengthening, with the help of new discovery, techniques and ideas.
the Hun Nationality; historical geography; national geography; history of nationality
K28
A
1001-0300(2016)05-0075-09
2016-03-08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11&ZD097)階段性研究成果
王興鋒,男,陜西寶雞人,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教師,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邊疆歷史地理、北方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