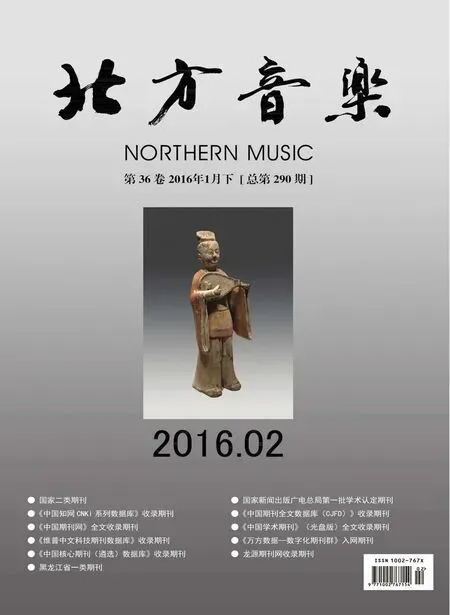從中外音樂教育的認知看中國未來音樂教育的發展方向
董 琳
(沈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遼寧 沈陽 110000)
?
從中外音樂教育的認知看中國未來音樂教育的發展方向
董 琳
(沈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遼寧 沈陽 110000)
【摘要】中外音樂教育狀況有著較大的區別,然而從歷史發源的角度來說,卻又殊途同歸。不同的教育形式和具體的教學形態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像。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由于家長與教師對音樂教育的認同和了解的不同,也造成了東西方音樂教育追求的區別化。國人的音樂教育更加傾向技術表達,而國外的則更重視感受互動。不同的關注點也使東西方青少年音樂學習的目的性有了差異。為了提升音樂教育的核心價值,則需要在音樂教育者的基礎教育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關鍵詞】音樂教育;教學法;中外音樂教育
音樂教育作為音樂傳承的必要途徑而受到人們的關注與重視。從拜火祭祀的勞動歌舞到傳唱廣泛的勞動號子,甚至東方宮廷音樂的演奏傳承和西方宗教音樂的教義傳授,早期的音樂流傳多以反復的模仿、指導、糾正為核心。在一代又一代的嘗試與進步中逐漸進化出更加科學有效的傳承辦法,這就是音樂教育的雛形。
而當代的音樂教育,淡化了階級統治的需求和信仰傳播的目的,脫身為藝術審美的具象體現。1930年,中國第一位音樂教師——沈心工先生在南洋公學附小開設“唱歌”課程;同年,由張之洞奏是學校章程,將“唱歌”列為學校必修課,標志著中國音樂教育走向正規化的開端。幾乎同一時代,西德著名音樂學家卡爾·奧爾夫開創“元素性音樂教育”體系,并在日后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六大音樂教學體系之一。
東西方當代音樂教育的萌芽時代,從教育的本質目標上,就產生了微妙而必然的區別。“唱歌”課程,是以結果為導向的課程,通過教師的示范、學生的模仿以及師生互動的糾正來完成歌曲的演唱,最終則以完成音樂審美體驗的目標。而奧爾夫教學法下的音樂教育模式,則更加強調參與,這是過程導向的直接需求。從兒童手、腦、律動的同時,主動與音樂互動,而完成音樂體驗審美與主動融合的目的。以此看來,隨著國人音樂教育的發展與教育程度的逐漸加深,對音樂審美的追求雖然并未改變,但其過程中相比于西方的音樂教育模式有著比較突出的功利心和目的性。而西方音樂教育中,沉浸體驗式的教育方式也更加暗合了諸如柯達伊等教學法中,對音樂修養理論與精神需求滿足的必要性。
當今社會的音樂教育,已從音樂學習目標的發端開始,產生了分立。中國的兒童比西方同年齡段的孩子更早的接觸到了音樂教育,在家長“技多不壓身”理念的指引下,越來越多的幼兒走進了音樂學習的領域,從唱歌到彈琴,再到舞蹈等等,這種“童子功”大多來源于家長的個人愛好與興趣。為了完成父母未完成的心愿,或單純家長之間“他家孩子在學某某某,如果我家孩子不學就要落后了!”的攀比心,在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學什么的兒童時代,孩子們就被強迫每天重復的練習,從而放棄了更多娛樂的時間。這也使原本并不枯燥的音樂學習在他們心中產生或多或少的抵觸情緒。而西方的家庭在對于孩子的音樂教育中卻更多展現了參與感的體驗。有個人音樂愛好的西方父母會在生活中安排孩子接觸音樂,讓他們在游戲中參與到父母的音樂生活中來,將音樂自然而然的接納為生活的組成部分。如果在孩子的成長歷程中表現出突出的音樂天分和興趣,家長會根據孩子的愛好而選擇相關的培養項目。使之成為孩子業余生活中的休閑娛樂,從而形成一種良性的音樂習慣。可以打個比方,當中國的孩子利用游戲的時間學習與練習音樂的時候,西方的孩子正在學習的閑暇之余體驗音樂帶給他們的快樂。
在這種教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學生,也有著明顯的區別。由于中國學生進入專業訓練較早,同年齡段的演奏技巧要高于西方的學生;而西方學生對音樂的感受力、理解力、領悟力則更強。中國學生的獨奏能力比較突出,而西方學生更加精于協奏配合。這與中國學生更加注重個人表現和榮譽有著很大的不同,西方學校在音樂教育過程中更加注重集體音樂行為的重要性,更多的音樂社團組織與表演機會,以及社會提供的實踐平臺都給了西方學生更多實現自我價值與審美感受的渠道。
由此,不同的音樂學習態度也催生出不同的社會現象。中國的家長,在先期的投入之后,大多會寄托于孩子的“一技之長”在升學中給予更多的助力。這便是國內“藝考”大軍的來源。排除真正向往專業音樂領域深造,并立志走入音樂領域行業的學生以外,更多的家長看重藝考生較低的分數線和文化課難度,而促使自己的孩子選擇藝術的學習方向。臨考前,則有大量沒有音樂基礎的考生臨時突擊音樂特長。這種應試教育下的音樂教育并不是良性的音樂教育,同樣這樣的教育教學中,也沒有任何審美感受與美的傳遞。反觀西方同年齡層的狀態,有音樂修養基礎的孩子會更加強化這項藝術技能,使之成為升學與日常學習生活的加分項。但這并不是強制性的,如果沒有相關特長的孩子,也可以根據個人的愛好選擇諸如體育社團或公益活動。這種“寬松”的機制,反而會促發有音樂特長的孩子進一步強化自己可以做的更好的領域,從而體驗更多的個人價值和成功感。這與我國藝考被動的學習形態有著巨大的反差,而中國式音樂教育的尷尬便如此產生了。
造成這一局面的誘因相對復雜但并不難以理解。當中國式音樂教育的最終目標始終定位在音樂審美感受的時候,實際的教學道路已經偏向越來越復雜的技巧練習與越來越繁瑣的演繹方式。單純的協作、審美、體驗,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弱化,從此與最高追求漸行漸遠。與此同時,這樣一代又一代的音樂學生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步入社會,成為新一代的音樂教育工作者,并延續著他們所受到的教育方式,將之傳遞給后續的學生們。如此一來,這種亞健康的音樂教育形態所生產出的音樂工作者便陷入了回環往復的循環中,而中國的音樂教育同樣陷入難以掙脫的怪圈。
改變這樣的局面,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治愈音樂教育者本身的造血機制,使新一代的音樂教育工作者以新的意識與視野將健康科學的音樂教育工作貫徹到后續的工作中來,由此也提高了針對音樂教育專業學生學習培養的流程難度。建設這種科學有效的教學機制就是當前音樂教育工作者的目標,使學生在擺脫單純追求音樂技巧的同時,提升其音樂修養與藝術品位。加大音樂協作的力度與含量,擺脫音樂孤獨,塑造音樂分享的大環境。在掌握教學方法的同時,掌控更多的教育手段,超越當前教育教學中單調的教授形態而引進更多的互動、參與、共享,從學習音樂到感受音樂,最終成為音樂享受。以此,才能讓“音樂使人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成為現實。
基金項目:本文是2015年度遼寧省社科聯與高校社科聯合作課題,名稱《全球化背景下音樂人才培養‘5C’模式研究》,編號:LSLGSLHL-136及2015年沈陽師范大學教學改革項目,名稱《全球化背景下音樂人才培養‘5C’模式研究》,編號:JG2015-YB085的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