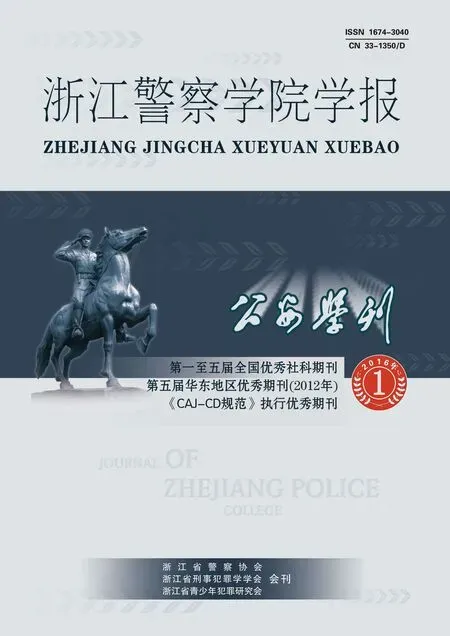城市新貧困群體與社會穩定研究綜述*
□劉昱彤(中國刑事警察學院,遼寧沈陽 110000)
?
城市新貧困群體與社會穩定研究綜述*
□劉昱彤
(中國刑事警察學院,遼寧沈陽110000)
摘要:既有研究中關于城市新貧困群體的分析都著眼于“轉型期”這一大背景,城市新貧困群體不僅應包括下崗失業群體,也應包括在城市化這一社會轉型進程中形成的城市社會的低收入的務工人員、失地農民等社會底層群體,其貧困特征是相對貧困。城市新貧困群體因貧富差距帶來的相對剝奪感,利益訴求的實現和表達渠道不暢,受到社會排斥而產生負面心理等特點是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因素,應引起全社會足夠的重視。
關鍵詞:轉型期;城市新貧困群體;社會穩定
*本文系公安部軟科學項目“創新社會治理體制視角下城市新貧困群體維穩模式研究”(2014LLY JXJXY011);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城鎮化進程中城市新貧困群體維穩問題研究”(L14BSH 011)階段性成果。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市逐漸形成了新的貧困群體并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城市中的社會矛盾和利益糾紛呈上升態勢,群體性特征明顯,城市居民相對缺乏安全感。中國城市社會、經濟的轉型賦予城市新貧困群體及社會穩定問題以新的時間與空間維度。在社會矛盾突出的轉型期,探討城市新貧困群體與社會穩定的問題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從微觀到宏觀:關于城市貧困問題研究視角的轉變
貧困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因此一直以來備受國內外不同專業領域學者的關注。人們普遍認為,對于貧困問題的系統研究始于英國經濟學家朗特里(Rowntree),1901年,他以英國約克鎮為調查樣本,完成了《貧困:城市生活研究》一書,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貧困一詞的內涵和外延也發生了變化,政府、社會以及學術界對貧困問題的關注焦點也不斷調整。從單一關注“缺乏”性表象因素到關注貧困者的能力、權利等內因因素,再到關注剝奪和社會排斥的外因因素,[1]期間經歷了一個從單一到多維,從個人、家庭等微觀視角到社會制度、結構等宏觀視角的轉變。
國外關于城市新貧困研究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研究內容主要是這種新型貧困的構成、特征及產生原因。許多社會學研究者認為:城市新貧困與“底層階級”(Underclass)有關,包括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方面,它被定義為工人階級以及在勞動年齡但卻不能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那些低收入者、無業者和失業者(Jordan and Redley,1994);[2]另一方面,它被用于指那些依靠福利制度而生活的窮人(Reed,1990)。[3]從其構成看,底層階級主要是無業或失業者、在業低收入者、貧困兒童、福利母親、非法移民和一些無家可歸者。在學術領域,早期有關貧困產生原因的解釋主要有個人學派、家庭學派兩個代表性學派。上世紀60年代,社會學家突破傳統的微觀解釋的框架,開始運用結構取向和文化取向的解釋范式對貧困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前者認為,貧困產生于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以及社會政治經濟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將貧困問題出現的原因歸結為社會。[4]在美國,大量研究認為,在業低收入是導致城市新貧困的主要原因。在歐洲,大量研究發現,高失業率是城市新貧困群體產生的主要原因。無論是美國的經濟高增長的在業低收入,還是歐洲國家的制度轉型失業,都是由一些城市化、工業化等宏觀的社會經濟新因素所導致。
國內關于貧困問題研究的焦點很長一段時間都集中在農村社會,正如美國學者卡恩所說:“中國官方的反貧困戰略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即貧困是一個農村地區的問題。”[5]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城市貧困人口主要是“三無人員”,即無勞動能力、無經濟來源、無法定贍養人,他們是傳統的民政救濟對象。由于這些人員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城市貧困問題并不突出。到20世紀末,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社會結構的變遷,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城市的貧困問題呈現日益突出的趨勢,于是中國對貧困問題的關注開始更多地轉向城市。世界銀行1992年出版的研究報告《中國減少貧困戰略》指出:198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例為28%,而城市貧困人口比例僅為2%,即400萬左右。到1995年,隨著我國扶貧政策實施,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例有了大幅度下降,用可比的調查方法和定義估計出的農村和城市的貧困發生率分別為12.4%和4.1%。[6]而到了“1999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比1995年上升了10%,貧困差距上升了36%,2005年城鎮人口貧困發生率為6%-8%,高于同期農村2.6%的水平。”[7]由此可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農村在貧困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時期的城市貧困問題卻呈現出上升趨勢。這不得不引起我們對城市貧困問題的重視。
綜上所述,不管是貧困的內涵還是對貧困問題研究的視角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如英國學者奧本海默(Oppenheim,1993)指出的“貧困本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它不具備確定性,并隨著時間和空間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而變化。”[8]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貧困問題不斷以新的形式和特征表現出來,致貧因素也變得多元復雜。相對于農村貧困問題和以“三無人員”為主的傳統城市貧困問題,當前中國城市的貧困問題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它發生于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的轉型期,是帶有時代烙印和社會結構特征的新問題,因此,對當前的城市貧困問題,我們應運用不同于農村貧困問題和傳統城市貧困問題的時空維度和研究視角,尤其要探尋我國社會結構轉型、經濟體制轉軌以及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因素對城市貧困問題的影響。
二、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界定與特征
(一)轉型期貧困: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界定及其形成。學術界關于城市貧困階層尚未有明確的定義,國外學者試圖從社會環境中探尋城市新貧困群體的致貧因素。Dahrendorf(1988)認為,城市新貧困群體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利益集團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9]Silverman和Yanowitch(2000)則從社會轉型與新貧困群體之間的關系來探討新貧困現象。[10]20世紀末以來,隨著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增長,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并嘗試探索其原因和主要人員結構。顧朝林(1997)在研究北京的社會空間結構時發現,盡管中國由于一個非常有限的社會福利制度,類似西方的“底層階級”社會群體并不能找到他們的“社會溫床”,但是新的城市貧困群體已經出現,主要是由于下崗、失業、低薪工作和流動人口的過快增長。[11]尹志剛(2002)在《北京城市居民貧困問題調查研究》的報告中提出“城市新貧困”的概念,認為新貧困群體的構成者主要是待崗職工和下崗后長期待業者,社會結構與經濟體制的轉型以及國有企業的改革等因素是新貧困出現的主要原因。[12]事實上,目前對于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界定,國內的學者們持不同觀點,主要爭議的問題是城市新貧困群體到底是專指城市非農業貧困人口還是包含了農村的流動人口。許多學者認同尹志剛對于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界定,也有學者認為城市貧困就是城市社會的貧困,因此城市新貧困群體應該包含城市社會的新成員。祝建華、顏桂珍(2007)認為,涌入城市的農村從業人員也屬于城市新貧困群體的成員。[13]林新聰(2006)認為,城鎮農民工是城市貧困的最大潛在群體。[14]吳克領(2013)認為,城市新型貧困是一種結構性貧困,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社會體制調整和改革的社會轉型期。這種新型貧困的出現,與單位制向社區制的轉變、住房市場化導致的城市居住空間階層化以及城市化導致的新貧困群體等因素密切相關,[15]即城市新型貧困形成于經濟體制改革時期,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不斷發展變化,城市新貧困群體既包括制度性失業、下崗工人也包括城市化所帶來的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相對于第一種觀點,后者的界定更為寬泛。但是兩種觀點在城市新貧困群體的形成原因方面卻達成了共識,即城市新貧困產生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兩個方面:一是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與國際市場細分;二是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及勞動力和資金向第三產業部門的轉化。[16]綜上所述,筆者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第一,不論哪一種界定方式,既有研究中關于城市新貧困的界定都是從宏觀視角入手,著眼于“轉型期”這一大的背景,因此,國內“城市新貧困”這一概念就是在這樣一種“轉型”的宏觀視角下產生的,可以被稱為“轉型期貧困”。[17]我國所經歷的“轉型”主要指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所謂經濟轉型是一個多維度、綜合性的概念和過程,它既包括了經濟體制的轉變,即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也包括了經濟結構的轉變,如經濟產業結構、市場結構、技術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等的轉變,具體表現為從傳統農業為主的農村經濟轉變為以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城鎮經濟。[18]而社會轉型是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表現為社會結構、運行機制以及價值觀念體系三個方面的轉換。
第二,對于前文總結的國內兩種學者關于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界定,筆者更傾向于范圍更為寬泛的后者。筆者認為,城市新貧困的“新”,主要是為了突出當前的城市貧困同傳統貧困之間的差異,因此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界定主要依據兩個標準:一是生活空間,即是否生活在城市、從事非農行業;二是時間背景,即是否產生于城市社會的這種“轉型期”。鑒于此,城市新貧困群體不僅僅包括20世紀末形成的缺乏再就業能力的下崗職工群體,也應包括在城市化這一社會轉型進程中形成的城市社會的低收入務工人員、失地的農民等社會底層群體。他們都生活在城市且從事第二、三產業,具有突出的社會經濟制度變遷和轉型的特征,屬于“轉型期”的城市新貧困群體。
第三,相比之下,前一種對于城市新貧困群體的界定范圍比較狹窄,這種局限性也是由“新城市貧困群體”這一概念產生的時間背景所決定的。城市新貧困群體同貧困的概念一樣,不論是其內涵還是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視角,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雖然“城市新貧困群體”這一概念在提出時并不包含城市底層的新移民群體,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社會結構轉型為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又增添了新的內容。
(二)相對貧困:我國城市新貧困群體的性質特征。貧困可以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朗特里(Rowntree,1901)在對貧困的研究中指出,絕對貧困就是收入不足以承擔維持基本生理需要的各種必需品。阿馬蒂亞·森(2001)認為,絕對貧困是由于消費權利組合不足以維持人基本生存的狀態。[19]而相對貧困是指收入可以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卻不能維持他們從屬社會所認可的最低生活標準。正如Townsend(1979)所指出:“他們(相對貧困家庭或者個人)擁有的資源嚴重低于社會一般家庭或個人的擁有量以至于他們沒有正常的社會生活方式,無法遵循社會風俗,不能參與正常的社會活動。”[20]池振合、楊宜勇(2013)通過對北京市城鎮住戶調查數據的分析得出結論:城市的低收入群體實際上就是相對貧困,收入水平低而導致社會認可的基本需要(如住房、教育、醫療等)得不到滿足是低收入群體所具有的本質特征。[21]謝呂元、宋峰(2014)認為,我國城市的新貧困的性質由收入貧困向機會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轉化。[22]低收入群體普遍面臨著生活質量低的問題。趙倫(2014)將我國目前相對貧困的實質內核歸納為三大類:一是生存貧困,收入與資源的缺乏,影響到維持健康的基本生活;二是權益貧困,能力與權利的缺乏,影響到獲得合理發展的公平機會;三是幸福貧困,人文知識與文明生活方式的缺乏,影響到人的人格尊嚴和內在幸福。[23]
筆者認為,當前我國城市新貧困的性質屬于一種相對貧困,這一群體普遍可以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卻面臨著生活質量低下的問題。從就業——收入的角度來說,城市新貧困群體人員主要由城市下崗工人、農民工、失地農民三大部分組成。從人員結構上來看,他們缺乏文化知識,下崗、失地后再就業能力差,缺乏謀生技能,與市場所需求的人員標準相差甚遠,因此再就業、穩定就業的幾率低,只能謀得一些技術含量低、報酬少的臨時性工作,或者成為流動小商販,盈利微薄,收入不穩定;從消費——支出的角度來說,城市新貧困群體的消費能力較低,這一群體家庭支出的主要內容除了衣、食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外,還包括住房、教育、醫療等必須費用,通常情況下子女教育經費和家人醫療經費就會使得許多家庭入不敷出,而娛樂等主動性消費幾乎沒有,因此可以說,城市新貧困群體的消費以被動消費為主;從權利——機會的角度來說,城市新貧困群體處于社會底層,不僅僅在經濟上是弱勢群體,在社會資源、流動機會、福利政策、利益表達等權利獲得方面也處于不利位置。
三、城市新貧困群體與社會穩定相關性研究
(一)城市新貧困群體對社會穩定具有潛在威脅。伴隨著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深入,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進入多發期,出現了城市貧困程度加深、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成為了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和諧因素和安全隱患。各國學術界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在國外,關于城市新貧困與社會穩定的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如威爾遜(2007)描述了在城市化迅速發展時期的美國,生活在最繁華都市中“真正的窮人”的生存狀況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城市犯罪和治安混亂現象。[24]國內學者則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城市新貧困群體與城市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指出了這一大量增長的新群體已經給城市社會的穩定帶來的威脅。我國城市“轉型期貧困”問題產生于轉型的特殊時期,有著貧困人口數量龐大、增長迅速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城市社會貧困群體數量快速增長。2001年,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據,全國共有1400萬的城市貧困人口,其中貧困職工約1000萬。2011年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顯示,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總數為5000萬左右,并且這一數字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十年的時間里,城市貧困人口增長了超3.5倍。陸學藝(2004)在研究中指出,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城市中新貧困群體的總量持續上升,已成為亟需面對的主要社會問題之一。[25]大量增長的城市新貧困群體一方面對社會福利、救助、疏導、支持等制度和體系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對社會的和諧、穩定狀態形成了潛在的威脅。尹志剛(2002)認為,城市新貧困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如果不能及時采取有效手段對其進行控制,必然對社會穩定以及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產生消極影響。[26]龔曉寬(2002)深入分析了西部地區城市貧困引發的社會矛盾并提出相應對策。[27]李建和(2001)認為,城市犯罪既是城市社會不穩定的成因也是城市社會不穩定的表現形式。[28]除此之外,國內還有大量定量研究指出了城市貧困與城市犯罪之間的相關性。由城市新貧困群體所引發的社會穩定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二)城市新貧困群體不穩定因素分析。關于城市新貧困群體具有哪些引發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國內既有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貧富差距帶來的相對剝奪感。趙倫(2014)認為,隨著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社會歸因主導下的相對貧困認知引起貧困群體心態的集體失衡,降低了人們對社會公正水平的正面性評價,可能導致嚴重的社會不滿和群體對立。[29]廉思(2014)認為,參照經濟社會地位較高的社會群體,經濟社會地位較低的群體占有的社會資源極為有限,兩個群體之間在權利資源占有上的差異容易引起群體間的對立情緒,尤其是地位較低社會群體的不滿足感和不公平感,這種不滿情緒容易引起群體甚至不同階層之間的沖突,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例如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將遷入地居民作為自己的參照群體,他們的生活滿意程度,是以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為參照,如果農民工對群體經濟、社會保障等的利益訴求長期得不到回應,他們便會通過抗議甚至是更為激烈的方式表達訴求,極易引發治安事件。[30]華雯文(2013)認為,隨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階層結構及利益格局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種轉型和變化引起不同群體心理的變化,導致人們產生對貧富分化和分配不公的不滿,增強了人們尤其是弱勢群體心理的不平衡感和低落情緒。而這種不平衡感和低落情緒正是滋生群體性事件的心理溫床。[31]
二是城市新貧困群體利益訴求的實現和表達渠道不暢。鄭濤(2013)詳細研究和分析了烏坎村事件,他認為,失地農民的利益訴求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表達機制是導致失地農民經常性選擇非正常渠道表達利益訴求的最直接原因,失地農民的這些極端或者違法行為來自于對相關機構無法及時做出有效回應而產生的壓力。[32]趙光偉(2010)認為,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導致城市農民工犯罪、群體性事件等治安問題的最主要原因[33]。
三是城市新貧困群體由于受到社會排斥而產生負面心理。林新聰(2006)分析了城市貧困者心理問題對社會穩定的影響。[34]周紅(2010)分析了農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社群心理邊緣化趨勢會對這一群體的行為產生消極的影響,繼而產生嚴重不良的社會后果。這種群體心理趨勢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得到有效疏導和控制。[35]
縱觀既有文獻研究,筆者發現,國內學者通常都是針對某一特定群體(如下崗職工、農民工、失地農民等)來分析其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原因;而在原因分析上,學者們往往都是從某一特定角度(如貧富差距、利益表達渠道、社會融入等)進行分析,缺乏層次性、系統性和完整性。由此可見,如果能對城市新貧困群體及其特征進行整體的總結和描述,并在此基礎上全面、深入剖析這一群體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類型和原因,將極大地有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參考文獻:
[1]黨春艷.轉型期我國城市貧困問題研究[D].上海:華中師范大學,2013.
[2]Jordan,B.and Redley,M.Polarisation, under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 [J].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995(8).
[3]Room,G.New povert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M].London: Macmillan.1990.
[4]周怡.貧困研究:結構解釋與文化解釋的對壘[J].社會學研究,2002(3).
[5]邵琨.我國城市新貧困問題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2.
[6]王麗艷.中國轉型期城鎮貧困與就業問題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08.
[7]楊敏.以積極創新的政策理路應對21世紀貧困挑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貧困的結構性現象[J].教學與研究,2009(6).
[8]Oppenheim,C.Poverty: the facts [M].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1993.
[9]Dahrendorf,R.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an essay on the politics of liberty [M].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88.
[10]Silverman and Yanowitch.New Rich, New Poor, New Russia: Winners and Losers on the Russian Road to Capitalism [M].New York: Sharp, 2000.
[11]顧朝林,C·克斯特洛德.北京社會極化與空間分異研究[J].地理學報,1997(5).
[12][26]尹志剛等.北京城市貧困人口制品原因分析[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4).
[13]祝建華,顏桂珍.我國城市新貧困群體的就業特征分析[J].中州學刊,2007(3).
[14][34]林新聰.城市貧困人口心理和社會穩定[J].社會心理科學,2006(2).
[15]吳克領.社會轉型與城市新型貧困的空間聚集化[J].學海,2013(4).
[16]唐鈞.確定中國城鎮貧困線方法的探討[J].社會學研究,1997(2).
[17]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82.
[18]李實,趙人偉.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J].經濟研究,1999(4).
[19]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0]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21]池振合,楊宜勇.城鎮低收入群體規模及其變動趨勢研究——基于北京市城鎮住戶調查數據[J].人口與經濟,2013(2).
[22]謝呂元,宋峰.我國城市新貧困問題的社會危害及其解決對策研究[J].科技創業月刊,2014(8).
[23][29]趙倫.相對貧困從個體歸因到社會剝奪[J].商業時代,2014(18).
[24](美)威爾遜.真正的窮人[M].成伯清,鮑磊,張戌凡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5]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流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7]龔曉寬.中國西部地區城市貧困與社會穩定問題探析[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
[28]李健和.城市犯罪與社會穩定的治安管理機制[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3(3).
[30]廉思.城市新移民群體的主要利益訴求與社會融入[J].探索與爭鳴,2014(1).
[31]華雯文.社會保障:規避群體性事件的有效機制[D].長春:吉林大學,2013.
[32]鄭濤.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利益訴求問題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
[33]趙光偉.農民工問題與社會穩定相關性研究[J].人民論壇,2010(17).
[35]周紅.農民工子女城市融入與社會穩定研究——基于社群心理邊緣化趨勢的分析[J].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10(1).
(責任編輯:常洵)
作者簡介:劉昱彤,中國刑事警察學院思政部副教授,社會學博士。
收稿日期:2016-01-05
中圖分類號:D9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040(2016)01-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