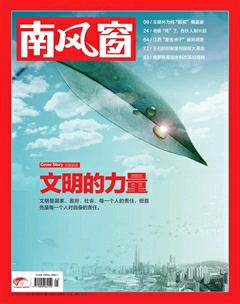中國社會及其未來
編者按: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西方金融危機引發種種問題,中國和世界的精英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樣的發展模式才是好的,中國應該尋找什么樣的道路。
近二十年來,關于如何認識中國當前社會狀況,如何分析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特點及其面臨的挑戰,國際和國內學術思想界有持續的研討和辯論。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和中國改革的持續推進,這些討論也在發生變化和拓展。
此前,薩米爾·阿明、汪暉、溫鐵軍、劉健芝、戴錦華等學者的論述、合作與對話,構成了相關討論的重要部分。今年10月中旬,由劉健芝、戴錦華組織和主持,阿明、汪暉、溫鐵軍與莫斯科國立大學的亞歷山大·布格林教授,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新的討論。我們特意把討論內容編發出來,以饗讀者。在討論中,四位學者先分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然后進行了一些更深入地探討。
當然,這一場討論并不代表本刊立場,我們只希望能把盡可能多的嚴肅討論呈現給讀者。我們也歡迎持不同觀點者聯系我們,為讀者提供更多的視角和更廣闊的視野。本期刊發的是下篇。
中國是一個處于漫長過渡期的國家
溫鐵軍:我不是政治領域的專家,只研究經濟問題。我將為你們提供例子,由你們來作分析。
當我們討論這一輪經濟危機時,大部分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德國等都陷入了危機。人們把中國作為例子,說中國仍然保持著7%的經濟增速,看起來這是全球唯一一個還保持著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國家。
而今天中國同樣面臨著諸多內外挑戰。中國如何面對全球危機的挑戰,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是跟隨其他發達國家做同樣的事情,還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它采取了不同的路徑?中國確實做了一些與發達國家不同的事情。
中國有著類似其他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剩的問題。1998年,當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出口需求減少,生產過剩的問題成為中國當時的主要挑戰。
中國如何處置過剩的工業產能?如果中國追隨發達國家的腳步,那么這會成為大麻煩。當你討論方向問題時,要意識到我們有巨大的工業產能需要轉移,轉移到哪兒?
當歐洲面臨同樣的困境時,二戰爆發了。而中國首先采用區域再平衡的策略來轉移產能。向經濟不發達地區投資的總量達到1.2萬億元,將其用于西部大開發。
中國采取的第二個策略是把另外1.2萬億元投向農村建設,使99%的農村都能通水通電通路,用上電話甚至互聯網。如果說中國只是一個市場社會,那么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能獲得回報嗎?不可能。
如果做一個比較研究,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國家能像中國對農村進行如此大規模投資。中國農民受益于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有一半的投資投向了當地醫院和學校,為當地農民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
中國有9億農民,98%的農業人口能夠被這一社會保障體系所覆蓋。這在其他任何國家,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都不可能做到。
這一農村醫療體系是建立在村集體的基礎上的。國家付80%,村集體只付20%,這樣就幾乎覆蓋了整個農村人口。而今天,連城市的社會保障體制也試圖向農村學習如何覆蓋全部的城市人口。
第二點同樣重要,中國可以改變經濟規則。當你遭遇危機,甚至歐洲也依然遵守著現有的經濟規則,但中國試著改變它。2013年美國結束量化寬松政策,幾乎所有“金磚國家”都陷入了危機,只有中國逃脫了。因為我們依然保留著金融主權。
美國可以通過印鈔票來增加貨幣泡沫,而中國政府做了類似的事情。對此我不打算評論,但這就是你用自己的泡沫來對抗別人的泡沫。這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這件事的國家。
阿明:我不僅同意你,我也從你那里學到很多,在我的文章里也用了很多你所提供的數據資料。在我看來,中國是一個處于漫長過渡期的國家,有著多種可能性。
對于中國的未來,有些人設想中國可以維持經濟發展,但同時朝向一種更為平等的模式,不是GDP,而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他們設想,人類將進入一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世界的中心將從大西洋轉向東亞,而中國則將是新的世界強國。
這恐怕也是一些普通中國人的愿望。我們有漫長的歷史,我們曾經長時間居于領先位置,為什么我們不能重溫舊夢呢?
但在我看來,如果中國想通過資本主義方式發展而達至成功,那是不可能做到的。這與我們喜不喜歡這條道路沒關系。在我看來,它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為全球體系既存的資本統治力量將不允許中國走向領導位置。
市場不是貓,而是老虎,必須非常小心
亞歷山大·布格林:我同意薩米爾所說的。但我想強調的是,如果中國喪失了它的某些社會主義要素,它很可能面臨增長率下降甚至是危機。這就是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所發生的事情。
中國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在發展中國家的不尋常結合。中國確實保留了一些社會主義的要素,但這并不是中國獨有的。中國現在是我們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榜樣。這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尤其是對不發達國家來說。
思考在這個過程中保留了哪些性質的社會關系,我認為這很重要。
在經濟領域,除了市場,還有國家的介入,強有力的工業政策,對高新技術的支持,針對不同地區的不同稅收政策,等等。有些國家也還存在這樣的模式,比如在斯堪的納維亞。
第二點,非常重要的是對基礎設施、高新技術、教育、醫療的社會投資。這是相當大的成就。如果這一路徑被放棄了,你們的經濟發展會遭遇挫折。這是某些領域國有資產的作用。
問題在于國有資產常常不止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好處,也給官僚和大資本帶來好處。我認為在許多方面,中國的國有資產仍然服務于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的共同利益。
人們擁有的真正的社會資產(是否屬于國家無關緊要,它可以屬于農業集體、市政、NGO、或者互聯網、文化、教育中的每個人每樣事物)越多,社會主義的要素越多。衡量的尺度是資產的社會性本質,而不是它的形式。
有時候,發展的過程需要經歷曲折,要使用一些非社會主義的手段。當列寧提到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他說是的,這并非我們的理想。我們需要學會如何建立市場,需要使用它,但市場是危險的。
市場不是貓,而是老虎,市場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一種社會關系的體系,所以必須非常小心。可以認為中國經濟的建設不能離開資本,如果能夠掌控工具,把老虎關在籠子里,那沒問題。但如果老虎跑出籠子,就是另一種情形了。
資本本身可以成為統治性的力量,背叛和破壞某些維持增長的要素。私有資本的目的不是中國的發展,而是更徹底的跨國合作和市場開放。
阿明:可以區分兩種發展模式。
第一種,中國保持年平均增長率,但與此相伴的是不平等的區分。少數人享用快得多的收入增長,而多數人得到慢一些的增長,但仍然是正增長。
這種并非平民化、卻減少了貧困的模式,我并不接受,但似乎對許多人來說是可以接受的不平等增長模式,因為沒有人失去什么。
第二種模式,增長的大部分好處被少數人占有,而多數人面臨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這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自1975年以來的模式。這也一直是不發達國家的模式,自19世紀以來就是如此。這是一種沒有正當性,不可接受的模式,也是不發達國家始終動蕩的原因。
汪暉: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就針對那些地方的國家行為而言,我認為有兩個進程在同時發生。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對貧困地區的巨額投資。雖然存有爭議,但是我認為其中積極的方面是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例如為貧困農民建設基本住宅,在南疆,80%的農民搬進了由政府出資建設的新房。
另一方面也是社會主義遺產,即沿海發達地區對邊疆的對口支援建設。沿海城市發展模式移植到新疆,雖然面臨著一些問題,但許多貧困農民仍然認為這是一種好的方式。
還有,很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有了“十三五”規劃,這種五年計劃模式在市場化改革中依然被延續下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一體制將會繼續。沒有這一體制的保證,你很難想象中央政府仍能保留針對老少邊窮地區的實質性政策。
(本文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袁先欣、林彥翻譯整理,未經發言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