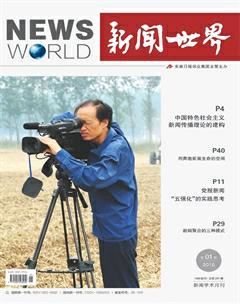論網絡社會輿論場的屬性與特征
劉榮
【摘 要】“兩個輿論場”現象產生于大眾傳媒主導的傳統媒介生態之下。在社會轉型和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共同作用下,網絡社會初步成型。“兩個輿論場”被吸收、融合,形成主體多元、場域統一的網絡社會輿論場。社會結構變化帶來的多元力量在新輿論場中意圖通過改變公眾的心理場,即物理事實、社會事實和概念事實來爭奪話語權,以占據社會資源分配的有利位置。
【關鍵詞】網絡社會;輿論場;多元化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社會化媒體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國社會輿論的主要載體以及輿情觀測的主要窗口。相對傳統傳播條件下的輿論場,當前中國的網絡輿論場的結構、作用方式以及對社會的功效都表現出了巨大的差異性。
一、傳統媒介生態下的輿論和輿論場
(一)“兩個輿論場”的形成
在國內,“輿論場”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最早由新華社原總編輯南振中在1998年新華社的一次工作會上提出,他結合馬克思“表達社會輿論”的觀點和當時的新聞實踐,提出“兩個輿論場”的觀點:即老百姓的“口頭輿論場”和官方主流媒體營造的輿論場的內容——“生活冷暖”和“宏大敘事”——相脫節現實。
“場”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發現的電磁場,后經考夫卡和勒溫將之引人心理學研究,最后由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集成,形成了社會科學領域的“場域”理論:“場是行為者和他們社會地位所在的空間,場中的行為者的地位是由他們在場中的角色、他們的慣習和他們的資本(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資本)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布爾迪厄提出社會分化導致林林總總的“場”的存在:“法律場”、“文學場”、“電視場”、“新聞場”等等。將當前中國語境中的“輿論場”和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相對照,可以發現后者是前者的理論來源。有國內學者將“輿論場”和布爾迪厄“場”的多樣化思想結合,并進一步發揮,提出當前中國不僅存在著“兩個輿論場”,還可以更多,比如“三個輿論場”、“四大輿論場”的觀點。
(二)輿論的屬性:“姓公”還是“姓私”?
所謂“姓公”還是“姓私”,指輿論是“公眾一致的意見”,還是“某些特定的人或群體的意見”,這需要結合不同歷史和現實條件來分析。
從中國當前正在經歷社會轉型來看,社會結構和利益主體呈現多元化的特征,而輿論和利益取向緊密相關,將輿論看作是“特定群體”而非“公眾一致”或“多數人”意見,符合當前中國的社會實踐。因此,本文采用《不列顛百科全書》對輿論詞條的定義:“輿論是社會中相當數量的人對于一個特定話題所表達的個人觀點、態度和信念的集合體。”
本來是特定群體的意見的“輿論”為什么會表現為“公眾一致的意見”?這正是主控“輿論”的特定群體刻意追求的結果。這種結果的產生和卡爾·曼海姆所說的大眾社會( Mass Society)的特質密不可分。大眾社會是資本的市場邏輯和權力的政治邏輯之下、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作用形成的群眾性的社會。其成員呈一盤散沙的原子狀分布,互相孤立無援,他們的精神生活被大眾文化全面占領,其意見被大眾媒介所“代表”而成為“公共輿論”。他們的真實意見則成為暗流在地下涌動——洶涌澎湃卻不見天日。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興盛之前,傳統媒體一統天下的狀態,實質也是大眾社會在媒介生態圈的投射,而所謂“兩個輿論場”現象正是傳統媒介生態下輿論特質的外顯。
二、網絡社會輿論場的特征及其形成
(一)網絡社會是現實結構和虛擬空間的結合
“兩個輿論場”的形成和大眾傳媒主導傳統媒介生態緊密結合,這種媒介生態結構隨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興盛而日趨衰落。特別是當公眾借助互聯網Web2.0技術和各種網絡移動終端重新整合起來——完成麥克盧漢的“再部落化”時,他們不再是大眾社會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一種全新的社會結構——網絡社會也因此成型。這正是馬克思在分析社會的本質時提出的“社會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論斷的體現。本文使用“網絡社會輿論場”的表達方式,正是為了強調互聯網不是僅僅形成了一種新的傳播條件,它作為一種技術環境,和幾乎同時到來的中國社會轉型一起,改變了社會的結構方式,新的輿論場正是在新的社會結構下起作用,發揮其功效。
仔細梳理當前漢語語境中“網絡社會”概念,可以發現其內涵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作為現實空間中一種新社會結構形態的“網絡社會”。即社會個體之間借助新的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互動而形成的新的、相對穩定的關系體系。這個意義上的網絡社會是一種現實的社會,是一種世界普遍交往的社會結構,在英文中稱之為Network society。另外一層含義的網絡社會是指基于互聯網架構的、模擬現實社會的計算機網絡虛擬空間或“電子空間”,在英文中稱之為Cyber society(賽博社會),當前漢語語境中的“網絡社會”更多的是后一含義指向。兩個“網絡社會”雖然概念不同,但存在著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現代社會是以互聯網為主的信息網絡與實體網絡高度整合的結果,也是虛擬‘網絡社會和現實‘網絡社會高度整合的結果”。
(二)社會轉型是新輿論場形成的社會條件
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突出表現為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原先利益平均化、主體單一的社會結構被解構。其中既包括原有的利益主體分化:如下崗工人、進城務工人員、承包經營的農民、國企高級主管等從原先的工農階層中分化出來。也有新利益主體的出現:如自由職業者、金融食利者、私營企業主等。在對外開放、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還包括來華從事經濟活動的外籍人士、NCO組織以及外資機構的中方雇員等。社會的縱向流動和橫向流動成為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常態。在網絡社會條件下,這些多樣化的利益主體借助新媒體互動,明晰了內部關系和外部邊界,形成了新的穩定的社會集團或階層。雖然在不同社會集團、階層之間廣泛存在著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也會因而出現“輿論一致”的情境。但是經濟利益本身就是區分人群、構成階級或階層的最基本因素,經濟利益沖突是迄今為止任何形態社會的常態。網絡社會的利益沖突必然通過互聯網——當前最主要的輿論場的角力顯現出來。
(三)互聯網發展是新輿論場形成的技術條件
在傳統的大眾傳媒主導的媒介生態中(或者說在大眾社會中),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群體和階層,但是在主導社會的精英集團(利用大眾傳媒)的控制之下,利益本不一致的各社會主體被以“公眾”的面目掩蓋,其紛繁的聲音被“代表”、過濾或重組,成為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輿論一致”。網絡社會的到來使公眾擺脫了大眾社會中“烏合之眾”的狀態。互聯網特別是Web2.0時代的互聯網強大的交互作用和社會傳播功能,使社會個體“人人擁有麥克風”,從原先單純的內容接受者的被動地位中解放出來,躋身內容制造者和傳播者之列。在互聯網的傳播條件下,社會轉型期的上述多元利益主體得以在虛擬空間重新集合、排序、維系和強化對所屬群體的歸屬感,階層分化不僅在事實上確立,在社會認知上也逐漸明晰。
因此,社會轉型帶來的利益分化使網絡社會的成員有意愿在輿論場發言,而互聯網帶來的傳播條件則使他們有能力在輿論場發言。這使得傳統傳播生態下線性的科層制社會組織結構向交叉的網絡型組織結構轉變,社會公眾的地位得到極大提升,成為新的輿論場中的話語主體和新的傳播秩序中的權力主體,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決策過程,政治和經濟的精英集團(通過大眾傳媒)壟斷輿論場的局面被打破。
(四)多元統一是新輿論場的主要特征
網絡輿論場的傳播主體除了社會轉型后形成的眾多利益主體之外,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也迫使傳統媒體紛紛進行互聯網轉型,開辦官方網站或社交網絡平臺(如微博、微信等),將傳播業務延伸到互聯網并與受眾積極互動。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在傳統傳播條件下不能合法存在的傳播主體,如定性為邪教的非法組織、境內外反現行體制的經濟和政治勢力,也利用互聯網的開放性(大多以隱蔽的方式)進入到中國互聯網的輿論場博弈。因此,在中國網民總數接近總人口半數,互聯網普及率接近50%、多元利益主體以及傳統媒體充分融人互聯網傳播、市場化和全球化形成的境內外多種勢力的不同聲音均在互聯網上得以體現的現實條件下,認為網絡輿論場已經充分融合傳統的大眾傳媒和民間傳播的“兩個輿論場”,形成了因子多元、場域和形式統一的總輿論場是符合邏輯和當前實踐的。
三、網絡輿論場是多元和霸權的統一
葛蘭西將上層建筑分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國家)兩個部分,“市民社會”是形成文化霸權的社會基礎。當前互聯網充分參與了包括政黨、宗教、學校、文化群體和新聞媒介在內的市民社會的構建,市民社會已經和網絡社會充分融合。同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輿論場的霸權不可能再用國家強力手段去爭奪,政府只能依靠(網絡)市民社會、通過提高社會治理的績效和知覺運用傳播規律來取得,這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工程,也是一場“陣地戰”。
另外,正如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拉克勞和墨菲對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提出的批評,不應該以階級斗爭為唯一主題而否認其它主題的存在,如目前全球的網絡社會共同關注的環保,女權、和平、反種族歧視甚至同性戀權益等問題。這和布爾迪厄的多場域的觀點發生共鳴,有助于我們認識人類發展主題的多樣性。但是不能由此否認網絡社會輿論場上經濟利益的核心地位,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輿論場是唯一的主場,其他的場域的基調由主場決定,并或多或少跟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相聯系。否則,無法對網絡社會輿論場的結構、決定力量,以及它和整個宏觀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認識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