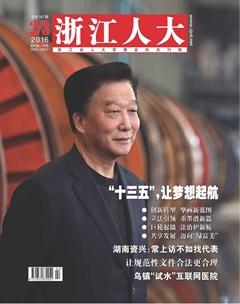“總比什么好”不能成為“擋箭牌”
曹林
北京近來(lái)似乎一直為單雙號(hào)限行做輿論準(zhǔn)備,又是大談單雙號(hào)限行帶來(lái)的種種好處,又是擺出如果不限行的話會(huì)有多少問(wèn)題,各種放風(fēng)試探。很顯然,政府注意到了輿論對(duì)單雙號(hào)限行的反對(duì)聲,北京一位官員近來(lái)苦口婆心地解釋:限號(hào)是討罵不討好的事兒,但不得已而為之,總比堵死好一些,希望大家理解。
官員還知道老百姓在罵,挺好——相比那種對(duì)輿論批評(píng)視而不見、自以為是的粗暴與傲慢,苦口婆心地解釋是一種進(jìn)步。但那句讓人熟悉的“總比堵死好一些”實(shí)在讓人不舒服,日常中我們聽到多少部門用過(guò)這樣的邏輯。
輿論批評(píng)大拆大建,會(huì)說(shuō),總比原地踏步好一些;公眾批評(píng)攝像頭侵犯隱私,會(huì)說(shuō),總比光天化日下被偷被搶好一些;公眾批評(píng)一刀切地禁止學(xué)生春游,會(huì)說(shuō),總比萬(wàn)一出事故好一些。“總比什么好”的邏輯似乎已成官方受到質(zhì)疑時(shí)萬(wàn)能的防衛(wèi)盾牌。
這邏輯貌似替公眾考慮,其實(shí)不講理。其一,“堵死”是一個(gè)偽問(wèn)題,是一個(gè)最壞的結(jié)果,起碼目前還沒(méi)有出現(xiàn)“堵死”這種極端狀態(tài),不能為了讓公眾接受,而把問(wèn)題推到“要么放任要么堵死”這兩個(gè)極端狀態(tài),用“堵死”這個(gè)極端狀態(tài)去嚇公眾。

其二,治理交通問(wèn)題有很多選項(xiàng),可以加大公共交通投入,可以進(jìn)一步完善大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可以在城市道路規(guī)劃上進(jìn)行挖潛,可以討論擁堵費(fèi)、提高停車費(fèi)等方式——單雙號(hào)限行的必要性在哪里?在其他方面是不是窮盡努力了?是不是有其他選項(xiàng)?這是需要論證的,而不是當(dāng)成惟一選擇,逼著市民做非此即彼的兩難選擇:要么堵死,要么接受單雙號(hào)限行。
其三,誰(shuí)才是公共利益的判斷者呢?到底是“寧愿忍受限行的不便,也不愿堵在路上”,還是“寧愿堵著慢一點(diǎn),也不想被單雙號(hào)限行”,這個(gè)選擇不能由政府專斷地替公眾決策了,然后強(qiáng)加給公眾一個(gè)“政府自以為對(duì)公眾有利”的決策,而需要經(jīng)過(guò)公眾討論和民主決策的程序。民眾的偏好,需要以民主方式去實(shí)現(xiàn)。
事實(shí)上,如此不“反躬自省,問(wèn)題于外”的粗放式行政管理思維在許多領(lǐng)域都普遍存在,管理部門永遠(yuǎn)是沒(méi)問(wèn)題的,問(wèn)題永遠(yuǎn)出在他人身上。這顯然與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要求不符,與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的改革精神不符。一個(gè)簡(jiǎn)單的邏輯是:治理交通是為了便民出行,依靠“限民出行”來(lái)緩解交通,收獲的只能是一個(gè)“零和”效益。
因此,政府開展的各項(xiàng)改革,應(yīng)該要多一些“帕累托改進(jìn)”,以此增進(jìn)社會(huì)福祉,而不是靠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lái)填補(bǔ)和壯大所謂的改革成果,這極為可能陷入勞民傷財(cái)?shù)膼盒匝h(huán)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