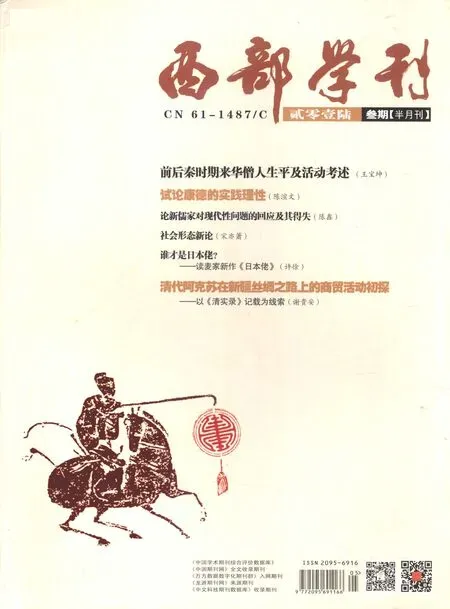《中庸》的“誠”思想
張 悅
《中庸》的“誠”思想
張 悅
本文以《中庸》為中心,探究儒家的“誠”思想。認為“誠”在殷商末期,人的地位提高,“德”日益受到青睞,“誠”由人對鬼神的崇拜轉成對道德的崇尚,尤其是孟子對“誠”作了理論性論述。關于“誠”的含義,文章分析了“誠”與“天命之謂性”和“率性之謂道”及“修道之謂教”的關系,即認為:“誠”是創造宇宙萬物的本源,是天道;是圣人之德,是圣人才能達到的至善境界;認為圣人至誠無不盡興,所以“誠”自然能夠顯現,普通人先明善,后將善付諸實現,達到無不善的境界,實現“明誠”的目的。
《中庸》;“誠”思想
北宋時期,眾多中國學者,尤其是程朱學派崇尚《中庸》,將其從《小戴禮(禮記)》中分離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共同構成了四書。就先后順序而言,《中庸》位于四書之末,因其內容總括全體,構成了貫通四書的基礎。而就其內容而言,少下學之事,多說無形影、上達之事,①條理井然,濃縮了儒學之根本精神,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因此,程子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授之心法”。而在《中庸》的哲學體系中,“誠”思想作為其核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②所以,本文將以《中庸》為中心,探究儒家的“誠”思想。
所謂“誠”,我們通常會自然地理解為誠信、誠實、忠誠等道德性詞目。但在儒家思想中,“誠”不僅作為一種道德倫理,對現實生活具有巨大意義,[1]328并且發展成為了一個哲學性概念。
一、古代儒家“誠”思想的淵源
許慎在《說文解字》“誠”字條中寫到:“誠,信也。從言,成聲”;在“信”字條中寫到,“信,誠也。從人言”。由此可見,從古代文字學角度,把“誠”看作“信”,把“信”看做“誠”。
要探討《中庸》中的“誠”思想,有必要考察一下古代儒家經傳中所出現的“誠”。即從詞源的角度對“誠”進行探究。“誠”的詞源可上溯到開始有文字記錄的殷商時期,主要有《尚書?盤庚》以及大量的金文、龜甲卜辭,但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喪失,無從考證。到了西周時期,相關的文獻資料較多,例如,《詩經》、《尚書》的一部分及《易經》的卦辭、爻辭等。但經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尚書》與《易經》中并未出現“誠”字。但有人主張《尚書》中出現了最早的“誠”字,因為《太甲上》中出現了“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大禹謨》中出現了“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但是值得注意的,《太甲》和《大禹謨》是兩漢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所以還不能列入西周時期的材料之中。《易經》乾卦中的“閑邪存其誠”和“修辭立其誠”中出現了“誠”字,但這是《文言傳》中對爻辭的解釋,而《文言傳》出現于戰國末期與秦漢之間,所以也無法成為觀察西周思想的確切資料。《詩經?大雅?嵩高》中“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第一次出現了“誠”,作為人的一種基本道德詞目。其意思是“真實”、“誠實”。
由上可見,要通過探究古代文獻了解古代(西周以前)的“誠”思想具有一定難度。但筆者認為觀察古人對天與神的態度變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捷徑(關于‘天’的觀念將在下一節詳細探討)。
殷商時期,天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具有絕對主宰地位;但到了殷商末期,神的權威地位開始動搖,人的地位逐步提高,“德”這一條目日益受到人們的青睞。在這樣的過程中,“誠”概念也由最初帶有宗教色彩,意味著人對鬼神的崇拜與恭敬,轉換成對道德的崇尚。后來,孔子進一步發展了天道觀,將天看作道德實體,看作人類道德的來源,“天生德于予”,進一步把“誠”引入道德領域,但孔子并未直接論“誠”。繼而,孟子傳承孔子思想,對“誠”進一步進行了理論性論述。在孟子看來,“誠”貫通天人,意味著真實無妄,已與《中庸》中的“誠”十分相似,但仍存在著差異。“誠”思想不斷發展,到《中庸》時,作為貫通天道和人道的媒介,成為儒家道德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具備了道德性和哲學性雙重意義。可謂構建了比較完善的“誠”學體系。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發現“誠”思想的發展過程即是儒家形而上體系構建的過程。所以,對《中庸》“誠”思想的研究對于縷清儒學思想的脈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中庸》的基本構成與“誠”的含義
《中庸》首章揭示了全書的要旨,說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第20章中說道:“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將兩句話比照來看,“誠”相當于首章中的“天命”,而“誠之”則相當于首章中的“教”。也就是說,《中庸》中的“誠”首先從外在的天道著手,然后內化為人之心性,即分成了“天之道”的“誠”與“人之道”的“誠”。③
《中庸》原文中,對于“誠”的解釋有以下7種。①誠者,天之道也;②誠之者,人之道也;③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⑤誠者,自成也;⑥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⑦誠者,非自成而已也。朱子認為①、③、⑤、⑥就天道而言,而②、④、⑦則就人道而言。④
具體來說,首先將人道上升到天道,使其獲得先驗的神圣性,從而具有超越絕對、真理性天與萬物的權威。可見《中庸》中的“誠”思想充分體現了中國倫理精神的傳統特征--以天道論人道,借助自然化生的規則解釋儒家圣人的天下治理和人倫規范。⑤接下來,本文將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為主線,探討《中庸》中的“誠”思想是如何展開的。
(一)“天命之謂性”與“誠”的含義
探討“天命之謂性”與“誠”關系的突破口在于厘清“天命”的含義。那么,將“天人合一”作為終極目標的儒家是如何認識這一問題的呢?
概括來說,“天”分為主宰之天、自然之天、義理之天三層含義。所謂的主宰之天指皇天上帝,即有人格之天;自然之天,指自然運行之天;義理之天,指宇宙之最高原理。[2]10
具體來說,商、周時期,天、帝被看作至高無上之神,具有意志與人格,是一切權威的主宰者。此時,人與天、帝僅僅是主宰與被主宰的關系而已,即,天、帝是價值的根源,而人則是受宿命、命運掌控,接受天、帝價值的受命者而已。到了春秋末期,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對于天的信仰逐步減弱,“敬德”、“立德”等觀念不斷增強。但后來隨著周王失德于天下,引起了百姓的日漸不滿,又導致了“敬德”、“立德”信仰的動搖。而這種信仰的動搖,必然會帶來全新觀念的登場,即自然天的登場。即孔子所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⑥這意味著儒家全新天道觀的胎動。后來,自然天又得到不斷發展,不僅具有宇宙論意義上的象征宇宙化生、與地并立之天的自然意義,還發展為啟示自然公正的人文精神,作為人類存在依據的形而上學概念。[3]335此即《中庸》《易經》中所出現的天。
通常,天與地是一切具有生命的存在得以生存的基礎。但關于天道、地道,《中庸》26章中說道:“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可見,在《中庸》中,天與地不僅指具有日月星辰的空間,還被賦予了博、厚、高、明、悠、久等‘德’,即價值意義。而《中庸》作為闡明儒家道德哲學含義之書,自然更重視“天”的第二層含義。
以上闡述了天的含義。關于“命”字,朱子解釋到“命猶令也”,⑦鄭玄也說道:“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⑧所以“天命”就意味著天作為萬物的創造者,將自己的“德”賦予萬物→命予萬物。
《中庸》26章中,還說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由此可見,天是生萬物的存在依據。另外,朱子注釋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⑨因此,“誠”便成了生萬物的存在依據,與天聯系在了一起。
關于“天命”與“性”,朱子說道:“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⑩20章中說道:“誠者,天之道也”,21章中說道:“自誠明,謂之性”,由此可知,天以“誠”為道,并將此“誠”命于萬物,萬物受此“誠”而作為自身的性。換言之,性即是受于天之“誠”,具體表現為仁、義、禮、智等“德”。
那么,在《中庸》中,“誠”具體有何含義?
20章中說道:“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朱子對此注釋道:“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25章中說道:“誠者……性之德”、“誠者,自成也”。可見,”誠”乃渾然天理,圣人之德,至純至善之物。
另外,25章中,“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26章中,“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朱子對26章注解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中庸》中,宇宙萬物皆出于一個本源,此本源即是“誠”。天道-“誠”在自身運動變化過程中,巧妙地創造出萬物,同時,將天道的生生之理賦予萬物。因此,宇宙萬物生生不已、層出不窮。
(二)“率性之謂道”與”誠”的含義
蒙培元先生在《中國心性論》中,主張《中庸》將人的主體意識與觀念提升為宇宙的根本性存在,從而建立起宇宙自然的秩序。這就使得自然界具有了人的特性,人的特性也投射到了自然界中。正如前文所述,天命向下貫通至萬物,萬物受此天命而具有性,明確了性的根源,便可知人類具有道德可能性。那么,接下來將探索一下“率性之謂道”與“誠”的含義。
首先,何為“率性”?鄭玄在《禮記正義》中說道:“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朱子注釋道:“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可見,所謂“率性”即是循天所賦之“天道”,即循性。另外,朱子還注釋道:“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與此類似,《中庸》25章中說道:“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可見,率性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意思不明晰)→率性即是一個天命自然發顯的過程,無需牽強附會,刻意用力。
關于“道”,朱子注釋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可見“道”即是“理”,但這樣說容易產生混淆,認為“道”與“理”、“性”是相同的概念。其實不然,兩者屬于不同的范疇,正如朱子所說的“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0“性”指的是內在于體內的天命,并不包含生來所乘之“氣”,是一種內在的潛能,是萬物都受于天命而具有的普遍的性,即所謂的天道或者“誠”。而“道”則是每個具體的事物在日常中當行的道理,根據事物的不同而不同。朱子還說道:“道卻是個無情底道理,卻須是人自去行始得”,1這就是說“道”不再是脫離氣質而獨立存在的“性”或“理”,而必須內在于事物之中,并強調實踐的重要性,這體現了朱子所主張的“理氣不離”觀點。并且,這與1章中“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一致的。簡而言之,“天命之謂性”是就不進行區分、渾然一體的天下之大本而言;而“率性之謂道”則是在這一渾然天下之大本的基礎上又進行的進一步細分。但在根本上,都出自“天道”。這樣,“道”就與“誠”聯系了起來。
關于“率性”與“誠”的關系,安炳周說道:“循天命之性的率性,其目標在于‘致中和’”。[4]39《中庸》20章中,“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可見,儒家所追求的圣人只要順其自然,率性而為就能達到“中和”這一最高境界。亦即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222章中還說道:“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所謂“天下至誠”,即圣人之德,即天道,是只有至誠的圣人才能夠達到的至善境界。
前面一節談到了道存在于具體事物之內,并且與實踐有關。這通過1章中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體現。而關于“誠”之特征,《中庸》中說道:“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至誠無息”,可見,“道”具有“誠”之特征,兩者關系緊密。
簡而言之,“性”的實現是一個自然向外呈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道”亦自然得到了施行,而“道”的作用即是作為本性之“誠”的實現。
(三)“修道之謂教”與“誠”的含義
關于“修道之謂教”,很多學者都做出了解釋。首先,鄭玄注釋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效之,是曰教”3;孔穎達注釋道:“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是修道之謂教也”4;朱子注釋道:“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5由以上觀點看,他們都一致地主張所謂“修道”是指依據圣人率性所得之“道”,制定禮法以教誨普通人,揭示了儒家傳統信仰中的圣人治世的“禮治”或“德治”的真諦。《左傳》中說道“禮以順天,天之道也”,朱熹說道:“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所謂的“禮法”即是天道的理論化、規范化,是“圣人則天之治”,在這樣的脈絡下,“修道之謂教”就與天道“誠”聯系了起來。
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中指出,天所賦予之性通過心呈現于形體,客觀化為人心中的“道”;相反,通過心也同樣能回歸到所賦之性。[5]41圣人的本性全體無不誠,在實踐過程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其德至誠無妄,是人類當行之實理。因此,圣人能夠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6將天道具體化,制定出一套道德倫理規范與行為準則,使得蔽于形氣的普通人,通過后天的修養,努力改變材質、回歸本性,達到圣人的境界。這就是《中庸》首節所說的“修道之謂教”。
另外,《中庸》21章中說道“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這可以看作是對“修道之謂教”的進一步闡述。圣人至誠無不盡性,所以“誠”自然能夠顯現,“自誠明”;而學者,即普通人,則通過學習首先明善,然后將所明之善付諸實踐,達到無不善的境界,所以說“自明誠”。小注中,勿軒熊氏曰:“......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后知。明誠謂之敎,學知利行之事,先知后仁”,闡明了“自誠明”與“自明誠”的區別,并揭示了實現“自明誠”通過“修道之謂教”而成為可能。
縱觀《中庸》全篇,從開篇的“天命之謂性”到結尾的“上天之載,無聲無息”,始終貫穿著以天道論人道的特征,即雖看似時時刻刻講宇宙的自然演化和存在狀態,但實際上則是在借助自然規則來解釋儒家的道德倫理和治世原則。作為《中庸》核心的“誠”自然也具有以上特征,這就揭示了實現“至誠”的內在可能性,為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修己修人的“大同社會”提供了途徑和無限力量源泉,也為當今和平世界、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方向指引與動力支持。
注釋:
①《中庸<讀中庸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
②《中庸<讀中庸法>》: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
③牟鐘鑒先生在《重建誠的哲學》一文中,主張孟子始正式言“誠”,并兼天人之道而言之。將最初指人言之實在不欺的“誠”擴大到天道,強調大自然的存在和變化是真實無妄的。并在天人一體的思維模式下,從道德論的角度強調人道對天道的效法和復歸,提出了人道思誠之說。
④參見《中庸章句》20、21、25章朱子注。
⑤單純:《論<中庸>的自然正義觀與政治理想》。
⑥《論語?陽貨》。
⑦-/5《中庸章句》1 大注。
⑧鄭玄:《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中庸篇>。
⑨《中庸章句》26 大注。
⑩《中庸章句》1 大注。關于性、命的關系還可參考周敦頤《通書?誠上》第一的朱子注:“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
,3鄭玄:《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中庸注>》。
.0《中庸章句》1小注。
1《中庸章句》25小注。
2《論語?為政》4。
4孔穎達:《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中庸疏>》。
6參考《中庸》第32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圣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1]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2]施湘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研究[M].臺北:正中書局,1981.
[3]金圣基.關于先秦儒學的天人關系的詮釋學解釋[A].儒教思想研究(第13輯),2000.
[4]安炳周.韓國名賢的中庸注釋資料集成[M].成均館大學大同文化研究院,1992.
[5]牟宗三.心體與性體[M].臺北:正中書局,1999.
(責任編輯:李直)
B222
A
CN61-1487-(2016)03-0025-04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恢復性司法與儒家倫理”(編號:14FFX028)。
張悅,山東淄博人,韓國成均館大學儒學院博士在讀,研究方向為儒家思想、周易哲學、韓國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