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邏輯分析
呂 進(jìn)
記憶的邏輯分析
呂 進(jìn)
記憶是認(rèn)知的基本要素,主體的認(rèn)知推理依賴于記憶。哲學(xué)家通常將記憶分為經(jīng)驗(yàn)的記憶、命題的記憶和實(shí)踐的記憶。從記憶內(nèi)容的角度,可以將命題記憶看作是經(jīng)驗(yàn)記憶的子集。從功能的角度說(shuō),記憶是現(xiàn)實(shí)主體對(duì)以往經(jīng)驗(yàn)到的信息的貯存和調(diào)用。長(zhǎng)時(shí)記憶與短時(shí)記憶的結(jié)構(gòu)在認(rèn)識(shí)論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真正影響主體行動(dòng)決策的是短時(shí)記憶。從內(nèi)容上可以將記憶劃分為幾個(gè)各自獨(dú)立的子集,由此導(dǎo)致了序言悖論和整體主義的一些問(wèn)題。
記憶;信念;時(shí)間
作者呂進(jìn),男,漢族,重慶人,哲學(xué)博士,重慶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副教授,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重慶 400044);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北京 102488)。
記憶作為主體認(rèn)知的基本要素,歷來(lái)是心理學(xué)、哲學(xué)、語(yǔ)言學(xué)等認(rèn)知學(xué)科的重要研究領(lǐng)域。柏拉圖認(rèn)為學(xué)習(xí)就是回憶。Sven Bernecker甚至認(rèn)為,鑒于記憶在認(rèn)知過(guò)程中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作用,記憶“是人之為人的標(biāo)志”[1]P1。隨著人工智能研究的發(fā)展,諸如認(rèn)知邏輯和認(rèn)知語(yǔ)言學(xué)等學(xué)科也開(kāi)始討論記憶的性質(zhì)、結(jié)構(gòu)和形式化分析。
一、記憶的概念分析
正如諸多看起來(lái)普通而且常用的日常概念一樣,似乎大家都能理解什么是記憶,但是一旦仔細(xì)思考,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很難清楚明白地說(shuō)出來(lái)。心理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們提出了多種觀點(diǎn),Sven Bernecker在他的著作《記憶:一個(gè)哲學(xué)研究》中詳細(xì)歸納梳理了關(guān)于記憶的各種概念。
心理學(xué)家至少?gòu)乃膫€(gè)方面來(lái)說(shuō)明記憶的性質(zhì)[2]P11:記憶儲(chǔ)存信息時(shí)間的長(zhǎng)度、主體對(duì)于所儲(chǔ)存的信息察知的程度、主體重新獲得所記憶信息的靈敏度以及記憶所儲(chǔ)存信息的種類。
根據(jù)信息記憶在人腦中停留的時(shí)間長(zhǎng)度,通常可以把記憶分為長(zhǎng)時(shí)記憶與短時(shí)記憶。短時(shí)記憶一般持續(xù)幾秒鐘,然后或者轉(zhuǎn)入長(zhǎng)時(shí)記憶被主體儲(chǔ)存起來(lái),或者被遺忘。根據(jù)信息內(nèi)容來(lái)區(qū)別記憶以劃分記憶的種類是最主要的方式。一個(gè)基本的劃分是將記憶內(nèi)容分為陳述性的和只能展示而不能陳述的兩類,其中影響很大的是心理學(xué)家Endel Tulving的劃分,他將陳述性記憶又區(qū)分為語(yǔ)義記憶和情景記憶兩個(gè)子類。語(yǔ)義記憶是用以儲(chǔ)存關(guān)于世界、概念、規(guī)則和語(yǔ)言的那些一般性知識(shí)的記憶,其特征是它不需要提及記憶形成的初始事件,而情景記憶則附有記憶的經(jīng)驗(yàn)或者是心靈回溯過(guò)去時(shí)間并對(duì)該事件的再體驗(yàn)過(guò)程。Jordi Fernandez認(rèn)為[3],情景記憶伴隨著對(duì)過(guò)去事件發(fā)生時(shí)形成的經(jīng)驗(yàn),而語(yǔ)言記憶則是伴隨著對(duì)過(guò)去事件發(fā)生時(shí)所形成的信念。
哲學(xué)家一般將記憶分為三類[4]P14:經(jīng)驗(yàn)(或個(gè)人)的記憶、命題(或事實(shí))的記憶以及實(shí)踐(或程序化)的記憶。經(jīng)驗(yàn)記憶與命題記憶在尋求表達(dá)世界方面有一些共通之處,而它們的內(nèi)容從原則上說(shuō)也有一些聯(lián)結(jié)。而實(shí)踐記憶則不同,實(shí)踐記憶是那種主體記得如何做什么的記憶,這樣的記憶指向做事前所需要的前提以及記住動(dòng)作技巧的特征。
經(jīng)驗(yàn)記憶與命題記憶的區(qū)別并不是必然兩分的。例如說(shuō),我記得我上個(gè)暑假有幾天時(shí)間在羅馬,這屬于經(jīng)驗(yàn)的記憶還是命題的記憶呢?似乎二者都有。經(jīng)驗(yàn)記憶和命題記憶的界線是模糊的,其主要的理由是區(qū)別這兩者的標(biāo)準(zhǔn)是多種多樣的。例如說(shuō),一個(gè)識(shí)別命題記憶的語(yǔ)法標(biāo)準(zhǔn)是記憶的內(nèi)容必然能夠形成一個(gè)“that”引導(dǎo)的從句;而識(shí)別經(jīng)驗(yàn)記憶的標(biāo)準(zhǔn)則是現(xiàn)象學(xué)的,即用諸如圖像和定性經(jīng)驗(yàn)這類的心靈的東西來(lái)顯示自己,更進(jìn)一步說(shuō),是與導(dǎo)致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那些事件聯(lián)系起來(lái)。一些經(jīng)驗(yàn)記憶依靠“記得”和某個(gè)動(dòng)名詞得以表達(dá),而另一些則用從句來(lái)表達(d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語(yǔ)法表達(dá)方式。
有一些哲學(xué)家用羅素的“親知的知識(shí)”與“描述的知識(shí)”這樣的劃分來(lái)區(qū)別經(jīng)驗(yàn)記憶和命題記憶。經(jīng)驗(yàn)記憶被看作是由親知而成的記憶,它的意向?qū)ο蟛皇鞘聦?shí)或命題,而是人、地點(diǎn)、事物、事件和狀態(tài)。而命題記憶則被看作是類似于描述的知識(shí)。但Sven Bernecker認(rèn)為這種類比不能幫助我們有效地區(qū)分經(jīng)驗(yàn)的記憶與命題的記憶,他提出三個(gè)理由反駁這種區(qū)分[5]P18:首先,通過(guò)描述而被記住的自傳之類的資料和客觀命題實(shí)際上是親知的;其次,在某一方面命題的記憶也類似于由親知獲得的知識(shí),而且即使是羅素本人也不認(rèn)為親知的知識(shí)和描述的知識(shí)能夠截然分開(kāi);第三,這種用親知/描述的區(qū)分來(lái)解釋經(jīng)驗(yàn)/命題的區(qū)分會(huì)產(chǎn)生一些反直觀的結(jié)果,嚴(yán)格地說(shuō),主體不能經(jīng)驗(yàn)地記住p。
事實(shí)上,如果能夠?qū)⒔?jīng)驗(yàn)記憶的內(nèi)容描述出來(lái),那么經(jīng)驗(yàn)記憶和命題記憶在邏輯上就是相等的。我們可以將命題記憶看作是經(jīng)驗(yàn)記憶的一個(gè)子集。
Sven Bernecker提出[6]P19-20,根據(jù)“記憶”這一概念在用法上的若干語(yǔ)詞的意義,可以將記憶分為主要的四類:關(guān)于對(duì)象(人與事物)的記憶、特征的記憶、事件的記憶和事實(shí)(命題)記憶。前三類記憶也可以稱為非命題的記憶。Sven Bernecker認(rèn)為命題的記憶是核心,凡是可以用形式“S記住that-p”表達(dá)的都屬于命題記憶,而不管p實(shí)際上指的是什么。他還認(rèn)為,“記住”通常用于“wh-從句”,但它們只不過(guò)是命題記憶的不完全表達(dá)方式,例如說(shuō),“我記得布魯特斯刺殺了誰(shuí)”(I remember whom Brutus stabbed)不過(guò)是“我記得布魯特斯刺殺了如此這樣的人” (I remember that Brutus stabbed so-and-so)的另外一種說(shuō)法而已。這就是說(shuō),Sven Bernecker認(rèn)為wh-從句可以改寫(xiě)為that-從句。
有意思的是,我們用語(yǔ)法標(biāo)準(zhǔn)來(lái)給記憶分類,但是記憶本身卻是可以不依賴語(yǔ)言的。記憶與語(yǔ)言是對(duì)象和描述之間的關(guān)系,而用什么樣的語(yǔ)言來(lái)描述記憶更多地可能在于不同主體間的分歧,包括個(gè)人與社會(huì)的、語(yǔ)言與文化的背景區(qū)別。極端情況下,不需要語(yǔ)言也能表明有記憶,例如說(shuō),狗用行動(dòng)證明它能夠清楚地記得它將食物藏在了什么地方。
同時(shí),盡管語(yǔ)言與記憶有很強(qiáng)的相關(guān)性,但是這種相關(guān)性也影響了或者說(shuō)削弱了記憶在現(xiàn)實(shí)主體認(rèn)知中的作用。例如說(shuō),我們完全可以用語(yǔ)言的方式來(lái)記載記憶內(nèi)容,使得主體的認(rèn)知不再需要記憶的參與,就像現(xiàn)代人工智能一樣。計(jì)算機(jī)理論通常將資料的存儲(chǔ)與調(diào)用看作是記憶,不過(guò)這樣的記憶已經(jīng)成為純粹客觀的了。
哲學(xué)家還根據(jù)其他標(biāo)準(zhǔn)給出記憶的分類。常見(jiàn)的有誠(chéng)實(shí)記憶與虛假記憶,推論的記憶與非推論的記憶,從言的記憶與從物的記憶,等等。誠(chéng)實(shí)記憶或者稱事實(shí)上的記憶,當(dāng)我們說(shuō)“S記得that-p”的時(shí)候,該語(yǔ)句暗示了p是一個(gè)事實(shí)。這里發(fā)生的事情成為記憶的條件,例如說(shuō),如果布魯特斯沒(méi)有刺殺凱撒,那么我們就不會(huì)記得這件事。與此相反,虛假記憶則是主體記住的事情中那些實(shí)際上沒(méi)有發(fā)生而只是主觀臆構(gòu)的事情。通常我們會(huì)認(rèn)為記憶是真實(shí)的,但是我們也承認(rèn)記憶在內(nèi)容上并不那么可靠,如果加上遺忘,那就更復(fù)雜了。
綜上所述,記憶是現(xiàn)實(shí)主體對(duì)以往經(jīng)驗(yàn)到的信息的貯存和調(diào)用,這種貯存和調(diào)用受到一些條件的限制。Natasha Alechina等提出一個(gè)資源上有限的推理主體受到的限制主要是記憶、時(shí)間和信息交流[7],詳細(xì)地說(shuō),這些條件主要包括:時(shí)間對(duì)記憶的影響,記憶內(nèi)容的真假條件,記憶內(nèi)容相互之間的作用與影響,記憶與其他認(rèn)知要素特別是信念的聯(lián)系條件,等等。對(duì)記憶的邏輯刻畫(huà)應(yīng)該說(shuō)明這些條件限制。
二、記憶的邏輯結(jié)構(gòu)
盡管對(duì)記憶有著各種不同的認(rèn)識(shí),但基本都認(rèn)為記憶有著自己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
記憶的一個(gè)基本結(jié)構(gòu)是長(zhǎng)時(shí)記憶(long-term memory)與短時(shí)記憶(short-term memory)。就現(xiàn)實(shí)主體來(lái)說(shuō),我們不可能同時(shí)記起所有我們記得的東西,而只能記起其中的一個(gè)子集。其中,當(dāng)下正在被回憶的那些我們所記得的信息就是短時(shí)記憶,其他被儲(chǔ)存在記憶中的信息就是長(zhǎng)時(shí)記憶。或者可以說(shuō),短時(shí)記憶就是正在起作用的記憶,長(zhǎng)時(shí)記憶就是當(dāng)下未能起作用但已經(jīng)被記住的記憶。從這個(gè)角度上說(shuō),瞬時(shí)記憶、短時(shí)記憶與長(zhǎng)時(shí)記憶的三分法可以簡(jiǎn)化為二分法。
心理學(xué)研究表明,現(xiàn)實(shí)人的記憶能力是無(wú)限的,也就是說(shuō)長(zhǎng)時(shí)記憶還沒(méi)有找到容量界限。但是短時(shí)記憶則有明顯的容量限制,通常只有6個(gè)(根據(jù)不同的資料來(lái)源、容量限制的數(shù)據(jù)略有不同)有意義的單位,而且在時(shí)間上也有限制,通常只有幾秒鐘,最長(zhǎng)不超過(guò)半分鐘時(shí)間,短的甚至只有幾毫秒。
將記憶區(qū)分為短時(shí)記憶與長(zhǎng)時(shí)記憶對(duì)于哲學(xué)家來(lái)說(shuō)是很有意義的。由于短時(shí)記憶是當(dāng)下起作用的記憶,而長(zhǎng)時(shí)記憶則是當(dāng)下未起作用的記憶,那么,真正影響主體推理與行動(dòng)決策的就只是短時(shí)記憶。在史密斯的例子[8]中,史密斯具有火柴能夠點(diǎn)燃汽油的信念,也有火柴能夠照明的信念。當(dāng)史密斯點(diǎn)燃火柴去查看汽油桶里是否還有汽油的時(shí)候,這兩種信念并沒(méi)有被史密斯同時(shí)記得,真正起作用的只有“火柴能夠用來(lái)照明”這一信念,而“火柴能夠點(diǎn)燃汽油”的信念沒(méi)有起作用,因而出現(xiàn)了他被燒傷的悲劇。
短時(shí)記憶的另一個(gè)重要特征是,它的內(nèi)容是被主體覺(jué)知的信息。這樣根據(jù)短時(shí)記憶與長(zhǎng)時(shí)記憶的劃分,可以將知識(shí)和信念劃分為被覺(jué)知的和未被覺(jué)知的。這一劃分在認(rèn)識(shí)論和邏輯學(xué)上都有很多好處,例如說(shuō),它可以解釋現(xiàn)實(shí)主體不具有邏輯全知能力的原因,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體由于短時(shí)記憶限制而不可能是邏輯全知的。
由于短時(shí)記憶的內(nèi)容都是長(zhǎng)時(shí)記憶的內(nèi)容,這就有一個(gè)短時(shí)記憶如何從長(zhǎng)時(shí)記憶調(diào)用的問(wèn)題。心理學(xué)研究認(rèn)為,記憶具有主動(dòng)索搜的功能,從而使得長(zhǎng)時(shí)記憶不斷地通過(guò)短時(shí)記憶所提示的信息進(jìn)入到短時(shí)記憶中,從而能夠?qū)χ黧w的推理和行為決策產(chǎn)生影響。
長(zhǎng)時(shí)記憶與短時(shí)記憶的結(jié)構(gòu)在認(rèn)識(shí)論上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可以用來(lái)解釋人的認(rèn)識(shí)能力為什么不可能達(dá)到全知的一個(gè)關(guān)鍵,成為現(xiàn)實(shí)理性主體的一個(gè)重要的認(rèn)識(shí)論上的特征,并且能夠?qū)⒆鳛槔硇灾黧w的現(xiàn)實(shí)人與人工智能區(qū)別開(kāi),因?yàn)槿斯ぶ悄軟](méi)有這一區(qū)分,在理論上人工智能的存貯(記憶)都是可以瞬時(shí)調(diào)取的,人工智能沒(méi)有記憶的限制而只有計(jì)算的限制。
記憶內(nèi)容是不是一致的?一般來(lái)說(shuō),理性主體會(huì)排斥相互矛盾的信息,因此記憶中的內(nèi)容應(yīng)該是一致的。但是序言悖論(preface paradox)提出了記憶內(nèi)容是不是具有一致性的問(wèn)題。序言悖論是說(shuō),一個(gè)人說(shuō)“我的信念之中,有某一個(gè)應(yīng)該不是真的”,那么這一命題也是他的信念,而且這一信念通常會(huì)被認(rèn)為是真的。將這一命題命名為F,然后將F加到此人的信念集中,則在直觀上會(huì)認(rèn)為這個(gè)人的信念集是矛盾的。
序言悖論是信念全知的一個(gè)變化形式,這一變化形式與記憶相關(guān)。通常,我們不可能相信一對(duì)相互矛盾的信念,但是,由于記憶的限制,在同一時(shí)間我們實(shí)際上不會(huì)記得或者說(shuō)不會(huì)查知信念集中的信念是否是有矛盾的,尤其在信念集中的元素?cái)?shù)量極其巨大的時(shí)候。一個(gè)人的信念集幾乎是無(wú)窮大的,因而記憶中的信念集包含矛盾是合理的。
一些心理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提出來(lái),記憶內(nèi)容實(shí)際上分為了幾個(gè)子集,子集之間的聯(lián)系并非是密切的,有可能互不相關(guān)。那么當(dāng)某一子集的內(nèi)容為主體調(diào)用的時(shí)候,由于所調(diào)用的子集中的內(nèi)容并沒(méi)有明顯的矛盾,則該主體不會(huì)認(rèn)識(shí)到自己的記憶是矛盾的,盡管他會(huì)認(rèn)為自己的記憶包含矛盾是合理的。
序言悖論說(shuō)明了現(xiàn)實(shí)主體并非是邏輯全知的,即理性是有限制的,這一限制內(nèi)在于主體的長(zhǎng)時(shí)記憶的內(nèi)容,使得理性只能是局部的。
討論記憶內(nèi)容的層次性源于蒯因的整體主義的認(rèn)識(shí)論思想。蒯因認(rèn)為[9]P40-41,知識(shí)或者信念是作為一個(gè)整體來(lái)接受檢驗(yàn)的,如果對(duì)一個(gè)陳述知識(shí)或信念的命題進(jìn)行真值的重新評(píng)價(jià)的話,那么會(huì)對(duì)整個(gè)知識(shí)與信念陳述的值或多或少地進(jìn)行調(diào)整,每一陳述都不具有絕對(duì)不可調(diào)整的地位,整體內(nèi)的任何陳述都可以被修正。
蒯因的整體論對(duì)記憶理論的影響在于,記憶內(nèi)容的真假是否能夠由主體自動(dòng)調(diào)節(jié)修正。根據(jù)蒯因的整體主義觀,理性主體具有根據(jù)信念的值對(duì)信念集中其他信念的值進(jìn)行自動(dòng)修正的能力。但是弗萊明的青霉素發(fā)現(xiàn)的例子說(shuō)明,現(xiàn)實(shí)主體不具有這樣的能力。該案例實(shí)際上還提出這樣的問(wèn)題:根據(jù)記憶所推理得到的是否也是主體的記憶,即記憶是否可以區(qū)分為直接記憶與由記憶推理所得到的記憶。蒯因的理論支持這一區(qū)分,而青霉素案例則不支持這一區(qū)分。
Christopher Cherniak提出[10],現(xiàn)實(shí)主體的記憶結(jié)構(gòu)是基于短時(shí)記憶與長(zhǎng)時(shí)記憶的劃分,記憶的內(nèi)容被組織起來(lái),即使是不對(duì)人的知識(shí)與行為推理發(fā)生直接影響的長(zhǎng)時(shí)記憶也是如此:“我們思考到的所有人類記憶的解釋斷定,長(zhǎng)時(shí)記憶的內(nèi)容是被組織起來(lái)的”。這些記憶被組織起來(lái),形成不同的信念子集,內(nèi)容的不一致性和層次性發(fā)生在不同子集之間:“信念之網(wǎng)并不是混亂的,它的語(yǔ)句組織被 ‘縫合’到各個(gè)有關(guān)聯(lián)而又相互獨(dú)立的系統(tǒng)縫合物中,連結(jié)不太可能形成于子集之間”。正因?yàn)槿绱耍瑥挠洃浀慕嵌葋?lái)說(shuō),蒯因的整體主義是失敗的。
三、記憶的邏輯性質(zhì)
上述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分析記憶的邏輯性質(zhì)。一般來(lái)說(shuō),記憶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同時(shí)間有關(guān)。Jordi Fernández提出[11]記憶有兩個(gè)性質(zhì):其一是時(shí)間性質(zhì),這里主要是指與形成信念的過(guò)去發(fā)生的事件的時(shí)間;其二是主體的存在性質(zhì),這里是指主體在發(fā)生事件的時(shí)間里存在。
Giacomo Bonanno從過(guò)去的信念角度刻畫(huà)了關(guān)于記憶的若干性質(zhì)[12],這些刻畫(huà)給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邏輯性質(zhì),然而是否能夠用過(guò)去時(shí)間和信念來(lái)代替記憶值得商榷。畢竟記憶的內(nèi)容則并非與時(shí)間尤其是過(guò)去時(shí)間必然相關(guān)。例如我可以記得關(guān)于未來(lái)的某個(gè)事情(明天有一個(gè)學(xué)術(shù)會(huì)議召開(kāi)),或者記得某個(gè)不受時(shí)間限制的必然真理(2+2=4),而有些事情則既與過(guò)去有關(guān)又和未來(lái)相關(guān)(昨天天氣預(yù)報(bào)告知明天會(huì)下雨)。
計(jì)算機(jī)理論中的邏輯往往傾向于將記憶看作是一個(gè)行為,因而可以用動(dòng)態(tài)邏輯來(lái)刻畫(huà)。一些認(rèn)知邏輯傾向于將記憶看作是一種資源而不是一種認(rèn)知狀態(tài)來(lái)加以刻畫(huà)。Audrey Yap提出[13],認(rèn)知邏輯給出的是主體認(rèn)為應(yīng)該怎么樣行動(dòng),而不是施行什么樣的行為,從這個(gè)角度可以思考解決邏輯全知問(wèn)題。
本文采用將記憶看作是一個(gè)意向性命題態(tài)度的觀點(diǎn)。這一觀點(diǎn)與將記憶看作是一個(gè)思維活動(dòng)的觀點(diǎn)有很大區(qū)別。如果把語(yǔ)句“主體記得一個(gè)命題p”,記為Mp,那么記憶僅僅表示為一個(gè)認(rèn)知命題態(tài)度,就如同“主體相信一個(gè)命題p”那樣。這樣我們只需要考慮“記憶”本身與時(shí)間的關(guān)系,而不需要考慮記憶內(nèi)容與時(shí)間的關(guān)系。而這一思考可以更細(xì)致地表達(dá)記憶與信念、記憶與時(shí)間、記憶與行為的邏輯聯(lián)系。
綜合前面對(duì)“記憶”這一概念的分析,記憶都具有“對(duì)過(guò)去認(rèn)知的內(nèi)容或習(xí)得的技能的喚醒”這一含義,即記憶是對(duì)過(guò)去某一認(rèn)知內(nèi)容或習(xí)得的技能在現(xiàn)在的重新喚醒。記憶這種頗為特殊的含義表明,它既與過(guò)去有關(guān),又發(fā)生在當(dāng)下。
主體的信念是影響主體認(rèn)知和實(shí)踐推理的一個(gè)核心要素,而記憶與信念是密切聯(lián)系的。首先,主體的信念通常會(huì)保存在記憶中,如果沒(méi)有記憶我們就只有當(dāng)下的信念,這樣我們的認(rèn)知能力以及相應(yīng)的行為能力就會(huì)大大下降;同時(shí),如果沒(méi)有記憶,即使沒(méi)有任何其他影響,當(dāng)下的信念也不會(huì)在未來(lái)對(duì)我們產(chǎn)生任何影響;第三,由于新信息的影響以及認(rèn)知選擇,我們的信念會(huì)發(fā)生改變,這種改變能夠被我們所認(rèn)知,在于我們能夠記得過(guò)去的信念,從而能夠?qū)Σ煌男拍钸M(jìn)行對(duì)比。由此可以考慮記憶與信念的邏輯刻畫(huà):
1.如果主體相信p,那么主體記得他相信p。
這可以看作是主體的信念與記憶相互關(guān)系具有內(nèi)省性質(zhì)的一個(gè)表達(dá)。正如“如果主體相信p,那么主體知道他相信p”。
這一表達(dá)可以形式化地記為:
Lp→MLp。
這一刻畫(huà)顯得直觀,因?yàn)槿绻黧w沒(méi)有對(duì)信念的記憶那么該信念對(duì)主體沒(méi)有任何意義。但這一性質(zhì)將導(dǎo)致主體記得他所有的信念,那么對(duì)于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體來(lái)說(shuō),這樣的性質(zhì)顯得太強(qiáng)了。一個(gè)補(bǔ)救的措施是將記憶限制在短時(shí)記憶,不過(guò)這樣一來(lái)又顯得太弱了。
2. 如果主體記得p,那么主體相信p。
這一表達(dá)說(shuō)明的是主體的記憶與信念具有一致性,即同樣我們記得的是我們相信的東西。例如說(shuō)“我記得中國(guó)第一個(gè)世界冠軍是容國(guó)團(tuán)”。即使有些我們記得的內(nèi)容是我們不相信的,其實(shí)表達(dá)的也是我們記得這一內(nèi)容的否定,例如說(shuō),“我記得有人告訴我2012年是世界末日,但我不相信他。”
這一表達(dá)可以形式化地記為:
Mp→Lp。
這一性質(zhì)是符合直觀的。
3.記憶的K公理:根據(jù)記憶推理所得到的命題仍然是該主體的記憶。
一些哲學(xué)家將記憶看作是知識(shí)的一個(gè)來(lái)源。這一來(lái)源在于將知識(shí)劃分為直接的知識(shí)與推理的知識(shí),而推理的知識(shí)往往要通過(guò)記憶。同樣的劃分也可以用之于記憶,即可以將記憶劃分為直接記憶與推理的記憶。推理的記憶實(shí)際上是根據(jù)記憶進(jìn)行推理所得到的結(jié)論。這一思想的形式化就是K公理:
Mφ∧M(φ→ψ)→Mψ。
很顯然,這一表達(dá)并非一般性地成立,從前面關(guān)于記憶的一致性與層次性的分析容易得到這一結(jié)論。例如如下是可能的:主體相信a=b,且相信b=c,但是主體不相信a=c。
要使得這一性質(zhì)成立,就必須加以限制,例如,將其限制在短時(shí)記憶上,則是可以成立的。
4.記憶的正內(nèi)省與負(fù)內(nèi)省。
我記得我的記憶嗎?根據(jù)長(zhǎng)時(shí)記憶與短時(shí)記憶的理論,我所能夠察知的記憶只能是當(dāng)下起作用的記憶,而長(zhǎng)時(shí)記憶則不能直接被主體察知,因而說(shuō)我記得我的記憶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shuō),記憶不滿足正自省性,因此如下表達(dá)不是恒真的:
Mφ →MMφ。
但是,當(dāng)我對(duì)某個(gè)陳述沒(méi)有記憶的時(shí)候,或者說(shuō),我不記得p時(shí),說(shuō)我記得我不記得p,則是恰當(dāng)?shù)摹_@就是說(shuō),記憶滿足負(fù)自省性,即如下表達(dá)是成立的:
記憶的內(nèi)容是不是應(yīng)該為真,即如果記得p,p就是真命題。如果把記憶看作是主體對(duì)過(guò)去的真實(shí)記錄,則記憶的內(nèi)容都是真的。對(duì)一個(gè)理想主體而言,記憶的都是真的,即理性主體滿足記憶的真實(shí)性,如下表達(dá)是成立的:
Mφ →φ。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常發(fā)現(xiàn)自己的記憶出錯(cuò)了。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體顯然不是理想主體,在青霉素那個(gè)案例中,表明主體會(huì)有遺忘等等導(dǎo)致記憶不清或者記憶錯(cuò)誤的問(wèn)題。因此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體沒(méi)有記憶的真實(shí)性。
5.記憶的理性:矛盾的內(nèi)容不同時(shí)出現(xiàn)在記憶中。
記憶還有一個(gè)遺忘和更新的問(wèn)題:如果我們把記得的東西都記下來(lái),那么記下來(lái)的東西是不是就是我的記憶呢?或者說(shuō),記憶是不是可以客觀外化?如果隔一段時(shí)間之后我完全否認(rèn)這是我記得的東西,那又怎么辦?
如果記憶是可以客觀外化的,那么現(xiàn)實(shí)的主體和人工智能主體就具有一致性。但是現(xiàn)實(shí)主體會(huì)有遺忘,而人工智能則不會(huì)遺忘,從這個(gè)角度說(shuō),人工智能是一個(gè)理想主體。
[1][2][4][5][6]Sven Bernecker.Memory: a philosophical Stud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11]Jordi Fernandez.Memory and time[J].Philosophy Study,2008.
[7]Natasha Alechina, Brian Logan, Hoang Nga Nguyen, Abdur Rakib. Verifying time, memory and communication bounds in systems of reasoning agents[J].Synthese,2009.
[8][10]Christopher Cherniak.rational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memory[J].Synthese,1983.
[9]蒯因.從邏輯的觀點(diǎn)看[M].江天驥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12]Giacomo Bonanno.Memory of past beliefs and actions[J].Studia Logica,2003.
[13]Audrey Yap.Idealization, epistemic logic, and epistemology[J].Synthese,2014.
責(zé)任編輯:陳 剛
LogicalAnalysisofMemory
LV Jin
Memory is a basic element of cognition, and the cognitive inference of the subject depends on memory. Philosophers tend to divide memory into experiential, propositional and practical memory. In terms of content, propositional memory can be regarded as a subset of experiential memory. In terms of function, memory is the storage and use of information by the realistic subject, which has been experienced. The structure of long-term and short-term memory is significant in epistemology, and it is short-term memory that in a real sense affects the decision-making on action by the subject. In terms of content, memory can be divided into independent subsets, which lead to such problems as preface paradox and holism.
memory; belief; time
B81.05
A
1003-6644(2016)02-0117-08
* 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實(shí)踐推理邏輯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10YJC7204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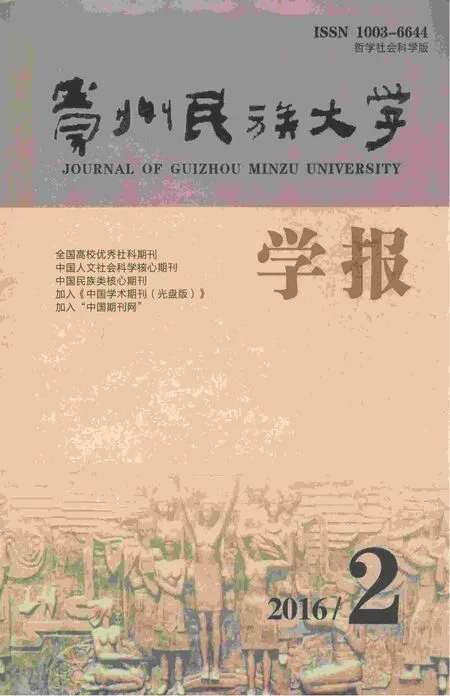 貴州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2期
貴州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2期
- 貴州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刑事案件陪審員制度實(shí)證研究———基于J 省、C 市部分基層法院的考察和分析
- 司法體制改革的憲法學(xué)評(píng)估
- 貴州民族村寨旅游開(kāi)發(fā)模式利益主體訴求及其效度分析
- 不甘隕落的歌者 ——肅南裕固族民間口頭傳統(tǒng)傳承人調(diào)查
- 略論故事形態(tài)學(xué)理論研究的新進(jìn)展
- Langacker的事件認(rèn)知模型與語(yǔ)言編碼中的工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