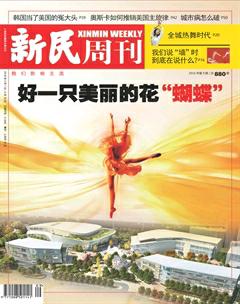上海曹楊新村經驗:重塑花園城市社區
中學、小學、電影院,還有圖書館、公共浴室、菜場、醫院,甚至大禮堂和必要的政府管理部門——房管所、公安派出所,在整個大型社區中的配置,都經過巧妙核算,分布在合理的區域。
“曹楊新村好風光哦,白墻壁,紅屋頂,石子路鋪得平,哎喲走路真稱心……”當年一曲楊柳青小調曾傳唱上海。中國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經歷了整整65年的歲月變遷,從規劃設計,到建設五角星型社區布局的曹楊一村,再到多次加建、擴建和改建,從一村、二村到五村……八村,乃至2010年代建造的商品房,各種富有年代感的住宅匯聚曹楊環浜周遭。
當歲月進入2016年,曹楊新村更新項目已列入上海中心城區城市更新試點,打通環浜綠地岸線,整體改造開發曹楊一村等方案,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上海歷史建筑研究專家婁承浩告訴《新民周刊》:“住宅街坊設計,過去積累了許多經驗,有成功實例,那就是‘大開放,小封閉,當然局部有圍墻,比如曹楊新村。”
老曹楊煥發新活力

曹楊一村外的小路。攝影\姜浩峰
取曹家渡到楊家橋之間的一片農田,打造屬于工人階級的宜居新村,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上海市市長陳毅做出的一個重大決定。
于是,1951年,曹楊一村開始興建。在具體規劃之前,有關方面曾邀請即將入住的居民——普陀區工人代表座談,充分聽取意見,確定建筑式樣和設備標準。
曹楊新村首期工程完工時,共建成樓房48幢,計167個單元,建筑面積32366平方米。從市區的曹家渡到郊區楊家橋的公路稱作曹楊路。因為這個大型社區靠近曹楊路,所以定名為曹楊新村,首期完工的住宅,就稱為曹楊一村。根據當時的住宅分配標準,新建住宅總共可安排1002戶居民,所以也被人稱為“1002戶工程”。
之后,除了在曹楊地區繼續建造工人新村外,上海市政府還分別安排在江灣、浦東、徐家匯等地,分九個基地建造大型社區,我們今日所見的楊浦區的鳳城、鞍山、控江、長白新村,浦東新區的嶗山新村,徐匯區的日暉等新村,都是繼曹楊新村之后建造的。獨特的新村文化也就此在上海形成并開始興盛。
同濟大學城規學院副教授朱曉明曾無數次在曹楊新村徜徉,令朱曉明訝異的是,當年百廢待興的上海,竟未采用蘇聯的軸線對稱、空間圍合,紀念性強的大街坊布局,而是運用美國上世紀20年代提出的“鄰里單元”理念:至少10%的社區土地為公共開放空間或公園;最多每隔3棟樓,必有一處敞闊的公共空間。曹楊一村以小學為核心,以600米的服務半徑布置街坊,五六分鐘步行范圍內即可享受各種公共配套設施。這是如今許多新開發樓盤所罕見的。

曹楊新村。攝影\姜浩峰曹楊一村經歷了六十多年風霜。攝影\姜浩峰
然而,歲月變遷,曹楊新村老了,舊了,特別是一村,即便曾經翻修特別是在外墻立面等處做了粉飾,卻難掩歲月滄桑。當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大媳婦成為了中老年人,上海工人階級心目中曾經的住房標桿,顯得似乎與時代接不上軌了。
2015年下半年,媒體披露,對于曹楊新村,普陀區提出4項更新策略。第一,將在歷史保護建筑曹楊一村改造過程中,借鑒靜安區東斯文里等經驗,通過“整體開發”模式進行功能置換;第二,將完善公交線路,在曹楊五村、桂巷新村等居住區入口設置站點,接駁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滿足老齡化需求;第三,將提升住宅品質,在一村、七村,計劃采取加層、擴建改造等方式,推進住宅成套化;第四,將設計之初是開放式后來封閉了的環浜通道重新打通,將連續開放岸線增加到約1500米長,在居住小區內部打造親水平臺,拆除違章建筑,并分時段開放門禁,保持通達,而對于環浜邊的單位,也準備打通圍墻,設置步道或慢行步道,還將搬遷一部分單位。
此規劃來自之前的摸底。從曹楊新村目前的狀況來看,現總用地2.14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超過13萬人。曹楊新村街道辦事處調查的結果顯示,從曹楊新村老年人分布年齡特征來看,其中最多的是60歲到65歲的老年人。從入住的人群結構分析,當年的勞模、先進工作者已所剩無幾,大量城市困難戶、外來打工者來到這里。同時,區域內缺乏開放空間,住房改造及設施增配擠占原有開放空間,建筑密度高。三是居住環境品質不高,老式居住小區內人均住宅面積低于20平方米,存在部分違章建筑。城區道路也被停車占據,導致高峰時段擁堵嚴重。“從居民調查結果來看,居住建筑滿意度和居住環境滿意度最低,分別為31%和27%,是居民改造呼聲較為迫切的兩大類矛盾。”曹楊新村街道辦事處相關人士指出。
從過往歲月探究未來
如何改造好曹楊新村,其工作方式大可以從曹楊新村的誕生來尋找未來發展的方向。
舊式里弄、新式里弄……人們印象中的上海民居,源于舊上海的風情。1990年代的8分錢上海民居郵票,就是典型的青磚石庫門里弄畫面。這種里弄,如今還能看到,比如位于陜西南路建國西路口的步高里,就是1930年代法國開發商建造的民宅,然而弄堂口卻又是顯眼的中國式牌樓。還有建于1939年的上海新村,位于如今的淮海中路1487弄,三層坡頂、局部有著簡單幾何圖案裝飾的房子,雖然不是花園洋房,但是每幢樓都有小陽臺和小花園。這類上海民居,不勝枚舉。
在一些人眼里,普陀區是城市的“下只角”,工人新村屬于當年國家分配住房,顯得簡陋,檔次不高。特別是采用水泥預制板等現代建筑材料,規整地一排排連起這個超大型的居住社區,是否具有美學價值?在當下又是否有回顧它的必要呢?在曹楊新村改造被提上議事日程之際,其實去回顧梳理此類問題,尤其必要。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院的張松教授說,曹楊新村是當年政府規劃、市民宜居的典范,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是另一類上海概念。親水,有人情味兒,有點兒符合霍華德“花園城市”的設計理念,城市中帶點兒農村的味道,生態環境和人居氛圍合理結合,這就是曹楊新村。它是適合大多數普通人生活的居所,生老病死的歲月,悲歡離合的故事,同樣在此地發生,只是不需要拿到銀幕上去表現,平常日子而已。
在張松眼里,原本的上海民居,無論是江南水鄉朱家角,還是后來法租界的石庫門里弄,都是隨著城市本身的肌理,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出自完整規劃,卻又如此有人情味的新村,曹楊新村堪稱首次。其實,在1940年代國民政府的“大上海計劃”第三稿中,就規劃有許多類似的社區、小城,計劃中的大上海正是由許多這樣的小城連綴起來的大都市。只是后來戰亂頻仍,“大上海計劃”被束之高閣。而曹楊新村的建造,某種程度實現了當年大上海計劃設計師的理念。
城市似花園
曹楊新村,是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后規劃實施的,當年陳毅市長親自選址真如鎮東廟前村進行開發,預留用地北可接真如鎮,南可接大夏大學,也就是如今的華東師范大學。這是新中國第一次采用現代建筑材料,也就是那些工業化程度高的東西,在整體規劃后施工建造的社區。
在建筑規劃領域,人們普遍認為,使用現代建筑材料,只能制造火柴盒子般的居所,無聊、無趣。而事實上并非如此。當記者走入曹楊一村,一種和新小區似曾相識,卻又截然不同的感覺——兩層、三層的小樓疏疏落落,花花草草點點染染。小廣場,晾衣區域,都緊湊又合理地布局著。曹楊新村一期工程的規劃設計者正是張松的前輩,當時的“海歸派”、同濟大學的金經昌教授。道路分級分類,住宅成組成團布置,在爭取好的朝向的同時,又通過規劃手法打破行列式的單調,也巧妙避開了封閉式小區必然的堵塞,這就是金教授規劃的巧妙。
從曹楊一村最中心的楓橋步行到周邊,往南,五分鐘,有曹楊電影院、曹楊商場;往西,五分鐘,有普陀區中心醫院;往北,三分鐘,有朝春中心小學;往東,五分鐘,有菜市場。中學、小學、電影院,還有圖書館、公共浴室、菜場、醫院,甚至大禮堂和必要的政府管理部門——房管所、公安派出所,在整個大型社區中的配置,都經過巧妙核算,分布在合理的區域。
沿著曹楊環浜走一圈,可以看到金經昌設計的曹楊新村,把原生河道以及河濱巧妙組合在綠化系統中,每幢房屋附近均有小片綠地,又集中安排一些成片的大綠地和草坪。從空中俯瞰曹楊一村,是一個五角星的形狀。新村內道路分主次兩類,主要道路寬21米,支路寬12米,將新村的各個角落網絡起來。
這就很符合霍華德的花園城市理念。1898年英國學者艾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的花園城市概念,要把城市生活的一切優點和農村的美麗、方便、福利統一結合。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霍華德還專門做了一個花園城市的圖解方案,他的花園城市人口只有3.2萬人,占地400公頃,周圍有2000公頃提供農業生產用的永久性的綠地。當然這座城市太小了,3.2萬人的入住規模,在上海只能算個中型社區,而如今擠進十幾萬人,確實顯得更為擁擠,顯得并不那么宜居了。怎樣讓這一規劃人口3.2萬規模的社區,能讓十幾萬人住得舒服,是本次曹楊新村改造應該重視的大問題。
回看霍華德的構想,他想到了一個根本點,就是把城市的優點和鄉村優點結合起來,使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這就是花園城市。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物質文化水平需求的提高,對居住環境也有了更多的思考與要求。盡管現代社區所具有的環境要素仍然保留,但其內在結構已遠遠落后于時代了,更落后于人口規模。如何改造與開發,如何讓花園城市社區理念繼續保留,又適當當今,確實是個難題,但難題必須解開。
當年百廢待興的上海,竟未采用蘇聯的軸線對稱、空間圍合,紀念性強的大街坊布局,而是運用美國上世紀20年代提出的“鄰里單元”理念。
親水,有人情味兒,有點兒符合霍華德“花園城市”的設計理念,城市中帶點兒農村的味道,生態環境和人居氛圍合理結合,這就是曹楊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