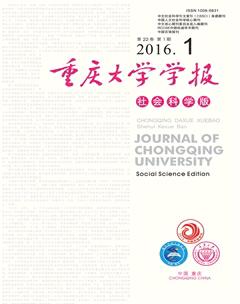城市內部因素對中國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影響








摘要:文章從城市主體行為出發,結合城市生產率、城市居民稅負等構建城市人口解釋模型。基于2008-2011年全國101個代表性城市數據,利用殘差分離、門檻回歸技術展開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城市人口規模與城市生產率、城市便利度呈正向關系,與居民稅負、征地成本呈負向關系;城市內部因素影響城市人口規模的路徑為“影響因素—城市房租水平—城市人口規模”,城市生產率具有決定性影響;城市生產率、城市便利性對城市人口的影響,越過人口規模門檻后會發生結構性變化;中國沿海三大都市圈中城市人口規模的主要影響因素迥異。
關鍵詞:人口規模;征地成本;生產率
中圖分類號:F29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
10085831(2016)01004010
一、引言及綜述
當今中國,城鎮化作為載體和平臺,在承載工業化和信息化發展、帶動農業現代化方面發揮著基礎性作用。目前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3.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6%左右,這低于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與中國相近的發展中國家60%的平均水平。那么,人口是否有序向城市轉移集聚,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及其影響機制如何,在政策實踐上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人口經濟學及城市經濟學文獻中,城市人口規模是指生活在一個城市中的實際人口數量。引導人口向城市有序集中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主要方向,對經濟福利有重大影響。20世紀90年代啟動房地產市場改革以來,中國城市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率大幅提升。城市是否達到其最優的城市人口規模曾是判斷城市有序擴張的一個思路。
最優城市人口規模往往被認為是社會人均社會福利最大化[1]、生產成本最小[2]時對應的城市人口規模。但由于各個城市規模與自身資源稟賦、區位特點、城市形態均有很大關系,突出的異質性使判斷城市人口規模是否達到最優不易實現,于是學者們轉而討論影響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重要因素。
影響城市人口規模的重要因素的理論研究主要從城市土地利用均衡、城市集聚經濟性、城市產業組織三個維度展開,具體而言:(1)城市土地利用均衡。重點考察地租在城市均衡中的關鍵性作用,并提出Alonso-Mills-Muth單中心城市均衡結構框架[3]。隨后在此基礎上用馬歇爾外部性概念進行綜合,提出多城市土地利用一般均衡模型[4];(2)城市空間集聚經濟性。重點從公共產品、市場機制考察城市空間集聚。城市人口擴張規模將主要由市場機制起作用[4],可由交通的擁擠程度和生產商規模[5]、邊際地租等于薩繆爾森公共物品支出[1]、人均資源成本邊際增加等于邊際資源節約[3]、城市總成本—總收益最優[6]等條件決定;(3)城市產業組織。Dixit[5],Abdal-rahman和Fujita[7],Henderson等[8]把城市產業分為最終產品產業、中間產品產業,從壟斷競爭角度出發構建了城市發展模型、城市產業結構演進模型、基于D-S的城市模型等框架,城市間交互作用凸顯了市場配置的缺點,因而需要適當的城市計劃[9]。基于城市間貿易、固定的農業內陸和地理的內生性,探討了基礎設施投資與最優城市規模增長關系[10-11]。另外還有從制度因素、城市生活質量、城市網絡因素等視角展開的研究[12]。
中國城市人口規模的實證研究主要從城市人口規模比較研究、影響因素兩方面展開。大量的文獻研究表明,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的城市體系,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偏小,尤其缺少處于100萬~1 200萬人口區間的城市[13-15]。城市人口規模分布基本符合zipf分布,中國城市間規模差距不足[16]。影響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因素主要是人均實際收入[13],人口遷移管制和土地制度不完善[17],地理位置、交通條件、城市化水平及經濟水平[14-15]。
從現有文獻看,關于城市人口規模的研究還存在改進空間。(1)集聚經濟的馬歇爾外部性解釋邏輯下常常遺漏土地利用因素。主要基于關聯產業聯系、共享設施和勞動力市場、知識溢出進行分析,從集聚經濟的分析重視空間區位的均衡,卻忽視了土地因素。(2)產業組織維度常常忽視城市內部的居民主體行為。由于重視產業間最優利潤均衡,而缺少對居民主體行為的分析,對城市發展的研究往往側重于產業區位尤其是工業區位的確定,卻忽視居民、商業區位確定。(3)提出的土地利用模型具有土地產權私有化制度前提。Alonso-Mills-Muth單中心城市均衡結構、多城市土地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均植根于歐美土地產權私有化的制度前提,進而在這一制度前提下展開地租投標。中國的土地市場所有權國有的特點與歐美國家土地私有化制度有很大差異。(4)忽略了城市內部因素的交互作用。最新的研究顯示,大城市生產率上的優勢會持續減少,需要由新工作創造和創新來補充,城市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在城市發展中有基礎性作用,決定城市人口規模及其制度特征[18]。這意味著,將城市的集聚經濟、產業組織、土地等具體因素融合成綜合反映城市總體情況的城市內部影響因素,如生產率、便利性、稅收負擔,有利于從微觀上理解城市人口規模擴張過程。
本文試圖回答,在中國土地市場化程度較低、戶籍分割、社會保障分類異質性背景下,城市人口規模擴張受到的影響有多大?本文嘗試從城市政府與居民行為互動等視角,融合成城市吸引居民移動的吸引力(生產率、便利性)、排斥力(城市居民稅負)等微觀內部因素[18-19],審視中國城市人口規模擴張。引入城市生產率
即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便利性在城市生活、工作的綜合便利性程度,將通過殘差分解找出便利性。、居民稅負即居民支付的稅率,以測量居民的稅負程度。等城市內部因素,考慮征地及土地整理費用,構建一般均衡模型,并結合2008-2011年中國101個代表性城市的微觀面板數據,使用Threshold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進行相對系統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全國范圍內,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產率,城市人口規模擴張關鍵變量是房租水平;生產率、便利性對于房租及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隨著跨越人口門檻后發生顯著的結構性變化。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研究的可能創新點體現在:其一,從城市居民和政府行為互動這一新角度出發,并引入了反映中國土地市場的征地成本、土地整理費用等變量,探討了土地市場與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內部機制;其二,探討了各內部因素對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影響是否存在結構性變化。
二、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理論分析
參考Desmet和Rossi-Hansberg[19]的城市福利分析框架,引入中國國情中特有的征地支出、土地整理費用等因素,本文構建基于內部因素的城市人口規模理論模型,得出理論假設作為實證研究的出發點。
考察標準單中心城市,包括兩類主體:城市居民和城市政府。城市擁有工人Nit(即城市人口),利用資本K和勞動H投入生產,城市i時期t生產函數為Yit=AitKitHit,城市生產率為:Ait=yit/(kithit),其中k、h表示人均資本、人均勞動水平。一階條件有:
Yit/Hit=(1-θ)Yit/Hit=wit(1)
Yit/Kit=θyit/kit=rit(2)
其中,w、r為工資、資本利率。
居民是城市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城市中心工作。上繳稅收后,根據收入水平、租金支出等決定居住區位。依據Desmet和Rossi-Hansberg[19],居民效用來源于消費(C)、閑暇時間(1-hit)、城市便利性(γi)。而居民總收入withit,等于稅負withitτit、房租Rit、通勤支出Tit 、消費(Cit)之和,面臨的優化問題為:
基于城市均衡狀態效用式(9),得出以下兩條推論。
假說1(平均地租ARit=kN1/2it/(3π1/2)+v,則有式(10):log(Nit)=2log(ARit-v)+ρ1,其中ρ1是常數,征地成本在現實中占比很小。城市總通勤成本為式(11):TCit=∫(Nit[]π)1[]20(2πd2)d(d)=2[]3[SX)]π-1[]2(Nit)3[]2[SX)],可知城市人口規模信息可主要由房租載荷解釋,城市總通勤成本與城市人口呈3/2次關系,假說1成立。):在不存在重大人口政策沖擊條件下,城市人口(Nit)與房租(ARit)呈正向關系,城市人口信息可主要由房租來解釋。
假說2:城市人口規模(Nit)與生產率(Ait)、便利性(γit)、征地成本(vit)呈正向關系,與居民稅負(τit,也可用git表征)呈負向關系。
從式(9)可知,u-隨著Nit增加而減小,隨著Ait增加而增加,隨著γit增加而增加,隨著git增加而減小,隨著v增加而減小,有假說2成立:
假說1、假說2說明了生產率、便利性的整體提高將促進城市人口規模擴張,而居民稅負將抑制城市人口規模擴張,影響城市人口區位選擇的關鍵性中介變量是房租。當城市發展階段處于城市集聚效應倒U型曲線的左側時,則生產性、便利性對人口擴張的影響將遠遠超過居民稅負影響;處于城市集聚效應倒U型曲線的右側時,則居民稅負將有效抑制城市人口增長,使城市人口規模不至于無序膨脹。
三、研究設計及數據
(一)計量模型設定
由于生產率、便利性、居民稅負均為綜合性因素,簡單地利用平均通勤時間來衡量便利性很可能存在偏誤,而居民稅負很難用某一特定的指標來衡量,采用殘差分離出內部因素更為合理。故本文將先用索洛剩余法估算生產率,隨后通過殘差分離的方法分離出便利性和居民稅負。利用提出的假說,結合Bai [20]、Desmet和RossiHansberg[19]的殘差分離和參數估計方法,確定以下四個回歸模型:
所有數據均取對數后進入模型。其中,式(13)將城市人口規模信息載荷到房租水平上,式(14)將城市人口規模分離成生產率解釋部分(即β1lnAit=lnN-it(Ait))和其他因素解釋部分(ε1it=ε1~(git,γit))。而式(15)對比式(8),可知ε2it絕大部分是稅負lngit信息量,極少部分與ε1it=ε1~(git,γit)有關,可以定義ε2it=ε2~(git,ε1~(git,γit)),這就分離出稅負因素(ε2it)。對照ε2it=ε2~(git,ε1~(git,γit))和ε1it=ε1~(git,γit),可以知道ε1it=ε1~(git,γit)主要是稅負因素(git),而ε1it=ε1~(git,γit)反映的主要是便利性因素(γit)。另外,lnτ~it=β2lnN~it(Ait)主要反映生產率因素(Ait)。核心回歸模型(16)中房租作為因變量,對生產率、便利性、稅負三大因素進行回歸,從而確定各因素對它的影響情況。房租將作為三大因素與城市人口規模之間的中介變量,便于討論三大因素與城市人口規模之間的深層次關系。具體從租金水平、城市人口規模引起結構性變化、城市所處區域范圍三個維度展開實證,采用分位數回歸、門檻回歸估計方法捕捉詳細信息。預計β3>0,β4>0,β5<0,β6=2。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
由于2008-2011年租金數據獲得性的限制,只能找到全國101個地級以上城市樣本。但是這些城市樣本中,已經包括了全國各省會城市、各省經濟大市、沿海三大都市圈內所有地級以上城市,所以采用101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對全國城市人口擴張具有明顯的代表意義。基于此,我們將采用101個地級以上城市2008-2011年的數據展開實證研究。數據來源于2008-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租金數據來源于《中國房地產統計年鑒》(2008-2012)、中國禧泰房地產數據庫,取對數后進入回歸模型,采用stata12軟件分析。變量具體說明見表1。
四、實證研究與討論
(一)城市人口規模與房租的關系
房租與城市人口規模關系顯著,房租增速相對于城市人口規模較慢。表2是估計式(11)進行的回歸,通過hausman檢驗可知固定(FE)效應模型效果優于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房租參數為正,符合我們的預期。但是其參數值處于(0,1)區間內,參數值小于式(7)所揭示的2和美國實證結果2.096 4[19]。這說明中國城市房租對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程度小于理論均衡水平和美國實證結果。人口越多,則對應的房租越高,這符合直觀和理論。相對于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城市租金水平提升速度較慢,主要由于目前除了少數特大型城市,大多數中國城市尚處于城市集聚效應的倒U型曲線的左側階段[21],城市人口規模離均衡水平尚有差距,具有可觀的發展潛力。房租對城市人口的彈性為正,解釋力較強,表2驗證了假說1。后續可以將城市人口規模信息載荷到房租變量上,以便于進一步解釋內部因素對城市人口的影響。
城市集聚的階段性特點使得房租與城市人口規模關系顯著。城市集聚時生產率將提高,引起收入上升進而吸引人口進城,最終導致投標租金推高房價。房租對人口的區位決策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人口集聚形成的投標租金競爭效應、考慮房租后的實際收入財富效應,這兩個效應將決定人口是否停留在城市。由于租房或購房的支出占居民總支出的最大比重,人口在進行區位選擇時,房租是關鍵變量。因此,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信息可主要由房租承載。
理解中國城市的房租,還需要討論土地市場與房租的關系。中國土地市場通過兩條途徑影響房租:征地過程、招拍掛過程。其一,通過征地協商確定征地成本。目前,征地方不是土地使用方而是地方政府,處于壟斷和優勢地位,而分散的農村居民具有壟斷競爭特點,處于談判劣勢地位,現實中征地成本不是通過市場機制而是談判形成的;其二,地方政府通過招拍掛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給使用單位。兩個環節先影響房租進而影響城市人口規模。現實中,征地成本占拍賣價的比例較低,建設用地的壟斷性供給對城市人口規模影響明顯。
(二)生產率、便利性、稅負對房租的影響
利用Bootstrap法進行混合OLS回歸、RE-GLS和門檻回歸,發現城市生產率、城市便利性對于城市人口均存在著單一門限效應。綜合方程(5)-(8)可得如下結果。
第一,全國范圍內,房租受生產率的主導性影響,便利性對城市房租水平的影響程度有限,影響路徑為理論模型所揭示的“因素—城市房租—城市人口規模”,驗證了假說1。
整體上,城市房租水平與城市生產率、城市便利性呈正向關系,而與城市稅負呈負向關系。方程(5)通過檢驗,其結果顯示,城市生產率(Ait)、城市便利性(γit)、城市治理水平或稅負(git)三大因素的回歸系數值β3、β5、β4分別為5.628、-0.108、0.300,說明城市房租隨著城市生產率、便利性提高而提升,而隨著稅負提高而下降,城市生產率對房租水平的影響是決定性的,這符合直觀和理論預期。這樣的結果主要是由中國所處的城市化階段和城市管理水平造成的。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目前處于城市集聚經濟倒U型曲線的上升階段,高生產率帶來的高回報是吸引人口進城的主要動力。城市空間面積的無序擴張、城市管理的相對滯后,使居住適宜、交通可達性等便利性難以顯著影響城市人口規模擴張。加上戶籍管制,使城市勞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務差距明顯,容易造成半城市化、被城市化問題,使包括新生代轉移人口的大量勞動人口難以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市民化。
第二,由于城市產業形態變遷,生產率、便利性對房租的影響機制將以121萬~168萬為門檻區間發生結構性轉換,超越門檻后迅速攀升。
為了減少內生性和估計誤差,引入生產率、便利性的滯后一期、滯后二期。方程(7)、(8)顯示,生產率、便利性與房租的關系存在單一門檻關系。其中,生產率與房租的關系以城市人口121.89萬為門檻值而發生結構性變化,門檻前后的生產率相對于房租的彈性分別為3.702、8.948,敏感度將提升1.42倍。在門檻值前后,便利性相對于房租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62、1.872,以城市人口168.4萬為門檻值發生結構性變化,靈敏性提高了2倍。當跨越門檻值后,生產率每提高1%,則房租將提升8.948%,當便利性提高1%,則房租提升1.872%,房租的增長速度快于生產率、便利性。這主要因為跨越121萬~168萬人口區間后,城市的集聚效應往往將帶來經濟形態變遷。城市區位中的經濟形態將從以初級制造業為主,逐步轉向以技術型制造業、服務業為主,產業形態變化對生產要素的集聚、生產率、便利性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具體體現為租金投標競爭程度加強。
第三,伴隨房租的上升,生產率、便利性等因素對于房租的影響分別呈現“S”、倒“U”型變化形態。結合表4和圖1可得如下結論。(1)生產率對于房租水平的影響強度呈“S”型發展形態。通過觀察表4中β3數值和圖1,可知生產率對房租水平的彈性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但保持在與前50%分位數城市不同的高位水平,呈現“S”型。處于50%~75%分位數區間的城市,保持著最高彈性6.562。位于房租75%~100%分位數區間的城市如北上廣等城市,房租相對企穩,生產率影響房租的強度逐漸下降。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武漢、沈陽均處于規模效率遞減階段[21],說明其城市人口規模進入城市集聚效應的倒U型曲線的右側下降階段。而目前人口規模擴張快速的城市是處于50%~75%房租區間的二線城市,這些城市生產率在上升,但是其生產率相對于房租的彈性超過全國水平,容易陷入“未發達,房租先升”的困境,發揮集聚經濟的同時需有效控制房租上漲速度,才可能使其競爭優勢不被高企的房租和房價所抵消。
(2)隨著城市房租水平的上升,城市便利性對于城市房租水平影響呈倒“U”型。整體上,城市便利性對于城市房租水平的影響強度先上升而后下降。處于75%~100%房租區間的城市,包括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便利性對于城市房租水平的影響強度最小,表明目前一線城市的便利性邊際增加對人口擴張的影響很有限。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國人口管制在這些城市最為嚴格,另一方面已經進入了集聚經濟倒U型曲線的均衡或下降水平,便利性的邊際增加很難促進人口擴張。而處于0%~25%、25%~50%房租分位數區間的城市,便利性相對于人口的彈性較大。因為這些城市尚處于城市集聚效應的倒U型曲線的左側上升階段,城市便利性的邊際增加將明顯促進城市的人口擴張。
(三)內部因素對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影響
綜合“內部因素—房租—城市人口規模”實證研究,可知:全國城市中,生產率是推動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決定性因素,便利性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人口規模擴張,稅負尚未體現出相對有力的抑制作用。其中,城市生產率增長1%,則城市人口規模則上升0.829%。生產率對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強度是便利性影響強度的18倍。
這主要因為城市具有集聚效應而農村缺乏集聚效應,城市平均產出相對較高,單個家庭總收入高。城市生產率、便利性引起城市人口規模擴張,而城市居民稅負會抑制人口規模擴張,三者的凈效應最終決定城市人口規模。三個力量此消彼長構成了城市規模效率的倒U型曲線變化。城鎮化處于曲線左側時,居民收入的增速快于居民的支出。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將出現集聚負外部性,具體表現有:居民稅負提高和便利性下降,生產率帶來的回報被集聚的負外部性逐漸抵消,支出尤其是房租高企降低實際財富,城市人口邊際增長率逐漸下降甚至為負。
生產率、便利性對城市人口規模影響強度的巨大懸殊,表明中國的城市化正在經歷生產率促進的階段,城市內部的軟硬件建設已相對滯后,亟需加強城市管理。按照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當城鎮化率達到40%~60%的時候,標志著城市進入成長關鍵期,“城市病”進入多發期和爆發期,城市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四)城市群背景下房租與城市三大因素的關系
生產率對珠三角、長三角城市群城市人口規模擴張具有決定性,便利性對京津冀城市人口擴張更重要。
方程(9)-(11)結果顯示,生產率相對于城市人口規模的彈性最大,這說明生產率對于珠三角、長三角都市圈的城市人口規模擴張具有決定性影響,但是京津冀都市圈的城市租金與生產率的關系不顯著,便利性相對于租金的彈性最高。可能的原因是:市場機制在珠三角、長三角城市中發揮作用的時間較長,行政層級相對平行。而京津冀由于存在中央、首都、直轄市、省、市多重行政層級,同時承載著保障首都的多項功能,導致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相互纏繞,兩大直轄市強烈的“空吸”作用、輻射帶動力弱導致出現孤島型經濟,京津冀都市圈的中等城市發育緩慢,難以實現經濟分工合作。加上北京、天津市歷史上單中心發展模式的慣性因素疊加影響,使京津冀城市群整體的生產率潛力無法有效釋放。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均處于規模效率遞減階段[21],倒逼城市群甚至跨城市一體化協同發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針對缺少從城市內部展開城市人口變化研究的現狀,本文引入了中國土地市場中的征地成本、土地整理費用等變量,整合成生產率、便利性、居民稅負等綜合性內部因素,構建了基于城市內部因素的理論模型。以具有代表性的101個地級以上城市為樣本,研究內部因素對中國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機制,結論如下:(1)房租與城市人口規模關系顯著,房租增速相對于城市人口規模較慢。全國范圍內,房租受生產率的主導性影響,受便利性的有限影響。影響路徑為“內部因素—城市房租—城市人口規模”。(2)生產率、便利性對房租、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機制,將以121萬~168萬為門檻區間發生結構性轉換,超越門檻后將迅速攀升。生產率、便利性對房租的影響分別以人口121.89萬、168.4萬為門檻值而發生結構性變化,跨越人口門檻值后,影響強度分別提升了1.42倍、2倍;隨著城市房租水平的上升,生產率、便利性對于房租水平的影響強度分別呈現“S”型、倒“U”型發展形態。(3)生產率是城市人口規模擴張的決定性因素,便利性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人口規模擴張,稅負尚未體現出相對有力的抑制作用。其中,城市生產率增長1%,則城市人口規模則大約上升0.829%。生產率對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強度大約是便利性影響強度的18倍。(4)生產率對珠三角、長三角都市圈城市人口規模擴張具有決定性,便利性對京津冀城市人口擴張更重要。
基于以上認識,有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基于人口基數、房租等重要指標進行城市分類管理,創新城市管理機制,加強城市內部結構的優化完善。根據人口規模和房租水平,對城市進行分類依據研究,建議區分121萬以下、121萬~164萬、164萬~352萬、35萬~932萬[21]、932萬以上人口城市,并實行差異化的城市人口政策。。房租高位城市需要提高城市便利性以降低房租增長速度。處于租金75%~100%分位數區間的城市,重點是提升城市公共交通設施銜接,治理城市污染。處于租金50%~75%分位數區間的城市,重點是加快城市公用交通設施建設、科學規劃城市內部結構。處于租金0%~50%分位數區間的城市,重點是產業有序發展、提高生產率以吸收人口集聚。改進城市空間結構的利用方式,盡量弱化城市人為隨意分區,鼓勵城市混合應用,以減少城市交通負擔,提高便利性。
其次,逐步推進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現行的土地征收和招拍制度將由工業化、城市化和與之伴隨的農業商品化所帶來的絕大部分土地收入截留,原本這一收入可以為農民特別是郊區農民完成城市化變遷提供扎實的資本基礎,也可為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供所需財力和激勵。因而有必要探索漸進式土地制度改革,理順農民、政府、用地單位等各類主體的利益機制。在符合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下,按市場需求規劃和建設,確立市場在城鎮化中的基礎性配置作用,這易于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實現包容性城鎮化。
再次,加快城市群的內部要素流動機制創新,加快基于戶籍制度改革的公共產品均等化進程。加強城市群現代產業體系輪換和對城市人口規模和結構的動態監測,制定個性化人口政策,優化城市群勞動力結構,促進城市人口與產業良性互動。推進戶籍制度逐步向居民制度轉變,梳理舊有的基于不同身份的公共服務產品供給,加快城市人口身份同質化,推進基于城市居民同質化的公共產品均等化進程。
最后,建立并完善城市群內的城市發展協調機制,適時研究跨城市群的機制創新。城市規模效率(即聚集經濟)的產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如完善的市場體系、高效的社會管理制度、原有的綜合能力基礎等。需要結合中國城市群實際和國外成功經驗,探索多種有效的跨區域城市發展協調模式。促進跨區域城市協調發展,建立健全市場尤其是勞動力市場開放機制,推進統一、開放、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推進跨區域公共產品均等化進程。參考文獻:
[1]ARNOTT R.Optimal city size in a spatial econom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79,6(1):65-89.
[2]EVANS A W.The pure theory of city size in an industrial economy[J].Urban Studies,1972,9(1):49-77.
[3]MILLS E S.Urban economics[M].North-Holland: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1987:321-356.
[4]FLATTERS F,HENDERSON V,MIESZKOWSKI P.Public goods, efficiency,and regional fiscal equalization[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4(3):99-112.
[5]DIXIT A.The optimum factory town[J].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3(6):637-651.
[6]DURANTON G,PUGA D.Nursery cities:Urban diversity,process innovation,and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6):1454-1477.
[7]RAHMAN H M A,FUJITA M.Product variety,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and city size[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0,30(2):165-183.
[8]FUJITA M.HENDERSON J V,KANEMOTO Y,et 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Japan and China [M]//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Holland: Elsevier, 2004:2911-2977.
[9]PALIVOS T,WANG P.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6,26(6):645-670.
[10]PAPAGEORIOUS Y,PINES D.Externalities,indivisibilities,nonreplicability and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0,48(3):509-535.
[11]PINES D,HAREL A.On alternative urban growth patterns[R].Tel Aviv University,the Eitan Berglas School of Economics,2000.
[12]PINES D.New economic geography’:revolution or counterrevolu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1(6): 9-146.
[13]AU C C,HENDERSON J V.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73(3):549-576.
[14]王小魯.中國城市化路徑與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2010,(10):20-32.
[15]王小魯,夏小林.優化城市規模 推動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1999(9):22-29.
[16]張濤,李波.關于我國城市化相關問題的研究[J].比較,2007,31:20-32.
[17]陸銘,向寬虎,陳釗.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體系調整:基于文獻的評論[J].世界經濟,2011(6):3-25.
[18]DURANTON G.Growing through c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4(6):6-15.
[19]DESMET K,ROSSI-HANSBERG E.Urban accounting and welfar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6):2296-2327.
[20]BAI C E, HSIEH C T,QIAN Y.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6,No. w12755.
[21]王業強.倒“U”型城市規模效率曲線及其政策含義——基于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率的比較研究[J].財貿經濟,2012(11):127-136.
(責任編輯傅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