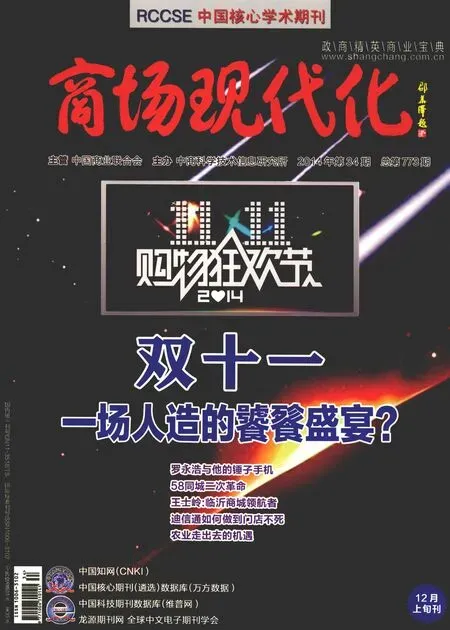員工知識共享研究述評
孫翠艷 張倩



摘 要:由于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不斷推進,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企業管理者越來越重視知識管理在應對挑戰中的積極作用。企業對知識型人才的渴求隨之不斷增強,而知識管理落實到個人層面,即員工之間的知識共享行為。由此,企業對知識共享的關注與日俱增。本文通過對已有知識共享相關研究的文獻綜述,旨在梳理知識共享研究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以此為據,進而對后續研究提出建議和展望。
關鍵詞:知識共享;前因與結果;測量;研究局限
知識管理是一切企業的核心與根本,也是企業戰略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企業的戰略性資源,知識儼然已經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在這個憑借實力以求得市場份額的競爭環境中,企業以擴大規模求得效益的方式已經被市場所淘汰。唯一能夠支撐企業立足于稂莠不齊的競爭市場的,便是企業原本就擁有的知識資源,而知識的來源則是企業各層級的所有員工。然而,個體并無義務貢獻其本身所擁有的全部知識。那么,如何最大限度促使員工將其所擁有的知識為企業所用,即如何促使員工進行知識共享,企業管理者以及學術界的研究者們紛紛對此展開深淺不一的研究,以便為企業獲取知識這一絕對的競爭優勢,從而穩固市場地位。本文首先對知識共享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然后梳理現有文獻對知識共享前因、結果與測量的研究,最后討論知識共享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一、知識共享相關定義
1.知識的概念
作為企業的無形資產,知識不同于其他企業資源,它能夠無限使用。目前,學者們關于知識的界定上尚未達成一致。知識是一種重要的組織資源,為企業在經濟競爭激烈和充滿活力的環境中提供了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它是指由個體加工處理的各種信息。
2.知識管理的概念
隨著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管理已經上升到戰略高度,也是近年來學術界熱議的課題。對于知識管理的界定,學者們也是眾說紛紜。主要定義見下表1。
3.知識共享的概念
知識共享是以知識為基礎的一種行為或活動,它是知識管理的關鍵內容。員工可以通過知識共享進行應用、創新,最終形成企業競爭優勢。迄今為止,學者們對于知識共享的定義可以歸納為個體通過各種方式及渠道與他人分享工作所需的信息和知識技能。
二、知識共享的前因與結果
1.知識共享的前因
知識共享的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兩大方面展開研究。具體如圖所示。
(1)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組織激勵。
①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各類資源傳播的途徑和模式。顯然,如若此類結構不利于知識的傳播、轉移與分享,那么勢必影響個體或團隊的知識共享意愿,從而阻礙其知識共享行為。組織結構從大體上主要區分為集權化和分權化組織結構。學者們對此進行了研究。Kim和Lee(2006)的研究證明,相對分權的組織結構有助于實現知識共享。由于分權化能夠促進員工之間的互動,因而促使知識共享行為頻繁出現。所以,組織應該建立有利于員工充分進行互動的組織結構,從而促進知識共享行為的產生。
②組織文化
關于組織文化對知識共享的影響已經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證實,不同的組織文化對于知識共享的作用截然不同。強調個人競爭的組織文化會阻礙知識共享,而鼓勵團隊合作的組織文化則有助于建立信任,從而促進知識共享(Willem&Scarbrough, 2006)。員工對組織知識共享文化的感知(如員工信任等)和知識共享的意愿正相關(Connelly&Kelloway,2003)。因此,整個企業的文化以及氛圍與個體的知識共享行為密不可分。
③組織激勵
知識共享作為角色外行為,只有在個體得到一定激勵的情況下方可產生。眾所周知,績效考核是企業管理者激勵員工的一種常用且重要的方式。文鵬等(2012)、趙書松和廖建橋探(2013)討了績效考核目的對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任務績效抑制知識共享行為,而關系績效能夠孵化知識共享行為。然而,當今企業激勵制度的不健全已然成為知識共享的一個重大障礙。Bock等(2005)發現外部獎勵與員工的知識共享意愿呈現負相關關系。由此可知,激勵不當不僅不會催生個體知識共享行為,甚至可能出現副作用,影響員工正常工作績效。
(2)內部因素
內部因素主要涉及個體動機和人際關系。
①個體動機
動機往往是行為產生的初始驅動力,而知識共享的動機極大程度上與其對該行為發生的成本和收益的預期密切相關。學者們基于社會交換理論對二者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預期收益與知識共享正相關,而預期成本則與知識共享負相關。Kankanhalli等(2005)曾指出,員工預期進行知識共享所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越多,他們越不容易進行知識共享。
②人際關系
處于企業或團隊中的個體并非獨立存在,他們通常需要與外界或者內部成員進行溝通與交流。那么,個體與外界或者組織成員的人際關系必然影響其行為方式與結果。Thomas等(2003)的研究發現,與其他團隊成員的社會關系也會作用于其知識共享行為。Bakker等(2006)和Srivastava等(2006)發現,團隊凝聚力越強以及授權型領導,即人際關系越密切,那么團隊成員進行知識共享的可能性就會更大。湯超穎等(2011)在探究積極情緒的社會功能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關系中引入隱性知識共享變量并加以實證分析。因此,人際關系對個體的知識共享行為具有重要影響作用。
2.知識共享的結果
相比前因變量而言,知識共享的結果變量的研究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創新上,體現在個人層面就是個體創造力,而反映在組織層面便是組織創新績效。
一方面,王國保(2014)通過對592名企業員工的調查,將知識共享細分為知識收集和知識貢獻,證明二者正向影響員工創造力。朱春玲、陳曉龍(2013)將知識共享作為中介變量,探討了其在高績效工作系統和員工創造力關系之間的影響機制。曹勇、向陽(2014)證明了知識共享在企業知識治理和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作用。
另一方面,王亞洲、林健(2014)分析了知識管理導向(包括知識共享傾向和偏好)對企業績效的影響。Hsiu-Fen Lin(2007)和Ipe(2003)指出,員工進行知識共享與企業創新能力密不可分,進而提高組織創新績效。
綜上所述,知識共享主要對個體和組織的創新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個體和組織層面的績效。
三、知識共享的測量
至今,隨著知識共享研究的不斷增加,學者們也在不斷開發科學合理的測量量表。現有的知識共享量表主要可分為單維量表和多維量表。其中,單維量表主要包括測量行為的量表、測量態度的量表以及測量能力的量表,如Bock&Kim(2002)和Chennamaneni(2006)的知識共享行為量表、Lin(2007)的隱性知識共享量表、Chowdhury(2005)的復雜知識共享量表、Wahect(2007)的知識共享傾向量表、Chow&Chan(2008)知識共享意向量表、Kim& Lee(2006b)知識共享能力量表等等。多維量表可細分為二維、三維和四維,具體如下表2。
由此可見,知識共享測量量表不斷豐富,多維量表逐漸成為重要測量工具。然而,目前學術界并未對知識共享的測量工具達成一致意見,且各測量量表具有一定特有情境,其廣泛適用性還有待考證。
四、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第一,本文所梳理的文獻中,定性研究居多,實證研究相對匱乏。雖然定性研究能夠為我們提供知識共享可能發生的組織環境的豐富和深入研究,但是由于定性研究缺乏一定的實踐驗證,因此,未來需要更多定量研究來幫助我們分析具體問題。
第二,本文所歸納整理的知識共享相關文獻的研究背景大多為西方國家。國內少有的研究也多是對國外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更談不上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對知識共享進行實證研究了,此類文獻猶如珍寶,少之又少。但是,毋容置疑的是不同背景下的知識共享的相關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異。如何將國外的知識共享研究本土化成為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也能為中國本土企業提供切實有效的管理建議和實踐指導。
第三,測量量表直接引用國外量表,不一定適用于中國情境,從而使得研究數據產生一定的偏差。為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后期研究應著力開發適合中國文化背景的成熟量表。
第四,采用上級評價或員工自我報告進行測量,均為單方面測量,不夠客觀和科學且問卷調查數據的收集集中在同一時間段,具有同源性。未來研究應該同時測量主觀和客觀知識共享,進行配對數據分析,增強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同時,在收集數據時,應避免同源誤差,可以分時段進行數據收集。
五、結論
本文通過對已有文獻的回顧發現,雖然知識共享研究現已相對豐富,但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興起以及實踐問題的不斷出現,知識管理仍然是管理者急需重點解決的問題,也是學者們持續討論的熱點課題。一方面,從實踐出發,基于企業戰略,管理者應該進一步加強對知識共享的重視程度,建立有效的員工信任體系,從而促使知識共享的頻繁出現,最終形成強有力的競爭優勢,提高企業競爭力,同時總結實踐中產生的問題,為理論研究提供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另一方面,從理論出發,基于實踐問題,研究人員應將知識共享的相關理論與管理實踐密切相連,針對性地進行研究,為實踐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和保障。綜上所述,有關知識共享的研究仍然有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參考文獻:
[1]Bakker, M., Leenders, R. T. A. J., Gabbay, S. M., Kratzer, J., & Van Engelen, J. M. L. Is trust really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sharing in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J].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2006, 13(6), 594-605.
[2]Kim, S., & Lee, H.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mployee knowledge-sharing capabiliti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3), 370-385.
[3]Thomas-Hunt, M. C., Ogden, T. Y., & Neale, M. A. Who's really sharing? Effects of social and expert status on knowledge exchange within group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3, 49(4),464-477.
[4]Willem, A., & Scarbrough, H.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bias in knowledge shar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J]. Human Relations, 2006, 59(10), 1343-1370.
[5]曹勇,向陽.企業知識治理、知識共享與員工創新行為--社會資本的中介作用與吸收能力的調節效應[J].科學學研究,2014,32(1):92-102.
[6]湯超穎,艾樹,龔增良.積極情緒的社會功能及其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隱性知識共享的中介作用[J].南開管理評論,2011,14(4):129-137.
[7]王國保.面子意識與知識共享、員工創造力關系的實證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17):96-101.
[8]王亞洲,林健.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知識管理導向與企業績效[J].科研管理,2014,5(2):136-144.
[9]文鵬,包玲玲,陳誠.基于社會交換理論的績效評估導向對知識共享影響研究[J].管理評論,2012,24(5):127-136.
[10]趙書松,廖建橋.關系績效考核對員工知識共享行為影響的實證研究[J].管理學報,2013,10(9):1323-1351.
作者簡介:孫翠艷(1990- ),女,湖南張家界人,土家族,廣西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文化創新與人力資源管理;張倩(1988- ),女,廣西桂林人,廣西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戰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