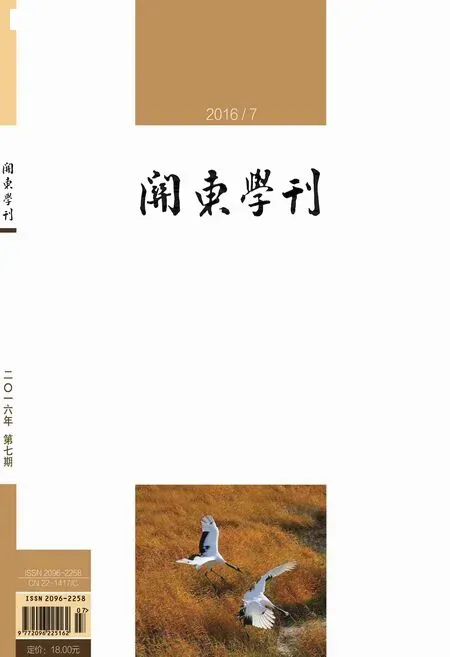東歐的兩種現代性
景凱旋
東歐的兩種現代性
景凱旋
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斯庫將現代性分為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由此揭示西方現代文學、藝術對社會現代性的批判與補充作用。本文對前東歐國家這兩種現代性的研究表明,東歐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矛盾具有自身的特征,表現為現代性的兩個要素進步理念與人的主體性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基于此,東歐的審美現代性強調道德與良知,回歸傳統的超驗世界觀,并將普遍倫理觀念的喪失看作是現代性危機的根源,從而既批判東歐的社會現代性,也質疑西方的審美現代性。
兩種現代性;進步;主體性;道德;審美
一
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考察了西方的兩種現代性,即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這兩種現代性的敘事是互相沖突的。本文擬討論前東歐國家的兩種現代性觀念。東歐國家在文化心理上屬于歐洲,在現代同樣經歷了傳統秩序的解體,同時在上世紀下半葉又采取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其現代性特征與西方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由于東歐現代化道路的失敗,東歐知識分子遭遇的觀念危機要比西方更為深重,因而他們的現代性思考也更富啟示。
如我們所知,在人類歷史上,“時代”是一個很晚才出現的概念,與某種獨特的時間意識有著密切聯系。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先民很早就有時間概念,但那是一種循環往復的自然世界的時間觀。諸如春夏秋冬、黑夜白晝以及生老病死,這些屬于時間性的變化只是與個人相關,不會與社會相關。一個人活在時間里,不會想到自己的生活與前人有什么不同,更不會想到遙遠的未來社會。
然而,古老的時間概念在文藝復興時期被打破,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了對不同時代的關切,將西方歷史分為三個時代,古代與光明相聯系,中世紀與黑暗相聯系,而現代則與復興相聯系。顯而易見,這不是一種自然時間的觀念,而是一種人文歷史的觀念。這種時代的劃分基于一種線性不可逆的時間意識,代表了人類中心主義推崇理性精神,擺脫傳統宇宙觀的思維。正如卡林內斯庫指出:“由于文藝復興是自覺的,且把自己視為一個新的歷史周期的開始,它完成了在意識形態上與時間的一種革命性結盟。它的整個時間哲學是基于下述信念:歷史有一個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現的不是一個超驗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內在的各種力之間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識地參與到未來的創造之中:與時代一致(而不是對抗它),在一個無限動態的世界中充當變化的動因,都得到了很高的回報。”*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21頁。
毫無疑義,現代性是啟蒙理性構想出來的一個時間概念,它基于人類自身對處在一個不可逆時間軸上的現時代的判斷,同時也意味著傳統超驗世界的消退。奧克塔維奧·帕斯就曾指出,現代性是一個純粹的西方概念,而且這個概念不能同基督教分離,因為“它只有在這種不可逆時間的思想中才會出現;它也只有作為對基督教永恒性的一種批評才能出現。”*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63頁。卡林內斯庫則指出:“盡管現代性的概念幾乎是自動地與世俗主義相關聯,其主要的構成要素卻只是對不可重復性時間的一種感覺,這個構成要素同猶太——基督教末世論歷史觀所隱含的那種宗教世界絕非不能相容。”*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11頁。反過來說,時間軸上的歷史是有目的性的,但這個目的不是來自基督教的超驗宇宙圖景,而是來自人類的自覺活動。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現代性就是宗教世界觀的“祛魅”。或者說,現代性的哲學基礎就是人的主體性與進步概念,由此產生出“現代”和“現代性”的概念。
闡明這一構成現代性基礎的時間模式是很重要的,既然現代性是建立在不可逆的線性時間基礎上,理性主義者自然相信,歷史是有方向的,而且是不斷進步的。進步的觀念假定有一個發展的模式,在時間上具有永恒意義,人類主體借助某種規律或原則,通過參與到歷史運動中,即可以創造美好的未來。進步的觀念因而被視為一種普遍主義的毋庸置疑的真理,所有現代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歧都不過是圍繞著何謂進步而展開,正如卡林內斯庫所說:“理性主義的進步概念同對價值觀念普遍與永恒性的信仰絕非不相容。”*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31頁。現代性與進步結盟,后者賦予前者以合法性,這就是啟蒙理性語境下現代性的本質內涵。但問題在于,既然歷史是一種必然的進步過程,人的主體性便不是最重要的,進步與主體性的內在對立使得現代性成為一個充滿分歧的概念。什么是現代性?它到底是指物質領域還是指精神領域?是指政治、經濟還是指倫理、美學?是指進步性還是指主體性?表面上看,現代性似乎是一個統一的概念,實際上卻又包含了許多截然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素。對一些人來說,現代性意味著帶來福祉,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卻意味著帶來災難。
按照卡林內斯庫的闡釋,社會現代性是指科學技術、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市場的產物,包括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中各種核心價值,諸如“進步的學說,相信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的可能性,對時間的關切(可測度的時間,一種可以買賣從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可計算價格的時間),對理性崇拜,在抽象人文主義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還有實用主義和崇拜行動與成功的定向”等等。*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42頁。一般而言,在西方社會,擁護社會現代性的主要是自由主義者,崇尚民主法治、責任政府、開放社會和政治多元,高度尊重契約精神、個人權益和市場競爭。而提倡審美現代性的則以人文知識分子為主,即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以及大學里的人文學者。由于后一個群體的素養、興趣和專業性質決定了他們更關注人性與倫理,因而激烈地反對私有經濟的實質不平等和非正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和科層制,反對資產階級的工具理性、功利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價值觀,以及物欲社會中人的異化、原子化和非人化的傾向等等。總而言之,正是這個群體及其所持觀念構成了反社會現代性的審美現代性。用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的話說,這種沖突反映了“近一百年的反資產階級的文化力圖擺脫社會結構,取得自身獨立”的努力,體現了“文化和社會的激烈機制斷裂”。*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第100頁。
有意思的是,兩種現代性是互相沖突的,又都自稱是“進步”的。如果說社會現代性包含了反對宗教對人的異化,那么審美現代性則主要包含反對金錢對人的異化。按照卡林內斯庫的分類,西方的審美現代性包括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刻奇(kitsch,或譯媚俗)。事實上,社會現代性不僅產生了其文化上的對立物,而且這些對立物之間也是相互抵牾的。它們之間既有流動性,也有重疊性。*“現代主義”一詞范圍很廣,在許多論者那里往往與“先鋒派”同義,有的甚至包括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等。按照卡林內斯庫的分類,現代主義主要指表現主義、未來主義、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等藝術流派,而波德萊爾、卡夫卡、存在主義等則被歸于頹廢主義。除“刻奇”外,所有這些思潮或流派都具有反社會現代性的特征。換言之,審美現代性對變化的崇拜和對權威的拒斥是現代的,而對市場和功利的批判又是反現代的。不過,如果僅就時間意識而言,卡林內斯庫所說的現代主義、先鋒派大體上認同線性的時間觀,而頹廢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刻奇則持相反的觀點,從而構成了各種不同的審美現代性。這里無法充分展開討論,僅以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理論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著名文章作為例證。
在1939年發表的《前衛與刻奇》中,格林伯格以審美現代性反對商業藝術的刻奇(媚俗)品味,其理論正是依據發展與變化的時間觀,認為“現今的資產階級社會秩序并不是一個永恒的自然的生活狀態,而僅僅是一系列社會秩序中的最新階段。”在格林伯格看來,“刻奇”是工業化、都市化和商業化的產物,代表了中產階級享樂和做作的審美趣味:“刻奇是間接經驗和冒充的感受,刻奇依時尚變化,但本質始終不變。刻奇是我們時代生活中所有那些贗品的縮影”,如通俗小說、雜志封面、插圖、廣告、卡通、流行歌曲、踢踏舞、好萊塢電影等。換言之,刻奇的實質是迎合大眾的物質主義,缺乏創作者的主體性。相反地,前衛藝術則代表了現代性的方向,不斷追求擺脫傳統的美學觀,如畢加索、勃拉克、蒙德里安、康定斯基、馬蒂斯和塞尚等人的畫,以及馬拉美、龐德、里爾克、葉芝和喬伊斯等人的文學作品,都體現出藝術的反抗與創新。*Clement Greenberg,“The Avant-garde and Kitsch”,Gillo Dorfles,ed.,Kitsch:The World of Bad Taste,Universe Books,1970,p.116-126.中譯本參見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前衛與媚俗》,秦兆凱譯,《美術觀察》2007年第5期。
進步理念總是隱含著不斷運動的意識,格林伯格由此認為,在崇拜新穎與變化的現代性意義上,前衛藝術體現了對永恒不變的資本主義秩序的批判。*Clement Greenberg,“The Avant-garde and Kitsch”,Gillo Dorfles,ed.,Kitsch:The World of Bad Taste,Universe Books,1970, p.116-126.中譯本參見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前衛與媚俗》,秦兆凱譯,《美術觀察》2007年第5期。而卡林內斯庫也從反面指出,“刻奇”體現了中產階級的時間意識,反對任何變化,不再相信進步神話所蘊含的過去與未來的真實性,從而將當下的娛樂消遣視為藝術追求的合理之事。*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270-271頁。大眾文化的刻奇(媚俗)最終被看作是一種審美標準的降低和主體性的喪失。
前衛藝術對刻奇的批判,表明兩種現代性的對立實質上就是物質與精神的對立,同時體現了審美現代性永遠不滿現實的特征。當西方資本主義宣稱現代性意味著物質生活的進步時,西方藝術家和人文知識分子看到的卻是文化的斷裂與危機。在這個意義上,葛蘭西、本雅明、阿多諾、霍克默爾、馬爾庫塞及哈貝馬斯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論的實質,就在于反抗資本主義的進步對個人主體性的壓制。就此而言,如果說社會現代性的本質是用理性取代宗教,那么審美現代性的本質就是丹尼爾·貝爾所說的“人們企望從文學藝術中尋求刺激和意義,以此頂替宗教的作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第74頁。
正如卡林內斯庫所指出:“在作為一個線性不可逆進程的時間概念中,上帝之死是無法想象的,因為上帝之死敞開了偶然性和無理性的大門。”*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63頁。因此,否定這一時間概念,就必然會否定上帝。與刻奇一樣,頹廢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特征也是非時間性的,即不再相信現代性的進步神話。不同的是,他們沒有像刻奇那樣走向享樂,而是走向了反抗。卡林內斯庫將這種審美現代性的起源追溯到波德萊爾,*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355頁。但就其時間意識而言,則似乎應當追溯到尼采的“永恒輪回”觀念。這位深刻意識到現代性危機的哲學家提出“上帝之死”,實質上是否定了宗教或世俗的終極目的論,否定了倫理主體和普遍理性的超驗意義。對尼采來說,現代性與基督教的時間意識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世界本來沒有任何先在的意義和目的,線性不可逆的時間意識不過是人對自己的謊言,目的是為了賦予進步以合法性,而“永恒輪回”則是來自古希臘周而復始的時間意識,無盡的重復揭示了人的生命本質就是痛苦和虛無,人類只能依靠主體的強力意志,以一種悲劇性的超人主義去面對存在的虛無困境。
尼采的思想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的哲學和文學,在海德格爾、薩特、加繆等無神論存在主義者那里,存在只是偶然的、非理性的、荒誕的,歷史沒有任何目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現代性的進步概念也是虛妄的。對于個體的自然生命來說,唯有活著與死亡才是真實的,這使得現代人充滿孤獨、焦慮、疏離和恐懼感。要想抵抗這種無所依傍的虛無狀態,個體必須賦予當下某種存在意義,抵抗物質社會造成的非人化現象,海德格爾的“詩意的棲居”、薩特的“自由選擇”、加繆的西西弗斯都是基于這種人的純粹主體性,試圖從荒謬中獲得自由,從絕望中感受希望,以一種頹廢甚至惡的方式,成為反抗人的異化的時代英雄。與此相應,崇拜行動、成功、斗爭、殘忍和暴力成為新的道德。
這表明,審美現代性始終存在著一種內在緊張,需要不斷否定自身。非理性或浪漫的現代主義邏輯最終翻轉為后現代主義,將批判社會現代性的矛頭指向人的主體性。對后現代主義而言,主體性的概念仍然是先驗的,事實上并不存在先驗的普遍理性和先驗的認知主體。福柯的“人之死”便是在“上帝之死”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認知主體的解構,要回到原始身體經驗的自我,而德里達、利奧塔、拉康等人同樣質疑自我主體的幻象,從非線性時間意識出發,質疑人文理性主義的本質主義和宏大敘事,強調世界的去中心化、平面化和碎片化,因而被布賴恩·麥克黑爾看作是從認識論到本體論的變化。*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338頁。這種反本質主義是對現代主義及前此文學觀的反撥,其相對主義又是前此文學觀的邏輯發展,后現代文學對于不確定性的感覺變得更加強烈,在貝克特、納博科夫、羅伯-格里耶、卡爾維諾、諾曼·梅勒、品欽等人的某些作品中,再也看不到對無意義存在的緊張和焦慮感,而是顯得越來越本能化以及善惡界線的混淆。
后現代意味著真理中心的彌散,最終導致主體的自我解構。有意味的是,后現代作家的初衷是出于對現實世界的消解,但其效果卻恰恰相反。盡管在反抗權威和傳統方面,后現代主義顯示出與現代主義、先鋒派和頹廢主義的相似之處,而在崇尚當下的特征上,又顯示出與刻奇的相似之處。對進步和主體的雙重否定意味著生命的虛無感與絕望感,也使得頹廢與厭倦的享樂主義獲得了某種反諷的正當性,正如丹尼爾·貝爾針對福柯的理論所說:“甚至連瘋狂本身也被當成是真理的優越形式。”*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第80頁。在這個意義上,對不可逆時間觀念的否定實際上恰恰是強化個人主體性的時代意識的體現。說到底,西方各種審美現代性在廣泛的意義上都有著精神上的內在聯系,無論某個思想家、藝術家在政治與審美上持何種立場,都是以個人主體性為基礎,以崇尚變化的時代意識為核心,對資本主義的物質進步不斷提出質疑,抨擊這種進步所包含的全部社會和倫理秩序。
這種藝術與社會的對立關系,表明現代藝術(尤其是文學)的特性就是創新的、批判的。在宗教衰退之后,西方藝術家與人文學者試圖以一種藝術價值觀代替宗教價值觀,使之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這便是審美現代性的實質。然而,問題在于,西方的審美現代性往往并不包含道德維度,甚至常常是反道德的。正如卡林內斯庫所說,審美現代性是“以一種對現代性的悲觀主義甚至是虛無主義批評的形式出現”。*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355-356頁。丹尼爾·貝爾更是一針見血指出:“現代主義文化不但不像宗教那樣設法去馴服邪惡,反而開始接受邪惡,探索邪惡,從中取樂,還把它(正確地)看作是某種創造性的源泉。”*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第209頁。這種對惡的贊揚如果限制在藝術領域,那還只是一個藝術思維是否僅僅以不斷創新為標準的問題,但如果將其運用于生活方式甚至政治領域,宣揚斗爭是人的本能,毫無疑義將使全社會將暴力視作正當的原則。
二
相比之下,東歐國家同樣面臨現代性問題,但東歐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批判卻與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這也造成了東、西方知識分子之間的隔膜。西方的現代性批判歸根到底是在現代性的方向上進行批判,即以崇尚變化為標準,而東歐的現代性批判則是以道德善為標準,這是因為對于掩藏在現代性進步敘事背后的惡,東歐知識分子有著切膚的痛感。對于厭倦的西方知識分子,自由是一種負擔,他們的精神造反總是能得到他們所批判的中產階級社會的贊揚和制度的保護,正如波蘭詩人米沃什在一次采訪中所說:“在西方,這種虛無主義存在于非常穩定的社會框架之內,這個社會清楚地知道應該怎么做,應該做什么,而且它的各項職能都運作良好。”*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會》,自印本,第372頁。但對于東歐知識分子,自由則是空氣、水和陽光。顯然,在沒有基本自由的前提下,他們不可能贊揚以任何變化與進步名義施行的暴力。前南斯拉夫學者米哈耶羅夫便曾深刻地道出其間的根本區別:“與法國思想家德日進相反,他認為人類可以分為兩類人,一類人相信進步,另一類人不相信進步,而我則相信通過觀察可以發現,人類之間有著最深刻的分類,一類人相信權力,另一類人相信自由。一類人相信專制,另一類人相信民主、法律和秩序。”*Mihajlo Mihajlov,Underground Notes, Caratzas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Rochelle, New York,1982,p.11.
可以說,東歐觀念的最大特點就是面對現代性的進步理念,在追求自由的前提下重新審視傳統道德的重要性。卡林內斯庫的兩種現代性針對的是西方社會,目的是揭示現代藝術與商業社會不可調和的沖突,并沒有將現代性與納粹集中營、古拉格群島聯系起來,這使得他的分析未能觸及二十世紀一個最重要的現象:現代性與極權的關系。就此而言,如果說西方面對的是現代性幻想的破滅,那么東歐面對的則是現代性悲劇的體驗。正如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所說:“現代性本身并不現代。但很顯然,在某些文明中有關現代性的沖突可能比在其他文明中更突出,而且從來沒有像我們時代這樣激烈。”*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頁。正是由于現代性與極權有著密切的關系,東歐國家的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沖突才表現得更加不可調和。
就現代性的時間不可逆意識以及崇尚科學、進步、工業化和科層管理而言,如果說蘇聯、東歐體制不是現代性,而是“偽現代性”的產物,*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364-365頁。那是說不通的。它所宣揚的歷史目的論將進步作為現代性的最重要標準,強調自由與進步的相互依存,歷史被劃分為不同階段,每一階段的人類生活都是前一個階段的結果,同時又是后一個階段的開始。按照這一歷史進步理論,私有制屬于低級的社會形態,它導致了社會的罪惡和人的異化,導致了人的自由的喪失,因而必然要被公有制所取代。在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權的政府有計劃地實行宏大的現代性規劃,并嚴格按照科層制進行管理,從而能比市場經濟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物質財富的快速增長。因此,東歐中央集權與計劃經濟的兩大特征并不與現代性相違背。德特列夫·波伊科特基于東德的情況,即認為斯大林體制包含了現代性的各個方面:“合理化的工業生產,官僚化的行政管理和服務活動,越來越小的農業部門,對工資增長加以限制,城市化的環境、廣泛的受教育機會,實行技術培訓,社會計劃化,發展科學,傳媒產品在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等等。*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79頁。
計劃經濟意味著政府能夠集中一切社會資源,在短時期內具有較高效率,但由于計劃經濟依賴的是行政管理,而不是市場調節,因而必然會受制于人類想象力的限制,正如哈耶克所指出:“對任何有才智者而言,去理解競取可用資源的不同人們的無窮無盡的不同需求,并一一定出輕重,將是不可能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61頁。它最終會導致經濟的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東歐各國的經濟都得到較快發展,但六十年代以后,東歐各國的物質產品凈值就一直呈下降趨勢,捷克斯洛伐克從7%下降至1.9%,東德從7.1%下降至3.4%,匈牙利從6%降至4.1,波蘭從6.5%降至6.2%。*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第157頁。從根本上說,東歐的蘇聯式制度是以歷史目標為其主要任務,為了加速工業現代化,經濟發展主要是靠重工業和基礎建設的投資和積累,而不是靠消費拉動。這種計劃經濟既無法預測全體人民的消費需求,也不準備滿足這個需求,結果必然會造成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所稱的“短缺經濟”。商店里總是空空如也,排隊購物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曾描寫道:“布加勒斯特昏暗的街道,寒冷沒有暖氣的居所,為等待食物排得像長龍一樣的隊伍。”*馬內阿:《論小丑》,章艷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3頁。這其實也是東歐各國的實情,這表明,計劃經濟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市場經濟是個人主義式的經濟,計劃經濟則是集體主義式的經濟,政府的一切努力都是“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第59頁。因此,這是一個受目標統制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在自發秩序上建立起法治的社會。一方面,權力本身成為目標,“集體主義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必須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人支配人的那種權力——并且他們的成功也取決于他們獲得這種權力的程度”。*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第139頁。政府壟斷了一切財富、權力和真理;另一方面,個人自由受到壓制,因為“對一個社會的共同目標的追求,可以無限制地忽略任何個人的任何權利和價值”,*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第144頁。人們對此毫無選擇,只能服從權力。正是通過經濟國有化和集體化,東歐國家將全體人民都納入體制的控制,實行比西方資本主義更加嚴格的勞動紀律。
這一切都是在歷史進步的名義下進行的,卡林內斯庫在解釋進化論概念時采用波普爾的自由主義觀念,指出如果將進化論正確地理解為變化與增長的有效模式,它就不能用神學的方式來理解,它不應當是有目標和規劃的,它是不可預言的、開放式的和非決定論的,按照可能性相互作用的原則而運作。*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第367-368頁。而蘇聯式制度則恰恰相反,它有著明確的歷史目標,自由被視作是對必然的認識,個人只是實現歷史目標的工具。為此,東歐各國還制定了龐大的社會改造計劃,通過集體主義教育來改造人的思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例如,1949年東德總理格羅特爾就宣稱,德國兒童是“我們最純凈和最好的人類材料”,是“我們未來的黃金儲備”。*Anne Applebaum,Iron Curtain,Random House.,New York,2012,p.301.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指出,現代極權是一種新文明,“它向我們承諾,要把人類個體轉變成為完全非人格的國家機器的可替換的零件。”*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第160頁。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是國家機器的齒輪和鑼絲釘,同時又是這部機器的潤滑劑。
社會的一體化必然要求思想的一體化,為了控制思想,當局采用各種高壓手段,封鎖外來信息,實行新聞出版檢查制度,目的就是讓多數藝術家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同時讓那些有批判思維的少數人保持沉默。所有藝術家們全都被組織起來,加入官方協會。在藝術國家化的制度下,國家慷慨地給藝術家們提供大量財政支持和有組織的受眾,藝術家們可以享受各種特權待遇,不用像資本主義社會的藝術家那樣擔心基本生活問題,但他們必須以創作自由為代價,服從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為塑造社會主義新人而創作。如果說西方審美現代性的宗旨就是批判社會現代性,那么在東歐國家,當局則是要求審美現代性必須與社會現代性保持一致,宣揚集體主義精神,展示光明的未來。這就是官方所規定的蘇聯式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實質,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取消藝術家的創作獨立性,取消藝術本身的美學屬性。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所有東歐國家都曾進行大規模的清洗運動,知識分子自然首當其沖。這使得知識分子的被迫害與反抗成為東歐國家的重要現象。例如,1952年捷克有15位作家總共被判220年的刑期,到1960年獲得釋放時,他們已經服了大約130年刑期。*澤曼:《布拉格之春》,上海市“五七干校六連翻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0頁。1956年匈牙利事件失敗后,許多知識分子遭到逮捕,作家協會和記者協會被停止工作。波蘭在1957天也曾大規模整肅知識分子,如《新文化》編輯部的大部分編輯被開除。六十年代,由于反對當局迫害科拉科夫斯基,就有22名著名作家被開除出黨。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后,約900名大學教師(包括65%的馬列教員)、40%的記者被開除公職,231名作家被禁止發表作品。根據米蘭·希麥爾的回憶,清洗的標準是“具有獨立思考的頭腦、慷慨、能容忍、受教育多,有高度的道德原則,有勇氣,等等。”*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第204頁。顯然,當局的目的就是要知識分子與公眾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完全脫離公共生活。
盡管東、西方都存在著非人化的現代性危機,但在西方國家,人性始終被視作是具有普遍性和本質性的東西,而在東歐國家,人性卻被視作是社會歷史的產物。人的主體性被解釋成集體,而不是個人。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東歐國家反對抽象的人性,同時又強調人的非個人化的社會性,個人生活完全被集體的歷史目標所遮蔽,沒有任何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個人空間,由此制造出來的是不同于西方的單子化個人,人人彼此相似,卻又互不關心。正如原籍捷克的作家昆德拉所言:“集中營,就是日日夜夜,人們永遠擠著壓著在一起生活的一個世界。殘酷和暴力不過是其次要特征(而且絕非必然)。集中營,是對私生活的徹底剝奪。”*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許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160頁。馬內阿也寫道:“隨著時間不斷被國家占用以致最終被徹底剝奪,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縮減直至最后消失:除了工作時間、上下班時間、上下班在公共交通上的痛苦奔波、開會、購物,人們還要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排隊、政治會議和集會上。等到你總算回到了鳥籠一般的家時,你發現自己迷失了,你一言不發,兩眼茫然地盯著空氣,在那里你看到的是無盡的絕望。”*馬內阿:《論小丑》,章艷譯,第4頁。這種個人性的徹底喪失,甚至導致東歐知識分子在許多美學觀念上與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昆德拉在闡釋“刻奇”(kitsch)一詞時,就認為它不是指西方意義上的娛樂,而是指歷史進軍激發的集體主義激情。
換言之,西方兩種現代性既是對峙的,又是同源的,因而審美現代性批判社會現代性導致人的異化,以個人主體性反抗資本主義的進步概念,并沒有超越現代性本身的內涵,它對社會現代性的批判必然會陷入自我矛盾,二者之間也不會產生體制上的根本沖突。而在經歷了兩次極權煉獄,經歷了人的尊嚴被任意踐踏,人的權利被任意剝奪的東歐知識分子看來,現代性的根本問題就是人的基本道德缺失,尤其在他們所處的國家,奉行的道德準則是米沃什所說的“倫理凱特曼”,政權具有冷酷迫害的特征,以崇高的名義殺人,“當他們盲目砍伐人的生命之樹時,用不著去考慮,這些樹中哪一棵是真正腐爛的”。*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烏蘭·易麗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89頁。因此,東歐社會的非人化危機,或者說主體性的喪失,不是由于物質主義造成的人的異化,而是由于集體主義對個人自由的扼殺。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茲提便曾寫道:“就連孤獨這類負面情緒,也統統被國有化收編。”*米克洛什·哈拉茲提:《天鵝絨監獄》,戴維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117頁。因為孤獨的情緒即意味著一個人脫離集體事業,走上個人主義的絕路。與西方個人主義社會中人的孤獨情緒相比,東歐極權的集體主義排除任何差異性和個體性,人們表面上融入群體,不再感到孤獨,但恰恰是孤獨的喪失意味著個人性的徹底喪失。千百年來人們遵循的基本道德準則在現代社會的衰亡,這才是產生現代性危機的最重要原因,它代表了真正的非人化的后果。
可以說,東歐審美現代性的特征就是捍衛被國家剝奪的個人主體性,反抗歷史目的論及一體化社會造成的非人化現象,尤其是人的人類意識的喪失。如米哈耶羅夫就曾指出,東歐不是一個不自由的社會,而是一個“積極的不自由”的社會。當局不僅要求人民順從,而且還要人民積極參與謊言和虛構,就像蘇聯學者雷達里赫所說,“積極的不自由”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愿望和感情在他的任何個人行為中都不再發揮任何作用的狀態。”*Mihajlo Mihajlov,Underground Notes,Caratzas Brothers,Publishers New Rochelle,New York,1982,p.34.波蘭詩人巴蘭察克也指出:“這個社會追求那些最世俗的價值,以便證明日常生存的痛苦是正當的。即使最簡單的需要都不能滿足——社會漸漸分裂,人們的沮喪通過相互仇恨的爆發而釋放出來。但是,即使這種仇恨是真實的也不會被釋放;每天的無力感已經摧毀了所有真正的沖動和道德體系。一切都溶解成偉大的無意義。”*Stanislaw Baranczak,Breathing under Wat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66-167.波蘭政治學家米奇尼克同樣指出,極權制度培育了一種亞文化,造就了一種新的人格,“他們不習慣自由和真實,無視尊嚴和自主性。”在一篇題為《尋求失去的意義》的文章中,米奇尼克描述了波蘭的狀況,這是一個受警察監控,由強加的意識形態、恐懼和虛偽統制的國家,“一個人被這個制度鞭撻和羞辱,靠著酒精的幫助,鼓足勇氣表達的是對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的仇恨。這個制度培養了一個人身上隱密的仇恨和世故的邪惡及虛弱。怯懦、卑鄙、機會主義、冷漠、玩世不恭成為普遍的現象。人們出于本能反應對無所不在的道德困境的厭惡一天天消失”。*Adam Michnik,In Search of Lost Mean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Angeles,California,2011,p.24.在這種制度下,沒有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夢想,唯一的希望就是別人和自己一樣悲慘,公眾的道德淪喪要遠遠甚于西方國家的人民。
正是從這一自我經驗出發,東歐知識分子不僅認為科學理性帶來了現代性危機,而且意識到現代極權是一個將理性世界觀與不受任何道德限制的權力結合起來的政治制度。這是因為,現代性的核心就是世俗性,無論社會現代性還是審美現代性,實際上都是世俗化過程的產物,建立在擯棄千百年來傳統道德的基礎上,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超越的道德內容。或者說,世俗化的現代性過程就是人類道德的粗鄙化過程,現代極權制度不過是這一過程的極端表現而已。由此看來,道德空虛與價值虛無既是丹尼爾·貝爾所說的科技理性(即社會現代性)的邏輯發展,*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第53頁。也是西方審美現代性的邏輯發展,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說:“現代性與反現代性都可以以野蠻和反人類的形式表現出來。”*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第13頁。尤其在東歐國家,階級斗爭與專政理論中已經包含有強烈的否定道德的因素,每個人對自己行為承擔的是歷史責任,而不是道德責任。因此,東歐知識分子強調的個人主體性不僅是一種獨立的自我,而且是一種具有良知的自我。
三
與西方知識界相比,東歐的審美現代性具有很強的道德內容,倫理是東歐知識分子一切思考的出發點,這決定了東歐觀念不僅具有批判性,而且具有建設性。在他們看來,人類的普遍性道德的標準并沒有改變,由于時代的變化而推崇特殊真理和特殊道德是沒有充足理由的,也是危險的。這種特殊的道德以符合人的主觀目的為標準,它意味著道德善或是源于生命意志,或是源于主觀理性。東歐知識分子對社會現代性的批判則是基于傳統的道德客觀性,而不是現代性的理性或反現代性的非理性。在這個方面,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社會學家鮑曼和捷克哲學家帕托切克的言說為我們提供了頗具啟發的論證。這些言說具有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的特征,這也是東歐觀念的特征。
這幾個東歐知識分子都沒有強調時間與進步意識,而是將道德責任感置于其理論的核心,既批判當局的社會現代性,也質疑西方的審美現代性。就此而言,他們的社會現代性批判已經遠遠超出了東歐的范圍,成為對整個世界現代文明的一種思考。在他們看來,西方的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在根本立場上是相同的,都是擯棄了對宇宙的總體性信仰,認為客觀事物本身沒有意義可言,從而否定了普遍價值的客觀性與永恒性。因此,東歐的審美現代性看上去似乎更有某種文化保守主義特色,它植根于傳統的宇宙圖景,肯定永恒的人性和人類道德,包括政治倫理、職業倫理、美學倫理以及生活倫理等等,并將這些普遍倫理的喪失看作是最核心的現代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東歐觀念從不贊揚惡的歷史作用,而是將惡的盛行視作是宗教去魅的有害結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在《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中就認為,現代開始于從神啟走向世俗理性的解放運動,笛卡爾“從宇宙概念中去除了充滿目的的自然秩序。世界變成了沒有靈魂的世界,而且只有在這個假設的基礎上現代科學才能展開。”*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第8頁。官方意識形態正是“對現代性、理性組織、技術進步的直言不諱的熱情與對古老共同體的渴望的混合物,這種混合在對未來完善的烏托邦期望中達到了頂峰。”*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第11頁。就是說,官方宣揚的現代性擯棄了自然秩序下的道德原則,將進步視為最高的道德評判標準,凡是促進歷史進步的就是道德的,為此必須放棄基于傳統道德的抵觸,傳統的善與惡之間的標準因此被徹底顛倒。
因此,在《責任與歷史》中,科拉科夫斯基進一步指出,進步與道德完全是兩回事,二者依據的是不同的判斷標準,倘若要將它們結合起來,就會產生無法解釋的矛盾。道德的原則是確信某些行為是目的本身,不可違背,而歷史目的論的原則卻是實現進步,“沒有絕對和普遍的道德標準,如果它們被證明是存在的,當它們與進步的要求沖突時就會馬上失去這種普遍性。”*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姜海波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12頁。因此,歷史必然論在邏輯上只能推導出禁止使用道德判斷,甚至為了實現歷史目的可以采用暴力的手段。盡管官方意識形態也提倡大公無私的倫理,但問題在于,“如果道德判斷同時從屬于歷史必然性的實現,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有什么東西是目的本身。換句話說,最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價值就不存在了。”*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姜海波譯,第115頁。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目的論以及由此產生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沒有任何內在的道德含義。
相較于千百年來的傳統道德,這種進步理論顯然具有崇尚惡的傾向,奉行黑格爾“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功利原則,進而相信暴力是進步的助產婆,為了到達理想的彼岸不惜讓整個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哪怕為此而趟過血海,米沃什曾引其堂兄奧斯卡·米沃什對二十世紀革命的看法,那就是“為微小的進步,流太多的血。”*米沃什:《第二空間》,周偉馳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10頁。所以它在本質上拒絕接受任何道德約束,拒絕接受任何人權和法治的概念。然而,“歷史哲學并不能決定人生中的主要選擇,它們由我們的道德感決定。”這是由于道德判斷有其自身的標準,即基于良心對善惡的定義,“道德行為的法則無法從任何歷史進步的理論中推導出來,沒有什么理論可以當作正當借口來違反我們信任的某些法則的有效性”。*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姜海波譯,第145頁。最有說服力的理論也不應使我們去迫害一個無辜者,每個人的具體行為都是一種道德選擇,都必須承擔個人責任。“士兵在道德上要對他依照上級命令而犯下的罪行負責。一個人更要對其接受其中不為人知的歷史使命——想象的或現實的——而采取的行為負責。”*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姜海波譯,第132頁。就此而言,阿倫特所稱的“平庸的惡”是不能替自己尋找借口的。然而現代的政治行為原則卻不是這樣,它根據的是職業責任,不是倫理責任,正如我們從納粹和斯大林極權制度下那些領導者與普通人的暴行中,以及他們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中所看到的那樣。
波蘭社會學家鮑曼與科拉科夫斯基一樣,也曾在華沙大學任教,并且由于反對當局的排猶宣傳,也是在1968年被迫移居國外。他的《現代性與大屠殺》是一部研究納粹與現代性關系的名著,但其中的分析同時也是基于他在斯大林極權下的經驗。對鮑曼來說,納粹極權不是向前現代社會的倒退,而是與科學理性的現代性深刻相連的結果。“沒有現代文明,大屠殺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現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讓大屠殺變得可以想像。”*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8頁。鮑曼在這部著作中指出,大屠殺與理性所崇尚的高效與秩序并沒有沖突,它的技術成就和組織能力也都是現代的。“大屠殺展示了如果現代性的理性化和機械化趨勢不受到控制和減緩,如果社會力量的多元化在實際中被銷蝕,那么現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趨勢就可能帶來的后果——因為一個有設計、徹底控制、沒有沖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諧調的社會的現代理想才會有這樣的趨勢。”也就是說,這樣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是以取消個人性為前提的。換言之,現代性的最大問題就是在世俗性的官僚管理體制下,個人良知變得不再重要。
道德責任感無疑是這部書的思考核心,在鮑曼看來,現代官僚機構具有一種理性的客觀化功能,或者說它是一種道德冷漠的社會生產,即造成執行者與對象之間的社會距離,以削弱人天生的同情心,如納粹對受害者采取的隔離方式,便是如此。這一非人化既造成權力的匿名性,同時吞噬了每一個人。鮑曼引用卡普托的話:“如果你用高度精密的武器遠遠把人殺死,你就能永遠不會出毛病。”*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譯,第253頁。由于有制度的保障,人性的惡全部被釋放出來,并到得充分的鼓勵。距離感使得暴力的執行者可以保持冷然的道德中立,將施暴的對象非人化,變成表格上的統計數字。而受害者也將自我保全視作最理性的選擇,使自己的價值世界縮減為只要活下去的本能欲望,每個人都盡力將自己與其他受害者區分開來,對同胞的受難漠然置之,即使他們知道,也許下一個受害者就會輪到自己。
歸根到底,極權暴政之所以能夠暢行無阻,不是由于現代人缺乏理性,而是由于現代人傾向于接受一個徹底的理性的設計,削弱了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倫理。理性、科學催生了最強烈的信仰,人類無所不能,然后是權力無所不能。在由理性設計的現代官僚體制中,組織紀律取代道德責任,成為行為的規范與美德,從而否定了個人良知的權威性。*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譯,第30頁。執行者只知忠實地執行命令,根本不想去了解行動的目的,因為他遵循的是公務員的榮譽,而不是個人的道德判斷。道德被簡單地等同于成為一個認真而有效率的職員,并將其視為個人人生價值的實現。“對象的非人化與積極的道德自我評價兩者互相強化。公務員可以在忠實地履行職責的同時保持他們自己的道德良知不受到任何的損害。”*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譯,第138頁。盡管鮑曼此書討論的主要是納粹現象,但就其揭示的理性根源而言,他對現代性與極權關系的闡述甚或更適用于東歐國家的制度。
作為一名具有極大的道德勇氣反抗極權并最終被迫害致死的哲學家,帕托切克被認為是捷克現象學的最重要代表,對捷克以及東歐各國知識分子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是他在1935年邀請自己的老師胡塞爾來到布拉格,發表了那篇關于歐洲人性危機的著名演講。在此后被長期禁止擔任教職的潦倒生涯中,帕托切克始終秉承胡塞爾的思想,堅持思考現代理性給歐洲帶來的精神危機,指出理性的歐洲文明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即試圖通過非人化來達到理性的尊嚴。在帕托切克看來,盡管理性的技術文明擁有巨大的抱負和不可否認的成功,但它“并沒有解決人類內在的最大問題——這也是它自身最主要的問題:怎樣才能不只是單純地活著,而是在歷史賦予的各種可能中真實地、有人性地活著。”*拉瓦斯汀:《歐洲精神》,范煒煒等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第169頁。現代性的根本問題在于,它主要是與人的物質幸福相關,而不是與人的精神生活相關,其本身就缺乏倫理基礎。在早期的著作中,帕托切克就曾指出,現代性導致人類的自我貶低,使得人們執著于日常生活,被物質的表象世界所迷惑,從而選擇了“最微不足道的生存意義,這是由于他們對物質生活的狂熱和對自身的過分關注所決定的。”*拉瓦斯汀:《歐洲精神》,范煒煒等譯,第139-140頁。
在《作為一個哲學問題的自然世界》這篇重要文章中,帕托切克借鑒胡塞爾“生活世界”的概念,認為現代人已經不屬于自己,他們沒有自主權和獨特性,只是進入一種工作狀態,完成交給自己的各種任務,不論它們對自己有利還是有害。這種以現在時為主的運動當然對我們理性能力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如果人類存在的重要部分都被其占據的話,那么我們便會有失去自我的危險。我們的生活將完全陷入物欲的圈套,所有的時間都將被耗費在滿足物質尋求上。人類只是簡單地為了生存而存在,生活的終極目標——自由,則永遠被籠罩在陰影中無人問津。*拉瓦斯汀:《歐洲精神》,范煒煒等譯,第137-138頁。帕托切克將這種自我貶低與道德墮落歸因于人們自身的責任,它使得人們滿足于外在的幸福,并將這種幸福的實現寄望于國家權力。在1977年一篇闡釋“七七憲章”精神的文章中,他指出現代人總是不滿足物質繁榮的狀況,他們“總在熱衷于尋求解決問題的最新技術方案。其中之一乃寄希望于依靠權力和政府。政府就像一座巨大的工廠和倉庫,可以支配一切以其他形式存在的力量。”*Marketa Goetz-Stankiewicz ed.Good-bye,Samizdat,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2,p.142.事實證明,這種希望必然會導致個人自由與權利的喪失。
在東歐知識分子看來,人權的概念具有本體和倫理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終極目標,與每個人的存在狀況與自我實現相關,所以它不限于日常生活的面包,而是面向存在的真實、責任與良知,不可能完全靠法治來保障。正如帕托切克所說:“真正自我的存在從來都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是一種實現。”*拉瓦斯汀:《歐洲精神》,范煒煒等譯,第146-147頁。因此,“人類絕對不能只是簡單地存在,他必須有使命和責任,每個人都應獲得這樣的特權。”*拉瓦斯汀:《歐洲精神》,范煒煒等譯,第193頁。也就是說,東歐以良知、倫理為基礎的人權概念具有自主的性質,即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包含了實現個人自由的美好生活及對他人權益的關心與捍衛。需要指出,伯林對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分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意義,消極自由是指不受別人限制的自由,積極自由是指自主的自由,然而這個區分同時也存在著語用上的悖論,盡管后者的確容易遭到濫用,但前者本身卻無法靠自己成為現實。在一個沒有建立起自由秩序的國家,一個權力不受任何限制且隨意侵犯個人權利的國家,爭取消極自由的努力顯然必須依靠積極自由,否則消極自由就會很容易地成為犬儒主義的代名詞,成為消極等待與逃避的借口。
在八十年代,“現實的社會主義”成為東歐各國社會制度的自我描述,表明政權已經放棄了宣揚最終目標,匈牙利政治學家基斯在1979年寫道:“意識形態的要求這時完全是消極的,不要向官方最高的意識形態挑戰,或者說在某些不常見的時刻在形式上慶祝慶祝,說愿意服從這種意識形態。”*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第253頁。便是指出了這一事實。掌權者自己已不再信仰他們最初的政治理念,而是采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極力鼓勵人性中自利的一面,去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這使得大多數人不再關心社會自由,從而在客觀上維持了政權。如果說極權造成道德的顛倒,那么后極權便是造成道德的冷漠。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使得東歐知識分子將審視的目光轉向更大的歷史背景,轉向整個世界的現代性進程。
這一切都是因為現代工具理性和功利主義排除人的心靈的結果,東歐觀念的核心就是將現代性問題的根源歸于道德,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把對制度的思考上升為對存在的思考,重新尋求真理與道德的形上根源,重申個人的道德責任。例如,科拉科夫斯基就認為,道德源于超驗的傳統權威即宗教,而不是理性,“在道德感上,沒有善惡的理性標準,即沒有任何標準是充分地建立在經驗和邏輯的基礎上的。”“廢除了權威、傳統和教義的純粹教育的結果經常就是道德虛無主義,雖非總是如此。”*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第185頁。就此而言,現代性最危險的特征正是由于“禁忌的消失”。傳統的道德禁忌構成了人類共同生活的紐帶,“沒有禁忌機制,這些人類的紐帶就不大可能存在下去。”*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第13-14頁。在傳統社會,人們的“實際選擇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是一種道德行為,這意味著是一種每個人都承擔自己個人責任的行為。”*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姜海波譯,第134頁。而科技理性卻造成了“禁忌的消失”,這反映出現代社會是“一個已經忘記了上帝,忘記了善惡之分的世界,一個使人類生命毫無意義的世界,已深深墮入虛無主義之中。”*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李志紅譯,第8頁。
鮑曼同樣認為,道德責任是主體的存在模式,是人與人之間聯結的紐帶。在本質上,道德行為是個人的和非理性的,“變得有責任是我作為主體的建構。因此它是我的事,而只屬于我。”它既與功利性的算計沒有共通之處,也與契約性的義務沒有任何關系。“道德意味著對他人負責,由此也對不是我的事,甚或與我不相干的事負責。”*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等譯,第239頁。帕托切克更是以一種先驗世界觀的立場指出:“任何一個社會,不管它的科技基礎多好,若沒有道德基礎以及與被允諾得益等優惠毫無相關的信仰,這個社會就不能運轉。然而,道德的存在不是只為了維系社會運轉,而是讓人成為人。人不是依據自己反復無常的需要、愿望、癖好與渴望來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Marketa Goetz-Stankiewicz ed.Good-bye,Samizdat,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2,p.143.由此定義的道德是一種具有形上根據的絕對律令,它是人類賴以存在的惟一真實而可靠的根基,超越所有職業責任和權力之上。因此,對于那些具有道德感的人來說,自由和責任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出于良知,是接受必須接受的東西。在絕對的、超驗的、普適的倫理面前,一個內心追求自由的人除了責任,別無選擇。
在科學理性統治一切的現代,強調道德因素往往被視作是過時的保守主義觀點,它已經由少數人徒勞地表達了幾百年,但如果能懂得東歐知識分子曾經在兩個極權制度下存活下來的特殊經驗,那么他們重申人類道德責任的主張就是值得思考的。要言之,現代社會的非人化意味著人不再是具有內心獨立感受的生物,意味著個人與世界失去了真實的聯系。這個聯系不僅靠法律、契約,而且更是靠個人的心靈、沉思。在閱讀東歐作家的著作時,給我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詞語就是:心靈與良知。這些古老詞語早已被現代理性所擯棄,但如今卻被東歐作家重新提出來討論,如帕托切克就曾借用古希臘哲學家的習慣措辭,把現代人面臨的危機稱作是“靈魂的憂慮”,按照他在一篇文章中的說法:“靈魂的憂慮構成了歐洲的根本,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創造了歐洲的歷史。”*拉瓦斯汀:《歐洲精神》,范煒煒等譯,第114頁。
正是由于理性與良知的分離,帕托切克才認為現代最大的危機是意義的危機,這個危機并不會因制度的改變而改變。帕托切克的好友科塞克在轉型后也指出,我們的時代之所以充滿危機,是因為一切事物都變成暫時性的,不再有永恒的了。這是一個“非本質戰勝本質”的時代。*拉瓦斯汀:《歐洲精神》,范煒煒等譯,第168頁。而米奇尼克在制度轉型后的一篇文章也是以“尋求失去的意義”為題。在其他東歐知識分子的著述中,同樣充滿了對本質、道德、良知與價值的思考,表現出與西方后現代理論反本質主義的區別。他們既反對西方的物質主義,同時又反對東歐的極權主義,其核心觀念則是對普遍的道德觀念的闡釋。用米奇尼克的話說,在現代性批判的意義上,東歐知識分子奉行的是一種“道德絕對主義”。*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會》,自印本,第414頁。
對于這個知識群體來說,“道德絕對主義”不是自我美化,也不是學院式的爭論,它意味著實實在在的冒險,包括事業的毀滅,個人、家庭和朋友的安全,甚至坐牢和犧牲。在這種嚴酷的環境里,一個人追求社會自由是一件嚴肅的事,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同時對自己又沒有任何好處,因而更需要堅定不移的絕對價值判斷。正如米奇尼克所說:“他們認同人道的價值,但卻生活在英雄的價值之中。”*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會》,自印本,第415頁。可以說,正是基于強烈的倫理訴求,重新關注良知、心靈之類的前現代話題,東歐知識分子才會將自由理解為對世界的責任,從而表現出極大的道德勇氣,不計個人犧牲,以微弱的個人與強大的權力對抗,最終動搖了極權體制的根本。
最后還要強調的一點是,盡管現代性是個需要闡釋的沖突的概念,但與前現代的等級社會相比,現代性在三個主要方面改變了人類的觀念:世俗性、個人權利和社會平等。這些價值構成了當今世界主流政治觀點的基礎,并以世俗政府、民主與法治作為保障這些價值的最重要手段。盡管世界現行的民主制度有著種種弊端,對政治家來說,獲得政治權力的最大驅動力仍然是功利目的,但現代性所內蘊的政治文明仍是值得肯定的。在西方啟蒙運動的主流政治思想中,哈耶克所說的泯滅個人自由的建構理性從來都是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解決方案。從另一個方面講,對于將道德與政治聯系起來的觀念,人們同樣需要保持警惕,不能忘記馬克斯·韋伯的提醒,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心志倫理,而是責任倫理。
歸根到底,政治與道德是各有邊界的,道德屬于社會之事,而不屬于政府之事。換言之,社會可以用道德的政治去反抗政府,政府則不能用道德的政治去管理社會,當然更不能用反道德的政治去管理社會,因為正是由于現代極權壟斷了政治、經濟和道德所有領域,無視民主與法治,個人權利和社會平等的現代價值才會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毀。在這個意義上,東歐觀念追求的目標恰恰是個人權利和社會平等,而不是權力。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二十世紀東歐批判文學”(13YJA752005)。
景凱旋(1954-),男,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