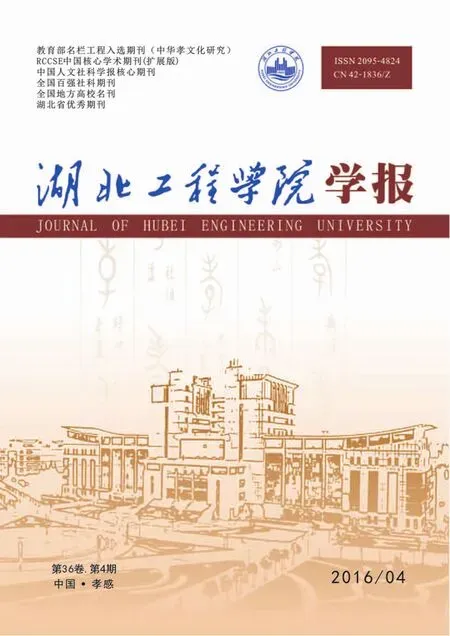東漢名士現象研究
何新楚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藝術與傳媒學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
東漢名士現象研究
何新楚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藝術與傳媒學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研究東漢名士現象,可以從名士的由來、東漢名士隊伍的兩大分野、名士形象的品格魅力、名士效應下的人文氣象等四個方面入手。東漢名士效應與漢末“建安文學”有內質性關系,具體表現為:一是為其文化背景,浸染了獨特的時代色彩;二是為作家的文學創作實踐,定下了全新的審美格調;三是激活了一代作家放眼天下、關注民生、感悟人生的赤子情懷。
關鍵詞:東漢;名士;人文氣象
在中國文化史上,名士之謂,就是指在社會生活中有影響的文化人。雖然他們中的有些人,寄身豪門貴族,人品、文品均名不副實,但是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失為士子階層的先進分子。在形成名士隊伍之后,其個體的有限影響,經由特定社會矛盾的刺激,構成某種非嚴密的組織性整合,進而會形成對現實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產生較大影響的正能量。而東漢末年的名士隊伍,其影響力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文學發展的內在質變來看,這種特有的文化現象,直接提升了漢末以來文學創作的第一生產力要素的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講,東漢名士現象直接作用了作家的審美創造能力,構成了“建安文學”得以產生的最重要淵藪。
一、名士的由來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新興士子階層以其勃勃生機,活躍在社會舞臺上,中華民族共同語中,遂有了“名士”一詞,即指士子中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和聲譽度的知名之士。大約在戰國末期,“名士”就已經出現在學者們的書面語言中了。《呂氏春秋·勸學》曰: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學于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1]
這段文字是說春秋戰國時期,那些或出身微賤,或品行不端,在鄉里頗受輕視、貶斥、痛恨乃至應該受到極刑懲罰者,經過圣賢們的教育培養,不但獲取了大學問,而且改邪歸正,成為了揚名天下的杰出人士,平安地活到壽終天年。一時間,在人們的意識里,名士不是出自儒學孔門,就是成就于墨家學派。其實,在思想相對解放的漢代,先秦諸子百家之學的承傳者,憑其專深造詣,都有可能成為名士。
大漢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整體上的真正繁榮發展期。士子階層在漢朝立國之初,已成為一統社會結構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亦即知識分子成為了推動國家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生力軍。諸如陸賈、賈誼、晁錯等,他們都被稱為“名士”,其才情與作為,得到了歷史的認可。南朝劉宋之初的社會話語,把“名士”的才情、風度、行為,概述為“名士風流”。事實上,在漢代,尤其是東漢中晚期,“名士風流”已成為社會文明走廊上的一道靚麗風景線,筆者姑且稱之為“名士效應”。這種“名士效應”中的人才培養、文化傳播及名士個體的學術、人格魅力,有效地轉化成時代的人文氣象,滋育了新的文學思潮,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萌芽后的人文生態環境 。
東漢時期,士子階層在讖緯之學和宦官政治、外戚政治的多重擠壓下,涌現了一支以學識淵博、滿腹經綸、唾棄禮法、任性而行、品評人物、縱論時政、好為人師等為基本特征的名士隊伍。著名歷史學家范曄,對這一極具時代特色的名士現象頗為關注。他在《后漢書·方術傳序》中有一段精辟的論述: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后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于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不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硋(礙)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于詭俗乎!如今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于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于數術者也。[2]792
在《后漢書·樊英傳》論中,他進一步作了結論性表述: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2]799
范曄認為,漢代名士隊伍的生成,有其客觀機遇,東漢名士隊伍,更有其獨特的生存空間與生態狀況。在漢初,“名士”一般是指士子中擅長醫、卜、星、相等學問與技能的知名之士。由于帝王所好,所以士子們趨之若鶩,其中許多人頗有方術造詣。他們先天與社會政治關系密切。名士在成為中央或地方執政者的座上賓之后,不自覺地影響著當時的執政。后來,由于儒家經學中的讖緯之學興起,方術中滲透了圖讖之說,“名士”的行為,更多了些對自然災異、社會變局的穿鑿附會。士子中的“通儒碩生”,奮然成為這類名士的反對派,形成了另類名士隊伍:他們以廣博而細密的經學研究為基礎,義無反顧地干預現實政治,以致在人生道路上備受打壓,卻無怨無悔。
范曄還認為,事物的發展,總會出現偏頗,不能沒有缺陷與短板。在推動人間大道運行的過程中,各種學說不免存有些許相同的障礙。有如研究《詩》,會出現愚昧之見;研究《書》,會出現騙人的假話;研究術數,必然也會出現肆無忌憚的詭詐。現實社會中,那些把握了《詩》“溫柔敦厚”特征的學者,就不愚昧,是深究于《詩》的文學名士;那些對《書》中的義理融會貫通、明白事物發展的學者,就不會說騙人的話,是深究于《書》的經學名士;那些精通術數,知曉災異變化與應對的學者,不會隨意詭詐世人,是深究于術數的方術名士。
在這里,范曄十分客觀地論述了各類名士的積極與消極效應,及其之所以成為名士的原因,似乎不經意地將東漢名士,從整體上歸屬為文學、經學、方術三種類型。他冷靜地指出,西漢以來的名士,并不都“能通物方、弘時務”,即許多人在曉諭事物規律、治國救時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時至今日,這仍是我們認識漢代名士應取的求實態度。
現代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對東漢名士現象的分析很有見地。他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中說:
當時名士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們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絕征召一次,他們的聲望和社會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們認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雖然不做官,他們的社會地位實際上抵得一個大官。這一類人數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類是言行剛勁疾惡如仇的名士。他們依據儒學的道德標準,實行了孔子“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格言,認為善的人,互相推薦標榜,自然結合成一類,認為惡的人,不分輕重,一概深惡痛疾,只想殺逐他們。這是宦官政治激發起來的一種憤怒反抗。他們的行動是勇敢的,但絲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勢力。這一類名士,是統治階級中的鯁直派,也是抱有正義感、對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在士人中卻起著倡導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類是迎合風氣的名士。這一類人數最多,是第二類名士得勢時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補者。[3]
他的這種分類研究,立足于名士與上流社會的關系及其社會表現,認為東漢的名士現象,是宦官政治的產物,說到了問題的關鍵處,對我們認識當時的名士現象不無幫助。事實上,東漢名士隊伍的生成,與當時的文化建設背景,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
二、東漢名士隊伍的兩大分野
檢索范曄《后漢書·列傳》對東漢各類名士生平行事的敘述,我們不難發現,他尤為關注名士的人際遭遇與行為效應。他筆下的東漢名士隊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漢今文經學派、古文經學派衍化而來的士林兩大分野。
1.讖緯之學應用派。東漢名士隊伍的讖緯之學應用派,是社會盛行圖讖之風的產物。以王梁、孫咸、鄭興、賈逵、任文公、郭憲、樊英等為代表。他們經學涵養深厚,明曉讖緯之學,擅長星象、術數,故范曄大多列之于《方術傳》。其中尤為知名者,則專門立傳,如《鄭興傳》《賈逵傳》等。在最高統治者由崇尚方術演變為迷信讖緯之學的背景下,這類名士的政治環境是相對優越的。盡管他們不刻意修飾儀表,言語出奇立異,但是,憑借其所專攻的“道藝”,或青云直上,位居三公;或幕僚州郡,備受禮遇;即或淡泊官場,云游四方,也是揚名朝野,身邊總有成群的粉絲。從中央到地方的執政者,出于維護自身的統治利益的需要,千方百計地征辟、籠絡他們,遇事求教他們,以至于屈尊師事他們。因此,許多人顯赫一時,極盡聲名尊貴。然而,更有些人不熱心于官宦,與上流社會不即不離,甚而恃才傲物,對皇帝也敢調侃揶揄一番。據《后漢書·樊英傳》載:
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于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征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鐘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2]798
樊英與順帝的這段對話,充滿機趣,鏗鏘生動,既表現了樊英超越壽、祿、富、貴,傲視權威的人格個性,又展示了這類名士的精神風貌。作為當時文化精英的一部分,他們具有多方面的學問修養,綜合素質較高。他們或因家學熏染,承繼祖業,或師承大儒碩學,兼通五經,學有專攻。他們在成為名士之前,首先是個儒生。博學多識,是他們相同的人生底色,多數人經歷過基層社會生活,富有人生閱歷與經驗。故而,他們對現實社會政治狀況的解說,對災異的預測,并非全然主觀臆斷、無端附會,更多地源于他們的學養與見識。他們身邊聚集著眾多的生徒和崇拜者,是名至實歸,客觀上奠定了他們作為學者與文化傳播者的地位。在他們的生徒和崇拜者中,有其“道藝”的衣缽傳人,也不乏文學藝術人才。
這類名士中,像賈逵這樣與班固齊名的人物,既是著名經學、史學研究者,又是知名文學家。賈逵所撰的《左氏解詁》《國語解詁》,是中國史學的寶貴財富,且開啟了學術研究上匯釋集成之風。據《后漢書·賈逵傳》載:
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余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后世稱為通儒。[2]368
不難想象,作為賈誼九世孫的賈逵,已然是當時學界大師,其在文學領域的影響,當不亞于班固。
據《后漢書·唐檀傳》載:
(唐檀)少游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后還鄉里教授,常百余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于蕭墻,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閆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征,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2]800
唐檀生逢東漢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斗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其思想行事很有代表性。他的知名,不只在于運用方術,預知了時局之變,更在于他憑著睿智,棄官隱居,全身遠禍,執著于文化傳播,在著書立說、教授生徒中,寄托政治理想。他昭示了這類名士,最終也歸于孔子所奠定的興教治學傳統。由此可見,至遲在安帝、順帝時期,這類名士已開啟了直面現實、慷慨時政、尊重自我、期望于后學的人文風氣轉變,合流于桓譚、王充等所開創的“疾虛妄”“尚實真”的人文思潮之中了。他們手中的“方術”,已由聲名的敲門磚,演變成干政的工具。今天的文學研究,不能簡單地因方術固有的迷信色彩,而對他們視而不見。
2.讖緯之學反對派。這類名士政治傾向鮮明,是與宦官集團、外戚集團相抗爭的堅強斗士。反對讖緯之學,是他們的學術思想旗幟,也是他們與前述名士分野的標志。大致表現為五種形態:
一是于東漢前期,以桓譚、尹敏、王充等為代表,尚實崇真,首倡從理論上清算讖緯之學。二是于中期,以馬融、李固、張衡、王符、王逸等為代表,經世致用。他們是東漢中興時期思想文化的代表。三是于后期,以李膺、陳蕃為領袖的清流派,他們是黨錮之禍的直接受害者。四是以梁鴻為代表的隱者,他們生存在宦官、外戚政治的夾縫里,是潔身自好而非忘情“時務”的高士。五是漢末黨錮解禁后,以橋玄、蔡邕、鄭玄等為代表的復興漢室派,他們有扶大廈將傾之志,而無挽狂瀾于既倒之力,孜孜于后學培養,是漢王朝悲壯的殉葬者,卻在建安文學的背景臺上,留下了不滅的輝光。
考察這類名士的現實作為與歷史影響,桓譚是個開風氣的人物,可謂雄視東漢文壇近兩百年。據《后漢書·桓譚傳》載:“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2]288可見,他既是西漢學術傳統的繼承人,也是東漢務實致用學術思想的奠基者。“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這種堅守節操、不茍流俗的人格精神,是他堅決反對讖緯之學的力量源泉。針對光武帝迷信圖讖之弊,他多次冒死直諫:
夫策、謀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者也。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圣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后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2]289-290
桓譚認為自己為朝廷獻策謀劃,是以符合民心、遵循事物規律為取向的。而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喜歡聽奇談異說,這是人之常情。但是,觀覽先王留下的文獻,莫不以仁義正道為根本,沒有奇異怪誕虛妄之事。至于上天的運行、人的壽命的長短,這是圣人都難以說清的,自孔門賢者子貢之后,再沒有誰談論這些事,況且后世那些見識淺薄的儒生,他們能通曉這些嗎?他把讖緯之學應用派,斥之為“巧慧小才伎數之人”,這些人肆意擴展圖讖、緯書,假稱是《讖記》,以欺騙迷惑貪婪邪僻之人,誤導皇上治國理政,怎能不受到抑制疏遠呢?
桓譚似這樣猛烈抨擊現實政治中倒行逆施的文章,有二十九篇,號曰《新論》,頗有漢初陸賈風度。同是名士的文學批評家王充,對桓譚的為人及其《新論》,評價很高。他在《論衡·佚文篇》中說:“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4]200意謂桓譚的學問和學術著作,比春秋時魯國富豪猗頓還富有。他在《超奇篇》中又說:
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也……王公子問于桓君山以揚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于玉;贊龜者,知神于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于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說論之徒,君山為甲。
在王充看來,桓譚的務實論理,比司馬遷、揚雄之類大家還強。從某種意義上說,桓譚是讖緯之學反對派名士人文精神的杰出代表,也是兩漢學術思潮的分水嶺,深深地影響著后來名士隊伍的形象塑造。
三、名士形象的品格魅力
如前所述,東漢名士的兩支隊伍,在社會生活中都發揮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就外在表現而言,這種影響力,一是來自他們所建樹的學術思想、政治主張,二是來自他們博聞強記,學有專攻;但從內質上看,則源于名士形象的品格魅力。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1.治學以勤,滿腹經綸,卓然獨立。在東漢名士中,對當時及至后世思想文化、文學發展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王充(27-約97)。在桓譚務本斥讖思想的影響下,王充建立了以“疾虛妄”“尚實真”“貴效驗”為核心的學說,哲理上同桓譚一脈相承。反映在文學觀念上,他實現了由頌揚帝國向批判現實轉變;其審美取向,則棄“弘麗”而取“真美”,有力地作用于時代的審美文化建設及文學創作對格調的追求。據《后漢書·王充傳》載: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少孤,鄉里稱孝。后到京 師受學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后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數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余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征,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5]186
范曄的敘述雖然簡潔,卻關注了幾個很重要的細節:
其一,王充“一見輒能誦憶”,稟賦極好,有超強記憶力;其二,他“少孤”,“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即很小死父,是謂“細族孤門”,后天成長環境極差,他以勤克貧,游學洛陽,遍讀書市所賣之書;其三,他在“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之后,又“受學太學”,師事著名學者班彪,遂成滿腹經綸;其四,一生不以官場得失、升降為意,鐘情于對社會形態作審美觀察,自覺地訴諸著書立說。
為學以勤,著述以勤,至老不懈,“勤”是王充人生有成的唯一路徑。王充卓然獨立的形象品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超凡拔俗的人格魅力,二是敢為人先的學術魅力。據其自述,他的著作,除《論衡》《養性書》之外,還有《譏俗節義》十二篇、《政務》《實論》等。他生前的聲名影響,有積極與消極兩端。其積極方面,是他成名之后,既有刺史董勤相聘,又有當朝名士謝夷吾向皇帝上書舉薦,且有超過孟軻、荀況、司馬遷、劉向、揚雄的高度評價。《后漢書》李賢《注》曰:“ 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5]186王充晚年還受到“肅宗(漢章帝)特詔公車征”的禮遇。其消極影響,最真實的景況見諸他自己的敘說。他在《自紀篇》敘述了《論衡》面世之后的種種非議乃至人身攻擊:
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秉階,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于眾而突出曰怪。君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寶斯而多賢?”[4]287
詆毀者認為,王充既無祖宗的美德做根基,又沒有先人詩文篇什、學術著述遺產作繼承,即使他所撰論文,博大華美,因無學術淵源,最終也是成就不高。盡管論事說理,出類拔萃,標新立異,但是,有如自然界的災變、異類、妖魔、怪物。王充祖先是誰?為何史書不載?況且他的學問,既非來自墨家的路徑,又不是出于儒學之門,所發議論幾十萬言,都是妖言亂語,怎能受到珍視和贊美?從桓譚及其《新論》受到俗儒“排抵”的境遇看,王充及其《論衡》,備受攻擊打壓的事實是存在的。這些恰從反面印證了王充的人格魅力與《論衡》在當時的影響。
據李賢《注》引東晉著名學者袁崧著《后漢書》的資料,可見證王充的《論衡》,長期在“中土未有傳者”,只是他的故鄉偶有發現[5]186,至漢末,王充終究被人們視為“異人”,而《論衡》則被看作“異書”。王朗因從《論衡》中受益匪淺,才學、能力大有長進。避難中的蔡邕,慧眼識珠,視《論衡》為寶典而密藏,招致好學者入室搜尋。顯然,王充形象及其《論衡》,在漢末已成為士子們為人行事、學以致用的精神食糧。
而在王充本人看來,其才情說“奇”也不“奇”,是自幼養成的勤奮好學品質使然;其論文說“異”也不“異”,是他為學博覽多識,為文慎獨潛思的必然結晶。他的《論衡·自紀》篇有如自傳,一個生性聰穎好學、沉靜多思、志存高遠、見識卓越的大學者形象,躍然紙上。不難想象,漢末士子經由蔡邕、王朗等人的現身說法,讀《論衡》至此,當是感悟多多,感奮切切。王充出身寒門,可謂庶族士子的代言人。他的成功及其所釋放的品格魅力,正是當時名士隊伍特有的強勁的正能量。這種正能量作用于文學發展,定然具有劃時代意義。
2.關心政治,富于理想,經世致用。一般說來,東漢名士都受過良好的正統經學教育,儒家的天下為公、仁政愛民思想,深深地扎根于腦海。隨著漢皇室日漸式微,天下愈益動蕩,尤其是在宦官集團與外戚集團更相擅權的時期,名士的主流思想是憂國憂民,敢當天下之大任。因此,關心政治,富于理想,積極用世,遂成名士隊伍整體形象的基本特征。王符(約85-162)是此中頗為典型的人物。
《后漢書·王符傳》述其生平很簡短,卻以很大的篇幅錄載其代表作,旨在以文見人。這些代表作也確實展現了王符的胸襟懷抱與才情: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 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鄉人所賤。 和安之后,世務游宦,當涂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余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2]479
范曄認為,《潛夫論》有五篇代表作:《貴忠篇》《浮侈篇》《實貢篇》《愛日篇》《述赦篇》,集中詮釋了王符終生的“志意蘊憤”。筆者理解,其“憤”有三:一憤僅因其母是孤女,自己就為“鄉人所賤”——民俗粗鄙低劣,故而自貴自重,不齒于流俗。二憤當道權貴、名門望族相相薦引,阻塞寒門士子進取之途——庶族讀書人陷于辛酸難堪的“游宦”之中,他因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不屑于茍且權門。三憤“衰世之務”:執政者本末倒置,名實相違;豪族權貴,朋黨為奸;朝廷歌舞升平,為虛造假,欺世盜名——政治黑暗,國將不國,故而發憤援筆,激揚文字,縱論國是。
王符以《潛夫論》名書,亮明自己卑微的地位和身份,公然挑戰當時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凝聚著大義凜然的真男兒氣概,也著力彰顯了一代名士“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豪邁胸襟。《潛夫論》除《敘錄》之外的三十五篇,多是討論治國安民之術的政論文章,也涉及到一些哲學問題。《敘錄》所述,是這三十五篇作品的寫作動機與意旨,也是閱讀理解《潛夫論》的指要。布衣王符,向往明君尊賢任能、信忠納諫,賢才勤政為國的太平盛世。因此,他的《潛夫論》對當時社會政治進行了廣泛而尖銳的批判。他歷數了現實中經濟、政治、邊防、社會風俗等方面的黑暗情形,尖銳地指出禍亂的根源在于統治者昏暗不明,“當途之人,咸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潛夫論·敘錄》)。這就充分體現了庶族名士的政治敏銳性及其積極進取的情懷。《后漢書·王符傳》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屐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2]484
皇甫規出身將門,是當時頗有影響的文武兼備的名士,多有戰功與政績,還有“賦、銘、碑、贊、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文學作品。他蔑視譏諷買官者,而禮遇一介布衣的儒者王符,不只是說明二人志趣相投,互為敬重,更在于這件事,透露了王符及其《潛夫論》所展示的“道義”,在當時得到了名士和普通百姓珍視的信息。這也是當時學界泰斗級人物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與他相友善的根本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王符代表了寒門士子的政治理想,彰顯著真名士超然拔俗的品格魅力,其人文影響是深刻而廣泛的。
毫無疑問,王符、皇甫規本屬于兩種不同出身、不同身份的名士,他們的為人行事,具有相同的人文價值訴求,這對桓帝、靈帝、獻帝時期的士子來說,是一種崇高的榜樣作用,必然內化為建安作家文學創作中特有的精氣神。
3.名士效應下的人文氣象。仔細研讀《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前四史”,總會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漢代尤其是東漢的廣大名士,構成了社會精英群體。他們的成名之路,演繹著各自人生中為學、為文、為人、為政、為事、為業的清晰足跡。這些足跡,訴諸他們生前的社會存在及其影響形態,是行為的、具象的、物質的;訴諸他們身后的社會存在及其影響形態,或傳說故事,或書面著作,是一種形諸物質與精神相結合的社會精神文化。這兩種存在與影響相互映照,經過歷史檢驗與篩選,凝練成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文化要素,我們姑且稱之為名士效應下的人文氣象,換言之,就是名士隊伍所彰顯的放眼未來,銳意經籍,提攜后進的風尚。
自從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實行推舉與考試并重的選人用人制度以后,國家在大力興辦以經學教育為主體的官學,奠定儒家文化主流地位的同時,允許各種形式形制的私學暢行,教育成為“文治”中的重頭戲。蓬勃發展的教育事業,推動思想文化領域避免了專制,形成了開放創新、諸家文化并存的良好生態。為教育服務的典籍整理,成為朝廷文化建設的重要抓手。經漢武帝大力提倡,淮南士子群體等初步努力,劉歆、劉向父子集大成,到東漢班固、賈逵、許慎、馬融等再為簡古鉤沉,遂為士子的立言、為政構建了博大的思想寶庫,又為他們治學著述拓展了廣闊的研究領域。受益于其中的東漢名士,則積極奉獻于其中。因而,放眼未來,銳意經籍,獎掖后進,是他們在亂世保持樂觀進取本色不變的重要行為方式。范曄《后漢書·儒林傳》所錄劉昆等43個儒林名士,他們在做學問的同時,莫不以培養后進為己任。順帝時的蔡玄,“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2]761。即便是建安時期大亂中的謝該,也是“門徒數百千人”[2]760。
在大名士李固、李膺背后的荀淑,是眾多被忽視的隱性名士中,尤為值得我們關注的人物。據《后漢書·荀淑傳》載: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征拜郎中,后再遷當涂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勛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2]595
荀淑是戰國后期儒學大師荀況的后裔,可謂家傳儒學稱名于世。他因堅持儒學正統,不作穿鑿附會,而被“俗儒所非”。因在對策中,他譏刺了以梁冀為代表的外戚及內寵,遭到貶謫,是個政治上備受打壓而又無怨無悔的悲情名士。他為官地方,盡顯才干,理政斷案,如有神助;他棄官歸隱,表面看,是不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奉行儒家亂則隱、治則見的處世理念,而內在目的,則是“養志”,亦即積極準備將來有更大的作為。“養志”的重點,不只是增加自己的德行涵養,更在于著意獎掖培養后進之士,此中包括家族子侄。同時,他著力興辦產業,以救助與自己志同道合的弱勢友人,這并非普惠性的慈善事業,而是注入了特定人文價值的以物質為手段的“濟世”行為。他的八個兒子:荀儉、荀緄、荀靖、荀燾、荀汪、荀爽、荀肅、荀專,并為名士,“時人謂八龍”。其中尤以“慈明(即荀爽)無雙”。他的兩個侄子荀昱、荀曇,“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大名士李固、李膺等,均出自其門,無怪乎他們后來成為反對外戚政治、宦官政治的領袖了。
建安時期的荀氏家族,仍是名士輩出。荀淑的孫子荀悅、荀彧,憑著淵博的學問,做了漢獻帝的老師。荀彧在政治上更有作為,又為曹操所害,其悲劇人生在后世有很高的關注度。其實,荀悅在當時乃至歷史上的影響,并不亞于荀彧。他雖然是名門之后,但是在先天稟賦、家境貧窮、沉靜好學、勤于著述等方面,與王充驚人地相似。盡管曾躋身上流社會,然而終究“謀無所用”,十分無奈地把滿腹經綸訴諸學術著作中,他影響于當時和后世的形式與效果,也與王充一樣。由此可見,荀淑及其子孫,屬于名士中的“奉官守儒”群體,出仕即堅守政治節操,頗顯為政才干,且素以識賢、禮賢、舉賢而聞名;歸隱則以培養后來人為己任。他們出仕與不仕,對社會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一如既往,不懈地向社會傳遞著正能量,弘揚老祖宗的作風與氣派。應該說,這是漢代經學教育成效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
在東漢末年名士中,真正以文學研究、文學育人終其一生的是鄭玄(127-200)。他的生平行事與業績,證明他是“放眼未來,銳意經籍,提攜后進”這一人文精神最真誠的實踐者。據《后漢書·鄭玄傳》載:
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玄自游學十余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2]358
青年的鄭玄,不屑于父親對他為官作吏的安排,立下研習經學的志向。他沖破重重阻礙,游學名師大儒,達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境界。對此,他在病中寫給兒子鄭益恩的信里坦言:自己游學關中十多年,師事名師,終于學有所成,目的不是為了封官授爵,光宗耀祖,而是志在“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2]359。他在成名之后,有多次進入官場的機會,一是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而召用,不就;二是得勢時的袁紹待為上賓,舉為茂才,表為左中郎將,也不就;三是漢朝廷公車征為大司農,又托病還家。而最讓他醉心的是經學研究,著書立說,培養復興國家的后來人。
鄭玄潛心著述,以古文經說為主,兼采今文經說,遍注群經,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他箋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等書,并撰寫《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等專論。其中《毛詩譜》是漢代詩學的著名代表作之一。鄭玄素有“純儒”之稱,是譽滿齊魯大地的一代宗師。據《后漢書·鄭玄傳》所載,他的知名門生,先后成為漢朝廷和魏國的重量級人才。鄭玄生前對自己的事業頗感欣慰:“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后人之羞。”[2]359這個意味深長的自鳴,為淡泊名利、執著學問、樂于育人的人生,畫了一個看似并不流光溢彩的句號,卻是贈給兒子及建安士子們的彌為珍貴的人生箴言。
漢末大學者、大名士蔡邕(132-192),是個最切近影響建安士子成長的“通才”型藝術大師。他少博學,好辭章,精通音律,善篆、隸二體書法,又創造了頗有影響的“飛白”之書。廣泛的愛好,成就他在經學、文學、音樂、書法等領域,均達到了很高的造詣。靈帝時,召拜郎中,不久升遷議郎,因上書直諫朝政得失,彈劾宦官,被流放朔方;遇赦后,畏宦官陷害,遂舉家“亡命江海,遠跡吳會”達十二年之久。據陳壽《三國志·王粲傳》載:
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6]445
又據《三國志·鐘會傳》注引《博物記》:“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6]592蔡邕基本上兌現了諾言。阮瑀與蔡邕是同鄉,也曾師事蔡邕。蔡邕始出仕,是靈帝建寧三年(171)“召辟橋玄府”,已是年過四十了,足見布衣的蔡邕,也是以治學授徒為事。他晚年得意時,門前造訪者絡繹不絕,堂上賓客滿座,當不只是仕途求進者,更多的應是經學、文學求教者。他禮遇少年王粲,其言行舉止是那樣真誠感人。一方面,他宣示了自己對前輩大名士“王公”(王暢)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委婉地告訴在場賓客:“豎子可教”,視王粲為自己的學業傳人,袒露了一代大師識才、愛才、育才的拳拳之心。
蔡邕平生勤于寫作,著有詩、賦、碑、誄、銘、贊等一百零四篇。其中《述行賦》,不僅開東漢小賦紀行題材的先例,且體現了十足的現實批判精神。賦中直敘了他從陳留往洛陽途中的聞見,聯想古人行事,諷喻當朝時政,揭露統治者荒奢淫逸,傾訴百姓貧困疾苦,寫下了辭情沉痛的名句:“窮變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消嘉谷于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這篇紀行小賦,對建安作家來說,堪為藝術創新的標本。在一次臣僚們偶然談及董卓被誅之事時,蔡邕不自覺地發了一聲嘆息,被司徒王允以“懷卓”之罪下獄。大難臨頭,他關注的不是身家安危,而是“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他希望像司馬遷那樣忍辱負重,完成史著。“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后史,為一代大典。而(同爾)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這是說情施救之言,更是知人論世之語。不難想見,蔡邕死后產生巨大反響的情景:“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2]581蔡邕未寫就的《漢史》文稿,在李傕、郭汜之亂中消失殆盡,但是,他的風范,當永遠留在“建安文學”中了。
總之,名士效應下的人文氣象的形成,既功在當時,又利在后代,因為它為結束天下大亂,實現天下大治,尤其是為文學藝術的發展,培養了至為重要的文化與人才資源。
綜上所述,東漢末年,朝廷在政治上倒行逆施,造成權奸當道,吏治黑暗。亂世中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當時的名士隊伍。善良的百姓希望教育事業能培養出更多的真名士,以替換奸臣酷吏,更希望名士隊伍中,產生力挽狂瀾的治世能人。在名士隊伍內部,隨著批判讖緯之學的日益深入,讖緯之學應用派名士,鑒于殘酷的社會現實,自覺與不自覺地轉變了風氣,有意與無意地向讖緯之學反對派靠攏,促使名士中更多的人憂國憂民,企望自己對濟世安邦有所貢獻,也希望自己所處的群體,有人脫穎而出,成為治國安民的英雄。因此,銳意經籍、著書立說、教書育人,訪賢、知賢、愛賢、論賢、品賢、舉賢、育賢,成為名士隊伍基本的人文風尚。勢位低微的名士曹操,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受到人們關注的,如李膺的兒子李瓚臨終時,囑咐其子李宣等人說:“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2]642橋玄也曾對曹操說:“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2]502許劭則說曹操:“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2]653各政治軍事集團的領袖,一方面歡迎有更多的名士投入自己的陣營,另一方面,希望名士隊伍孵化出更多的人才來為我所用。這樣,“人才”遂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百姓寄安民興邦的希望于人才;士子刻意砥礪成才;名士出仕盡顯才干,隱逸則傾心育才;覬覦大漢江山的勢力集團,則把招納、籠絡、爭奪人才作為最重要的謀略。
然而,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先天生成的劣根性,決定了當時各勢力集團的人才戰略,脫不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惟我性桎梏,即如曹操所言:“寧我負人,毋人負我。”[6]4當時的名士一旦坐上他們的戰車,為其所用順心,則是香餑餑;稍有差池,輕則貶謫驅逐,重則格殺勿論。這就奏響了漢末名士隊伍的命運交響曲:志存高遠、銳意進取,又苦悶彷徨、愁腸郁結;既慷慨豪壯,又凄愴悲涼。這種命運交響曲所揭示的人文特質,直接作用于“建安文學”,一是為其文化背景,浸染了獨特的時代色彩;二是為作家的文學創作實踐,定下了全新的審美格調;三是激活了一代作家放眼天下、關注民生、感悟人生的赤子情懷。這就構建了東漢名士效應與“建安文學”的內質性關系。
[參考文獻]
[1]呂不韋.呂氏春秋[M].// 諸子集成:六.上海:上海書店,1986:38.
[2]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7.
[3]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M].4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46.
[4]王充.論衡[M]// 諸子集成:七.上海:上海書店,1986.
[5]范曄.后漢書[M]//二十五史: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6]陳壽.三國志[M]//簡體字本前四史.北京:中華書局,2005.
(責任編輯:李天喜)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簡介:何新楚(1949-),男,湖北安陸人,湖北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中圖分類號:B25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824(2016)04-0042-09
On the Phenomeno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He Xinchu
(SchoolofArtsandMedia,HubeiPolytechnicInstitute,Xiaogan,HubeiProvince, 432000,China)
Abstract:When studying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Eastern Han Dynasty, we have 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arried out preliminary study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humanistic atmosphere, which is the origi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wo divisions of celebrity group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characters of celebrities’ images and the humanistic atmosphere due to the effect of celebrities. In order to make further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background for “Jian’ an Literature”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a new horizon was opened. In fact, the glorious and resplendent “Jian’ an Literature” is inseparably linked to the phenomeno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Eastern Han Dynasty; celebrities; humanistic atmo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