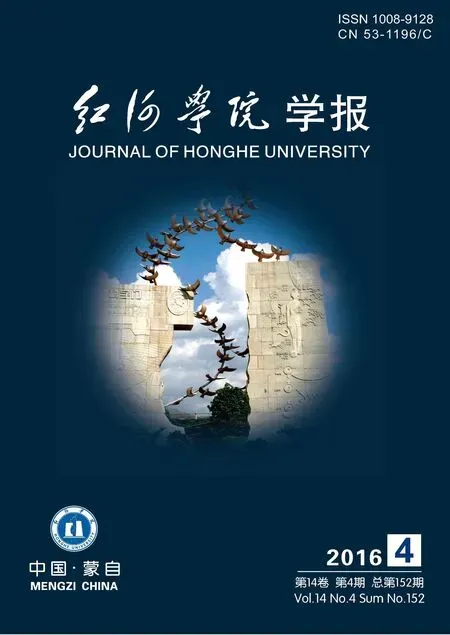解讀《德伯家的苔絲》之生態維度
林曉青
(三明學院外國語學院,福建三明 365004)
解讀《德伯家的苔絲》之生態維度
林曉青
(三明學院外國語學院,福建三明 365004)
生活在英國工業革命處于全盛時期的托馬斯·哈代是一位具有超前的生態意識的作家。在經典之作《德伯家的苔絲》中既有對自然風景的細致刻畫也有對工業化生產帶來的生態危機的揭示。文章以新興的生態批評為理論為依托,從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切入,解讀作品所蘊含的生態思想,旨在激發人們與哈代產生共鳴對自然心懷敬畏,對環境盡心保護。
苔絲; 生態批評;工業文明;農業文明;生態危機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4.017
托馬斯·哈代生活在大英帝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彼時正值英國經濟文化的全盛時期,工業革命抵達巔峰狀態,當時人們正沉浸在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工商業繁榮的喜悅之中,對工業文明之下的“欣欣向榮”盲目樂觀。哈代對此冷靜旁觀,清醒地意識到人類以自我為中心、狂妄自大、欲望膨脹、對自然索求無度最終危及的是人類生存的空間,陷人類自身于生態危機的深淵。哈代將這份關注與思考投射在作品創作中,因而,無論是在其小說還是詩歌當中都能閱讀到他對自然的深切關照。哈代一方面以靈動的筆觸展示著大自然無以比擬的美,另一方面以現實主義批判的眼光控訴著人類對于自然的肆意破壞。哈代的遠見卓識、深憂遠慮成就了哈代生態文學大師的美譽。
當人類在享樂主義的思維模式下不斷追求物質文明帶來的短暫歡愉之時,伴隨著的是大自然被過度消費,在人類對它無限制的開發和利用當中,自然生態危機隨之而來。機械化生產代替傳統勞動,使人與人之間缺乏有效的情感交流,彼此變得冷漠疏離、關系異化,社會生態危機的出現在所難免。在犧牲自然田園風光以換取城市化進程的過程當中,人們對自然的敬畏心逐漸消淡,人類在自我為中心的路上越走越遠,迷失在欲壑難填的困境里,精神生態危機相伴而生。自然生態危機、社會生態危機以及精神生態危機都是生態批評視域之下至關重要的生態維度。生態批評是一個非常龐雜、開放的批評體系,同時兼備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的特征。“生態批評立足于生態哲學整體的觀點、聯系的觀點、將文化與自然聯系在一起,揭示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類文明的危機、人性的危機、想象力的危機。其理論內涵為重新闡釋文學作品,挖掘創作文本中體現出來的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批判滲透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反生態觀念,重新構建文學經典。”[1]16《德伯家的苔絲》很好地體現了生態批評視野下的不同維度之中的生態危機,以此為依托解讀作品中的生態思想,探析哈代的生態觀。
一 自然生態危機:自然的夢幻與幻滅
哈代將自身對于自然的尊崇喜愛訴諸筆端,在哈代的作品里不缺自然的玄遠、靜謐、柔美與瑰麗奇特,然而這些讓人迷戀的無限風光最后往往招致人類的破壞,難以保持原貌。其原因主要在于哈代筆下的風景往往與人物命運息息相關,并不止于單純地描繪自然景色。“那些令人無法忽略的景色優美時刻,如小說開篇的馬洛特村五月節游行跳舞,還有小說結尾處懸石壇上的日出,都讓人們相信,哈代未經雕琢的電影表現手法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景色描寫。”[2]225其實質上,苔絲生活場地的每一次變化都與所從事的職業及不同的景色相聯系。伴隨著苔絲的勞動環境越來越惡劣,承擔的工作越來越繁重的是機械化生產的參與越來越多,風景遭受的破壞程度越來越嚴重,作品中自然美景從夢幻到幻滅正是苔絲的命運從生機勃發到黯然消亡的過程。
苔絲出生在田野綠意蔥蘢、大氣清澈透明、景色如詩如畫的馬洛特村,“這兒距離倫敦雖然不過四個小時路程,它的大部分地區卻還是旅游者和風景畫家足跡未曾到過的。”[3]8在這片未經開發的土地上生長著未諳世事、天真爛漫、未經雕琢、自然純樸的苔絲。由于苔絲的疏忽家中賴以生存的老馬死于非命,這迫使苔絲不得不離開佳木豐沛的出生地去從事新的謀生職業景色也隨之變化:“廣闊無垠的景物往四面伸展,背后是苔絲從小生長的青山
坐落在川特里奇的杜伯維爾莊園是“一座純粹為了享樂而建造的鄉間別墅”[3]33這新建的大廈色彩艷麗在溫和的自然環境里張揚、突兀與周邊的自然景象格格不入。而家禽飼養員苔絲的工作場地在一幢古老的茅屋里,“茅屋所在的場地原是個花園,現在踩得平平的,鋪了沙子,成了個方形的廣場。”[3]52這里的自然明顯已有人為加工的痕跡,按人的需求進行了改建。莊園里還有催熟的草莓與溫室里嬌艷的玫瑰,他們都無需遵從自然的生長規律,在現代技術手段之下按人的意志開花結果。如果說花床、果園、溫室只是年輕的少莊主阿歷克對自然生長規律的違逆,那么他對“自然之女”苔絲的侵犯已然注定了自身命運里無可挽回的悲劇。自然對于人類的肆意破壞絕不會無動于衷,她必將對阿歷克做出審判,因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在第一線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在第二線和第三線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它常常把第一個結果重新消除。”[4]304-305阿歷克看似主導了自然,利用技術手段成功地違抗了自然,但等待他的則是自然的報復,自然之手將他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從馬洛特村到川特里奇,經歷的肉體與心靈雙重折磨的苔絲已明白了人世之險惡,她回到了家鄉,離群索居,在大自然的撫慰中慢慢走出陰霾:“她在寂寞的山巒和峽谷里默默獨行,和周圍的自然元素化成了一體。她那悄悄閃動的身影化作了景物的的一部分。”[3]85她與自然相處如此和諧,很好地詮釋了哈代人與自然理當并駕齊驅,“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大自然仿佛有著神奇的魔力,具備療傷的本領,與自然身心交融的苔絲懂得了過去的終將會成為過去,時間能把一切苦難不幸淹沒,并不會因為她的痛苦而有所改變:“樹還是照樣地發綠,鳥兒還是照樣地嬌鳴,太陽還是照樣地輝煌。她再憂傷,這熟悉的環境也不會因之暗淡;她在痛苦,它也不會因之凋萎。”[3]91人類究其實只是浩瀚自然中渺小的一份子,唯有心懷敬畏,真誠以待,才能獨善其身,享受生命的自由與美好。
在自然中汲取了力量的苔絲為了遵循生命的本能去尋求更多的歡樂,第二次離開了家鄉,來到了“空氣清爽可人、質地輕靈”的泰波特斯從事擠奶工的工作。“佛魯姆河的水卻清澈得如同福音傳播者所見到的的生命之河,迅疾得如流云的影子,還有卵石歷歷的淺瀨,整天想著天空潺潺碎語。”[3]105生機勃勃、美麗富饒、迤邐磅礴的牛奶場,讓苔絲精神煥發,宛若新生,在這里苔絲度過了人生中最愉快的時光。她自然的天性發揮到了極致,連脾氣最壞的奶牛在她溫柔的手指下都變得百依百順。年復一年沉浸于各種學問,未曾對自然加以關注的克萊爾在苔絲到來之后,被她的自然本色深深吸引,他不由感嘆“那個擠奶姑娘真是個大自然的女兒,多么鮮活,多么天然純真啊!”[3]121他們傾心相愛,攜手走進婚姻殿堂。然而在新婚當夜,苔絲坦承了從前所受過的屈辱,思想被傳統的基督道教準則所左右的克萊爾無法體諒苔絲的艱難處境,棄她于不顧,選擇遠走巴西。這對苔絲而言無疑是重重的一擊,婚姻失守的她再次踏上顛沛流離的艱辛人生路。
心靈再次受到重創的苔絲勞動場所再一次發生轉移,她從泰波特斯來到了燧石頂,景色再次變幻,初踏上這片土地,展現在她面前的是:“一片淺洼地上,有一個殘破不堪的荒村”[3]281而且“那兒的凄涼冷落幾乎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四面一望連一棵樹也沒有,在這個季節也沒有綠色的草場;除了休耕地便只有蘿卜;土地被結扎得十分單調的樹籬分成了一大片、一大片。”[3]283在燧石頂苔絲的勞動顯得“那么單調、沉悶、毫無變化”[3]313然而繁重的勞動并沒有使她屈服,抱著對愛人回歸的熱切盼望,苔絲自尊自強地與命運抗爭,只是冷酷無情的命運再一次將難題擺在了她面前:母親病重,父親去世,弟妹衣食無著,家人流離失所,愛人遲遲不歸,生活的重重困難再一次把苔絲逼入絕境。在現實困境的步步威逼之下苔絲最終淪為阿歷克的情婦,移居桑德波恩。
幡然醒悟的克萊爾追尋苔絲的腳步來到了桑德波恩,徘徊在這個舊世界中的新世界:“他能在樹木掩映之中和星光襯托之下看到它高聳的屋頂、煙囪、陽臺和塔樓。這也是一個由一幢幢獨立的大廈構成的城市……”[3]377苔絲在這新興的現代化城市里,猶如受困于籠中的金絲雀。阿歷克代表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征服了象征著自然,代表著農業文明的苔絲。然而“哈代還是相信外部世界的物質力量,他不支持,甚至不容許個體的絕對勝利,他反復強調社群的重要和環境的力量”[2]106最終,自然借助苔絲之手終結了阿歷克的生命,這是生態文明完成了對工業文明的終極復仇。人與自然若不能和諧相處,那便只能是兩敗俱傷的結局。
“人類歷史長期以來是建立在農業文明的根基之上的,農業文明的一大特性是人與自然尚且保留著較為密切的親和關系。”[5]209以生態批評的視角來看,在工業文明的推動之下,人類不斷犧牲鄉土田園風光以交換城市的高速發展,這必不是現代化值得推崇的成功經驗,而恰恰是人類理應反思之處。隨著工業革命影響的逐漸擴大,隨著時代的潮流奔流不息向前涌去,大量的維持著農村傳統風俗的農民失去了土地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勞作模式,“只好往大的人口中心逃亡了”。[3]352短短幾年的時間,一切面目全非,鄉村自然景色分崩離析,苔絲不無凄涼地發現,祖先遺址“周圍的丘陵與山坡當年原是園林,現在樹木已被砍個精光,土地也分割成了小片。”[3]361。巴西歸來的克萊爾再次經過當年第一次遇見苔絲的草場時,驚覺“那里也是一片衰敗的景象”。[3]373哈代飽含深情地親筆毀滅了自己精心描繪的令人心馳神往的自然美景,他以自然風光從夢幻到幻滅的過程無聲控訴著工業文明無孔不入式的入侵給農業文明帶來的傷害。
二 社會生態危機: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異化與彌合
“自然讓人曾經是多么幸福而良善,而社會卻使人變得那么墮落而悲慘。”[6]16可是人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厭世逃避也不能擺脫社會對人產生的影響。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一旦失衡,社會生態危機一觸即發。《德伯家的苔絲》中,人與人的關系異化有幾個方面的體現。一是苔絲與父母的關系上。天下父母心,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但是苔絲的父母親卻把女兒當成擺脫貧困的工具。鼓動她去認親,一心希望她能嫁給有錢的少爺,她的母親“幾乎是從她女兒出生之日起就在為她自己挑選著乘龍快婿呢。”[3]43只要有錢,愛不愛自己的女兒似乎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苔絲要到有錢的本家莊園里做工了,父親已經喝起了慶賀的酒,在心里頗為篤定地認為女兒一去將攀上高枝,麻雀變鳳凰了。事情并未盡如人意,苔絲遭到所謂的本家闊少爺阿歷克的奸污懷孕產子,母親希望她能以此要挾阿歷克締結婚姻,以過上富裕的生活。但苔絲卻選擇獨自承受一切,她無法跟自己不愛的人共同生活,寧愿選擇面對現實社會的責難也不愿屈就于沒有愛情的婚姻。
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在苔絲與阿歷克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上得到更充分的體現。苔絲到杜伯維爾莊園去認親,遇見了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阿歷克·杜伯維爾,從此活在了此人的陰影之下,開始了悲劇的一生。成長于民風淳樸村落的苔絲對人世之險惡懵懂無知,最終被玩弄女性于股掌之中的阿歷克騙取了貞操。她只能問責母親“太太小姐們知道要防范些什么,因為她們讀小說,小說里告訴她們這些花樣。但是我是沒有機會用那種辦法學習的,而你又不幫我!”[3]83家庭貧困缺乏教育機會是苔絲失貞的一個因素,但阿歷克的成心糾纏才是主要原因。受了傷害的苔絲選擇離去,但命運之神并未就此給她予享受生命的自由,它讓苔絲在生活最為艱難無助的時候重逢了阿歷克。此時的阿歷克已經是一位披著仁慈的宗教外衣,道貌岸然的牧師滔滔不絕地給農民布道,真是多么具有諷刺性的一幕。再見苔絲,阿歷克馬上拋棄了子虛烏有的宗教信仰露出本來粗鄙惡俗的樣子,對她糾纏不休,威逼利誘。苔絲自強自立,絕不依附男人。但是,基于巧合或是必然,苔絲為了家人生計再一次向命運低頭,委身阿歷克。偏在此時備受挫折明白真愛可貴的克萊爾從巴西歸來,欲與妻子再續前緣,阿歷克對此冷言嘲諷,觸到了苔絲的底線,她一刀結束了這個毀了她幸福的惡魔。而苔絲也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法律后果,付出生命的代價。
另一方面,苔絲與當時的社會也存在矛盾與沖突。苔絲生活在資本主義侵襲農村并強烈沖擊固有的風俗傳統的維多利亞時代,美麗聰慧、善良純真、勤勞簡樸的她對經濟拮據的家庭主動承擔責任。她處于社會的下層,作為一個無權無錢的農業勞動者,毋庸置疑會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與欺凌。這些壓迫與欺凌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有經濟的、權勢的、肉體和精神的、還有宗教的、道德的、傳統觀念的。盡管苔絲大膽反抗傳統的道德觀念,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然而她卻不能從心理上徹底擺脫世俗道德觀念的羈絆。當社會輿論與深植于苔絲內心的傳統道德觀念跳出來阻止苔絲追求幸福的步伐時,她自己也猶豫了,自我懷疑了,也認可自己是有罪的,是不貞潔的。因而即便她離開故土,時間與空間都將協助她將往事掩埋的時候,她依然卸不下自己身上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只能一再拒絕克萊爾的追求,明明想靠近卻只能選擇躲閃。雖然苔絲最終聽從了內心的呼喚,與克萊爾沐浴愛河,只可惜知道了苔絲過往的克萊爾狠心拋棄了她。她卻為了維護丈夫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委屈自己遷居別處去從事繁重的體力活不能回到泰波特斯的牛奶場工作。“她的返回難免會使她那備受崇拜的丈夫遭到譴責。還有,別人的憐憫她也受不了,別人在她背后對她的奇怪處境的竊竊私語更叫她難堪。”[3]275克萊爾對苔絲的放棄,使苔絲精神上背負了更重的負擔,“她害怕城市,害怕大戶人家、有錢人家、害怕世故,害怕農村以外的習俗禮數,因為黑色的憂患就是從上流社會來的。”[3]275社會給苔絲造成了內心難以撫平的創傷。哈代賦予苔絲堅強的信念,她始終勇敢地同命運搏斗,然而反抗的結果卻是悲劇性的。
最終苔絲從自然中來,回歸到自然中去,如梭羅所言:“最甜美、溫柔、鼓舞人心的社會,都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7]101苔絲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對自然的回歸,找到了內心世界里最溫暖舒適的人間社會,再沒有嘲笑與傷害,只有安息與長眠。這是社會生態危機的環境之下苔絲能夠得到的最好的結局。
三 精神生態危機:心靈的迷失與回歸
在《德伯家的苔絲》的勞動場景中可以看到工業文明簡單粗暴地把自然當作原材料,把人當作生產機器,不僅把自然破壞得千瘡百孔,也使人的精神世界癱瘓、喪失生命活力。工業文明摧殘的不僅僅是自然同時也扼殺人類天性中的美好。唯有回歸自然、回歸本性,才可以挽救人類。
作品中苔絲的社會身份隨著勞動場所的轉移而變化,她這樣不斷遷徙的狀態伴隨著的是她精神上的飄零,歸屬感的缺失。肩負養家糊口使命的苔絲原本可以活得順其自然,在天然淳樸的馬洛特村過著雖然艱苦但是精神狀態健康、情緒飽滿、充滿希望,村里“每個姑娘感到外在太陽的溫暖的同時,她們的靈魂也還沐浴在各自的小太陽的光中,那是一種美夢,一種純情,一種習慣,至少是一種渺茫遼遠的幻想。”[3]11但是,父親對財富的渴盼將苔絲推出了馬洛特村,讓她自此遠離自然,走向了居無定所,精神漂泊無依的悲慘人生。
不同于馬洛特村,川特里奇從環境到鄉民都已然是被工業文明浸淫的狀態:“川特里奇一帶以它的年輕婦女的輕佻惹人注目,這也許絕妙地反映了大梁子一帶的精神狀態。這一帶還有個歷史悠久的毛病:酗酒。附近農莊上的主要話題是:攢錢沒有用。”[3]58“吃光、用盡、花完”為特征的資本主義極致享樂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了川特里奇的主導。在這樣的民風里,天真純凈的苔絲遭遇肉體和精神上的苦難似乎顯得理所當然,合情合理。在工業化的社會里,勤勞樸實的苔絲難以找到容身之所,可是當她身心俱傷,回曾經遠離城市喧囂的生養之地時,面對的是物卻是人非的無奈。
苔絲在馬洛特村默默地將息了兩年多之久,這期間工業文明倚仗著蠻橫的力量滲透到了這個原本“峰巒環抱,與世隔絕”的原生態村莊,小麥的收割交付于強大的機器,勞動人民機械地重復著捆麥捆的動作“單調得像時鐘一樣”[3]88麥子收割機強勢霸道“機器每走一圈,圍著麥地的窄巷便變寬一片,直立的小麥的面積也隨著早上時光的消逝而縮小一片。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還有蛇,紛紛后撤,好像躲進了城堡,并不懂得它們的避難所也壽命有限,也不懂得毀滅正等待著它們。到了下午它們的藏身之地便會縮小到越來越可怖的程度。”[3]87弱小的生命對大型機器心懷恐懼,無處藏身,以死而終,這是機器文明對自然的漠視與扼殺。當人類對自然喪失敬畏心,自然的報復也就開始了,其結果必然是自然生態及精神生態失衡。或許,即便苔絲沒有離開馬洛特村,她也遲早會以某一種形式被傷害,因為忽視自然生態的工業文明已無處不在,代表著自然的苔絲已無處可逃,滋養著她成長的村莊再不是原來的樣子。
輾轉流離,像一只失去家園的小鳥在尋找詩意棲居地,始終不能如愿。從馬洛特村到川特里奇然后到泰波特斯而后是布萊地港繼而來到燧石頂,苔絲的精神負擔越來越重,當她抵達燧石頂時,苔絲已經像一只“掉進了羅網的小鳥”[3]290機械化的工作不僅傷害了她美麗的容顏,還滋生了心靈的褶皺“此刻,她身上已沒有絲毫青春激情的跡象”[3]280在燧石頂的工作幾乎都是協同機器而進行,脫粒機一轉動“對她們的肌肉和神經忍耐力都會提出苛刻蠻橫的要求”[3]325歇工的時候“由于機器震動得太厲害,她的兩個膝蓋已經弄得顫顫巍巍的,幾乎連路都走不動了。”[3]327無論是切蘿卜機還是蒸汽脫谷機,本意是讓人民的勞動更加容易,減輕負擔的技術發明,其實質上去是讓勞動變得重復單調,動作機械化,精神疲乏卻得不到片刻喘息的機會。“持續不斷的震動透進了她身上的每一根纖維,把她投入了一種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雙手脫離了意識的支配,只是機械的工作著。”[3]333人成了機器的奴隸,失去了自我意識,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沒有了生命活力“原先精力最充沛的人也一個個弄得面無人色、眼圈發黑了。”[3]333在這遠離自然的工業文明壓迫之下,苔絲的生命逐漸失去了華彩,當她與殘酷現實的抗爭失敗成為阿歷克的情婦,也意味著她精神上的死亡,成了只為家人而茍活的無魂之軀。
在生態批評視域中,農業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對自然的一種破壞,“但相較于工業文明而言,由于農業文明中大自然是直接決定人類命運的主宰因素,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多地呈現出相融相諧的一面。”[1]270農業文明中的人類仰仗自然,對自然崇拜、尊重、順應自然而動以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在農業文明下勞作的人民,磨練出勤勞勇敢、艱苦樸素、誠實守信、樂天知命的優良品質。人與自然形成共生共榮的和諧關系,這種共生相攜的關系又促進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睦友善,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然而工業文明下的人類盲目自大、唯我獨尊,懷揣無盡的物欲與征服欲對自然巧取豪奪。“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現代社會中自然的衰敗與人性的異化是同時展開的。人與自然的沖突不僅傷害了自然,同時也傷害了人類賴以棲息的家園,傷害了人類原本質樸的心。呵護自然同時也是守護我們自己的心靈。”[5]55當人類在追求物質享樂主義的過程中忘卻人與自然具有整體性,彼此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時,必然迷失本心。其實精神生態并不與物質基礎成正比,相反,物質過于豐富并不利于精神和文化的發展,反而是給享樂主義的滋生提供暖房。湯因比在研究文明發生時就指出,艱苦的環境有利于人的精神成長。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長”那就應當對萬物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而不是站在高處藐視自然、駕馭自然、索取無度。有科學家預測,一旦人類退出地球舞臺,只需500年,我們留下的印記就基本上淡渺無痕。大自然有自身的修復系統和繁衍的能力,它并不需要依存人類而存在,相反地,是人類無法離開自然而獨立生存。依存自然的人類理應心懷感激,知恩圖報,而不是用現代技術設備的強悍逆天而行,以為“人定勝天”。
結 論
“生態文學對工業和科技的批評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工業和科技本身,而是要突顯人類現存的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致命缺陷,促使人類思考和探尋發展工業和科技的正確道路,以及如何開創一種全新的綠色工業和綠色科技。”[8]230人類傳統的勞動模式和新興的工業生產之間應該找到一種更好的平衡,讓人民在勞動中感受快樂,而不是被機器壓制得喘不過氣來。《德伯家的苔絲》激發了我們對自然源于內心的真摯情感,引導我們去探尋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能途徑,探討解決自然生態危機、社會生態危機與精神生態危機的辦法。哈代深切關注人與自然環境的生態關聯,對社會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哈代的生態觀里人物不應是人類生存活動的中心,而是一個組成部分,與自然環境相輔相成,共生共榮構成適應生存活動的生態體系。只有順應自然規律,對自然心懷敬畏人類才能獲得幸福,對自然悖逆漠視者最終只能消亡于世。
[1]王喜絨,等.生態批評視域下的中國當代文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聶珍釗,馬弦. 哈代研究文集[C].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3]托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絲[M].孫法理,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4]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于光遠,等譯.人民出版社,1984.
[5]魯樞元.文學與生態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6]恩斯特·卡西勒.盧梭問題[M].王春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7]亨利·梭羅.瓦爾登湖[M].田偉華,譯.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
[8]王諾.歐美生態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張燦邦]
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LIN Xiao-q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anming College, Sanming 365004, China)
Thomas Hardy with advance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lived in a heyday of Britai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one of his famous work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he not only described the fabulous natural scenery but also revealed the ecological crisis brought by commercial production. The thesis based on the burgeoning theory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to analyze the author's ecological se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 and anticipate that readers can resonate with Hardy, then harbor an awe to nature and try our best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ess; Eco-criticis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risis
I106
A
1008-9128(2016)04-0062-04
2015-10-31
福建省教育廳科研基金項目:托馬斯·哈代作品中的生態批評研究(JBS14158);三明學院科研發展基金項目(A201315/Q)
林曉青(1981-),女,福建三明人,講師,研究方向:外國文學研究。翠谷,前面是一片灰色的田野。”[3]48這前后色彩的過渡仿若昭示著苔絲從馬洛特村到川特里奇的遷移她的人生也將從青蔥懵懂走向灰暗慘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