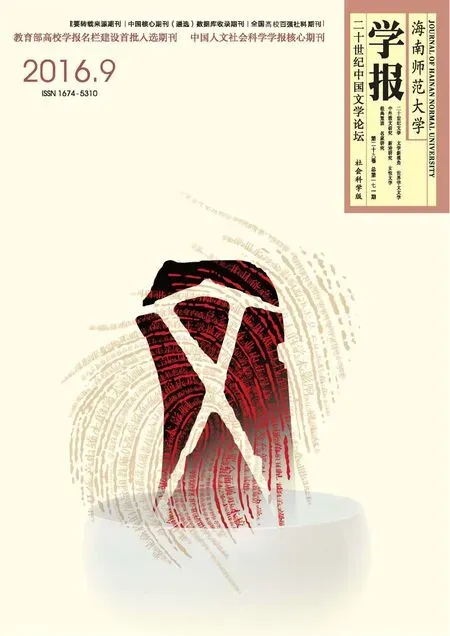家國同構:“中國夢”的民族精神認同基礎
王贈怡
(四川文理學院 美術學院, 四川 達州 635000;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 北京 100872 )
?
家國同構:“中國夢”的民族精神認同基礎
王贈怡
(四川文理學院 美術學院, 四川 達州 635000;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 北京 100872 )
“中國夢”不僅是整個民族的,而且也是每個個體的。“中國夢”能達成個體全面發展和民族偉大復興之間的有機統一,就在于“中國夢”作為執政理念本質上是中華民族在悠久傳統文化中所生成的集體精神認同的一種現代表達。這個傳統文化生成的集體精神認同就是家國同構思想,它是“中國夢”將個體發展和民族復興貫穿起來的理論基石。
中國夢;民族精神認同;家國同構
習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國夢”不僅“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只要我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斗,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我們每個人為實現自己夢想的努力就擁有廣闊的空間。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①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3月17日。習總書記的講話特別注重中國夢的主體即中華民族與每個中國人之間關系的處理,強調國家發展與個體人生出彩的一致性。這樣,“中國夢”就把至偉的民族振興和至微的個體追求置于了一個榮辱與共、相互依存的邏輯整體中,其深刻的哲學意味就在于:中國夢將民族復興的普遍性與個別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中國夢”之所以能把民族整體和具體個人統一起來就在于其作為執政理念深深地根植于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認同中,這種精神認同就是深植于我們每個中國人心里的“家國同構”意識。“家國同構”的形成有著悠遠而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它遠遠早于人類文明精神有重大突破的“軸心時代”,是在各民族的不斷融合中生成的。“中國民族初為炎黃二宗,始分終合,今并其名不存。于山東、江蘇求夷族,不可得也。于山西、陜西求戎狄,不可得也。同化既久,界畔早失,截至今日,已偉然薈為一族。”②王獻堂:《炎黃氏族文化考》,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第58頁。這“一族”就是中華民族。“家國同構”在民族的產生、民族國家的建構、國家的治理、民族國家的生存等問題的探索中不斷完善和強化,最終成為民族的精神信仰,這也是中國夢之所以能達成個體夢想和國家民族夢想統一的根本所在。“家國同構”能夠成為中國夢的精神認同基礎的合理性就體現在它的形成過程中。
一、族群社會的政治化衍變是“家國同構”的生成基礎
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群體社會的最突出文化表征就是有關“姓”、“氏”、“族”的身份認同體系出現。雖然血緣關系是群體社會以姓、氏、族作為組織形式的根本依據,但是這些組織形式所強調的內容又各有側重。如“姓強調的是血統,氏突出的地域,族彰顯的是武力”*張法:《中與中國審美關系的起源》,《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7期。。“姓”從血緣上標明了早期社會群體的親疏關系,具有恒常性。《春秋左傳·隱公八年》正義云:“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733頁。由于姓與生相關,它就意味著種的繁衍和血脈的延續,被賦予了永恒之義。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就是從“姓”繁衍不斷來理解“死而不朽”的,他說:“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雖然穆叔認為范宣子的說法是“世祿”而不是“不朽”的體現,但是穆叔客觀上也承認了“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的普遍性。不僅如此,同姓兄弟之間的情感關系也是人們衡量統治者人心向背的一條重要準則。如《左傳·昭公七年》“詩曰:‘即鳥鸰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不吊;況遠人,誰敢歸之?”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姓”就是“氏”“族”的不同稱謂而已。《春秋左傳·隱公八年》孔穎達正義云:“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髙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春秋左傳注疏·卷三》)與“姓”相比較,“氏”突出的是地域性,在遷徙流動中“氏”是“姓”分支衍變情況的文化表征。《春秋左傳·隱公八年》就有“胙之土而命之氏”之說,其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同也。”*阮元:《阮刻春秋左傳注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93-294頁。由此可見“氏”的源起與地域有緊密關系。當然“氏”的含義并不僅且而此,正義又云:“《禮記·大傳》云‘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733頁。從“子孫當別氏”看,“氏”是“姓”的分化延伸,用以區別子孫之所由出生。至于“族”,徐中舒《甲骨文詞典》云:“從方人從矢,方人所以標眾,眾所以殺敵。古代同一家族或氏族即為一戰斗單位,故方人矢會意為族。”*徐中舒:《甲骨文詞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第735頁。可見,族的最初產生與一個群落的安全防務相關,而其組織的劃分依據可能與血緣姻親或者地域相關。居于族內的人們往往會在生命財產方面得到保障而產生一種安全感、歸屬感,進而形成一種族群信仰。如《左傳·僖公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說法,就佐證了當時人們這種信仰的專一。氏與族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春秋左傳·隱公八年》正義認為氏與族是同一的,其差別在于“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為族”,并舉例說:“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舉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733頁。以姓、氏、族為基礎的氏族社會建立的目的大致表現為這樣幾方面:其一,族類之間的相互扶助;其二,相互保險;其三,同族的繁榮。同時基于這樣的目的又形成了一套倫理秩序:一是同祖者間血緣情感的喚醒,如我們對軒轅黃帝的祭拜就是通過共同的血脈深情喚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二是敬祖情感的激揚;三是依輩分、排行等世代順序和出生先后所形成的長幼之序;四是由長老掌控的人治、道德統治。*[日]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王瑞根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91頁。可以說氏族社會是國家形成的最初形式。如古文字學家唐瀾先生便認為“中”最初為氏族社會中的徽幟,它有著重要的功能作用:“蓋有大事,聚眾于曠地,是建中焉,群眾望見中而趨附。群眾來自四方,則建中之地為中央矣。列眾為陣,建中之酋長或貴族恒居中央,而群眾左之右之望見中之所在,即知為中央矣。”*李圃:《古文字詁林》第一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8頁。可見先民最早的國家觀念就是在氏族或者部落的“建中”之地發展而成的,而主宰國家的君王也是由居中央的酋長和貴族衍化過來的。
隨著氏族社會向階級國家的演變和確立,統治者逐漸把“姓、氏、族”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組織方式納入到國家管理中去,以至于成為了安邦定國的經營謀略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從現存的典籍看來,在帝堯的時期就注重家族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尚書·堯典》就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的主張。《詩經·大雅·板》“大宗維翰”、“宗子維城”等語亦表明了宗族在維護國家統治的重要作用。《左傳·文公二年》云:“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可見人們很清楚地意識到宗族對公室完成治理國家有非常重要的裨益作用。而與公族相對的異族,就被居統治地位的階層小心提防。《左傳·成公四年》就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由于統治階級認識到宗族關系到國家的生存安危,便自覺地參與到宗族的管理中;這種把宗族納入邦國建構的舉措事實上開啟了家國之間的貫通渠道。如《左傳·隱公八年》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所以“賜姓賜族”作為一種家族殊榮,并非人人可得。孔穎達正義云:“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髙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眾,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余人哉?’”(《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春秋左傳注疏·卷三》)這些以“姓、氏、族”作為組織社會的形式經過代表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的政治權力渲染之后,亦成為了家族榮耀的文化標志。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人們有意識地自覺收集整理姓氏的譜系,官方也積極參與姓氏譜系的編纂和修訂。宋人鄭樵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表述:“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將咨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后魏河南《官氏志》,此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氏錄》二百卷,路敬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鄭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氏族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頁。不過,政治因素介入也打破了主要以血緣為依據的早期社會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尚書·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從《堯典》可見,宗族以外的“百姓黎民”同樣重要。《尚書·泰誓(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章句上》亦引用了《泰誓》該語),把民意放到了天意的高度。《尚書·洪范》就如何進行公天下的“王道”提出了要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左傳·昭公三年》的“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已經從觀念上超越了血緣家族的狹隘,以更博大的胸懷思考國家了。《論語》提出的“仁”的思想已經把血緣之愛升華為普天下之愛。如《論語·述而》云:“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顏淵》甚至打破血緣小家的局限,提出了四海如一家的理想主義思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荀子那里,如何處理好與庶人的關系已經成為統治階級思考天下安危的首要問題了。《荀子·王制》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隨著大一統的天下觀念的牢固樹立,統治階級在選賢任能方面更加開放。如曹操“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紀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頁。的用人機制以及唐宋科舉制度的完善等等都對基于血緣宗族的門閥制度的削弱,宋代尤為突出:“‘士庶婚姻,浸成風俗’,即使后妃,也‘不欲選于貴戚’,最理想的倒是‘小官門戶’。……‘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在宋代蔚為風氣。那種依靠血親門第來維系其特權的貴族勢力,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王朝聞、鄧福星:《中國美術史·宋代卷(上)》,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頁。這就使人們在由家到國的認識上更具了廣泛性和普遍意義。當然最重要的是國家政權參加到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建構的舉措不但打開了最基本社會組織形式——家與最高的政權組織形式——國之間聯系的通道,而且使家族倫理(如尊尊、親親)與國家治理形成了內在的統一。如《禮記·大傳》云:“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材用足,材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后樂。”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家族倫理的政治化演繹路徑:基于血緣的家族、敬宗之愛是如何一步一步上升為國家百姓之愛,再由國家百姓之愛如何一環一環地轉化為有效治國方略的具體實踐。
二、治國與齊家在理念上的同質是家國同構的認識依據
家國同構思想的生成還體現在治國和齊家之道在本質上相通,齊家與否通常作為治國的前提和考量準則。以舜為例,《尚書·堯典》說舜的家庭“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而舜卻能與他們和諧相處,于是堯選用他作為繼承人,堯啟用舜的重要標準就是齊家。孔子亦贊嘆舜說:“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章句下》)如果家都不治,何談理國呢?!在《尚書·牧誓》里,周武王正是用這種家國同質的邏輯去聲討紂王的:“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那么,齊家何以能通向治國呢?那是因為齊家之法和治國之道在手段上同質:基于血緣的家之所以能與國這樣最高的政治組織關系之間形成內在的聯系,其要義就在于一個“親”字。《孟子·盡心章句上》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禮記·中庸》還把“親”作為君子的修身、知人和知天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這里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齊家與治國在手段上的同構:由親親人到泛愛天下之眾,也即是以事親之心對待天下百姓,恰如孟子所講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這種以親親之心事民的治國策略早在《尚書》已經很明確了。從《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看,天子之所以能君天下,就在于他能以父母之心關愛天下百姓。《左傳·昭公三年》同樣認識到以親親之心治國的重要性:“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與《洪范》“天子作民父母”句不同的是“愛之如父母”強調的是以子女之心敬奉天下,不過,無論是“作民父母”還是“愛之如父母”都是根源于“事親”的家庭倫理。而以“親”作為貫通家、國關系的邏輯實踐行為在本質上又最終表現為個人的倫理精神,那就是“孝”。因此,家國天下之重任實系于個人一身,在傳統文化中個體價值總是被要求貫穿于家國的統一體中。《尚書·伊訓》云:“立愛惟親,立敬為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孟子亦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章句上》)而考量個人對于家、國之本的價值意義則主要通過“親”、“孝”這樣的倫理精神體現出來。如《孝經·三才章》稱“孝”為“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孝經·圣治章》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經》的《天子章》、《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還從個人的不同身份諸如“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等維度闡述了“親”和“孝”對于家、國的建構方面所具有的社會實踐意義。如《天子章》就引孔子的話說:“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孝經》用了較多的篇幅肯定了“親親”與治國之間的必然聯系,把基于血緣親情之上的家族倫理之“孝”廣泛納入到國家秩序的宏大建構中,其把“孝”類化為“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舉措已經充分彰顯出家族倫理親情與國家建構之間的互文性意義:由狹隘的親親之愛、敬親之孝升華為百姓、國家之愛。這種典型思想還較豐富地體現于《孝經》其它篇章。如《廣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廣至德章》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正是由于這種貫穿于家國建構的倫理精神已經深植于中華民族的情懷中,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利用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思維方式把傳統中的孝治天下的倫理精神創造性地轉化為對人民的無私的愛。毛澤東同志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把黨對人民的這種深情提煉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鄧小平同志1981年在《鄧小平文集》序言中把黨對人民的這種情感凝煉為:“我榮幸地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而成為世界公民。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在鄧小平同志那里不僅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而且世界人民也是一個大家庭。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在常委見面會上的講話通過重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來體現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人民的深情愛戴。2014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級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公仆,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0月9日。2015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主旨演講中亦以中國古人為榜樣,把國家的治理納入到傳統家庭親情倫理的考量之中,總書記動情地說:“25年前,我在中國福建省寧德地區工作,我記住了中國古人的一句話:‘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至今,這句話依然在我心中。”*習近平:《攜手消除貧困,促進共同發展——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7日。有學者認為考察人們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狀況如何,不是看他們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多少范疇、原理,而是應看他們是否把握住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獨特的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和思維邏輯;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就是實踐的思維方式。*倪志安、楊志鵬:《“以實踐思維方式解讀中國夢戰略”的方法論意義》,《重慶郵電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我們黨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之所以能不斷超越自身的局限實現自我更新和自我升華,就在于能通過實踐的思維方式,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不斷探索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路徑。我們黨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正是通過實踐的思維方式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家族倫理創造性結合起來的結果。
從中華民族的演變史看,對于個體來說“家國同構”思想中的家、國不是兩個抽象的符號:一方面個體的實踐貫穿于家國的建構中,個體賦予了“家國同構”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個體只有在家、國的關系中才能彰顯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禮記·大學》云“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個體作為“人君”“人臣”“人子”“人父”以及“與國人交”的行為者,使家國成為了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統一體;同時個體價值、抱負施展的始基和依托正是家、國的存在,個體對象化的價值只有在家國統一體才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實現。因此,傳統文化總是把個體的價值成敗與否納入家國體系中進行考量,家的價值也同樣需要從國家的層面予以確認。恰如《禮記·大學》所講的“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故而,家國的興衰榮辱總是與個體生存發展休戚相關。習總書記之所以自信地說“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就是因為家國同構的民族心理意識的廣泛存在。“中國夢”也正是基于這一廣泛而深刻的民族精神認同,將民族復興的普遍性與個體發展的個別特殊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王贈怡:《論“中國夢”作為執政理念的美學化解讀的意義和表現》,《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8期。所以,“中國夢”的實現不僅從國家、民族的層面體現出來,亦從個體層面彰顯出來。不僅如此,國家、民族夢想的實現也最終訴諸于每個個體的躬身實踐。習總書記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夙愿。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內部戰爭,中國人民遭遇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真正是苦難深重、命運多舛。中國人民發自內心地擁護實現中國夢,因為中國夢首先是13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習近平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人民日報》2013年3月20日。當然與傳統家國同構語境中所強調的個體對家國的責任和義務相比較,“中國夢”特別注重突出國家對于實現個體價值的責任和義務,充分體現個體存在的豐富性和個別差異性,而不是簡單的以“類”的充分理由和口實去遮蔽個體享有的權利和尊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所以習總書記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實現人民幸福……全面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現有人掉隊。”*習近平:《攜手消除貧困,促進共同發展——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7日。
三、文人志士對“家國同構”的不斷抒寫強化了民族的精神認同
早在商周時期我們就有了“家國同構”的精神追求,這鮮明地體現在我們的典籍文化中。《詩經·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大雅·思齊》:“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小雅·桑扈》:“君子樂胥,家邦之屏”;《左傳·僖公十九年》引《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不僅如此,典籍中還流露出對國家生存狀況的一種憂患意識。如《大雅·桑柔》“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大雅·瞻卬》“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甚至還涉及到民意的考量及內部關系穩定的處理:《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大雅·民勞》“惠此中國,國無有殘”。在戰國末期的屈原、宋玉那里這種家國同構思想已經轉化成為中國文人矢志不渝的精神認同。屈原的“家國同構”情懷既見諸他那離鄉去國的悲愴情感中:“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九章·哀郢》);“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遠游》)。又見諸報國無門的絕望中:“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時之不當”(《離騷》);“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九章·哀郢》);“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九章·懷沙》)。背井離鄉的悲愴裹挾著報國無門的絕望真實地呈現了屈原內心深沉的家國憂患意識。“屈原的‘深固難徙’、‘受命不遷’、‘橫而不流’,絕不是出于‘潔身’,更不是出于‘泄憤’,而是出于他堅定不移的愛國思想和信念。”*董運庭:《楚辭與屈原辭再考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53頁。那么屈原的愛國思想基礎是什么呢?無疑是其“家國同構”情懷的深沉堅守,正所謂“深固難徙,更一志兮”(《橘頌》)。屈原在《離騷》開篇就用“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來呈現自己的家族世系,其目的就是要表明他與楚國血緣上的淵源關系,屈原對這種淵源關系的重視表明楚國對他來說家國是一體的,他所眷顧的“故鄉”、“舊鄉”大抵是關乎家、國的雙重喻指。屈原愛國思想之深切至今為中華民族所敬仰和謳歌。在宋玉那里我們同樣感受到其深沉的家國同構情懷:“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九辯》)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說屈原和宋玉文風“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其實屈原、宋玉特別是屈原對后代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他們的文風上,更主要地還體現在他們那種強烈的家國意識上。從《禮記·大學》可以清楚地看到家國同構觀念的實踐路徑如何在個人那里得以實現:“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隨著漢代《禮》的經學地位的確立,家國同構思想就演變成為了民族精神普遍認同,個體生存與家國盛衰休戚與共,興家立國也成為歷代中國文人的共同追求,這種情感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的演進中愈來愈得到強化,我們從歷代文人志士的詩歌創作中就可以見證到這種濃烈而深沉的情懷:六朝江淹《薦豆呈毛血歌辭》“愿靈之降,祚家佑國”;唐代劉商《金井歌》“贍國肥家在仁義”;元稹《遣興十首》“理國如理家”,杜牧《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樽前豈解愁家國”,呂巖《贈劉方處士》“悠悠憂家復憂國”;宋代邵雍《家國吟》“邪正異心,家國同體”,馮時行《和王祖文》“憂國憂家連夢寐”,李處權《賀雨》“憂國如家愿年豐”,趙蕃《宜春道中贈邢公昭二首》“問君家在離騷國”,洪咨夔《送興元聶帥》“憂國如憂家”;元代侯善淵《滿庭芳·太古真風》“修家國,臣忠子孝,民業自安淳”,謝應芳《題杜拾遺像》“國破家何在”;明代瞿佑《旅舍書事》“平生家國縈懷抱,濕盡青山總淚痕”,韓邦靖《感事》“便因家國淚橫流”,邢侗《送方胥成之薊門塞》“紛紛家國堪垂涕”;近現代譚嗣同《戊戌入都別友人》“家國兩愁絕”,梁啟超《澳亞歸舟雜興》“姹女不知家國恨”,秋瑾《七律》“如許傷心家國恨”,宋教仁《晚泊梁子湖》“家國嗟何在”,郁達夫《秋興》“須知國破家何在,豈有舟沉櫓獨浮”。上述諸例表明,家國同構思想正是在無數文人志士的不斷抒寫中得到強化,并升華成為民族普遍的精神信仰和心靈家園。
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投入到了慘烈的民族救亡運動中,“家國同構”的民族精神信仰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在求得民族獨立的抗爭中同仇敵愾、前赴后繼。這一時期最能體現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的就是《保衛黃河》這首抗日救亡之歌了,尤以“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之詞最能震撼人心,其要害就在它喚起了我們深沉的民族情操——“家國同構”。從上古到近現代,“家國同構”思想是我們民族能夠生生不已、繁榮昌盛的精神法寶。所以習總書記說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15篇講話系統闡述“中國夢”》(2013年6月1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619/c40531-21891787-3.html。正因為中國人有“家國同構”思想的普遍認同,所以每當中華民族到了危機的時刻,這種根深蒂固的民族信仰就會自覺轉化為浩浩湯湯的精神洪流,激勵仁人志士投入到民族自救的實踐抗爭中去。這種精神信仰我們今天可以通過另外一種民族現象感受出來,那就是最盛大的傳統節日春節了。每年春節期間數以億計的中國人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回家,短短幾天的合家團聚折射的卻是中國人的那種強烈的親情之愛和濃烈而溫馨的鄉戀,正是這種信念構成了愛國主義的基石和民族偉大復興的凝聚力。有了它,我們就形成了由家到國的情感升化,這也是習總書記“中國夢”特別強調個體夢想價值的根源所在。“家國同構”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生存和發展中積累下來的最為寶貴精神財富,它依然是我們今天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精神法寶。一個外國學者把中國的社會主義稱之為“禮治”的社會主義:“突破宗族框架的國家規模的禮治社會,構成其物質基礎的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礎上依賴‘大公無私’的公有性而實現的重工業化,以及支撐這些新社會關系的男女平等、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交通、通訊網絡等等,總而言之,這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正是在這些現代化成果的基礎上才有了1987年以后的改革開放,也就是對‘私有性營利’活動的開放。”*[日]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王瑞根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91頁。從其描述看,我們說這種“禮治”的社會主義正是我們黨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家國同構”政治理念所做的現代轉換,這對社會主義的初期建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們今天迫切要做的就是如何把“家國同構”的傳統思想和當前中國深化改革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以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思維方式形成富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理念,而“中國夢”正是適應這一需求而生的經典范例。習總書記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03月17日。“中國夢”之所以能將國家的夢想和中國每位老百姓的個體夢想統一起來,就在于“家國同構”根植于每位中國人的心靈中。想起佛法大師慧能有一句經典的話:“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尋菩提,恰如覓兔角。”(《壇經》)同樣我們政治的現代性也萬萬不可離開文化母體的支撐。習近平同志說:“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可見習總書記以“中國夢”作為執政理念的舉措實際上就是為中國政治現代性建構提供了一個富有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國模式。
四、結 語
上述分析表明“家國同構”是無數仁人志士幾千年來為圖謀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而探索出來的經驗總結和精神認同,其關鍵在于將個體的價值訴求與國家建構置于一種互生共榮的互為因果的統一體中,它給我們呈現出了一幅理想的政治美學圖景。構建于“家國同構”的民族認同基礎上的“中國夢”,勢必讓每位中國人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個體全面發展的多重福祉中充分享受政治美學所帶來的生存愉悅。
(責任編輯:王學振)
Homogeneity of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the Basis of Recognition for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Dream
WANG Zeng-yi
(SchoolofFineArts,Sichu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Dazhou635000,China;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he Chinese Dream” involves not only the entire nation but also individuals. The reason for the Chinese Dream to make an organic unity between individual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es in its giving a modern expression to the collective spirit recognition formed in the l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governing idea. The collective spirit recognition refers to the view that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 are homogeneous, which is a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connect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i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hinese Dream; collective spirit recognition; homogeneity of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
四川省教育廳2015年重點項目 “‘中國夢’美學化解讀的意義研究”(項目編號:15SA0107)
2016-05-11
王贈怡(1972-),男,四川平昌人,四川文理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美學、藝術美學。
B83-02
A
1674-5310(2016)-09-0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