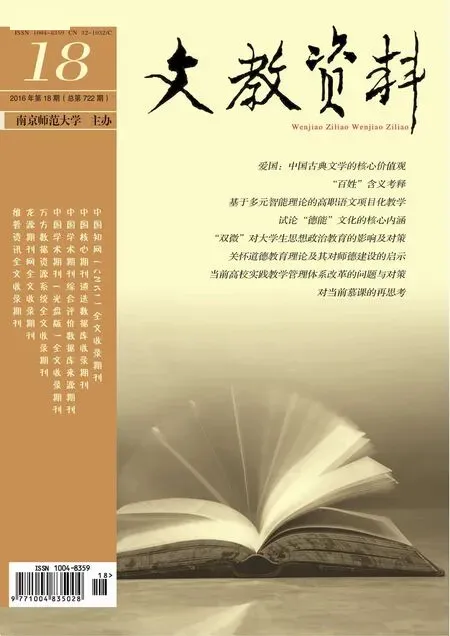敦煌置傘文研究
陳元俊
(陜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敦煌置傘文研究
陳元俊
(陜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陜西 西安710119)
在敦煌發現的文獻中,《置傘文》記載了這一時期敦煌全城官員、百姓和僧侶舉行置傘祈福活動。《置傘文》在吐蕃時期大量流行,到歸義軍時期則很少,同時其內容體例發生一些變化,隨之其主旨內涵較吐蕃時期逐漸淡化,置傘活動在此時更多的是流于形式。置傘活動是在敦煌權貴勢力包括佛教界與吐蕃的合作下產生的,對吐蕃加強對敦煌的統治、安定民心、促進吐蕃與敦煌佛教勢力間的關系有重要的影響。
敦煌佛教置傘活動加強統治
敦煌地處甘肅河西走廊的西端,是絲綢之路的咽喉,溝通西域。自佛教從印度、經西域由敦煌東傳到中原,敦煌就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歷漢唐而成為古代佛教昌盛之地。隋唐時期,國力強盛,有力地促進佛教的發展,敦煌佛教在這一時期更繁榮。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由盛轉衰,因而無力控制河西。吐蕃乘機侵吞河西地區,于建中二年(781)占領了敦煌,到848年張議潮起義的67年間敦煌的歷史被深深地打上吐蕃印記。本地佛事活動中的重要道具白傘蓋及“置傘文”亦承載種種異域特征①。
一、白傘蓋及其功用
經學者考訂,《置傘文》中的傘指白傘蓋,這個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可,所以展開《置傘文》前,要弄清傘蓋的功用含義、儀軌及當時的供養方式。唐代敦煌地區,密宗一直盛行不衰,吐蕃統治時期依然如故,同時大量《白傘蓋經》的流行傳抄說明白傘蓋佛在敦煌一直很盛行,實施白傘蓋儀軌,能滿足諸愿,護佑一方。除對個人功效外,將其安置于寶幢頂上供養,再置于大城門上、城中、村落中等處,能保佑國家和地方的安寧,平息各種疫病、戰爭等各種災難②。白傘蓋的信持方式是持手印、念咒語。白傘蓋的功用在《白傘蓋經》中云:“此如來頂髻白傘蓋余無能敵大回遮母,能滅一切魔鬼,能斷除他者之明咒,能回遮非時之死亡,使一切有情從束縛中得解脫,回遮兇狠和一切噩夢。能摧毀八萬四千妖魔,令二十八星宿歡悅,摧毀八大星曜,回遮一切怨敵,從猛厲恐怖的噩夢,及毒、兵器、火、水的災難中解脫。”③白傘蓋稱白傘蓋佛母、白傘蓋佛頂,安置寶幢來供養,以表達誠敬皈命之意。而白傘蓋佛頂輪王持傘,表示覆蓋保護一切有情之意。幢是作為驅除魔鬼的用具,《置傘文》記載,敦煌舉行置傘活動,主要是認為有魔鬼作亂;“因行城將殄于妖氛”、“恐妖氛肆惡于城中”④,才引起災禍的,所以驅魔顯得比較重要,這是置幢多的原因。寶幢來源于寶幢佛,寶幢佛持蓮花合掌手印。寶幢除莊嚴道場外,還有降伏魔鬼、保平安之意。幡,與幢同為莊嚴用具,用以象征佛、菩薩的威德。所以在置傘的時候也要置幡。
二、《置傘文》體例
吐蕃占領河西時期,佛教在吐蕃已占據主導地位,并處于“前弘期”。由于吐蕃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扶持及吐蕃文化同漢文化的交流融合,促使敦煌佛教得到迅猛發展:民間信徒劇增,各種佛事活動也隨之更興盛。這在敦煌出土的文獻中多有記載除佛經等正典外,主要包括大量齋愿文、寫經題記、碑銘贊、變文、牒狀等。“齋愿”類目下“置傘文”記載的是敦煌全城官吏百姓僧侶舉行置傘祈福活動。本文以黃征、吳偉合作編校的《敦煌愿文集》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對《置傘文》的內容、置傘活動產生的緣由、主旨內涵及歸義軍時期的變化作一考察。《置傘文》的全貌,主要以S2146NO.10、B2854NO.7兩篇展現。頁數.70S2146,存文12篇,此為第10篇。另有S4544與S2146相同。B2854,存文17篇,此為第7篇,標題為原有。因其內容體例基本相同,則全歸為《置傘文》下。學者通過從官名等方面的考察認為,S2146屬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所作,B2854NO.7歸義軍時期所作。
《置傘文》文體結構分為三部分;開頭部分稱為“號頭”。在唐宋佛事活動道場文的開端部分,俗語又稱開場白。《置傘文》的號頭則告訴世人除災集福的最好方法,是置傘供養白傘蓋佛頂,并要念誦經文舉行并參加置傘活動。中間部分則記載舉行置傘活動的時間、組織者、參與者、置傘緣由、傘的規模數量(包括置傘地點)等內容。最后部分記載的是祝福。中間和最后部分作為《置傘文》的主要內容,因而對置傘活動的具體內容及其祝福進行詳細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置傘活動的主旨內涵及其特殊的社會背景。現以吐蕃時期的《置傘文》為例,對置傘活動進行詳細研究。
置傘活動舉行的時間,在每年的“三陽令月”、“蟄戶將開”、“和風物動”、“春陽令月”、“三春令月,四序初辰”、“三春令月,四序初分”⑤等時節,更多的是在“三陽令月”和“三春令月”這兩個時間,“三陽”指春天,也指正月,“三春”指春天,和“三陽”都表示新的一年的開始,“令月”指的是吉月。就是選擇正月這個吉月進行置傘活動,祈求新的一年風調雨順、安定平和等,滿足人們對新的一年的期望。置傘地點則選擇在“敦煌之府內、四門(外)”、“內豎白法之勝幢,外設佛頂與四門”⑥,數量為“白撞五所”,傘一般為“白幢”或“白法之勝幢”。這就和前文提到的白傘蓋儀軌方式一樣,將佛頂安置于寶幢頂上供養,然后置于城門上、宮宅中,就能保佑國家和地方的安寧,平息各種疫病、戰爭等各種災難。
置傘活動是在節兒及都督的主持帶領下舉行,節兒、都督為敦煌地區職位較高的官職,其上有節度使,節兒、都督則是敦煌的兩位蕃、漢副貳。在置傘活動中有節兒和都督帶領舉行,從中可以看出置傘活動的重要性和受重視程度。
置傘的緣由,是因為當時敦煌不但要面臨各種天災,尤其是“恐疾流行”、“妖氛”這類流行疾病的傳播,“霜雹之災”對莊稼的破壞,還要面對戰爭及盜賊的破壞掠奪。面對天災人禍,人們舉行佛事活動,希望得到保佑,免于各種災難的侵擾。
最后進行祝福;國家君王“寶位恒昌,天長地久”或者“寶位永固”。官僚階層“為霜為雨,濟枯旱于明朝”、“惟清惟直”。而平民階層則是“勝愿享,福長空”、“五谷登,百殃除,萬祥集”。可以看出不同的階層,祝福內容也有明顯的差別,但都滿足了各個階層的需求。這樣的祝福層次是《二月八日文》、《行城文》、《結壇文》等佛教禮儀愿文中固定的莊嚴層次。
三、歸義軍時期的變化
吐蕃時期,《置傘文》在體例內容、祝福上大致一樣,但到了歸義軍時期,則有一些明顯的變化。
首先,置傘活動在吐蕃時期由“節兒尚論及都督杜公等”主持、資助,到歸義軍時期顯示為“釋門僧正和尚爰及郡首、都督、刺史等奉為當今大中皇帝建茲弘業也”。吐蕃支持置傘活動并讓地方高級官吏資助和主持,表示對佛教的支持和對敦煌百姓的關懷。而到歸義軍時期,則由僧官和其他高級官吏奉唐朝皇帝的旨意去置傘,吐蕃時期對敦煌百姓的關懷在此時變為唐朝皇帝對敦煌百姓的關懷。這就可以看出置傘活動在不同時期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宣揚統治者的恩德。
其次,置傘活動的祝福對象、內容也發生變化。吐蕃時期祝福層次先是吐蕃贊普,然后是各級官吏,最后是整體祝福。到歸義軍時期變為先祝福唐朝皇帝,接著是整體祝福。對皇帝祝福的意思和吐蕃時期大致一樣。但不同的是祝福中沒有對各級官吏的祝福,只是在祝福皇帝時提到“魚水同心,君臣合運”。這樣的祝福層次,一方面是符合上下尊卑關系,另一方面能滿足統治者加強其權威的需要。
最后,從《置傘文》可以看到敦煌佛教界立場的變化。吐蕃時期的記錄為:“時則有我節兒尚論及都督杜公等我圣神贊普,唯愿圣躬堅遠,日往月來。”可以看出,此時敦煌佛教界已承認吐蕃統治的合法地位。到歸義軍時期變為“則我釋門僧正和尚爰及郡首、都督、刺史等奉為當今大中皇帝建茲弘業也”,此時敦煌佛教界的態度則又倒向李唐。這除了文體格式的需要外,更多的是敦煌佛教界在不同時期與占領敦煌的政權合作,是其生存發展必然的選擇,同時為占領敦煌的政權及君王服務是其職責所在。
《置傘文》從吐蕃到歸義軍時期,其形式體例內容等發生一定的變化,但更大的變化則呈現在其主旨內涵方面。吐蕃時期舉行置傘活動,其目的是祈求消災除難、延壽集福、五谷豐登、海內澄清,君主寶位永固等。其內涵是傳播君王的權威、教化人民、平息各種矛盾、使人民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到歸義軍時期則更多的是出于形式。置傘活動聯合拉攏敦煌佛教界和其他大家勢力地作用在此時則淡化甚至消除了。敦煌佛教界也需要歸義軍的保護,所以此時統治階層不需要強力的拉攏敦煌佛教界。此時,置傘作為一種佛事活動,成為寺院和僧侶的分內之事,由寺院資助、僧侶主持進行也是理所當然的。敦煌遠離中原,又被吐蕃占領67年,所以在舉行這種活動的過程中,向唐王朝表示忠心是必然的。但是其祈求消災除難、延壽集福、君主寶位永固的目的和傳播君王的權威、教化人民、平息各種矛盾、使人民獲得精神上的慰藉等內涵開始逐漸淡化。
注釋:
①杜斗城.河西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341.
②才讓.敦煌藏文密宗經典《白傘蓋經》初探.《敦煌學輯刊》2008:1.
③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38.
④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岳麓書社,1995.11:453.
⑤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岳麓書社,1995.11:451,455,457.
⑥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岳麓書社,1995.11:452.
[1]李錦繡.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3,第1版.
[2]杜斗城.河西參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2,第1版.
[3]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岳麓書社,1995.11.
[4]李覺正.佛教百科全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
[5]李德龍.敦煌文獻與佛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5(1).